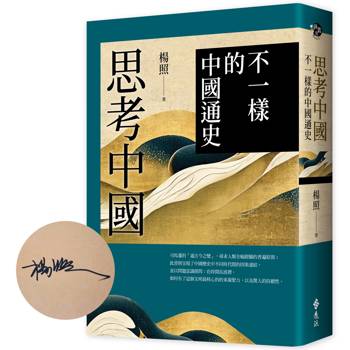前言
「通史」的精神與價值
1
這是一部講述「中國通史」的書。開始之前,要先對於「通史」這個名詞、概念稍加說明。
「通史」這個詞在中文裡極為平常,但如果換到西方文明脈絡中,可就沒有那麼理所當然。在中國傳統裡,「通史」有特殊來歷,因而取得了明確的意義,以及明確的知識地位。
「通史」來自太史公司馬遷及其《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自序〉,解釋這本著作的來源。〈太史公自序〉文章有兩個重點,一個是鋪陳司馬家的淵源。司馬家從周初一直到漢代都是負責掌管歷史的,一代又一代累積了豐富的歷史知識與歷史見解,繼承「世代典史」的家業,司馬遷欲將近千年傳留的知識整理出來,視為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
第二項重點則在於陳述了這部書和儒家信念間的密切關係。司馬遷的史學使命感傳自父親司馬談,而司馬談在立場上很明顯傾向道家,兒子司馬遷卻以儒家孔子為他最尊崇、仿效的對象。
儒家最重視「禮」。「禮」是人與人之間的正確對應行為。人與人交往、互動,自然會有規範,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會都必定有,然而孔子從這樣的行為規範中建立起理論來。
這是孔子的野心,也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在孔子之前,周代封建制度早已有了一套、甚至很多套繁複的規範,大家都要遵守,如此來建構、保障社會秩序。但孔子主張要扣問、探索「禮之本」,也就是不只要遵守固定的禮節,更應該要了解禮節為什麼如此規定的道理。孔子的信念,後來形成了儒家普遍的哲學態度,那就是:「禮」背後必有「理」,所以人活在世上,在人際間過日子,就不能只學表面的、行為層次的「禮」,應該要而且一定要理解深層的、普遍的「理」。
從孔子到孟子,這方面的關懷一脈相承。孟子的論理一般被描述為「性善論」,這意思是孟子相信每個人在本性上、在骨子裡都是好人?那不是有點太天真了嗎?
孟子的「性善」有更深刻的用意,指向要解釋人間社會為何出現了「禮」,而這種人與人相處的規範又為什麼能帶來讓大家都安心、舒服的秩序。孟子將解釋的根源放在人的本性上。
孟子最精彩的論辯之一,就是推演葬禮的起源。周代封建禮制中,葬禮極為重要,《儀禮》、《禮記》記載了多少關於葬禮的規定與討論。而孟子卻以一種推倒繁瑣細節的氣魄,描述了想像中的原始場景。沒有葬禮之前,有人的父母死了,屍體就丟在溝邊,他經過時就目睹了屍體上開始腐爛、長出了蟲,或是被動物啃食了。看到那樣的畫面,他很自然地額頭上冒出汗來,沒有人教他,更沒有人規定他,他一動念,就趕回家拿了工具,急急地在土裡挖出一個坑洞,將屍體埋了進去,才有辦法安心。
這就是葬禮的起源,源自於人要求自己安心,完全來自人的本性。人有這種自然的要求,禮來自人的本性,禮帶給人秩序安定,禮是好的善的,那麼人的本性必然也是好的善的。這是孟子「性善論」真正的依據。
如果人性是惡的,是反秩序的,那怎麼會有禮的秩序?換句話說,「性善論」主張倫理、社會秩序來自人的天性,因此才是確切、不可動搖的。
這和歷史有什麼關係?我們真的不該忽略司馬遷清楚的儒家本位。要如何顯示並證明孔子、孟子對於「禮」與「理」的解釋是正確的,最堅實也最徹底的一種方式,就是去整理歷史,從曾經出現過的人與事中找出律則,那就是人性在社會事務上的影響與表現。
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這個「通」字,指的是囊括人類行為的所有現象,從中找到的普遍原則,構成了誰都無法推翻的一份真理。
2
一般從哲學的角度討論孟子的「性善論」,常出現簡單的質疑推理─找出你所知道、確切存在過的一個壞人,最壞的人,然後問:「如果人性本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從他身上找不到任何一點善,不是所有人都有善良的本性,那麼孟子的道理就被推翻了。
在某個意義上,司馬遷更認真、更全面地應對這個推論。真要了解什麼是人的本性通則,就應該回到歷史,將古往今來所有人做過的事都集合在一起,從中整理歸納。這樣的整理歸納必須在人類全幅經驗的層次上才能達成目的。
在我解讀《史記》的專書《史記的讀法》中,一開頭就提醒讀者:很多人在《史記》裡讀到了好看的故事,但一來《史記》不只有好看的故事,二來光挑出好看的故事看,就錯失了司馬遷不惜以生死代價寫這部書的用心。
我們要尊重司馬遷的主觀意圖。他的野心是統合所知的人類經驗,找出其中的「古今之變」的通則。如果和西方古希臘的史學立場相比,我們或許更能體會這份野心的非凡意義。
表現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 384-322 BC)的《詩學》(De Poetica)中,古希臘人的價值信念認定:詩比歷史重要,甚至兩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對等,不能相提並論。詩探觸普遍與永恆,提煉人的行為與情感,將瑣碎、平庸與偶然篩洗掉,萃取出內在的純粹;詩的美來自那份純粹,詩的意義在於呈現超越特定時空性的真相。
對古希臘人來說,歷史相對地只是材料,保留了個別事件,必須經由哲學或詩予以加工淬鍊,才能形成真理與真相。要有歷史,歷史不可或缺,因為哲學與詩、真理與真相無法憑空獲致,但在知識的層級上,歷史明顯低於哲學與詩。
但司馬遷凸顯並強調了「通」,讓中國的史學精神和古希臘的觀念大不相同。「通」就是普遍原則,但這原則是扎扎實實來自具體的過去經驗,是在盡量蒐羅所有已知經驗、整理消化後才有可能得到。要找的是普遍的原則,所以如果在人類經驗中發現了不符合的例證,我們就必須持續修正原本的原則,直到形成真正的「通」。
《史記》開始於「五帝本紀」,那是司馬遷能夠追溯最古遠的歷史,等於是有記錄、能知道的人類經驗的開端;而《史記》的結尾呢?在時間上一直往下到司馬遷自己的時代。他當然知道人類經驗還會有未來,但那是他無從得知的了,他就推到自己所能知道的最晚近時代。這意謂著《史記》的時間範圍徹上徹下,盡可能完整涵蓋,唯有如此,才能從中得到「通」,才是「通史」。
司馬遷這種求「通」的歷史態度,仍然給予我們在學習歷史知識時很大的刺激與啟發。當然如果依照那樣的「通」的標準,以全人類經驗為範圍,那今天要講的就不會是「中國通史」了,這樣的「通史」只能是、必須是「世界通史」或「人類通史」。
3
說到「人類通史」,可能就有人想到一部國際暢銷書,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寫的《人類大歷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那部書的主體是Homo sapiens,現代智人,為這個人種的變化發展,寫了一部上下兩百萬年的歷史。這其實是最符合司馬遷的「通史」精神,足以代表「通史」精神在現代實踐的一部著作。
我們可以藉由比對《史記》與《人類大歷史》,進一步掌握「通史」的追求與意義。
哈拉瑞的《人類大歷史》以Homo sapiens(智人)這個人種為對象,牽涉到物種觀念,也就牽涉到了演化過程。四十六億年前地球形成,大約三十九億年前出現最早的生命現象,經過了漫長的演化,地球上有了愈來愈多的物種,目前科學實證發現登錄的大約有一百六十萬種,不過推斷物種總體的數量可能到達一千萬左右。
而不論幾十億年間地球上究竟有過多少物種,有一項驚人的事實再明確不過,那就是這中間有一個分布最廣的物種,幾乎完全不受各種環境條件限制,到哪裡都活得下去,到哪裡都有。這個物種就是Homo sapiens,我們現代「智人」。其他物種都有適合生存的環境,亞熱帶臺灣的螞蟻被搬到寒帶挪威就存活不了,卻只有大約兩百萬年前從原有非洲環境中出走的物種Homo sapiens,成了唯一的例外。
現代「智人」布滿整個地球。人類憑什麼可以擺脫環境的限制,甚至人類還將整個地球都改變了?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了極具說服力的洞見─因為人類在演化的過程中得到了一項最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學習。
透過學習,人類可以不斷地自我改造,依照道金斯的看法,甚至人類也就因此走到了自然演化的終點。意思是:原本自然生物演化的方式,已經遠遠追趕不上人類藉由學習所產生的適應環境能力,人類現在甚至都取得了徹底改造環境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環境條件壓力下,以緩慢的速度,如未來二、三十萬年後我們的手變成了不同形狀,多了或少了手指指節什麼的。在那樣的演化發生前,人類早就藉由製造出的工具,更有效地應付了環境所帶來的挑戰與考驗。
從這樣的物種特性出發,我們不意外地在《人類大歷史》書中看到一個清楚的主題,那就是人的多樣性。現代智人能夠學習、模仿其他動物,找到適應不同環境的策略,意謂著分散到不同環境的人,就發展出不同的特性。於是從整理這個物種的歷史來看,得到的不再是人的共通性,而是人的分歧異質可能。
這看起來好像和司馬遷藉「通史」要尋求普遍原則的用心剛好相反,事實上卻是提醒我們看到,「通史」因為是透過整理實際的人類經驗,不同於抽象推論,只要蒐羅整理的人類經驗夠廣、夠多,最終總是會凸顯出多元多樣的性質。
4
司馬遷整理人類經驗,是為了要得知「人的共通性」,而他在《史記》裡給了我們什麼樣的答案?
放在〈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叔齊」,放在〈世家〉第一篇是「吳太伯」,而這兩篇就有著微妙的共同性─他們都具備人倫秩序中最高貴的性質,那就是「讓」。伯夷要將王位讓給弟弟叔齊,吳太伯要將王位讓給弟弟季歷和季歷的兒子文王。他們所面對的都是極高的權力,安穩又有地位可享受的生活,不只不必費吹灰之力去追求,而且還是理所當然地降臨在自己身上。他們都是具備合法身分的嫡長子,在制度中保障了他們的繼承權。
然而他們都拒絕了,因為他們有更高的信念與考量。伯夷知道弟弟叔齊比自己更適合當孤竹國的國君,太伯知道父親心中更屬意弟弟來接位,他們還為了放棄自己原有的權利,等於自我流放,離國遠去。而在伯夷的故事中又再增添了一段,他要「讓」的對象弟弟叔齊,和他同樣選擇了「讓」,無論如何都不願當國君,寧可陪哥哥一起離去,兩人最終餓死在首陽山。
更廣泛些看,他們都是重視自我內在是非原則、遠遠超過現實考量的人。所以伯夷、叔齊無法認同周武王起兵伐紂「以暴易暴」的做法,儘管歷史上早有共識定論,推崇武王「解民倒懸」的戰爭是正義的,但司馬遷寫歷史,卻藉著記錄伯夷叔齊的故事,彰顯了另外一種很不一樣的評斷態度。
如果換一個方向延伸,我們另外看到的是人的高度自尊。即使對方是父親,即使牽涉的是自己未來一生的地位與財富,像太伯這樣的人,他的自尊心使得他無法在察覺父親認定弟弟比他適合當國君的情況下,去行使自己嫡長子的身分特權。他知道如果自主選擇,父親會選弟弟而不是選他,所以他成全父親的這份意願。
這種人在我們的現實環境中,至少就絕對不會捲入MeToo性騷擾的風波中。因為他們會立即、敏銳地察知別人的不情願、甚至厭惡,他的自尊立刻會讓他避開可能產生的騷擾。君子的操守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內在高度自尊,而司馬遷的「通史」要記錄的,就是人性的寬廣多樣光譜,從最高貴的那端開始,一直到最卑下、最黑暗的,都能在《史記》中找到。
這樣的「通」並不是以中國或華夏為範圍,毋寧是要整理、呈現司馬遷所知道的人類全幅經驗。各種思想、感情、動機、行為……光譜的全部構成了人類歷史,也才是我們應該認識的人類完整面貌。
5
理解中國通史,一層重要的意義是從人類多樣性中來的。這一片區域曾經有過的歷史非常獨特,出現了具備高度連續性的特殊文明。這文明早從一開始,就建立了「華夏」和「蠻夷」區別的自覺,這份存在、持續超過三千年的自覺,構成了集體認同、集體意識,決定並範限了這個區域的人們生活變化的可能性。
從比較文明的角度看,幾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文明有著如此長遠且強烈的社會規範性。因而我們不得不好奇地探問: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獨特文明?現代智人在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學習能力才能夠適應不同環境,散布到地球各個地方,相應不同地理條件而產生了幾千個、甚至幾萬個規模大大小小、歷時長長短短的文明。如果以對於文明內部成員的形塑強度與延續性標準衡量,中國文明在其中必定名列前茅。
學習得到了中國文化的種種內容,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樣的內容對人類的影響很深、很牢靠,不容易擺脫,不會輕易褪色。我們今天處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強弩之末狀態,大部分的人已經很少感知中國文化的作用。然而,例如當身處在一個有著明式桌椅家具、牆上掛著書法作品的空間裡,我們不會覺得陌生,我們的身體與感官會很自然地配合、適應那個空間,表示在我們的身體裡確實存在著某種中國文化基因,那基因仍然在作用著。
這是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只不過今天的狀況是,有些人意識到這件事時視之為負擔,有些人則視之為值得珍惜的資產。不管採取哪種態度,我認為且主張我們都應該承認這事實,並且弄清楚:如此強悍、長期的中華文化約束力究竟如何來的,又如何不斷發揮作用。
我之前寫過一套十三冊的《不一樣的中國史》,篇幅較大,可以在特定時代中另外展開橫向多角度的描述與討論。而這次重新講述、撰寫「通史」,會更聚焦在縱向變化上,也就是呈現中國歷史中不同時代前後彼此間的因果連結。而建立這項因果鏈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是對歷史內容進行檢核、選取的主要標準,即:在時間長流裡,如何有了這個文明最核心的約束凝聚力,以及更驚人的持續性質。
另外,十三冊本的《不一樣的中國史》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路講述到辛亥革命,與司馬遷的「通史」概念比較,顯然缺漏了從民國建立(一九一二年)到當前現今的一百年。那一套書停在辛亥革命的理由我多次說明過了,這次相對篇幅短小,對於史料探究到史事陳述的要求降低了許多,因而我得以一鼓作氣,會將歷史觀照,一直推進到現今,以求對得起「通史」之稱,也對得起司馬遷提出的宏偉架構。
「通史」的精神與價值
1
這是一部講述「中國通史」的書。開始之前,要先對於「通史」這個名詞、概念稍加說明。
「通史」這個詞在中文裡極為平常,但如果換到西方文明脈絡中,可就沒有那麼理所當然。在中國傳統裡,「通史」有特殊來歷,因而取得了明確的意義,以及明確的知識地位。
「通史」來自太史公司馬遷及其《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自序〉,解釋這本著作的來源。〈太史公自序〉文章有兩個重點,一個是鋪陳司馬家的淵源。司馬家從周初一直到漢代都是負責掌管歷史的,一代又一代累積了豐富的歷史知識與歷史見解,繼承「世代典史」的家業,司馬遷欲將近千年傳留的知識整理出來,視為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
第二項重點則在於陳述了這部書和儒家信念間的密切關係。司馬遷的史學使命感傳自父親司馬談,而司馬談在立場上很明顯傾向道家,兒子司馬遷卻以儒家孔子為他最尊崇、仿效的對象。
儒家最重視「禮」。「禮」是人與人之間的正確對應行為。人與人交往、互動,自然會有規範,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會都必定有,然而孔子從這樣的行為規範中建立起理論來。
這是孔子的野心,也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在孔子之前,周代封建制度早已有了一套、甚至很多套繁複的規範,大家都要遵守,如此來建構、保障社會秩序。但孔子主張要扣問、探索「禮之本」,也就是不只要遵守固定的禮節,更應該要了解禮節為什麼如此規定的道理。孔子的信念,後來形成了儒家普遍的哲學態度,那就是:「禮」背後必有「理」,所以人活在世上,在人際間過日子,就不能只學表面的、行為層次的「禮」,應該要而且一定要理解深層的、普遍的「理」。
從孔子到孟子,這方面的關懷一脈相承。孟子的論理一般被描述為「性善論」,這意思是孟子相信每個人在本性上、在骨子裡都是好人?那不是有點太天真了嗎?
孟子的「性善」有更深刻的用意,指向要解釋人間社會為何出現了「禮」,而這種人與人相處的規範又為什麼能帶來讓大家都安心、舒服的秩序。孟子將解釋的根源放在人的本性上。
孟子最精彩的論辯之一,就是推演葬禮的起源。周代封建禮制中,葬禮極為重要,《儀禮》、《禮記》記載了多少關於葬禮的規定與討論。而孟子卻以一種推倒繁瑣細節的氣魄,描述了想像中的原始場景。沒有葬禮之前,有人的父母死了,屍體就丟在溝邊,他經過時就目睹了屍體上開始腐爛、長出了蟲,或是被動物啃食了。看到那樣的畫面,他很自然地額頭上冒出汗來,沒有人教他,更沒有人規定他,他一動念,就趕回家拿了工具,急急地在土裡挖出一個坑洞,將屍體埋了進去,才有辦法安心。
這就是葬禮的起源,源自於人要求自己安心,完全來自人的本性。人有這種自然的要求,禮來自人的本性,禮帶給人秩序安定,禮是好的善的,那麼人的本性必然也是好的善的。這是孟子「性善論」真正的依據。
如果人性是惡的,是反秩序的,那怎麼會有禮的秩序?換句話說,「性善論」主張倫理、社會秩序來自人的天性,因此才是確切、不可動搖的。
這和歷史有什麼關係?我們真的不該忽略司馬遷清楚的儒家本位。要如何顯示並證明孔子、孟子對於「禮」與「理」的解釋是正確的,最堅實也最徹底的一種方式,就是去整理歷史,從曾經出現過的人與事中找出律則,那就是人性在社會事務上的影響與表現。
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這個「通」字,指的是囊括人類行為的所有現象,從中找到的普遍原則,構成了誰都無法推翻的一份真理。
2
一般從哲學的角度討論孟子的「性善論」,常出現簡單的質疑推理─找出你所知道、確切存在過的一個壞人,最壞的人,然後問:「如果人性本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從他身上找不到任何一點善,不是所有人都有善良的本性,那麼孟子的道理就被推翻了。
在某個意義上,司馬遷更認真、更全面地應對這個推論。真要了解什麼是人的本性通則,就應該回到歷史,將古往今來所有人做過的事都集合在一起,從中整理歸納。這樣的整理歸納必須在人類全幅經驗的層次上才能達成目的。
在我解讀《史記》的專書《史記的讀法》中,一開頭就提醒讀者:很多人在《史記》裡讀到了好看的故事,但一來《史記》不只有好看的故事,二來光挑出好看的故事看,就錯失了司馬遷不惜以生死代價寫這部書的用心。
我們要尊重司馬遷的主觀意圖。他的野心是統合所知的人類經驗,找出其中的「古今之變」的通則。如果和西方古希臘的史學立場相比,我們或許更能體會這份野心的非凡意義。
表現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 384-322 BC)的《詩學》(De Poetica)中,古希臘人的價值信念認定:詩比歷史重要,甚至兩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對等,不能相提並論。詩探觸普遍與永恆,提煉人的行為與情感,將瑣碎、平庸與偶然篩洗掉,萃取出內在的純粹;詩的美來自那份純粹,詩的意義在於呈現超越特定時空性的真相。
對古希臘人來說,歷史相對地只是材料,保留了個別事件,必須經由哲學或詩予以加工淬鍊,才能形成真理與真相。要有歷史,歷史不可或缺,因為哲學與詩、真理與真相無法憑空獲致,但在知識的層級上,歷史明顯低於哲學與詩。
但司馬遷凸顯並強調了「通」,讓中國的史學精神和古希臘的觀念大不相同。「通」就是普遍原則,但這原則是扎扎實實來自具體的過去經驗,是在盡量蒐羅所有已知經驗、整理消化後才有可能得到。要找的是普遍的原則,所以如果在人類經驗中發現了不符合的例證,我們就必須持續修正原本的原則,直到形成真正的「通」。
《史記》開始於「五帝本紀」,那是司馬遷能夠追溯最古遠的歷史,等於是有記錄、能知道的人類經驗的開端;而《史記》的結尾呢?在時間上一直往下到司馬遷自己的時代。他當然知道人類經驗還會有未來,但那是他無從得知的了,他就推到自己所能知道的最晚近時代。這意謂著《史記》的時間範圍徹上徹下,盡可能完整涵蓋,唯有如此,才能從中得到「通」,才是「通史」。
司馬遷這種求「通」的歷史態度,仍然給予我們在學習歷史知識時很大的刺激與啟發。當然如果依照那樣的「通」的標準,以全人類經驗為範圍,那今天要講的就不會是「中國通史」了,這樣的「通史」只能是、必須是「世界通史」或「人類通史」。
3
說到「人類通史」,可能就有人想到一部國際暢銷書,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寫的《人類大歷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那部書的主體是Homo sapiens,現代智人,為這個人種的變化發展,寫了一部上下兩百萬年的歷史。這其實是最符合司馬遷的「通史」精神,足以代表「通史」精神在現代實踐的一部著作。
我們可以藉由比對《史記》與《人類大歷史》,進一步掌握「通史」的追求與意義。
哈拉瑞的《人類大歷史》以Homo sapiens(智人)這個人種為對象,牽涉到物種觀念,也就牽涉到了演化過程。四十六億年前地球形成,大約三十九億年前出現最早的生命現象,經過了漫長的演化,地球上有了愈來愈多的物種,目前科學實證發現登錄的大約有一百六十萬種,不過推斷物種總體的數量可能到達一千萬左右。
而不論幾十億年間地球上究竟有過多少物種,有一項驚人的事實再明確不過,那就是這中間有一個分布最廣的物種,幾乎完全不受各種環境條件限制,到哪裡都活得下去,到哪裡都有。這個物種就是Homo sapiens,我們現代「智人」。其他物種都有適合生存的環境,亞熱帶臺灣的螞蟻被搬到寒帶挪威就存活不了,卻只有大約兩百萬年前從原有非洲環境中出走的物種Homo sapiens,成了唯一的例外。
現代「智人」布滿整個地球。人類憑什麼可以擺脫環境的限制,甚至人類還將整個地球都改變了?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了極具說服力的洞見─因為人類在演化的過程中得到了一項最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學習。
透過學習,人類可以不斷地自我改造,依照道金斯的看法,甚至人類也就因此走到了自然演化的終點。意思是:原本自然生物演化的方式,已經遠遠追趕不上人類藉由學習所產生的適應環境能力,人類現在甚至都取得了徹底改造環境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環境條件壓力下,以緩慢的速度,如未來二、三十萬年後我們的手變成了不同形狀,多了或少了手指指節什麼的。在那樣的演化發生前,人類早就藉由製造出的工具,更有效地應付了環境所帶來的挑戰與考驗。
從這樣的物種特性出發,我們不意外地在《人類大歷史》書中看到一個清楚的主題,那就是人的多樣性。現代智人能夠學習、模仿其他動物,找到適應不同環境的策略,意謂著分散到不同環境的人,就發展出不同的特性。於是從整理這個物種的歷史來看,得到的不再是人的共通性,而是人的分歧異質可能。
這看起來好像和司馬遷藉「通史」要尋求普遍原則的用心剛好相反,事實上卻是提醒我們看到,「通史」因為是透過整理實際的人類經驗,不同於抽象推論,只要蒐羅整理的人類經驗夠廣、夠多,最終總是會凸顯出多元多樣的性質。
4
司馬遷整理人類經驗,是為了要得知「人的共通性」,而他在《史記》裡給了我們什麼樣的答案?
放在〈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叔齊」,放在〈世家〉第一篇是「吳太伯」,而這兩篇就有著微妙的共同性─他們都具備人倫秩序中最高貴的性質,那就是「讓」。伯夷要將王位讓給弟弟叔齊,吳太伯要將王位讓給弟弟季歷和季歷的兒子文王。他們所面對的都是極高的權力,安穩又有地位可享受的生活,不只不必費吹灰之力去追求,而且還是理所當然地降臨在自己身上。他們都是具備合法身分的嫡長子,在制度中保障了他們的繼承權。
然而他們都拒絕了,因為他們有更高的信念與考量。伯夷知道弟弟叔齊比自己更適合當孤竹國的國君,太伯知道父親心中更屬意弟弟來接位,他們還為了放棄自己原有的權利,等於自我流放,離國遠去。而在伯夷的故事中又再增添了一段,他要「讓」的對象弟弟叔齊,和他同樣選擇了「讓」,無論如何都不願當國君,寧可陪哥哥一起離去,兩人最終餓死在首陽山。
更廣泛些看,他們都是重視自我內在是非原則、遠遠超過現實考量的人。所以伯夷、叔齊無法認同周武王起兵伐紂「以暴易暴」的做法,儘管歷史上早有共識定論,推崇武王「解民倒懸」的戰爭是正義的,但司馬遷寫歷史,卻藉著記錄伯夷叔齊的故事,彰顯了另外一種很不一樣的評斷態度。
如果換一個方向延伸,我們另外看到的是人的高度自尊。即使對方是父親,即使牽涉的是自己未來一生的地位與財富,像太伯這樣的人,他的自尊心使得他無法在察覺父親認定弟弟比他適合當國君的情況下,去行使自己嫡長子的身分特權。他知道如果自主選擇,父親會選弟弟而不是選他,所以他成全父親的這份意願。
這種人在我們的現實環境中,至少就絕對不會捲入MeToo性騷擾的風波中。因為他們會立即、敏銳地察知別人的不情願、甚至厭惡,他的自尊立刻會讓他避開可能產生的騷擾。君子的操守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內在高度自尊,而司馬遷的「通史」要記錄的,就是人性的寬廣多樣光譜,從最高貴的那端開始,一直到最卑下、最黑暗的,都能在《史記》中找到。
這樣的「通」並不是以中國或華夏為範圍,毋寧是要整理、呈現司馬遷所知道的人類全幅經驗。各種思想、感情、動機、行為……光譜的全部構成了人類歷史,也才是我們應該認識的人類完整面貌。
5
理解中國通史,一層重要的意義是從人類多樣性中來的。這一片區域曾經有過的歷史非常獨特,出現了具備高度連續性的特殊文明。這文明早從一開始,就建立了「華夏」和「蠻夷」區別的自覺,這份存在、持續超過三千年的自覺,構成了集體認同、集體意識,決定並範限了這個區域的人們生活變化的可能性。
從比較文明的角度看,幾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文明有著如此長遠且強烈的社會規範性。因而我們不得不好奇地探問: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獨特文明?現代智人在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學習能力才能夠適應不同環境,散布到地球各個地方,相應不同地理條件而產生了幾千個、甚至幾萬個規模大大小小、歷時長長短短的文明。如果以對於文明內部成員的形塑強度與延續性標準衡量,中國文明在其中必定名列前茅。
學習得到了中國文化的種種內容,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樣的內容對人類的影響很深、很牢靠,不容易擺脫,不會輕易褪色。我們今天處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強弩之末狀態,大部分的人已經很少感知中國文化的作用。然而,例如當身處在一個有著明式桌椅家具、牆上掛著書法作品的空間裡,我們不會覺得陌生,我們的身體與感官會很自然地配合、適應那個空間,表示在我們的身體裡確實存在著某種中國文化基因,那基因仍然在作用著。
這是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只不過今天的狀況是,有些人意識到這件事時視之為負擔,有些人則視之為值得珍惜的資產。不管採取哪種態度,我認為且主張我們都應該承認這事實,並且弄清楚:如此強悍、長期的中華文化約束力究竟如何來的,又如何不斷發揮作用。
我之前寫過一套十三冊的《不一樣的中國史》,篇幅較大,可以在特定時代中另外展開橫向多角度的描述與討論。而這次重新講述、撰寫「通史」,會更聚焦在縱向變化上,也就是呈現中國歷史中不同時代前後彼此間的因果連結。而建立這項因果鏈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是對歷史內容進行檢核、選取的主要標準,即:在時間長流裡,如何有了這個文明最核心的約束凝聚力,以及更驚人的持續性質。
另外,十三冊本的《不一樣的中國史》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路講述到辛亥革命,與司馬遷的「通史」概念比較,顯然缺漏了從民國建立(一九一二年)到當前現今的一百年。那一套書停在辛亥革命的理由我多次說明過了,這次相對篇幅短小,對於史料探究到史事陳述的要求降低了許多,因而我得以一鼓作氣,會將歷史觀照,一直推進到現今,以求對得起「通史」之稱,也對得起司馬遷提出的宏偉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