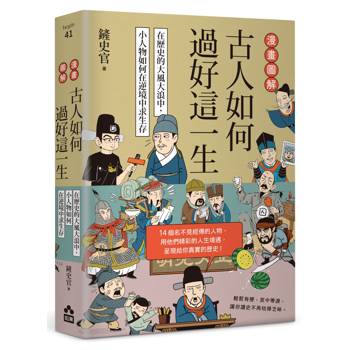【杜環】他為大唐而戰,卻被命運流放到非洲(節錄)
跨國旅行對現代人來講,只是花點錢的事。但在古代,遠渡重洋後能活著回來的,都永垂不朽了。比如鄭和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就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
其實,在鄭和出發之前約七百年,就有中國人遠赴非洲了。這位不太出名的旅者叫杜環,出身於京兆杜氏。正是這趟旅行,讓他與那些大老族親一樣名垂青史。
不過,在這趟為期十一年的旅行中,杜環一開始就被回家的念頭折磨著,因為他是被人抓過去的。在大唐天寶十年(751)的怛羅斯之戰中,他不幸被大食人俘虜。
怛羅斯,是西域小邦石國(在今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一帶)的一座城池,即現今哈薩克的塔拉茲市,與長安的直線距離有三千三百多公里。
大食,則是當時的阿拉伯帝國。
現今的二十多個阿拉伯國家,都遠在非洲和西亞。但當年的大食是一個遼闊統一的帝國,與大唐只隔了幾個西域國家。初唐時,大食東進,西域諸國害怕,抱住大唐的大腿。大唐也樂於收下這群小弟。
幾十年來,大唐多是「嘴炮」支援,而大食的進攻卻是真刀真槍,不少小弟撐不住「跪」了。唐玄宗正發愁時,機會來了,大食出現了內亂!黑衣大食正忙著推翻白衣大食,而位於唐附近的小邦石國,也政局不穩。
天寶十年,唐玄宗遣安西軍西征石國。杜環就在這支隊伍裡,作為「官N代」,杜家在軍界頗有人脈:叔祖父杜希望,曾任隴右節度使,是很多西北宿將的老上級。
安西軍將領高仙芝,曾遠征小勃律(在今喀什米爾吉爾吉特)、奇襲羯師(在今巴基斯坦北部),一年前又活捉了石國國王,此次西征,理應輕車熟路。對杜環而言,跟著常勝將軍「混人頭」,應該是萬無一失的。
高仙芝率領隊伍長途奔襲,深入敵境七百餘里,最後在怛羅斯與大食軍隊遭遇。雙方激戰五天,最終唐軍戰敗。據《舊唐書》記載,此戰唐軍只有幾千人倖存,大批唐軍被大食軍俘虜,被迫踏上西行之路。據《經行記》可知,杜環也在其中,此時,他大概是一名價值六百第納爾(阿拉伯帝國第一種用文字做錢文的硬幣)的奴隸。
在大食東方軍團的押解下,戰俘們從石國前往寧遠國(今烏茲別克的費爾干納地區)。在怛羅斯之役中,寧遠國人曾與唐軍並肩作戰,這自然招致了大食的報復。
作為昔日的大唐將士,杜環此時能做的,卻只有動動筆,述說唐人在這裡曾經的歡歌與榮耀。
離開寧遠後, 戰俘們穿過現今的烏茲別克,渡過阿姆河,輾轉前往大食東方(呼羅珊)總督的駐地木鹿(今土庫曼馬雷市),並滯留於此。這與百年前玄奘西行的路線有所重疊。
只是玄奘弘法西域的願望,此時已成泡影。大食人早已焚毀了康國(在今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一帶)的佛寺。
杜環行經時,康國的祆祠和木鹿的佛寺尚存,但大唐的戰敗,已經為祆教和佛教在西域諸國的消亡埋下伏筆。(未完)
編後語
讓杜環名載史冊的怛羅斯之戰,是網路上的熱門話題。不同於被大唐輕鬆按在地上「摩擦」的古印度,地跨歐亞非的大食──阿拉伯帝國,是中國戰爭史上少有的強悍對手。
阿拉伯人原本是不起眼的角色。他們出身於散居阿拉伯半島大漠的遊牧部族,生活在羅馬、波斯等大帝國的陰影下,如沙塵般卑微。但西元七世紀上半葉,在新興宗教的感召下,這些沙塵竟匯聚起遮天蔽日的風暴,席捲了從西班牙到印度西部的廣闊天地,史稱「大征服」。
在「大征服」的風暴中,波斯帝國轟然倒塌,中亞從此暴露在阿拉伯人的刀鋒前;而與此同時,天下初定的大唐,為應對來自北方草原的威脅,也在向西域拓展勢力。
到高宗年間,雙方在中亞的碰撞,已不可避免。永徽二年(651),大食首次遣使赴唐;大概同一時期,唐朝開始支持波斯復國運動。唐、食雙方初接觸,即拉開對抗的序幕。
這場對抗拉鋸百年,並不輕鬆:唐軍將士贏得過逾越蔥嶺(帕米爾高原)、耀兵異域的榮耀,也品嚐過折戟黃沙的苦痛。天寶十年的怛羅斯之戰,為這場對峙劃上了一個並不美好的休止符:此戰之後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大唐再也無力爭雄西域,將士百年浴血犧牲的成果,化為烏有。而杜環,正是這群犧牲者中的一分子。
相較於埋骨沙場、無聞於史冊的無數士卒,杜環無疑是幸運的。這要感謝他有力的堂叔、大唐名相杜佑。在《通典》中,杜佑這樣記載: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杜佑《通典.邊防七》)
《通典》中不多的記載,以及杜氏家族的史料,足以為我們勾勒出杜環的半生。他的家族—京兆杜氏,是漢代以來著名的門閥世族,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說,西晉滅吳名將杜預、唐初名相杜如晦,大詩人杜甫、杜牧,都出自這個家族。杜佑的父親、杜環的叔祖父杜希望,曾任隴右節度使,後來的名將王忠嗣、哥舒翰等,都曾是杜希望的下級。杜希望「行義每揮金」,為杜氏家族累積官場人脈,以此推之,西北軍界中應該有他的人際網絡,這也有可能是杜環從軍赴西域的緣由。
怛羅斯之戰爆發時,杜佑年僅十七歲。按唐制,二十一歲才可參軍,由此推斷,杜環應該比他的叔叔大一些。關於杜環西行路程的細節,學者們仍存在爭議,分歧主要集中在他離開巴格達後的路線,以及他最遠抵達了非洲何地,目前有馬利、衣索比亞等多種說法。本文參考學者宋峴《杜環遊歷大食國之路線考》一文,採納杜環抵達突尼斯附近一說。
《經行記》僅有關於西方各國風土人情的千餘字被輯錄在杜佑的《通典》中,其他內容已湮滅無聞,岑仲勉先生認為此乃「天壤間一恨事」。所幸,即便在這千餘字中,我們也能感受到近一千三百年前的一位士兵孤身赴異域的孤獨感。在大食的一座都會(宋峴先生考證為建設中的巴格達),杜環遇到四位同胞,並記錄了他們的姓名: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呂禮。(杜佑《通典.邊防九》引杜環《經行記》)
那個通信不便的年代,在遙遠的巴格達,聽到熟悉的語言時,不知杜環的內心會湧動起怎樣的漣漪。阿拉伯史料則永遠記住了另一群中國工人:造紙匠。
在怛羅斯被俘的唐軍士兵,於康國建造了阿拉伯人記載中的首家造紙廠。憑藉輕便、廉價、耐用、可防篡改的特性中國紙將西方的羊皮紙和莎草紙送進了博物館,掀起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讀寫不再是貴族階層的專利。當中國紙第一次出現在歐洲時,在羊皮紙上抄《聖經》的時代,已注定走向終結;而書寫載體向大眾的推廣,注定將加快歷史車輪旋轉的速度。
帝國爭雄的霸業,或許總會褪色;而文明與技術的力量,以及其承載的情感,則更加持久。
跨國旅行對現代人來講,只是花點錢的事。但在古代,遠渡重洋後能活著回來的,都永垂不朽了。比如鄭和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就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
其實,在鄭和出發之前約七百年,就有中國人遠赴非洲了。這位不太出名的旅者叫杜環,出身於京兆杜氏。正是這趟旅行,讓他與那些大老族親一樣名垂青史。
不過,在這趟為期十一年的旅行中,杜環一開始就被回家的念頭折磨著,因為他是被人抓過去的。在大唐天寶十年(751)的怛羅斯之戰中,他不幸被大食人俘虜。
怛羅斯,是西域小邦石國(在今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一帶)的一座城池,即現今哈薩克的塔拉茲市,與長安的直線距離有三千三百多公里。
大食,則是當時的阿拉伯帝國。
現今的二十多個阿拉伯國家,都遠在非洲和西亞。但當年的大食是一個遼闊統一的帝國,與大唐只隔了幾個西域國家。初唐時,大食東進,西域諸國害怕,抱住大唐的大腿。大唐也樂於收下這群小弟。
幾十年來,大唐多是「嘴炮」支援,而大食的進攻卻是真刀真槍,不少小弟撐不住「跪」了。唐玄宗正發愁時,機會來了,大食出現了內亂!黑衣大食正忙著推翻白衣大食,而位於唐附近的小邦石國,也政局不穩。
天寶十年,唐玄宗遣安西軍西征石國。杜環就在這支隊伍裡,作為「官N代」,杜家在軍界頗有人脈:叔祖父杜希望,曾任隴右節度使,是很多西北宿將的老上級。
安西軍將領高仙芝,曾遠征小勃律(在今喀什米爾吉爾吉特)、奇襲羯師(在今巴基斯坦北部),一年前又活捉了石國國王,此次西征,理應輕車熟路。對杜環而言,跟著常勝將軍「混人頭」,應該是萬無一失的。
高仙芝率領隊伍長途奔襲,深入敵境七百餘里,最後在怛羅斯與大食軍隊遭遇。雙方激戰五天,最終唐軍戰敗。據《舊唐書》記載,此戰唐軍只有幾千人倖存,大批唐軍被大食軍俘虜,被迫踏上西行之路。據《經行記》可知,杜環也在其中,此時,他大概是一名價值六百第納爾(阿拉伯帝國第一種用文字做錢文的硬幣)的奴隸。
在大食東方軍團的押解下,戰俘們從石國前往寧遠國(今烏茲別克的費爾干納地區)。在怛羅斯之役中,寧遠國人曾與唐軍並肩作戰,這自然招致了大食的報復。
作為昔日的大唐將士,杜環此時能做的,卻只有動動筆,述說唐人在這裡曾經的歡歌與榮耀。
離開寧遠後, 戰俘們穿過現今的烏茲別克,渡過阿姆河,輾轉前往大食東方(呼羅珊)總督的駐地木鹿(今土庫曼馬雷市),並滯留於此。這與百年前玄奘西行的路線有所重疊。
只是玄奘弘法西域的願望,此時已成泡影。大食人早已焚毀了康國(在今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一帶)的佛寺。
杜環行經時,康國的祆祠和木鹿的佛寺尚存,但大唐的戰敗,已經為祆教和佛教在西域諸國的消亡埋下伏筆。(未完)
編後語
讓杜環名載史冊的怛羅斯之戰,是網路上的熱門話題。不同於被大唐輕鬆按在地上「摩擦」的古印度,地跨歐亞非的大食──阿拉伯帝國,是中國戰爭史上少有的強悍對手。
阿拉伯人原本是不起眼的角色。他們出身於散居阿拉伯半島大漠的遊牧部族,生活在羅馬、波斯等大帝國的陰影下,如沙塵般卑微。但西元七世紀上半葉,在新興宗教的感召下,這些沙塵竟匯聚起遮天蔽日的風暴,席捲了從西班牙到印度西部的廣闊天地,史稱「大征服」。
在「大征服」的風暴中,波斯帝國轟然倒塌,中亞從此暴露在阿拉伯人的刀鋒前;而與此同時,天下初定的大唐,為應對來自北方草原的威脅,也在向西域拓展勢力。
到高宗年間,雙方在中亞的碰撞,已不可避免。永徽二年(651),大食首次遣使赴唐;大概同一時期,唐朝開始支持波斯復國運動。唐、食雙方初接觸,即拉開對抗的序幕。
這場對抗拉鋸百年,並不輕鬆:唐軍將士贏得過逾越蔥嶺(帕米爾高原)、耀兵異域的榮耀,也品嚐過折戟黃沙的苦痛。天寶十年的怛羅斯之戰,為這場對峙劃上了一個並不美好的休止符:此戰之後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大唐再也無力爭雄西域,將士百年浴血犧牲的成果,化為烏有。而杜環,正是這群犧牲者中的一分子。
相較於埋骨沙場、無聞於史冊的無數士卒,杜環無疑是幸運的。這要感謝他有力的堂叔、大唐名相杜佑。在《通典》中,杜佑這樣記載: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杜佑《通典.邊防七》)
《通典》中不多的記載,以及杜氏家族的史料,足以為我們勾勒出杜環的半生。他的家族—京兆杜氏,是漢代以來著名的門閥世族,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說,西晉滅吳名將杜預、唐初名相杜如晦,大詩人杜甫、杜牧,都出自這個家族。杜佑的父親、杜環的叔祖父杜希望,曾任隴右節度使,後來的名將王忠嗣、哥舒翰等,都曾是杜希望的下級。杜希望「行義每揮金」,為杜氏家族累積官場人脈,以此推之,西北軍界中應該有他的人際網絡,這也有可能是杜環從軍赴西域的緣由。
怛羅斯之戰爆發時,杜佑年僅十七歲。按唐制,二十一歲才可參軍,由此推斷,杜環應該比他的叔叔大一些。關於杜環西行路程的細節,學者們仍存在爭議,分歧主要集中在他離開巴格達後的路線,以及他最遠抵達了非洲何地,目前有馬利、衣索比亞等多種說法。本文參考學者宋峴《杜環遊歷大食國之路線考》一文,採納杜環抵達突尼斯附近一說。
《經行記》僅有關於西方各國風土人情的千餘字被輯錄在杜佑的《通典》中,其他內容已湮滅無聞,岑仲勉先生認為此乃「天壤間一恨事」。所幸,即便在這千餘字中,我們也能感受到近一千三百年前的一位士兵孤身赴異域的孤獨感。在大食的一座都會(宋峴先生考證為建設中的巴格達),杜環遇到四位同胞,並記錄了他們的姓名: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呂禮。(杜佑《通典.邊防九》引杜環《經行記》)
那個通信不便的年代,在遙遠的巴格達,聽到熟悉的語言時,不知杜環的內心會湧動起怎樣的漣漪。阿拉伯史料則永遠記住了另一群中國工人:造紙匠。
在怛羅斯被俘的唐軍士兵,於康國建造了阿拉伯人記載中的首家造紙廠。憑藉輕便、廉價、耐用、可防篡改的特性中國紙將西方的羊皮紙和莎草紙送進了博物館,掀起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讀寫不再是貴族階層的專利。當中國紙第一次出現在歐洲時,在羊皮紙上抄《聖經》的時代,已注定走向終結;而書寫載體向大眾的推廣,注定將加快歷史車輪旋轉的速度。
帝國爭雄的霸業,或許總會褪色;而文明與技術的力量,以及其承載的情感,則更加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