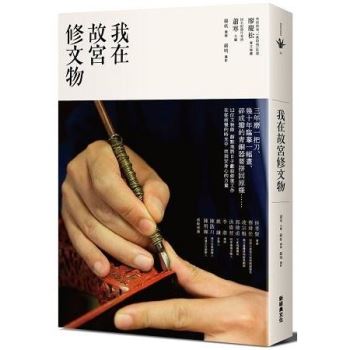1-1 安靜,讓時間動起來──鐘錶修復師
從神武門進,順著建福宮西牆拐進一個長夾道,穿出去,就到了文保科技部所在的西三所,這是故宮博物院整個工作區唯一設有門禁、須刷卡進入的部門。
西三所與壽康宮只有一牆之隔,這個在很多宮廷劇中屢屢出現的院落,是野史和傳說中清朝冷宮的所在地。因為年久失修,灰瓦紅牆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光澤,但是不經意間,棟樑上明代的彩繪得以保留,與清代的明豔繁複相比,它們更為簡約清麗。
小院裡綠植蔥蘢,有木器組史連倉父親種下的棗樹,金石組惲小剛種的君子蘭,漆器組閔俊嶸的漆樹,摹章組沈偉的玉米和茄子,以及清代的杏樹與棗樹。小院也生態豐富,文物部門不加班,五點下班以後,巨大的空間留給了動物,有興許是御貓後代的流浪貓、黃鼠狼、還有木器組收養的各種鳥。每天,青銅器修復師王有亮和摹章高手沈偉自覺地擔當起餵貓職責,連《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劇組人員都知道,想逗貓,可以去摹畫室所在的第四進小院找找看;而木器組屈峰雖貌似委屈地抱怨收留了許多「別人養著養著不要了送給我們,最後慢慢養著養著就成負擔了」的動物,但下班時他不會忘記拎鳥籠回屋,否則「第二天你可能見到的只有幾根毛」。
每年五、六月份,御杏樹上的青杏慢慢變成了甜軟的蜜黃色,年輕人暗暗興奮起來:又可以打杏了。但二○一五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展,每個組都領有大量修復任務,滿樹的杏子熟了無人採摘,密密麻麻地落了一地,引來黑壓壓的螞蟻。一個清晨,上班前的一刻鐘,木器組的人領頭,辦公室的姑娘拿出了蓋文物的強韌度白紙來接著,工人登上梯子打下來許多黃杏。大家嬉笑著來分,沒趕上的還特意來要。
這是西三所難得的喧聲笑語時刻,隨著八點鐘的到來,這裡像被施了魔法的空間,時間、人聲,都凍結起來。
「靜」,是這裡給人最深的印象。在鐘錶室採訪王津,除了我們的說話聲,就只有自鳴鐘整點報時的鐘鳴,悠揚,悅耳。他的徒弟亓昊楠安靜得彷彿不存在,雖然他明明在房間另一隅修理鐘錶。「靜」,變成一個整體的氣場,人不由自主也靜下來,感覺大聲說話、用力走路都顯得浮躁。那一瞬,你突然明白這裡的人反覆提到的「磨性子」、「靜下心」、「沉住氣」是什麼意思。任何一門宗教都把修靜入定、獲得專注作為入道的途徑,靜者心不妄動,專注已包含身心合一,修道如此,修文物何嘗不如此。1-2 修文物,是與前任工匠的對話──王津
下班的時候,老師傅不洗手,我們也不敢洗。原先這兒有一個盆架子,每天必須把這個水給打好了,洗手水。差一刻鐘十二點,一打鈴師父洗手,洗完手就下班了。師父先走,我們鎖門、關燈、斷電什麼的,基本就差個五六分鐘再走。肯定師父先走,哪能我們先走,師父關燈鎖門?打水必須得是徒弟打,哪有師父去給你提水去。家裡沒教,就是習慣,覺得就是這樣,一個傳統。也沒人說過。你看亓昊楠早上來得比較早,到這兒把水都打好了,就是這樣。
那會兒師父給你一個活兒,你老幹不出來不成,自己著急,有什麼問題自己先琢磨,實在琢磨不透再說,一般情況下不敢輕易地問,一問,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還不知道,不是招師父說嘛。
基本功包括自己做工具。每天弄點銅絲,粗的細的,銼銷子什麼的,也是練手感,讓你掌握手工工具。現在外面有現成銷子賣,我們還是手工銼,不愛用外邊的。手工的做出來方便,而且也快。銼銷子很容易,打一個鋼貼兒,銼一個斜的,然後一削。現在有用車床削,我覺得還是手工的更好,車床弄這幾下,還得找準,勁大它就彎了,還不如手工快。
你看我們桌上,桌沿加裝一根竹條,就是為了銼東西。
修復鐘錶流程,第一步先做紀錄、照相,拍下原始情況;第二步除塵;下一步拆解;第四步清洗,清洗當中看看有需要修的,需要補的;第五步,修補;然後是組裝,一步步調試,恢復它的部分機能,最後再整體組裝。要一步步的,底層中層上層,最後總體組裝咬合。
宮廷鐘錶都是特製的,恢復演藝功能是最難的,因為它表演功能多,稍微差一點都不成,沒法湊合。有的東西差不多就行了,這鐘錶的東西差一點都不成,本身比較精密,你差一點,你要糊弄它,到最後肯定給你擱這兒了,轉不了。必須從底層開始修,就是精細地一步一步往上,最後出了問題你還好找點,要是說底下就想湊合的話,將來就麻煩了。
難度比較大的,我覺得還是前幾年修的魔術鐘 ,東西不是特別大,六、七十釐米高,但是結構緊密,又表演又變魔術。據說原來提出過修,後來沒修,是趕上文革了還是什麼,又退回庫。聽老師傅說那東西破得比較厲害,時間長了。二○○七年跟荷蘭合作,荷蘭看見它想展覽用,我就給它提出來,修了將近一年。
當時荷蘭也參與修,他們修的是比較簡單的,幾個小的,我們這個魔術人鐘他們沒參與。一開始也想修,小道消息是他們想請俄羅斯專家修,但俄羅斯人開價比較高。而且那會兒也沒決定讓他們修,因為這種複雜鐘錶很稀少,他們只拿走幾件小東西,像升降塔鐘,故宮升降塔挺多的;魔術鐘有代表性,我覺得應該咱們自己修。
它一共有七套傳動裝置,走時一套,音樂一套,鳥叫一套,開門一套,底下連動變魔術一套……每一套,都有自己的運轉模式,這七套還有一個連接,不能說這門沒開就開始變魔術,應該是門打開同時變魔術;開這個碗,出什麼樣的球;什麼情況下,中間碗一開,小鳥飛出來;都是要有時間連動性,錯一個都不行。
開始修時,也沒有圖紙,一步步拆下來一大片東西,拆得挺散的。發條不行了,配幾盤發條;表演的小鳥什麼的,裡面都壞了,有的桿都是彎折的,接起來;小鳥交換的氣囊全糟了,蟲子打爛了,從荷蘭買皮子,重新糊。當時咱們還沒有這麼薄的皮子;裡面那些小氣門都是重新做的。
調試最費工夫。這麼點小地方裡有四個東西在互相變,這個起來那個上來,差一點就互相打起來,一打架就卡那兒出不來了。還不敢輕易下手,不是說覺得不合適就調,動錯一點,將來恢復起來更難,所以必須看準了,才能調試。
整個修復花了將近一年時間。沒有修不下去的時候,就是難點,就是慢,一點一點琢磨,時間長了,性子也就磨出來了,你越急它越不轉,以前師父說急了就別幹,否則幹有可能還出婁子。上周邊轉轉,安安心,接著幹。所以在這裡最大的基本功就是耐心,坐不住的人幹這個比較困難。時間長了,要是喜歡,再急的性格也能磨出來。
從神武門進,順著建福宮西牆拐進一個長夾道,穿出去,就到了文保科技部所在的西三所,這是故宮博物院整個工作區唯一設有門禁、須刷卡進入的部門。
西三所與壽康宮只有一牆之隔,這個在很多宮廷劇中屢屢出現的院落,是野史和傳說中清朝冷宮的所在地。因為年久失修,灰瓦紅牆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光澤,但是不經意間,棟樑上明代的彩繪得以保留,與清代的明豔繁複相比,它們更為簡約清麗。
小院裡綠植蔥蘢,有木器組史連倉父親種下的棗樹,金石組惲小剛種的君子蘭,漆器組閔俊嶸的漆樹,摹章組沈偉的玉米和茄子,以及清代的杏樹與棗樹。小院也生態豐富,文物部門不加班,五點下班以後,巨大的空間留給了動物,有興許是御貓後代的流浪貓、黃鼠狼、還有木器組收養的各種鳥。每天,青銅器修復師王有亮和摹章高手沈偉自覺地擔當起餵貓職責,連《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劇組人員都知道,想逗貓,可以去摹畫室所在的第四進小院找找看;而木器組屈峰雖貌似委屈地抱怨收留了許多「別人養著養著不要了送給我們,最後慢慢養著養著就成負擔了」的動物,但下班時他不會忘記拎鳥籠回屋,否則「第二天你可能見到的只有幾根毛」。
每年五、六月份,御杏樹上的青杏慢慢變成了甜軟的蜜黃色,年輕人暗暗興奮起來:又可以打杏了。但二○一五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展,每個組都領有大量修復任務,滿樹的杏子熟了無人採摘,密密麻麻地落了一地,引來黑壓壓的螞蟻。一個清晨,上班前的一刻鐘,木器組的人領頭,辦公室的姑娘拿出了蓋文物的強韌度白紙來接著,工人登上梯子打下來許多黃杏。大家嬉笑著來分,沒趕上的還特意來要。
這是西三所難得的喧聲笑語時刻,隨著八點鐘的到來,這裡像被施了魔法的空間,時間、人聲,都凍結起來。
「靜」,是這裡給人最深的印象。在鐘錶室採訪王津,除了我們的說話聲,就只有自鳴鐘整點報時的鐘鳴,悠揚,悅耳。他的徒弟亓昊楠安靜得彷彿不存在,雖然他明明在房間另一隅修理鐘錶。「靜」,變成一個整體的氣場,人不由自主也靜下來,感覺大聲說話、用力走路都顯得浮躁。那一瞬,你突然明白這裡的人反覆提到的「磨性子」、「靜下心」、「沉住氣」是什麼意思。任何一門宗教都把修靜入定、獲得專注作為入道的途徑,靜者心不妄動,專注已包含身心合一,修道如此,修文物何嘗不如此。1-2 修文物,是與前任工匠的對話──王津
下班的時候,老師傅不洗手,我們也不敢洗。原先這兒有一個盆架子,每天必須把這個水給打好了,洗手水。差一刻鐘十二點,一打鈴師父洗手,洗完手就下班了。師父先走,我們鎖門、關燈、斷電什麼的,基本就差個五六分鐘再走。肯定師父先走,哪能我們先走,師父關燈鎖門?打水必須得是徒弟打,哪有師父去給你提水去。家裡沒教,就是習慣,覺得就是這樣,一個傳統。也沒人說過。你看亓昊楠早上來得比較早,到這兒把水都打好了,就是這樣。
那會兒師父給你一個活兒,你老幹不出來不成,自己著急,有什麼問題自己先琢磨,實在琢磨不透再說,一般情況下不敢輕易地問,一問,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還不知道,不是招師父說嘛。
基本功包括自己做工具。每天弄點銅絲,粗的細的,銼銷子什麼的,也是練手感,讓你掌握手工工具。現在外面有現成銷子賣,我們還是手工銼,不愛用外邊的。手工的做出來方便,而且也快。銼銷子很容易,打一個鋼貼兒,銼一個斜的,然後一削。現在有用車床削,我覺得還是手工的更好,車床弄這幾下,還得找準,勁大它就彎了,還不如手工快。
你看我們桌上,桌沿加裝一根竹條,就是為了銼東西。
修復鐘錶流程,第一步先做紀錄、照相,拍下原始情況;第二步除塵;下一步拆解;第四步清洗,清洗當中看看有需要修的,需要補的;第五步,修補;然後是組裝,一步步調試,恢復它的部分機能,最後再整體組裝。要一步步的,底層中層上層,最後總體組裝咬合。
宮廷鐘錶都是特製的,恢復演藝功能是最難的,因為它表演功能多,稍微差一點都不成,沒法湊合。有的東西差不多就行了,這鐘錶的東西差一點都不成,本身比較精密,你差一點,你要糊弄它,到最後肯定給你擱這兒了,轉不了。必須從底層開始修,就是精細地一步一步往上,最後出了問題你還好找點,要是說底下就想湊合的話,將來就麻煩了。
難度比較大的,我覺得還是前幾年修的魔術鐘 ,東西不是特別大,六、七十釐米高,但是結構緊密,又表演又變魔術。據說原來提出過修,後來沒修,是趕上文革了還是什麼,又退回庫。聽老師傅說那東西破得比較厲害,時間長了。二○○七年跟荷蘭合作,荷蘭看見它想展覽用,我就給它提出來,修了將近一年。
當時荷蘭也參與修,他們修的是比較簡單的,幾個小的,我們這個魔術人鐘他們沒參與。一開始也想修,小道消息是他們想請俄羅斯專家修,但俄羅斯人開價比較高。而且那會兒也沒決定讓他們修,因為這種複雜鐘錶很稀少,他們只拿走幾件小東西,像升降塔鐘,故宮升降塔挺多的;魔術鐘有代表性,我覺得應該咱們自己修。
它一共有七套傳動裝置,走時一套,音樂一套,鳥叫一套,開門一套,底下連動變魔術一套……每一套,都有自己的運轉模式,這七套還有一個連接,不能說這門沒開就開始變魔術,應該是門打開同時變魔術;開這個碗,出什麼樣的球;什麼情況下,中間碗一開,小鳥飛出來;都是要有時間連動性,錯一個都不行。
開始修時,也沒有圖紙,一步步拆下來一大片東西,拆得挺散的。發條不行了,配幾盤發條;表演的小鳥什麼的,裡面都壞了,有的桿都是彎折的,接起來;小鳥交換的氣囊全糟了,蟲子打爛了,從荷蘭買皮子,重新糊。當時咱們還沒有這麼薄的皮子;裡面那些小氣門都是重新做的。
調試最費工夫。這麼點小地方裡有四個東西在互相變,這個起來那個上來,差一點就互相打起來,一打架就卡那兒出不來了。還不敢輕易下手,不是說覺得不合適就調,動錯一點,將來恢復起來更難,所以必須看準了,才能調試。
整個修復花了將近一年時間。沒有修不下去的時候,就是難點,就是慢,一點一點琢磨,時間長了,性子也就磨出來了,你越急它越不轉,以前師父說急了就別幹,否則幹有可能還出婁子。上周邊轉轉,安安心,接著幹。所以在這裡最大的基本功就是耐心,坐不住的人幹這個比較困難。時間長了,要是喜歡,再急的性格也能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