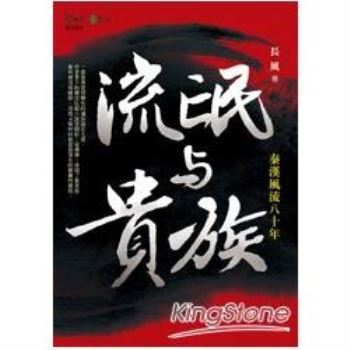第一章
祖龍已死
分權與集權哪個好
公元前二二一年,這一年,在秦王趙政的領導下,秦國終於完成了幾代秦人的目標──統一六國。紛亂的戰國時代就此結束,歷史開始了新的篇章。趙政自然要為統一的帝國制定一系列的統治政策。御前會議上,除了自封皇帝名號讓趙政感到愉悅外,丞相(國務院總理)王綰等人的提議也引起了他的極度重視。
王綰等人認為,六國剛剛被滅,燕地、齊地、楚地距離中央過於遙遠。如果不置封國恐怕難以固守,建議始皇帝把這些地方分封給皇室子弟。秦始皇把提案下發,徵詢大家的意見。大家普遍認為提案有的放矢,極為精當,應該獲得通過並予實施。那麼王綰等人為何提此方案呢?這就涉及到分封制(也稱封建制)了。
西周初年,為了實現對廣袤領土的有效管理,周王「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也就是在廣大疆域內圍繞首都(鎬京)及其直轄地區以外分土建國,以實現對王室的層層保護。因為受封的絕大多數是姬姓親戚,便形成了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大家族,周王既是族群之長又是一國之君,如此,家就是國,國就是家。
按照與王室關係的親疏遠近,諸侯君主被授予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且爵位世襲。諸侯除對王室盡一定義務外,享有高度自治權。一旦作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出現危機,諸侯要在第一時間趕到援助。我們比較熟悉的「烽火戲諸侯」就是如此,昏聵的周幽王為了博得美女褒姒一笑,竟然點燃驪山的烽火臺。諸侯以為王室遭到武裝進犯,馬上率領軍隊前往救援,這是他們的職責與義務。只要生育持續進行,那麼天下就永遠姓姬。即使周王無嗣,也能在親戚中找到合適的繼承人。當然如果實行「只生一個好」的政策的話,分封制也就沒什麼意義了。畢竟它是靠多得不能再多的親戚來防衛。不管分封制那時如何,但有一點是清晰的──周王朝糊裡糊塗統治了七百九十年。
既然趙政希望趙氏能夠統治帝國千秋萬代,那麼王綰的提案無疑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在王綰看來,有理想是好的,但沒有好的制度保障是行不通的。你秦始皇也不能保證死後帝國會怎麼樣吧?如果有人要爭奪皇權怎麼辦?回顧歷史,有制度可循的統一大王朝就是周王朝,無疑分封制是大秦帝國最不壞的選擇。
然而這份提案遭到廷尉(司法部長)李斯的堅決反對。他認為,周朝文王、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及其同姓諸侯是不少,但後來血緣關係疏遠,互相進攻如仇敵。諸侯們接連不斷地相互誅殺征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海內一統,國家賦稅養起來的宗室與功臣也易控制,應力行郡縣制度,此乃國家安定的根本制度。搞分封不利於治理國家。
郡縣制始於春秋,流行於戰國。它打破了貴族世襲權力的傳統,而由中央依據才能委派官吏到地方進行管理,憑其政績提升或罷免。與分封制相比,中央委派的官吏在郡縣只擁有行政管理權,而分封下的諸侯擁有行政、司法、軍事、財政權力。郡縣制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由法家提出並實施的,其實質是集權制;而被儒家推崇的分封制就實質而言是分權制。儘管兩種制度建立的初衷都是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管理,但隨著地緣政治取代血緣政治,郡縣制越發被人看好。
李斯認為長達數百年的戰爭實乃分封制造成的。這些諸侯你吃我,我吃你,也不顧及什麼親戚不親戚;而周王因為權力衰微,也管不了這些不肖子孫。基於此,李斯認為至上的權力對於君主而言至關重要,只要中央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天下就不會有異議,那麼國家就穩定和諧了。以此推之,秦帝國統治的時間自然會長久,而郡縣制完全能滿足這一要求。
對於雙方的激辯,趙政最後作了總結性發言。中國的第一位皇帝表示:天下戰爭之所以連續不斷就是因為諸侯的存在。感謝祖宗保佑,我們平息了戰爭,社會得以安寧。倘若再建國封王無疑再造戰亂,想要社會穩定豈不難哉!廷尉(司法部長)說得對。
趙政的一番陳述其實為分封制定了性。他與李斯都認為分封造成了戰亂,這樣會不會造成戰亂成了秦帝國最高層對分封制與郡縣制評估的標準。既然皇帝已經表了態,作為臣子的也就不敢再提出異議。於是,郡縣制推向全國,起初設置三十六個郡,以後增至四十個。有關分封制與郡縣制的爭論也暫時告一段落。
集權就是好,就是好
公元前二一三年,也就是秦帝國建立的第八年。始皇帝於咸陽宮宴請帝國的高級官員。官員們沉浸在歡快喜悅中,溜鬚拍馬之士也可大顯身手,讚美一下帝國的開創者與總設計師。當時來了七十位博士(皇家顧問官)祝酒。博士僕射(主管博士的首長)周青臣頌揚道:「從前秦國方圓不過千里,仰賴陛下文治武功,平定海內,驅逐蠻夷。凡日月所照,無不順服。廢分封制改行郡縣制,人人得以安居樂業,遠離戰爭之禍難,其偉業可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之威德。」周青臣的祝酒辭說到趙政的心坎裡,趙政心情相當爽。
而博士(皇家顧問官)淳于越的一番反駁頓時把宴會的氣氛降至冰點。他說:「我聽說商朝、周朝統治天下一千餘載,靠的是分封子弟與功臣來輔佐王室。如今陛下擁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卻是平民。一旦有像齊國的田常弒君和晉國六卿擅權的亂臣賊子,沒有皇室宗族的輔助,拿什麼挽救危局?凡事不師古制而能長久的,我還沒聽說過。如今周青臣又當面奉承而使陛下加重過失。他算不得國家忠臣。」
事隔八年,有關兩制的辯論再次風起。按照常理,郡縣制已在帝國強力推行了八年,而當年關於兩制的討論隨著始皇帝的總結性發言,已經成為定論,沒有再探討的必要。但淳于越的舊事重提也不是沒有依據,畢竟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郡縣制再好,它被實踐檢驗的時間顯然不如分封制長久,郡縣制是秦帝國最好的制度本身值得懷疑。即便當年的御前會議辯論也是說得模棱兩可,誰也沒有說服誰,只是靠大裁判趙政的一句話定輸贏罷了。在過去的八年裡,就發生過韓國的貴族張良訓練大力士刺殺始皇帝的事件。帝國並非人們想像的那麼安寧。趙政可以到處在石碑上刻字,突顯自己的偉大,但這並不意味著秦制度「就是好,就是好」。
相比上次的辯論,淳于越特意提出兩點質疑:
第一,皇帝之子豈能是平民?
淳于越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作為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其子弟怎麼能沒有任何權力,而是像動物一樣地被豢養起來。難道最親的人是皇權最大的敵人嗎?一旦出現篡權之事,怎麼解決危機?
第二,經驗難道不重要嗎?
淳于越的看法是經驗的,是保守的。他認為對以往的經驗要有所尊重與敬畏,畢竟它是經過實踐與時間檢驗的。對法家只看現在、不屑過去的歷史觀,淳于越持否定態度。
我們能夠發現,無論是八年前還是這次,尊儒的知識分子都沒有敵視郡縣制。他們要實行分封制,但並不意味著絕對反對郡縣制的實行,然而他們又沒有足夠的遠見卓識提出「一國兩制」。這樣,就導致兩種制度在秦帝國表現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按理趙政聽完淳于越的慷慨陳詞後,無論作為法家的堅定信仰者,還是作為郡縣制實施的決策者,他完全可以直接給出否定答案。但讓我們深感意外的是,趙政讓大家各抒己見,並委派李斯來處理。不難看出趙政也拿不定主意,畢竟這又牽扯到趙氏天下能否存在千秋萬代的問題。
再次接招的李斯,已經從八年前的廷尉(司法部長)晉升為丞相(國務院總理)。對於孔子徒子徒孫的「翻案風」,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李斯該做如何反擊呢?李斯認為淳于越的提案很荒謬,根本不採納。為此他特意上書秦始皇。
李斯說道:「五帝的施政方針是不重複的,三代的國家制度也是不承襲的,各自都是按照實際情況而定,不是有意搞特殊,因為社會國情不同了。現在陛下創立了偉大基業,建立了萬世功勳,這不是那些迂腐的知識分子所能瞭解的。況且淳于越所說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又有什麼值得效法?」
話說到這裡,李斯已經表明觀點,當下是最好的,沒必要去學習古人。我們大秦帝國就是要基業常青,我們所建立的制度是最好的,也是後人學習的榜樣。什麼三皇五帝,總拿死人嚇唬活人感覺良好嗎?八年之前的李斯,如果說到此處也就終止了,只需等待皇帝聖裁。
不過此時的李斯地位已經大變,他要把這個問題的討論從根源終結,於是他話鋒一轉,繼續說道:
舊社會,諸侯搞國力競賽,所以大量投資人才工程,吸引知識分子效力本國。現在是新社會、新國家,法律規章都由中央政府制定,普通國民當務之急是耕田做工。知識分子也該自我更新,學習法律知識、規章制度。可是眼下的一些知識分子跟不上形勢,鼓吹舊制度,抨擊新政策,胡說八道,蠱惑人心。作為大秦帝國的總理我冒死提議:
舊時,天下混亂,沒有誰能夠統一天下,致使諸侯火拼,烽煙不斷。知識分子一說話言必談古代,諷刺當下,盡說些空洞無物的話混淆是非,人人都喜歡自己所學的那一套,指責中央制定的方針政策。現在陛下已經統一天下,把權力集於一身,制定了辨別是非的規章制度。可一些異議分子非法聚會,非議中央的法令規章。每當中央精神傳達下去,他們就會從所學專業議論,自以為是,不知天高地厚。吹牛、扯淡、胡說八道,說些驚世駭俗的話無非是自我炒作。沒事吃飽撐的,沒別的能耐,就會帶著一群粉絲造謠誹謗。
這種情況如果再不禁止的話,皇帝的權威何在?中央的權威何在?這種情況如果再不取締的話,就會出現拉幫結派,就會出現非法組織。我認為是時候了,禁止這種趨勢泛濫是合適的。
基於以上認識,我強烈建議:凡不是秦政府官方記載的史書,一律焚毀。除了博士(皇家顧問官)研究需要外,其他任何人收藏的《詩經》、《書經》等書籍,都要限期交出,並在當地官員監視下燒毀。兩人以上膽敢討論《詩經》、《書經》者當眾砍頭。以古非今者誅殺全族。政府官員如果知情不報,與收藏者同罪。政府令下達三十日內,有拒絕執行者,處以黥刑並發配到邊疆無期勞改(城旦) 。但是醫藥、算卦、種植方面的書籍不在焚毀之列。有人想學習法令請去求教官員。
今天再讀李斯的奏摺,我們感到殺氣騰騰。關於兩制的討論,無論主張哪一種都是為了秦帝國的長治久安,都想拿出最佳方案,這樣的討論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然而李斯在反駁了淳于越的「師古論」後,卻把矛頭直接對準知識分子,進而又對準了知識分子所讀的書。於是一個有益的探討被無情地擴大外延,莫名其妙地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對立,大有「寧可要法家的草,也不要儒家的苗」之勢。真是沒有一點風度!
可惡的是,這篇奏摺大張旗鼓地要改造知識分子,取締學術自由,禁錮人的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當這份重磅奏摺被趙政閱覽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經歷了一番思考,只知道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留下了趙政的一個字答覆:「可」。
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支持,轟轟烈烈的思想、文化革命開始了。後來郭沫若著有《十批判書》,就曾指責秦帝國的愚蠢行為。毛澤東看了此書,特意寫了首詩〈讀〈封建論〉──呈郭老〉,這首詩當時家喻戶曉。詩曰: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翻譯一下:
奉勸您啊──老郭,少點罵人家秦始皇,
燒書,活埋知識分子的事情咱們還要商量商量。
秦始皇儘管死了,但秦帝國依然活在我們當中,
孔子學說的調子倒是挺高,其實就是糟粕垃圾。
兩千來年,歷朝歷代都實行秦制度,
很不客氣地說,您的《十批判書》寫的真不怎麼地。
多翻翻柳宗元寫的〈封建論〉,不要倒退去搞分封制。
如果讀李斯的高論,看到趙政的「可」,還是感覺迷茫的話,那麼看到毛澤東的詩,再聯繫到一九五七至一九七六年,我們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趙政和李斯都認為多元文化是干擾社會穩定的根本因素,而知識分子則是威脅皇權的一支重要力量。只有實行集權專制才能維護有效統治。對於民眾?對不起,愚民政策!既然李斯已經把話題引向了十萬八千里,那麼關於兩制的討論在秦帝國也就戛然而止。
祖龍已死
分權與集權哪個好
公元前二二一年,這一年,在秦王趙政的領導下,秦國終於完成了幾代秦人的目標──統一六國。紛亂的戰國時代就此結束,歷史開始了新的篇章。趙政自然要為統一的帝國制定一系列的統治政策。御前會議上,除了自封皇帝名號讓趙政感到愉悅外,丞相(國務院總理)王綰等人的提議也引起了他的極度重視。
王綰等人認為,六國剛剛被滅,燕地、齊地、楚地距離中央過於遙遠。如果不置封國恐怕難以固守,建議始皇帝把這些地方分封給皇室子弟。秦始皇把提案下發,徵詢大家的意見。大家普遍認為提案有的放矢,極為精當,應該獲得通過並予實施。那麼王綰等人為何提此方案呢?這就涉及到分封制(也稱封建制)了。
西周初年,為了實現對廣袤領土的有效管理,周王「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也就是在廣大疆域內圍繞首都(鎬京)及其直轄地區以外分土建國,以實現對王室的層層保護。因為受封的絕大多數是姬姓親戚,便形成了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大家族,周王既是族群之長又是一國之君,如此,家就是國,國就是家。
按照與王室關係的親疏遠近,諸侯君主被授予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且爵位世襲。諸侯除對王室盡一定義務外,享有高度自治權。一旦作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出現危機,諸侯要在第一時間趕到援助。我們比較熟悉的「烽火戲諸侯」就是如此,昏聵的周幽王為了博得美女褒姒一笑,竟然點燃驪山的烽火臺。諸侯以為王室遭到武裝進犯,馬上率領軍隊前往救援,這是他們的職責與義務。只要生育持續進行,那麼天下就永遠姓姬。即使周王無嗣,也能在親戚中找到合適的繼承人。當然如果實行「只生一個好」的政策的話,分封制也就沒什麼意義了。畢竟它是靠多得不能再多的親戚來防衛。不管分封制那時如何,但有一點是清晰的──周王朝糊裡糊塗統治了七百九十年。
既然趙政希望趙氏能夠統治帝國千秋萬代,那麼王綰的提案無疑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在王綰看來,有理想是好的,但沒有好的制度保障是行不通的。你秦始皇也不能保證死後帝國會怎麼樣吧?如果有人要爭奪皇權怎麼辦?回顧歷史,有制度可循的統一大王朝就是周王朝,無疑分封制是大秦帝國最不壞的選擇。
然而這份提案遭到廷尉(司法部長)李斯的堅決反對。他認為,周朝文王、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及其同姓諸侯是不少,但後來血緣關係疏遠,互相進攻如仇敵。諸侯們接連不斷地相互誅殺征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海內一統,國家賦稅養起來的宗室與功臣也易控制,應力行郡縣制度,此乃國家安定的根本制度。搞分封不利於治理國家。
郡縣制始於春秋,流行於戰國。它打破了貴族世襲權力的傳統,而由中央依據才能委派官吏到地方進行管理,憑其政績提升或罷免。與分封制相比,中央委派的官吏在郡縣只擁有行政管理權,而分封下的諸侯擁有行政、司法、軍事、財政權力。郡縣制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由法家提出並實施的,其實質是集權制;而被儒家推崇的分封制就實質而言是分權制。儘管兩種制度建立的初衷都是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管理,但隨著地緣政治取代血緣政治,郡縣制越發被人看好。
李斯認為長達數百年的戰爭實乃分封制造成的。這些諸侯你吃我,我吃你,也不顧及什麼親戚不親戚;而周王因為權力衰微,也管不了這些不肖子孫。基於此,李斯認為至上的權力對於君主而言至關重要,只要中央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天下就不會有異議,那麼國家就穩定和諧了。以此推之,秦帝國統治的時間自然會長久,而郡縣制完全能滿足這一要求。
對於雙方的激辯,趙政最後作了總結性發言。中國的第一位皇帝表示:天下戰爭之所以連續不斷就是因為諸侯的存在。感謝祖宗保佑,我們平息了戰爭,社會得以安寧。倘若再建國封王無疑再造戰亂,想要社會穩定豈不難哉!廷尉(司法部長)說得對。
趙政的一番陳述其實為分封制定了性。他與李斯都認為分封造成了戰亂,這樣會不會造成戰亂成了秦帝國最高層對分封制與郡縣制評估的標準。既然皇帝已經表了態,作為臣子的也就不敢再提出異議。於是,郡縣制推向全國,起初設置三十六個郡,以後增至四十個。有關分封制與郡縣制的爭論也暫時告一段落。
集權就是好,就是好
公元前二一三年,也就是秦帝國建立的第八年。始皇帝於咸陽宮宴請帝國的高級官員。官員們沉浸在歡快喜悅中,溜鬚拍馬之士也可大顯身手,讚美一下帝國的開創者與總設計師。當時來了七十位博士(皇家顧問官)祝酒。博士僕射(主管博士的首長)周青臣頌揚道:「從前秦國方圓不過千里,仰賴陛下文治武功,平定海內,驅逐蠻夷。凡日月所照,無不順服。廢分封制改行郡縣制,人人得以安居樂業,遠離戰爭之禍難,其偉業可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之威德。」周青臣的祝酒辭說到趙政的心坎裡,趙政心情相當爽。
而博士(皇家顧問官)淳于越的一番反駁頓時把宴會的氣氛降至冰點。他說:「我聽說商朝、周朝統治天下一千餘載,靠的是分封子弟與功臣來輔佐王室。如今陛下擁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卻是平民。一旦有像齊國的田常弒君和晉國六卿擅權的亂臣賊子,沒有皇室宗族的輔助,拿什麼挽救危局?凡事不師古制而能長久的,我還沒聽說過。如今周青臣又當面奉承而使陛下加重過失。他算不得國家忠臣。」
事隔八年,有關兩制的辯論再次風起。按照常理,郡縣制已在帝國強力推行了八年,而當年關於兩制的討論隨著始皇帝的總結性發言,已經成為定論,沒有再探討的必要。但淳于越的舊事重提也不是沒有依據,畢竟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郡縣制再好,它被實踐檢驗的時間顯然不如分封制長久,郡縣制是秦帝國最好的制度本身值得懷疑。即便當年的御前會議辯論也是說得模棱兩可,誰也沒有說服誰,只是靠大裁判趙政的一句話定輸贏罷了。在過去的八年裡,就發生過韓國的貴族張良訓練大力士刺殺始皇帝的事件。帝國並非人們想像的那麼安寧。趙政可以到處在石碑上刻字,突顯自己的偉大,但這並不意味著秦制度「就是好,就是好」。
相比上次的辯論,淳于越特意提出兩點質疑:
第一,皇帝之子豈能是平民?
淳于越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作為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其子弟怎麼能沒有任何權力,而是像動物一樣地被豢養起來。難道最親的人是皇權最大的敵人嗎?一旦出現篡權之事,怎麼解決危機?
第二,經驗難道不重要嗎?
淳于越的看法是經驗的,是保守的。他認為對以往的經驗要有所尊重與敬畏,畢竟它是經過實踐與時間檢驗的。對法家只看現在、不屑過去的歷史觀,淳于越持否定態度。
我們能夠發現,無論是八年前還是這次,尊儒的知識分子都沒有敵視郡縣制。他們要實行分封制,但並不意味著絕對反對郡縣制的實行,然而他們又沒有足夠的遠見卓識提出「一國兩制」。這樣,就導致兩種制度在秦帝國表現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按理趙政聽完淳于越的慷慨陳詞後,無論作為法家的堅定信仰者,還是作為郡縣制實施的決策者,他完全可以直接給出否定答案。但讓我們深感意外的是,趙政讓大家各抒己見,並委派李斯來處理。不難看出趙政也拿不定主意,畢竟這又牽扯到趙氏天下能否存在千秋萬代的問題。
再次接招的李斯,已經從八年前的廷尉(司法部長)晉升為丞相(國務院總理)。對於孔子徒子徒孫的「翻案風」,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李斯該做如何反擊呢?李斯認為淳于越的提案很荒謬,根本不採納。為此他特意上書秦始皇。
李斯說道:「五帝的施政方針是不重複的,三代的國家制度也是不承襲的,各自都是按照實際情況而定,不是有意搞特殊,因為社會國情不同了。現在陛下創立了偉大基業,建立了萬世功勳,這不是那些迂腐的知識分子所能瞭解的。況且淳于越所說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又有什麼值得效法?」
話說到這裡,李斯已經表明觀點,當下是最好的,沒必要去學習古人。我們大秦帝國就是要基業常青,我們所建立的制度是最好的,也是後人學習的榜樣。什麼三皇五帝,總拿死人嚇唬活人感覺良好嗎?八年之前的李斯,如果說到此處也就終止了,只需等待皇帝聖裁。
不過此時的李斯地位已經大變,他要把這個問題的討論從根源終結,於是他話鋒一轉,繼續說道:
舊社會,諸侯搞國力競賽,所以大量投資人才工程,吸引知識分子效力本國。現在是新社會、新國家,法律規章都由中央政府制定,普通國民當務之急是耕田做工。知識分子也該自我更新,學習法律知識、規章制度。可是眼下的一些知識分子跟不上形勢,鼓吹舊制度,抨擊新政策,胡說八道,蠱惑人心。作為大秦帝國的總理我冒死提議:
舊時,天下混亂,沒有誰能夠統一天下,致使諸侯火拼,烽煙不斷。知識分子一說話言必談古代,諷刺當下,盡說些空洞無物的話混淆是非,人人都喜歡自己所學的那一套,指責中央制定的方針政策。現在陛下已經統一天下,把權力集於一身,制定了辨別是非的規章制度。可一些異議分子非法聚會,非議中央的法令規章。每當中央精神傳達下去,他們就會從所學專業議論,自以為是,不知天高地厚。吹牛、扯淡、胡說八道,說些驚世駭俗的話無非是自我炒作。沒事吃飽撐的,沒別的能耐,就會帶著一群粉絲造謠誹謗。
這種情況如果再不禁止的話,皇帝的權威何在?中央的權威何在?這種情況如果再不取締的話,就會出現拉幫結派,就會出現非法組織。我認為是時候了,禁止這種趨勢泛濫是合適的。
基於以上認識,我強烈建議:凡不是秦政府官方記載的史書,一律焚毀。除了博士(皇家顧問官)研究需要外,其他任何人收藏的《詩經》、《書經》等書籍,都要限期交出,並在當地官員監視下燒毀。兩人以上膽敢討論《詩經》、《書經》者當眾砍頭。以古非今者誅殺全族。政府官員如果知情不報,與收藏者同罪。政府令下達三十日內,有拒絕執行者,處以黥刑並發配到邊疆無期勞改(城旦) 。但是醫藥、算卦、種植方面的書籍不在焚毀之列。有人想學習法令請去求教官員。
今天再讀李斯的奏摺,我們感到殺氣騰騰。關於兩制的討論,無論主張哪一種都是為了秦帝國的長治久安,都想拿出最佳方案,這樣的討論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然而李斯在反駁了淳于越的「師古論」後,卻把矛頭直接對準知識分子,進而又對準了知識分子所讀的書。於是一個有益的探討被無情地擴大外延,莫名其妙地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對立,大有「寧可要法家的草,也不要儒家的苗」之勢。真是沒有一點風度!
可惡的是,這篇奏摺大張旗鼓地要改造知識分子,取締學術自由,禁錮人的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當這份重磅奏摺被趙政閱覽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經歷了一番思考,只知道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留下了趙政的一個字答覆:「可」。
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支持,轟轟烈烈的思想、文化革命開始了。後來郭沫若著有《十批判書》,就曾指責秦帝國的愚蠢行為。毛澤東看了此書,特意寫了首詩〈讀〈封建論〉──呈郭老〉,這首詩當時家喻戶曉。詩曰: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翻譯一下:
奉勸您啊──老郭,少點罵人家秦始皇,
燒書,活埋知識分子的事情咱們還要商量商量。
秦始皇儘管死了,但秦帝國依然活在我們當中,
孔子學說的調子倒是挺高,其實就是糟粕垃圾。
兩千來年,歷朝歷代都實行秦制度,
很不客氣地說,您的《十批判書》寫的真不怎麼地。
多翻翻柳宗元寫的〈封建論〉,不要倒退去搞分封制。
如果讀李斯的高論,看到趙政的「可」,還是感覺迷茫的話,那麼看到毛澤東的詩,再聯繫到一九五七至一九七六年,我們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趙政和李斯都認為多元文化是干擾社會穩定的根本因素,而知識分子則是威脅皇權的一支重要力量。只有實行集權專制才能維護有效統治。對於民眾?對不起,愚民政策!既然李斯已經把話題引向了十萬八千里,那麼關於兩制的討論在秦帝國也就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