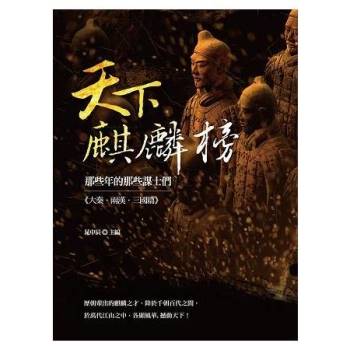輔佐始皇天下一統 阿順苟合身被五刑
李斯傳
王振富
李斯(西元前?年~西元前二〇八年)是秦朝重臣,兩朝元老,幾與秦王朝的興亡相始終。他既是興秦的元勛,也是亡秦的罪臣,這就形成了他獨特的風貌。他一方面通過不遺餘力的政治實踐,輔佐秦始皇兼併六國,為建立和鞏固統一的封建國家縱橫捭闔,功勛蓋世;另一方面,他毫不掩飾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為維護榮華富貴而不惜向惡勢力屈膝,終於身敗名裂,又充分暴露了他醜陋和自私的一面。因此,他對秦王朝的短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斯是一個謀略出眾且又複雜多變的人物。他的一生,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為後人昭示了身敗名裂的深刻教訓。
一、奮發進取求功名
戰國時期,歷史正處於一場社會大變革之際。自春秋以來,人民群眾飽受分裂戰亂之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要求儘快結束列國紛爭的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各國統治階級出於對土地、人口、財寶無止境的追求,互相兼併,你爭我奪。這種紛亂的時局,為那些欲建功業之士提供了活動舞台。就在七雄並爭的戰國末期,李斯出生於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的一個平民家庭。
李斯年輕時曾做過郡中小吏,即管理鄉文書的辦事員。小吏的地位低下,侍奉長官,唯恐有所閃失,滿懷理想與抱負的李斯自然不甘久居其位。有一天,他看到官舍廁所中的老鼠偷吃糞便,一旦人來狗咬,立刻驚恐萬狀,倉皇逃竄。他又來到官倉中,看到這裡的老鼠很自在地吃著糧食,住著高大寬敞的庫房,盡情享受,公然出入,根本不害怕人來,也不用擔心有狗來咬。兩相對照,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斯由此及彼,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老鼠處於不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有君子小人之別,就像老鼠一樣,在於自己選擇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這就是說,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就應該像在官倉裡偷吃糧食的老鼠,這樣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戰國時期人人爭名逐利的情況下,李斯也不滿於布衣或小吏的處境。他決心拋開貧賤,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在李斯眼裡,人生最大的榮耀莫過於取得高貴的身份,最大的快樂莫過於享受榮華富貴。在李斯的胸中,雄心與野心混合在一起,化為一團追求功名富貴的熊熊燃燒的慾望之火。
「學而優則仕」,李斯很懂得這句話的含義,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李斯為了改變生活航向,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通常的道路,即先投師受教。因此,李斯辭去了郡小吏的職務,遠離家鄉,來到千里之外的齊國蘭陵(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求學,拜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大師荀況為師。荀況,史稱荀卿或孫卿,人尊之為荀子。他是戰國晚期新興地主階級的理論代言人,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荀況的學說雖然仍以孔子為宗,但又結合戰國時期變化了的形勢,對儒學進行了發揮和改造,因而很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統一天下的形勢需要。從荀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來看,他把儒學的「禮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結合在一起,即後人所說的「儒中有法」。李斯投師荀況門下,主要著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如何滿足君主的擴張慾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學說。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韓非。他們都拋棄了老師的儒家仁義道德,而吸收他那符合法家理論的「帝王之術」。後來,韓非終於成為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化理論為實踐,成為真正實現法家理想的政治家。李斯學成之後,反覆思考應該到哪個地方才能顯露才幹。他想效力於自己的國家楚國,又眼看著楚國江河日下,楚王已難有作為。其他東方各國也正在走下坡路,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只有秦最強盛,顯得朝氣蓬勃,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初步條件。於是,李斯決定西入秦國,一試身手。臨行之前,荀卿曾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態:「我聽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現在各國都在爭雄,這正是遊說之士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王羽翼豐滿,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人生在世,卑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莫大的悲哀。一個人總處於卑賤窮困的地位,那是會令人譏笑的。處士橫議而又說自己羞於富貴,如此『無為』,只是掩飾自己無能的表現,這是不合人之常情的,更不是讀書人的想法。我將到秦王那裡以取富貴。」李斯公然摒棄禮義,毫不虛偽,追求功利,這正是他的品性。這種強烈而褊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為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是這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視野,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選擇,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個人悲劇。
秦莊襄王三年(西元前二四七年)五月,李斯來到秦國時,正值莊襄王病死,十三歲的嬴政(秦始皇)即位,相國呂不韋總攬朝政。因此,李斯就去投靠呂不韋,成為呂門「舍人」,也就是門下的食客。當時,諸侯貴族養士之風甚盛,呂不韋也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中,李斯很快顯露出才華,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呂不韋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裡,擔任郎官,郎官雖然品級低微,職責是守護宮門,侍衛人君,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但由於職務之便,李斯有了接近國王的機會。
在此期間,天下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韓國入朝稱臣,魏亦舉國聽命於秦。這一年,雖有魏國信陵君率五國聯軍偶敗秦將蒙驁,實為迴光返照,垂死掙扎而已。而秦國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歷經惠王、武王、昭王、文王、莊襄王六世,國力大增,兵強民富,實力遠遠超過了東方六國。秦統一宇內的形勢已經基本形成。當時秦王嬴政雖然年輕,但志向遠大,思想活躍,在丞相呂不韋的輔助下,正在為統一全國做準備。對此,李斯也和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一樣,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認準時機,及時地提出謀略和方案,為秦王獻計獻策。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個向秦王上書的機會,便立刻提出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的戰略建議。這封上書以簡潔明晰的語言剖析了形勢變化,以推動秦國加快統一六國的步伐。李斯綜觀時局,既指出了此時正是兼併六國的良機,又指出了倘若坐失良機,有諸侯復強的危險,精闢而透澈。果然,這封奏書正合秦王嬴政的心意,也是眾大臣日思夜想的主要問題,秦王不能不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於是「乃拜李斯為長史,聽其計」。
李斯剛從東方來,對那裡各國政權的腐敗和君臣離心的狀況瞭如指掌。他建議,暗中派遣能言善辯、巧於謀略的官員,各帶金銀財寶,去遊說諸侯。各諸侯國的大臣權貴如果貪財,就行賄收買;如果不為金錢所動,就派刺客把他殺掉。總的謀略是遠交近攻,並利用一切手段,在六國君臣之間挑撥離間,破壞其團結,使其內部越來越亂,然後等待機會,派出良將勁旅各個擊破。秦王嬴政聞言大喜,更加信任李斯,不久便提升他為客卿。客卿是秦國專為從別國來的人才而設置的高級官位。李斯躋身於客卿之列,終於可以與國王和眾大臣共謀國家大事了。
在以秦王嬴政為首的決策層中,李斯占有重要的一席。他雖未能像王翦等武將那樣,率領大軍,開赴前線,效命疆場,但作為秦王的謀士,他參與了整個統一戰爭的重大決策。東方諸國疆域廣大,犬牙交錯,強弱不一,情況複雜,統一戰爭應從何著手,必須有一個全面規劃。正是李斯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擬定出了攻滅六國的戰略決策,即由近及遠,避實就虛,選擇弱點,正面突破,先滅掉韓,再掃兩翼,最後消滅齊國。以後統一戰爭的進程說明,這個策略十分正確。
同時,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戰爭固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是,還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與之配合,如設法從內部瓦解,渙散敵國的軍事力量,使其失去抵抗力等,從而使戰爭更加順利地進行。這時候,李斯的策略就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趙國名將李牧,曾兩次擊退秦軍的進攻,趙國將亡,他還率領趙軍,堅持抵抗秦軍達一年之久。於是,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國派人持金玉收買權臣郭開。郭開在趙王面前誣告李牧勾結秦國,陰謀反叛。趙王中計,殺死李牧,自毀長城,秦軍乘亂進攻,不久就滅了趙國這個勁敵。又如在最後滅齊的過程中,由於秦已用金錢收買了齊的相國後勝,因此他一再向齊王保證,秦決不會來攻齊國。正是在這種麻痺鬆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秦國毫不費力地就把偌大一個齊國滅亡了。在這期間,秦國基本上是按照李斯的戰略安排逐步吞食六國,從而大大加快了統一戰爭的進程。正是由於這一策略的成功,秦王嬴政才得以「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而李斯也贏得了秦王的信賴,官位不斷陞遷,逐漸成為秦國決策的主要人物。
二、上「諫逐客書」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風順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政治生涯。
秦國和關東諸國相比,一向重用外來人才。自商鞅變法後,秦國地位蒸蒸日上,更吸引了大批關東士人入秦。這對秦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但同時也引起了秦國一些舊貴族的忌恨。秦王嬴政元年(西元前二四六年),韓國因為抵抗不住秦國的進攻,就派「水工」(水利專家)鄭國去「間秦」,慫恿秦王修築一條溝通涇河與洛河的渠道,引涇水灌田,幹渠長三百多里,即歷史上著名的「鄭國渠」。韓國的本意是想使秦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疲勞不堪,騰不出手來再向東征伐,以便暫時減輕秦對韓的軍事壓力。此術之愚蠢,猶如以肉投虎,雖然耗費了秦國十年之功,卻可灌溉田地四萬餘頃,從此「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國更加富強,為兼併戰爭做了充足的物質準備。正如鄭國後來所說的:水渠修成,「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渠將修成,鄭國的間諜身份也暴露了,秦國上下一片嘩然。接著,秦王嬴政九年(西元前二三八年),長信侯嫪毐發動叛亂。次年,又查明相國呂不韋與嫪毐之亂有關,遂罷斥其相。鄭國、呂不韋都不是秦國人,這就為一向守舊的宗室大臣提供了藉口。他們本來就對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滿,認為大量異國異姓的人充塞秦國上下,堵住了他們的仕途,因此乘機推波助瀾,在秦王面前煽動:「一切在秦做官的外來人都是間諜,是為其本國利益來破壞秦國的。請把他們一概驅逐出境,免貽後患。」秦王嬴政對此也不能不加懷疑,於是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逐客令」,「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作為楚人的李斯,當然也在被逐之列。
當時的李斯已到中年,是個頗有影響的客卿,成為被驅逐的重點對象。眼看自己的前途將被斷送,李斯心有不甘,他很清楚,這種缺乏遠見的偏激行為,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業也相當不利,甚至有可能引起國內的動亂,削弱秦國實力。於是,在被逐的路上,李斯毅然向秦王上書,力請改變逐客的決定。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諫逐客書》。
〈諫逐客書》一文洋洋灑灑,多用排比句式和形象比喻,並巧於運用虛詞助字作轉折過渡,來增加文章氣勢和襯托作者的精神。文章思想犀利,邏輯性強,很有說服力。文章開宗明義:「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針鋒相對,觀點鮮明。接著,李斯用透澈、明快、雄辯、激切的言詞,連物比類,就秦國本身發展的歷史事實,歷述異國人的豐功偉績和關鍵作用。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是強秦的奠基之君,他從西戎迎來由余,從宛地(今河南南陽)得到百里奚,從宋國招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這五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兵強國富,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同盟,迫使他們一個個西面事秦。秦昭王得到魏國人范雎,計除秦國王廷上專權的親貴大臣魏冉,加強了王權,併吞食諸侯,奠定了秦國帝業的基礎。上述四位國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大大促進了秦國的發展。李斯借助無可辯駁的事實有力地反問道:「客何負於秦哉?」假如這四位君主也「卻客不用」,那怎麼會有今天強大的秦國呢?李斯又以秦王對來自異國的明珠美玉,駿馬利劍、音樂、舞蹈、礦產、美女的喜愛為例,發問道,陛下並不因為這些所好不是秦國出產就捨棄不用,為什麼獨獨對客卿要一概驅逐呢?「逐客」將破壞秦國威望,從此天下背秦,這實際是拋棄百姓去資助敵國,排除「客」籍人才而去成就各諸侯國的功業,這決不是「跨海內製諸侯」的君主所應採取的態度,而是俗語所說的「借寇兵而齎盜糧」的做法。他由此得出結論,逐客之舉是既損害了人民,又資助了敵國,「內自虛而外樹怨」,破壞秦國統一天下的大好形勢。這對秦國來說簡直太危險了!李斯的上述議論表明,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如何對待外國異域人士的問題,而且涉及要不要廣泛地爭取人才,實現統一的大問題。很顯然,「逐客」與秦王橫掃宇內的既定方針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諫逐客書》一氣呵成,情辭懇切,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充分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深刻見解。秦王嬴政讀後,頗受感動,頓時醒悟,明白了利害得失,立刻廢除逐客令,並派人把李斯追了回來。當時,李斯由於對秦王嬴政的瞭解與信心,所以一路慢慢地走。追回的命令下達時,他才走到離京師不遠的驪邑(今陝西臨潼市東北)。這也說明李斯性格的機敏及其政治預見性。
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李斯挺身而出,呈上〈諫逐客書》,秦王是決不會輕易收回成命的。這一事件能否正確處理,保守貴族那閉塞的宗法統治能否被打破,對於秦王今後的事業能否成功,關係極大。正是由於秦王聽取了李斯的正確意見,保持了這種政策的連續性,廣泛地招攬外國異域賢士,使得當時各國的佼佼者都幾乎西奔入秦,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聚集在秦王周圍。李斯、尉繚之類的「士」人自不必說,就是在殲滅六國中戰功赫赫的王翦、王賁、王離、馮劫、李信、蒙武、蒙恬等武將,皆系異域之人。他們群集於秦國都城咸陽,呈現出「大略駕群才」的壯觀局面。這期間雖然曾有一段荊軻刺秦王的插曲,秦王嬴政本人幾乎喪命,但一直未動搖他對外國異域人士的信任和重用。若無這些來自異域的文臣武將的協助策劃,秦王要迅速實現「六王畢,海內一」的目標是不可能的。李斯的〈諫逐客書》,預示了秦國將要改變歷史航向而一統天下的輝煌前景,具有深遠的意義。
李斯的直言進諫既保住了客卿在秦國的地位,也為他在秦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秦王嬴政也因此更加器重李斯,並很快把他提升為廷尉。廷尉是主管全國刑獄的長官,又是朝廷的所謂九卿之一,對國家的基本決策有重要的發言權。
李斯傳
王振富
李斯(西元前?年~西元前二〇八年)是秦朝重臣,兩朝元老,幾與秦王朝的興亡相始終。他既是興秦的元勛,也是亡秦的罪臣,這就形成了他獨特的風貌。他一方面通過不遺餘力的政治實踐,輔佐秦始皇兼併六國,為建立和鞏固統一的封建國家縱橫捭闔,功勛蓋世;另一方面,他毫不掩飾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為維護榮華富貴而不惜向惡勢力屈膝,終於身敗名裂,又充分暴露了他醜陋和自私的一面。因此,他對秦王朝的短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斯是一個謀略出眾且又複雜多變的人物。他的一生,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為後人昭示了身敗名裂的深刻教訓。
一、奮發進取求功名
戰國時期,歷史正處於一場社會大變革之際。自春秋以來,人民群眾飽受分裂戰亂之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要求儘快結束列國紛爭的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各國統治階級出於對土地、人口、財寶無止境的追求,互相兼併,你爭我奪。這種紛亂的時局,為那些欲建功業之士提供了活動舞台。就在七雄並爭的戰國末期,李斯出生於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的一個平民家庭。
李斯年輕時曾做過郡中小吏,即管理鄉文書的辦事員。小吏的地位低下,侍奉長官,唯恐有所閃失,滿懷理想與抱負的李斯自然不甘久居其位。有一天,他看到官舍廁所中的老鼠偷吃糞便,一旦人來狗咬,立刻驚恐萬狀,倉皇逃竄。他又來到官倉中,看到這裡的老鼠很自在地吃著糧食,住著高大寬敞的庫房,盡情享受,公然出入,根本不害怕人來,也不用擔心有狗來咬。兩相對照,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斯由此及彼,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老鼠處於不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有君子小人之別,就像老鼠一樣,在於自己選擇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這就是說,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就應該像在官倉裡偷吃糧食的老鼠,這樣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戰國時期人人爭名逐利的情況下,李斯也不滿於布衣或小吏的處境。他決心拋開貧賤,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在李斯眼裡,人生最大的榮耀莫過於取得高貴的身份,最大的快樂莫過於享受榮華富貴。在李斯的胸中,雄心與野心混合在一起,化為一團追求功名富貴的熊熊燃燒的慾望之火。
「學而優則仕」,李斯很懂得這句話的含義,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李斯為了改變生活航向,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通常的道路,即先投師受教。因此,李斯辭去了郡小吏的職務,遠離家鄉,來到千里之外的齊國蘭陵(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求學,拜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大師荀況為師。荀況,史稱荀卿或孫卿,人尊之為荀子。他是戰國晚期新興地主階級的理論代言人,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荀況的學說雖然仍以孔子為宗,但又結合戰國時期變化了的形勢,對儒學進行了發揮和改造,因而很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統一天下的形勢需要。從荀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來看,他把儒學的「禮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結合在一起,即後人所說的「儒中有法」。李斯投師荀況門下,主要著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如何滿足君主的擴張慾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學說。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韓非。他們都拋棄了老師的儒家仁義道德,而吸收他那符合法家理論的「帝王之術」。後來,韓非終於成為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化理論為實踐,成為真正實現法家理想的政治家。李斯學成之後,反覆思考應該到哪個地方才能顯露才幹。他想效力於自己的國家楚國,又眼看著楚國江河日下,楚王已難有作為。其他東方各國也正在走下坡路,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只有秦最強盛,顯得朝氣蓬勃,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初步條件。於是,李斯決定西入秦國,一試身手。臨行之前,荀卿曾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態:「我聽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現在各國都在爭雄,這正是遊說之士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王羽翼豐滿,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人生在世,卑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莫大的悲哀。一個人總處於卑賤窮困的地位,那是會令人譏笑的。處士橫議而又說自己羞於富貴,如此『無為』,只是掩飾自己無能的表現,這是不合人之常情的,更不是讀書人的想法。我將到秦王那裡以取富貴。」李斯公然摒棄禮義,毫不虛偽,追求功利,這正是他的品性。這種強烈而褊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為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是這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視野,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選擇,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個人悲劇。
秦莊襄王三年(西元前二四七年)五月,李斯來到秦國時,正值莊襄王病死,十三歲的嬴政(秦始皇)即位,相國呂不韋總攬朝政。因此,李斯就去投靠呂不韋,成為呂門「舍人」,也就是門下的食客。當時,諸侯貴族養士之風甚盛,呂不韋也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中,李斯很快顯露出才華,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呂不韋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裡,擔任郎官,郎官雖然品級低微,職責是守護宮門,侍衛人君,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但由於職務之便,李斯有了接近國王的機會。
在此期間,天下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韓國入朝稱臣,魏亦舉國聽命於秦。這一年,雖有魏國信陵君率五國聯軍偶敗秦將蒙驁,實為迴光返照,垂死掙扎而已。而秦國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歷經惠王、武王、昭王、文王、莊襄王六世,國力大增,兵強民富,實力遠遠超過了東方六國。秦統一宇內的形勢已經基本形成。當時秦王嬴政雖然年輕,但志向遠大,思想活躍,在丞相呂不韋的輔助下,正在為統一全國做準備。對此,李斯也和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一樣,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認準時機,及時地提出謀略和方案,為秦王獻計獻策。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個向秦王上書的機會,便立刻提出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的戰略建議。這封上書以簡潔明晰的語言剖析了形勢變化,以推動秦國加快統一六國的步伐。李斯綜觀時局,既指出了此時正是兼併六國的良機,又指出了倘若坐失良機,有諸侯復強的危險,精闢而透澈。果然,這封奏書正合秦王嬴政的心意,也是眾大臣日思夜想的主要問題,秦王不能不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於是「乃拜李斯為長史,聽其計」。
李斯剛從東方來,對那裡各國政權的腐敗和君臣離心的狀況瞭如指掌。他建議,暗中派遣能言善辯、巧於謀略的官員,各帶金銀財寶,去遊說諸侯。各諸侯國的大臣權貴如果貪財,就行賄收買;如果不為金錢所動,就派刺客把他殺掉。總的謀略是遠交近攻,並利用一切手段,在六國君臣之間挑撥離間,破壞其團結,使其內部越來越亂,然後等待機會,派出良將勁旅各個擊破。秦王嬴政聞言大喜,更加信任李斯,不久便提升他為客卿。客卿是秦國專為從別國來的人才而設置的高級官位。李斯躋身於客卿之列,終於可以與國王和眾大臣共謀國家大事了。
在以秦王嬴政為首的決策層中,李斯占有重要的一席。他雖未能像王翦等武將那樣,率領大軍,開赴前線,效命疆場,但作為秦王的謀士,他參與了整個統一戰爭的重大決策。東方諸國疆域廣大,犬牙交錯,強弱不一,情況複雜,統一戰爭應從何著手,必須有一個全面規劃。正是李斯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擬定出了攻滅六國的戰略決策,即由近及遠,避實就虛,選擇弱點,正面突破,先滅掉韓,再掃兩翼,最後消滅齊國。以後統一戰爭的進程說明,這個策略十分正確。
同時,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戰爭固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是,還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與之配合,如設法從內部瓦解,渙散敵國的軍事力量,使其失去抵抗力等,從而使戰爭更加順利地進行。這時候,李斯的策略就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趙國名將李牧,曾兩次擊退秦軍的進攻,趙國將亡,他還率領趙軍,堅持抵抗秦軍達一年之久。於是,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國派人持金玉收買權臣郭開。郭開在趙王面前誣告李牧勾結秦國,陰謀反叛。趙王中計,殺死李牧,自毀長城,秦軍乘亂進攻,不久就滅了趙國這個勁敵。又如在最後滅齊的過程中,由於秦已用金錢收買了齊的相國後勝,因此他一再向齊王保證,秦決不會來攻齊國。正是在這種麻痺鬆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秦國毫不費力地就把偌大一個齊國滅亡了。在這期間,秦國基本上是按照李斯的戰略安排逐步吞食六國,從而大大加快了統一戰爭的進程。正是由於這一策略的成功,秦王嬴政才得以「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而李斯也贏得了秦王的信賴,官位不斷陞遷,逐漸成為秦國決策的主要人物。
二、上「諫逐客書」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風順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政治生涯。
秦國和關東諸國相比,一向重用外來人才。自商鞅變法後,秦國地位蒸蒸日上,更吸引了大批關東士人入秦。這對秦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但同時也引起了秦國一些舊貴族的忌恨。秦王嬴政元年(西元前二四六年),韓國因為抵抗不住秦國的進攻,就派「水工」(水利專家)鄭國去「間秦」,慫恿秦王修築一條溝通涇河與洛河的渠道,引涇水灌田,幹渠長三百多里,即歷史上著名的「鄭國渠」。韓國的本意是想使秦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疲勞不堪,騰不出手來再向東征伐,以便暫時減輕秦對韓的軍事壓力。此術之愚蠢,猶如以肉投虎,雖然耗費了秦國十年之功,卻可灌溉田地四萬餘頃,從此「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國更加富強,為兼併戰爭做了充足的物質準備。正如鄭國後來所說的:水渠修成,「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渠將修成,鄭國的間諜身份也暴露了,秦國上下一片嘩然。接著,秦王嬴政九年(西元前二三八年),長信侯嫪毐發動叛亂。次年,又查明相國呂不韋與嫪毐之亂有關,遂罷斥其相。鄭國、呂不韋都不是秦國人,這就為一向守舊的宗室大臣提供了藉口。他們本來就對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滿,認為大量異國異姓的人充塞秦國上下,堵住了他們的仕途,因此乘機推波助瀾,在秦王面前煽動:「一切在秦做官的外來人都是間諜,是為其本國利益來破壞秦國的。請把他們一概驅逐出境,免貽後患。」秦王嬴政對此也不能不加懷疑,於是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逐客令」,「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作為楚人的李斯,當然也在被逐之列。
當時的李斯已到中年,是個頗有影響的客卿,成為被驅逐的重點對象。眼看自己的前途將被斷送,李斯心有不甘,他很清楚,這種缺乏遠見的偏激行為,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業也相當不利,甚至有可能引起國內的動亂,削弱秦國實力。於是,在被逐的路上,李斯毅然向秦王上書,力請改變逐客的決定。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諫逐客書》。
〈諫逐客書》一文洋洋灑灑,多用排比句式和形象比喻,並巧於運用虛詞助字作轉折過渡,來增加文章氣勢和襯托作者的精神。文章思想犀利,邏輯性強,很有說服力。文章開宗明義:「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針鋒相對,觀點鮮明。接著,李斯用透澈、明快、雄辯、激切的言詞,連物比類,就秦國本身發展的歷史事實,歷述異國人的豐功偉績和關鍵作用。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是強秦的奠基之君,他從西戎迎來由余,從宛地(今河南南陽)得到百里奚,從宋國招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這五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兵強國富,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同盟,迫使他們一個個西面事秦。秦昭王得到魏國人范雎,計除秦國王廷上專權的親貴大臣魏冉,加強了王權,併吞食諸侯,奠定了秦國帝業的基礎。上述四位國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大大促進了秦國的發展。李斯借助無可辯駁的事實有力地反問道:「客何負於秦哉?」假如這四位君主也「卻客不用」,那怎麼會有今天強大的秦國呢?李斯又以秦王對來自異國的明珠美玉,駿馬利劍、音樂、舞蹈、礦產、美女的喜愛為例,發問道,陛下並不因為這些所好不是秦國出產就捨棄不用,為什麼獨獨對客卿要一概驅逐呢?「逐客」將破壞秦國威望,從此天下背秦,這實際是拋棄百姓去資助敵國,排除「客」籍人才而去成就各諸侯國的功業,這決不是「跨海內製諸侯」的君主所應採取的態度,而是俗語所說的「借寇兵而齎盜糧」的做法。他由此得出結論,逐客之舉是既損害了人民,又資助了敵國,「內自虛而外樹怨」,破壞秦國統一天下的大好形勢。這對秦國來說簡直太危險了!李斯的上述議論表明,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如何對待外國異域人士的問題,而且涉及要不要廣泛地爭取人才,實現統一的大問題。很顯然,「逐客」與秦王橫掃宇內的既定方針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諫逐客書》一氣呵成,情辭懇切,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充分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深刻見解。秦王嬴政讀後,頗受感動,頓時醒悟,明白了利害得失,立刻廢除逐客令,並派人把李斯追了回來。當時,李斯由於對秦王嬴政的瞭解與信心,所以一路慢慢地走。追回的命令下達時,他才走到離京師不遠的驪邑(今陝西臨潼市東北)。這也說明李斯性格的機敏及其政治預見性。
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李斯挺身而出,呈上〈諫逐客書》,秦王是決不會輕易收回成命的。這一事件能否正確處理,保守貴族那閉塞的宗法統治能否被打破,對於秦王今後的事業能否成功,關係極大。正是由於秦王聽取了李斯的正確意見,保持了這種政策的連續性,廣泛地招攬外國異域賢士,使得當時各國的佼佼者都幾乎西奔入秦,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聚集在秦王周圍。李斯、尉繚之類的「士」人自不必說,就是在殲滅六國中戰功赫赫的王翦、王賁、王離、馮劫、李信、蒙武、蒙恬等武將,皆系異域之人。他們群集於秦國都城咸陽,呈現出「大略駕群才」的壯觀局面。這期間雖然曾有一段荊軻刺秦王的插曲,秦王嬴政本人幾乎喪命,但一直未動搖他對外國異域人士的信任和重用。若無這些來自異域的文臣武將的協助策劃,秦王要迅速實現「六王畢,海內一」的目標是不可能的。李斯的〈諫逐客書》,預示了秦國將要改變歷史航向而一統天下的輝煌前景,具有深遠的意義。
李斯的直言進諫既保住了客卿在秦國的地位,也為他在秦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秦王嬴政也因此更加器重李斯,並很快把他提升為廷尉。廷尉是主管全國刑獄的長官,又是朝廷的所謂九卿之一,對國家的基本決策有重要的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