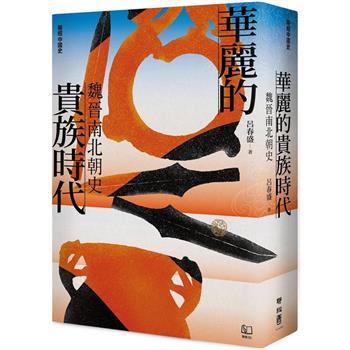導言
魏晉南北朝作為夾在秦漢帝國與隋唐帝國之間,一段長達四百年動盪不安的年代,常被形容為中國歷史曲線上兩次高峰間的低谷。在傳統的「治亂史觀」下,被認為是一個黑暗的分裂時代,是一段只有戰亂沒有光彩的年代。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誤解。其實魏晉南北朝儘管政治動盪,但在社會經濟、學術、宗教以及文化藝術各個層面,都是多彩多姿的。
一、政權分立與均勢演變
政權分立與「分合史觀」的謬誤
東漢靈帝光和七年(一八四)爆發了黃巾之亂,導致漢帝國走向崩潰,歷經群雄割據,最終形成魏、吳、蜀三國鼎立。再經數十年的演變,由司馬氏的西晉再造一統。然而,西晉王朝短暫承平不到十年,就因政爭導致八王之亂, 再引爆永嘉之亂。司馬氏流寓江東,成立東晉政權,華北則陷入五胡政權的統治,此後大致維持南北對峙的情勢。南方在東晉之後,又歷經宋、齊、梁、陳四個王朝的遞嬗。北方則由後起的北魏鮮卑拓跋氏入主中原,後來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再各自演變為北齊、北周。最後北周滅北齊,隋文帝楊堅篡北周,又滅南朝的陳(五八九),結束了長久分立的局面。
魏晉南北朝政權分立,戰亂頻仍,令人眼花繚亂。相較於兩漢四百年的大帝國,以及其後三百年的隋唐帝國,確實可稱之為大分裂的時代。元末小說家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一句氣勢磅礡的名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深刻地影響後世,認為中國歷史演變是依循「統一」與「分裂」而循環,成為一種以大一統為常態的「分合史觀」。然而,小說家之言雖然精彩動人,但不應該盲目地奉為金科玉律。就邏輯上而言,「分合史觀」可說是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y),即恆真式,因為就狀態而言不是分就是合,因此到底多久會分?多久會合?如果不說清楚「多久」,就是詭辯。而且這種史觀只拘泥於形式,完全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實質內涵,無意中陷入了「形式論」的謬誤。何況就世界史的經驗來看,「分合史觀」也不是普遍的法則,譬如歐洲的「天下」,就無法用「分合史觀」來理解了。
至於把「分裂的時代」進一步認定為「黑暗的時代」,則可能是受孟子思想「一治一亂」、「天下定於一」(《孟子.滕文公下》)的影響。事實上不論政治上是否維持統一的秩序,都不必然決定歷史其他方面的走向。換言之,政治上的動盪不安,不必然會導致文化的黑暗。譬如孟子自認所處是「禮樂崩壞」(封建體制瓦解)的「一亂」時代,但從後世來看,當時在文化上卻是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的古典黃金時代。同樣的,儘管魏晉南北朝在政治上確實是動亂不已,但也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次文化輝煌燦爛的時代,此點稍後再述。
由均勢平衡論大分裂
話再說回來,探討東漢帝國崩潰之後何以迎來四百年的大動亂,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從外在形勢來看,這四百年的大動亂可簡單地由國際政治的均勢平衡來解釋。兩漢以前,中國政治經濟的重心在華北,因此統一華北即意謂著新王朝即將成立,然而三國時代曹魏統一華北,卻無法併滅孫吳與蜀漢,這又是為什麼呢?略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四個財富區,即(一)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二)以冀州為中心的關東地區、(三)以揚州、荊州為中心的東南地區、(四)以益州為中心的西南地區。三國的鼎足實際上是南北各二個財富區對峙的均勢平衡,後來蜀漢被滅而均勢破壞,才會有西晉的統一。
永嘉之亂後,東晉主要據守江南,巴蜀另有成漢,華北則有前、後趙的對立,形成四方對峙的平衡。前趙併後趙,經過後趙末年的動亂,最後由前秦苻堅統一華北。南方則東晉併滅成漢,與前秦形成南北對峙的平衡。
淝水之戰後,華北再度陷入分裂。東晉趁勢追擊到黃河以南,但是內部隨即陷入政爭,並引爆孫恩之亂,最後由北府兵將領出身的劉裕平亂,進而篡東晉,建立南朝的劉宋政權。北方經過一段混亂,由後起的鮮卑拓跋氏入主中原。局勢又回到南北對峙的平衡。
到了北魏末年爆發六鎮之亂,北魏分裂為東魏與西魏,而與南朝的梁國再度形成三足鼎立,可稱之為「後三國時代」。東、西魏互爭正統,形同水火,東魏交好梁國又連結塞北的柔然、青海的吐谷渾,對西魏形成四面包圍之勢。西魏實力最弱,猶如三國時期的蜀漢。但東魏始終未能併滅西魏,而南朝梁國也沒有積極進取,因而維持三足鼎立。
六世紀中葉,整個形勢又有了大變化。南方爆發侯景之亂後,由陳霸先收拾殘局建立的陳國,已失去江北、巴蜀之地。華北則演變為北齊、北周,雖然仍是三足鼎立,但是由西魏蛻變的北周,已攻取巴蜀之地,領土貫穿關中與巴蜀二個財富區,三百多年前蜀漢諸葛亮試圖由巴蜀北伐關中沒有成功,如今西魏宇文泰卻由北而南完成了。北周聯合新興的突厥威脅北齊,後來滅了北齊,形成對陳三面包圍,均勢平衡的局面再遭破壞,最後由篡北周的隋文帝楊堅滅陳,重歸一統。
以上的均勢平衡與破壞,只是就「中國本部」概要言之,若再把東亞與北亞的情勢考慮進來,則更為複雜。近代日本、韓國學界多留意中原動亂對東北亞地區的刺激,以及東亞歷史世界的形成問題,就是跨越「中國本部」,而關切整個東亞歷史的發展。
均勢的演變,看似雜亂無章,但仔細觀察仍有脈絡可循。大致上,力圖突破平衡的力量主要來自北方,一方面當時北方仍為政治經濟的重心,在生產秩序逐漸恢復後,客觀實力上對南方仍然保有優勢;另一方面,北方政權無論是西晉司馬氏、胡族君主或隋文帝楊堅,主觀上都有較為強烈的南侵野心。相對的南方政權則漸趨保守,因此雖然局勢一再重整均勢平衡,但北強南弱的氣勢仍然一再破壞平衡,而這種均勢平衡與破壞的一再拉鋸,遂造成長達四百年的動盪局勢。
以上只是從外顯形勢來說明而已,如果要再深入解釋長期動亂的原因,勢必要再追察造成均勢平衡與破壞的複雜因素,而這些複雜因素,多源自於兩漢以來深藏於社會底層的種種矛盾,可簡單歸結為「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嚴重的民族矛盾」兩大問題,而這也是魏晉南北朝的另一項時代特色。
二、社會階層分化與民族矛盾
社會階層的分化
兩漢四百年相對和平的統治,社會經濟的發展雖然累積了巨大的財富,但也導致土地兼併、貧富差距的擴大,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地方社會形成擁有大量土地的各種形態的豪族階層。又由於漢武帝之後「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考試及格就可當官(通經致仕),因而也出現許多知識官僚階層。其結果是原本以龐大庶民百姓(編戶齊民)為主的社會結構(即一君萬民),發生巨大的變化,社會上出現許多具有地方勢力或深具民望的領導階層。這種發展趨勢在魏晉南北朝達到最高點,傳統史書對其較上層者多以門閥、門第或士族(甲族、膏腴等)稱之,日本學界則多以貴族稱之;至於地位稍次者,則又有豪族、豪強、大姓、寒門等等稱呼。
由於門閥貴族利用曹魏以來的選官制度「九品官人法」,長期任官而維持權勢,造成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士庶天隔」的現象,因此這個時代又被稱為門第社會的時代或貴族時代。
另一方面,一般「編戶齊民」的小自耕農,由於疾病或天災等種種原因而出售土地,成為半自耕農或「無產階級」,淪落為大地主的佃客、部曲、奴客、奴僕而賤民化。再加上長期的動亂,大量的流亡人口投靠豪門,社會的中上階層都掌握著大量的依附人口,甚至後來佛教發展出寺院經濟,也有大量的依附人口,都不在朝廷掌握的戶籍之中,政府的稅基也因此大量的流失。
社會階層分化與長期動亂的關係
據《通典.食貨》記載,東漢桓帝永壽三年(一五七)約有一千零六十八萬戶、五千六百四十九萬口,但到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再統一時,只剩約二百四十六萬戶、一千六百一十六萬口。一百多年間,戶數減少超過四分之三,人口減少超過三分之二。其中固然有部分是死於戰亂、饑荒或疾疫,但更多的是投靠豪門,成為隱藏性的戶口。因此這時期的政治可說是帝王與門閥豪族瓜分戶口而治的政治,當彼此的利益激烈矛盾,常導致政爭或動亂。總之,此時期的社會階層分化,衍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乃是造成長期動亂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民族矛盾的由來
兩漢以來盤據在邊地的外族非常複雜,漢帝國對外的擴張,不論是征服外族或接納外族來降,最後都衍生出「少數民族」問題,成為帝國的隱憂。以西南邊的羌族為例,早在東漢之初,《漢書》作者班固的父親班彪就曾上書說:「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後漢書.西羌傳》)
再以南匈奴為例。南匈奴來降之初,漢以「客禮」待之,尊匈奴單于位在諸侯王之上。但是魏晉以後南匈奴地位日益低下,匈奴貴族形同帝國屬下的官僚。一般匈奴民眾漸習農耕,或農牧並行,但遇荒年天災不免貧困,經常遭受地方官吏的剝削,或受地方豪強的欺壓,以致有淪落到賣身為奴的悲慘境地。西晉末年南匈奴貴族劉宣鼓動劉淵起兵時,曾說:「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晉書.劉元海載記》)充分顯示「少數民族」淪落到奴隸般的命運。
據日本學者田村實造的估計,四世紀到六世紀約有一千萬的匈奴、烏桓、鮮卑、氐、羌(即所謂的五胡)等民族移動,潛居華北,其人口之多、規模之雄偉,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可比擬歐洲史上日耳曼民族的大移動。或許民族移動的數量有所高估,但即使是打個折扣仍然是很驚人的。
民族矛盾與長期動亂的關係
基本上,「五胡」起兵帶來的「永嘉之亂」,以及隨後牽動的南北民族大移動,都可以看做是漢帝國對外擴張帶來的後遺症,或者說是漢帝國對四邊擴張的反作用力。如上述帝國內的「少數民族」,數百年來遭受到奴隸般的壓迫,民族矛盾形同潛藏的火藥庫,因此傳統所謂的「五胡亂華」,實際上是被奴隸的「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
此時胡族進入華北已數百年,既已習得農耕生活,又長期受到漢文典籍的影響,具有大一統的中華帝王思想。因此他們起兵叛變後,並不想要回到塞外再過游牧生活,而是要在中原建造統治包括胡漢的大一統帝國。然而,胡漢之間長期累積的矛盾與仇恨,並不是那麼容易化解的,因此這個時期的民族衝突此起彼落,如何超越胡漢之間的藩籬反而是有作為的胡族君主的歷史課題。像後趙石勒、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無不致力於「民族融合」的政策,包括任用漢人、採用漢人制度、推行儒教等等,一般泛稱之為「漢化」政策。
話再說回來,不論胡族君主本身如何的「漢化」、實行多少的「漢化」政策,胡族國家的主體性仍然在胡族。因此當漢族勢力威脅到胡族統治時,其血腥鎮壓絕不手軟,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屠殺漢族名門崔浩的「國史之獄」,「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魏書.崔浩傳》)。另外,華北的民族衝突不限於胡漢之間,各胡族彼此之間的衝突也非常激烈,譬如前秦在淝水戰敗之後,內部各種胡族勢力趁機叛離,帝國也隨即土崩瓦解。
華中、華南的民族問題,又是另一番景象。華中、華南的非漢族土著族群(蠻、越、俚、獠、溪等等),在總人口數上雖然遠多於漢族,但由於地形多山川沼澤、部落組織鬆散、缺乏有力的政治組織,大多處於被漢族分化統治的狀態。早在三國時代的孫吳政權,就對土著「山越」展開大規模的征討,掠奪其土地與人民,動輒數以千計的斬殺,大肆搜括人口,「彊者為兵,羸者補戶」(《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永嘉之亂後大舉南逃的北方漢族,在大致上是孫吳舊境的華中、華南地區建立東晉流亡政府,其領導階層被稱為僑姓士族,把持政經大權,壓抑吳人。即使到了南朝,連南方的吳姓士族也還是受到壓抑,更何況是居於社會最底層的非漢族土著,幾乎是永不得翻身。
東晉南朝政權以開發之名,對非漢族土著進行無止境的搜括與屠殺。其慘烈之狀,梁代沈約在《宋書.夷蠻傳》記載,劉宋將領「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連孩童老人都一律斬殺,沈約行筆至此,也為之鼻酸。
總之,當時的北方與南方民族矛盾都非常嚴重。不論是忙於解決內部的民族矛盾,或抵禦外部不同民族政權的侵略,都是造成這個時期動亂的結構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