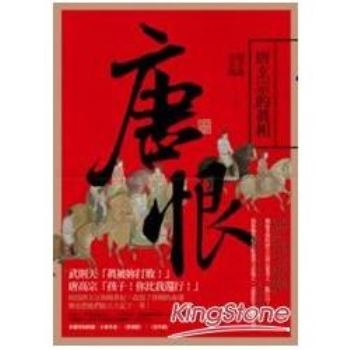選自〈十四、張九齡與李林甫〉
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十月初二日,京師長安發生了震級不算很高的地震,似乎是在輕輕召喚已經離開它兩年零十個月的遊子歸來。也實在是巧合,就在這一天,玄宗改變了來年二月西返的決定,提前離開了洛陽。不想這一去竟是永別東都。儘管開元二十六年玄宗還下過在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上作行宮的詔令,想為來往於兩都之間做好準備,但事實上,玄宗再也沒有來過東都。由於關中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玄宗可以久居長安,不用再當「逐糧天子」了。除華清宮和長安城郊的苑圃,他甚至連長安城也沒有遠離過。
十月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長安。回到長安不到一個月,他對宰相人事做了重大的變動。十一月二十七日,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左僕射),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解除了他們的宰相職務。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從此,李林甫掌握中樞大權達十六年之久。
張九齡的下臺和李林甫的上臺都不是偶然的。
張九齡是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市)人,進士出身,又應制舉登第。以文學為張說所親重,張說常對人說:「後來詞人稱首也。」曾不止一次向玄宗推薦他堪為集賢院學士,以備顧問。張說死後,張九齡服母喪尚未期滿,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就被重新任命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第二年四月,遷中書令,成為朝政的主要執掌者,首席宰相。
玄宗欣賞張九齡的器識、文辭和風度,曾經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事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早朝時玄宗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百官,對左右說:「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來用人時也常問:「風度得如九齡否?」但對九齡事事固執己見,卻是越來越不耐煩了,玄宗要以李林甫為宰相,張九齡薄其無文,對玄宗說:「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
張守珪調任幽州節度使後,大破契丹,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迅速扭轉了東北邊的緊張形勢。玄宗欣賞張守珪的才幹,欲任為宰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不同意玄宗的意見。玄宗退而求其次,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張九齡也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而加以反對。
在討擊奚、契丹時,安祿山恃勇輕進,為敵人所敗。玄宗惜安祿山之才,免其死罪,「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張九齡也以「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而固爭。
玄宗欲廢太子瑛,張九齡對玄宗說得就更難聽了,使玄宗表現了明顯的不快。
在玄宗和張九齡君臣的衝突中,除了太子問題外,都是圍繞著獎勵軍功、重用吏幹之士進行的。隨著邊疆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矛盾的發展,玄宗的注意力越來越轉移到邊事和現實問題的解決上。張九齡的意見雖然不是每次都被玄宗拒絕,但他們在政事上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了。
這樣的爭論,一次比一次激烈,隨著爭論的逐步升級,張九齡作為首席宰相中書令的權力也在逐步滑失。張九齡以其文人的敏感,深深感到自己地位的不穩。開元二十四年夏他借玄宗賜宰相白羽扇的機會,作〈白羽扇賦〉獻給玄宗,最後寫道:「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玄宗看到後,敕報曰:「朕頃賜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揖篋笥,義不當也。」表示對張九齡沒有棄而不用,要他不要多心。八月初五日玄宗過生日,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獨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要玄宗以歷代興亡為鑑,玄宗也賜書褒美。玄宗對張九齡老是反對他的意見雖然有些厭煩,對李林甫的信任也在迅速地增加,但還沒有把張九齡一腳踢開的意思。他還是想把開元九年召回張說後同時任用文學之士張說和吏幹之士宇文融這樣兩套人馬的格局保持下去。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回到長安後,玄宗欲以曾在河西頗有建樹的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為尚書。牛仙客,涇州鶉觚(今甘肅靈臺)人,初為縣小吏,後以軍功吏幹,由州司馬而節度判官,蕭嵩為相時薦為河西節度使。仙客在軍,清勤不倦,倉庫盈滿,器械精良。玄宗派人核查後,對他甚為讚賞,欲任命為尚書,張九齡反對;欲加實封,張九齡還是反對。李林甫乘機對玄宗說:「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玄宗聽後很高興,第二天又對張九齡提及要給牛仙客加實封。張九齡固執如初。玄宗大為惱怒,變色道:「事總由卿?」(什麼事情都要依著你嗎?)並責問說:「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張九齡慌忙回答說:「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下朝後,李林甫對玄宗說:「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經李林甫這麼一說,玄宗不顧張九齡的反對,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賜牛仙客爵陝西縣公,食封三百戶。四天後,二十七日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耀卿、張九齡同時罷相。
這次人事上的變動和開元十四年四月崔隱甫、宇文融、李林甫共同奏彈張說,把張說拉下中書令的位置頗有一些類似。不同的是那一次是雙方各為朋黨的結果,玄宗對兩派全都斥而不用。而這一次,李林甫立即被任命為中書令,執掌了政府大權。這是文學和吏治兩派大臣長期鬥爭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所謂文學,如前所述,指進士和其他科舉出身,長於文學之士;吏治,指長於吏幹,富有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人才。他們之間的鬥爭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玄宗即位後姚崇和張說之間的矛盾雖然是圍繞著穩定皇位展開的,但已隱藏著文學、吏治之爭的萌芽。在以前,兩派的鬥爭中,大多是圍繞某一具體政策或政治措施如括戶之類進行的,皇帝還凌駕於兩派之上,處於超然的地位。而這一次,鬥爭不僅在李林甫和張九齡之間進行,而且皇帝也直接成為衝突的一方。鬥爭的內容也不僅和人事安排有關,而且直接和用人標準聯繫起來。在是否提拔和重用牛仙客的爭論中,玄宗提出了「有無門閥」這個南北朝沿襲下來的傳統的用人標準。這主要是為了堵張九齡的口,在實際用人中他並沒有按這個標準行事。張九齡提出文學,李林甫提出材識,其實是正在發展的才學標準的兩個方面,本來是不矛盾的,而張、李卻各執一端,恰恰反映了當時官吏素質上的缺陷和官僚隊伍中的一些內在矛盾。
張說、張九齡雖然由文學、科舉出身,但由於他們是在武則天時期培養和選拔出來的,而當時僅有文學而無政事是很難擠進高級官僚隊伍的。因此,他們除了具有卓越的文學才能,同時也具有經世治國的政治才能。張說不僅是一代文宗,而且出將入相,對政事和軍事都很熟悉。張九齡雖然在總體素質上已不如張說那樣能文能武,但還是具有獨立的政治見解。而開元時期科舉出身的文學之士,由於玄宗粉飾文治,由於張說提拔文士,其中一些人即以文學才能而做到中書舍人一類的高官。因而「掌綸誥」。替皇帝起草詔敕,便成為文士最大的榮耀和最後的歸宿。開元二十三年孫逖掌貢舉,「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張九齡也是以「踐臺閣,掌綸誥」來作為自己擔任宰相的同義語。在這樣的風氣下,一般文士雖然具有文學才能,但是他們「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不學習儒家經典,歷史知識也很貧乏,對於政事就更不那麼內行了。而開元中期以後,政事日益紛繁,邊疆日益緊張,制度需要不斷調整,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這些又是大多數文學之士不願也無力解決的。這不僅是由於他們的素質,而且是因為他們代表了那些在唐朝興起、並已取得了政治經濟權勢的上層地主官僚。他們不僅要求在農村繼續實行高宗、武則天以來的放縱政策,而且反對一切損害他們政治經濟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張說反對過括戶,張九齡曾請不禁私鑄錢,而對一切具有變革舊制意義的措施,他們也都採取消極態度。這樣,把開元中期開始的各項變革繼續下去並加以總結、規範的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以李林甫為代表的吏治派官吏身上。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門蔭出身。開元初先後為太子中允(正五品下)、太子諭德(正四品下),後為國子司業。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引為御史中丞,共同傾倒了中書令張說。正是在文學和吏治兩派官吏的鬥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李林甫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開元二十年前後,李林甫由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協助宰相兼吏部尚書裴光庭行用循資格。當時通過流外入流和各種途徑獲得做官資格的達兩千餘人,而每年需要補充的官吏在六百人上下,因此,得到一個官職是很不容易的,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即使做了官,升遷也很困難,很多人老於下位。針對這種情況,裴光庭奏用循資格,規定各級官任職期滿後,需過一定年限,即若干選才能再到吏部應選,一般都可獲得官職並按年資逐步升級。這對於才俊之士固然是一種限制,但對長期得不到官職或沉滯下位的一般官吏,卻是一種福音。因此李林甫繼續行用循資格,自然得到廣大中下級官吏的支持,這就奠定了他日後大展宏圖的基礎。
在吏部侍郎任期內,李林甫「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玄宗把他提升為黃門侍郎。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又任命他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並為宰相。李林甫擔任宰相職務後,在由東都返回西京、太子廢立,特別是獎勵軍功、重用吏幹官吏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上都支持了玄宗。因而最後玄宗拋棄了張九齡而選中了李林甫去繼續進行各項制度的變革,並將之穩定下來。
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十月初二日,京師長安發生了震級不算很高的地震,似乎是在輕輕召喚已經離開它兩年零十個月的遊子歸來。也實在是巧合,就在這一天,玄宗改變了來年二月西返的決定,提前離開了洛陽。不想這一去竟是永別東都。儘管開元二十六年玄宗還下過在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上作行宮的詔令,想為來往於兩都之間做好準備,但事實上,玄宗再也沒有來過東都。由於關中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玄宗可以久居長安,不用再當「逐糧天子」了。除華清宮和長安城郊的苑圃,他甚至連長安城也沒有遠離過。
十月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長安。回到長安不到一個月,他對宰相人事做了重大的變動。十一月二十七日,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左僕射),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解除了他們的宰相職務。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從此,李林甫掌握中樞大權達十六年之久。
張九齡的下臺和李林甫的上臺都不是偶然的。
張九齡是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市)人,進士出身,又應制舉登第。以文學為張說所親重,張說常對人說:「後來詞人稱首也。」曾不止一次向玄宗推薦他堪為集賢院學士,以備顧問。張說死後,張九齡服母喪尚未期滿,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就被重新任命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第二年四月,遷中書令,成為朝政的主要執掌者,首席宰相。
玄宗欣賞張九齡的器識、文辭和風度,曾經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事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早朝時玄宗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百官,對左右說:「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來用人時也常問:「風度得如九齡否?」但對九齡事事固執己見,卻是越來越不耐煩了,玄宗要以李林甫為宰相,張九齡薄其無文,對玄宗說:「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
張守珪調任幽州節度使後,大破契丹,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迅速扭轉了東北邊的緊張形勢。玄宗欣賞張守珪的才幹,欲任為宰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不同意玄宗的意見。玄宗退而求其次,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張九齡也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而加以反對。
在討擊奚、契丹時,安祿山恃勇輕進,為敵人所敗。玄宗惜安祿山之才,免其死罪,「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張九齡也以「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而固爭。
玄宗欲廢太子瑛,張九齡對玄宗說得就更難聽了,使玄宗表現了明顯的不快。
在玄宗和張九齡君臣的衝突中,除了太子問題外,都是圍繞著獎勵軍功、重用吏幹之士進行的。隨著邊疆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矛盾的發展,玄宗的注意力越來越轉移到邊事和現實問題的解決上。張九齡的意見雖然不是每次都被玄宗拒絕,但他們在政事上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了。
這樣的爭論,一次比一次激烈,隨著爭論的逐步升級,張九齡作為首席宰相中書令的權力也在逐步滑失。張九齡以其文人的敏感,深深感到自己地位的不穩。開元二十四年夏他借玄宗賜宰相白羽扇的機會,作〈白羽扇賦〉獻給玄宗,最後寫道:「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玄宗看到後,敕報曰:「朕頃賜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揖篋笥,義不當也。」表示對張九齡沒有棄而不用,要他不要多心。八月初五日玄宗過生日,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獨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要玄宗以歷代興亡為鑑,玄宗也賜書褒美。玄宗對張九齡老是反對他的意見雖然有些厭煩,對李林甫的信任也在迅速地增加,但還沒有把張九齡一腳踢開的意思。他還是想把開元九年召回張說後同時任用文學之士張說和吏幹之士宇文融這樣兩套人馬的格局保持下去。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回到長安後,玄宗欲以曾在河西頗有建樹的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為尚書。牛仙客,涇州鶉觚(今甘肅靈臺)人,初為縣小吏,後以軍功吏幹,由州司馬而節度判官,蕭嵩為相時薦為河西節度使。仙客在軍,清勤不倦,倉庫盈滿,器械精良。玄宗派人核查後,對他甚為讚賞,欲任命為尚書,張九齡反對;欲加實封,張九齡還是反對。李林甫乘機對玄宗說:「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玄宗聽後很高興,第二天又對張九齡提及要給牛仙客加實封。張九齡固執如初。玄宗大為惱怒,變色道:「事總由卿?」(什麼事情都要依著你嗎?)並責問說:「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張九齡慌忙回答說:「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下朝後,李林甫對玄宗說:「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經李林甫這麼一說,玄宗不顧張九齡的反對,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賜牛仙客爵陝西縣公,食封三百戶。四天後,二十七日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耀卿、張九齡同時罷相。
這次人事上的變動和開元十四年四月崔隱甫、宇文融、李林甫共同奏彈張說,把張說拉下中書令的位置頗有一些類似。不同的是那一次是雙方各為朋黨的結果,玄宗對兩派全都斥而不用。而這一次,李林甫立即被任命為中書令,執掌了政府大權。這是文學和吏治兩派大臣長期鬥爭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所謂文學,如前所述,指進士和其他科舉出身,長於文學之士;吏治,指長於吏幹,富有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人才。他們之間的鬥爭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玄宗即位後姚崇和張說之間的矛盾雖然是圍繞著穩定皇位展開的,但已隱藏著文學、吏治之爭的萌芽。在以前,兩派的鬥爭中,大多是圍繞某一具體政策或政治措施如括戶之類進行的,皇帝還凌駕於兩派之上,處於超然的地位。而這一次,鬥爭不僅在李林甫和張九齡之間進行,而且皇帝也直接成為衝突的一方。鬥爭的內容也不僅和人事安排有關,而且直接和用人標準聯繫起來。在是否提拔和重用牛仙客的爭論中,玄宗提出了「有無門閥」這個南北朝沿襲下來的傳統的用人標準。這主要是為了堵張九齡的口,在實際用人中他並沒有按這個標準行事。張九齡提出文學,李林甫提出材識,其實是正在發展的才學標準的兩個方面,本來是不矛盾的,而張、李卻各執一端,恰恰反映了當時官吏素質上的缺陷和官僚隊伍中的一些內在矛盾。
張說、張九齡雖然由文學、科舉出身,但由於他們是在武則天時期培養和選拔出來的,而當時僅有文學而無政事是很難擠進高級官僚隊伍的。因此,他們除了具有卓越的文學才能,同時也具有經世治國的政治才能。張說不僅是一代文宗,而且出將入相,對政事和軍事都很熟悉。張九齡雖然在總體素質上已不如張說那樣能文能武,但還是具有獨立的政治見解。而開元時期科舉出身的文學之士,由於玄宗粉飾文治,由於張說提拔文士,其中一些人即以文學才能而做到中書舍人一類的高官。因而「掌綸誥」。替皇帝起草詔敕,便成為文士最大的榮耀和最後的歸宿。開元二十三年孫逖掌貢舉,「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張九齡也是以「踐臺閣,掌綸誥」來作為自己擔任宰相的同義語。在這樣的風氣下,一般文士雖然具有文學才能,但是他們「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不學習儒家經典,歷史知識也很貧乏,對於政事就更不那麼內行了。而開元中期以後,政事日益紛繁,邊疆日益緊張,制度需要不斷調整,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這些又是大多數文學之士不願也無力解決的。這不僅是由於他們的素質,而且是因為他們代表了那些在唐朝興起、並已取得了政治經濟權勢的上層地主官僚。他們不僅要求在農村繼續實行高宗、武則天以來的放縱政策,而且反對一切損害他們政治經濟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張說反對過括戶,張九齡曾請不禁私鑄錢,而對一切具有變革舊制意義的措施,他們也都採取消極態度。這樣,把開元中期開始的各項變革繼續下去並加以總結、規範的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以李林甫為代表的吏治派官吏身上。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門蔭出身。開元初先後為太子中允(正五品下)、太子諭德(正四品下),後為國子司業。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引為御史中丞,共同傾倒了中書令張說。正是在文學和吏治兩派官吏的鬥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李林甫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開元二十年前後,李林甫由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協助宰相兼吏部尚書裴光庭行用循資格。當時通過流外入流和各種途徑獲得做官資格的達兩千餘人,而每年需要補充的官吏在六百人上下,因此,得到一個官職是很不容易的,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即使做了官,升遷也很困難,很多人老於下位。針對這種情況,裴光庭奏用循資格,規定各級官任職期滿後,需過一定年限,即若干選才能再到吏部應選,一般都可獲得官職並按年資逐步升級。這對於才俊之士固然是一種限制,但對長期得不到官職或沉滯下位的一般官吏,卻是一種福音。因此李林甫繼續行用循資格,自然得到廣大中下級官吏的支持,這就奠定了他日後大展宏圖的基礎。
在吏部侍郎任期內,李林甫「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玄宗把他提升為黃門侍郎。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又任命他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並為宰相。李林甫擔任宰相職務後,在由東都返回西京、太子廢立,特別是獎勵軍功、重用吏幹官吏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上都支持了玄宗。因而最後玄宗拋棄了張九齡而選中了李林甫去繼續進行各項制度的變革,並將之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