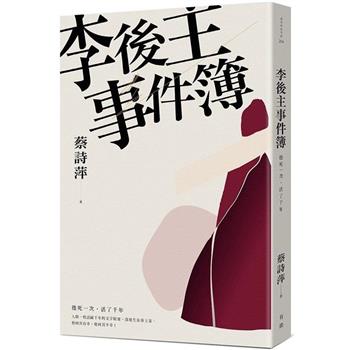【內文節選一】
問君能有幾多愁。他鑲嵌的文字直扣人心
為何千百年後我們每一顆受傷的靈魂,仍願隨著李後主的詞,詞裡的意境,詞句的節奏,而輕輕地擺盪,輕輕地被療癒呢?
大概是,李後主「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卻承受了命運最暴烈的撞擊。從帝王,淪為階下囚,備受屈辱吧。
他用文字,發抒了幽怨。由於天賦的異稟,這些文字,兀自有了頻率,始終能穿透時代,讓每顆有傷痕的靈魂,都能對他頻頻點頭,了然於心。
歷史上的亡國之君,處境比李後主更慘的,比比皆是。
宋朝重文輕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讓他享有「仁君」美名,免掉了不少皇帝誅殺開國元勛的暴戾之氣。繼承他大位的弟弟趙光義,「兄終弟及」,亦標榜文人治國,也不至於非要置李後主於死地不可。
李後主如果戒愼恐懼,甘心俯首稱臣,未必不能安然在大宋的國都裡,度過餘生。
麻煩就麻煩在,李後主「太文靑性格」了。
他如果像三國時期蜀漢的皇二代劉禪,安於現實,「樂不思蜀」,生命線理當不會停留在四十二歲上。然而,劉禪除了留下「扶不起的阿斗」名號外,還剩什麼?歷史提到他,還有什麼可資深掘的餘地嗎?
中唐詩人劉禹錫的《蜀先主廟》,最能代表這樣的感嘆:「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蜀漢故伎,舞於魏宮,換來的卻是故主劉禪的樂不思蜀,除了感傷,還能怎樣?
李後主不然。
他本身的心思,留在詞句裡,纏綿悱惻,淒涼糾結,激盪了後人更多的漣漪。而他的文靑風格,千餘年來,被不斷閱讀,被不斷按讚。
李後主詞,甚至被民國初年一代宗師王國維,評價為「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
啊不過是,一些些文字,依照詞牌的規格,把適當韻腳的字,一一塡寫進去,而且篇幅並不長,也就那麼些首,竟然就可以被推高到,宛如釋迦牟尼佛,宛如耶穌基督的宗教精神!
這評價,即便不免過譽,但至少表明了,文字創作的意境,是有著極為寬闊之能量的。
而千百年來,世人之所以一讀再讀李後主詞,早就不在意他是個不稱職的帝王,是個亡國之君了。
文字創作的地位,竟然可以超出世俗評價如此之高,怎麼不令人讚歎 !
但我們文靑的讚歎,對身為皇帝的執政者宋太宗,則可能嗅出某些「文字不服從」的味道,而深深引以為憂了。
宋太宗怕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那首〈虞美人〉吧。
我閉上眼,都可以背誦了。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樂不思蜀」的後主劉禪,若聽到這闋詞,妳覺得他會由衷感觸,潸然淚下嗎?
我想,肯定不會。
他不就是在曹魏的都城洛陽,大將軍司馬昭刻意安排的一場蜀樂演出中,當擧坐蜀漢舊臣都忍不住落淚時,他才說出那句傳世金句:「樂不思蜀」嗎?
妳可以說他傻人傻福,通過了司馬昭的「通關檢測」,但從人格特質來看,「阿斗」本來就不是聰慧敏感之人,他不必裝,他就是「傻人」於是「有傻福」啊!
但,李後主,怎麼可能「無感」呢?往事歷歷,要忘也忘不了,只好喝酒麻痹。但偏偏起了東風,故國景致,一一浮上心頭。景色依舊,人事全非。
妳能承受多少這樣的時空變遷,人事更迭,而我們已不再是「從前的我們」那般沁骨的傷痛呢?
聽在宋太宗耳裡,你還「故國」,你還「幾多愁」,你還要「春水向東流」哩,你去死吧!
但我們懂文學的,沒有掌權者一切以權力的思維做考量,於是乎,我們便更懂王國維的意思了。
李後主原意是透過詞句,舒展他眉宇之間的積鬱,誰知,塡詞一離手,抑揚頓挫之間,意境便情挑了千萬「傷心人」的靈魂。我們不管怎麼痛,都彷彿在李後主鑲嵌的字句中,輕輕被撫慰了。
他不是宗教領袖,他只是亡國之君、階下之囚,但他的詞,是在靈魂的黑白琴鍵上,直扣人心的撞擊。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字字,敲在靈魂上。
句句,敲在歷史上。
【內文節選二】
夜長人奈何。他的詞句盪漾著音樂
李後主的詞,是靈魂的黑白鍵上,直扣人心的撞擊。
寫詩塡詞的人很多,卻不是每個人,都有這能耐的。我是指,敲擊你靈魂,韻律你思緒的。
詩詞要直擊人心,用字遣詞一定要精準無比。不落俗套,或者落了俗但能翻新,亦可。
詞,跟詩不同。
詞,是用來搭配曲子,如同歌詞,要放進音樂的套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歌詞,雖有押韻的要求,但基本上作詞人相當自由。
塡詞,則恰恰相反,極不自由。
每一闋詞,都依照詞牌,在一定的規格下進行。例如,〈虞美人〉原本是曲調,為了能讓人隨曲而唱,就需要歌詞。於是〈虞美人〉便成了一首詞牌。任何人想寫歌詞都可以,但必須依照〈虞美人〉的規格公式,塡進適當的字。於是,宋朝詞人大概每個都寫過〈虞美人〉,即便李後主也不只一首〈虞美人〉。
問題來了,既然這麼多人寫,而且是在一套架構下你寫我寫他寫,前人寫今人也寫,寫到最後,會不會抄襲?會不會模仿?會不會詞窮?
我吿訴妳,還眞會。
這也是宋詞之後,明代、淸代,詞人難為的困境。每個詞牌,都被寫爛了啊!
我手上一套《全宋詞》,淸朝唐圭璋編著,共收錄了宋代詞人一千三百三十家,詞作兩萬一千一百一十六首。
想想看,同一闋詞,有多少名家寫過?
後代詞人想出頭天,多難啊。那些前代名家在同一詞牌下,塡過的詞,宛如大山,你要一一克服、超越,談何容易啊!反過來講,即便你是開山祖師,但在後代名家紛紛加入戰局後,你寫的詞,能否留下?能否不湮滅於浩瀚的詞海中,說眞的,又哪裡容易呢?
李後主的詞,包括眞偽有爭議的,不過三十來首。眞是不多,卻含金量超高,幾乎每首都大有名氣。尤其是他在汴京當宋朝皇帝的俘虜那兩年多,寫出來的詞,首首皆膾炙人口,奠定了他無可取代的詞界地位。
這是不公平的。有人就是有文字出奇的天賦敏銳度。
李後主的詞好,天賦應是先決條件。但文字敏銳度高,也要學習,亦須磨煉。
李後主的父親,南唐中主李璟,本身是一位優秀的詞家,且致力收藏圖書、字畫,主政時期,大量接納北方文人南來避亂。在南唐疆土上,構築出一塊北方中原之外,兵荒馬亂的世外桃源。李後主在這環境下長大,耳濡目染,勤奮好學,替他自己打下了很紮實的文字根基。
而且,我們不該漏掉的是,李後主精通音律。就是他很懂音樂,能演奏樂器的意思。他的元配周后,也擅長音律,又國色天香,跟李後主是非常速配的琴瑟和鳴。
這項音樂專長,對治國,對挽救國勢頹唐,一點幫助也沒有。但,對塡詞,助益極大。
我們之所以讀李後主的詞有感,除了被他用字遣詞的高明所撼動外,往往也是不知不覺,被他行雲流水一般的文字裡,流蕩的音樂性所吸引。
妳坐下來,我隨意挑一首,念給妳聽聽。
我選〈長相思〉吧!
妳且閉目,且傾聽。
上闋:「雲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先不急著問他講什麼,光是聽我念,是不是就有一種音樂的,流動的韻律感?
再來。
下闋:「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是不是節奏感十足?聽完,閉上眼,餘音仍在,嫋嫋,不去。
整首詞,不過是相思泛濫,春情盪漾,思春寂寥的宣洩啊。但運用客觀環境的白描,以大自然的變化,來襯托心底按捺不住的,對伊人的思念。
想念妳啊,想念妳盤起來堆卷的濃密黑髮;想念妳啊,想念妳插在髮上的玉簪子。想念妳啊,想念妳薄薄的衣衫,想念妳微微的蹙眉。
但無奈啊~無奈!秋風颳起,秋雨綿綿,我只能望著窗外被秋風秋雨吹打的芭蕉,嘆息著,嘆氣著,夜∼夜怎麼這麼長,我~我怎麼這麼淸醒呢!
李後主在千百年前便示範了,漢字是有線條的有感情的。線條之美,在字的形體;感情之美,在字裡傳遞的意境;但感情之美,還不僅於此,還有字的音聲,以及字與字在堆疊時,發出的節奏感。單字與單字,堆疊起來,三個字,五個字,七個字,每句都疊出韻律感。
懂了這,妳也就明白了,情眞意切,千言萬語,無非要靠文字來表白。
像我年輕時,寫給妳的詩。
來,閉上眼,再聽我念一遍吧:
「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秋天未必寂寥。
秋雨未必蕭瑟。
但,妳不在我身邊,我便寂寥且蕭瑟。
時光靜靜的流淌。
睡不著,睡不著,誰來入夢呢?
問君能有幾多愁。他鑲嵌的文字直扣人心
為何千百年後我們每一顆受傷的靈魂,仍願隨著李後主的詞,詞裡的意境,詞句的節奏,而輕輕地擺盪,輕輕地被療癒呢?
大概是,李後主「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卻承受了命運最暴烈的撞擊。從帝王,淪為階下囚,備受屈辱吧。
他用文字,發抒了幽怨。由於天賦的異稟,這些文字,兀自有了頻率,始終能穿透時代,讓每顆有傷痕的靈魂,都能對他頻頻點頭,了然於心。
歷史上的亡國之君,處境比李後主更慘的,比比皆是。
宋朝重文輕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讓他享有「仁君」美名,免掉了不少皇帝誅殺開國元勛的暴戾之氣。繼承他大位的弟弟趙光義,「兄終弟及」,亦標榜文人治國,也不至於非要置李後主於死地不可。
李後主如果戒愼恐懼,甘心俯首稱臣,未必不能安然在大宋的國都裡,度過餘生。
麻煩就麻煩在,李後主「太文靑性格」了。
他如果像三國時期蜀漢的皇二代劉禪,安於現實,「樂不思蜀」,生命線理當不會停留在四十二歲上。然而,劉禪除了留下「扶不起的阿斗」名號外,還剩什麼?歷史提到他,還有什麼可資深掘的餘地嗎?
中唐詩人劉禹錫的《蜀先主廟》,最能代表這樣的感嘆:「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蜀漢故伎,舞於魏宮,換來的卻是故主劉禪的樂不思蜀,除了感傷,還能怎樣?
李後主不然。
他本身的心思,留在詞句裡,纏綿悱惻,淒涼糾結,激盪了後人更多的漣漪。而他的文靑風格,千餘年來,被不斷閱讀,被不斷按讚。
李後主詞,甚至被民國初年一代宗師王國維,評價為「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
啊不過是,一些些文字,依照詞牌的規格,把適當韻腳的字,一一塡寫進去,而且篇幅並不長,也就那麼些首,竟然就可以被推高到,宛如釋迦牟尼佛,宛如耶穌基督的宗教精神!
這評價,即便不免過譽,但至少表明了,文字創作的意境,是有著極為寬闊之能量的。
而千百年來,世人之所以一讀再讀李後主詞,早就不在意他是個不稱職的帝王,是個亡國之君了。
文字創作的地位,竟然可以超出世俗評價如此之高,怎麼不令人讚歎 !
但我們文靑的讚歎,對身為皇帝的執政者宋太宗,則可能嗅出某些「文字不服從」的味道,而深深引以為憂了。
宋太宗怕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那首〈虞美人〉吧。
我閉上眼,都可以背誦了。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樂不思蜀」的後主劉禪,若聽到這闋詞,妳覺得他會由衷感觸,潸然淚下嗎?
我想,肯定不會。
他不就是在曹魏的都城洛陽,大將軍司馬昭刻意安排的一場蜀樂演出中,當擧坐蜀漢舊臣都忍不住落淚時,他才說出那句傳世金句:「樂不思蜀」嗎?
妳可以說他傻人傻福,通過了司馬昭的「通關檢測」,但從人格特質來看,「阿斗」本來就不是聰慧敏感之人,他不必裝,他就是「傻人」於是「有傻福」啊!
但,李後主,怎麼可能「無感」呢?往事歷歷,要忘也忘不了,只好喝酒麻痹。但偏偏起了東風,故國景致,一一浮上心頭。景色依舊,人事全非。
妳能承受多少這樣的時空變遷,人事更迭,而我們已不再是「從前的我們」那般沁骨的傷痛呢?
聽在宋太宗耳裡,你還「故國」,你還「幾多愁」,你還要「春水向東流」哩,你去死吧!
但我們懂文學的,沒有掌權者一切以權力的思維做考量,於是乎,我們便更懂王國維的意思了。
李後主原意是透過詞句,舒展他眉宇之間的積鬱,誰知,塡詞一離手,抑揚頓挫之間,意境便情挑了千萬「傷心人」的靈魂。我們不管怎麼痛,都彷彿在李後主鑲嵌的字句中,輕輕被撫慰了。
他不是宗教領袖,他只是亡國之君、階下之囚,但他的詞,是在靈魂的黑白琴鍵上,直扣人心的撞擊。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字字,敲在靈魂上。
句句,敲在歷史上。
【內文節選二】
夜長人奈何。他的詞句盪漾著音樂
李後主的詞,是靈魂的黑白鍵上,直扣人心的撞擊。
寫詩塡詞的人很多,卻不是每個人,都有這能耐的。我是指,敲擊你靈魂,韻律你思緒的。
詩詞要直擊人心,用字遣詞一定要精準無比。不落俗套,或者落了俗但能翻新,亦可。
詞,跟詩不同。
詞,是用來搭配曲子,如同歌詞,要放進音樂的套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歌詞,雖有押韻的要求,但基本上作詞人相當自由。
塡詞,則恰恰相反,極不自由。
每一闋詞,都依照詞牌,在一定的規格下進行。例如,〈虞美人〉原本是曲調,為了能讓人隨曲而唱,就需要歌詞。於是〈虞美人〉便成了一首詞牌。任何人想寫歌詞都可以,但必須依照〈虞美人〉的規格公式,塡進適當的字。於是,宋朝詞人大概每個都寫過〈虞美人〉,即便李後主也不只一首〈虞美人〉。
問題來了,既然這麼多人寫,而且是在一套架構下你寫我寫他寫,前人寫今人也寫,寫到最後,會不會抄襲?會不會模仿?會不會詞窮?
我吿訴妳,還眞會。
這也是宋詞之後,明代、淸代,詞人難為的困境。每個詞牌,都被寫爛了啊!
我手上一套《全宋詞》,淸朝唐圭璋編著,共收錄了宋代詞人一千三百三十家,詞作兩萬一千一百一十六首。
想想看,同一闋詞,有多少名家寫過?
後代詞人想出頭天,多難啊。那些前代名家在同一詞牌下,塡過的詞,宛如大山,你要一一克服、超越,談何容易啊!反過來講,即便你是開山祖師,但在後代名家紛紛加入戰局後,你寫的詞,能否留下?能否不湮滅於浩瀚的詞海中,說眞的,又哪裡容易呢?
李後主的詞,包括眞偽有爭議的,不過三十來首。眞是不多,卻含金量超高,幾乎每首都大有名氣。尤其是他在汴京當宋朝皇帝的俘虜那兩年多,寫出來的詞,首首皆膾炙人口,奠定了他無可取代的詞界地位。
這是不公平的。有人就是有文字出奇的天賦敏銳度。
李後主的詞好,天賦應是先決條件。但文字敏銳度高,也要學習,亦須磨煉。
李後主的父親,南唐中主李璟,本身是一位優秀的詞家,且致力收藏圖書、字畫,主政時期,大量接納北方文人南來避亂。在南唐疆土上,構築出一塊北方中原之外,兵荒馬亂的世外桃源。李後主在這環境下長大,耳濡目染,勤奮好學,替他自己打下了很紮實的文字根基。
而且,我們不該漏掉的是,李後主精通音律。就是他很懂音樂,能演奏樂器的意思。他的元配周后,也擅長音律,又國色天香,跟李後主是非常速配的琴瑟和鳴。
這項音樂專長,對治國,對挽救國勢頹唐,一點幫助也沒有。但,對塡詞,助益極大。
我們之所以讀李後主的詞有感,除了被他用字遣詞的高明所撼動外,往往也是不知不覺,被他行雲流水一般的文字裡,流蕩的音樂性所吸引。
妳坐下來,我隨意挑一首,念給妳聽聽。
我選〈長相思〉吧!
妳且閉目,且傾聽。
上闋:「雲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先不急著問他講什麼,光是聽我念,是不是就有一種音樂的,流動的韻律感?
再來。
下闋:「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是不是節奏感十足?聽完,閉上眼,餘音仍在,嫋嫋,不去。
整首詞,不過是相思泛濫,春情盪漾,思春寂寥的宣洩啊。但運用客觀環境的白描,以大自然的變化,來襯托心底按捺不住的,對伊人的思念。
想念妳啊,想念妳盤起來堆卷的濃密黑髮;想念妳啊,想念妳插在髮上的玉簪子。想念妳啊,想念妳薄薄的衣衫,想念妳微微的蹙眉。
但無奈啊~無奈!秋風颳起,秋雨綿綿,我只能望著窗外被秋風秋雨吹打的芭蕉,嘆息著,嘆氣著,夜∼夜怎麼這麼長,我~我怎麼這麼淸醒呢!
李後主在千百年前便示範了,漢字是有線條的有感情的。線條之美,在字的形體;感情之美,在字裡傳遞的意境;但感情之美,還不僅於此,還有字的音聲,以及字與字在堆疊時,發出的節奏感。單字與單字,堆疊起來,三個字,五個字,七個字,每句都疊出韻律感。
懂了這,妳也就明白了,情眞意切,千言萬語,無非要靠文字來表白。
像我年輕時,寫給妳的詩。
來,閉上眼,再聽我念一遍吧:
「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秋天未必寂寥。
秋雨未必蕭瑟。
但,妳不在我身邊,我便寂寥且蕭瑟。
時光靜靜的流淌。
睡不著,睡不著,誰來入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