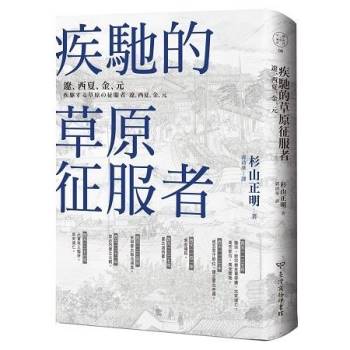唐王朝的巨大身影
以王朝的形式來說,「唐」可說是相當長壽。觀看歷代年表,唐以王朝的形式存在時間為西元六一八年到西元九○七年,共有二百九十年之久,看起來確實似乎是一個長壽的「大王朝」。用這麼長的「時間」來進行一個時代,如此說來,「唐代」便消耗了三個世紀之久,但真的可以想得這麼簡單嗎?
一開始,唐朝確實是一個大王朝。它雖然接受過突厥(曾是內陸世界霸主)的後援,但很快就跳脫出擁有政權的「半屬國」狀態,反而壓制了突厥,還間接地控制、收服其他遊牧民族的軍事勢力。另外,在東邊,唐與新羅合作,擊敗了百濟與日本的聯合軍,更讓高句麗倒臺,短暫地統治了朝鮮半島。唐的勢力後來雖然被逐出新羅,但威令仍然遠達東方的海邊。因為曾有這樣的盛況,所以有人以「世界帝國」來稱呼唐朝。
不過,稍微誇大、像廣告詞一樣的「世界帝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開始衰敗了,隨著東突厥的復興,草原世界的民族再度成為中華的對抗者;而高句麗的遺民們也獨立起來並且建國,就是後來的渤海國。客觀的說,唐朝的「大勢力圈」,事實上只存在於唐王朝的初期。
更有一種看法是,唐朝處於超越實際統治範圍的「東亞世界」,或者說是「東亞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很多人都知道,最早提出這個看法的人,是已故的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先生的看法。然而,正如學者李成市指出的,西嶋定生的看法是源自日本人對漢字文化圈的偏頗觀點,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
還有,草原世界原本就不是接受唐朝「冊封」的地方。舉例說明的話,例如落款年為開元二十年(西元七三二年)的「闕特勤碑」,據說漢文的碑文內容是唐玄宗「自筆、自撰」的,其中明白的表示了唐與突厥是「父子之國」,原則上是將對等的王室雙方比擬為「父子」,遠不是君臣的關係;還有,取代東突厥的回鶻遊牧國家,也以唐為保護國,而打敗了回鶻的黠戛斯與唐關係也是對等的—這些都可以從國書中清楚地看出來。
用近現代的眼光來看有現存國家框架,並以此為前提而自然形成的「文化圈」印象為基礎,把應該不可能納入「冊封體制」的乾燥世界遊牧軍事權力,也納入巨大設定下的「東亞世界論」或「冊封體制論」,這是想超越「一國史」觀點的做法。歷史研究者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應該是不可能成為事實、難以成立的事情。
唐王朝與八世紀的亞洲
然而,唐的「大王朝」形象,對生活在日本列島的人們來說,是堅定不移的。從前日本向唐學習的想法,與對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代代表性詩人的詩文世界的憧憬,非常單純地支撐著日本人對唐的嚮往。和對於其他中華王朝有著極大的不同,日本人對唐朝的好感與敬意,在日本列島上代代相傳、生生不息,這可說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種天真的「過譽」,反過來影響了歷史的真貌。但是,現實中的唐王朝與它的巨大形象並不相符,做為一個統一中華的王朝,它的版圖在不久之後就變得與西漢、東漢時期差不多大小了。進入八世紀後,唐朝進入玄宗的漫長統治時期,把玄宗的開元、天寶兩個年號的統治時期加起來,從西元七一二年到七五六年,共有四十五年。四十五年不是平常的「時間」,和一個短命的王朝比起來,玄宗的統治時期算得上長壽了。
因為之前有武后的周王朝和韋后的掌政,唐到了玄宗王朝時,可說是面貌一變,和以前完全不同。唐朝的政治、經濟結構不管是好還是壞,都在玄宗時期穩定了,因此表面上看起來一派平和,所謂的「唐文化」當然也在這個這個時候出現了精華。不過,此時的亞洲已經明顯地面臨變動,各種變化都準備好要萌芽了。
這之前的七世紀,中東出現了伊斯蘭教,從現在通稱為拜占庭帝國,自稱為「羅馬」的帝國手中,陸續奪下了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等地,不久之後又與中東最大的伊朗帝國、超過四百年歷史的薩珊王朝進行了兩次大戰役,並且獲勝,勢力一下子高漲起來。這個伊斯蘭教團體克服了長久以來部族間對立的問題,在伊斯蘭教的信仰下,短暫地凝聚了阿拉伯遊牧部族的軍事力,奇蹟似的獲得了成功。相對於出現在亞洲東方,並且短暫形成「大版圖」現象的唐朝,伊斯蘭教大版圖的形成或者稍微晚了一點,但也只是些微的差距。
伊斯蘭教持續擴大,沿著地中海南岸地區的北非往西前進,在進入八世紀時,已經侵入了伊比利亞半島。橫跨了亞洲、非洲、歐洲地域的龐大伊斯蘭教圈,終於在歷史上現身。伊斯蘭教從「神的使者」(阿拉的使者)穆罕默德開始,在穆罕默德過世後,經歷了阿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阿里等四代「繼任者」(哈里發),開創出伊斯蘭教的戲劇性成果後,「哈里發」之位開始世襲化,進入倭馬亞王朝的時代,這中間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在不認同哈里發世襲化的什葉派人士叛變,與阿拉伯部族間的相互抗爭難以平息之下,倭馬亞王朝的「和平」飄搖不定。在上述的情況下,哈里發之位頻頻輪換,王朝的國運於是日漸衰微了。同為「帝國」,比較東方的唐朝與西方的伊斯蘭國家時,會發現兩者的步伐有某些相似之處,都呈現出在等待下一扇門開啟的姿態。
草原上的變化
另一方面,草原世界也出現了激烈的變動。占有蒙古高原的東突厥第二次政權,在復興了六十多年後,於西元七四四年至七四五年初,被以回鶻為中心的勢力所取代。回顧突厥的歷史,自西元五五二年建國以來,雖然經過了種種波折,但一直維持著草原「王權」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至此滅亡了。如果把包括非獨立的時期也算進去,阿史那氏所統治的突厥王朝時間,超過兩百二十年。
遊牧部族聯合而成的權力體,幾經重組與再編後,誕生了回鶻遊牧國家。而站在這個國家頂點的,便是藥羅葛氏。不過,回鶻遊牧國家也和突厥國家一樣,以「可汗」來稱呼君主。值得一提的是,把這樣的政權交替視為「民族的興亡」,似乎並不恰當,「民族的興亡」是近現代想法的反射結果。事實上,更換負責權力核心的集團與君權,及隨著替換而重新檢視組織,才是這樣政權交替的本質。因為這樣的交替對遊牧國家的系統來說,基本上應該沒有很大的改變。
話雖如此,在回鶻這支新旗幟下,草原世界變得有活力了。舊有的權威消失,諸事有了新的規定,而這些變動幾乎可以說是在瞬間發生。在對唐朝的態度上,之前玄宗和東突厥王室的友誼,當然也在這個時候產生了變化。
惡化的「玄宗王朝」
回顧玄宗時期的唐朝,及玄宗統治時期下的社會,在陰霾逐年加深下,變化的徵兆也越來越明顯。眾所周知,均田制早已窒礙難行,「府兵制」的評價雖然有好有壞,但也在西元七四○年時不得不換為「募兵制」。另外,還為了防禦外敵,不得不在國內的邊疆要地設置節度使,並擴充原有的兵權,容忍節度使有自己的軍事力量。至此,可說唐朝已經開始走向分權化之路了。
再加上「玄宗王朝」的時間特別長,又諸事墨守成規,這造成國家組織的退化,促成了下一步的局勢發展。說到這裡,就要稍微批評一下玄宗後來對政治的熱情消退,與李林甫、楊國忠等人對權力的壟斷與濫用了。這或許是造成後來國家局勢的誘因,但應該不是主因。總之,唐朝這個系統本身也進入了衰退與解體的過程,玄宗前期被稱頌一時的「開元之治」,也止不住唐朝往下沈淪的齒輪。幸運的「建國」將近一百四十年後,唐朝國體的制度疲態,是再也無法掩蓋了。
無論如何,唐玄宗四十五年的統治歲月,確實是太長了。不管是人生裡還是組織裡,都必需要「更新」。不管在什麼時代,在連結世代與世代、構成人的世代過程中,每一代所背負的「時間」,最多也就是十年至十五左右。那是人類的本質,理當如此。
人的顛峰不會永遠持續,這是非常單純的事,也是超越「時間」的通則。八世紀中葉以後,時代在等待變化。也就是說,通往「開始」的入口,已經出現在眼前了。
◎奔向帝國之路的助跑
被遺忘的英雄
契丹帝國可以說就是耶律阿保機一生的「事業」。西元九○七年唐室滅亡時,阿保機三十六歲,登上契丹的「可汗」之位,於西元九二六年、五十五歲時出人意外地突然離世,統領契丹約二十年左右。阿保機將以前鬆散的契丹部族聯盟結合在一起,建了契丹國家,他一再帶領部隊東南西北地征討,終於創建了跨越多個種族與地域的「帝國」。在他的世代裡,不只契丹,包括內陸草原地帶,乃至於亞洲東方,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把歷史上的特定人物定位為「英雄」時,應該特別慎重,甚至不應有那樣的行為—很多人發出了這樣的呼籲,以歷史研究者尤甚。以人類的進展過程為名的歷史,其核心便是人類群體的整體是處於何種狀態?做了何種改變?而且是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然而,在歷史的進展過程中,確實也存在著「若不是這個人,歷史就會變得不一樣」的人,這是事實,不必怯於承認。
耶律阿保機就是這樣的一位英雄人物。只是,即使他是英雄人物,他的事蹟、人物形象,還有他存在於歷史上的意義等等,是否得到了相應的適當評價?這就很難說了。儘管他的名字留在歷史上了,但他的人物形象卻不如名字來得被人熟悉。或許可以說,耶律阿保機是被遺忘的英雄吧!
同時崛起的契丹與沙陀
安史之亂是將契丹導向獨立的重大因素。安史之亂後,割據中國各地的藩鎮紛紛熱衷於在邊防之處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就算契丹發動攻勢,已經分化、弱化的大唐,也完全失去軍事威脅力。總之,契丹聯盟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來臨了。
契丹與奚族看透了唐室的無能,幾十位部落首領成群來到長安,然後帶著唐朝所給的賞賜滿載而歸,是常有的事;而部落首領的下屬們,則以數百人為單位,逗留在邊境要地的幽州。西元八四○年,回鶻一瓦解,號稱耶瀾可汗的契丹屈戍首長,就以從回鶻那邊得到的王印,向唐要求換新印,然而,這不過是向唐索取賞賜的手段。
唐朝年號咸通年間(西元八六○至八七二年)末期,契丹王習爾(或曰習爾之)自立為巴剌可汗,契丹聯盟的勢力強大起來,逐漸擴展疆域,有「土宇始大」的記載。當沙陀族的首長朱邪赤心平定龐勛之亂,站上歷史舞臺的西元八六八年時,契丹也開始變大了。也就是說,開展下一個時代的沙陀與契丹躍上歷史的舞臺,是同一個時期的事。
沙陀的根據地在山西地方,契丹的根據地在其東北方的西拉木倫河一帶,兩者可以說是鄰居。只是「現成」的鄰近新勢力沙陀接受了唐室的賜姓「李」,但與唐室及拓跋氏有著長期權力糾葛的契丹,卻以自己是契丹為傲,很乾脆地捨棄「李」姓。契丹聯盟的盟主,以自拓跋、柔然、突厥、回鶻以來,內陸世界傳統的「可汗」為自己的稱號。同樣背負著「時代」的兩個對手,在對唐室與中華的立場上卻是兩極的,兩者可以說是「看似相同其實不然」的存在。
阿保機之死
阿保機滅了渤海國,在返回契丹的路上,於六月時在慎州正式聽到李存勗死亡的訊息。繼承了李存勗的沙陀唐王朝的李嗣源,派遣供奉官姚坤,前去向阿保機報喪。穿著錦袍、身高九尺的阿保機現身於大帳內,接見了來報喪的姚坤。阿保機聽到李存勗的死訊,立即放聲大哭,淚流滿面,說道:「我與河東(李克用)先世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
阿保機痛哭不已,但過了一會兒後,便問為何李嗣源沒有去救李存勗?又問李嗣源繼承帝位的正統性。於是姚坤便回答:李存勗失德,養了兩千宮婢,一千樂人,每日只知放鷹逐犬,沈溺於酒與女人之間,又極盡搜括百姓之能事,把政治之事交給他人處理,百姓因此怨聲載道而被眾人所棄。阿保機聞言,便說:我很早就聽說了此事,一直很擔心他會被推翻,並且一個月前就聽說了存勗不幸之事。所以,我已舉家戒酒,放走了家中的鷹、犬,散去了樂人們,不參與公宴以外的宴席;我以我兒為戒,若像我兒那樣,國將不保。
阿保機與姚坤進行了交談。阿保機與他的「漢國之子」李存勗既是父子,也是相互競爭的對手,所以彼此仍抱有敵意,但他與當下的沙陀唐朝天子李嗣源並無舊日的恩怨,便提議雙方結盟,若李嗣源讓出幽州,自己便不會入侵「漢界」。阿保機又說自己精通漢語,此事要對內部保密。姚坤停留了三天,據說阿保機當時得了傷寒或急性的發熱性疾病。之後的某天傍晚,天上一顆星星殞落於阿保機帳前,又不久後,阿保機突然在扶餘城去世了。那天是七月二十七日。
關於阿保機去世的詳情為何,世人不得而知,總之其間似乎有著什麼不可解的陰影。扶餘城位於契丹與渤海國的國境上,阿保機於三月時便踏上歸途,為何過了四個月還沒有回到契丹,留連在渤海國的領內?讓他如此緩慢西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阿保機的弟弟迭剌,剛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東丹國左大相,比阿保機早十一天離開人間;阿保機死後兩個月,任契丹國家首席宰相、至親的弟弟耶律蘇也死了。征討渤海國,滅了渤海國後,契丹國家像被霧一樣的東西籠罩了,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很遺憾的,至今還沒有答案。
回頭看阿保機與智囊團的構想,就是想要有效地利用匈奴帝國以來的遊牧國家長處,補足其不足、克服其缺點,一邊維持國家的軍事力與機動性,一邊開創出可以讓國家安定而持久的道路。具體而言,就是以移動的遊牧宮廷和不動的首都這兩個中央機構為中心,把包括多集團的契丹族、奚、霫、室韋等遊牧系諸部族和他們各自的地域,及領地內的定居型人民與他們的固定建築、生活空間結合起來,並且開拓、振興人跡稀少的遼寧平原等等,將多種族、多區域連結成一個大系統。這可以說是一個嶄新的歷史創作。
順帶一提,若將此構想單純地說是處理草原與中華的折衷方案,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結論呢?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把中華的方式完全移植過去,是不是太過於崇拜中華了呢?這是太不了解草原世界裡連綿不絕的國家系統的說法。
阿保機開拓出來的新道路,很快就在契丹帝國的歷史中穩定前進,並且在更大的歷史轉折中跨越時代、跨越地域,成為國家、社會的應有狀態,持續到下一個世代。阿保機的創業也是時代性的創業,無論如何,他都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戰場英雄,他可以說是戰鬥者、軍事指揮官英雄之上的政治與建設上的英雄,這就是耶律阿保機能夠在歷史中受人矚目的最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