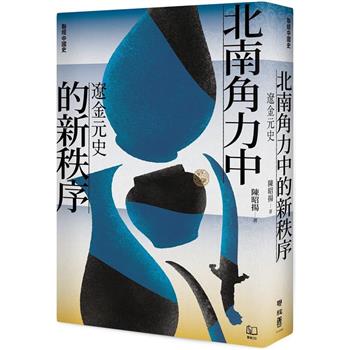一、初步的印象
各自的面貌
十至十三世紀之間,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繼於中國北方建國,開始向外擴張。隨後,南方的漢人世界遭受波及。漢人的國家──尤其是宋朝──面對著北方的挑戰,短期來看是一波波的衝擊,長期來看則是持續的進逼,終於在西元一二七九年被完全征服。蒙古的征服宋朝,傳統觀點中是北族國家首次全面入主漢人世界,傅斯年在〈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便指出,宋朝滅亡後,中國「全為胡虜之運,雖其間明代光復故物,而為運終不長矣」,中國歷史進入了下一個階段。最初,南方的漢人極力抗拒這些侵略,試圖否定北方族群入主中原的資格,但在這三個北族國家的努力下,被統治的漢人也逐漸認同了他們。另一方面,在曾經統治過部分或全部的中國之後,這三個北族國家深受中國影響,他們將有類近中國王朝的表現,有了「大遼」、「大金」、「大元」等中國風格的國號,並在日後被視為中國朝代的一部分,「遼朝」、「金朝」、「元朝」因此得名。
本書將介紹遼、金、元三國的發展及其時代。在此之前,先說明本書的介紹重點與遼、金、元這三國的基本樣貌。首先,雖然以遼、金、元這三國的歷史為敘述範圍,然而為了解釋他們的建國歷程,本書將會追溯他們的開國族群,也就是契丹、女真、蒙古三族的早期活動。只是因為仍以三國而非三族的歷史為主,本書便未繼續說明這三族於其國滅亡後的活動,如女真、蒙古在明代的發展等。此外,「大元」國號乃是西元一二七一年由忽必烈汗所建,此前蒙古本以成吉思汗所建的「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之名為號,學界常以「蒙元」合稱這兩個階段的蒙古統治時期,因此本書也將連同介紹大蒙古國時代的史事。
再者,本書屬於中國史的系列叢書之一,敘述重點乃為中國歷史,此一角度既使遼、金、元的歷史可被視為中國歷史的「時代」,也使本書對於部分距離中國歷史較遠的三國活動,例如遼國後人在中亞的復興,以及大蒙古國在中亞、西亞、歐俄等地的統治等情形,便無法描述過多。這種取捨既是結合叢書體例的規劃,也凸顯出這三國與中國漢人王朝之間的差異。
最後,遼、金、元雖然先後相承,可是這三國的疆域與轄內百姓實是各有樣貌,不少各國當時的歷史現象其實是透過不同的人地條件而展現。例如疆域,如以極盛時期來看,遼朝的東西統治範圍約是今日的中國東北地區到蒙古共和國西緣之間,金朝則是從日本海沿岸到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之間。至於北、南界,兩國的北界一向模糊,南界則較清楚,其中遼朝已達中國河北、山西的北部,金朝則以秦嶺、淮河與宋為鄰。整體而言,金朝疆域的位置比起遼朝更往東、南兩方偏移。關於元朝,其前身的大蒙古國在蒙哥汗的統治期間,西界已達歐俄草原與西亞,東、南兩界則與金朝略同。到了元朝,其西界大幅退縮,南界則大幅推進,實際統治之處已近今日中國,西、南界遂與今日中國相當,而東界如果算入設立征東行省的高麗,或許還能推得更遠。
在這種疆域形勢下,雖然三國皆能統治漢地,但遼朝僅得幽燕,金朝已轄漢人半壁江山,元朝則是混一漢人世界的南北。雖然皆有北方經營,但金朝一直無法有效控制蒙古草原,遼朝與元朝不僅可以,還能自本族原居地一路往西推進,而元朝前身的大蒙古國甚至能將統治範圍延伸至草原以外的西方世界。這種疆域形勢的差別所造成的影響不言可喻。百姓部分,三國的人口規模相去甚遠,估計在極盛期間,遼朝約有九百萬人,金朝約有五千六百萬人,元朝則可能達到九千萬人。又在疆域形勢的影響下,三國所轄百姓的族屬成分與各族人口比例也有差異。這些現象提醒我們,即便這三國有著一些類近的特徵,時代相承下似可一體看待,但當三國的人地格局落差如此之大時,各國將有許多因應各自環境而生的獨特表現,貌同而因果有別的情形也是不少,討論時便需謹慎斟酌。
共同的特徵
但若將視野拉高,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三國歷史的共相,這也是許多討論能將此三國視為一組論述對象,將其歷史視為一個階段的原因。雖然歷史共相的歸納容易造就一些刻板印象,卻不能放棄,畢竟這是探究長期變化趨勢的線索,而歷史也需要從宏觀到微觀而層次各異的理解。稍後簡單整合一下這三國的歷史,先說明遼、金、元的共相及異於其他時代或政權的特徵,作為深入介紹的基礎。
即便被視為中國的朝代,遼、金、元這三個北族國家的樣貌終究與一般認識的漢人國家有著相當的差距。這些差距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數點:第一,北族國家的統治者,其族屬皆非漢人,均是來自北亞;第二,當這些政權擴張到本族以外的地區,三國的開國族群,即「統治族群」,其數量將少於被征服的族群,即所謂的「被統治族群」,此時的國家將呈現出「少數統治」(minority rule)的形態;第三,為了延續少數統治並維護統治族群的利益,國家政策將有特別考量,族群分際的強調會是施政原則;第四,少數統治的局面,加上征服過程中的衝突經驗,北族國家將會致力保持武力的優勢,統治手段因而相對殘暴,軍事管理風格強烈;第五,統治族群雖然強勢,被統治族群卻是多數,加上被征服地區的文化常能比本族文化更能協助在地管理,也有部分內容能在全國的範疇中具備更好的統治效能,國家遂難專尊本族,兼容並蓄的文化政策甚是顯目;第六,在百姓治理的場合中,既是北方長期以來的政治傳統,也為了安撫被統治族群,北族國家相對尊重被統治地區的習慣做法,願意維持各地社會原有的權力秩序,以「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為原則所設定的地方管理措施因此普遍。就初步印象所見,我們可以很快地分辨出他們與傳統漢人王朝的不同。
這三國又與早期中國歷史的一些北族國家不同。對於遼、金、元,也包含十一世紀建國的夏,不少宋人常以「胡虜」、「夷狄」等語詞統稱他們。這種說法呈現了華夷區隔,也使遼、金、元看來就與更早之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鶻等北族國家一般。不過,已有部分宋人察覺到了這些「夷狄」的新特性,擔心這種一體涵蓋的說法會輕忽了這些新興「夷狄」的威脅,他們有了新觀點。對此,早在宋初,宋太宗便曾指出「今之玁狁,群眾變詐,與古不同」。類似說法,後代宋臣繼續發揮,富弼(一○○四-一○八三)或為代表。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於國際局勢瞭解甚深,在宋仁宗慶曆三年(一○四三)任職樞密副使時所上奏的〈河北守禦十二策〉中,他便指出遼和夏已非「上古之夷狄」,因為他們「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富弼明言遼、夏兩國是宋朝需要謹慎面對的大敵,與「上古夷狄」不同。這些不同,富弼逐一陳說,但關鍵也許是最後的總結,即兩國已是「中國所有,彼盡得之」。這個說法當然有些偏失,無論如何學習,在現實需求與本族情感的考量下,北國君臣總對中國事物多有取捨,北族國家並未盡得「中國所有」。然而即便未能盡得,仍可看到這些新型北族國家學習中國事務的成就,他們與漢人政權的樣貌更加接近,而與先前的北族國家有所差別。
中國事務的學習
學習中國事務的動力,最初大概是來自於現實的需求,此即遼、金、元需要統治大量的漢人地區。當擴張告一段落後,國內漢人的數量,在遼約占全國人口半數以上,在金、在元甚至多過北族人口的十倍以上。這種人口的基本格局使得漢地管理成了北族國家的統治要務。管理漢地,直接沿用北族舊慣是種選項,然而經過一些實驗,也發現這種做法的缺失甚多。由於不易適應,北族舊慣常令漢人排拒,如果牴觸到漢人生活的基本利益或核心價值亦是容易催動漢人的反抗。長期發展後,漢人制度已是管理農耕定居社會的有效工具,相對而言,北族舊慣不是因此而生,對於漢地的管理便有風土不宜的問題。經過長期實驗,先以漢人制度為底,再添入一些臨機應變的構思,或是延續一些北族舊慣,或是根據時勢創建新辦法,一種北族國家管理漢地的基本章法便慢慢成形了。為了鞏固漢地的統治,北族統治者不但需要瞭解,也要使用漢人世界的制度及其周邊配套的文化價值,漢地統治的現實需求成了北族國家學習中國事務的關鍵動機。
還有一些學習中國事務的機會。經過千年來的發展,到了十世紀左右,中國已經逐步建立了一些基本的政治運作原則,尤其是透過皇帝制度來強化統治者的權威,利用更多的中央集權措施與官僚管理規章來提升統治的效能。另一方面,北族國家所要面對的挑戰,既有外敵,也有自家人。早期的政治傳統常令北族之內分分合合,君長輪換也比同時的中原政權相對激烈。這種紛擾有其歷史背景,但對多數的北族君長而言,無論是何族屬,或是為了鞏固統治者的權位,或是希望減少本國力量的內耗,強化領導權威與提升管理效能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經濟生產部分,雖然自古以來北族在牧業經營上有其獨到之處,但是受限於自然人文條件,有許多其他的生產技術仍是不如南方,尤其是較能穩定提供糧食的農業,以及技術門檻較高的礦冶業與民生用品製造業。無法自給的物資,早年可以透過貿易或者劫掠周遭農業地區取得,但如能在本族居地自行穩定生產,對於國家與百姓都是件好事。似乎就在唐朝的影響下,北方世界比起過去更加熟悉了漢人世界的種種,看了南方的示範後,參考漢人辦法解決本族在政治與經濟生產中的問題也是不錯的選擇。最初的學習帶有現實目的,無論是為了解決本族問題或強化漢地統治,中國知識是個好工具。
經由與漢人世界的長期接觸,對於中國知識的理解與情感,部分北族的態度也有了變化。無論是統治者、社會優勢群體、抑或平民百姓,各類的北族人群所能接觸到中國事務的機會一直不均勻,需求也不一致。有些人的生活環境不太需要中國的知識,他們繼續過著北方風格的生活,但對部分北人而言,尤其是涉入較多國家事務、接近漢人生活圈、能從漢人資源得到更多利益的北人,他們將有更多意願學習這些中國事務。維持本族傳統或是學習中國事務都是選項,看來也需要一些信念合理化他們的選擇。逐漸地,選擇學習中國事務的北人也將以實踐中國的生活方式視為一種價值,進一步積極推動北族國家對於中國事務的學習。長期下來,由上而下,由現實到信念,就在北族國家強化了南方統治時,南方的影響也在北人內部加深加廣,這些現象都在緩慢地改造著這些北族國家的面貌。
中國事務的學習,使得遼、金、元與較少涉入中國事務的匈奴、突厥等北族國家相較,其中國風貌相對濃重。不過就所有涉入中國歷史的北族國家而言,早在中古時期創建的拓跋魏等「五胡」國家也有類似的發展。但除了拓跋魏外,其餘的「五胡」國家都無法長期且緊密地控制他們的本族原居地,而北方的「祖地」一直都是遼、金、元的國家重心之一。此外,所有「五胡」國家也都沒有本族的文字,契丹、女真、蒙古則皆有。「祖地」的保有與本族文字的運用,使得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雖然受到漢地的深刻影響,卻依舊可以持續與本族的文化傳統保持聯繫,隨時接受著本族文化對於本族乃至於整體國家一直都有其重要性的提醒。這些現象,造就了一些現今或許可以視為北族風格的做法與思維的生成,避免過分漢化與維持本族主體性的立場便也長期存在於這些新型北族國家的活動中。最後,雙核心的政權形態與多元的文化政策,都將共構成為十世紀以後北族國家的新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