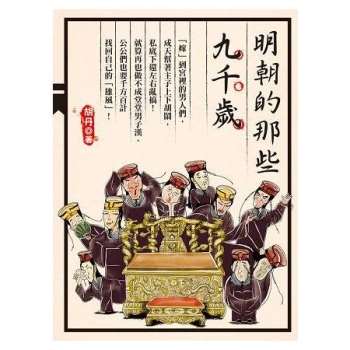第一章 特務頭子是宦官
廣袤的華北平原被稀疏的林木分割開來,極目望去,千里荒涼。除了偶爾出現幾隊衣衫襤褸、步履蹣跚的難民,幾乎看不到人煙或較大的聚落。
前年仲秋(農歷八月),正是田作收獲的時節,朝廷興六十萬大軍來伐鎮守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老朱家自家人內訌起來,今天你打過去,明天我打過來,在北平、河南、山東數省間反覆鏖戰。天天交兵,莊稼地裡已容不下農夫耕作的腳步,全被馬蹄踐得稀爛,人民生活陷入極端的痛苦之中。
昔日鎮守北邊雄鎮的燕王,如今已成了朝廷集重兵討伐、必欲繩之誅之的叛逆。在朝廷的詔書裡,燕王已不再是燕王,他被削去王爵,成了百官口誅筆伐的「燕庶人」。
但燕王朱棣並不甘心束手就擒,而是假借「祖制」,打出「靖難」的旗號,在險惡的環境下,頑強地為生存而戰。燕王領導的「靖難軍」(或稱燕軍、北軍)像哪吒一樣,越長越大,生出三頭六臂,硬是把緊緊纏裹住他的蟬蛹捅出幾個大窟窿。
建文元年到二年(西元一三九九年~西元一四〇〇年),朝廷官軍(或稱南軍)在真定、白溝河等地(均在今河北北部一帶)接連慘敗,損失了數十萬人馬,輜重的損失更是不計其數。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朝廷畢竟擁有萬里的版圖,人口眾多,物力充沛,在經歷了最初的敗績後,漸漸從頹勢中復蘇。建文二年末,盛庸在山東東昌重創來犯的燕軍,斬其大將張玉,燕軍敗回北平。
這是用兵兩年來,朝廷難得的一次完勝。為此,建文帝朱允炆在建文三年正月祭享太廟時,特將東昌之捷焚黃告於祖先(稱「告廟」)。太廟是帝室的宗祠,裡頭供奉著太祖皇帝朱元璋的神主,不知這位大明的開國之君在獲悉朝廷討逆大勝的消息後做何感想,是該為孫皇帝朱允炆快慰呢,還是替四皇子燕王朱棣擔憂?
朝廷借東昌大捷,振作士氣,試圖重新凝聚對北平的鐵壁合圍。七月間,平燕副將軍平安由真定(今河北正定)進攻北平,這是自建文二年夏曹國公李景隆白溝河大敗後,官軍首次如此近地接近燕軍老巢北平。
北平城裡,焦躁不安的情緒隨著大批難民與敗兵的湧進而蔓延,許多人對燕王能否繼續扛住朝廷的打擊開始持悲觀的態度。這兩年,仗打得實在太苦,雖然燕軍鐵騎縱橫華北,看起來銳不可當,但也只能像北虜流寇一樣四處劫掠,所占城池,往往是今日占領,明日即丟失,始終無法穩定一條鞏固的戰線,更別說擴大了。便宜沒占到多少,還損折了張玉、譚淵等數位重要將領。
燕軍方面在保持兵力上還不成問題,大量失業的流民可以隨時補充所缺兵員,但其饟道時刻面臨著官軍的威脅,糧食供應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北平城內,各種流言隨著高漲的物價、迅速擴大的糧荒而加速傳播,簡直到了一日三驚的地步。
軍中已發生好幾起小規模的譁變。燕王朱棣最為擔心的,就是內部出現反抗他的分裂勢力。為此朱棣密令親信內侍劉通,暗中組織一支祕密的「偵緝隊」,專門刺察市井坊巷及文武將吏的各種情報,直接向他匯報。這支小型的特別偵緝隊,即是後來東廠的前身。
明代第一位宦官特務頭子劉通,其實早已出了茅廬。據其墓誌所載,早在洪武二十九年(西元一三九六年)時,劉通即奉燕王令旨,在開平、大寧等處修築城堡,那時他年僅十六歲。
劉通不是漢人,而是女真人,父名阿哈,世居東北,為「三萬戶大族」。他生於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年),大概是明軍在經略遼東時,將還是兒童的劉通兄弟(弟名劉順)俘虜,閹為內臣,令其侍奉燕王於北平府邸。
劉通保存了騎射民族的彪悍性格,他的墓誌稱其「性剛毅,及長,勇略過人」。這從劉通參加靖難之役,及多次從駕北征、屢建戰功上,可以得到證明。但他最重要的品質,還是「忠謹」,即對上忠誠,為人謹慎,不好虛飾夸詐,很令主子放心,所以燕王才「委以腹心,俾察外情」,成為燕王府「軍統局」的特務頭子。
其實,使用宦官來刺探外情,在洪武時代已有先例。
朱元璋除了從到外地出差的宦官那裡了解地方事務及輿情,還差遣宦官到地方與軍中,充當自己的耳目,搜集各種情報,並對官民進行監視。
有這樣一個例子:在明朝建國以前,有人告發鎮守和州(今安徽和縣)的大都督府參軍郭景祥,說他的公子仗著其父的權勢,為所欲為。朱元璋很重視這件事,派按察司書吏唐原嘉前去探察。回報確有其事,還說郭景祥因為兒子實在不像話,十分生氣,打算攆他走,結果這逆子竟然抄起一支長矛,欲刺殺父親。朱元璋聞奏大怒,下令將郭公子抓起來,回宮後對馬皇后表示:「我一定要宰了那小子!」馬皇后卻有些擔心:「猾吏所言恐不實。況且老郭只有一個兒子,殺之若不實,豈不冤枉?還絕了老郭之後。」殺老朋友的親兒,這事可得慎重。朱元璋想想也是,於是改派心腹宦官佛保再去探察。佛保回報說,郭氏父子的確發生過衝突,但並無兒子持矛殺父之事。這個事實非常關鍵,因為以子弒父,屬於大逆不道,罪在十惡不赦之條。朱元璋聽說沒這回事,便釋放了郭公子,而將奏報不實的書吏狠狠打了一頓屁股。
可見朱元璋兩口子不信外臣(稱之為「猾吏」)而信閹奴,是久有其心理基礎的。
明朝建國後,宦官組織迅速擴張,內府「二十四衙門」的格局,在洪武時期大抵形成。朱元璋甚至還開始嘗試建立以宦官為頭領的情報機構,成立於洪武九年(西元一三七六年)八月的一個名叫「繩頑司」的機構,值得注意。
「繩頑」之義甚明,「繩」是繩之以法的意思,「頑」指「奸頑」。繩頑司的職掌,《皇明祖訓錄.內官》記云:「掌治內官、內使之犯罪者。」就是管理宦官犯罪的專門機構。
《明太祖實錄》記載了繩頑司行事的一件實例:洪武十年六月的一天,有一名「圬者」,即粉刷牆壁的工匠,帶著家小上京服役,不幸病死了。圬者地位低下,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所說:「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一個小工匠的死,芝麻綠豆大一點兒小事,竟然被繩頑司「上達天聽」,奏給皇上知道了。朱元璋覺得此人可憐,賜給他一口薄皮棺材,還資助路費,送其家小還鄉。
繩頑司幹了一件「包打聽」的事。由此事來看,該司的職掌,可能並不像祖訓文本記載得那樣單純,只負責懲治犯罪的內官、內使。
想來也是,好比今天政法機關辦案,首先不得偵查嗎?繩頑司辦案,也得先派出幹探,四下緝訪,才能掌握內臣「犯罪」的事實。
朱元璋設立這樣一個機構,明裡是加強對日益龐大的宦官隊伍的監察,對外掛這樣一塊牌子,而事實上該司的職掌,卻可能包括訪查京城內外官民之事(稱「緝事」,或「行事」),事無大小巨細,都必須向朱元璋奏報。皇帝放的眼線多,耳聰目明,才聰明嘛!
繩頑司後來併入司禮監。至於它什麼時候取消的,史籍並無記載。這也好解釋,祕密戰線工作嘛,自然不會那麼張揚。
幫皇帝打聽臣民隱情,不是一般外人都能做的,必為皇帝的親信。所以劉通對自己領導「地下工作」的經歷非常得意,在自己的墓誌裡曝了光。還不忘添寫一筆,稱他接受「俾察外情」的「心腹」之任後,「廣詢博採,悉得其實以聞」,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將他探聽來的情報,如實地向燕王做了匯報。
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七月,正是朝廷大軍再次兵臨城下、戰局遽然而危之時,一個人夾在逃難的人群中混入北平城。此人姓張名安,說話是北方口音,人卻來自南京,真實身份是錦衣衛千戶。
錦衣衛與永樂年間設立的東廠,合稱「廠衛」,都被認為是明代的特務機關。其實錦衣衛的職權範圍非常廣,將錦衣衛官校等同於特務,實在是以偏概全,需要說明的是,只有「行事校尉」才稱得上是特務。
張安此次脫去鮮豔的大紅官服,不騎高頭大馬(錦衣衛因這身豔麗的行頭和坐騎,又被稱為「緹騎」。緹,赤也。),微服易容,潛行至北平,確是承擔了一項重要的「特別任務」。說他是特務,他當得起!
在張安貼肉的衣服裡縫著一封密信,寫信人是建文皇帝的老師、著名學者方孝孺。而收信人不是別人,正是燕王世子朱高熾。
敵對陣營的兩個對頭怎麼通起信來?定有大事!
劉通的情報工作果然極富成效,朝廷的密使進城後,只在燕王府前踅摸了兩圈,已陷入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他本人尚惘然不覺。劉通很快摸清,張安打南軍中來,此行的目的是要面見世子朱高熾。
由於事關世子,劉通不敢馬虎,趕緊將此事上報。
此時燕王朱棣正率軍在外,與朝廷大將平安激戰,世子高熾照例被留在北平城中「居守」,全面主持城防及前方後勤保障工作。劉通當然不會把朝廷祕遣奸細北來、試圖與世子接觸的情報,報告給在根據地「總負責」的世子─那是找死!─他將這個重要情報呈遞給了燕王府承奉正黃儼,請示是否收網逮捕張安。
過去一說起明代的大太監,總從正統年間的王振說起。其實大謬不然,明代拔頭籌的第一號權閹,應該從燕王手下查起,頭一分兒,非黃儼莫屬!
黃儼此時正坐在王府南門端禮門內右側的承奉司衙門裡,得報後,頓時像打了雞血,無比興奮起來。
他叮囑劉通,暫時不要觸動張安,對其保持嚴密監控,勿使其漏網就好了。他特別告誡劉通,雖然此事牽涉到世子,你也不要有任何的疑慮和忌諱,探子有任何舉動,你都當速速如實來報。
在燕王府裡,黃儼是宦官中的前輩,極得王爺寵信,在燕王駕前說話,也是一口唾沫一顆釘,王爺不在,他替王爺交代公事,也是作數的。劉通忙稱「是」,退出。
張安哪裡知道,他一到北平,就像落入玻璃瓶中,被一雙雙監視的眼睛透視著。他通過舊識的引見、祕密謁見世子朱高熾的情報,已第一時間擺在黃儼的案頭。
廣袤的華北平原被稀疏的林木分割開來,極目望去,千里荒涼。除了偶爾出現幾隊衣衫襤褸、步履蹣跚的難民,幾乎看不到人煙或較大的聚落。
前年仲秋(農歷八月),正是田作收獲的時節,朝廷興六十萬大軍來伐鎮守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老朱家自家人內訌起來,今天你打過去,明天我打過來,在北平、河南、山東數省間反覆鏖戰。天天交兵,莊稼地裡已容不下農夫耕作的腳步,全被馬蹄踐得稀爛,人民生活陷入極端的痛苦之中。
昔日鎮守北邊雄鎮的燕王,如今已成了朝廷集重兵討伐、必欲繩之誅之的叛逆。在朝廷的詔書裡,燕王已不再是燕王,他被削去王爵,成了百官口誅筆伐的「燕庶人」。
但燕王朱棣並不甘心束手就擒,而是假借「祖制」,打出「靖難」的旗號,在險惡的環境下,頑強地為生存而戰。燕王領導的「靖難軍」(或稱燕軍、北軍)像哪吒一樣,越長越大,生出三頭六臂,硬是把緊緊纏裹住他的蟬蛹捅出幾個大窟窿。
建文元年到二年(西元一三九九年~西元一四〇〇年),朝廷官軍(或稱南軍)在真定、白溝河等地(均在今河北北部一帶)接連慘敗,損失了數十萬人馬,輜重的損失更是不計其數。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朝廷畢竟擁有萬里的版圖,人口眾多,物力充沛,在經歷了最初的敗績後,漸漸從頹勢中復蘇。建文二年末,盛庸在山東東昌重創來犯的燕軍,斬其大將張玉,燕軍敗回北平。
這是用兵兩年來,朝廷難得的一次完勝。為此,建文帝朱允炆在建文三年正月祭享太廟時,特將東昌之捷焚黃告於祖先(稱「告廟」)。太廟是帝室的宗祠,裡頭供奉著太祖皇帝朱元璋的神主,不知這位大明的開國之君在獲悉朝廷討逆大勝的消息後做何感想,是該為孫皇帝朱允炆快慰呢,還是替四皇子燕王朱棣擔憂?
朝廷借東昌大捷,振作士氣,試圖重新凝聚對北平的鐵壁合圍。七月間,平燕副將軍平安由真定(今河北正定)進攻北平,這是自建文二年夏曹國公李景隆白溝河大敗後,官軍首次如此近地接近燕軍老巢北平。
北平城裡,焦躁不安的情緒隨著大批難民與敗兵的湧進而蔓延,許多人對燕王能否繼續扛住朝廷的打擊開始持悲觀的態度。這兩年,仗打得實在太苦,雖然燕軍鐵騎縱橫華北,看起來銳不可當,但也只能像北虜流寇一樣四處劫掠,所占城池,往往是今日占領,明日即丟失,始終無法穩定一條鞏固的戰線,更別說擴大了。便宜沒占到多少,還損折了張玉、譚淵等數位重要將領。
燕軍方面在保持兵力上還不成問題,大量失業的流民可以隨時補充所缺兵員,但其饟道時刻面臨著官軍的威脅,糧食供應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北平城內,各種流言隨著高漲的物價、迅速擴大的糧荒而加速傳播,簡直到了一日三驚的地步。
軍中已發生好幾起小規模的譁變。燕王朱棣最為擔心的,就是內部出現反抗他的分裂勢力。為此朱棣密令親信內侍劉通,暗中組織一支祕密的「偵緝隊」,專門刺察市井坊巷及文武將吏的各種情報,直接向他匯報。這支小型的特別偵緝隊,即是後來東廠的前身。
明代第一位宦官特務頭子劉通,其實早已出了茅廬。據其墓誌所載,早在洪武二十九年(西元一三九六年)時,劉通即奉燕王令旨,在開平、大寧等處修築城堡,那時他年僅十六歲。
劉通不是漢人,而是女真人,父名阿哈,世居東北,為「三萬戶大族」。他生於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年),大概是明軍在經略遼東時,將還是兒童的劉通兄弟(弟名劉順)俘虜,閹為內臣,令其侍奉燕王於北平府邸。
劉通保存了騎射民族的彪悍性格,他的墓誌稱其「性剛毅,及長,勇略過人」。這從劉通參加靖難之役,及多次從駕北征、屢建戰功上,可以得到證明。但他最重要的品質,還是「忠謹」,即對上忠誠,為人謹慎,不好虛飾夸詐,很令主子放心,所以燕王才「委以腹心,俾察外情」,成為燕王府「軍統局」的特務頭子。
其實,使用宦官來刺探外情,在洪武時代已有先例。
朱元璋除了從到外地出差的宦官那裡了解地方事務及輿情,還差遣宦官到地方與軍中,充當自己的耳目,搜集各種情報,並對官民進行監視。
有這樣一個例子:在明朝建國以前,有人告發鎮守和州(今安徽和縣)的大都督府參軍郭景祥,說他的公子仗著其父的權勢,為所欲為。朱元璋很重視這件事,派按察司書吏唐原嘉前去探察。回報確有其事,還說郭景祥因為兒子實在不像話,十分生氣,打算攆他走,結果這逆子竟然抄起一支長矛,欲刺殺父親。朱元璋聞奏大怒,下令將郭公子抓起來,回宮後對馬皇后表示:「我一定要宰了那小子!」馬皇后卻有些擔心:「猾吏所言恐不實。況且老郭只有一個兒子,殺之若不實,豈不冤枉?還絕了老郭之後。」殺老朋友的親兒,這事可得慎重。朱元璋想想也是,於是改派心腹宦官佛保再去探察。佛保回報說,郭氏父子的確發生過衝突,但並無兒子持矛殺父之事。這個事實非常關鍵,因為以子弒父,屬於大逆不道,罪在十惡不赦之條。朱元璋聽說沒這回事,便釋放了郭公子,而將奏報不實的書吏狠狠打了一頓屁股。
可見朱元璋兩口子不信外臣(稱之為「猾吏」)而信閹奴,是久有其心理基礎的。
明朝建國後,宦官組織迅速擴張,內府「二十四衙門」的格局,在洪武時期大抵形成。朱元璋甚至還開始嘗試建立以宦官為頭領的情報機構,成立於洪武九年(西元一三七六年)八月的一個名叫「繩頑司」的機構,值得注意。
「繩頑」之義甚明,「繩」是繩之以法的意思,「頑」指「奸頑」。繩頑司的職掌,《皇明祖訓錄.內官》記云:「掌治內官、內使之犯罪者。」就是管理宦官犯罪的專門機構。
《明太祖實錄》記載了繩頑司行事的一件實例:洪武十年六月的一天,有一名「圬者」,即粉刷牆壁的工匠,帶著家小上京服役,不幸病死了。圬者地位低下,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所說:「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一個小工匠的死,芝麻綠豆大一點兒小事,竟然被繩頑司「上達天聽」,奏給皇上知道了。朱元璋覺得此人可憐,賜給他一口薄皮棺材,還資助路費,送其家小還鄉。
繩頑司幹了一件「包打聽」的事。由此事來看,該司的職掌,可能並不像祖訓文本記載得那樣單純,只負責懲治犯罪的內官、內使。
想來也是,好比今天政法機關辦案,首先不得偵查嗎?繩頑司辦案,也得先派出幹探,四下緝訪,才能掌握內臣「犯罪」的事實。
朱元璋設立這樣一個機構,明裡是加強對日益龐大的宦官隊伍的監察,對外掛這樣一塊牌子,而事實上該司的職掌,卻可能包括訪查京城內外官民之事(稱「緝事」,或「行事」),事無大小巨細,都必須向朱元璋奏報。皇帝放的眼線多,耳聰目明,才聰明嘛!
繩頑司後來併入司禮監。至於它什麼時候取消的,史籍並無記載。這也好解釋,祕密戰線工作嘛,自然不會那麼張揚。
幫皇帝打聽臣民隱情,不是一般外人都能做的,必為皇帝的親信。所以劉通對自己領導「地下工作」的經歷非常得意,在自己的墓誌裡曝了光。還不忘添寫一筆,稱他接受「俾察外情」的「心腹」之任後,「廣詢博採,悉得其實以聞」,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將他探聽來的情報,如實地向燕王做了匯報。
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七月,正是朝廷大軍再次兵臨城下、戰局遽然而危之時,一個人夾在逃難的人群中混入北平城。此人姓張名安,說話是北方口音,人卻來自南京,真實身份是錦衣衛千戶。
錦衣衛與永樂年間設立的東廠,合稱「廠衛」,都被認為是明代的特務機關。其實錦衣衛的職權範圍非常廣,將錦衣衛官校等同於特務,實在是以偏概全,需要說明的是,只有「行事校尉」才稱得上是特務。
張安此次脫去鮮豔的大紅官服,不騎高頭大馬(錦衣衛因這身豔麗的行頭和坐騎,又被稱為「緹騎」。緹,赤也。),微服易容,潛行至北平,確是承擔了一項重要的「特別任務」。說他是特務,他當得起!
在張安貼肉的衣服裡縫著一封密信,寫信人是建文皇帝的老師、著名學者方孝孺。而收信人不是別人,正是燕王世子朱高熾。
敵對陣營的兩個對頭怎麼通起信來?定有大事!
劉通的情報工作果然極富成效,朝廷的密使進城後,只在燕王府前踅摸了兩圈,已陷入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他本人尚惘然不覺。劉通很快摸清,張安打南軍中來,此行的目的是要面見世子朱高熾。
由於事關世子,劉通不敢馬虎,趕緊將此事上報。
此時燕王朱棣正率軍在外,與朝廷大將平安激戰,世子高熾照例被留在北平城中「居守」,全面主持城防及前方後勤保障工作。劉通當然不會把朝廷祕遣奸細北來、試圖與世子接觸的情報,報告給在根據地「總負責」的世子─那是找死!─他將這個重要情報呈遞給了燕王府承奉正黃儼,請示是否收網逮捕張安。
過去一說起明代的大太監,總從正統年間的王振說起。其實大謬不然,明代拔頭籌的第一號權閹,應該從燕王手下查起,頭一分兒,非黃儼莫屬!
黃儼此時正坐在王府南門端禮門內右側的承奉司衙門裡,得報後,頓時像打了雞血,無比興奮起來。
他叮囑劉通,暫時不要觸動張安,對其保持嚴密監控,勿使其漏網就好了。他特別告誡劉通,雖然此事牽涉到世子,你也不要有任何的疑慮和忌諱,探子有任何舉動,你都當速速如實來報。
在燕王府裡,黃儼是宦官中的前輩,極得王爺寵信,在燕王駕前說話,也是一口唾沫一顆釘,王爺不在,他替王爺交代公事,也是作數的。劉通忙稱「是」,退出。
張安哪裡知道,他一到北平,就像落入玻璃瓶中,被一雙雙監視的眼睛透視著。他通過舊識的引見、祕密謁見世子朱高熾的情報,已第一時間擺在黃儼的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