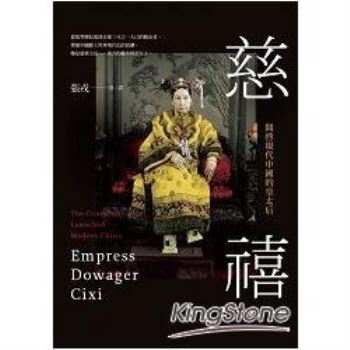推動對外貿易的慈禧
*
隨著太平天國的終結,其他農民戰爭也接二連三地失敗,燃燒多年的造反烈火一點點化為灰燼中將滅的火星。奪權之後不幾年,慈禧在全國恢復了和平。這樹立了她在統治階層中不爭的權威,同時減少了對她未來政策的反對力量。慈禧的政策是振興中國。大大小小的戰爭耗費了三億兩銀子,大部分地區滿目瘡痍,北京街頭到處是乞丐,通常不在人前露面的婦女,也近乎赤身露體地向行人討食。然而,在慈禧統治下,中國不僅迅速恢復了元氣,而且開始了「同治中興」。
中興的關鍵因素是有了一個可觀的新財源:開放政策帶來與日俱增的對外貿易,海關稅收直線上升。慈禧早就看到外貿的巨大潛力。政變後不久的一八六二年初,她跟恭親王提到太平軍威脅下的上海時說:「上海僻處一隅,勢如累卵,而該處華洋商賈輻輳,餉源甚裕。近聞兩月之間,洋稅已收至八十萬兩。」她要竭力「保全」上海。她推動對外貿易,一八六三年,六千八百多艘貨船來到上海,而她丈夫執政時僅僅年均一千艘。
要擴展對外貿易,中國必須有高效率並且廉潔的海關。經恭親王推薦,慈禧任命已在海關工作的二十八歲英國北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為「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不到一年,她傳旨嘉獎赫德,封他為正三品大員「按察使」。
赫德與慈禧同年,出生於一八三五年,就讀貝爾法斯特的女王學院。他初來中國時十九歲,聰明、誠摯、天真,預備做英國領事部門的翻譯。除了傑出的語言才能,他還得過各種不同領域的獎,包括邏輯學、拉丁文、英國文學、歷史、玄學、自然科學、法理學和地理學。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關心道德與正義,並且深切地同情中國人。日記中有一段描述剛到香港時,一天傍晚在海邊散步,同行者叫斯德斯(Stace)。赫德寫道:「斯德斯對待中國人的行為叫我很吃驚。他上了一條船,叫他們划出港,他們不肯划。這是他們的晚飯時間,對他們是神聖的,他們一定要吃完才工作。可他竟用手杖把他們的東西甩到水裡去,還用手杖戳點他們。」
在中國工作十年,赫德被一致認為公正而才幹超人,善於調停並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協。他知道自己的長處,十分自信。當他接到正式任命書時,他沒有急於拆開,而是「照常吃我的早餐,然後像往常一樣,讀聖經、祈禱……看當天來信。」在一堆來信中,他最後看的才是任命他為總稅務司的公文。
赫德把舊式海關改造為具有一整套嚴格管理制度、高效率、無貪腐的現代機構,為北京政府提供了一個穩定並不斷增長的稅收來源,對中國經濟發展作用極大。到了一八六五年,他已上交三千二百多萬兩銀子的關稅。對英法的戰爭賠款由海關收入支付,到一八六六年中完全付清,國計民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有了新財源,慈禧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大量進口糧食。中國長期以來生產的糧食不夠養活人口,清王朝一直禁止糧食出口。但全國性的糧食進口據海關紀錄是一八六七年。那年慈禧政府用一百一十萬兩銀子購買大米。「採買洋米」是赫德海關的重要工作之一,有關官員受到慈禧的嘉獎。
雇傭赫德和一大批西方人在海關任職,自然引起部分中國官員不滿。慈禧堅持政策不變。
*
慈禧政府的宗旨是建設強盛的中國。赫德想向他們說明,這個目標只有「現代化」才能達到。他在日記裡寫道,他要「讓這個國家擁有基督教文明帶給人類的一切舒適、一切福祉,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他要中國「進步」,而進步在那個年代意味著新式採礦、電報電話,尤其是鐵路。一八六五年十月,赫德給恭親王遞上一份建議書:「局外旁觀論」。
赫德急切地要「更新」古老的中國,開的是一劑苦藥。他稱:「自四海各國觀之,竟莫弱於中國。」中國皇上「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國民性差勁:「常聞外論,中國官民,大半可以利動,勢處極弱而不守信。」如果不照他說的辦,將來會「為人所勉強」,「必動干戈」,而「無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勝之勢。」
赫德的話代表了當時西方人一種普遍的態度,即他們「比中國人更知道中國需要什麼」,他們應當「掐住這個古老帝國的喉嚨,逼著她進步」。
恭親王把赫德的建議書壓了幾個月才呈給慈禧。這一不尋常的拖延很可能是因為他怕慈禧震怒之下解雇赫德,用一句老話說:失去這隻會下金蛋的雞。儘管慈禧鼓勵尖銳的批評和直言不諱的建議,但沒人敢用如此傲慢的口氣「恫嚇挾制」。奕訢拿不準慈禧會如何反應。他決定讓赫德暫離中國,這樣如果慈禧一氣之下要辭掉他,還有迴旋的餘地。赫德曾要求回國休假,正是在這時,他的休假要求批准了。
赫德於一八六六年三月底離開中國。四月一日,他的建議書呈遞慈禧。同時還有威妥瑪的「說帖」,談的是大致同樣的問題,用的是大致同樣的口氣。呈上這些文件之後,恭親王忐忑不寧。一天,英國公使館隨員米特福特來見他,再提「鐵路、電報和那些說了一百遍的老話題」。隨員注意到,「親王非常緊張不安,像隻受驚的兔子。」
恭親王低估了慈禧。她仔細看了兩份建議書,然後把它們發給十名外交、貿易和地方大員,請他們提意見。她的信上沒有對赫德、威妥瑪的憤怒和敵意,而恭親王本人的報告不時流露激憤的情緒,還猜疑道:「窺洋人之立意,似目前無可尋釁,特先發此議論,為日後藉端生事。」慈禧沒有這樣的疑心。她肚裡能撐船,不讓西方的傲慢影響自己的決策。相反地,她從建議中尋找有利於中國的東西。她以為「該使臣所論,如中國文治武備財用等事之利弊,並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都說得對。「至所論外交各情,如中國遣使分駐各國,亦係應辦之事。」針對恭親王的猜疑,她指出:「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準。」對建議書的非禮語言,她說中國只有自己努力,才能「不至為外國人所輕視」。事後,恭親王警告西方使節寫信不能「措言不遜」。結果是西方人遞交的信件,「不遜之語全刪」。
有幾位大員對赫德表示憤慨,但是慈禧從未對他反感。赫德誠實地、卓有成效地管理海關,在貪腐成風的中國社會很了不起,對她,這就足夠了。慈禧只關心大問題。不久她晉升赫德為「布政使」。直到慈禧病故,赫德都執掌著中國海關。讓一個外國人管理中國主要財政來源之一近半個世紀,是件異乎尋常的事,顯示出慈禧不含偏見和判斷力。對赫德的信任不是盲目的。她明白赫德的忠誠最終屬於他的祖國:英國。一次她與外交官郭嵩燾談到赫德。她問:赫德「為中國辦事用心否」。郭答道:「赫德是極有心計的人,在中國辦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卻是英吉利人民,豈能不關顧本國?臣往嘗問之:君自問幫中國,抑幫英國?赫德言……我只有兩邊調停。臣問:無事時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將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國人也。」
慈禧盡力不讓赫德被迫在英中兩國之間抉擇,清政府上層也鮮有人鼓吹辭掉赫德,那些反感西方的人也信任這個西方人。赫德對得起這種信任。他不光對中國財政有重大貢獻,而且幫助中國協調對外關係。凡是與西方有關的問題,恭親王都請教他,找他幫忙,他也盡力而為。而慈禧太后藉由他認識西方,儘管他們無緣見面。
*
赫德提議的現代化項目被慈禧的大員一致否決。甚至最有改革頭腦的李鴻章也激烈反對,稱電報、鐵路:「此兩事有大利於彼,有大害於我。而鐵路比銅線尤甚。」大害是:「鑿我山川,害我田廬,礙我風水,占我商民生計。」沒人能想像這些昂貴的工程對中國有什麼好處,西方人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恭親王對慈禧說,威妥瑪等「亦未將如何有益中國之處,切實指出」。
對西方的好處倒是很明顯。中國的戰爭賠款就要付清,將有一筆貿易順差,有錢辦工程。進入中國內地後,外國人發現這裡富有尚未開發的自然資源。英國海軍軍官亨利.諾爾(Henry Noel)寫道:「據權威估計,煤礦蘊藏地有四十一萬九千平方英里,是歐洲礦區的二十多倍。其他礦藏,特別是優質鐵礦,據說每個省都有不少。」
中國的地下寶藏會被外國人控制、攫取,是反對西式工程的無數理由之一。其他的還有一旦外國入侵,鐵路可以為他們運兵;旅行、通訊行業中趕車的、挑擔的、送信的、開店的都將失業。諸大員沒人認為減輕勞力是一大優點,也沒人認識到現代工程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最不能為他們接受的是機器的轟鳴與黑煙滾滾:這將觸犯自然,尤其是驚動那遍布中國大地的祖墳魂靈。
在那個年代,每個家族都有一塊自己的墳地。這些墳地神聖不可侵犯。米特福特觀察到,「在這裡,最美的環境、最好的土壤,被選用來埋葬死人。」人們認定這些墓地是他們的最終歸宿,死後他們將在那裡與親人團聚。這個前景緩解了對死亡的恐懼。那時最可怕的懲罰是挖祖墳,讓受懲者全家永無安息之地。
就像同時代人一樣,慈禧對祖墳也有著宗教式的虔誠。信仰對她不可或缺,她唯一害怕的是上天──神祕無形的、當時中國人的上帝。相信上天跟信仰佛教、道教還不矛盾,中國人的宗教情緒不像基督教世界那樣經緯分明,一個人同時信幾種教很常見。在葬禮儀式中,佛教、道教、喇嘛教的教士都會被請來輪流念經。基於這個傳統,慈禧既信佛教,也信道教。她最尊崇的是觀音,慈悲的化身,菩薩中唯一的女性,道教稱之為「觀音大士」。慈禧在自己的住處設密室供奉觀音獨自祈禱,在決定重大決策前也常到觀音像前尋求安靜,澄清頭腦。身為佛教徒,她遵循「放生」的傳統,過生日總要買大批鳥以備放生之用。到生日那天,她登上山頂,把太監手提的鳥籠一個個打開,看著鳥飛走。
一八六○年代,祖墳問題是慈禧政府拒絕現代工業的主要原因。死去的先人無論如何不能受驚。恭親王告訴外國使節他們的要求「萬不可行」,「即令失和,亦不能允」。慈禧擔心西方動武,下令「各省督撫將中外交涉事件迅速了結……萬不可一味延遲,致彼族有所藉口,激成他變,是為至要。」赫德承認:「我不知道〔中方〕有任何違約之處。」西方公司在又一番爭取之後放棄了努力。似乎箭在弦上的中
*
隨著太平天國的終結,其他農民戰爭也接二連三地失敗,燃燒多年的造反烈火一點點化為灰燼中將滅的火星。奪權之後不幾年,慈禧在全國恢復了和平。這樹立了她在統治階層中不爭的權威,同時減少了對她未來政策的反對力量。慈禧的政策是振興中國。大大小小的戰爭耗費了三億兩銀子,大部分地區滿目瘡痍,北京街頭到處是乞丐,通常不在人前露面的婦女,也近乎赤身露體地向行人討食。然而,在慈禧統治下,中國不僅迅速恢復了元氣,而且開始了「同治中興」。
中興的關鍵因素是有了一個可觀的新財源:開放政策帶來與日俱增的對外貿易,海關稅收直線上升。慈禧早就看到外貿的巨大潛力。政變後不久的一八六二年初,她跟恭親王提到太平軍威脅下的上海時說:「上海僻處一隅,勢如累卵,而該處華洋商賈輻輳,餉源甚裕。近聞兩月之間,洋稅已收至八十萬兩。」她要竭力「保全」上海。她推動對外貿易,一八六三年,六千八百多艘貨船來到上海,而她丈夫執政時僅僅年均一千艘。
要擴展對外貿易,中國必須有高效率並且廉潔的海關。經恭親王推薦,慈禧任命已在海關工作的二十八歲英國北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為「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不到一年,她傳旨嘉獎赫德,封他為正三品大員「按察使」。
赫德與慈禧同年,出生於一八三五年,就讀貝爾法斯特的女王學院。他初來中國時十九歲,聰明、誠摯、天真,預備做英國領事部門的翻譯。除了傑出的語言才能,他還得過各種不同領域的獎,包括邏輯學、拉丁文、英國文學、歷史、玄學、自然科學、法理學和地理學。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關心道德與正義,並且深切地同情中國人。日記中有一段描述剛到香港時,一天傍晚在海邊散步,同行者叫斯德斯(Stace)。赫德寫道:「斯德斯對待中國人的行為叫我很吃驚。他上了一條船,叫他們划出港,他們不肯划。這是他們的晚飯時間,對他們是神聖的,他們一定要吃完才工作。可他竟用手杖把他們的東西甩到水裡去,還用手杖戳點他們。」
在中國工作十年,赫德被一致認為公正而才幹超人,善於調停並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協。他知道自己的長處,十分自信。當他接到正式任命書時,他沒有急於拆開,而是「照常吃我的早餐,然後像往常一樣,讀聖經、祈禱……看當天來信。」在一堆來信中,他最後看的才是任命他為總稅務司的公文。
赫德把舊式海關改造為具有一整套嚴格管理制度、高效率、無貪腐的現代機構,為北京政府提供了一個穩定並不斷增長的稅收來源,對中國經濟發展作用極大。到了一八六五年,他已上交三千二百多萬兩銀子的關稅。對英法的戰爭賠款由海關收入支付,到一八六六年中完全付清,國計民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有了新財源,慈禧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大量進口糧食。中國長期以來生產的糧食不夠養活人口,清王朝一直禁止糧食出口。但全國性的糧食進口據海關紀錄是一八六七年。那年慈禧政府用一百一十萬兩銀子購買大米。「採買洋米」是赫德海關的重要工作之一,有關官員受到慈禧的嘉獎。
雇傭赫德和一大批西方人在海關任職,自然引起部分中國官員不滿。慈禧堅持政策不變。
*
慈禧政府的宗旨是建設強盛的中國。赫德想向他們說明,這個目標只有「現代化」才能達到。他在日記裡寫道,他要「讓這個國家擁有基督教文明帶給人類的一切舒適、一切福祉,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他要中國「進步」,而進步在那個年代意味著新式採礦、電報電話,尤其是鐵路。一八六五年十月,赫德給恭親王遞上一份建議書:「局外旁觀論」。
赫德急切地要「更新」古老的中國,開的是一劑苦藥。他稱:「自四海各國觀之,竟莫弱於中國。」中國皇上「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國民性差勁:「常聞外論,中國官民,大半可以利動,勢處極弱而不守信。」如果不照他說的辦,將來會「為人所勉強」,「必動干戈」,而「無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勝之勢。」
赫德的話代表了當時西方人一種普遍的態度,即他們「比中國人更知道中國需要什麼」,他們應當「掐住這個古老帝國的喉嚨,逼著她進步」。
恭親王把赫德的建議書壓了幾個月才呈給慈禧。這一不尋常的拖延很可能是因為他怕慈禧震怒之下解雇赫德,用一句老話說:失去這隻會下金蛋的雞。儘管慈禧鼓勵尖銳的批評和直言不諱的建議,但沒人敢用如此傲慢的口氣「恫嚇挾制」。奕訢拿不準慈禧會如何反應。他決定讓赫德暫離中國,這樣如果慈禧一氣之下要辭掉他,還有迴旋的餘地。赫德曾要求回國休假,正是在這時,他的休假要求批准了。
赫德於一八六六年三月底離開中國。四月一日,他的建議書呈遞慈禧。同時還有威妥瑪的「說帖」,談的是大致同樣的問題,用的是大致同樣的口氣。呈上這些文件之後,恭親王忐忑不寧。一天,英國公使館隨員米特福特來見他,再提「鐵路、電報和那些說了一百遍的老話題」。隨員注意到,「親王非常緊張不安,像隻受驚的兔子。」
恭親王低估了慈禧。她仔細看了兩份建議書,然後把它們發給十名外交、貿易和地方大員,請他們提意見。她的信上沒有對赫德、威妥瑪的憤怒和敵意,而恭親王本人的報告不時流露激憤的情緒,還猜疑道:「窺洋人之立意,似目前無可尋釁,特先發此議論,為日後藉端生事。」慈禧沒有這樣的疑心。她肚裡能撐船,不讓西方的傲慢影響自己的決策。相反地,她從建議中尋找有利於中國的東西。她以為「該使臣所論,如中國文治武備財用等事之利弊,並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都說得對。「至所論外交各情,如中國遣使分駐各國,亦係應辦之事。」針對恭親王的猜疑,她指出:「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準。」對建議書的非禮語言,她說中國只有自己努力,才能「不至為外國人所輕視」。事後,恭親王警告西方使節寫信不能「措言不遜」。結果是西方人遞交的信件,「不遜之語全刪」。
有幾位大員對赫德表示憤慨,但是慈禧從未對他反感。赫德誠實地、卓有成效地管理海關,在貪腐成風的中國社會很了不起,對她,這就足夠了。慈禧只關心大問題。不久她晉升赫德為「布政使」。直到慈禧病故,赫德都執掌著中國海關。讓一個外國人管理中國主要財政來源之一近半個世紀,是件異乎尋常的事,顯示出慈禧不含偏見和判斷力。對赫德的信任不是盲目的。她明白赫德的忠誠最終屬於他的祖國:英國。一次她與外交官郭嵩燾談到赫德。她問:赫德「為中國辦事用心否」。郭答道:「赫德是極有心計的人,在中國辦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卻是英吉利人民,豈能不關顧本國?臣往嘗問之:君自問幫中國,抑幫英國?赫德言……我只有兩邊調停。臣問:無事時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將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國人也。」
慈禧盡力不讓赫德被迫在英中兩國之間抉擇,清政府上層也鮮有人鼓吹辭掉赫德,那些反感西方的人也信任這個西方人。赫德對得起這種信任。他不光對中國財政有重大貢獻,而且幫助中國協調對外關係。凡是與西方有關的問題,恭親王都請教他,找他幫忙,他也盡力而為。而慈禧太后藉由他認識西方,儘管他們無緣見面。
*
赫德提議的現代化項目被慈禧的大員一致否決。甚至最有改革頭腦的李鴻章也激烈反對,稱電報、鐵路:「此兩事有大利於彼,有大害於我。而鐵路比銅線尤甚。」大害是:「鑿我山川,害我田廬,礙我風水,占我商民生計。」沒人能想像這些昂貴的工程對中國有什麼好處,西方人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恭親王對慈禧說,威妥瑪等「亦未將如何有益中國之處,切實指出」。
對西方的好處倒是很明顯。中國的戰爭賠款就要付清,將有一筆貿易順差,有錢辦工程。進入中國內地後,外國人發現這裡富有尚未開發的自然資源。英國海軍軍官亨利.諾爾(Henry Noel)寫道:「據權威估計,煤礦蘊藏地有四十一萬九千平方英里,是歐洲礦區的二十多倍。其他礦藏,特別是優質鐵礦,據說每個省都有不少。」
中國的地下寶藏會被外國人控制、攫取,是反對西式工程的無數理由之一。其他的還有一旦外國入侵,鐵路可以為他們運兵;旅行、通訊行業中趕車的、挑擔的、送信的、開店的都將失業。諸大員沒人認為減輕勞力是一大優點,也沒人認識到現代工程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最不能為他們接受的是機器的轟鳴與黑煙滾滾:這將觸犯自然,尤其是驚動那遍布中國大地的祖墳魂靈。
在那個年代,每個家族都有一塊自己的墳地。這些墳地神聖不可侵犯。米特福特觀察到,「在這裡,最美的環境、最好的土壤,被選用來埋葬死人。」人們認定這些墓地是他們的最終歸宿,死後他們將在那裡與親人團聚。這個前景緩解了對死亡的恐懼。那時最可怕的懲罰是挖祖墳,讓受懲者全家永無安息之地。
就像同時代人一樣,慈禧對祖墳也有著宗教式的虔誠。信仰對她不可或缺,她唯一害怕的是上天──神祕無形的、當時中國人的上帝。相信上天跟信仰佛教、道教還不矛盾,中國人的宗教情緒不像基督教世界那樣經緯分明,一個人同時信幾種教很常見。在葬禮儀式中,佛教、道教、喇嘛教的教士都會被請來輪流念經。基於這個傳統,慈禧既信佛教,也信道教。她最尊崇的是觀音,慈悲的化身,菩薩中唯一的女性,道教稱之為「觀音大士」。慈禧在自己的住處設密室供奉觀音獨自祈禱,在決定重大決策前也常到觀音像前尋求安靜,澄清頭腦。身為佛教徒,她遵循「放生」的傳統,過生日總要買大批鳥以備放生之用。到生日那天,她登上山頂,把太監手提的鳥籠一個個打開,看著鳥飛走。
一八六○年代,祖墳問題是慈禧政府拒絕現代工業的主要原因。死去的先人無論如何不能受驚。恭親王告訴外國使節他們的要求「萬不可行」,「即令失和,亦不能允」。慈禧擔心西方動武,下令「各省督撫將中外交涉事件迅速了結……萬不可一味延遲,致彼族有所藉口,激成他變,是為至要。」赫德承認:「我不知道〔中方〕有任何違約之處。」西方公司在又一番爭取之後放棄了努力。似乎箭在弦上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