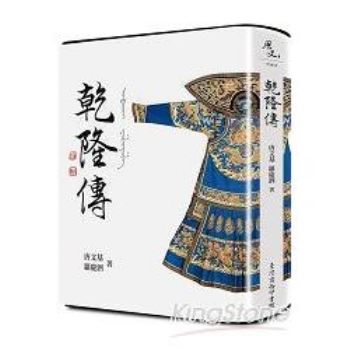第一章 從皇孫到初政(康熙五十年至乾隆五年)
靑少年弘曆
一、弘曆出世
康熙五十年(西元一七一一年)八月十三日子夜,雍親王胤禛忐忑不安的心情,頓時興奮起來。他得知格格①鈕祜祿氏生下了一個男孩。雍王邸(後改稱雍和宮)霎時間似乎明亮得多。
此前,胤禛已得四子。長子弘暉,出皇后烏喇那拉氏,康熙四十三年八歲夭折。齊妃李氏爲胤禛生有三子,卽弘盼、弘昀、弘時。但弘盼未滿兩周歲殤逝,還不曾敍齒排行;弘昀排行第二,十一歲死去;眼前就只有八歲的三子弘時。胤禛貴爲親王,僅有一子,未免單薄。那正是諸王子間爲爭王儲地位明爭暗鬥白熱化之時。太子胤礽廢而復立,而昏庸暴戾秉性不改,康熙是斷難容忍的,其地位岌岌可危。胤禛與幾個兄弟一樣有覬覦皇位之心,卻處處巧加掩飾,口頭上説,儲貳之事,「避之不能,尙有希圖之舉乎!」暗中卻在作周密部署,以川撫年羹堯與同母弟胤祥等爲核心組成了奪權小集團。胤禛心裏明白,在諸阿哥中,誰能得到老皇帝的歡心,誰就能在未來主宰天下。多年來,他按這一信條制約自己的言行。現在,他又給康熙老皇帝增添一個孫子,這肯定會使自己在康熙内心天平上,增加一個砝碼。
鈕祜祿氏是四品典儀凌柱的女兒,乃父官爵並不顯。她生下的這個兒子,排行第四,取名弘曆。弘曆便是後來在中國歷史上執政長達六十三年的乾隆皇帝。
淸朝的前幾位皇帝,歷來都有些奇怪的傳説。諸如順治因失戀而出家當和尙;康熙被兒子雍正害死,雍正爲了奪取皇位,篡改乃父遺詔。這位未來的乾隆皇帝弘曆傳説更離奇,説他不是滿族血統,而是漢族官宦之後。淸季陳某,署名「有嬀血胤」,所撰《淸秘史》中〈弘曆非滿種與易服色之不成〉篇寫道:
(浙江海寧)陳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漸聞於時。至(陳)之遴始以降淸,位至極品。厥後,陳詵、陳世倌、陳元龍等父子叔侄,並位極人臣,遭際最隆。康熙間,雍正與陳氏尤相善,會兩家各生子,其歲月日時皆同。雍正聞乃大喜,命抱以來,久之始送歸,則竟非己子,且易男爲女矣。陳氏殊震怖,顧不敢剖辨,遂力秘之。
《秘史》所説陳氏,指的是浙江海寧陳元龍。據陳敬懋《海寧渤海陳氏宗譜第五修》記載②,陳元龍有一妻二妾,共生一男二女③。兒子陳邦直,生於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④,比弘曆大十六歲。陳邦直的第二個女兒嫁給徐德秩。徐德秩是康熙時左都御史徐乾學的孫子,據乾隆《梧州府志》卷十二《職官志》載,於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任梧州知府。另據闕名《徐乾學家譜》記載,徐德秩生於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其妻是海寧陳元龍次女,與徐德秩同齡⑤。也就是説,陳元龍次女比弘曆大二十四歲,更勿論其長女了。可見,《淸秘史》所云:「會兩家各生子」,雍正以女易陳元龍之子云云,純係無稽之談。這本書的作者有著濃厚的排滿思想,《淸秘史》的序甚至不用淸朝年號,用的是黃帝紀年。他杜撰弘曆非滿種這天方夜譚,其用心不是很淸楚嗎?
二、康熙帝掌上明珠
弘曆聰明伶俐,六歲就學,過目成誦。他先後受業於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朱軾、徐元夢和翰林院編修蔡世遠等人,這幾個人各有專長。福敏字龍翰,滿洲鑲白禛人。雍正請他爲弘曆啓蒙,無疑是因爲福敏性剛直,能夠對自己兒子嚴格督課。在福敏指導下,弘曆於十三歲以前,已熟讀《詩經》、《尙書》、《易經》、《春秋》和《戴氏禮記》等儒家經典和宋儒著作,以及《通鑑綱目》、《史記》、《漢書》等史籍,學業大有長進⑥。日後弘曆曾説,自己「沖齡就儒時,(福敏)啓迪之力多也」⑦。朱軾字若曦,江西高安人,負一時重望,被雍正命爲弘曆師傅,設敎席於懋勤殿,受弘曆行拜師禮。朱軾以經訓進講,授弘曆賈誼、董仲舒和宋儒學説⑧。蔡世遠字聞之,福建漳浦人,是當時著名學者,雍正元年在上書房敎弘曆等讀四書五經、宋儒著述以及諸史、載籍。蔡世遠講儒學,「必引而近之,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卽以近傍實際,闡述儒家理論,而不是引導弘曆讀死書。他講史,「則卽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述」⑨,卽通過對以往朝代興亡、古人沉浮以及執政者思想修養等剖析,向弘曆灌輸治國平天下的歷史經驗和敎訓。這幾位老師對弘曆的影響很大,弘曆自己説「於軾得學之體,於世遠得學之用,於福敏得學之基」⑩。
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春,胤禛的私園圓明園牡丹盛開。有一天,康熙乘興到園中「鏤月開雲」牡丹台觀花。胤禛向康熙引見弘曆。十二歲的弘曆長得前庭方廣,眉目淸秀,身材頎長,舉步穩重,談吐聲音旣洪亮又悅耳。眼前這個翩翩少年,康熙一見就喜愛上了,卽時帶回宮中「養育撫視」。從此,祖孫形影相隨,據弘曆後來回憶:「夙興夜寐,日覲天顏;綈几繙書,或示章句;玉筵傳膳,每賜芳飴;批閱章奏,屏息待勞;引見官吏,承顏立側」(11)。儲君問題長時間折磨著老皇帝。父子成仇,兄弟側目,垂暮老人内心是痛苦的。如今,這個小孫子成了他精神寄託。宋儒周敦頤《愛蓮説》,是當時靑少年必讀名作。有一天,康熙要弘曆背誦。弘曆朗朗誦道: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淸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淸,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弘曆不僅背誦娓娓動聽,而且解釋融徹,康熙「獎悅彌至」。騎馬射箭,原是愛新覺羅氏祖傳家法。康熙要弘曆向貝勒允禧學射箭,向莊親王允祿學火器。這二人也是皇族中佼佼者。允禧是康熙的第二十一子,不僅善射箭,而且能詩能畫。允祿是淸太宗皇太極第五子碩塞的兒子,精數學、通樂律。弘曆在他們傳授下,騎射本領日見長進,無論是宮門挽弓,還是南苑圍獵,命中率都甚高。垂髫少年的英武氣概,觀者嘆服。
當年秋天,弘曆被康熙帶往避暑山莊,住在萬壑松風讀書。萬壑松風在山莊的湖南山上松林之中。一天,御舟泊晴碧亭,康熙在船上遠遠地傳呼弘曆。弘曆應聲從岩壁滿布的山坡上,踏跳而下。這可使老皇帝心驚肉跳,連聲高呼:「勿疾行,恐致蹉跌!」直到弘曆上了御舟,康熙才鬆一口氣。祖孫情深,於兹可見。
避暑山莊近側獅子園,是康熙賞給胤禛的私園。一天,康熙攜弘曆臨幸獅子園,傳見了弘曆生母鈕祜祿氏。老皇帝愛屋及烏,連聲稱讚鈕祜祿氏是「有福之人」。這一年木蘭秋獮,康熙帶著弘曆到永安莽喀圍場打獵。康熙射倒一隻熊後,命弘曆再射。弘曆剛上馬,帶傷倒地的熊突然立起撲來。弘曆控轡自若,毫不驚慌。康熙急忙補一槍,將熊擊倒。老人眼見小孫子臨危不懼,十分讚賞。回帳之後,激動地對溫蕙貴妃説:此兒「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這一年十一月,康熙病危。臨終前,他對大學士馬齊説:「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爲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爲太子」(12)。康熙彌留之際,已把大淸的江山,付託給胤禛和愛孫弘曆了。
登上皇帝寶座
一、《樂善堂文鈔》的輿論準備
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去世,胤禛繼位。第二年改元雍正。十二歲的弘曆成了皇子。
元年(一七二三年)正月,雍正首行大祀之典。祈穀禮成,召弘曆到養心殿,賜食臠。據史家解釋,這是寓意「承福受胙」,雍正有意將來把江山付託給弘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符合雍正賜臠本意,我們在以後便會明白,雍正元年,新皇帝確已把弘曆定爲自己的接班人。
雍正八年秋,年僅二十歲的弘曆,將他從十四歲以來的詩文,挑選出一部分,輯成《樂善堂文鈔》付梓。樂善堂是弘曆的書齋。他在《樂善堂記》一文中寫道:
余有書屋數間,淸爽幽靜,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呈於前。菜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於人以爲善之意也。(13)
應當指出,今存於《四庫全書》集部的《樂善堂集定本》共三十卷,是乾隆二十三年戶部尙書蔣溥等奉命重輯的,非雍正八年《樂善堂文鈔》原本。《樂善堂文鈔》刊行後,乾隆曾多次重訂。但是,以後增加進去的詩文,也都是作者在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前的作品。所以,《樂善堂集》不論文鈔還是定本,都是弘曆靑年時期所作。
關於編輯刊刻《樂善堂文鈔》目的,弘曆在序言中寫道:
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講論至再至三。顧質魯識昧,日取先聖賢所言者以內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於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課論一篇,間以詩歌雜文,雖不敢爲奇辭詭論,以自外於經傳儒先之宗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載道者。內返竊深慚恧,每自念受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爲之擇賢師傅以受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遊之中,得以厭飫詩書之味,而窮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養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懼。用是擇取庚戌(雍正八年)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後,序、論、書、記、雜文、詩賦,分爲十有四卷,置在案頭,便於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顧行,行顧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檢所行。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14)
弘曆説他刊刻《樂善堂文鈔》,是爲了常常能以自己所言,自檢所行。這是堂皇之論,究其眞實目的,絕非如此單純。《樂善堂文鈔》付梓時,弘曆請十四個人爲他作序。其中有莊親王允祿、康熙第十七子果親王允禮、貝勒允禧、平郡王福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以及當時在士林頗有名氣的蔡世遠、邵基、胡熙等人,還有他自己的弟弟弘晝。這些人的序言,對弘曆是一片讚揚聲。或説作者飽覽羣書,精通經史詩賦,「自經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閫奧,諸賦之源流,靡不情覽」(張廷玉序);「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章,窮其旨趣,探其精蘊」(朱軾序)。或説作者才思敏捷,「每爲文筆不停輟,千言立就,而文思泉湧,采翰雲生」(福彭序)。或説《樂善堂文鈔》是稀世之作,「其氣象之崇宏,則川渟嶽峙也;其心胸之開浚,則風發泉湧也;其詞采之高華,則雲蒸霞蔚也;其音韻之調諧,則金和玉節也」(邵基序)。這些語言,除了含有阿諛奉承的調子之外,更多的是文人互相吹捧積習的表露。但耐人尋味的是,有人已經把弘曆吹捧爲懷有治國平天下道德和才能的儲君。如張廷玉説: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古通今之學,循循乎祗遹聖訓,敬勤無斁。
鄂爾泰説: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聖之心傳者,莫不此會而極。
朱軾説:
聖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發而爲蕩平正直之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皇子天稟純粹,志氣淸明,晨夕侍奉之下,其熏陶涵育聖德聖訓者,固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承無斁,優遊厭飫。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旣接,進德修業之功,得而窺其所至。
旣是「天授之才」,「又上接列聖之心傳」,「進德修業之功」更不可「窺其所至」,未來的天子已經在這些序言中呼之欲出了。
弘曆聰明過人,對自己的未來,會有樂觀的估計。他不必像父輩那樣爲奪權而明爭暗鬥。他要做的事情是,應當在皇族和朝臣之中,樹立起自己未來英明君主的形象。其妙著就是借助於這一部《樂善堂文鈔》,以表示自己不僅精通書史,擅長詩賦,而且有經世之才。果然,他的弟弟弘晝在序言中公開表示自愧弗如:
弟之視兄,雖所處則同,而會心有淺深,氣力有厚薄,屬辭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語也。吾兄隨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寢食相同。及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愼溫恭。皇父見之,未嘗不喜。
皇父聞之,未嘗不樂。……兄之樂善無窮而文思因以無盡。凡古聖賢之微言大義,修身體道之要,經世宰物之方,靡不發揮衍繹娓娓暢爲。
作者不僅承認弘曆曾受皇祖撫愛,而且説弘曆已得聖賢「經世宰物之方」,自己不敢與哥哥「同年而語」。弘晝是皇位最有力的競爭者,他旣然心悅誠服,誰還能與弘曆匹敵。在《樂善堂文鈔》中,弘曆多次提到康熙對自己的鍾愛。説皇祖曾賜他「長幅一,復賜橫幅一、扇一」,「恩寵迥異他人」(15),「得皇祖之澤最深」(16)。如此念念不忘皇祖恩寵,儘管包含著孫子對祖父的懷念,但這畢竟是弘曆最榮耀的政治資本,怎能不經常注於筆端。總之,弘曆刊刻《樂善堂文鈔》是有政治意圖的,目的在於爲日後當皇帝作輿論準備。他把自己的讀書處命之曰「樂善堂」,「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這無異於以大舜自詡。
二、受詔登基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在圓明園處理政務,雖身體偶感不適,但未曾重視。二十二日深夜,病情突然加劇。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公豐盛額、訥親、内大臣海望應召入寢宮。二十三日子時,這位統治中國十三年的皇帝去世了,年僅五十八歲。關於雍正死因,或説中風,或説服用了道士煉的丹藥。孰是孰非,有待研究。還有一種傳説,雍正是被呂留良的女兒呂四娘刺殺。呂留良因反滿文字賈禍,被戮死梟首。乃女呂四娘學得一身武藝,入宮刺殺雍正。這種傳説當然缺乏依據。
雍正去世,内宮一片哭聲。鄂爾泰、張廷玉對允祿、允禮説,雍正「因傳位大事,親書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無有知者。此旨收藏宮中,應急請出,以正大統」(17)。早在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冬時,雍正染病,寒熱時發,飲食不常,夜不能熟寢。八年六月,召見允祿、弘曆、弘晝和大學士、内大臣數人,「面諭遺詔大意」(18)。九月,又將立儲密詔示知張廷玉,十年正月再次密示鄂爾泰、張廷玉,「此時聖諭曰,汝二人外,再無一人知之」(19)。鄂、張所説「親書密旨」,就是指十年正月這一次。
不久,總管太監捧出黃封一函,内藏硃筆親書傳位弘曆詔。張廷玉於燈下宣讀,弘曆跪拜受命之後宣布,「遵皇考遺旨,令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
淸朝的秘密建儲制度始於雍正。康熙年間,康熙帝二次立太子,又二次廢太子。儲君問題,幾乎折騰了半個世紀。雍正接受這一敎訓,創立了秘密立儲辦法。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乾淸宮西暖閣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和九卿,宣布:
今朕諸子尙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愼,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旣將大事付託於朕,朕身爲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淸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20)
但是,據雍正去世時在場人張廷玉記載,當夜用的是雍正十年藏於圓明園的傳位詔。這是可信的。雍正遺體夤夜運回宮中,「倉卒中得官廄駑馬乘之,幾至蹶踣」(21)。這短短十餘字可以看出,其時行色匆忙,情景相當狼狽。
八月二十四日,弘曆頒布數道諭旨。其中諭内外大臣旨,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朕受皇考付託,凡皇考辦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當敬謹繼述。這實質上是宣布自己將繼續處理先帝未竟之業,維護政策連續性。第二,諸王大臣均是深受重恩之人,各宜殫心竭力,輔朕不逮。這是要求朝中大臣必須效忠自己。第三,外省文武大臣,如果因皇考「龍駛上賓」,將已經上奏的本章「中途趕回,另行反改,或到京後撤回不進者,經朕查出,定行從重治罪」(22)。這是要求各級地方官處理事務應一如旣往,不得欺慢。
還有一道是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莊親王允祿等人的,内容是關於鄂爾泰、張廷玉配享太廟問題:
雍正八年六月內,欽奉皇考諭旨,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聖祖仁皇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巨。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爲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終始不渝。朕萬年之後,二臣著配享太廟。今朕欲將皇考此旨入於遺詔內頒發。(23)
配享太廟對於封建官僚來説,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弘曆宣布要將此事寫入皇考遺詔,等於以雍正遺詔作爲最權威的兌現保證。這種超出常格的作法,目的在於拉攏這二位滿漢大臣的領袖人物,並通過他們爭取整個官僚隊伍對自己效忠。鄂、張二人故作姿態,「屢行固辭」,謙讓一番,最後還是感激涕零地接受了。兩天後,鄂、張二人上奏,「不敢當輔政之名,請照例稱總理事務」。弘曆同意,降旨「凡宮門一切陳奏,先告知總理事務王大臣,再行進呈」(24)。
弘曆還注意到穩定内宮問題。八月二十五日,他對太監頒諭説,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妄行傳説。皇太后仁慈,撫愛朕躬,凡有所知,豈有不告之理?但市井傳説,多有舛誤。今後凡外間傳聞,無故向廷傳説者,卽爲背法,查出定行正法。這一諭旨是爲了防止太監向内宮走遞朝廷信息,撥弄是非,干擾政局。
弘曆還降諭都統莽鵠立,命令他把煉丹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趕出西苑。雍正生前迷信道家丹藥,張、王等就在西苑替皇帝煉丹。所以,雍正突然死亡,史家疑爲丹藥中毒,絕非捕風捉影之論。而弘曆在乃父屍骨未寒之時,就急忙把煉丹道士驅逐出西苑,更使人有理由相信丹藥對雍正健康造成嚴重損害。弘曆這份詔諭寫得很奇妙:
皇考萬幾之餘,聞外間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爲遊戲淸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爲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卽正法,決不寬貸。(25)
上諭從爲親者尊者諱角度出發,輕描淡寫地説他父親視張太虛等煉丹術爲「遊戲消閒之具」,也知道這批人是「市井無賴之徒」,從未用過一藥。這位年輕皇帝對煉丹術的鄙視與厭惡,表明他具有反對愚昧的可貴精神。
九月三日黎明,大駕鹵簿全設。弘曆先著素服向雍正帝梓宮行九拜禮。然後更換禮服,奉皇太后到永壽宮,亦行九拜禮。接著,至中和殿受内大臣和執事官行拜,再到太和殿卽皇帝位,受親王以及文武百官、朝鮮等國使臣朝拜,頒詔天下,以明年爲乾隆元年。
靑少年弘曆
一、弘曆出世
康熙五十年(西元一七一一年)八月十三日子夜,雍親王胤禛忐忑不安的心情,頓時興奮起來。他得知格格①鈕祜祿氏生下了一個男孩。雍王邸(後改稱雍和宮)霎時間似乎明亮得多。
此前,胤禛已得四子。長子弘暉,出皇后烏喇那拉氏,康熙四十三年八歲夭折。齊妃李氏爲胤禛生有三子,卽弘盼、弘昀、弘時。但弘盼未滿兩周歲殤逝,還不曾敍齒排行;弘昀排行第二,十一歲死去;眼前就只有八歲的三子弘時。胤禛貴爲親王,僅有一子,未免單薄。那正是諸王子間爲爭王儲地位明爭暗鬥白熱化之時。太子胤礽廢而復立,而昏庸暴戾秉性不改,康熙是斷難容忍的,其地位岌岌可危。胤禛與幾個兄弟一樣有覬覦皇位之心,卻處處巧加掩飾,口頭上説,儲貳之事,「避之不能,尙有希圖之舉乎!」暗中卻在作周密部署,以川撫年羹堯與同母弟胤祥等爲核心組成了奪權小集團。胤禛心裏明白,在諸阿哥中,誰能得到老皇帝的歡心,誰就能在未來主宰天下。多年來,他按這一信條制約自己的言行。現在,他又給康熙老皇帝增添一個孫子,這肯定會使自己在康熙内心天平上,增加一個砝碼。
鈕祜祿氏是四品典儀凌柱的女兒,乃父官爵並不顯。她生下的這個兒子,排行第四,取名弘曆。弘曆便是後來在中國歷史上執政長達六十三年的乾隆皇帝。
淸朝的前幾位皇帝,歷來都有些奇怪的傳説。諸如順治因失戀而出家當和尙;康熙被兒子雍正害死,雍正爲了奪取皇位,篡改乃父遺詔。這位未來的乾隆皇帝弘曆傳説更離奇,説他不是滿族血統,而是漢族官宦之後。淸季陳某,署名「有嬀血胤」,所撰《淸秘史》中〈弘曆非滿種與易服色之不成〉篇寫道:
(浙江海寧)陳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漸聞於時。至(陳)之遴始以降淸,位至極品。厥後,陳詵、陳世倌、陳元龍等父子叔侄,並位極人臣,遭際最隆。康熙間,雍正與陳氏尤相善,會兩家各生子,其歲月日時皆同。雍正聞乃大喜,命抱以來,久之始送歸,則竟非己子,且易男爲女矣。陳氏殊震怖,顧不敢剖辨,遂力秘之。
《秘史》所説陳氏,指的是浙江海寧陳元龍。據陳敬懋《海寧渤海陳氏宗譜第五修》記載②,陳元龍有一妻二妾,共生一男二女③。兒子陳邦直,生於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④,比弘曆大十六歲。陳邦直的第二個女兒嫁給徐德秩。徐德秩是康熙時左都御史徐乾學的孫子,據乾隆《梧州府志》卷十二《職官志》載,於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任梧州知府。另據闕名《徐乾學家譜》記載,徐德秩生於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其妻是海寧陳元龍次女,與徐德秩同齡⑤。也就是説,陳元龍次女比弘曆大二十四歲,更勿論其長女了。可見,《淸秘史》所云:「會兩家各生子」,雍正以女易陳元龍之子云云,純係無稽之談。這本書的作者有著濃厚的排滿思想,《淸秘史》的序甚至不用淸朝年號,用的是黃帝紀年。他杜撰弘曆非滿種這天方夜譚,其用心不是很淸楚嗎?
二、康熙帝掌上明珠
弘曆聰明伶俐,六歲就學,過目成誦。他先後受業於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朱軾、徐元夢和翰林院編修蔡世遠等人,這幾個人各有專長。福敏字龍翰,滿洲鑲白禛人。雍正請他爲弘曆啓蒙,無疑是因爲福敏性剛直,能夠對自己兒子嚴格督課。在福敏指導下,弘曆於十三歲以前,已熟讀《詩經》、《尙書》、《易經》、《春秋》和《戴氏禮記》等儒家經典和宋儒著作,以及《通鑑綱目》、《史記》、《漢書》等史籍,學業大有長進⑥。日後弘曆曾説,自己「沖齡就儒時,(福敏)啓迪之力多也」⑦。朱軾字若曦,江西高安人,負一時重望,被雍正命爲弘曆師傅,設敎席於懋勤殿,受弘曆行拜師禮。朱軾以經訓進講,授弘曆賈誼、董仲舒和宋儒學説⑧。蔡世遠字聞之,福建漳浦人,是當時著名學者,雍正元年在上書房敎弘曆等讀四書五經、宋儒著述以及諸史、載籍。蔡世遠講儒學,「必引而近之,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卽以近傍實際,闡述儒家理論,而不是引導弘曆讀死書。他講史,「則卽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述」⑨,卽通過對以往朝代興亡、古人沉浮以及執政者思想修養等剖析,向弘曆灌輸治國平天下的歷史經驗和敎訓。這幾位老師對弘曆的影響很大,弘曆自己説「於軾得學之體,於世遠得學之用,於福敏得學之基」⑩。
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春,胤禛的私園圓明園牡丹盛開。有一天,康熙乘興到園中「鏤月開雲」牡丹台觀花。胤禛向康熙引見弘曆。十二歲的弘曆長得前庭方廣,眉目淸秀,身材頎長,舉步穩重,談吐聲音旣洪亮又悅耳。眼前這個翩翩少年,康熙一見就喜愛上了,卽時帶回宮中「養育撫視」。從此,祖孫形影相隨,據弘曆後來回憶:「夙興夜寐,日覲天顏;綈几繙書,或示章句;玉筵傳膳,每賜芳飴;批閱章奏,屏息待勞;引見官吏,承顏立側」(11)。儲君問題長時間折磨著老皇帝。父子成仇,兄弟側目,垂暮老人内心是痛苦的。如今,這個小孫子成了他精神寄託。宋儒周敦頤《愛蓮説》,是當時靑少年必讀名作。有一天,康熙要弘曆背誦。弘曆朗朗誦道: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淸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淸,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弘曆不僅背誦娓娓動聽,而且解釋融徹,康熙「獎悅彌至」。騎馬射箭,原是愛新覺羅氏祖傳家法。康熙要弘曆向貝勒允禧學射箭,向莊親王允祿學火器。這二人也是皇族中佼佼者。允禧是康熙的第二十一子,不僅善射箭,而且能詩能畫。允祿是淸太宗皇太極第五子碩塞的兒子,精數學、通樂律。弘曆在他們傳授下,騎射本領日見長進,無論是宮門挽弓,還是南苑圍獵,命中率都甚高。垂髫少年的英武氣概,觀者嘆服。
當年秋天,弘曆被康熙帶往避暑山莊,住在萬壑松風讀書。萬壑松風在山莊的湖南山上松林之中。一天,御舟泊晴碧亭,康熙在船上遠遠地傳呼弘曆。弘曆應聲從岩壁滿布的山坡上,踏跳而下。這可使老皇帝心驚肉跳,連聲高呼:「勿疾行,恐致蹉跌!」直到弘曆上了御舟,康熙才鬆一口氣。祖孫情深,於兹可見。
避暑山莊近側獅子園,是康熙賞給胤禛的私園。一天,康熙攜弘曆臨幸獅子園,傳見了弘曆生母鈕祜祿氏。老皇帝愛屋及烏,連聲稱讚鈕祜祿氏是「有福之人」。這一年木蘭秋獮,康熙帶著弘曆到永安莽喀圍場打獵。康熙射倒一隻熊後,命弘曆再射。弘曆剛上馬,帶傷倒地的熊突然立起撲來。弘曆控轡自若,毫不驚慌。康熙急忙補一槍,將熊擊倒。老人眼見小孫子臨危不懼,十分讚賞。回帳之後,激動地對溫蕙貴妃説:此兒「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這一年十一月,康熙病危。臨終前,他對大學士馬齊説:「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爲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爲太子」(12)。康熙彌留之際,已把大淸的江山,付託給胤禛和愛孫弘曆了。
登上皇帝寶座
一、《樂善堂文鈔》的輿論準備
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去世,胤禛繼位。第二年改元雍正。十二歲的弘曆成了皇子。
元年(一七二三年)正月,雍正首行大祀之典。祈穀禮成,召弘曆到養心殿,賜食臠。據史家解釋,這是寓意「承福受胙」,雍正有意將來把江山付託給弘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符合雍正賜臠本意,我們在以後便會明白,雍正元年,新皇帝確已把弘曆定爲自己的接班人。
雍正八年秋,年僅二十歲的弘曆,將他從十四歲以來的詩文,挑選出一部分,輯成《樂善堂文鈔》付梓。樂善堂是弘曆的書齋。他在《樂善堂記》一文中寫道:
余有書屋數間,淸爽幽靜,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呈於前。菜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於人以爲善之意也。(13)
應當指出,今存於《四庫全書》集部的《樂善堂集定本》共三十卷,是乾隆二十三年戶部尙書蔣溥等奉命重輯的,非雍正八年《樂善堂文鈔》原本。《樂善堂文鈔》刊行後,乾隆曾多次重訂。但是,以後增加進去的詩文,也都是作者在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前的作品。所以,《樂善堂集》不論文鈔還是定本,都是弘曆靑年時期所作。
關於編輯刊刻《樂善堂文鈔》目的,弘曆在序言中寫道:
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講論至再至三。顧質魯識昧,日取先聖賢所言者以內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於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課論一篇,間以詩歌雜文,雖不敢爲奇辭詭論,以自外於經傳儒先之宗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載道者。內返竊深慚恧,每自念受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爲之擇賢師傅以受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遊之中,得以厭飫詩書之味,而窮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養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懼。用是擇取庚戌(雍正八年)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後,序、論、書、記、雜文、詩賦,分爲十有四卷,置在案頭,便於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顧行,行顧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檢所行。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14)
弘曆説他刊刻《樂善堂文鈔》,是爲了常常能以自己所言,自檢所行。這是堂皇之論,究其眞實目的,絕非如此單純。《樂善堂文鈔》付梓時,弘曆請十四個人爲他作序。其中有莊親王允祿、康熙第十七子果親王允禮、貝勒允禧、平郡王福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以及當時在士林頗有名氣的蔡世遠、邵基、胡熙等人,還有他自己的弟弟弘晝。這些人的序言,對弘曆是一片讚揚聲。或説作者飽覽羣書,精通經史詩賦,「自經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閫奧,諸賦之源流,靡不情覽」(張廷玉序);「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章,窮其旨趣,探其精蘊」(朱軾序)。或説作者才思敏捷,「每爲文筆不停輟,千言立就,而文思泉湧,采翰雲生」(福彭序)。或説《樂善堂文鈔》是稀世之作,「其氣象之崇宏,則川渟嶽峙也;其心胸之開浚,則風發泉湧也;其詞采之高華,則雲蒸霞蔚也;其音韻之調諧,則金和玉節也」(邵基序)。這些語言,除了含有阿諛奉承的調子之外,更多的是文人互相吹捧積習的表露。但耐人尋味的是,有人已經把弘曆吹捧爲懷有治國平天下道德和才能的儲君。如張廷玉説: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古通今之學,循循乎祗遹聖訓,敬勤無斁。
鄂爾泰説: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聖之心傳者,莫不此會而極。
朱軾説:
聖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發而爲蕩平正直之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皇子天稟純粹,志氣淸明,晨夕侍奉之下,其熏陶涵育聖德聖訓者,固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承無斁,優遊厭飫。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旣接,進德修業之功,得而窺其所至。
旣是「天授之才」,「又上接列聖之心傳」,「進德修業之功」更不可「窺其所至」,未來的天子已經在這些序言中呼之欲出了。
弘曆聰明過人,對自己的未來,會有樂觀的估計。他不必像父輩那樣爲奪權而明爭暗鬥。他要做的事情是,應當在皇族和朝臣之中,樹立起自己未來英明君主的形象。其妙著就是借助於這一部《樂善堂文鈔》,以表示自己不僅精通書史,擅長詩賦,而且有經世之才。果然,他的弟弟弘晝在序言中公開表示自愧弗如:
弟之視兄,雖所處則同,而會心有淺深,氣力有厚薄,屬辭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語也。吾兄隨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寢食相同。及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愼溫恭。皇父見之,未嘗不喜。
皇父聞之,未嘗不樂。……兄之樂善無窮而文思因以無盡。凡古聖賢之微言大義,修身體道之要,經世宰物之方,靡不發揮衍繹娓娓暢爲。
作者不僅承認弘曆曾受皇祖撫愛,而且説弘曆已得聖賢「經世宰物之方」,自己不敢與哥哥「同年而語」。弘晝是皇位最有力的競爭者,他旣然心悅誠服,誰還能與弘曆匹敵。在《樂善堂文鈔》中,弘曆多次提到康熙對自己的鍾愛。説皇祖曾賜他「長幅一,復賜橫幅一、扇一」,「恩寵迥異他人」(15),「得皇祖之澤最深」(16)。如此念念不忘皇祖恩寵,儘管包含著孫子對祖父的懷念,但這畢竟是弘曆最榮耀的政治資本,怎能不經常注於筆端。總之,弘曆刊刻《樂善堂文鈔》是有政治意圖的,目的在於爲日後當皇帝作輿論準備。他把自己的讀書處命之曰「樂善堂」,「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這無異於以大舜自詡。
二、受詔登基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在圓明園處理政務,雖身體偶感不適,但未曾重視。二十二日深夜,病情突然加劇。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公豐盛額、訥親、内大臣海望應召入寢宮。二十三日子時,這位統治中國十三年的皇帝去世了,年僅五十八歲。關於雍正死因,或説中風,或説服用了道士煉的丹藥。孰是孰非,有待研究。還有一種傳説,雍正是被呂留良的女兒呂四娘刺殺。呂留良因反滿文字賈禍,被戮死梟首。乃女呂四娘學得一身武藝,入宮刺殺雍正。這種傳説當然缺乏依據。
雍正去世,内宮一片哭聲。鄂爾泰、張廷玉對允祿、允禮説,雍正「因傳位大事,親書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無有知者。此旨收藏宮中,應急請出,以正大統」(17)。早在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冬時,雍正染病,寒熱時發,飲食不常,夜不能熟寢。八年六月,召見允祿、弘曆、弘晝和大學士、内大臣數人,「面諭遺詔大意」(18)。九月,又將立儲密詔示知張廷玉,十年正月再次密示鄂爾泰、張廷玉,「此時聖諭曰,汝二人外,再無一人知之」(19)。鄂、張所説「親書密旨」,就是指十年正月這一次。
不久,總管太監捧出黃封一函,内藏硃筆親書傳位弘曆詔。張廷玉於燈下宣讀,弘曆跪拜受命之後宣布,「遵皇考遺旨,令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
淸朝的秘密建儲制度始於雍正。康熙年間,康熙帝二次立太子,又二次廢太子。儲君問題,幾乎折騰了半個世紀。雍正接受這一敎訓,創立了秘密立儲辦法。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乾淸宮西暖閣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和九卿,宣布:
今朕諸子尙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愼,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旣將大事付託於朕,朕身爲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淸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20)
但是,據雍正去世時在場人張廷玉記載,當夜用的是雍正十年藏於圓明園的傳位詔。這是可信的。雍正遺體夤夜運回宮中,「倉卒中得官廄駑馬乘之,幾至蹶踣」(21)。這短短十餘字可以看出,其時行色匆忙,情景相當狼狽。
八月二十四日,弘曆頒布數道諭旨。其中諭内外大臣旨,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朕受皇考付託,凡皇考辦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當敬謹繼述。這實質上是宣布自己將繼續處理先帝未竟之業,維護政策連續性。第二,諸王大臣均是深受重恩之人,各宜殫心竭力,輔朕不逮。這是要求朝中大臣必須效忠自己。第三,外省文武大臣,如果因皇考「龍駛上賓」,將已經上奏的本章「中途趕回,另行反改,或到京後撤回不進者,經朕查出,定行從重治罪」(22)。這是要求各級地方官處理事務應一如旣往,不得欺慢。
還有一道是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莊親王允祿等人的,内容是關於鄂爾泰、張廷玉配享太廟問題:
雍正八年六月內,欽奉皇考諭旨,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聖祖仁皇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巨。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爲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終始不渝。朕萬年之後,二臣著配享太廟。今朕欲將皇考此旨入於遺詔內頒發。(23)
配享太廟對於封建官僚來説,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弘曆宣布要將此事寫入皇考遺詔,等於以雍正遺詔作爲最權威的兌現保證。這種超出常格的作法,目的在於拉攏這二位滿漢大臣的領袖人物,並通過他們爭取整個官僚隊伍對自己效忠。鄂、張二人故作姿態,「屢行固辭」,謙讓一番,最後還是感激涕零地接受了。兩天後,鄂、張二人上奏,「不敢當輔政之名,請照例稱總理事務」。弘曆同意,降旨「凡宮門一切陳奏,先告知總理事務王大臣,再行進呈」(24)。
弘曆還注意到穩定内宮問題。八月二十五日,他對太監頒諭説,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妄行傳説。皇太后仁慈,撫愛朕躬,凡有所知,豈有不告之理?但市井傳説,多有舛誤。今後凡外間傳聞,無故向廷傳説者,卽爲背法,查出定行正法。這一諭旨是爲了防止太監向内宮走遞朝廷信息,撥弄是非,干擾政局。
弘曆還降諭都統莽鵠立,命令他把煉丹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趕出西苑。雍正生前迷信道家丹藥,張、王等就在西苑替皇帝煉丹。所以,雍正突然死亡,史家疑爲丹藥中毒,絕非捕風捉影之論。而弘曆在乃父屍骨未寒之時,就急忙把煉丹道士驅逐出西苑,更使人有理由相信丹藥對雍正健康造成嚴重損害。弘曆這份詔諭寫得很奇妙:
皇考萬幾之餘,聞外間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爲遊戲淸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爲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卽正法,決不寬貸。(25)
上諭從爲親者尊者諱角度出發,輕描淡寫地説他父親視張太虛等煉丹術爲「遊戲消閒之具」,也知道這批人是「市井無賴之徒」,從未用過一藥。這位年輕皇帝對煉丹術的鄙視與厭惡,表明他具有反對愚昧的可貴精神。
九月三日黎明,大駕鹵簿全設。弘曆先著素服向雍正帝梓宮行九拜禮。然後更換禮服,奉皇太后到永壽宮,亦行九拜禮。接著,至中和殿受内大臣和執事官行拜,再到太和殿卽皇帝位,受親王以及文武百官、朝鮮等國使臣朝拜,頒詔天下,以明年爲乾隆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