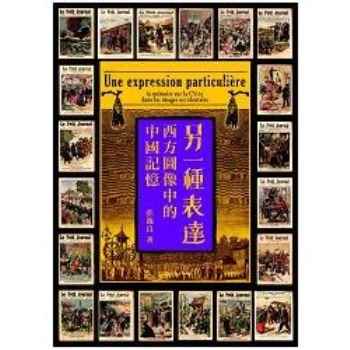光環與陰影
英雄主宰歷史還是人民主宰歷史,「精英史觀」和「人民史觀」的爭論就從未停息。漫長的歷史長河當中,究竟有多少英雄真實存在,有多少英雄是人為誇大創造出來的,這難以一時分清,比如路易十四就是典型被加工出來的暴君。平心而論,如果缺少了這些大人物,歷史的片段中將會缺少起伏和曲折,也會因此少了個性的流露;但過度強調英雄創造歷史,會將這些大人物背後的小人物的貢獻磨滅。《小日報》當中,曾經兩度在封面刊載中國人的肖像,一次是慈禧,一次是李鴻章。圖1的西太后肖像刊登於1900年7月8日,而圖3的李鴻章肖像刊登於1896年7月26日,縱觀《小日報》的發行歷史,除了把西方國家元首、皇帝肖像作為封面人物,西太后與李鴻章的這兩張報紙是為數不多的兩位「外國領導人」封面。刊發西太后肖像的時間點很有意思,1900年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西總部胡同遭襲身亡,6月21日,清廷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國等十一個國家宣戰,隨即清廷官兵百姓都投入到抗擊鬥爭當中。7月8日刊登的西太后照片,像一個標誌,即中國開始與十一國為敵,公然宣戰。
女皇的形象很奇怪。她有男人的精神、力量和身體;有人說她在神秘的皇宮中,通過搏鬥戰勝了她的對手。兩年前,她突然垂掌政權,她不知打了別人多少耳光,獲得了對她侄子光緒的攝政權。女皇七十多歲了;有人曾誤認為她是手藝人的女兒,其實她是貴族將軍的女兒,十六歲以妃子的身份進宮。正宮皇后,即東太后,頭五年沒給咸豐生兒子,使皇帝權力受損。根據傳統,皇帝不得不指定一個繼承人,此人享有重要特權。慈禧幸運多了,她有一個兒子,與皇后一同養育,且兩人在各方面意見一致。皇帝沒有讓她們攝政,皇帝下葬後,她們把攝政的大臣依序砍頭或毒死。西太后的兒子同治早死,她立了她妹妹和醇親王的兒子光緒,謊稱是皇帝的遺囑。兩年前她又推翻了光緒,還抽他耳光。另一太后早已死去,西太后獨掌大權,此前,康親王和李鴻章曾同她一起掌權。現在發生的針對歐洲人的事件,無疑是她的傑作。她說只反對英國人,可能是為分化對手,但盟國不會被這個人騙了。法國人對於慈禧的評價一向不高,尤其是在她向聯軍宣戰之時,洋人除了在諷刺其以卵擊石之外,不忘描述她對權勢的極度佔有慾,以及她與洋人的較量與周旋。為了保有自己的權力,她無視他人性命,不怕與洋人作對,也絕不吝嗇自己的「耳光」。但慈禧也並非一無是處,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慈禧也曾有過非常積極的舉動。而這些場景,卻很少出現在慈禧的史料記錄當中,也與時人所認識的慈禧大相徑庭。1911年2月5日的《小日報》在描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慈禧這些有進步意義的舉動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描繪:中國現在正進行現代化和西化。十五年來,中國表現出了與傳統反戰思想相決裂的傾向。
1894年中日戰爭以及1900年聯軍進入北京,在讓中國遭受到劇烈損失的同時有了深刻的教訓。從那時起,中國政府要建立一支軍隊,為此他們聘請日本教官,派年輕人去歐洲學習,派中國軍官去觀摩軍事演習。今天,中國軍隊有統一制式的軍服和裝備,按照西方的運作標準,中國同樣也在改革行政,中國高官在歐洲考察我們的行政運作。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朝向人民的革命,這場革命不僅發生在組織當中,也表現在思想觀念的領域上。1908年去世的慈禧曾經全力支持這個變革,希望通過改革婦女教育並且使得婦女教育朝著歐洲的標準發展。慈禧首先命令皇族的女孩要學習新東西,她在1905年從歐洲買了六架縫紉機,第二年又花了三十七萬五千法郎在北京建了一所女子中學。但是她提出了一個要求:學校不教授拉丁文,只要求教授刺繡和養蠶。1903年,慈禧要求家長不得讓女孩纏足。八年前,慈禧命令禁止纏足,兩江總督,江蘇、安徽、江西巡撫都相繼發佈命令禁止纏足,纏足會使母親的善良受到影響,影響女子的貞操,使女子身體虛弱,也會因她們的虛弱而造成家庭的貧困。這些御令頒佈之後在杭州張姓家族舉行了一個家庭會議,年紀大的族人都發言,年輕的族人背誦反對纏足的詩,所有女性一致同意廢除纏足,甚至有的中國女性要求做手術以讓她們的腳恢復正常。
就像中國駐美國公使的夫人一樣,她在1905年接受了一個腳部整形手術。慈禧御令受到廣泛歡迎,富家女表示接受,但是在底層有些地方,傳統還是根深蒂固,一些婦女繼續纏足,慈禧為此大為生氣。後來她又專門頒佈詔書,如果女兒纏足,父親不得參加科舉,此舉產生極好的社會效果,幾年之內這種惡俗就消失了。慈禧同樣關心男人的腦袋,就像關心女人的腳一樣。1903年她表示如果男人願意的話,可以剪掉自己的辮子。由於慈禧一開始允許大家剪辮子的時候,大家顯得很猶豫,她在1904年底頒佈御令,從1905年正月開始(2月4日),中國軍隊中的官兵要剪掉自己的辮子,同時邀請三品以上官員也剪辮子,所以幾個月來中國的「髮型革命」正在快速發展,在各大城市都出現了這種景象。1910年12月,在香港六個德高望重的人當眾剪了辮子,旁邊還有人奏樂,幾百個人隨後也跟著剪了辮子。但是這場運動讓一些商人感到擔憂,這些中國人不僅要剪掉辮子還要改變服飾。因此三年前,中國的公共教育部頒佈法令,禁止中國學校的學生穿著洋裝。但因為穿長袍馬褂影響做操,所以在做操的時候,學生可以穿著洋裝,但是洋裝必須用中國生產的布料。歐洲的時尚逐步在中國站穩腳跟,剪辮子就是人們朝著歐式發展的第一步,中國已經註定要朝著歐洲文明的方向發展。也許速度慢,但會像日本一樣堅定。剪辮子與清廷統治看似密切關聯,不少人認為剪辮子實際上意味著清廷統治力的衰弱,民眾開始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但從慈禧下令剪辮子這件事來看,如此論斷也值得商榷。尤其是到了清廷統治的最後十年,清廷在不斷的失敗中意識到了現代化的必要性,閉關鎖國並不能阻擋現代化的潮流。
而作為這個國家的實際掌權者,從不許女人纏足,到對於男人剪辮子持寬容的態度,逐步表現出了慈禧接受現代思想的過程。況且纏足、留辮子在生活當中的確多有不便,慈禧也深諳此道,不想因為這些落後的習俗干擾中國的現代化。私心一點來講,放手是另一種掌握—— 靠強硬手段的壓制不利於清廷的統治,更不利於慈禧掌握權力。這樣生動的片段,很少出現在中國人的認識當中,通常人們對於慈禧的認識一貫都是片面的,只認為她控制慾極強,不惜用整個國家的未來作為賭注。1907年6月,法國《插圖報》曾經刊文,對慈禧後期的執政進行了一番梳理與評價: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慈禧明白要重塑中國的形象。她勇敢地放棄了傳統,領導改革運動。她是在壓力和當時思潮推動下進行改革的,目的是維持住中國帝國。她很好地控制著改革,讓人相信她會成功。
雖然歲月磨去了她的熱情,改變了她異想天開的人性,但精神和身體依然堅強。慈禧接見使團夫人時,儘管她已經七十四歲,但在花園裡仍舊像小女孩一樣爬過假山,搞得跟隨的使團夫人們氣喘吁吁。但這一切總要結束,最堅強的人也要接受歲月的規律。一年半前(1906年),她患過面癱,身體大受影響,能力下降,只能時不時來施政。近期事件的影響,讓她的決策顯得思維混亂,從而讓國家形勢愈來愈危急。她一會兒傾向這邊,一會兒傾向那邊,有時候的理由顯得很幼稚。最後一個向她諫言的人總是有理,有些大臣失寵被召回朝廷,覲見慈禧之後如日中天,幾天後又失去信任。慈禧的多變導致政策沒有連續性,因而改革也隨之變來變去。兩年來,中國的政策反覆程度為他國所未見。政策的多變加劇了大臣的對立,畢竟誰都想得到慈禧的重視。而此時的中國,恰恰需要的是團結,只有慈禧能夠將對立的集團攏到一起。一旦她失去控制力,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中國將陷入混亂並最終終結。她似乎看到了這一前景,拚命想去避免,因而她調解對立集團,啟用袁世凱、張之洞,讓兩人聯手以緩和他們的矛盾。可以感到她在努力將各股勢力集合在搖搖欲墜的皇權周圍,但著實步履維艱,這讓能夠讀懂事實的人感到悲傷。今天這位絕望掙扎以滿足統治的女皇被病魔和歲月侵襲,但看上去仍舊讓人印象深刻。儘管矮、胖、身材平常,但一種超現實的力量使她自有威望。長臉、鈎鼻、敏銳的目光使她有君臨天下的面容,但這還遮不住疾病造成的面頰下垂和嘴唇歪斜,她的聲音輕柔而果斷。與一些中國和滿洲的女人不同,她不化妝,指套、華麗的衣服、首飾、珍珠頭飾把她打扮得像偶像一樣。
除了歐洲人外,包括皇帝在內的人都跪著和她說話。這就是四十七年以來統治無數黃種人的遠東女皇,給我們留下印象的,不僅是她多變的生活經歷、神授儀表以及強大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個古老而垂死文明的代表,輝煌的歷史將隨她一起進入墳墓。慈禧的宣戰徹底激怒了洋人,一場戰爭在所難免。圖2是當期《小日報》的內頁,印有一張八國聯軍進入中國的地圖,上面明確標誌了中國的重要港口和城市,以及英、法等國軍隊的行進路線。在華北地區有一個大大的紅圈,圖例當中明確指出北京、天津、塘沽,而後來的侵略路線正是從天津登陸,進而攻下北京城。對此法國人寫道:我們今天發表的圖可以使讀者瞭解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情況。反外國人的暴亂從北京開始,得到中國政府暗中支援,後擴展到所有有歐洲人的城市。動亂從雲南發展到長江流域。法國人在雲南修鐵路以連接雲南府和東京灣(位於越南北部,即現時的北部灣)殖民地,長江流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在雲南我們的領事被非法扣押,在法國政府強力交涉後才同家人一起獲釋。歐洲各國及美、日紛紛干涉,以保護僑民,恢復秩序,維護鐵路權益,歐洲公司剛獲得鐵路權,以發展同西方的交通。決定性行動只能在各國增援抵達後展開,儘管歐洲人在人數上與中國人相比處於劣勢,但轟炸塘沽,解放天津已經使對手感到害怕,變得老實了一些。相較於慈禧,法國人似乎更加關注李鴻章,作為清廷舉足輕重的大臣,李鴻章的一舉一動無不在釋放新的信號。1896年7月13日至1896年8月2日,李鴻章帶領一個考察團來到法國進行考察,而這次考察也得到了當時法國政府及媒體的高度關注。李鴻章到達法國之前,法國政府特地為接待李鴻章的事宜召開會議。圖3,《小日報》罕見的在7月26日頭版刊登了一張李鴻章身穿黃色馬褂的半身像,這是東方人面孔首次登上西方的主流報刊。在法國的二十一天,對於李鴻章來說意義重大,他參觀了法國的工廠、銀行、煤礦,並拜會了法國總統富爾以及法國外交部的諸位要員。特別值得說的是,7月14日是法國的國慶日,李鴻章作為貴賓出席了法國國慶日的慶祝活動,包括閱兵式和焰火晚會,待遇之高實屬難得。但李鴻章卻對7月14日的整個儀式印象一般,他認為檢閱部隊的環節很出色。但是總的來說,他的態度始終保持低調,以免在歐洲體現出厚此薄彼的情緒。李鴻章在整個訪問之中,很關注歐洲的工業進步,特別是在軍事技術的進步,有法國人認為他訪問歐洲是帶著很多軍事目的的。法國人記錄了如下情景:一位來自遠東的特殊政治家正在歐洲訪問。李鴻章並不總是高興,特別是在對日戰爭之後,皇帝先賞後殺,去掉了他的黃袍馬褂,這一受皇帝恩寵的象徵。現在他穿的黃馬褂回去後會不會被奪去?
不得而知。要判斷他的任務是否成功,首先要知道任務是什麼,這很微妙。李鴻章什麼都看,什麼都考察,但什麼也不說。德國人給了他盛大的場面,手裡拿著訂單本,等著訂購軍火、武器和聘用教官。李鴻章表現得很滿意,但對採買很冷淡。在法國,我們讓他去了隆尚宮,他好像有點累,他看了鐵塔、歌劇院,在愛麗舍宮接受招待。他出席了晚宴,但跟沒去一樣,因為他只吃中餐。這好像透露出一個信號,他只看不參與。他通過翻譯與總統交談,向總統贈送了皇帝及他本人的禮物,會見了現任及前任部長。正如古斯騰斯(M. Constans)所說,大家都為他著迷,但誰也沒得到一句重要的話。這位用水晶扣子的大臣不說一句真話。
他經過街道時,好奇的人向他歡呼,以他的精明,他會琢磨這是為什麼。我們從來就不太喜歡他。無論如何,如果他對法國之行沒好印象,就太忘恩負義了。法國總是好客的,李鴻章回國後可能會想到這一點,我們希望但不指望。在甲午戰爭之前,李鴻章曾經視察天津的一所兵工廠。但是因為當時從西方採購炮彈費用很高,工廠又沒有充足財力來購買,所以他們用陶土製造了一個假炮彈,刷上黑漆,借此成功糊弄了李鴻章。在李鴻章視察完之後,這個炮彈被摔碎了賣給一個英國人,英國人用它來鋪花園。中日戰爭失敗,日本人佔領了威海衛之後,繳獲了不少用陶土、鋸末為材料製作的炮彈,射擊之後都不爆炸,當然也不能用於戰鬥。還有人說,中國的軍艦出征時竟然沒有大炮,原來是中國艦長把大炮典當出去了,開拔的時候還沒有贖回來。後來,中國政府訂購了製造炮彈的機器,機器如期運抵中國。兩個省的大臣都想把機器弄到自己控制的地盤,但遲遲爭執不下,所以他們每個人拿走了這個機器的一部分零件,戰爭開始的時候這些零件還在相距遙遠的兩個地方。顯然,李鴻章希望通過在歐洲的訪問,學習歐洲人在軍事管理上的先進經驗,以便改變當下國內捉襟見肘,甚至有些荒誕的現狀。雖然李鴻章心中急切,但在表情上卻並不過分流露。「只看不參與」—— 法國人對於李鴻章的訪問做了一個形象註解。其中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注意:由於西方人的晚宴多安排在晚上七點半或是八點舉行,習慣六點吃飯的李鴻章特地在下榻的寓所叫自己的廚師做了幾道中國菜墊墊肚子,法國人還特地將菜譜抄了下來放入報導之中,可見當時西方媒體報導的細緻程度。李鴻章生活得比較簡單,我們可以通過一張菜單看出來,在他被邀請去愛麗舍宮參加晚宴之前,他用了一餐飯包括:鴨子豆角,黃瓜、醬炒肉片,蔥、蘑菇爆蝦仁,燉雞,香菇叉燒肉,鴿子肉泥,米飯。他的隨從吃的大米都是從國內帶來的,他們喝茶,但是不加糖。
李鴻章曾經寫道:「我邦自炎農唐虞以前,以天下為公;嬴秦而降,以天下為私。以天下為公則民主之,以天下為私則君主之」、「至我大清,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此剖判未有之奇,聖賢莫測之理,鬱瀉勃然而大發,非常於今日,殆將復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可想而知,作為一個弱國的特使,民主與開放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即使考察了,實現它們也並不現實,面對法蘭西的一片日新月異,縱是心裡歆羨,也深知羸弱的大清難以複製這樣的景象。
踏上別人的領土之時,笑是苦的,心是澀的,李鴻章深知國家處境的艱難。法蘭西人愈是榮耀的招待,愈讓人不由地屈服於強大。法國人在李鴻章訪問時,也開始思考中國軍事發展遲緩的癥結所在,同時表露出自己的擔憂:在發動大的戰爭,或者在進行軍事重組和培訓之前,中國應該對自己的執政理念進行改革。如果沒有這一條,儘管中國像日本一樣獲得了現代的戰爭機器,它也不可能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但是,今天的中國人可以對歐洲人發動一場經濟和工業的可怕競爭,他們能夠悄悄派勞工滲透歐洲,這些人生活簡單、可以接受極其低廉的工資。
最近德國的一家工廠就僱傭了大批中國人。一旦中國人在工業上強大起來,他能夠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生產我們需要的產品,任何海關壁壘都無法抵擋這一進攻。
我不知道歐洲的文明如何抵擋這一災難。不管是西太后,還是李鴻章,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人物,鮮艷的光環從他們走向歷史舞台之時,便已不由自主照在身上。也許在失敗和頹勢面前,他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歷史的陰影與厚重所籠罩,但這些努力不該被忘卻,他們也是歷史組成的一部分。畢竟人就一個,手只有一雙,托不起那個急速下墜的中國。榮耀只是一時,但這並非就意味在失敗和頹勢面前需要承擔所有。
圖1《小日報》 1900/7/8 作者收藏
圖2《小日報》 1900/7/8 作者收藏
圖3《小日報》 1896/7/26 作者收藏
英雄主宰歷史還是人民主宰歷史,「精英史觀」和「人民史觀」的爭論就從未停息。漫長的歷史長河當中,究竟有多少英雄真實存在,有多少英雄是人為誇大創造出來的,這難以一時分清,比如路易十四就是典型被加工出來的暴君。平心而論,如果缺少了這些大人物,歷史的片段中將會缺少起伏和曲折,也會因此少了個性的流露;但過度強調英雄創造歷史,會將這些大人物背後的小人物的貢獻磨滅。《小日報》當中,曾經兩度在封面刊載中國人的肖像,一次是慈禧,一次是李鴻章。圖1的西太后肖像刊登於1900年7月8日,而圖3的李鴻章肖像刊登於1896年7月26日,縱觀《小日報》的發行歷史,除了把西方國家元首、皇帝肖像作為封面人物,西太后與李鴻章的這兩張報紙是為數不多的兩位「外國領導人」封面。刊發西太后肖像的時間點很有意思,1900年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西總部胡同遭襲身亡,6月21日,清廷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國等十一個國家宣戰,隨即清廷官兵百姓都投入到抗擊鬥爭當中。7月8日刊登的西太后照片,像一個標誌,即中國開始與十一國為敵,公然宣戰。
女皇的形象很奇怪。她有男人的精神、力量和身體;有人說她在神秘的皇宮中,通過搏鬥戰勝了她的對手。兩年前,她突然垂掌政權,她不知打了別人多少耳光,獲得了對她侄子光緒的攝政權。女皇七十多歲了;有人曾誤認為她是手藝人的女兒,其實她是貴族將軍的女兒,十六歲以妃子的身份進宮。正宮皇后,即東太后,頭五年沒給咸豐生兒子,使皇帝權力受損。根據傳統,皇帝不得不指定一個繼承人,此人享有重要特權。慈禧幸運多了,她有一個兒子,與皇后一同養育,且兩人在各方面意見一致。皇帝沒有讓她們攝政,皇帝下葬後,她們把攝政的大臣依序砍頭或毒死。西太后的兒子同治早死,她立了她妹妹和醇親王的兒子光緒,謊稱是皇帝的遺囑。兩年前她又推翻了光緒,還抽他耳光。另一太后早已死去,西太后獨掌大權,此前,康親王和李鴻章曾同她一起掌權。現在發生的針對歐洲人的事件,無疑是她的傑作。她說只反對英國人,可能是為分化對手,但盟國不會被這個人騙了。法國人對於慈禧的評價一向不高,尤其是在她向聯軍宣戰之時,洋人除了在諷刺其以卵擊石之外,不忘描述她對權勢的極度佔有慾,以及她與洋人的較量與周旋。為了保有自己的權力,她無視他人性命,不怕與洋人作對,也絕不吝嗇自己的「耳光」。但慈禧也並非一無是處,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慈禧也曾有過非常積極的舉動。而這些場景,卻很少出現在慈禧的史料記錄當中,也與時人所認識的慈禧大相徑庭。1911年2月5日的《小日報》在描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慈禧這些有進步意義的舉動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描繪:中國現在正進行現代化和西化。十五年來,中國表現出了與傳統反戰思想相決裂的傾向。
1894年中日戰爭以及1900年聯軍進入北京,在讓中國遭受到劇烈損失的同時有了深刻的教訓。從那時起,中國政府要建立一支軍隊,為此他們聘請日本教官,派年輕人去歐洲學習,派中國軍官去觀摩軍事演習。今天,中國軍隊有統一制式的軍服和裝備,按照西方的運作標準,中國同樣也在改革行政,中國高官在歐洲考察我們的行政運作。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朝向人民的革命,這場革命不僅發生在組織當中,也表現在思想觀念的領域上。1908年去世的慈禧曾經全力支持這個變革,希望通過改革婦女教育並且使得婦女教育朝著歐洲的標準發展。慈禧首先命令皇族的女孩要學習新東西,她在1905年從歐洲買了六架縫紉機,第二年又花了三十七萬五千法郎在北京建了一所女子中學。但是她提出了一個要求:學校不教授拉丁文,只要求教授刺繡和養蠶。1903年,慈禧要求家長不得讓女孩纏足。八年前,慈禧命令禁止纏足,兩江總督,江蘇、安徽、江西巡撫都相繼發佈命令禁止纏足,纏足會使母親的善良受到影響,影響女子的貞操,使女子身體虛弱,也會因她們的虛弱而造成家庭的貧困。這些御令頒佈之後在杭州張姓家族舉行了一個家庭會議,年紀大的族人都發言,年輕的族人背誦反對纏足的詩,所有女性一致同意廢除纏足,甚至有的中國女性要求做手術以讓她們的腳恢復正常。
就像中國駐美國公使的夫人一樣,她在1905年接受了一個腳部整形手術。慈禧御令受到廣泛歡迎,富家女表示接受,但是在底層有些地方,傳統還是根深蒂固,一些婦女繼續纏足,慈禧為此大為生氣。後來她又專門頒佈詔書,如果女兒纏足,父親不得參加科舉,此舉產生極好的社會效果,幾年之內這種惡俗就消失了。慈禧同樣關心男人的腦袋,就像關心女人的腳一樣。1903年她表示如果男人願意的話,可以剪掉自己的辮子。由於慈禧一開始允許大家剪辮子的時候,大家顯得很猶豫,她在1904年底頒佈御令,從1905年正月開始(2月4日),中國軍隊中的官兵要剪掉自己的辮子,同時邀請三品以上官員也剪辮子,所以幾個月來中國的「髮型革命」正在快速發展,在各大城市都出現了這種景象。1910年12月,在香港六個德高望重的人當眾剪了辮子,旁邊還有人奏樂,幾百個人隨後也跟著剪了辮子。但是這場運動讓一些商人感到擔憂,這些中國人不僅要剪掉辮子還要改變服飾。因此三年前,中國的公共教育部頒佈法令,禁止中國學校的學生穿著洋裝。但因為穿長袍馬褂影響做操,所以在做操的時候,學生可以穿著洋裝,但是洋裝必須用中國生產的布料。歐洲的時尚逐步在中國站穩腳跟,剪辮子就是人們朝著歐式發展的第一步,中國已經註定要朝著歐洲文明的方向發展。也許速度慢,但會像日本一樣堅定。剪辮子與清廷統治看似密切關聯,不少人認為剪辮子實際上意味著清廷統治力的衰弱,民眾開始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但從慈禧下令剪辮子這件事來看,如此論斷也值得商榷。尤其是到了清廷統治的最後十年,清廷在不斷的失敗中意識到了現代化的必要性,閉關鎖國並不能阻擋現代化的潮流。
而作為這個國家的實際掌權者,從不許女人纏足,到對於男人剪辮子持寬容的態度,逐步表現出了慈禧接受現代思想的過程。況且纏足、留辮子在生活當中的確多有不便,慈禧也深諳此道,不想因為這些落後的習俗干擾中國的現代化。私心一點來講,放手是另一種掌握—— 靠強硬手段的壓制不利於清廷的統治,更不利於慈禧掌握權力。這樣生動的片段,很少出現在中國人的認識當中,通常人們對於慈禧的認識一貫都是片面的,只認為她控制慾極強,不惜用整個國家的未來作為賭注。1907年6月,法國《插圖報》曾經刊文,對慈禧後期的執政進行了一番梳理與評價: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慈禧明白要重塑中國的形象。她勇敢地放棄了傳統,領導改革運動。她是在壓力和當時思潮推動下進行改革的,目的是維持住中國帝國。她很好地控制著改革,讓人相信她會成功。
雖然歲月磨去了她的熱情,改變了她異想天開的人性,但精神和身體依然堅強。慈禧接見使團夫人時,儘管她已經七十四歲,但在花園裡仍舊像小女孩一樣爬過假山,搞得跟隨的使團夫人們氣喘吁吁。但這一切總要結束,最堅強的人也要接受歲月的規律。一年半前(1906年),她患過面癱,身體大受影響,能力下降,只能時不時來施政。近期事件的影響,讓她的決策顯得思維混亂,從而讓國家形勢愈來愈危急。她一會兒傾向這邊,一會兒傾向那邊,有時候的理由顯得很幼稚。最後一個向她諫言的人總是有理,有些大臣失寵被召回朝廷,覲見慈禧之後如日中天,幾天後又失去信任。慈禧的多變導致政策沒有連續性,因而改革也隨之變來變去。兩年來,中國的政策反覆程度為他國所未見。政策的多變加劇了大臣的對立,畢竟誰都想得到慈禧的重視。而此時的中國,恰恰需要的是團結,只有慈禧能夠將對立的集團攏到一起。一旦她失去控制力,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中國將陷入混亂並最終終結。她似乎看到了這一前景,拚命想去避免,因而她調解對立集團,啟用袁世凱、張之洞,讓兩人聯手以緩和他們的矛盾。可以感到她在努力將各股勢力集合在搖搖欲墜的皇權周圍,但著實步履維艱,這讓能夠讀懂事實的人感到悲傷。今天這位絕望掙扎以滿足統治的女皇被病魔和歲月侵襲,但看上去仍舊讓人印象深刻。儘管矮、胖、身材平常,但一種超現實的力量使她自有威望。長臉、鈎鼻、敏銳的目光使她有君臨天下的面容,但這還遮不住疾病造成的面頰下垂和嘴唇歪斜,她的聲音輕柔而果斷。與一些中國和滿洲的女人不同,她不化妝,指套、華麗的衣服、首飾、珍珠頭飾把她打扮得像偶像一樣。
除了歐洲人外,包括皇帝在內的人都跪著和她說話。這就是四十七年以來統治無數黃種人的遠東女皇,給我們留下印象的,不僅是她多變的生活經歷、神授儀表以及強大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個古老而垂死文明的代表,輝煌的歷史將隨她一起進入墳墓。慈禧的宣戰徹底激怒了洋人,一場戰爭在所難免。圖2是當期《小日報》的內頁,印有一張八國聯軍進入中國的地圖,上面明確標誌了中國的重要港口和城市,以及英、法等國軍隊的行進路線。在華北地區有一個大大的紅圈,圖例當中明確指出北京、天津、塘沽,而後來的侵略路線正是從天津登陸,進而攻下北京城。對此法國人寫道:我們今天發表的圖可以使讀者瞭解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情況。反外國人的暴亂從北京開始,得到中國政府暗中支援,後擴展到所有有歐洲人的城市。動亂從雲南發展到長江流域。法國人在雲南修鐵路以連接雲南府和東京灣(位於越南北部,即現時的北部灣)殖民地,長江流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在雲南我們的領事被非法扣押,在法國政府強力交涉後才同家人一起獲釋。歐洲各國及美、日紛紛干涉,以保護僑民,恢復秩序,維護鐵路權益,歐洲公司剛獲得鐵路權,以發展同西方的交通。決定性行動只能在各國增援抵達後展開,儘管歐洲人在人數上與中國人相比處於劣勢,但轟炸塘沽,解放天津已經使對手感到害怕,變得老實了一些。相較於慈禧,法國人似乎更加關注李鴻章,作為清廷舉足輕重的大臣,李鴻章的一舉一動無不在釋放新的信號。1896年7月13日至1896年8月2日,李鴻章帶領一個考察團來到法國進行考察,而這次考察也得到了當時法國政府及媒體的高度關注。李鴻章到達法國之前,法國政府特地為接待李鴻章的事宜召開會議。圖3,《小日報》罕見的在7月26日頭版刊登了一張李鴻章身穿黃色馬褂的半身像,這是東方人面孔首次登上西方的主流報刊。在法國的二十一天,對於李鴻章來說意義重大,他參觀了法國的工廠、銀行、煤礦,並拜會了法國總統富爾以及法國外交部的諸位要員。特別值得說的是,7月14日是法國的國慶日,李鴻章作為貴賓出席了法國國慶日的慶祝活動,包括閱兵式和焰火晚會,待遇之高實屬難得。但李鴻章卻對7月14日的整個儀式印象一般,他認為檢閱部隊的環節很出色。但是總的來說,他的態度始終保持低調,以免在歐洲體現出厚此薄彼的情緒。李鴻章在整個訪問之中,很關注歐洲的工業進步,特別是在軍事技術的進步,有法國人認為他訪問歐洲是帶著很多軍事目的的。法國人記錄了如下情景:一位來自遠東的特殊政治家正在歐洲訪問。李鴻章並不總是高興,特別是在對日戰爭之後,皇帝先賞後殺,去掉了他的黃袍馬褂,這一受皇帝恩寵的象徵。現在他穿的黃馬褂回去後會不會被奪去?
不得而知。要判斷他的任務是否成功,首先要知道任務是什麼,這很微妙。李鴻章什麼都看,什麼都考察,但什麼也不說。德國人給了他盛大的場面,手裡拿著訂單本,等著訂購軍火、武器和聘用教官。李鴻章表現得很滿意,但對採買很冷淡。在法國,我們讓他去了隆尚宮,他好像有點累,他看了鐵塔、歌劇院,在愛麗舍宮接受招待。他出席了晚宴,但跟沒去一樣,因為他只吃中餐。這好像透露出一個信號,他只看不參與。他通過翻譯與總統交談,向總統贈送了皇帝及他本人的禮物,會見了現任及前任部長。正如古斯騰斯(M. Constans)所說,大家都為他著迷,但誰也沒得到一句重要的話。這位用水晶扣子的大臣不說一句真話。
他經過街道時,好奇的人向他歡呼,以他的精明,他會琢磨這是為什麼。我們從來就不太喜歡他。無論如何,如果他對法國之行沒好印象,就太忘恩負義了。法國總是好客的,李鴻章回國後可能會想到這一點,我們希望但不指望。在甲午戰爭之前,李鴻章曾經視察天津的一所兵工廠。但是因為當時從西方採購炮彈費用很高,工廠又沒有充足財力來購買,所以他們用陶土製造了一個假炮彈,刷上黑漆,借此成功糊弄了李鴻章。在李鴻章視察完之後,這個炮彈被摔碎了賣給一個英國人,英國人用它來鋪花園。中日戰爭失敗,日本人佔領了威海衛之後,繳獲了不少用陶土、鋸末為材料製作的炮彈,射擊之後都不爆炸,當然也不能用於戰鬥。還有人說,中國的軍艦出征時竟然沒有大炮,原來是中國艦長把大炮典當出去了,開拔的時候還沒有贖回來。後來,中國政府訂購了製造炮彈的機器,機器如期運抵中國。兩個省的大臣都想把機器弄到自己控制的地盤,但遲遲爭執不下,所以他們每個人拿走了這個機器的一部分零件,戰爭開始的時候這些零件還在相距遙遠的兩個地方。顯然,李鴻章希望通過在歐洲的訪問,學習歐洲人在軍事管理上的先進經驗,以便改變當下國內捉襟見肘,甚至有些荒誕的現狀。雖然李鴻章心中急切,但在表情上卻並不過分流露。「只看不參與」—— 法國人對於李鴻章的訪問做了一個形象註解。其中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注意:由於西方人的晚宴多安排在晚上七點半或是八點舉行,習慣六點吃飯的李鴻章特地在下榻的寓所叫自己的廚師做了幾道中國菜墊墊肚子,法國人還特地將菜譜抄了下來放入報導之中,可見當時西方媒體報導的細緻程度。李鴻章生活得比較簡單,我們可以通過一張菜單看出來,在他被邀請去愛麗舍宮參加晚宴之前,他用了一餐飯包括:鴨子豆角,黃瓜、醬炒肉片,蔥、蘑菇爆蝦仁,燉雞,香菇叉燒肉,鴿子肉泥,米飯。他的隨從吃的大米都是從國內帶來的,他們喝茶,但是不加糖。
李鴻章曾經寫道:「我邦自炎農唐虞以前,以天下為公;嬴秦而降,以天下為私。以天下為公則民主之,以天下為私則君主之」、「至我大清,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此剖判未有之奇,聖賢莫測之理,鬱瀉勃然而大發,非常於今日,殆將復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可想而知,作為一個弱國的特使,民主與開放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即使考察了,實現它們也並不現實,面對法蘭西的一片日新月異,縱是心裡歆羨,也深知羸弱的大清難以複製這樣的景象。
踏上別人的領土之時,笑是苦的,心是澀的,李鴻章深知國家處境的艱難。法蘭西人愈是榮耀的招待,愈讓人不由地屈服於強大。法國人在李鴻章訪問時,也開始思考中國軍事發展遲緩的癥結所在,同時表露出自己的擔憂:在發動大的戰爭,或者在進行軍事重組和培訓之前,中國應該對自己的執政理念進行改革。如果沒有這一條,儘管中國像日本一樣獲得了現代的戰爭機器,它也不可能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但是,今天的中國人可以對歐洲人發動一場經濟和工業的可怕競爭,他們能夠悄悄派勞工滲透歐洲,這些人生活簡單、可以接受極其低廉的工資。
最近德國的一家工廠就僱傭了大批中國人。一旦中國人在工業上強大起來,他能夠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生產我們需要的產品,任何海關壁壘都無法抵擋這一進攻。
我不知道歐洲的文明如何抵擋這一災難。不管是西太后,還是李鴻章,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人物,鮮艷的光環從他們走向歷史舞台之時,便已不由自主照在身上。也許在失敗和頹勢面前,他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歷史的陰影與厚重所籠罩,但這些努力不該被忘卻,他們也是歷史組成的一部分。畢竟人就一個,手只有一雙,托不起那個急速下墜的中國。榮耀只是一時,但這並非就意味在失敗和頹勢面前需要承擔所有。
圖1《小日報》 1900/7/8 作者收藏
圖2《小日報》 1900/7/8 作者收藏
圖3《小日報》 1896/7/26 作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