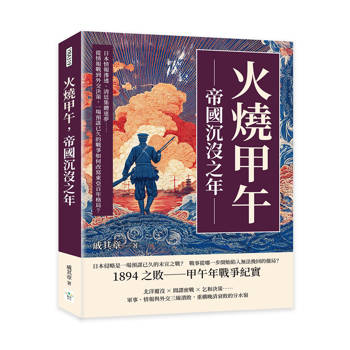第一章 戰端初啟
第一節 明治黷武
水有源,樹有根。凡是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根由、它的原委、它的因果關係。有因必有果;反之,有果必有因。甲午戰爭當然不能例外。甲午戰爭,這是中國人的稱呼。日本人叫日清戰爭。在某些日本歷史學者的著作裡,經常宣揚一種觀點:日清戰爭是偶發事件,日清戰爭不是日本明治政府有預謀的戰爭,而是由於某些偶然因素才陰錯陽差地發生的,日本並不是戰爭的責任者。這種觀點,可以叫它「偶發」論。在日本學術界,雖然「偶發」論並未取得普遍認同,有些日本歷史學者還對「偶發」論持指責的態度,但「偶發」論者通常都很頑固,時不時就會把「偶發」論改頭換面地拿出來宣揚一番,所以絕不能小看它。
我們之所以認為「偶發」論不能成立,主要是基於日本明治政府的實際表現,也就是基於許多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
第一,銳意擴張。西元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開始推行「武國」方針,確立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為基本國策。他發表所謂〈天皇御筆信〉,宣稱「日本乃萬國之本」,需要「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不言而喻,日本要布國威的首要目標,就是一衣帶水的西鄰朝鮮和中國。
睦仁的〈天皇御筆信〉發表後,在日本政壇颳起了一股旋風,鼓吹「征韓論」一時蔚然成風。當時,倡導「征韓論」主導者是參議木戶孝允。他有一套說辭云:
韓地之事乃皇國建立國體之處,推廣今日宇內之條理故也。愚意如為東海生輝,應以此地始。倘一旦動起干戈,不必急於求成,大致規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後,要好自確立今後戰略,竭盡全力,不倦經營,不出兩三年,天地必將為之一變。如行之有效,萬事不拔之皇基將愈益鞏固矣。
木戶所論與外務省的意見完全相合。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對「征韓論」的闡述更為透澈:
皇國乃是絕海之一大孤島,此後縱令擁有相應之兵備,而保周圍環海之大地於萬世始終,與各國並立,弘張國威,乃最大難事。然朝鮮國為北連滿洲、西連韃清之地,使之綏服,實為保全皇國之基礎,將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本。
第一步,征服朝鮮;第二步,占領中國東北;第三步,「綏服」中國;第四步,「經略進取萬國」,稱霸世界。這就是日本「征韓論」者的如意算盤和實施步驟。
於是,日本政府選中了激進的「征韓論」者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派他去朝鮮調查政情和軍備。西元1870年3月,佐田向政府上了一篇著名的〈建白書〉,其主要內容是:(一)朝鮮有必伐之罪,不愁找不到出兵藉口。(二)伐朝鮮必勝無疑,「不出五旬而虜其王」。(三)伐朝鮮有利而無損。「朝鮮則金穴也,米麥亦頗多,一舉拔之,徵其人民與金谷。」、「故伐朝鮮者,富國強兵之策。」(四)伐朝既可防列國對朝鮮的覬覦,又是實行海外擴張的大好機會,「呂宋、臺灣可唾手而得」。(五)伐朝可繼之伐清。「當天朝加兵之日,則遣使於清國,告以伐朝鮮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則可並清而伐之。」
但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決策層,在討論如何或何時對朝鮮開戰的問題時卻產生了意見分歧:一派是急征派,以時任參議的陸軍大將西鄉隆盛為首,恨不得馬上出兵伐朝,主張由自己充當使臣赴朝,先設下圈套,誘朝鮮政府入彀,必然帶來開戰之機;另一派是緩征派,以參議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為首,主張處理朝鮮要講究步驟,必須周密計畫,統一方略,緩緩圖之。雙方意見對立,爭論激烈,演成一場勢不兩立的政爭,最終以急征派的下臺而結束了這場「征韓論」之爭。
第一節 明治黷武
水有源,樹有根。凡是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根由、它的原委、它的因果關係。有因必有果;反之,有果必有因。甲午戰爭當然不能例外。甲午戰爭,這是中國人的稱呼。日本人叫日清戰爭。在某些日本歷史學者的著作裡,經常宣揚一種觀點:日清戰爭是偶發事件,日清戰爭不是日本明治政府有預謀的戰爭,而是由於某些偶然因素才陰錯陽差地發生的,日本並不是戰爭的責任者。這種觀點,可以叫它「偶發」論。在日本學術界,雖然「偶發」論並未取得普遍認同,有些日本歷史學者還對「偶發」論持指責的態度,但「偶發」論者通常都很頑固,時不時就會把「偶發」論改頭換面地拿出來宣揚一番,所以絕不能小看它。
我們之所以認為「偶發」論不能成立,主要是基於日本明治政府的實際表現,也就是基於許多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
第一,銳意擴張。西元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開始推行「武國」方針,確立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為基本國策。他發表所謂〈天皇御筆信〉,宣稱「日本乃萬國之本」,需要「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不言而喻,日本要布國威的首要目標,就是一衣帶水的西鄰朝鮮和中國。
睦仁的〈天皇御筆信〉發表後,在日本政壇颳起了一股旋風,鼓吹「征韓論」一時蔚然成風。當時,倡導「征韓論」主導者是參議木戶孝允。他有一套說辭云:
韓地之事乃皇國建立國體之處,推廣今日宇內之條理故也。愚意如為東海生輝,應以此地始。倘一旦動起干戈,不必急於求成,大致規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後,要好自確立今後戰略,竭盡全力,不倦經營,不出兩三年,天地必將為之一變。如行之有效,萬事不拔之皇基將愈益鞏固矣。
木戶所論與外務省的意見完全相合。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對「征韓論」的闡述更為透澈:
皇國乃是絕海之一大孤島,此後縱令擁有相應之兵備,而保周圍環海之大地於萬世始終,與各國並立,弘張國威,乃最大難事。然朝鮮國為北連滿洲、西連韃清之地,使之綏服,實為保全皇國之基礎,將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本。
第一步,征服朝鮮;第二步,占領中國東北;第三步,「綏服」中國;第四步,「經略進取萬國」,稱霸世界。這就是日本「征韓論」者的如意算盤和實施步驟。
於是,日本政府選中了激進的「征韓論」者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派他去朝鮮調查政情和軍備。西元1870年3月,佐田向政府上了一篇著名的〈建白書〉,其主要內容是:(一)朝鮮有必伐之罪,不愁找不到出兵藉口。(二)伐朝鮮必勝無疑,「不出五旬而虜其王」。(三)伐朝鮮有利而無損。「朝鮮則金穴也,米麥亦頗多,一舉拔之,徵其人民與金谷。」、「故伐朝鮮者,富國強兵之策。」(四)伐朝既可防列國對朝鮮的覬覦,又是實行海外擴張的大好機會,「呂宋、臺灣可唾手而得」。(五)伐朝可繼之伐清。「當天朝加兵之日,則遣使於清國,告以伐朝鮮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則可並清而伐之。」
但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決策層,在討論如何或何時對朝鮮開戰的問題時卻產生了意見分歧:一派是急征派,以時任參議的陸軍大將西鄉隆盛為首,恨不得馬上出兵伐朝,主張由自己充當使臣赴朝,先設下圈套,誘朝鮮政府入彀,必然帶來開戰之機;另一派是緩征派,以參議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為首,主張處理朝鮮要講究步驟,必須周密計畫,統一方略,緩緩圖之。雙方意見對立,爭論激烈,演成一場勢不兩立的政爭,最終以急征派的下臺而結束了這場「征韓論」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