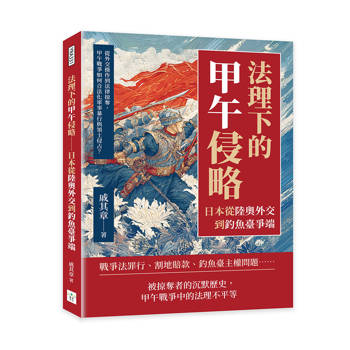第五章 戰爭前的設局:陸奧外交的謀略與行動
第一節 「六二出兵」的虛實:日本軍事部署背後的戰略算計
陸奧宗光身為日本外務大臣,以外交方式「狡獪」而聞名,對促成日本開戰負有重大的責任。但在日本,歷來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如今,在日本外務省院裡,歷屆外務大臣中只樹了陸奧宗光的銅像,即足以說明這一點。不僅如此。長期以來,在日本史學界,陸奧宗光還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來進行宣傳。這種觀點能否成立,是值得重新加以研究的。
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以顯示「陸奧外交」的性質,故研究「陸奧外交」者多重視對「六二出兵」的研究。所謂「六二出兵」,就是西元1894年6月2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召集內閣會議,決定向朝鮮派遣軍隊。陸奧宗光本人記述此事道:
適接杉村(濬)來電報告朝鮮政府已向中國政府請求援兵。這確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默視不顧,就將使中日兩國在朝鮮已經不平衡的權力更為懸殊,中國今後對朝鮮的問題就只有聽憑中國為所欲為了。而且日朝條約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壞的危險。因此,我在當天的會議開始後,首先將杉村的電報給閣員們看過,同時提出我的意見:「如果中國確有向朝鮮派遣軍隊的事實,不問其用任何名義,中國也必須向朝鮮派遣相當的軍隊,以備不測,並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均勢。」閣員們都贊成這個意見。伊藤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熾仁親王殿下及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陸軍中將參加會議。二人到後,立即對今後派兵赴朝問題作出祕密決議;內閣總理大臣隨即攜帶此項祕密決議……進宮,循例奏請天皇裁奪施行。
在陸奧宗光的筆下,把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六二出兵」寫得如此輕鬆,這就容易示人以假象,似乎「六二出兵」並不意味著要與中國交戰,而只是想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勢力均衡而已。這就是有些人所謂的「維護勢力均衡」政策。
正由於此,有不少論者斷定,「陸奧外交就是這樣的和平主義」。日本已故歷史學家信夫清三郎即持有此觀點。他認為,陸奧宗光的出發點是和平地解決朝鮮問題,出兵是出於無奈和被迫的。「陸奧外相必須為和平收拾時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國已經出兵的情況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已經不能厚著臉皮後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張「維護勢力均衡」政策。至於後來走向戰爭,「這就不是陸奧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
此說在日本為很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現在在日本歷史學界仍有很大的影響。如京都大學的高橋秀直寫了一部題曰《走向日清戰爭的道路》的書,進一步發揮了信夫清三郎的觀點,認為:「日本政府的對朝政策,並非即使與清相爭也要獨霸朝鮮,對清朝一貫是避免戰爭的。……這一時期日本政府為對抗清朝進行了大規模的擴軍,但這是出於對清朝海軍較日本處於優勢而產生的危機感,而並非是積極地圖謀與清對戰。它是準備對付萬一發生的事態的,只要日清間的懸案未解決,就有可能發生不測。」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要開戰才出兵的。……是試圖保持和清朝的協調的」。熊本大學的大澤博明也認為:「甲申事變以後,日本政府在外交、軍事上的對朝政策不是指向對清戰爭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鮮案的提出也不是要『挑釁』清朝;實現日清共同改革朝鮮,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圖。」並指出:「從全局看,對清開戰是起初的政策目標失敗的結果,是日本外交的失敗。」、「並不存在從一開始就特地準備對清開戰並克服種種障礙最終實現開戰的過程。」1995年夏,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專門舉辦了一次「陸奧宗光與日清戰爭特別展示史料」的展覽,在所陳列史料的選擇與設計上也刻意地突顯「陸奧外交」的和平色彩。由此可見,此說在日本的影響之廣。
但是,種種事實顯示,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動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說日本早就想伺機挑起戰端,即從甲午戰爭前夕所發生的一些情況來看,即足以說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劃這場戰爭。
首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後,日本報紙爭相傳布,大造輿論,甚至鼓吹「宣揚國威此其時,百年大計在一戰」。陸奧宗光與之心有靈犀,也認為此乃確立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之難得良機,切不可失之交臂。但從外交的角度考慮,此時出兵未免過早,而出兵總須有所藉口,故寄希望於中國派兵,然後伺機行事。於是,他密令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密切注意東學黨的動向,並仔細觀察朝鮮政府對東學黨採取何種措施,以及朝鮮政府與中國使節之間的關係」。到5月29日,陸奧宗光早已急不可待,再次密令杉村濬探聽朝鮮政府是否已向中國求援。6月1日,杉村濬探知朝鮮國王李熙決定向中國借兵,但不知中國態度如何,急派書記生鄭永邦訪清政府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凱,一面問「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露出急盼中國出兵的心情,一面又表示「我政府必無他意」,用此虛偽的口頭保證來麻痺袁世凱。翌日,杉村濬又親訪袁世凱,進一步表示「盼華速代戡」的迫切願望,以誘袁世凱上鉤。
第一節 「六二出兵」的虛實:日本軍事部署背後的戰略算計
陸奧宗光身為日本外務大臣,以外交方式「狡獪」而聞名,對促成日本開戰負有重大的責任。但在日本,歷來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如今,在日本外務省院裡,歷屆外務大臣中只樹了陸奧宗光的銅像,即足以說明這一點。不僅如此。長期以來,在日本史學界,陸奧宗光還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來進行宣傳。這種觀點能否成立,是值得重新加以研究的。
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以顯示「陸奧外交」的性質,故研究「陸奧外交」者多重視對「六二出兵」的研究。所謂「六二出兵」,就是西元1894年6月2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召集內閣會議,決定向朝鮮派遣軍隊。陸奧宗光本人記述此事道:
適接杉村(濬)來電報告朝鮮政府已向中國政府請求援兵。這確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默視不顧,就將使中日兩國在朝鮮已經不平衡的權力更為懸殊,中國今後對朝鮮的問題就只有聽憑中國為所欲為了。而且日朝條約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壞的危險。因此,我在當天的會議開始後,首先將杉村的電報給閣員們看過,同時提出我的意見:「如果中國確有向朝鮮派遣軍隊的事實,不問其用任何名義,中國也必須向朝鮮派遣相當的軍隊,以備不測,並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均勢。」閣員們都贊成這個意見。伊藤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熾仁親王殿下及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陸軍中將參加會議。二人到後,立即對今後派兵赴朝問題作出祕密決議;內閣總理大臣隨即攜帶此項祕密決議……進宮,循例奏請天皇裁奪施行。
在陸奧宗光的筆下,把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六二出兵」寫得如此輕鬆,這就容易示人以假象,似乎「六二出兵」並不意味著要與中國交戰,而只是想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勢力均衡而已。這就是有些人所謂的「維護勢力均衡」政策。
正由於此,有不少論者斷定,「陸奧外交就是這樣的和平主義」。日本已故歷史學家信夫清三郎即持有此觀點。他認為,陸奧宗光的出發點是和平地解決朝鮮問題,出兵是出於無奈和被迫的。「陸奧外相必須為和平收拾時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國已經出兵的情況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已經不能厚著臉皮後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張「維護勢力均衡」政策。至於後來走向戰爭,「這就不是陸奧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
此說在日本為很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現在在日本歷史學界仍有很大的影響。如京都大學的高橋秀直寫了一部題曰《走向日清戰爭的道路》的書,進一步發揮了信夫清三郎的觀點,認為:「日本政府的對朝政策,並非即使與清相爭也要獨霸朝鮮,對清朝一貫是避免戰爭的。……這一時期日本政府為對抗清朝進行了大規模的擴軍,但這是出於對清朝海軍較日本處於優勢而產生的危機感,而並非是積極地圖謀與清對戰。它是準備對付萬一發生的事態的,只要日清間的懸案未解決,就有可能發生不測。」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要開戰才出兵的。……是試圖保持和清朝的協調的」。熊本大學的大澤博明也認為:「甲申事變以後,日本政府在外交、軍事上的對朝政策不是指向對清戰爭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鮮案的提出也不是要『挑釁』清朝;實現日清共同改革朝鮮,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圖。」並指出:「從全局看,對清開戰是起初的政策目標失敗的結果,是日本外交的失敗。」、「並不存在從一開始就特地準備對清開戰並克服種種障礙最終實現開戰的過程。」1995年夏,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專門舉辦了一次「陸奧宗光與日清戰爭特別展示史料」的展覽,在所陳列史料的選擇與設計上也刻意地突顯「陸奧外交」的和平色彩。由此可見,此說在日本的影響之廣。
但是,種種事實顯示,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動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說日本早就想伺機挑起戰端,即從甲午戰爭前夕所發生的一些情況來看,即足以說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劃這場戰爭。
首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後,日本報紙爭相傳布,大造輿論,甚至鼓吹「宣揚國威此其時,百年大計在一戰」。陸奧宗光與之心有靈犀,也認為此乃確立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之難得良機,切不可失之交臂。但從外交的角度考慮,此時出兵未免過早,而出兵總須有所藉口,故寄希望於中國派兵,然後伺機行事。於是,他密令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密切注意東學黨的動向,並仔細觀察朝鮮政府對東學黨採取何種措施,以及朝鮮政府與中國使節之間的關係」。到5月29日,陸奧宗光早已急不可待,再次密令杉村濬探聽朝鮮政府是否已向中國求援。6月1日,杉村濬探知朝鮮國王李熙決定向中國借兵,但不知中國態度如何,急派書記生鄭永邦訪清政府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凱,一面問「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露出急盼中國出兵的心情,一面又表示「我政府必無他意」,用此虛偽的口頭保證來麻痺袁世凱。翌日,杉村濬又親訪袁世凱,進一步表示「盼華速代戡」的迫切願望,以誘袁世凱上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