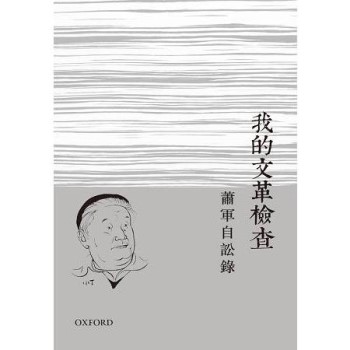第一部分
寫給全國人民的「公開檢查」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致中共中央政務院文教委員會 (一九五三年.北京)
一、五年間
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天“八.一五”紀念日以後,在哈爾濱由魯迅文化出版社出版,我所主編的《文化報》和在光華書店出版、由宋之的等人所編的《生活報》,因了《文化報》在“八.一五”紀念日刊載了幾篇文字,《生活報》認為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解放戰爭的,提出了嚴厲指摘,因而引起了雙方的爭論——繼續了約有兩個月時間——結束以後,到今年的“八.一五”整整是五個週年。這五年間整個中國——除台灣而外——早已獲得了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土改完成,五年建設計劃開始實施……在這些偉大的事跡對比下,這屬於歷史過程上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似乎再沒有提起的必要。不過最近政務院中央文教委員會指示我,還應該把這問題根據我今天的認識,在群眾面前交代清楚,這於我於人民是有益的。對於這指示,我是很愉快地立刻接受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更是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我認為有這義務和責任把自己底思想本質——好或壞——由於這事件所引起的於革命文化事業,政治影響有害的結果,我應負的責任……向人民交代明白,弄清是非——且不管我將來是否還從事文學這工作——使讀過我書或文字的人易於批判,不致盲目地再受毒害;同時也可和某一些自稱或真正能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掌握了馬列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們有所區別,免得“魚目混珠”——這是必要的。
這五年間我盡幹了些什麼呢?應該簡要地在這裏提一提。因為過去間接、直接我曾聽到過很多“謠言”:有的說我被弄到某個礦山去背煤“勞動改造”並因背煤而死了;有的說我自殺了,有的說我被殺了,有的說我被關進監獄了……等等。這些謠言底產生,有的是出於暗藏敵人們惡意污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的是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底本質還認識不清所致。礦山我確是住過一時期,卻並沒背煤,而是在作工會工作。一九四八年底瀋陽解放前,在哈爾濱由我所主持的魯迅文化出版社就交給了公家(原來就是公家的資本),《文化報》也作了結束。瀋陽解放後,我就隨同中共東北局到了瀋陽,而後去鞍山作了一次旅行。一九四九年春(大約三月間)中共東北局宣傳部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發表了他底“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接着東北局對我底“決定”也發表了,同時也發表了其他一些批評我的文字,接着在東北各機關、學校展開了三個月“蕭軍思想討論”的同時,東北局決定我去一處礦山改造和學習(我也是這樣要求的。原來我要求去解放戰爭的前線,未被允許)。我就去到了撫順。在撫順一面做些工會工作——因為這工作可以經常到各礦廠接近工人群眾——同時也幫助那裏建立了一個京劇團,在這劇團裏也做些工作。在撫順工作了約一年半,於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從四月初開始續寫長篇小說《第三代》第八部後半部,結束後,從六月初開始寫一部新小說《五月的礦山》。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間寫完了它(約二十八萬字)。經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委的審查,最近(一九五三年五月)已被決定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和我的家屬在瀋陽都是供給制待遇,我來北京後,寫作中的生活費用,因為中共東北局劉副部長不同意我來北京,而我來了,又不願再回去,這是無組織觀念的“自由行動”,東北局就沒給轉“關係”,當然這裏也就不會“供給”我——這是完全對的。所以我個人的“供給”到北京後就斷絕了。可是我底家屬一直到今天倒還是被供給着的,因為他們是經過批准先到的北京。這期間北京市政府還每月津貼我三百斤小米房費,另外,由於我向周總理的請求,“文聯”曾借給我過三百萬元(舊幣,合現在300元——注)。政府和共產黨在生活上對我這樣破格的照顧,我是衷心感激着的。
《五月的礦山》寫完以後,我着就被決定到市政府文教委員會所屬文物組做研究員,一直工作到今天。這期間市政府對於我生活上的困難也破格地給以解決了很多,因此,我底生活上、工作上、寫作上……是和政府和共產黨底照顧是分不開的,為了使某些人明瞭真相,我覺得有必要應該在這裏寫出來。當我接到政務院文委要我做“公開檢討”的指示時——它是和批示我的小說《五月的礦山》、《第三代》、京劇腳本《武王伐紂》出版等問題載在一封信裏的——立刻就寫了回信,表明對於“公開檢討”我是完全同意的。但為了使這檢討能夠更深刻、更全面、更具體……對於人民或類似我這樣的文藝工作者們能收到更有教育意義的效果,於中國革命更有好處,曾請示他們給我個檢討的方向、範圍、重點或似“提綱”之類的標準;可能時也請他們派一位同志來具體幫助我,以期把這檢討作得更完美一些。又經文委辦公廳覆信,指示我可根據東北局對我的“決定”精神來檢討,待我檢討文字寫好,呈出後,認為有必要時,也可約我面談等等。
前面說過,對於這指示我是感到很愉快的,因為在自己底政府指示下,在廣大人民面前來檢討自己,這是光榮的,完全必要的。這樣可以使人民認清自己,批判自己,監督自己……使自己不致墮落,不致毀滅;使自己更向上,更進步,此後可以完全按照人民所需要的來進行工作。記得毛主席好像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既然全心全意為人民了,生命全可以犧牲,還有什麼“面子”等類值得保留呢?羅曼羅蘭在他底《悲多汶傳記》裏也曾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主要是做到偉大,而不是裝做偉大”。我在這裏引用這些話並非是意味着我來檢討是“偉大”了——這就成了阿Q——而是說,一個人在廣大人民面前應該謙卑,應該虛心,同時更應該勇敢地,對自己毫無憐惜地讓人民來檢查。在人民面前裝腔作勢或玩花頭想法掩藏自己最醜惡的東西,這是對人民的犯罪,對真理的犯罪,也是世界上最可羞恥的懦夫!我個人還不願意做這樣的懦夫,因此把我任何可羞恥的思想全部擺在人民的面前來,決不隱瞞。(我底思想根源將在最後一部分談到。)一九四八年秋在哈爾濱,當《文化報》和《生活報》論爭將近結束,當時東北局宣傳部是這樣決定的:由我和《生活報》負責者雙方各寫一篇“自我檢討”的文字,刊載在各自的報紙上。我用去了差不多二十天的時間寫成了“檢討”一份(《生活報》是否寫了我不知道)交給了劉芝明副部長,但他認為不滿意,覺得我底檢討“避重就輕”,要我按照他底意圖重寫,我不同意,這檢討就沒發表。接着《文化報》停刊了,我到了瀋陽(《生活報》還在繼續出版),接着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就發表了他那“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此文後來曾印成各種單行本發行過。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也分贈過代表們。我看到天津出的一個版本,封面是一幅版畫,一頭牛,兩肩上各插了一把刀子,這可能就是象徵着對我的 “批評”,也看到北京本,封面是一幅清算地主鬥爭圖。)接着東北文藝界也發表了“宣言”,接着東北局也發表了對於我的“決定”以及其他批評文字等(前面已經說過)。
這說明,為了對人民負責,對革命事業負責,即是在哈爾濱我並沒拒絕檢討過。但是要我底檢討一定要按照別人的意圖來進行,我以為這是值得考慮的。
過去我是不能同意《生活報》和劉芝明副部長等把一切問題全提到原則高度,加給我那些“反蘇、反共、反人民”等等的“帽子” 的。這五年間,我既不能承認這些“帽子”,但是我也沒機會發表我底辯解文字,我只有沉默。我沉默地做我應該做的工作,寫我要寫的東西……讓一切冷一冷澄清澄清再說。我是相信歷史和群眾,也相信共產黨和毛主席底英明領導的,凡事總會有個是非分明,水落石出的一天。因此我準備一年不成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那時候從歷史發展證明,如果我所主張的一些問題是錯了,我會毫無躊躇地承認自己應該承認的錯誤,甚至也可承擔人民給予我應得的懲罰,決無怨尤;如果錯誤——或者某一部分是錯了的——屬於別人,那是別人對革命,對人民負責的問題,我無話說。
寫給全國人民的「公開檢查」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致中共中央政務院文教委員會 (一九五三年.北京)
一、五年間
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天“八.一五”紀念日以後,在哈爾濱由魯迅文化出版社出版,我所主編的《文化報》和在光華書店出版、由宋之的等人所編的《生活報》,因了《文化報》在“八.一五”紀念日刊載了幾篇文字,《生活報》認為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解放戰爭的,提出了嚴厲指摘,因而引起了雙方的爭論——繼續了約有兩個月時間——結束以後,到今年的“八.一五”整整是五個週年。這五年間整個中國——除台灣而外——早已獲得了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土改完成,五年建設計劃開始實施……在這些偉大的事跡對比下,這屬於歷史過程上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似乎再沒有提起的必要。不過最近政務院中央文教委員會指示我,還應該把這問題根據我今天的認識,在群眾面前交代清楚,這於我於人民是有益的。對於這指示,我是很愉快地立刻接受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更是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我認為有這義務和責任把自己底思想本質——好或壞——由於這事件所引起的於革命文化事業,政治影響有害的結果,我應負的責任……向人民交代明白,弄清是非——且不管我將來是否還從事文學這工作——使讀過我書或文字的人易於批判,不致盲目地再受毒害;同時也可和某一些自稱或真正能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掌握了馬列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們有所區別,免得“魚目混珠”——這是必要的。
這五年間我盡幹了些什麼呢?應該簡要地在這裏提一提。因為過去間接、直接我曾聽到過很多“謠言”:有的說我被弄到某個礦山去背煤“勞動改造”並因背煤而死了;有的說我自殺了,有的說我被殺了,有的說我被關進監獄了……等等。這些謠言底產生,有的是出於暗藏敵人們惡意污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的是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底本質還認識不清所致。礦山我確是住過一時期,卻並沒背煤,而是在作工會工作。一九四八年底瀋陽解放前,在哈爾濱由我所主持的魯迅文化出版社就交給了公家(原來就是公家的資本),《文化報》也作了結束。瀋陽解放後,我就隨同中共東北局到了瀋陽,而後去鞍山作了一次旅行。一九四九年春(大約三月間)中共東北局宣傳部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發表了他底“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接着東北局對我底“決定”也發表了,同時也發表了其他一些批評我的文字,接着在東北各機關、學校展開了三個月“蕭軍思想討論”的同時,東北局決定我去一處礦山改造和學習(我也是這樣要求的。原來我要求去解放戰爭的前線,未被允許)。我就去到了撫順。在撫順一面做些工會工作——因為這工作可以經常到各礦廠接近工人群眾——同時也幫助那裏建立了一個京劇團,在這劇團裏也做些工作。在撫順工作了約一年半,於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從四月初開始續寫長篇小說《第三代》第八部後半部,結束後,從六月初開始寫一部新小說《五月的礦山》。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間寫完了它(約二十八萬字)。經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委的審查,最近(一九五三年五月)已被決定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和我的家屬在瀋陽都是供給制待遇,我來北京後,寫作中的生活費用,因為中共東北局劉副部長不同意我來北京,而我來了,又不願再回去,這是無組織觀念的“自由行動”,東北局就沒給轉“關係”,當然這裏也就不會“供給”我——這是完全對的。所以我個人的“供給”到北京後就斷絕了。可是我底家屬一直到今天倒還是被供給着的,因為他們是經過批准先到的北京。這期間北京市政府還每月津貼我三百斤小米房費,另外,由於我向周總理的請求,“文聯”曾借給我過三百萬元(舊幣,合現在300元——注)。政府和共產黨在生活上對我這樣破格的照顧,我是衷心感激着的。
《五月的礦山》寫完以後,我着就被決定到市政府文教委員會所屬文物組做研究員,一直工作到今天。這期間市政府對於我生活上的困難也破格地給以解決了很多,因此,我底生活上、工作上、寫作上……是和政府和共產黨底照顧是分不開的,為了使某些人明瞭真相,我覺得有必要應該在這裏寫出來。當我接到政務院文委要我做“公開檢討”的指示時——它是和批示我的小說《五月的礦山》、《第三代》、京劇腳本《武王伐紂》出版等問題載在一封信裏的——立刻就寫了回信,表明對於“公開檢討”我是完全同意的。但為了使這檢討能夠更深刻、更全面、更具體……對於人民或類似我這樣的文藝工作者們能收到更有教育意義的效果,於中國革命更有好處,曾請示他們給我個檢討的方向、範圍、重點或似“提綱”之類的標準;可能時也請他們派一位同志來具體幫助我,以期把這檢討作得更完美一些。又經文委辦公廳覆信,指示我可根據東北局對我的“決定”精神來檢討,待我檢討文字寫好,呈出後,認為有必要時,也可約我面談等等。
前面說過,對於這指示我是感到很愉快的,因為在自己底政府指示下,在廣大人民面前來檢討自己,這是光榮的,完全必要的。這樣可以使人民認清自己,批判自己,監督自己……使自己不致墮落,不致毀滅;使自己更向上,更進步,此後可以完全按照人民所需要的來進行工作。記得毛主席好像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既然全心全意為人民了,生命全可以犧牲,還有什麼“面子”等類值得保留呢?羅曼羅蘭在他底《悲多汶傳記》裏也曾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主要是做到偉大,而不是裝做偉大”。我在這裏引用這些話並非是意味着我來檢討是“偉大”了——這就成了阿Q——而是說,一個人在廣大人民面前應該謙卑,應該虛心,同時更應該勇敢地,對自己毫無憐惜地讓人民來檢查。在人民面前裝腔作勢或玩花頭想法掩藏自己最醜惡的東西,這是對人民的犯罪,對真理的犯罪,也是世界上最可羞恥的懦夫!我個人還不願意做這樣的懦夫,因此把我任何可羞恥的思想全部擺在人民的面前來,決不隱瞞。(我底思想根源將在最後一部分談到。)一九四八年秋在哈爾濱,當《文化報》和《生活報》論爭將近結束,當時東北局宣傳部是這樣決定的:由我和《生活報》負責者雙方各寫一篇“自我檢討”的文字,刊載在各自的報紙上。我用去了差不多二十天的時間寫成了“檢討”一份(《生活報》是否寫了我不知道)交給了劉芝明副部長,但他認為不滿意,覺得我底檢討“避重就輕”,要我按照他底意圖重寫,我不同意,這檢討就沒發表。接着《文化報》停刊了,我到了瀋陽(《生活報》還在繼續出版),接着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就發表了他那“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此文後來曾印成各種單行本發行過。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也分贈過代表們。我看到天津出的一個版本,封面是一幅版畫,一頭牛,兩肩上各插了一把刀子,這可能就是象徵着對我的 “批評”,也看到北京本,封面是一幅清算地主鬥爭圖。)接着東北文藝界也發表了“宣言”,接着東北局也發表了對於我的“決定”以及其他批評文字等(前面已經說過)。
這說明,為了對人民負責,對革命事業負責,即是在哈爾濱我並沒拒絕檢討過。但是要我底檢討一定要按照別人的意圖來進行,我以為這是值得考慮的。
過去我是不能同意《生活報》和劉芝明副部長等把一切問題全提到原則高度,加給我那些“反蘇、反共、反人民”等等的“帽子” 的。這五年間,我既不能承認這些“帽子”,但是我也沒機會發表我底辯解文字,我只有沉默。我沉默地做我應該做的工作,寫我要寫的東西……讓一切冷一冷澄清澄清再說。我是相信歷史和群眾,也相信共產黨和毛主席底英明領導的,凡事總會有個是非分明,水落石出的一天。因此我準備一年不成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那時候從歷史發展證明,如果我所主張的一些問題是錯了,我會毫無躊躇地承認自己應該承認的錯誤,甚至也可承擔人民給予我應得的懲罰,決無怨尤;如果錯誤——或者某一部分是錯了的——屬於別人,那是別人對革命,對人民負責的問題,我無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