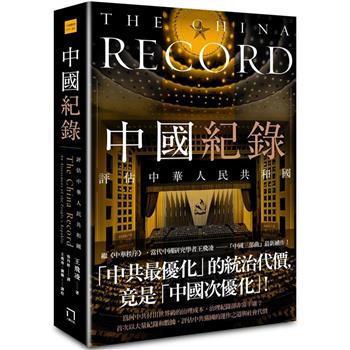1.引言
在2017年出版的《中華秩序》一書中,我試圖重新解讀並分析中國的歷史及世界觀,透過考察秦漢式政體與中華天下之世界秩序,釐清中國的政治傳統以及價值觀念結構。本書《中國紀錄》是《中華秩序》的續篇,將聚焦於現代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評議其做為一個另類的政治體系模式和一個獨特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型之紀錄。
隨著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力量雙雙往世界第一衝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體系,將益發影響全人類,遠不只是僅僅塑造中國人民的命運及未來。在2021年和2022年,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公開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力量的崛起,已經形成一個系統性的挑戰,甚至對全球秩序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生存威脅。因此,扎實地了解和評估中國的政治治理模式及社會經濟發展模型,對全世界(包括中國人民)來說,都是迫切之舉。在現今的全球主義(globalism)及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時代之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系的強項或優點、弱點或缺陷,在理論上及實務上都十分關鍵。為此目的,我希望本書呈上的簡明分析,能夠使讀者去全面、精準而有用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就與不足、強項及弱點。在探討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CCP-PRC)的活力(viability)及可取性(desirability)等議題時,我希冀能對這個黨國,提出一個客觀事實性的論述,以及一個規範批判性的分析。希望本書的發現會有助於世界對中國力量崛起之現實的政策考量,並由此制定合適的回應戰略。
本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評估,是基於分析其在四個領域的組織特徵及運作表現: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環境保育。考察此四項的目的,在於確認崛起的中國力量做為目前世界領袖候選人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和其取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能力,以及北京追求以「中華秩序」代替西方主導的「西發里亞式」(Westphalian)世界秩序之可行性及可取性。在過去七十多年裡,中國經歷了許多史詩級的動盪:改革、進步、成功、失敗及倒退,有無數的英雄、惡人、倖存者及犧牲者。我很清楚這非凡的連貫性及偉大的變動,使得拙著之寫作,充滿了許多引人入勝卻又令人謙謹的挑戰。
我首先將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治理,即中共統治下的人民民主專政(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尤其是其在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及權利、提供社會秩序與安定,以及公共服務及政府效率等方面的紀錄。接著,我將試圖報告並評議中國經濟,尤其是其在近數十年間的成就及問題,最後再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生活與精神及實體生態。本書將著重於中共治理在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司法正義、財政及貨幣政策、國家主導型經濟成長模式(state-led growth model)、創新、學術及教育、不平等與貧窮、災難救助及流行病預防、文化與道德、社會安定、古蹟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的運作及影響。透過規範性評估(normative evaluation)與量性及質性資料之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相結合,本書試圖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與特徵,尤其是探討中共做為一個代表不同價值觀及規範的新興強權、乃至一個潛在的世界新領袖,具有或者缺乏哪些效能、效率、力量、永續性及可取性。做為推進中國研究的一個小小努力,本書選擇聚焦於總體紀錄,以提供評價及判斷,而非試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做一個面面俱到的細微敘述。
更明確地說,本書意在展現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面貌及其究竟代表著什麼。本書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帶給中國的政治次優化(the China suboptimality)、社會經濟表現不佳、文化及環境飽受損害,都是只為達成驚人的中共統治最優化(the CCP optimality),以維繫其政權的壽命與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前三十年(1949至79年),是一個千真萬確、規模龐大的悲劇。中國共產黨受其內在邏輯驅使,再加上獨裁領導人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及無能,硬是使得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一世紀(1840年代至1949年)裡取得的種種進步及改變生生倒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中共的權力載具,同時中共也企圖重定整個世界的中心並重整世界秩序,以達成其政權的終極安全。為此,中共使得中國走上漫長而慘痛的大彎路,在許多方面都辜負了中國人民,最後面臨一個理所當然要崩潰的局面。
毛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的應對之道,則是退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民族國家主義(statist and nationalist)軌道及政策上,以求其政權的生存。因此,在過去四十年之間,猶如巨大的歷史諷刺,中共被其始終想取代的西方主導之西發里亞式國際體系所挽救並且致富,中國人民重新獲得相當程度(但依舊有限)的社會經濟自由及自主權。中國經濟因此經歷了驚人的爆炸式成長,使得數億人口脫離赤貧。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廣泛的科學技術(多來自國外),打造出相當完整且具競爭力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社會和人民日常生活也大幅改善及轉變,且大致是往現代化及西方化的總體方向而去。本書稍後將會詳細報告,大批擁有可觀可支配收入及資產的「中產階級」湧現,且能經常在國內外旅行。成文法的發展和個人權利規範的增生,尤其是在商業領域,提升了可預測性及信任度,促進了市場導向型商業。宗教活動和社會文化普遍也都重新煥發活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積極參與了國際合作:從在全球生產鏈舉足輕重的位置和提供大量外援,到派出大批軍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在毛式政治體系的治理之下;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確保中共一黨獨裁的安全與權力,能在中國延續下去。這個黨國的DNA,即所謂「紅色基因」,大多依舊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一個統計數字上的巨人,從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中汲取海量資源;而中國的經濟成就完全有賴於比較自由了的勤奮的中國人民,更仰賴大量外資及技術的挹注。總體而言,若兼具質性與量性地評估生命安全、民權及人權、自由與安定、生活水平及醫療、經濟效率與創新、道德與文化發展、社會經濟正義與平等、自然災害與流行病管理、古蹟及環境保育等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及社會經濟發展,最好也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常常是次優化(suboptimal)的表現。除了系統性地剝奪權利及自由,中共還在中國人民身上強加了極高的機會成本,對中國的社會結構、道德規範、創造精神及生態,造成深遠且多方面的影響。這些重大後果有些也許還來得及彌補挽救,但有些就算不是藥石罔效,也是積重難返,且早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人們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中共持續掌權,並企圖按自身形象來影響重列各國,被中共侵占使用的崛起中的中國力量,代表了一個次優化且不可取、但可行且不容忽視的現存國際社會西方領袖之替代選擇,深深地影響人類文明的未來。
(摘自:《中國紀錄》,〈引言〉)
2.〈第二章 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從生活水平、經濟效率、創新和社會文化進步等方面來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一場災難,充滿了苦難、倒退、禍害和危機。再加上前一章所述,毛主義經濟政策創下了破紀錄的死亡人數,以及對人民公民權利及人權的大規模剝奪,釀成了「中國悲劇」,並在「一場脫軌的革命」過程中造成了廣泛而巨大的破壞。
自1980年代以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情況要好得多,經濟增長令人矚目,技術進步迅速,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隨著毛主義災難逐漸平息,中共為求政權生存,不情願但明智地躲藏起來,即所謂「韜光養晦」。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性地接受了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版西發里亞體系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以換取西方的關鍵救援,為其提供合法性、技術、資本、市場、資源和食品。北京被迫放鬆和調整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極權控制,在相當程度上退出了人民群眾的日常社會與經濟生活;透過進口和模仿,讓中國回到1949年以前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state-capitalistic development)及國家自強(self-strengthening)軌道上,資金來源則是依靠出口和外資。成果就是,毛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爆發性的經濟增長,並取得兩項格外耀眼的成就:GDP的快速增長,以及打破世界紀錄的外匯儲備。據估計,多達4.3億中國人,即總人口的30%,現在擁有可觀的可支配收入,其購買力構成了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之大可媲美美國或歐盟。筆者親眼見證了中國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驚人崛起,並親身體會到中國人民對其社會經濟成就理所當然感受到的巨大喜悅和深切自豪。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不斷發表文章書籍,記錄和讚揚中國數十年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藉機自我誇耀,各種各樣追逐私利、有如推銷員的人物自然更是大加捧場和宣揚。
本章旨在超越浮華的外表和一般的常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紀錄進行一個力圖平衡的評估。結果發現,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裡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方旗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基本上是在由發展型國家主導的原始資本主義(developmental state-directed raw capitalism)或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軌道上擴展。中共仍維持對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專制統治,過度汲取且管理不良,尤其是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低效率、缺乏創新、資源配置紊亂與金融泡沫、不平等與貧困仍舊是廣泛且持續的現象,甚至嚴重惡化。中國的整體社會經濟表現仍然相當平庸,而且大多次優化,往往表現不佳且成本高昂,從長遠來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綜合觀之,中國經濟仍牢牢地位居發展中國家之列。高GDP增長率和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兩大耀眼成就,在詳加檢視後,尤其顯得暗淡許多。
中國模式
坊間已有無數著作出版,大加讚美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顯著、甚至「奇蹟式」的經濟增長,並常常將其歸功於一個勝過其他經濟體系,獨特而卓越的「中國模式」。然而,正如我將在本章中所詳述的,中國過去四十年來的經濟紀錄雖然迷人,但既沒有展現出什麼奇蹟,也沒有提出什麼新的經濟模式,更不代表中共的治理方式有多優越。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南韓、新加坡、臺灣等發展型國家的經驗高度相似,也深受其影響,都帶上了一層傳統「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的意識形態色彩。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在香港和臺灣)和海外華人僑胞的「推助」角色尤其關鍵:他們提供了資本、技術、管理知識,並打通至關緊要的出口管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功勞不過是放鬆了對經濟的部分控制,讓中國人民有空間自主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同時解除了中國的自我孤立狀態,讓國際資本和外國技術進入。該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廣為人知的作用,或者說某種值得注意的功勞,就在於透過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央計畫機制,能壟斷資源、與資本家交好、控制和安撫勞工,因此得以專注於支持一些大型發展主義項目,例如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以及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大規模發展。然而,正如我後續將在本章所記錄的,這個角色充其量只是好壞參半,它確實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但也伴隨極大的成本和問題,並導致經濟增長的效率持續低落和下降。
趙紫陽等務實的中共領導人在1980年代精明地引用了1920年代莫斯科的權宜之計「新經濟政策」和1950至1970年代東歐「同志們」的經濟改革,在意識形態上掩蓋其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位名聲顯赫的中國老記者曾一針見血地說道,毛後時期的改革「只是試圖回頭與1930年代相銜接」。中共自1980年代以來看似沒完沒了的「改革」,「並不是制度創新」,儘管官方說詞和標籤都如是說。正如一位美國漢學家的分析,發展主義的中國政府允許、甚至「指導」民眾視情況即興發揮,嘗試「用你所擁有的」來致富,才是中國在1980至2010年代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不是中共的「集中威權控制」。一位中國經濟理論史學家在2021年也得出類似的結論:過去四十年來,「當代中國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的演變」既沒有理論上的創新,也沒有提出高超的遠見;政府只是嘗試(以不同的想法)去「管理同一個問題」,即要政治控制還是要經濟增長,目的則是讓國家「變得富強」,從而「超越」西方。
任何對經濟增長感興趣的集權且活躍的發展型國家(無論其動機為求合法性和權力或其他),種族比較單一同質,又遇到張開雙臂歡迎的西方國家,當然可以享有可觀的經濟增長。在積累資本和繞過劉易斯轉型(Lewis Transition)以吸收大量「過剩」勞動力的經濟「起飛」之關鍵時刻尤其如此。正如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所總結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正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逐漸退出經濟。」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以及更加克制和記取教訓的江澤民及胡錦濤政權,確實讓出了更多空間,讓中國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潤和舒適生活。隨著束縛稍懈,雖然仍處於黨國政治治理而持續的「中國次優化」狀態下,勤勞又具創業精神的中國人民迅速證明他們完全有能力創造財富和進行經濟競爭,也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和巨大的進步,足以媲美(如果不是超越)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前經濟學家提出的「後發者的優勢」,即利用現成技術和長期積累的豐富的比較優勢,可預期地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增長。
因為其政治基因,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一個控制和汲取型國家,因其有限、策略性和暫時地退出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中獲得了超額的報償。在沒有真正政治轉型的情況下,毛式秦漢政體的基礎仍然持續著,這種政體始終對中國政治菁英具有高度誘惑力,並且有著深深的結構性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尤其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似乎感到更安全、更強大了,因此一如預料地斷然恢復和延續舊制,拒絕社會政治改革,加強汲取和壟斷,鎮壓異見,抗拒遵從世界的主流規範和價值觀模式。正如一名觀察家在2022年所總結的,中共黨國就像一個巨大的中國公司(China Inc),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中共公司(CCP Inc),滲透並控制著中國經濟,徹底利用其「低人權優勢和其他國家的容忍度(……並表現得好像)國有企業是其業務部門或子公司,民營企業是其合資企業,而外國公司則是該黨的加盟商。」
因此,毛後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社會經濟表現,在本質上,儘管與許多人的直覺相悖,仍然是相當平庸且大多為次優化的,往往表現不佳,並迫使中國人民無止盡地忍受艱辛,即口語所說的「吃苦」。中國的政治經濟,尤其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仍然是政治化且由中共主宰。中國有種特殊的腐敗情事,是所謂的「買路錢」(access money),即企業家賄賂官員以獲得空間和幫助,進而開展和發展某事,如今看來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弊已經大於利,因為它越來越無法與其他對增長不那麼友好但更為普遍的腐敗行為競爭,例如掠奪和欺詐。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一大赤字海洋和無數的泡沫,深深拖累著中國經濟,並造成了嚴重的低效率和缺乏創新。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在2021年秋天指出:「自2009年以來,尤其是過去八至九年,中國經濟基本上進入了更深的泡沫化。」從資本回報、能源消耗等方面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擁有世界第二大 GDP的中國,看似是經濟超級大國,但這主要是數字上的結果。兩大亮眼成就,高GDP增長率和全球最大外匯儲備,細究之下卻是問題重重。用中國經濟學家因謹慎而含糊的話來說,中國經濟增長是得益於在國內和國外的兩個「逐底競爭」;由於國家對土地、資源和金融體系的壟斷,這種競爭也越來越不可持續。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表現之所以不可改變地走向次優化,肯定有很多原因;一個國家的集體命運也是如此。但具影響力的學者,從謬達爾(Gunnar Myrdal)和諾思(Douglass North),到沈恩(Amartya Sen)及其他人,長期以來都認為政治治理和經濟制度(及其內化或文化),特別是一個適合的國家(proper state)及其有能力的政策,能與運作良好的市場系統合作無間,才是決定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一項採用多種方法的計量經濟學研究在2019年總結道,「民主確實會導致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增長」,尤其從長遠來看,「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近因之間,存在許多相輔相成之處」。一位受過美國培訓的中國學者依此脈絡主張政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並認為民主「在促進發展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中國的一位「馬克思主義專家」也同意「決定國家富庶或貧困的祕密在於國家的治理之道」。
儘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一種19世紀式的原始資本主義相當盛行;但該黨國仍然是一個「基本上不自由的經濟體」,其「經濟自由指數」的分數始終「低於地區和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21年,香港和澳門幾十年來享有的極高經濟自由,由於北京對兩個「特區」的政治絞殺,也被視為「丟失」了。面對中共激烈但絲毫不見功效的遊說努力,西方、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各大經濟體,都在2020年代認證中國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體,更不用說是具有可靠法治的市場經濟了。近年來,所謂「中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更被理解為退化至「黨國資本主義」──中共的政治控制邏輯,進一步取代了中國經濟中的市場機制。「追趕式」(catch-up)增長的快速勃發開始消減,以及在習近平身上狂熱再造一個毛二世(Mao the Second),都強烈昭示著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似乎將面臨更艱困的未來,即便不是全面回歸中國悲劇那樣的毛主義災難。
像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後來者」國家,可能享有可觀的「後發優勢」,得以輕鬆且通常以低廉價格獲得世界一流的技術、大量國際資本,以及發達國家已經開發好的廣大市場。然而,它也可能遭受所謂的「後來者詛咒」(latecomer’s curse)或「後發劣勢」,即一度繁榮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時間的過去而停滯衰退之現象,甚至因其社會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不足而面臨更糟的情況。這或許類似於惡名昭彰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或「富足悖論」(paradox of plenty),毀了許多自然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從發達國家進口和模仿現有技術以發展經濟,即使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增長一段時間,後來者國家的統治者往往沒有多少理由、動機、意願或能力,同時複製發達國家的政治規範和制度。但事實上,這些制度和規範正是永續技術創新和社會經濟發展得來不易且歷經考驗的先決條件和必要夥伴。這種「後來者詛咒」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許多發展中國家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而無法躋身為發達國家。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所總結的,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只是空談,往往流於表面」。因此,後發劣勢所帶來的詛咒性制度赤字的影響,似乎將持續發生並且仍在加劇,風險越來越大,嚴重性也越來越明顯。
(摘自:《中國紀錄》,〈第二章、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2017年出版的《中華秩序》一書中,我試圖重新解讀並分析中國的歷史及世界觀,透過考察秦漢式政體與中華天下之世界秩序,釐清中國的政治傳統以及價值觀念結構。本書《中國紀錄》是《中華秩序》的續篇,將聚焦於現代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評議其做為一個另類的政治體系模式和一個獨特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型之紀錄。
隨著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力量雙雙往世界第一衝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體系,將益發影響全人類,遠不只是僅僅塑造中國人民的命運及未來。在2021年和2022年,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公開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力量的崛起,已經形成一個系統性的挑戰,甚至對全球秩序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生存威脅。因此,扎實地了解和評估中國的政治治理模式及社會經濟發展模型,對全世界(包括中國人民)來說,都是迫切之舉。在現今的全球主義(globalism)及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時代之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系的強項或優點、弱點或缺陷,在理論上及實務上都十分關鍵。為此目的,我希望本書呈上的簡明分析,能夠使讀者去全面、精準而有用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就與不足、強項及弱點。在探討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CCP-PRC)的活力(viability)及可取性(desirability)等議題時,我希冀能對這個黨國,提出一個客觀事實性的論述,以及一個規範批判性的分析。希望本書的發現會有助於世界對中國力量崛起之現實的政策考量,並由此制定合適的回應戰略。
本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評估,是基於分析其在四個領域的組織特徵及運作表現: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環境保育。考察此四項的目的,在於確認崛起的中國力量做為目前世界領袖候選人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和其取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能力,以及北京追求以「中華秩序」代替西方主導的「西發里亞式」(Westphalian)世界秩序之可行性及可取性。在過去七十多年裡,中國經歷了許多史詩級的動盪:改革、進步、成功、失敗及倒退,有無數的英雄、惡人、倖存者及犧牲者。我很清楚這非凡的連貫性及偉大的變動,使得拙著之寫作,充滿了許多引人入勝卻又令人謙謹的挑戰。
我首先將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治理,即中共統治下的人民民主專政(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尤其是其在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及權利、提供社會秩序與安定,以及公共服務及政府效率等方面的紀錄。接著,我將試圖報告並評議中國經濟,尤其是其在近數十年間的成就及問題,最後再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生活與精神及實體生態。本書將著重於中共治理在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司法正義、財政及貨幣政策、國家主導型經濟成長模式(state-led growth model)、創新、學術及教育、不平等與貧窮、災難救助及流行病預防、文化與道德、社會安定、古蹟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的運作及影響。透過規範性評估(normative evaluation)與量性及質性資料之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相結合,本書試圖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與特徵,尤其是探討中共做為一個代表不同價值觀及規範的新興強權、乃至一個潛在的世界新領袖,具有或者缺乏哪些效能、效率、力量、永續性及可取性。做為推進中國研究的一個小小努力,本書選擇聚焦於總體紀錄,以提供評價及判斷,而非試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做一個面面俱到的細微敘述。
更明確地說,本書意在展現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面貌及其究竟代表著什麼。本書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帶給中國的政治次優化(the China suboptimality)、社會經濟表現不佳、文化及環境飽受損害,都是只為達成驚人的中共統治最優化(the CCP optimality),以維繫其政權的壽命與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前三十年(1949至79年),是一個千真萬確、規模龐大的悲劇。中國共產黨受其內在邏輯驅使,再加上獨裁領導人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及無能,硬是使得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一世紀(1840年代至1949年)裡取得的種種進步及改變生生倒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中共的權力載具,同時中共也企圖重定整個世界的中心並重整世界秩序,以達成其政權的終極安全。為此,中共使得中國走上漫長而慘痛的大彎路,在許多方面都辜負了中國人民,最後面臨一個理所當然要崩潰的局面。
毛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的應對之道,則是退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民族國家主義(statist and nationalist)軌道及政策上,以求其政權的生存。因此,在過去四十年之間,猶如巨大的歷史諷刺,中共被其始終想取代的西方主導之西發里亞式國際體系所挽救並且致富,中國人民重新獲得相當程度(但依舊有限)的社會經濟自由及自主權。中國經濟因此經歷了驚人的爆炸式成長,使得數億人口脫離赤貧。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廣泛的科學技術(多來自國外),打造出相當完整且具競爭力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社會和人民日常生活也大幅改善及轉變,且大致是往現代化及西方化的總體方向而去。本書稍後將會詳細報告,大批擁有可觀可支配收入及資產的「中產階級」湧現,且能經常在國內外旅行。成文法的發展和個人權利規範的增生,尤其是在商業領域,提升了可預測性及信任度,促進了市場導向型商業。宗教活動和社會文化普遍也都重新煥發活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積極參與了國際合作:從在全球生產鏈舉足輕重的位置和提供大量外援,到派出大批軍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在毛式政治體系的治理之下;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確保中共一黨獨裁的安全與權力,能在中國延續下去。這個黨國的DNA,即所謂「紅色基因」,大多依舊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一個統計數字上的巨人,從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中汲取海量資源;而中國的經濟成就完全有賴於比較自由了的勤奮的中國人民,更仰賴大量外資及技術的挹注。總體而言,若兼具質性與量性地評估生命安全、民權及人權、自由與安定、生活水平及醫療、經濟效率與創新、道德與文化發展、社會經濟正義與平等、自然災害與流行病管理、古蹟及環境保育等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及社會經濟發展,最好也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常常是次優化(suboptimal)的表現。除了系統性地剝奪權利及自由,中共還在中國人民身上強加了極高的機會成本,對中國的社會結構、道德規範、創造精神及生態,造成深遠且多方面的影響。這些重大後果有些也許還來得及彌補挽救,但有些就算不是藥石罔效,也是積重難返,且早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人們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中共持續掌權,並企圖按自身形象來影響重列各國,被中共侵占使用的崛起中的中國力量,代表了一個次優化且不可取、但可行且不容忽視的現存國際社會西方領袖之替代選擇,深深地影響人類文明的未來。
(摘自:《中國紀錄》,〈引言〉)
2.〈第二章 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從生活水平、經濟效率、創新和社會文化進步等方面來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一場災難,充滿了苦難、倒退、禍害和危機。再加上前一章所述,毛主義經濟政策創下了破紀錄的死亡人數,以及對人民公民權利及人權的大規模剝奪,釀成了「中國悲劇」,並在「一場脫軌的革命」過程中造成了廣泛而巨大的破壞。
自1980年代以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情況要好得多,經濟增長令人矚目,技術進步迅速,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隨著毛主義災難逐漸平息,中共為求政權生存,不情願但明智地躲藏起來,即所謂「韜光養晦」。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性地接受了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版西發里亞體系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以換取西方的關鍵救援,為其提供合法性、技術、資本、市場、資源和食品。北京被迫放鬆和調整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極權控制,在相當程度上退出了人民群眾的日常社會與經濟生活;透過進口和模仿,讓中國回到1949年以前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state-capitalistic development)及國家自強(self-strengthening)軌道上,資金來源則是依靠出口和外資。成果就是,毛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爆發性的經濟增長,並取得兩項格外耀眼的成就:GDP的快速增長,以及打破世界紀錄的外匯儲備。據估計,多達4.3億中國人,即總人口的30%,現在擁有可觀的可支配收入,其購買力構成了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之大可媲美美國或歐盟。筆者親眼見證了中國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驚人崛起,並親身體會到中國人民對其社會經濟成就理所當然感受到的巨大喜悅和深切自豪。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不斷發表文章書籍,記錄和讚揚中國數十年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藉機自我誇耀,各種各樣追逐私利、有如推銷員的人物自然更是大加捧場和宣揚。
本章旨在超越浮華的外表和一般的常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紀錄進行一個力圖平衡的評估。結果發現,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裡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方旗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基本上是在由發展型國家主導的原始資本主義(developmental state-directed raw capitalism)或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軌道上擴展。中共仍維持對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專制統治,過度汲取且管理不良,尤其是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低效率、缺乏創新、資源配置紊亂與金融泡沫、不平等與貧困仍舊是廣泛且持續的現象,甚至嚴重惡化。中國的整體社會經濟表現仍然相當平庸,而且大多次優化,往往表現不佳且成本高昂,從長遠來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綜合觀之,中國經濟仍牢牢地位居發展中國家之列。高GDP增長率和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兩大耀眼成就,在詳加檢視後,尤其顯得暗淡許多。
中國模式
坊間已有無數著作出版,大加讚美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顯著、甚至「奇蹟式」的經濟增長,並常常將其歸功於一個勝過其他經濟體系,獨特而卓越的「中國模式」。然而,正如我將在本章中所詳述的,中國過去四十年來的經濟紀錄雖然迷人,但既沒有展現出什麼奇蹟,也沒有提出什麼新的經濟模式,更不代表中共的治理方式有多優越。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南韓、新加坡、臺灣等發展型國家的經驗高度相似,也深受其影響,都帶上了一層傳統「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的意識形態色彩。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在香港和臺灣)和海外華人僑胞的「推助」角色尤其關鍵:他們提供了資本、技術、管理知識,並打通至關緊要的出口管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功勞不過是放鬆了對經濟的部分控制,讓中國人民有空間自主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同時解除了中國的自我孤立狀態,讓國際資本和外國技術進入。該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廣為人知的作用,或者說某種值得注意的功勞,就在於透過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央計畫機制,能壟斷資源、與資本家交好、控制和安撫勞工,因此得以專注於支持一些大型發展主義項目,例如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以及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大規模發展。然而,正如我後續將在本章所記錄的,這個角色充其量只是好壞參半,它確實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但也伴隨極大的成本和問題,並導致經濟增長的效率持續低落和下降。
趙紫陽等務實的中共領導人在1980年代精明地引用了1920年代莫斯科的權宜之計「新經濟政策」和1950至1970年代東歐「同志們」的經濟改革,在意識形態上掩蓋其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位名聲顯赫的中國老記者曾一針見血地說道,毛後時期的改革「只是試圖回頭與1930年代相銜接」。中共自1980年代以來看似沒完沒了的「改革」,「並不是制度創新」,儘管官方說詞和標籤都如是說。正如一位美國漢學家的分析,發展主義的中國政府允許、甚至「指導」民眾視情況即興發揮,嘗試「用你所擁有的」來致富,才是中國在1980至2010年代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不是中共的「集中威權控制」。一位中國經濟理論史學家在2021年也得出類似的結論:過去四十年來,「當代中國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的演變」既沒有理論上的創新,也沒有提出高超的遠見;政府只是嘗試(以不同的想法)去「管理同一個問題」,即要政治控制還是要經濟增長,目的則是讓國家「變得富強」,從而「超越」西方。
任何對經濟增長感興趣的集權且活躍的發展型國家(無論其動機為求合法性和權力或其他),種族比較單一同質,又遇到張開雙臂歡迎的西方國家,當然可以享有可觀的經濟增長。在積累資本和繞過劉易斯轉型(Lewis Transition)以吸收大量「過剩」勞動力的經濟「起飛」之關鍵時刻尤其如此。正如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所總結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正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逐漸退出經濟。」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以及更加克制和記取教訓的江澤民及胡錦濤政權,確實讓出了更多空間,讓中國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潤和舒適生活。隨著束縛稍懈,雖然仍處於黨國政治治理而持續的「中國次優化」狀態下,勤勞又具創業精神的中國人民迅速證明他們完全有能力創造財富和進行經濟競爭,也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和巨大的進步,足以媲美(如果不是超越)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前經濟學家提出的「後發者的優勢」,即利用現成技術和長期積累的豐富的比較優勢,可預期地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增長。
因為其政治基因,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一個控制和汲取型國家,因其有限、策略性和暫時地退出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中獲得了超額的報償。在沒有真正政治轉型的情況下,毛式秦漢政體的基礎仍然持續著,這種政體始終對中國政治菁英具有高度誘惑力,並且有著深深的結構性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尤其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似乎感到更安全、更強大了,因此一如預料地斷然恢復和延續舊制,拒絕社會政治改革,加強汲取和壟斷,鎮壓異見,抗拒遵從世界的主流規範和價值觀模式。正如一名觀察家在2022年所總結的,中共黨國就像一個巨大的中國公司(China Inc),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中共公司(CCP Inc),滲透並控制著中國經濟,徹底利用其「低人權優勢和其他國家的容忍度(……並表現得好像)國有企業是其業務部門或子公司,民營企業是其合資企業,而外國公司則是該黨的加盟商。」
因此,毛後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社會經濟表現,在本質上,儘管與許多人的直覺相悖,仍然是相當平庸且大多為次優化的,往往表現不佳,並迫使中國人民無止盡地忍受艱辛,即口語所說的「吃苦」。中國的政治經濟,尤其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仍然是政治化且由中共主宰。中國有種特殊的腐敗情事,是所謂的「買路錢」(access money),即企業家賄賂官員以獲得空間和幫助,進而開展和發展某事,如今看來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弊已經大於利,因為它越來越無法與其他對增長不那麼友好但更為普遍的腐敗行為競爭,例如掠奪和欺詐。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一大赤字海洋和無數的泡沫,深深拖累著中國經濟,並造成了嚴重的低效率和缺乏創新。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在2021年秋天指出:「自2009年以來,尤其是過去八至九年,中國經濟基本上進入了更深的泡沫化。」從資本回報、能源消耗等方面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擁有世界第二大 GDP的中國,看似是經濟超級大國,但這主要是數字上的結果。兩大亮眼成就,高GDP增長率和全球最大外匯儲備,細究之下卻是問題重重。用中國經濟學家因謹慎而含糊的話來說,中國經濟增長是得益於在國內和國外的兩個「逐底競爭」;由於國家對土地、資源和金融體系的壟斷,這種競爭也越來越不可持續。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表現之所以不可改變地走向次優化,肯定有很多原因;一個國家的集體命運也是如此。但具影響力的學者,從謬達爾(Gunnar Myrdal)和諾思(Douglass North),到沈恩(Amartya Sen)及其他人,長期以來都認為政治治理和經濟制度(及其內化或文化),特別是一個適合的國家(proper state)及其有能力的政策,能與運作良好的市場系統合作無間,才是決定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一項採用多種方法的計量經濟學研究在2019年總結道,「民主確實會導致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增長」,尤其從長遠來看,「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近因之間,存在許多相輔相成之處」。一位受過美國培訓的中國學者依此脈絡主張政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並認為民主「在促進發展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中國的一位「馬克思主義專家」也同意「決定國家富庶或貧困的祕密在於國家的治理之道」。
儘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一種19世紀式的原始資本主義相當盛行;但該黨國仍然是一個「基本上不自由的經濟體」,其「經濟自由指數」的分數始終「低於地區和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21年,香港和澳門幾十年來享有的極高經濟自由,由於北京對兩個「特區」的政治絞殺,也被視為「丟失」了。面對中共激烈但絲毫不見功效的遊說努力,西方、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各大經濟體,都在2020年代認證中國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體,更不用說是具有可靠法治的市場經濟了。近年來,所謂「中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更被理解為退化至「黨國資本主義」──中共的政治控制邏輯,進一步取代了中國經濟中的市場機制。「追趕式」(catch-up)增長的快速勃發開始消減,以及在習近平身上狂熱再造一個毛二世(Mao the Second),都強烈昭示著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似乎將面臨更艱困的未來,即便不是全面回歸中國悲劇那樣的毛主義災難。
像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後來者」國家,可能享有可觀的「後發優勢」,得以輕鬆且通常以低廉價格獲得世界一流的技術、大量國際資本,以及發達國家已經開發好的廣大市場。然而,它也可能遭受所謂的「後來者詛咒」(latecomer’s curse)或「後發劣勢」,即一度繁榮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時間的過去而停滯衰退之現象,甚至因其社會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不足而面臨更糟的情況。這或許類似於惡名昭彰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或「富足悖論」(paradox of plenty),毀了許多自然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從發達國家進口和模仿現有技術以發展經濟,即使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增長一段時間,後來者國家的統治者往往沒有多少理由、動機、意願或能力,同時複製發達國家的政治規範和制度。但事實上,這些制度和規範正是永續技術創新和社會經濟發展得來不易且歷經考驗的先決條件和必要夥伴。這種「後來者詛咒」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許多發展中國家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而無法躋身為發達國家。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所總結的,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只是空談,往往流於表面」。因此,後發劣勢所帶來的詛咒性制度赤字的影響,似乎將持續發生並且仍在加劇,風險越來越大,嚴重性也越來越明顯。
(摘自:《中國紀錄》,〈第二章、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