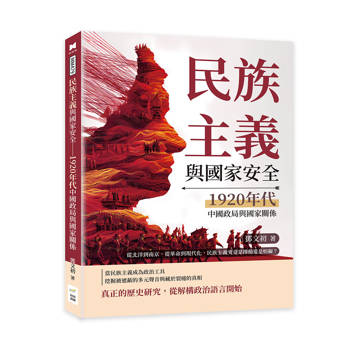第一章、引論
民族主義研究自1990年代開始,成為國際政治、歷史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流風所及,對研究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從出版論文、論著,還是研討會的展開角度來看,也是蔚為大觀。以民族主義為博士、碩士學位論文選題的文章,在近五年時間達59部。可以想見,研究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社會潮流與學界新寵。
但也正因為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時尚,無論是在社會思潮的波動層面,還是在學術研究的建構層面,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理性回應與反思。「民族主義」成為一種社會與學界的「眾因之因」,諸凡現象都可以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中得到解釋。學術研究的時尚化,隨著開始流行「民族主義」的話語而趨於混亂。作為一種非學術的,無法精確界定的術語,「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在學術研究領域是否還有價值?這樣的疑問,已經成為學界無法迴避的問題。
回顧1990年代以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我們發現:對民族主義的界定與分析,所關注的重點與解釋的框架,是與中國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思想史的整體正規化轉型無法分離。隨著近代中國史研究的正規化,由革命史框架向現代化框架的轉變,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分析也經歷了這一轉型。在20世紀最後幾年,在近代中國史研究正規化中,出現了由現代化向後現代正規化的轉移,又一次使研究民族主義步趨時尚,採用了這一分析模式。在這種研究正規化的汰舊換新的遊戲中,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研究所關注的問題,也由早期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往「民族國家建構與認同」移動。如果反思這樣的「正規化變革」的動因,我們很難在其中找到「民族主義」研究的內在證據、變革的動因,最終總是存在於思想史,以及作為思想史研究框架的近代中國史的解釋中。這種研究正規化的「騰籠換鳥」遊戲,為「民族主義」研究的學理化帶來諸多困境,也一再引發學界的反思──民族主義,或者思想史研究是否擁有自身的解釋架構? 沒有自身解釋架構的學術研究如何可行?如果要建立一個自足的解釋框架,這一框架的建構應該在什麼層面上展開?顯然地,這些問題與其說是針對「民族主義」這一具體問題,不如說是針對思想史的整體研究狀況更為妥當。
也就是說,我們關注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思想史研究?
對於這一系列的思想史問題,學界的討論已經初露端倪。本文不準備做純概念的分析,只針對本論著所關注的論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現狀,做接近經驗式的觀察。
(下面的討論不準備做系統的學術史分析──在一個學術出版氾濫的時代,學術史分析在整體上已經不可能,而且也沒有必要。與其將有限的精力耗費在魚龍混雜的各種文字中,不如只關注問題的重心。因此,本文的展開並不迴避因個人的選擇所造成的偏頗與遮蔽等困難。)
民族主義研究自1990年代開始,成為國際政治、歷史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流風所及,對研究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從出版論文、論著,還是研討會的展開角度來看,也是蔚為大觀。以民族主義為博士、碩士學位論文選題的文章,在近五年時間達59部。可以想見,研究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社會潮流與學界新寵。
但也正因為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時尚,無論是在社會思潮的波動層面,還是在學術研究的建構層面,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理性回應與反思。「民族主義」成為一種社會與學界的「眾因之因」,諸凡現象都可以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中得到解釋。學術研究的時尚化,隨著開始流行「民族主義」的話語而趨於混亂。作為一種非學術的,無法精確界定的術語,「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在學術研究領域是否還有價值?這樣的疑問,已經成為學界無法迴避的問題。
回顧1990年代以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我們發現:對民族主義的界定與分析,所關注的重點與解釋的框架,是與中國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思想史的整體正規化轉型無法分離。隨著近代中國史研究的正規化,由革命史框架向現代化框架的轉變,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分析也經歷了這一轉型。在20世紀最後幾年,在近代中國史研究正規化中,出現了由現代化向後現代正規化的轉移,又一次使研究民族主義步趨時尚,採用了這一分析模式。在這種研究正規化的汰舊換新的遊戲中,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研究所關注的問題,也由早期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往「民族國家建構與認同」移動。如果反思這樣的「正規化變革」的動因,我們很難在其中找到「民族主義」研究的內在證據、變革的動因,最終總是存在於思想史,以及作為思想史研究框架的近代中國史的解釋中。這種研究正規化的「騰籠換鳥」遊戲,為「民族主義」研究的學理化帶來諸多困境,也一再引發學界的反思──民族主義,或者思想史研究是否擁有自身的解釋架構? 沒有自身解釋架構的學術研究如何可行?如果要建立一個自足的解釋框架,這一框架的建構應該在什麼層面上展開?顯然地,這些問題與其說是針對「民族主義」這一具體問題,不如說是針對思想史的整體研究狀況更為妥當。
也就是說,我們關注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思想史研究?
對於這一系列的思想史問題,學界的討論已經初露端倪。本文不準備做純概念的分析,只針對本論著所關注的論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現狀,做接近經驗式的觀察。
(下面的討論不準備做系統的學術史分析──在一個學術出版氾濫的時代,學術史分析在整體上已經不可能,而且也沒有必要。與其將有限的精力耗費在魚龍混雜的各種文字中,不如只關注問題的重心。因此,本文的展開並不迴避因個人的選擇所造成的偏頗與遮蔽等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