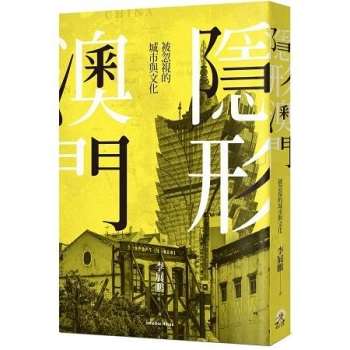台灣人如何閱讀澳門?
澳門的問題不只是澳門的問題,而是有跨地域價值。那麼,對於今天的台灣人來說,「了解澳門」的意義是什麼?
台灣人看澳門歷史,其實十分有趣。以往談兩岸淵源,我們的討論常常是「土向」的,多強調兩者共有的中華文化土壤,同文同種。然而,澳門跟台灣的聯繫也可以是「水向」的:數百年前,台南跟澳門同樣是最早跟大量歐洲人接觸的華人城市。
在十六世紀,荷蘭人對中國南門戶虎視眈眈,進攻澳門,與葡國人開戰。結果,荷軍敗陣,把陣地轉到台南。如果葡國人戰敗,澳門與台灣的歷史都會隨之改寫。原來,台灣跟澳門共享了一段世界歷史——那是早期歐洲航海事業對亞洲的衝擊。因此,兩地的文化都有外向的特質。了解澳門,也許可以令我們更了解台灣。
台南與澳門其實是兩張歷史悠久的羊皮紙重寫本(Palimpsest)。古人用羊皮紙作紀錄,並會重複使用,每隔一段時間,他們會把字擦掉,然後寫上新的字。但是,由於舊有的字難以完全抹去,紙上會有顏色深淺不一的新舊文字並存。就正如一個地方的文化在不同年代被不同的人創造改寫,最後變成複雜的體系,仿如一張不斷被塗抹與書寫的羊皮紙。
台南的赤崁樓就累積了不同時代的痕跡。荷蘭人數百年前建的城堡,遺址仍有殘留;清代在其上建的書院與廟堂,至今屹立著;日治時代,赤崁樓又再被改建。安平古堡也是異曲同工,它是十七世紀荷蘭人所建的堡壘,鄭成功驅逐荷人後繼續用作城堡,後來日本人則把它改建成海關宿舍。這些古蹟正是台灣的縮影:不同時代的不同政權與文化,形塑了這個人種與文化都多元的小島。
澳門又如何?在十六世紀中葉葡國人進駐之前,澳門是小漁村。之後,葡國人定居澳門,跟明清兩朝的官員和平共處達三百年之久。葡國人帶來的不只是歐洲文化,還有他們在航海過程中從馬來西亞及印度等地學來的東西。這種文化跟中國的嶺南文化碰撞,之後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移民亦把不同文化帶到澳門。澳門文化相當混雜,是另一張羊皮紙。
台南與澳門的案例,都為近年流行的本土主義提供了有力說明。所謂的「本土」往往是一種由眾多外來事物構成的混合體。越古老的東西,有時不是越純正,而是越不純;歷史越久,就越可能摻雜了不同文化。身為澳門人,當我看到台南的城市年輪,我亦首次發現了澳門跟台灣的一種很少談論的聯繫。
除了歷史文化,今天的澳門亦為台灣提供某種參照:就是發展賭博旅遊業究竟是怎麼回事。過去幾年,澎湖兩次公投反對開賭場,金門的反賭方亦在公投大獲全勝,但二○一二年馬祖的博奕公投過關。雖然最重要的《離島觀光賭場管理條例》未有下文,但未來台灣仍有可能開賭場。而就算不開賭場,大力發展旅遊業已是台灣的不二方向。
旅遊業掛著一張歡樂的臉,被稱為是零污染的無煙工業,但它是否如此潔白無瑕?當一個地方大力發展旅遊業,重要建設都是為了遊客,大量人口為旅客服務,這會帶來什麼畸形發展?近年在台灣已有問題漸次浮現,包括旅遊熱點人滿為患,造成環境污染,不良經營手法橫行,以及刻意建設與當地格格不入的人工景點等。
在西方,早有大量著作及研究揭示旅遊業不光彩的一面,而鄰近台灣的澳門正正就在過去十年發展驚人的賭博旅遊業而致富,如今的人均GDP已是亞洲第一,但卻惹得澳門人怨聲載道,抱怨生活品質下降,社會風氣敗壞,城市景觀被破壞,交通系統不勝負荷。澳門走過的軌跡,值得台灣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