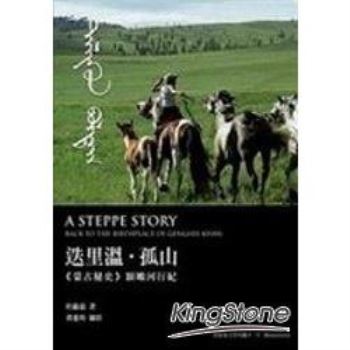第二章 烏蘭巴托
時勢不永駐;
草地不長青。
—蒙古古諺
「下次」,說來有趣,已經到了下一個世紀。二零零四年八月,距離法國西北列車的冬之旅,有五年多了;距離上一次我們走出烏蘭巴托火車站,則是整整六年又一個月。
六年時間,可以造就許多事物,足夠讓一個皺巴巴還沒睜眼的小嬰兒,長成活蹦亂跳的小學一年級新生。從一九九八到二零零四的六年裏,蒙古連續兩年雪災,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遭到轟炸與種族戰爭,千年前玄奘曾目睹的阿富汗巴米安大佛,被塔里班軍隊蓄意炸毀了,紐約發生九一一事件,美國入侵伊拉克,SARS造成群眾恐懼、也讓我們將這次的蒙古行延後了一年。或者,從這些例子看來,也許該說六年時間可以「毀滅」許多事物才對。(1)
幸好,以我們幾個孤家寡人的小市民立場來說,生活沒有類似生養孩子或是轟炸槍擊的戲劇性變化:惠玲辭掉一天工作十八小時的廠長職務,壯烈揮別待了十二年的製造業;我按照一九九八年旅行前的計畫,去美國唸完書又回來,其間並與她合作完成<地圖上的藍眼睛>,之後兩人又合作經營一份小小的事業;上次在蒙古結識的朋友達娜蘇榮,也已經大學畢業、到中國留了學,又回到母校蒙古國立大學任教了。
這一次進蒙古,依然搭乘西伯利亞鐵路蒙古支線,從北京到烏蘭巴托;不過旅伴的組成及其行為,與上次不同了。當然,惠玲還在,她還帶著那機齡十年以上的手動相機,以及長長短短的幾個鏡頭、數十捲正片膠卷。至於那位新成員,也就是我的妹妹,一面站在廊上與我低聲討論窗外的塞北風景,一面忙著使用手掌大小的新型數位相機,其間還不忘給正在上班的同事傳送令人羨妒的手機簡訊,炫耀自己昨天剛在北京吃了新疆菜,今天可就在西伯利亞鐵路上,遠眺八達嶺長城,剛過了青龍橋車站,現在豪氣干雲地開往蒙古高原啦。
我發現,這幾年的時光也反映在其他一些事實上頭。比如,儘管一年半前才來過一次,我卻愈來愈不認得北京新起的龐大建築、拆掉的舊街區。在火車站等著通過檢票口的時候,看看乘客的裝扮與行李,就可以知道,這列終點站莫斯科的第二十三號國際列車上,已經完全沒有那些氣勢驚人的蒙古單幫客了;這表示中國與蒙古之間已經建立起穩固的正常貿易,蒙古的市場供應充足,不再需要這些人。沿路上幾班反向的列車,都滿載運往中國的原木,這一點也可以做為佐證。
由於已經過了七月的國家那達慕,車上的觀光客比例降低。我偶然發現,佔了這個車廂大部分的蒙古乘客,都是同一團成員。隔壁包廂的一位年輕蒙古小姐,梳著馬尾,穿著牛仔褲與T恤,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她告訴我,這一團七十幾位全是蒙古國的漢語教師,接受濟南大學邀請,趁著暑假前往中國研習,現在結束歸國。多麼有趣的對比!少了從中國進口低廉民生物資的單幫客,卻增加了向蒙古輸入語言能力及競爭力的教師。
當天午夜,列車停靠中蒙邊界的二連浩特。火車站外,幾年前曾令我們瞠目結舌的夜半市集,原本是因列車上的蒙古單幫客而生,可想而知,現在果真如唐人傳奇裏不似人間的可疑聚會,永遠消失在沙漠裏了。
從這一切看來,也許不該令我驚訝的是,六年的時光,也足夠這個日益繁盛的邊城,豎立起一座龐大的霓虹燈標誌。數里外就能望見的燈光,火紅燭天,讓我再也看不見冷冽的沙漠夜空裏,數如繁沙的星星。
說來荒謬卻又合理,由於這些觀察與事實,我們從進入蒙古國境以來,心中某種只能形容為「近鄉情怯」的感受愈來愈明顯。在戈壁邊緣的日出之後,惠玲與我懷著矛盾的提心吊膽與萬分欣喜,始終不離窗邊。轆轆前進的火車車窗舒展開一幅無盡畫卷,我們一路重覽記憶中的蒙古,清朗藍天,綠草羊群,間或幾頭悠哉的駱駝,還有遠遠的一兩座蒙古氈房。
當列車減低速度,開始穿行在緩丘之間,我們不禁興奮相告,那四座聖山之間的城市,烏蘭巴托,快到了。列車轉過彎,車上的人們可以從丘陵之間望見遠方蒼綠的山脈,山懷裏就是烏蘭巴托。列車再轉過一個彎,第二眼卻讓我們驚訝,因為,跟六年前比起來,市郊邊緣的民居區明顯擴張,遠遠望來好似遍野螞蟻大軍,或是無數灰色大頭針,蠶食了綠色的山坡,不斷往上蔓延。
我們驚訝甚至憂心,並不是因為烏蘭巴托房屋與居民增加。這六年來雖然沒回過蒙古,但是我們一直注意各種關於蒙古的新聞,所以明白,這些由拼湊的小屋與半舊氈房組成的新區域,許多並不屬於都市開發計畫,因此往往沒有水電,沒有公共建設,景況極其可憐;這幾年烏蘭巴托的街頭遊童愈來愈多,與這一事實也有關。烏蘭巴托市的老居民各安其位,不需要住到這種地方來,來的都是鄉間牧民;好一點的,是年輕人嚮往都市,離鄉背井,最可憐的,是這幾年因雪災及自然失衡而破產的牧民,無以為繼,只好舉家遷移,在城郊邊緣再添一個灰色的針頭。
失去了牲口的草原人家,就算不得牧民了;從更深遠的意義上來說,也許連他們的「蒙古人」這個身份也打了折扣。
不過,重返蒙古的興奮激動之情,蓋過了心中對於現實問題的憂慮。列車緩緩穿過城南的倉庫與民居,我們三人已經大小背包披掛停當,坐在舖位上就等著到站停車了。龐大的行李讓我們總是禮讓別人先下車,當我們還在走廊上掙扎的時候,看來依然如學生的達娜,還是跟六年前一樣機伶,隔著車窗就找到我們了。
那一刻,我不由自主笑開了嘴,停下來朝著玻璃窗外揮手,想想卻又滑稽,人都到了,還耽擱什麼呢?下車吧!準備好呼吸六年來的第一口蒙古空氣——當然列車裏也是蒙古空氣,不過感覺不同——準備好在這一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踏下渺小的、歸來的第一步吧。
懷著這股豪氣出了站、上了吉普,十分鐘後,我們還被眾車堵在原地,上不了馬路。
烏蘭巴托的路上,再也沒有蘇聯車了,全是日本、韓國、美國、德國、瑞典、義大利、法國、英國的各式休旅車、小汽車、豪華轎車。簡言之,我們到了蒙古的第一步——「離開火車站」,就被八國聯軍圍攻。無論方向盤在左在右,絲毫不影響這些剽悍的駕駛們奮勇爭先。
不得不承認,對於蒙古城市生活的變化,我感到一點輕微的文化震盪,但是更強烈的感受是新奇、有趣。上一次,蒙古是行程第一站,考慮其後旅途的花費與載重,我們捨不得買紀念品,何況可買的也不多。可這一次,我們發現自己在烏蘭巴托居然能夠逛街了——或者該這麼說才精確:居然「有街可逛」了!而且連逛三天還停不下來!
到處剛開幕不久的超級市場、貨色更加多樣齊全的商店、連鎖唱片行(新概念!),以及滿街價廉物美的蒙古與國際餐飲(也是新概念!),即使對烏蘭巴托市民來說,也比從前方便許多。某天,我們與達娜的友人站在一排臨街的時髦小餐館前,研究著該進哪家吃晚飯?還是該去兩條街外吃某某烏克蘭菜?或是去那家法國餐廳呢?順便說一句,老闆可是拿破崙的同鄉,來自科西嘉島!想起六年前我們要請達娜與父母吃飯,整個烏蘭巴托市卻只有兩家餐廳可供選擇,我實在有股仰天大笑的衝動。
然而,變化中依然有不變。從前是零售主力的小售貨亭依然存在,惠玲還是照樣藉著各種機會到旅館旁的小售貨亭買東西,因為這種五臟俱全的超迷你麻雀始終令她著迷。最受歡迎的連鎖餐館,賣的是蒙古傳統主食各式餃子。上次烏蘭巴托唯一一家超市只有進口貨,而現在大小超市裏卻買得到傳統的酸奶條零嘴、奶油炸餑餑,甚至馬奶也做成了奶粉。
不過最令我們欣賞的新商品,還得算是蒙古奶茶隨身包。從此即使離開了蒙古,只要帶上幾包,也能回味在蒙古氈房裏手捧一碗氤氳熱茶的滋味。感激之餘,惠玲甚至為大看板上微笑舉杯的老K商標,照相一幀留念,我說也許她該在照片上題字:「惠我良多」!
在烏蘭巴托過了三天都市觀光客生活,由於妹妹休假有限,無法跟我繼續前往東部的額嫩河流域,所以達娜帶大家到親戚在南郊的氈房去住兩天,稍微領略一下蒙古牧民生活。
氈房雖在市郊,卻非上述的違建區,這一帶南臨土拉河,適合發展郊區牧業,零星分佈的人家,有的立起了嶄新的氈房,有的蓋起了俄羅斯式的寬敞木屋,顯得頗為興旺。
達娜的這位姻舅,自己在市區裏忙和別的事業,應該很成功,所以供得起大兒子出國留學,小女兒就讀俄羅斯人在烏蘭巴托辦的私校。他雇用了一家人在這塊地上照顧十幾頭奶牛,這兒是投資之一,也是週末的別墅。木板圍牆裏,一座簇新潔白的氈房,裏面是朱紅油飾的全套傳統家具,一套極其講究的蒙古鞍具按規矩放在左手邊上。
我看著惠玲爬進牛欄,蹭在龐大的眾位牛媽之間搶拍照片。這一次重回蒙古,惠玲居然習慣了蒙古羊肉、習慣了不吃蔬果,但是對於隨時可能鞋踩獸糞一事,還是不太自若。妹妹則徒勞地練習擠牛奶,雖然她從小就能很快學會溜冰滑雪開手排車跳標準舞乃至三四種外語,兩小時前又學會了騎馬牧牛,無奈擠牛奶這件事顯然有更大的學問,我只慶幸那可憐的牛媽媽好耐性,沒踹她一蹄。
從大夥兒開懷大笑的情景看來,我們這些作客人的無疑給主人帶來很多歡樂。我想,這不知是否算得蒙古的新式牧民生活:人住在都市公寓裏,開一輛日本車,出錢在鄉間養牛;別墅是蒙古包,跟祖祖輩輩一樣騎馬。
當夜,是六年來第一次在氈房裏過夜。早上醒來第一眼,我看見的是氈房屋頂正中,喜慶朱紅的木圈頂。正圓形的頂圈,彷如蒙古長調所贊頌的、日復一日溫暖著大地的太陽,放射出一輪上百根同樣是朱紅色的頂杆,撐住潔白的毛氈帳。天色尚早,天窗中露出的一小塊半圓形天空,還未顯現亙古的藍色;但見房頂正中,按照傳統,繫著一條經過誦經持咒的天藍色哈達,安詳地垂下。
我笑了,滿意地呼一口氣。蒙古,我回來了。
時勢不永駐;
草地不長青。
—蒙古古諺
「下次」,說來有趣,已經到了下一個世紀。二零零四年八月,距離法國西北列車的冬之旅,有五年多了;距離上一次我們走出烏蘭巴托火車站,則是整整六年又一個月。
六年時間,可以造就許多事物,足夠讓一個皺巴巴還沒睜眼的小嬰兒,長成活蹦亂跳的小學一年級新生。從一九九八到二零零四的六年裏,蒙古連續兩年雪災,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遭到轟炸與種族戰爭,千年前玄奘曾目睹的阿富汗巴米安大佛,被塔里班軍隊蓄意炸毀了,紐約發生九一一事件,美國入侵伊拉克,SARS造成群眾恐懼、也讓我們將這次的蒙古行延後了一年。或者,從這些例子看來,也許該說六年時間可以「毀滅」許多事物才對。(1)
幸好,以我們幾個孤家寡人的小市民立場來說,生活沒有類似生養孩子或是轟炸槍擊的戲劇性變化:惠玲辭掉一天工作十八小時的廠長職務,壯烈揮別待了十二年的製造業;我按照一九九八年旅行前的計畫,去美國唸完書又回來,其間並與她合作完成<地圖上的藍眼睛>,之後兩人又合作經營一份小小的事業;上次在蒙古結識的朋友達娜蘇榮,也已經大學畢業、到中國留了學,又回到母校蒙古國立大學任教了。
這一次進蒙古,依然搭乘西伯利亞鐵路蒙古支線,從北京到烏蘭巴托;不過旅伴的組成及其行為,與上次不同了。當然,惠玲還在,她還帶著那機齡十年以上的手動相機,以及長長短短的幾個鏡頭、數十捲正片膠卷。至於那位新成員,也就是我的妹妹,一面站在廊上與我低聲討論窗外的塞北風景,一面忙著使用手掌大小的新型數位相機,其間還不忘給正在上班的同事傳送令人羨妒的手機簡訊,炫耀自己昨天剛在北京吃了新疆菜,今天可就在西伯利亞鐵路上,遠眺八達嶺長城,剛過了青龍橋車站,現在豪氣干雲地開往蒙古高原啦。
我發現,這幾年的時光也反映在其他一些事實上頭。比如,儘管一年半前才來過一次,我卻愈來愈不認得北京新起的龐大建築、拆掉的舊街區。在火車站等著通過檢票口的時候,看看乘客的裝扮與行李,就可以知道,這列終點站莫斯科的第二十三號國際列車上,已經完全沒有那些氣勢驚人的蒙古單幫客了;這表示中國與蒙古之間已經建立起穩固的正常貿易,蒙古的市場供應充足,不再需要這些人。沿路上幾班反向的列車,都滿載運往中國的原木,這一點也可以做為佐證。
由於已經過了七月的國家那達慕,車上的觀光客比例降低。我偶然發現,佔了這個車廂大部分的蒙古乘客,都是同一團成員。隔壁包廂的一位年輕蒙古小姐,梳著馬尾,穿著牛仔褲與T恤,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她告訴我,這一團七十幾位全是蒙古國的漢語教師,接受濟南大學邀請,趁著暑假前往中國研習,現在結束歸國。多麼有趣的對比!少了從中國進口低廉民生物資的單幫客,卻增加了向蒙古輸入語言能力及競爭力的教師。
當天午夜,列車停靠中蒙邊界的二連浩特。火車站外,幾年前曾令我們瞠目結舌的夜半市集,原本是因列車上的蒙古單幫客而生,可想而知,現在果真如唐人傳奇裏不似人間的可疑聚會,永遠消失在沙漠裏了。
從這一切看來,也許不該令我驚訝的是,六年的時光,也足夠這個日益繁盛的邊城,豎立起一座龐大的霓虹燈標誌。數里外就能望見的燈光,火紅燭天,讓我再也看不見冷冽的沙漠夜空裏,數如繁沙的星星。
說來荒謬卻又合理,由於這些觀察與事實,我們從進入蒙古國境以來,心中某種只能形容為「近鄉情怯」的感受愈來愈明顯。在戈壁邊緣的日出之後,惠玲與我懷著矛盾的提心吊膽與萬分欣喜,始終不離窗邊。轆轆前進的火車車窗舒展開一幅無盡畫卷,我們一路重覽記憶中的蒙古,清朗藍天,綠草羊群,間或幾頭悠哉的駱駝,還有遠遠的一兩座蒙古氈房。
當列車減低速度,開始穿行在緩丘之間,我們不禁興奮相告,那四座聖山之間的城市,烏蘭巴托,快到了。列車轉過彎,車上的人們可以從丘陵之間望見遠方蒼綠的山脈,山懷裏就是烏蘭巴托。列車再轉過一個彎,第二眼卻讓我們驚訝,因為,跟六年前比起來,市郊邊緣的民居區明顯擴張,遠遠望來好似遍野螞蟻大軍,或是無數灰色大頭針,蠶食了綠色的山坡,不斷往上蔓延。
我們驚訝甚至憂心,並不是因為烏蘭巴托房屋與居民增加。這六年來雖然沒回過蒙古,但是我們一直注意各種關於蒙古的新聞,所以明白,這些由拼湊的小屋與半舊氈房組成的新區域,許多並不屬於都市開發計畫,因此往往沒有水電,沒有公共建設,景況極其可憐;這幾年烏蘭巴托的街頭遊童愈來愈多,與這一事實也有關。烏蘭巴托市的老居民各安其位,不需要住到這種地方來,來的都是鄉間牧民;好一點的,是年輕人嚮往都市,離鄉背井,最可憐的,是這幾年因雪災及自然失衡而破產的牧民,無以為繼,只好舉家遷移,在城郊邊緣再添一個灰色的針頭。
失去了牲口的草原人家,就算不得牧民了;從更深遠的意義上來說,也許連他們的「蒙古人」這個身份也打了折扣。
不過,重返蒙古的興奮激動之情,蓋過了心中對於現實問題的憂慮。列車緩緩穿過城南的倉庫與民居,我們三人已經大小背包披掛停當,坐在舖位上就等著到站停車了。龐大的行李讓我們總是禮讓別人先下車,當我們還在走廊上掙扎的時候,看來依然如學生的達娜,還是跟六年前一樣機伶,隔著車窗就找到我們了。
那一刻,我不由自主笑開了嘴,停下來朝著玻璃窗外揮手,想想卻又滑稽,人都到了,還耽擱什麼呢?下車吧!準備好呼吸六年來的第一口蒙古空氣——當然列車裏也是蒙古空氣,不過感覺不同——準備好在這一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踏下渺小的、歸來的第一步吧。
懷著這股豪氣出了站、上了吉普,十分鐘後,我們還被眾車堵在原地,上不了馬路。
烏蘭巴托的路上,再也沒有蘇聯車了,全是日本、韓國、美國、德國、瑞典、義大利、法國、英國的各式休旅車、小汽車、豪華轎車。簡言之,我們到了蒙古的第一步——「離開火車站」,就被八國聯軍圍攻。無論方向盤在左在右,絲毫不影響這些剽悍的駕駛們奮勇爭先。
不得不承認,對於蒙古城市生活的變化,我感到一點輕微的文化震盪,但是更強烈的感受是新奇、有趣。上一次,蒙古是行程第一站,考慮其後旅途的花費與載重,我們捨不得買紀念品,何況可買的也不多。可這一次,我們發現自己在烏蘭巴托居然能夠逛街了——或者該這麼說才精確:居然「有街可逛」了!而且連逛三天還停不下來!
到處剛開幕不久的超級市場、貨色更加多樣齊全的商店、連鎖唱片行(新概念!),以及滿街價廉物美的蒙古與國際餐飲(也是新概念!),即使對烏蘭巴托市民來說,也比從前方便許多。某天,我們與達娜的友人站在一排臨街的時髦小餐館前,研究著該進哪家吃晚飯?還是該去兩條街外吃某某烏克蘭菜?或是去那家法國餐廳呢?順便說一句,老闆可是拿破崙的同鄉,來自科西嘉島!想起六年前我們要請達娜與父母吃飯,整個烏蘭巴托市卻只有兩家餐廳可供選擇,我實在有股仰天大笑的衝動。
然而,變化中依然有不變。從前是零售主力的小售貨亭依然存在,惠玲還是照樣藉著各種機會到旅館旁的小售貨亭買東西,因為這種五臟俱全的超迷你麻雀始終令她著迷。最受歡迎的連鎖餐館,賣的是蒙古傳統主食各式餃子。上次烏蘭巴托唯一一家超市只有進口貨,而現在大小超市裏卻買得到傳統的酸奶條零嘴、奶油炸餑餑,甚至馬奶也做成了奶粉。
不過最令我們欣賞的新商品,還得算是蒙古奶茶隨身包。從此即使離開了蒙古,只要帶上幾包,也能回味在蒙古氈房裏手捧一碗氤氳熱茶的滋味。感激之餘,惠玲甚至為大看板上微笑舉杯的老K商標,照相一幀留念,我說也許她該在照片上題字:「惠我良多」!
在烏蘭巴托過了三天都市觀光客生活,由於妹妹休假有限,無法跟我繼續前往東部的額嫩河流域,所以達娜帶大家到親戚在南郊的氈房去住兩天,稍微領略一下蒙古牧民生活。
氈房雖在市郊,卻非上述的違建區,這一帶南臨土拉河,適合發展郊區牧業,零星分佈的人家,有的立起了嶄新的氈房,有的蓋起了俄羅斯式的寬敞木屋,顯得頗為興旺。
達娜的這位姻舅,自己在市區裏忙和別的事業,應該很成功,所以供得起大兒子出國留學,小女兒就讀俄羅斯人在烏蘭巴托辦的私校。他雇用了一家人在這塊地上照顧十幾頭奶牛,這兒是投資之一,也是週末的別墅。木板圍牆裏,一座簇新潔白的氈房,裏面是朱紅油飾的全套傳統家具,一套極其講究的蒙古鞍具按規矩放在左手邊上。
我看著惠玲爬進牛欄,蹭在龐大的眾位牛媽之間搶拍照片。這一次重回蒙古,惠玲居然習慣了蒙古羊肉、習慣了不吃蔬果,但是對於隨時可能鞋踩獸糞一事,還是不太自若。妹妹則徒勞地練習擠牛奶,雖然她從小就能很快學會溜冰滑雪開手排車跳標準舞乃至三四種外語,兩小時前又學會了騎馬牧牛,無奈擠牛奶這件事顯然有更大的學問,我只慶幸那可憐的牛媽媽好耐性,沒踹她一蹄。
從大夥兒開懷大笑的情景看來,我們這些作客人的無疑給主人帶來很多歡樂。我想,這不知是否算得蒙古的新式牧民生活:人住在都市公寓裏,開一輛日本車,出錢在鄉間養牛;別墅是蒙古包,跟祖祖輩輩一樣騎馬。
當夜,是六年來第一次在氈房裏過夜。早上醒來第一眼,我看見的是氈房屋頂正中,喜慶朱紅的木圈頂。正圓形的頂圈,彷如蒙古長調所贊頌的、日復一日溫暖著大地的太陽,放射出一輪上百根同樣是朱紅色的頂杆,撐住潔白的毛氈帳。天色尚早,天窗中露出的一小塊半圓形天空,還未顯現亙古的藍色;但見房頂正中,按照傳統,繫著一條經過誦經持咒的天藍色哈達,安詳地垂下。
我笑了,滿意地呼一口氣。蒙古,我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