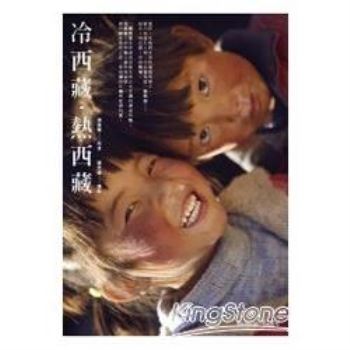我在桑耶, 度過了一個零下十五度的農曆新年。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在沒有暖氣支援下, 度過的一個零下十五度的夜。
我們抵達桑耶,天色已全黑了。
桑耶說不上是一個鎮,只是在公路旁邊的數十間二、三層樓高的藏式平房而已。
以前來桑耶的遊人,就只有桑耶寺旁邊簡陋的招待所可以投宿。我們住的旅館是新建的,只開業了兩年。旅館的設計,和我在洛杉磯拍廣告時住過的汽車酒店,根本上是一樣的。兩層樓高的樓房,像四面牆,圍著中間的停車空地。一下車,便可以逕自回房間。旅館簡單乾淨,沒有多餘的裝飾,燈光微黃,服務員很友善。
我經過二樓昏黃寬闊的走廊,四方形大窗前,背著我的少女,回頭向我微笑。那微笑的背後,是桑耶寺黝黑的輪廓。在少女的微笑和寺院的黝黑中間,是綻放的煙花,很小,很近。
我差點忘記了這是漢族的農曆年三十晚。不過,那藏地零星的小煙花,沒有增添多少節日的熱鬧,反而讓古寺前的人間歡樂顯得更加剎那。
在陝西人的飯館,老闆特地煮了餃子,和我們過年,那是北方的風俗,讓我感受到人間溫暖。不過回到房間,我卻要面對人間真實的冷──飯店沒有暖氣供應。
我穿著羽絨夾克、羊毛褲、羊毛襪,再蓋上兩張重重的棉被,嘗試著睡覺。不過,只一會兒,我便感到腦袋有一種從未經歷過的麻痺,伸手摸一摸頭髮,怎麼像冰箱中年初一吃剩的髮菜蠔子裡的髮菜一樣冰冷。噢,我多大意,忘了戴上帽子睡覺。在零下的空氣中,體溫會從身體任何外露的地方溜走,後果可是很麻煩的。不過,戴上羊毛帽,寒風還是從棉被邊緣和我肩頸的縫隙中鑽進來,像刀子一樣。
我翻來覆去的,在零下十五度的寒風中,和小黑斷續的咳嗽聲中,我竟然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人的身體的適應力,真的很奇妙。
我在造夢嗎?
從飯店徒步到桑耶寺,天還未全亮。在寺旁的招待所,喝著酥油甜茶,等待寺院開門。揚聲器播放著誦經的歌聲,慢慢的,歌聲混和了艾草燃燒的香味,我知道,是時候可以進去寺院了。
噢,桑耶寺,我曾經作過一個夢,一個人蹲在桑耶寺頂,金色的法輪和鹿兒的後面,天上的銀河閃耀著永恆的光。
現在,桑耶寺就在我的前面。那一千多年前的crossover建築,第一層是藏式,第二層中國式,第二層印度式,象徵著三位建築者─藏王松贊干布、漢人皇后文成公主、印度僧人寂護大師建寺的虔誠。
寺院的入口,夾道整齊的是兩排討錢的貧窮婦女和孩子。我們一邊布施,一邊進寺。
整個西藏,桑耶寺是我最魂牽夢繫的地方。不光是因為它的歷史,還有寂護。
我對寂護大師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我的佛學碩士論文就是研究寂護的。他是印度佛教後期的邏輯因明大師。他的邏輯是溫文的,甚至可以說是漂亮的。可惜的是,他的經論沒有同期的古漢譯本。
一進桑耶寺大殿,第一眼看見的,正正是寂護的雕像。很生動地,那intellectual look的表情,淡金色的學者風範。我很自! 然的做了一個五體投地的大禮拜,以示尊重。
他的旁邊,是蓮花生大師的金像。就是他們兩人把佛教帶進西藏。寂護大師是顯學,蓮花生大師是密宗。
可能是由於天還未全亮,寺內的光線很暗。不過,僧侶已開始誦經了。幾十個僧人,坐在一排一排整齊的沈色古木前,木上面放著長方形昏黃的經書,正搖擺著身體在誦經。在寒冷中,他們穿的不多,只是披著一襲藏紅色的僧袍,裡面還可以看見紅色黃邊夾衣那外露的整條手臂。究竟是誦經的節奏,還只是寒冷的哆嗦,令他們旋轉地搖動
身子呢?
寺院內的光線,主要來自兩個源頭:酥油供燈的燭光和斜照的淡黃晨光。不過,晨曦的淡光斜照,似乎更具有宗教性。
寺院七、八米樓高的佛殿,掛滿了五彩金黃的寶幢,從二樓斜照進來的昏黃晨光,穿過空氣中飄浮的微塵,似乎每顆微塵都反射著光蘊,融和著誦經的咒音,掀動我深層的某種神聖的悸動。
在土耳其的紫色蘇菲亞教堂、義大利的聖彼得大教堂,你都可以感受同樣的悸動,無論你是哪一個宗教的信徒。彷彿人類的深處,就是有某種宗教性的弦線,等待著一次靈性的牽動。
桑耶寺的正堂,端坐著四、五米高的佛陀! 釋迦牟尼金像,左邊是四大菩薩,右邊是四大天王。人物是一樣的,但造型就跟漢地的不一樣。佛教重視的是「覺」,佛像只是一個符號,是世俗的一個相、一個建立,所以佛像的造型會融合不同文化和時代的特色,像是不同的翻譯文本。
希臘的佛、印度的佛、中國的佛、男身的、女身的、夜叉的……,林林總總;印度傳來的不二法門、中國禪宗說的無相而相、西藏說的大圓滿大手印……;在桑耶寺,我感受到的,是一種不能言說的悸動,慢慢地忘我起來。
西藏狗的生死書
佛教把所有的生命體稱為「有情」。有情基於過去的業力,分別居於六道。上三道是天人、阿修羅和人類;下三道是畜生、餓鬼和地獄。西藏人認為,在畜生道中,最接近人道的是狗,所以西藏人對狗的態度是特別親切的。
在這次西藏的旅程中,我就認識了一隻擁有人的眼神的狗。牠長了一身全白的長毛,一點都不骯髒,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尖尖的鼻子,眼神是矇矓的,像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似的。牠一見我們就像老朋友一樣,非常的親切。
我們是在路邊的一個小鄉村遇上牠的。當小黑在拍照的時! 候,牠就用後腿蹬直,站起了身子,右手靠著小黑,左手在空中揮動,像指導著小黑,哪一個是最好的拍攝角度一樣。我們走的時候,牠傻勁的要鑽進我們的吉普車。開車後,還在後面跟著跑。車行了幾百米,發生了故障,停下來修。牠卻從老遠跑來,把頭柔柔的伏在我的臂彎中,在那一刻,我覺得已經和牠結了緣,可能在下一生,牠會是我的鄰居、同學,或者是同事,會說一些爛笑話,我買彩票輸了,牠還會安慰我呢!
一會兒,牠抬頭,望向很遠的地方,在無雲的藍天下,清風吹拂著白色的長毛,投出了一個形而上的眼神,令人動容,不知是否在想一些生與死的問題。
我不會忘記,牠在我們車後一直追趕的樣子。牠的名字叫小白。
不過,隔一天的清晨,事情卻往另一個方向走。
天還未全亮,兩隻狗突然衝出了馬路,我們的吉普車閃避不來,輾過了一隻。我還記得車子輾過時,那一個令人心裡絞痛的跳動。我沒有回頭看。司機沒奈何的說:「死了。」然後,我看見扎西‧星期五不停的轉著佛珠,不停的念渡亡咒。然後,他打了幾個電話。
幾天之後,談到輾過的狗,他說他心裡還是不舒服。雖然我們不是有意的,不過,他已經打了電話給他! 的姊姊,找一個僧人為狗兒超渡,也叫了每天繞著大昭寺步行八公里的媽媽,為狗兒轉經筒,念觀音六字大悲咒。
西藏人對狗兒生死的尊重,讓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對的,眾生都有情,都是平等的,一條生命就是一條生命。我們對每一個生命,又是否有足夠的尊重呢?
我在日喀則市的一間網咖內,
坐在我旁邊的藏族少年,正抽著菸,看港片《古惑仔》。
他非常溫文,還教我如何上網,顛覆了叛逆青少年的刻板印象。
西藏青少年是不是不反叛的呢?我不肯定……
離開網咖,我進了一間理髮店洗頭。
札西‧星期五老是說:「最好不要洗澡、洗頭,很容易會感冒。受不了的話,去理髮店吧。」
這是一間以玻璃和銀色金屬裝修的理髮店,挺現代感的,牆上還貼了韓星的海報。
在暖氣中洗頭,很舒服,只需二十元罷了。
我在享受著現代文明。
日喀則是西藏第二大城市,二十多萬人,是黃教格魯派的發源地。這幾百年,格魯派一直是執政教派,而黃教的大寺、紮什倫布寺就是在日喀則。西藏似乎就只有在拉薩市和日喀則市(好像還有林芝市)可以享受一點現代化的文明。其他的地方,都是樸素得近乎原始的。
抵達日喀則前一晚,落腳在定日縣唯一的小旅館。晚上沒有暖氣,甚至沒有電力。
旅館的小餐室,煲著一大壺水,上升的蒸氣集中在壺上的一條長鐵管中,不停流動。我抱著一隻可能因為看烈日太久而眼神矇矓的黑貓,滿足於生命之間渴望撫貼的皮膚下血液流動的溫暖。
從黃昏,到深夜,在這十八世紀古老的蒸氣暖爐旁,透著遙遠的溫柔。
聖湖的冰河時期
我們是幸運的。
西藏的聖湖,叫羊卓雍錯,簡稱羊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好幾年才結一次冰。恰好,我們參觀羊湖的時候,就遇上了羊湖結冰,可以在湖上漫步。
在山上看聖湖,和在湖面上漫步,是截然的兩種感覺。一個是莊嚴壯觀,另一個是如夢如幻。
太陽猛烈的照耀著,而我們卻漫步在冰的世界裡。這是一個不冷的零下世界,冷裡透著溫暖,暖中又帶著清涼。很西藏式熱情的冷,是西藏人那種熱愛生命又沒有被生命之火燃燒的清涼。腳底下的冰塊,像把我們和世俗隔開,站立在一個神聖的境界中。不過,步行了幾步,就聽見不知從哪傳來像是冰裂的微聲,打斷了我那神聖的玄思,肉體好像又要下墜到什麼的地方了……
在羊湖邊,我們真的遇上了一個羊男。是一個趕著一大群羊的牧羊青年。他名叫旺堆,二十三歲,矮小的個子,長期曝曬的臉,灰紅色的,長出了深深的皺紋,像一個中年人。
我問他:「你有什麼夢想?」
他回答:「我喜歡織布。」
西藏人就是這樣。他們沒有不切實際的夢想,比如做一個投資銀行家呀、鋼琴家呀等等。他們的夢想,都是很生活的、很貼近的東西。
也許,生活的本質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也說不定。
也許,不是America dream那種自我膨脹的意識型態的顛倒也說不定。
不過,我們好像已經習慣了生活在西方文化的設定中,而忘掉了純粹。
不知該怎樣解釋,在冰河時期的聖湖邊,聽羊男說他的夢想:「我喜歡織布。」突然給我一種浪漫的感覺,是一種很遙遠、超越了時空、很純白的浪漫感覺。
我買了, 他親手做的香
離開了聖湖,吉普車一路下山,結冰的湖在車窗外慢慢褪去,然後我只看見沙漠。
吉普車一直開往沙漠的深處,灰色的山離我越來越遠,好像將會在遠處慢慢消失。突然面前出現了一個寺院──桑丁寺。
不知道是由於寺院每層樓底比一般的寺院高,還是由於它被孤立在沙漠中心的緣故,桑丁寺顯得格外的壯觀好看。
桑丁寺高高的大門前,有四、五個僧人,正操作著一部簡單的機器,像在製作什麼似的。我趨前去看看,原來他們在做藏香。桑丁寺的藏香是很有名的,分銷全國各地。
設在沙漠中心的藏香工廠,會不會違反了物流的邏輯?
算了吧,香港人!
我們攀上了寺頂,在金色的法輪前面,我看見廣闊的沙漠中出現了龍捲風。那真的是奇景。不過那龍捲風似乎很友善,幼幼的一條小龍,一、二十米高,在廣闊的沙漠自在的遊走,一點都不像電影常見的惡龍。其實,西藏沙漠最惡的是沙塵暴,一旦刮起,就算站在廟頂,也會什麼都看不見。
在寺院的二樓,我們認識了一個小僧人。他在做好像包裝的最後工序。不要想像成廣東工廠production line那種作業模式,他只是把檯面上零零星星的小三角椎形藏香入盒而已,還不時和身邊的僧友談笑。
他叫仁珠多傑,十八歲,來桑丁寺一年了。他說他不喜歡上學校,喜歡做僧人,便跟父母說要出家。他說他現在很開心。當然嘛,不用上學,做自已喜歡的事情,父母又不反對,怎會不開心?
臨走的時候,我跟他買了剛剛入盒的幾盒藏香,他自豪的說:「這是我親手做的!」
白居寺的紅
白居寺是江孜的代表性寺廟。很有風格,簡簡單單的,一間黑色的寺,一個白色的塔。許舜英見了,可能會說:「是川久保玲的黑。」
寺院的黑,其實是特大的布門。
暖和的陽光,悠閒的寺廟,藏式的黑布門隨風微微的飄動。兩個年輕的媽媽坐在廣場,自然的敞開胸脯在餵奶。我在寺院內買了一串觸感粗糙的大佛珠,跟在兩個轉經的老婆婆後面,在寺院的廣場來回。一個康巴的帥哥經過我,往轉經廊。
這是一個很快樂的上午。這快樂沒有宗教性,是屬於人間的。
太陽開始到正頂。我們三人登上白色的佛塔。這個佛塔有十萬個佛像,分佈在佛塔內像山洞般大小不同的佛龕中。我們到了塔頂,遇見了一個紅衣少女和她的小兒子。
「少婦」這詞對她來說,是不合適的。一方面,她很年輕,看上去只有二十歲。最重要的是,她有少女的氣質──清純、靦腆和詩意的神情。我們請她讓小黑拍一張照片。起先她不好意思的拒絕了,經過札西‧星期五的誠意哀求,才終於答應。
她手拖著她的兒子,站在塔頂一面白牆的前面。這時中午的陽光很烈,照在牆上反射著刺眼的白,與少女的紅色藏服和像曬傷了的紅色肌膚,強烈地反差著,卻又互相穿透著。噢,很和諧啊!
A picture says a thousand words.
這就是我想說的「冷的熱情」。西藏的「冷的熱情」。
一種熱愛生命卻沒有被生命之火炙燒的清涼的熱。是超越了冷和熱之後的和諧統一。是回歸到生和死之前,那周遍的生機和宏淵的愛。這愛,也是屬於人間的,卻又不只是人間。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在沒有暖氣支援下, 度過的一個零下十五度的夜。
我們抵達桑耶,天色已全黑了。
桑耶說不上是一個鎮,只是在公路旁邊的數十間二、三層樓高的藏式平房而已。
以前來桑耶的遊人,就只有桑耶寺旁邊簡陋的招待所可以投宿。我們住的旅館是新建的,只開業了兩年。旅館的設計,和我在洛杉磯拍廣告時住過的汽車酒店,根本上是一樣的。兩層樓高的樓房,像四面牆,圍著中間的停車空地。一下車,便可以逕自回房間。旅館簡單乾淨,沒有多餘的裝飾,燈光微黃,服務員很友善。
我經過二樓昏黃寬闊的走廊,四方形大窗前,背著我的少女,回頭向我微笑。那微笑的背後,是桑耶寺黝黑的輪廓。在少女的微笑和寺院的黝黑中間,是綻放的煙花,很小,很近。
我差點忘記了這是漢族的農曆年三十晚。不過,那藏地零星的小煙花,沒有增添多少節日的熱鬧,反而讓古寺前的人間歡樂顯得更加剎那。
在陝西人的飯館,老闆特地煮了餃子,和我們過年,那是北方的風俗,讓我感受到人間溫暖。不過回到房間,我卻要面對人間真實的冷──飯店沒有暖氣供應。
我穿著羽絨夾克、羊毛褲、羊毛襪,再蓋上兩張重重的棉被,嘗試著睡覺。不過,只一會兒,我便感到腦袋有一種從未經歷過的麻痺,伸手摸一摸頭髮,怎麼像冰箱中年初一吃剩的髮菜蠔子裡的髮菜一樣冰冷。噢,我多大意,忘了戴上帽子睡覺。在零下的空氣中,體溫會從身體任何外露的地方溜走,後果可是很麻煩的。不過,戴上羊毛帽,寒風還是從棉被邊緣和我肩頸的縫隙中鑽進來,像刀子一樣。
我翻來覆去的,在零下十五度的寒風中,和小黑斷續的咳嗽聲中,我竟然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人的身體的適應力,真的很奇妙。
我在造夢嗎?
從飯店徒步到桑耶寺,天還未全亮。在寺旁的招待所,喝著酥油甜茶,等待寺院開門。揚聲器播放著誦經的歌聲,慢慢的,歌聲混和了艾草燃燒的香味,我知道,是時候可以進去寺院了。
噢,桑耶寺,我曾經作過一個夢,一個人蹲在桑耶寺頂,金色的法輪和鹿兒的後面,天上的銀河閃耀著永恆的光。
現在,桑耶寺就在我的前面。那一千多年前的crossover建築,第一層是藏式,第二層中國式,第二層印度式,象徵著三位建築者─藏王松贊干布、漢人皇后文成公主、印度僧人寂護大師建寺的虔誠。
寺院的入口,夾道整齊的是兩排討錢的貧窮婦女和孩子。我們一邊布施,一邊進寺。
整個西藏,桑耶寺是我最魂牽夢繫的地方。不光是因為它的歷史,還有寂護。
我對寂護大師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我的佛學碩士論文就是研究寂護的。他是印度佛教後期的邏輯因明大師。他的邏輯是溫文的,甚至可以說是漂亮的。可惜的是,他的經論沒有同期的古漢譯本。
一進桑耶寺大殿,第一眼看見的,正正是寂護的雕像。很生動地,那intellectual look的表情,淡金色的學者風範。我很自! 然的做了一個五體投地的大禮拜,以示尊重。
他的旁邊,是蓮花生大師的金像。就是他們兩人把佛教帶進西藏。寂護大師是顯學,蓮花生大師是密宗。
可能是由於天還未全亮,寺內的光線很暗。不過,僧侶已開始誦經了。幾十個僧人,坐在一排一排整齊的沈色古木前,木上面放著長方形昏黃的經書,正搖擺著身體在誦經。在寒冷中,他們穿的不多,只是披著一襲藏紅色的僧袍,裡面還可以看見紅色黃邊夾衣那外露的整條手臂。究竟是誦經的節奏,還只是寒冷的哆嗦,令他們旋轉地搖動
身子呢?
寺院內的光線,主要來自兩個源頭:酥油供燈的燭光和斜照的淡黃晨光。不過,晨曦的淡光斜照,似乎更具有宗教性。
寺院七、八米樓高的佛殿,掛滿了五彩金黃的寶幢,從二樓斜照進來的昏黃晨光,穿過空氣中飄浮的微塵,似乎每顆微塵都反射著光蘊,融和著誦經的咒音,掀動我深層的某種神聖的悸動。
在土耳其的紫色蘇菲亞教堂、義大利的聖彼得大教堂,你都可以感受同樣的悸動,無論你是哪一個宗教的信徒。彷彿人類的深處,就是有某種宗教性的弦線,等待著一次靈性的牽動。
桑耶寺的正堂,端坐著四、五米高的佛陀! 釋迦牟尼金像,左邊是四大菩薩,右邊是四大天王。人物是一樣的,但造型就跟漢地的不一樣。佛教重視的是「覺」,佛像只是一個符號,是世俗的一個相、一個建立,所以佛像的造型會融合不同文化和時代的特色,像是不同的翻譯文本。
希臘的佛、印度的佛、中國的佛、男身的、女身的、夜叉的……,林林總總;印度傳來的不二法門、中國禪宗說的無相而相、西藏說的大圓滿大手印……;在桑耶寺,我感受到的,是一種不能言說的悸動,慢慢地忘我起來。
西藏狗的生死書
佛教把所有的生命體稱為「有情」。有情基於過去的業力,分別居於六道。上三道是天人、阿修羅和人類;下三道是畜生、餓鬼和地獄。西藏人認為,在畜生道中,最接近人道的是狗,所以西藏人對狗的態度是特別親切的。
在這次西藏的旅程中,我就認識了一隻擁有人的眼神的狗。牠長了一身全白的長毛,一點都不骯髒,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尖尖的鼻子,眼神是矇矓的,像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似的。牠一見我們就像老朋友一樣,非常的親切。
我們是在路邊的一個小鄉村遇上牠的。當小黑在拍照的時! 候,牠就用後腿蹬直,站起了身子,右手靠著小黑,左手在空中揮動,像指導著小黑,哪一個是最好的拍攝角度一樣。我們走的時候,牠傻勁的要鑽進我們的吉普車。開車後,還在後面跟著跑。車行了幾百米,發生了故障,停下來修。牠卻從老遠跑來,把頭柔柔的伏在我的臂彎中,在那一刻,我覺得已經和牠結了緣,可能在下一生,牠會是我的鄰居、同學,或者是同事,會說一些爛笑話,我買彩票輸了,牠還會安慰我呢!
一會兒,牠抬頭,望向很遠的地方,在無雲的藍天下,清風吹拂著白色的長毛,投出了一個形而上的眼神,令人動容,不知是否在想一些生與死的問題。
我不會忘記,牠在我們車後一直追趕的樣子。牠的名字叫小白。
不過,隔一天的清晨,事情卻往另一個方向走。
天還未全亮,兩隻狗突然衝出了馬路,我們的吉普車閃避不來,輾過了一隻。我還記得車子輾過時,那一個令人心裡絞痛的跳動。我沒有回頭看。司機沒奈何的說:「死了。」然後,我看見扎西‧星期五不停的轉著佛珠,不停的念渡亡咒。然後,他打了幾個電話。
幾天之後,談到輾過的狗,他說他心裡還是不舒服。雖然我們不是有意的,不過,他已經打了電話給他! 的姊姊,找一個僧人為狗兒超渡,也叫了每天繞著大昭寺步行八公里的媽媽,為狗兒轉經筒,念觀音六字大悲咒。
西藏人對狗兒生死的尊重,讓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對的,眾生都有情,都是平等的,一條生命就是一條生命。我們對每一個生命,又是否有足夠的尊重呢?
我在日喀則市的一間網咖內,
坐在我旁邊的藏族少年,正抽著菸,看港片《古惑仔》。
他非常溫文,還教我如何上網,顛覆了叛逆青少年的刻板印象。
西藏青少年是不是不反叛的呢?我不肯定……
離開網咖,我進了一間理髮店洗頭。
札西‧星期五老是說:「最好不要洗澡、洗頭,很容易會感冒。受不了的話,去理髮店吧。」
這是一間以玻璃和銀色金屬裝修的理髮店,挺現代感的,牆上還貼了韓星的海報。
在暖氣中洗頭,很舒服,只需二十元罷了。
我在享受著現代文明。
日喀則是西藏第二大城市,二十多萬人,是黃教格魯派的發源地。這幾百年,格魯派一直是執政教派,而黃教的大寺、紮什倫布寺就是在日喀則。西藏似乎就只有在拉薩市和日喀則市(好像還有林芝市)可以享受一點現代化的文明。其他的地方,都是樸素得近乎原始的。
抵達日喀則前一晚,落腳在定日縣唯一的小旅館。晚上沒有暖氣,甚至沒有電力。
旅館的小餐室,煲著一大壺水,上升的蒸氣集中在壺上的一條長鐵管中,不停流動。我抱著一隻可能因為看烈日太久而眼神矇矓的黑貓,滿足於生命之間渴望撫貼的皮膚下血液流動的溫暖。
從黃昏,到深夜,在這十八世紀古老的蒸氣暖爐旁,透著遙遠的溫柔。
聖湖的冰河時期
我們是幸運的。
西藏的聖湖,叫羊卓雍錯,簡稱羊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好幾年才結一次冰。恰好,我們參觀羊湖的時候,就遇上了羊湖結冰,可以在湖上漫步。
在山上看聖湖,和在湖面上漫步,是截然的兩種感覺。一個是莊嚴壯觀,另一個是如夢如幻。
太陽猛烈的照耀著,而我們卻漫步在冰的世界裡。這是一個不冷的零下世界,冷裡透著溫暖,暖中又帶著清涼。很西藏式熱情的冷,是西藏人那種熱愛生命又沒有被生命之火燃燒的清涼。腳底下的冰塊,像把我們和世俗隔開,站立在一個神聖的境界中。不過,步行了幾步,就聽見不知從哪傳來像是冰裂的微聲,打斷了我那神聖的玄思,肉體好像又要下墜到什麼的地方了……
在羊湖邊,我們真的遇上了一個羊男。是一個趕著一大群羊的牧羊青年。他名叫旺堆,二十三歲,矮小的個子,長期曝曬的臉,灰紅色的,長出了深深的皺紋,像一個中年人。
我問他:「你有什麼夢想?」
他回答:「我喜歡織布。」
西藏人就是這樣。他們沒有不切實際的夢想,比如做一個投資銀行家呀、鋼琴家呀等等。他們的夢想,都是很生活的、很貼近的東西。
也許,生活的本質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也說不定。
也許,不是America dream那種自我膨脹的意識型態的顛倒也說不定。
不過,我們好像已經習慣了生活在西方文化的設定中,而忘掉了純粹。
不知該怎樣解釋,在冰河時期的聖湖邊,聽羊男說他的夢想:「我喜歡織布。」突然給我一種浪漫的感覺,是一種很遙遠、超越了時空、很純白的浪漫感覺。
我買了, 他親手做的香
離開了聖湖,吉普車一路下山,結冰的湖在車窗外慢慢褪去,然後我只看見沙漠。
吉普車一直開往沙漠的深處,灰色的山離我越來越遠,好像將會在遠處慢慢消失。突然面前出現了一個寺院──桑丁寺。
不知道是由於寺院每層樓底比一般的寺院高,還是由於它被孤立在沙漠中心的緣故,桑丁寺顯得格外的壯觀好看。
桑丁寺高高的大門前,有四、五個僧人,正操作著一部簡單的機器,像在製作什麼似的。我趨前去看看,原來他們在做藏香。桑丁寺的藏香是很有名的,分銷全國各地。
設在沙漠中心的藏香工廠,會不會違反了物流的邏輯?
算了吧,香港人!
我們攀上了寺頂,在金色的法輪前面,我看見廣闊的沙漠中出現了龍捲風。那真的是奇景。不過那龍捲風似乎很友善,幼幼的一條小龍,一、二十米高,在廣闊的沙漠自在的遊走,一點都不像電影常見的惡龍。其實,西藏沙漠最惡的是沙塵暴,一旦刮起,就算站在廟頂,也會什麼都看不見。
在寺院的二樓,我們認識了一個小僧人。他在做好像包裝的最後工序。不要想像成廣東工廠production line那種作業模式,他只是把檯面上零零星星的小三角椎形藏香入盒而已,還不時和身邊的僧友談笑。
他叫仁珠多傑,十八歲,來桑丁寺一年了。他說他不喜歡上學校,喜歡做僧人,便跟父母說要出家。他說他現在很開心。當然嘛,不用上學,做自已喜歡的事情,父母又不反對,怎會不開心?
臨走的時候,我跟他買了剛剛入盒的幾盒藏香,他自豪的說:「這是我親手做的!」
白居寺的紅
白居寺是江孜的代表性寺廟。很有風格,簡簡單單的,一間黑色的寺,一個白色的塔。許舜英見了,可能會說:「是川久保玲的黑。」
寺院的黑,其實是特大的布門。
暖和的陽光,悠閒的寺廟,藏式的黑布門隨風微微的飄動。兩個年輕的媽媽坐在廣場,自然的敞開胸脯在餵奶。我在寺院內買了一串觸感粗糙的大佛珠,跟在兩個轉經的老婆婆後面,在寺院的廣場來回。一個康巴的帥哥經過我,往轉經廊。
這是一個很快樂的上午。這快樂沒有宗教性,是屬於人間的。
太陽開始到正頂。我們三人登上白色的佛塔。這個佛塔有十萬個佛像,分佈在佛塔內像山洞般大小不同的佛龕中。我們到了塔頂,遇見了一個紅衣少女和她的小兒子。
「少婦」這詞對她來說,是不合適的。一方面,她很年輕,看上去只有二十歲。最重要的是,她有少女的氣質──清純、靦腆和詩意的神情。我們請她讓小黑拍一張照片。起先她不好意思的拒絕了,經過札西‧星期五的誠意哀求,才終於答應。
她手拖著她的兒子,站在塔頂一面白牆的前面。這時中午的陽光很烈,照在牆上反射著刺眼的白,與少女的紅色藏服和像曬傷了的紅色肌膚,強烈地反差著,卻又互相穿透著。噢,很和諧啊!
A picture says a thousand words.
這就是我想說的「冷的熱情」。西藏的「冷的熱情」。
一種熱愛生命卻沒有被生命之火炙燒的清涼的熱。是超越了冷和熱之後的和諧統一。是回歸到生和死之前,那周遍的生機和宏淵的愛。這愛,也是屬於人間的,卻又不只是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