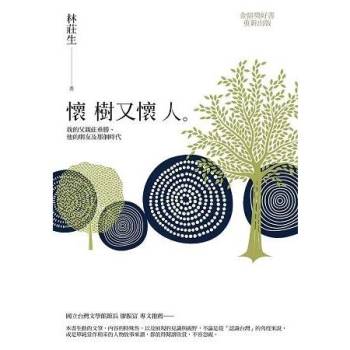第一章 日據時代
身世
父親莊垂勝,字遂性,號負人,一號徒然居士,日本據台後第三年(一八九七)生於鹿港。
先祖父莊士哲,是前清秀才,一九○二年任鹿港區區長。據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其家產約八千圓,對其治績有如下評語:「鹿港原是一大商埠,近時海口淤塞,舟楫不通,不能見舊時繁華也。君既是以為憂,通鐵軌於彰化,以便交通,邑人積咸稱其功。其他修溝洫興水利,或建學校而盛風化,大小事業,凡裨補地方公益者,莫不出於君胸算,上下信賴,聲譽遠聞……志操高潔亦可識矣。」(錄自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北文獻》直字第七十九期)。祖父有六個男孩子,父親排行第四。大伯、二伯畢業於當時的「中等學校」。祖父是中上級的公務人員,再無資力撫育其他小孩,三伯與父親均送進糖業講習所。
父親畢業該所後,得霧峰林家之資助去日本留學,回台後一九二八年跟母親結婚。
母親有坎坷的命運,一生下來,外祖母就逝世,再過三個月,外祖父林俊臣也逝世,真的變成天涯孤兒。幸好當時外曾祖父母還在,母親就在他們之撫育下長大。外曾祖父有三個男孩子,外祖父是長男,畢業於當時設立在彰化的「台中師範」(註一),甚受外曾祖父之器重,一切金錢由他管理。二叔公當時還未婚,精神不甚正常,大概因金錢上管束太嚴,大為不滿,一天竟一氣之下用槍把午睡中的外祖父打死,後來受良心譴責也自盡。外曾祖父的三個兒子,只剩下最小的一個林其賢,我叫他七叔公。外曾祖父在母親七歲時逝世,留下相當龐大的田產,大概有一萬租左右,大部分由七叔公和過房的十一叔公(林阿華)繼承。當時的社會女子沒有繼承權,不過母親究竟是外祖父唯一的親生女,因此也分到一點,差不多等於外曾祖父百分之三至四的租額。因外祖父這一房沒有丁男,父母親結婚時約定,將來生男即用母姓,生女即用父姓,這是我姓林的原因(註二)。
我是一九三○年出生。四、五歲的時候,全家搬到台中市,住在公園附近「鹽館」對面的二樓,那裡離「中央書局」很近,我想那次搬家一定是為了父親工作方便。記得那時候家裡有一個怪習慣,就是入寢之前,規定傭人要把兩個皮箱放在樓梯下。據說這是父親在東京大震災時獲得的大教訓。就是把重要的物件放置在小箱裡,緊急之事發生時,不必著慌,提著小箱子馬上就可以走開。這件事我記得相當清楚,原因是有一天晚上鄰家火警,我們一家確實按照父親平時的指示,不慌不亂拿著皮箱避難到附近榮鐘叔家了。說到東京大震災,這是父親在東京留學時發生的一大事件。對他來說,不但印象鮮明,對他以後的人生觀似乎發生相當深遠的影響。他常對我們說,從那次大震災以後,他對世事比較「看破」了些。他本來是一個非常儉樸的人,平常總是穿較舊、較壞的衣服,而把新的、好的收在皮箱內,結果震災那一天,他身上只穿古舊的衣服跑出來,好的衣服反而燒光了。「有福應該享受一下,不必太刻薄自己。」大概就是那時候領悟到的人生哲學吧。不過依我的觀察,他在這方面並沒有很大的改變。父親鹿港的竹馬之友施玉斗先生曾說過:「吃花生的時候,榮鐘是由大的、好的先吃;遂性是由小的、壞的先吃。」
父親的性格有目共睹。如果父親經過這次災難而有「看破」的地方,那就是他對生死有了較超越的看法。我五歲(一九三四)時,我們又搬了一次家;這一次搬家,不知是因上次火警,怕樓上的生活不安全,或是為我上學方便,父親選了柳川旁邊的初音町。記得我們搬進去的第二天,三弟正生出生了。我們定居在這裡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遷移霧峰萬斗六為止。我七歲入台中師範學校的附屬公學校,八歲時七七事變發生。有一天下午父親要帶我們去公園玩,正要踏出門口的時候,來了一個日警,他對父親講了什麼話,我沒注意,只聽到他大聲叫:「不要強辯,跟我來警察局。」父親跟他去後,我們起初以為是警察故意要為難他,叫他去「說教」,後來聽到書局的張星建、施學禮先生也被傳喚,才知道事情有點不妙。
父親當天就被扣留,過兩三天,高等科(主管思想方面)的警察來「家宅索查」,把父親的文件書籍包成幾大包帶走了。後來不知道用什麼名義,判他四十九天的徒刑。葉榮鐘先生在〈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記錄〉(註三)說:
七月蘆溝橋的槍聲一響,祖國開始八年的長期抗戰。八月上海事變發生,同月十五日,台灣軍宣佈台灣實施戰時體制,並由古莊軍司令官發表談話,其中一節說「島人(按:即台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論,若一旦聞知,即與剪除」云云。在古莊聲明以後,台灣各地的知識分子動輒得咎,被憲兵及特高警察干擾侮辱的事件,時時發生於各地。就中最聳動耳目的是台中的莊遂性,及台南歐清石兩先生,他們兩人可說是代表的犧牲者。莊先生是中部知識分子的領導者,平時頗有聲望,他於九月二日被台中警察署拘置四十餘天,所犯何罪,無人知道,連他本人在內。只有被捕數日後,台北的某報用兩欄的篇幅報導這件事說「民族意識濃厚,常作反抗言論的台中莊某,北支事變爆發後,對於南京播送的支那戰況,極表關心,這次當局發表對於收聽南京播送者將予嚴罰,莊某竟對此項處置,大鳴不平」云云。
父親進獄後,施維堯(註四)先生從台北趕來照顧我們,在這個時候他教我畫畫,這是我對繪畫發生興趣的開端。父親入獄之事,我相當懊惱。那時還不懂事,只知道壞人才會被警察抓去,所以覺得這是件很不名譽的事情,好在沒有同學來問我家裡發生什麼事。就在這個期間,我也做了一件很開心的事。我自幼小到小學二年級一直留著頭髮,這在現在看來是天經地義的行為,但在五十年前的台灣,所有小學生都是剃光頭,只有我一個留頭髮,常受同學的譏笑。我屢次要求父親讓我把頭髮剃掉,他都不答應。我趁他不在的機會,懇求母親准我剃光頭。媽媽到底較好商量,答應了。我馬上跑去常去的理髮廳,要求統統剃光。那位理髮師半信半疑問我:「真的?有沒有得到你爸爸的許可?」
我很高興地告訴他:「有,沒錯。」這樣我就跟多年來一直是我苦悶象徵的頭髮告別了。我還記得剃光頭回家時,母親一時認不得我,以為我是隔壁日本人的小孩子。對我來說,這次剃光頭不但使我面目一新,精神也鬆弛多了。少年時期我常埋怨父親只知道他自己的道理,而不了解我在學校的處境,時常迫我在父命與師命之間掙扎。留頭髮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受難。
還有一次,是在中學一年級時(一九四三)發生的。那時「皇民化運動」正推行得如火如荼,學校當局規定在校中將使用日本名字。當時改姓名頗風行,台中一中是台灣人的學校,素來以富民族意識而聞名,不過還是抵不住時代的狂流,同學中,小林、大林(原姓林者)、宮下(原姓呂)之類的日本名字日日增加。學校當局鑑於中國名、日本名,參差不齊,那些家長頑固老不改名的人,至少在學校中可以換一換日本名字叫叫,以增加大家的「日本人意識」。因為這是學校內的叫名,與戶籍上之名字沒有關係,我想一定沒問題,回家後隨便告訴父親這件事的經過,同時問他能不能替我取一個日本名字。他不經思索,衝口而出:「Hayasi Takeo 」。我問他怎麼寫,他用台灣話回答我:「林莊生。」
我的天啊!他是要我改音不改字,是要把「林莊生」這三個漢字改用日式的讀法而已。
原來日本人唸漢字有兩種讀法:一種叫「音讀」,一種叫「訓讀」。一般地說,中國人名是用「音讀」(我的名字音讀是 Rin So-Sei),日本人的名字是用訓讀。日本人也有林姓,所以「Hayasi」是可以的,「Takeo」也是很普遍的名字,但都是寫「武雄」或「武夫」。
我沒看過日本人有「莊生」這個名字,而這兩個漢字可以唸成「Takeo」也是頭一次聽到。當時那種以「皇國民」教育為宗旨的學校,如果按照父親的說法報上去,一定被教官痛打一頓,因為日本人最痛恨口從心不從的人。我當時覺得父親的頑固與不近人情竟到這個地步,一面驚愕,一面抱怨他。我沒告訴他這樣做可能引起的後果,只說這種改法學校一定不准。他反駁說:「為什麼不准?林茂生先生不也是『Hayasi Sigeo』嘛!」林先生所以能用這種高等政策對付日人,除了靠祖先姓林(如果姓蔡、陳、張,就沒有可能)而得通用之便以外,他是台灣人數一數二的民族主義派的知識分子,日人對這種改音不改字的作法,說起來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只是林先生之社會地位特殊,日人也無可奈何。日據時代如此改姓者恐怕只有他一人(其實這等於沒改,因為戶籍上之名字並不注音)。父親的意思好像也要我效法他。可是我只是中學一年級的學生啊!我知道跟他爭論也沒用,沒說下去,不過私下很埋怨他,覺得:「你要做不歸順的人(nonconformist)你去做好了,何必把我拉進去。」後來我還是瞞著父親,告訴老師說,我要用「林武雄」(用父親指定的音,不用他指定的字)。
這雖是一件小事,不過當時確實給我精神上很大的不安。後來過了好久,父親偶然在筆記簿上看到這個名字,問我:「誰給你這個名字?」我騙他說:「奧田先生以為這樣比較雄壯一點。」父親用輕蔑的口吻回答一句:「俗不可耐。」但沒再追問下去。我鬆了一口氣─就像小學時的理髮一樣。
說起學校內改姓名,我還有一次經驗。那是一九六一年到美國時,我發現從主任教授到系裡的同學,都對我的名字感到很難發音,他們的發音很像叫Johnson,因此我即告訴他們,以後就叫我 John 就好,免得彼此不方便。這次確實沒人要我「增加美國人意識」,我完全自動的,結果非常成功,在當時英文不十分通達的時候,我靠這個名字和洋同學親近了不少。此後我對國內、國外的通信均以 John Lin 自稱。我本來以為父親對此可能會閒言幾句,可是都沒有。他是唸過古書的人,大概知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罷!後來他逝世後,我整理他的來信,一律都是 Chuang-Sheng Lin,一字不改,真是頑固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