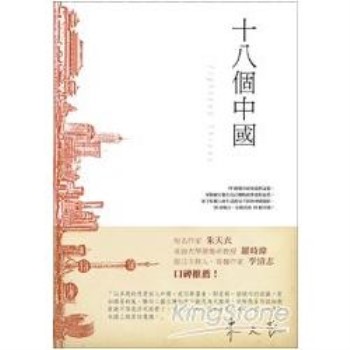五年一夢
文∣衛軻
我不知道該怎麼定義一個生活了五年的城市,這個城市離家的距離只有短短的九十二公里,小時候,沒有所謂的地理概念,覺得除了首都北京,省會合肥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那兒有大人們經常去的城隍廟,有孩子們憧憬的逍遙津公園,有車水馬龍的三孝口、四牌樓,有著長達半個世紀歷史的長江飯店。多少年後,走過城隍廟,人頭攢動依舊如母親所形容的那樣,但卻發現與它格格不入,那個年代的痕跡已在自己身上尋摸不著,如同一個八○後對於五、六○年代的印象影影綽綽般不真切,歷史與自己無關,剩下的只有木然、徬徨和街口的一碗涼皮米線。於是,路過兒時朝思暮想的逍遙津,雖然沒有再踏入,卻很值得開心。每個人,或許都有幾個這樣的地方,放在最深處,曠遠而又真切,一旦想到就會打開記憶的閘門,頃刻間,無數的冷暖和人情湧上心頭。這種體驗源於獨自靜靜斟酌的美,走近了,觸摸了,也許,就不那麼美好了,景沒變,我們的心態已千差萬別。
青春,如同一場春夢,從沒想過,自己會把最美好的青蔥歲月留在這樣一片土地上,如果可以,我希望這個夢不要醒來。
二○○四年的某個早晨,一家老小把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送到這裡,然後這個孩子在這個城市結識了一幫稱為朋友的傢夥,開心的度過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直至第五個年頭,某天即將遠行之際突然發覺對這個城市依依不捨,與朋友們抱頭痛哭一場後堅定地背著包坐著火車離開。很難說清楚這個城市給予了什麼,就如同很難界定我與這個城市的關係:朋友,家人抑或是戀人。記憶真是個奇妙的東西,我與她似乎談了一場短暫的戀愛,醒來後,愛情已經變為親情,濃香得久久無法忘懷。依稀記得車子在高架橋上穿梭,望著縱橫交錯的水泥墩子,彷彿初戀般莫名興奮。
剛來到合肥的時候,總喜歡去找尋每一條以省內城市命名的街道,彷彿這樣離家的距離就不那麼遙遠,多少次徜徉在紅星路、淮河路、長江路、金寨路,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路,將這五年的青春軌跡連同那些歡笑、失意、癡語串在一起,於是青春也就不那麼渺小了。
每次透過大巴的車窗遠遠望見大蜀山,我就知道合肥已不遠了。這座因火山噴發的大別山餘脈,不管是在豔冶如笑的春天,蒼翠欲滴的夏天,明淨如故的秋天,還是慘澹如臥的冬天,始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安靜地訴說著關於這個城市的故事,見證著屬於這個城市的歷史。
讀大學沒多久,高速的動車將原本兩小時的回家車程縮短到半個小時,但對於生性就有很多不安因素的我來說,離群索居似乎是最好的自我釋放方法,所以,也只有在節日才會踏上歸程。日子像爬滿牆上的藤,對這城市的漸漸熟悉就如同生命個體的長大,有些東西會悄無聲息地鑽入身體內部,安營紮寨,將自己與原本毫無關聯的它緊緊聯繫。你探尋得越多,根紮得越深,直到某天不得不離開時,才發現腳步已沉重的不能自已。
在一個地方住久了,身體的氣息就會散發出這個城市的特質,一種純粹屬於這個城市的精神能量。人需要不停的行走,從一個地方搬去另一個地方,將所有路過的不同幻化成自己的逍遙快樂。但很多時候,我們真的快樂嗎?離開合肥幾年,現在的我,每天忙忙碌碌穿梭在多米諾的夾縫中,幾乎看不到日月交替,卻總是站在窗邊看著夕陽映射在遠處的玻璃幕牆上,想念遠方的親人和朋友,想念四季更替的噓寒問暖,想念落日餘暉下天鵝湖飛奔的快感,想念著家鄉的方圓一百公里,想念那回不去、只能如電影膠片般在腦海中閃過的從前。
在陌生的城市聽到鄉音,辨識鄉人,如同在一個黑暗房間裡,跌跌撞撞地打開一個開關,所有的燈在瞬間點亮的同時,那種久違的安全感又肆無忌憚地俘獲了我們的心。這是一個永遠玩不膩的遊戲,雖然知道終將擦肩而過,茫茫人海中散佈著、點綴著多少說著同一種方言的人,但偶爾的捕捉,使得語言早已喪失其原有的功能,只是扭轉到同一個頻率,一切都回歸到質樸的原點,簡單、純粹。
生命中有多少個五年,如果每個五年都待在一座城市中,又可以在自己小小的地圖上,驕傲地添上幾個圈,掐指算算,除去前面不諳世事的二十幾年,也不過十個城市左右。我們以不同的方式與路過的風景打照面,希望從一去不復返的點滴中,再去挖掘被時光磨滅的影子,城市一次次包容著我們的無理取鬧,一次次寬恕著我們的可悲,把人們從迷失中拉回正軌。走得遠了、累了,我們需要的就僅僅只是一份安寧,合肥這樣一個圈,給予了我滿滿的存在感,她不需要過多的修辭,在「天地轉,光陰迫」的歷史輪迴中,本分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每次面對她,心會變得越來越柔軟,每當手指劃過她的皮膚,會有驚喜和悸動,會感覺到她的每一個毛孔都在呼吸,會感知她的脈搏,願意傾聽她訴說的故事,沉浸在她的臂彎中沉沉睡去,哪怕這個故事只有開頭沒有結尾。難道這些不足以說明你對這個城市的渴求?
這幾年,我與合肥唯一的交集就是從機場降落,再從同樣的機場起飛,機場等候廳的面孔始終是我為之牽盼的理由。二○一三年,機場搬遷到了郊區,我也許會直接坐上機場大巴回家,不再路過合肥,我不知道自己與她邂逅的機率還有多少,但我知道,這個被稱作「兩個胖子」的城市,承載著我刻骨銘心的青春記憶,是我不管走到哪兒都會魂牽夢繞的地方。
我與這個城市的夢漸行漸遠,卻仍願一醉方休。
重慶人都是孫悟空
文∣甘果
是重慶人還是四川人?
以前大學宿舍有一部特別破舊的座機,聽筒的透聲性能特別囂張,每次閨蜜打電話來,我都得把聽筒拿開距離耳朵二十公分的位置,才能在避免耳朵折壽的情況下聽清她說什麼。終於幾次後,幾個室友終於忍不住問我為什麼她老是打來吵架。我嘿嘿:這就是典型的重慶妹兒嘛!日常聊天都有本事突然激動起來,且邏輯清晰語速極快,得理不饒人,語感似罵人。就像外地遊客在重慶問路,可能會得到對方劈哩啪啦外加手舞足蹈的指路,不要以為他不耐煩,他只是熱情過頭,講不清楚,又容易激動。
我人生的前二十四年是重慶土著,幾個室友都是外地人,山西、江西、浙江這幾個地方對那時剛進校的我來說算是擴展了本人在中國地圖西南角以外的認知,很欣喜自己總算認識了活的川渝以外的朋友了。在那之前對我和我的小夥伴來說,介不介意被叫做四川人,和成都之間長久的西南老大之爭誰又贏了一局,成渝快線什麼時候建成,可以提速多少,重慶火鍋還是成都串串更好吃,這就是我們的「世界觀」。自從直轄後,大多重慶人就開始介意被叫做「四川人」,可當別人講四川人壞話時,又忍不住跳出來罵他。這十六年來重慶與成都的關係變化很微妙,也很自然:從早期默默積蓄怨恨、明爭暗鬥,到中間不知什麼時候矛盾突然爆發開始公開口水戰,再到後來兩地都各自經歷幾次巨大天災人禍時的相親相愛互幫互助,到如今把口水戰升級為爭奪西南話事權的實戰——其實就是一對相愛相殺的親兄弟。
這裡是江湖
許多在外地念了幾年書、至今仍飄泊在外的重慶人,說起家鄉,那都是各自各話,沒個準調。譬如,有人認為杭州的城市形象和氣質好過重慶,擁有全球聞名的美景,富有藝術氣息的城市空間,乾淨的街道,完善的公共設施,和相對高素質的市民……。而相比這樣的陽春白雪,重慶當然就特別的下里巴人了:沒什麼特別拿得出手的城市景點,混亂無章的空間佈局,垃圾隨處可見的街道,小巷裡橫七豎八的小攤兒,在哪兒都能高分貝私聊的市民……。但是我要說,這些表面上看來特別讓人厭惡的缺點,在我看來就是重慶的魅力。如果每個城市都如杭州般「完美」,你真的還會愛它們?如果不能半夜出門就吃到路邊的燒烤,人生還有什麼樂趣?重慶自古就沒有高冷的命,可我們本來走的就是接地氣的路線,包括重慶人的俠氣和豪邁使得這個城市更具有別的城市無法複製的個性。當然,也有人恨鐵不成鋼,也有人認為花是自家香……我們雖然無法預測或引導重慶未來的樣子,但都希望它的個性和素質能共存。
瘋狂的石頭 vs. 重慶森林 vs. 盜夢空間
幾年前的那部電影《瘋狂的石頭》讓重慶很是火了一把,托它的福,這幾年羅漢寺的香火旺得有點過分,過江索道也成了外地遊客的必遊景點,這簡直就是部重慶城市的宣傳廣告片。《重慶森林》倒是跟重慶沒什麼關係,可莫名地讓眾多根本沒看過此片的文青認為重慶就是一座特別文藝的森林城市。而對我來說,《盜夢空間》才是最能描述重慶如此奇葩的城市空間的電影,只有在這裡你才能體會走進大樓門口發現竟是三樓,而回家得下一層且還不是地下室的奇幻感受。
在香港坐巴士路過西營盤那幾條向山上延伸坡度近三十度的街道時,同行朋友都覺得不可思議,只有我覺得特別親切;每天爬十分鐘的陡坡上到位於半山腰的學校後,其他同學都快斷氣,只有我氣閑神定;當大家對深夜的小巴車神以F1速度靈活地穿梭在扭曲糾結的羊腸小巷中表示下次再也不坐的時候,我想起了重慶幾年前由於超速屢屢出事故、已被取締的七字頭小巴。作為山裡的孩子,從幼稚園到高中,我前十八年求學生活都必有一天往返兩次、一次近一個小時的翻山越嶺。爬坡上坎不喘氣是每個重慶人的天生自帶技能,而相反的,作為眾多城市重要交通工具的自行車,在重慶只能淪為娛樂項目,因為街道大都與山體走向自由連接,毫無邏輯規劃和東南西北。如果你跟計程車司機講「請一直往北走到頭,然後向西轉」的話他會請你下車,這時你應該機智地開啟重慶模式說「直起開抵攏左倒拐」。山地城市就是3D城市。
除了山,我們還有江。兩江匯合的朝天門是重慶的門戶,是重慶古城十八座城門之首,也是自古以來這座城市的大碼頭。如果非要說出這個毫無生長邏輯的城市原點,那必屬朝天門——山體圍繞而立,江水以此發散,說得朝天門者得重慶一點也不過。也因兩江貫穿主城,重慶的橋多到讓人覺得江上總有未建完的鋼筋巨柱。而前面提到拉風的過江索道曾在兩江上各有一座,而如今只剩下長江索道,既是居民日常通勤工具,也是如摩天輪般的休閒娛樂設施,它們在二○一○年成為了重慶最年輕的文物。
重慶可能是全國、甚至全球唯一除基本地面交通外,還同時擁有地鐵、輕軌、索道、渡輪等交通工具的大型城市。遊覽重慶最好的方式就是將這些交通工具挨個兒坐一遍,繞著主城區一圈下來就一天了,這個城市也就立體地收進你心裡了。上山下海淩空穿梭,山城兩江四岸天塹變通途,重慶人每天都做孫悟空。
真正的魅力在全景
時不時有外地朋友問我「去重慶玩一兩天,有什麼推薦的景點?」,原來我總是不經大腦地脫口而出:「當然就是解放碑購物,朝天門觀江,洪崖洞小吃,磁器口毛血旺,歌樂山辣子雞,南山一棵樹,洋人街遊樂場啦……。」後來發現這些旅遊書式的推薦太過千篇一律,且不能體現重慶獨特的山城魅力,於是我開始告訴朋友:你將所有交通工具都挨個坐一遍,繞著主城區轉一圈,幾乎就可以感受整個重慶的特色了。如果可能,相信你離開之後還會再想起這座城市。因為我覺得一個城市真正值得被瞭解的不應該是幾個精彩的景點,而是平淡的全景,整體的感受。再者說,去景點多半遇上的也是同樣的遊客,還不如搭個索道跟旁邊的棒棒兒(重慶話:替人搬運物件維生的體力勞動者)學兩句重慶話呢。
重慶天氣不好,冬冷夏熱,天空常年都是灰濛濛的,哪天突然來個藍天白雲,我們可能會懷疑是不是要地震了。所以白天蹲在街邊打望(重慶話:打量觀望,賓語多為美女)就好,到了晚上就可以出來活動了,兩江四岸的燈光工程還是很能唬一唬人的,被稱「小維港」是不用臉紅的。
攔都攔不住的熱愛
如今的重慶,已經開啟了準大城市發展模式。每隔幾個月不見,再見的時候必定能發現一些不知道何時冒出的高樓。其中不乏全國,乃至全球著名建築師的作品。城市天際線開始被重視,主要街道的舊樓立面改造很新穎,至少從外表上整個城市翻了個新。規劃更新,街道擴寬,交通整治,景觀改造,再加上軟實力的全面提升,它正在為成為西南第一城市拼命地努力著。在發展程度上重慶還沒趕上「北上廣」,可對它的發展潛力,任何一個稍有眼力的人都不會忽視。它發展速度之快以至於我連它一年後的樣子也無法預估。我沒能力也沒足夠客觀的心態去評論好與壞,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會繼續愛它。
《新週刊》有期重慶特刊是這麼說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人,能像重慶人一樣,如此熱愛他們的城市」。我很贊同。
北方版江南
文∣劉二囍
剛出濟南西火車站,回望這個建築物,北方的厚重感撲面而來,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北回歸線以南的人而言,此時,北方這個字眼很帶感。
晚飯跟一個久違的大學同學謀面,約在了一個大排檔,這是一個市井味十足的地方,我很是喜歡。在這裡,民間百態很容易被察覺,有時,這樣的場景,就是一個城市的縮影。在不算炎熱的盛夏傍晚,燒烤攤的大排檔熱鬧非凡。一群老少爺們赤著上身三三兩兩地圍坐在餐桌前,壯碩的屁股下面是弱不禁風的小馬紮,而放眼望去,大街小巷四處可見,光膀子儼然已經成為了漢子們的生活習慣;旁邊一桌,走了幾個,換來一對夫婦,約莫四十歲左右,檯面上擺滿了啤酒,只見兩人如嘮家常一般,坐在熱風陣陣偶爾散發著下水道騷臭味的街邊,暢飲甚歡,上演了一場民間的市井浪漫;服務員端上來一大把烤肉串,香噴噴的孜然,惹得人眼饞,來不及等它稍稍涼下,就放到了嘴邊,定眼一看,肉串的中間都間隔著放有大蒜,真是應驗了無蔥無蒜不歡。一頓飯的時間,讓我深感這裡是北方,這裡是山東。
除了東北大漢、西北大漢以外,在中國地理名詞中,唯有山東作為前綴最為順耳了,即便是東北大漢,很多都是山東人闖過關東定居後留下的後人。耳聽周邊人的山東腔,口音厚重中氣十足,眼觀老闆眉宇之間,濃眉上斜兩側漸寬,恍惚間,我有身處《水滸傳》場景的錯亂感,作為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故事背景正是發生在山東,一幫梁山好漢,群起為雄,依仗著江湖義氣,謀其公平正義。水泊梁山的這一群大漢,雖為草寇,言行舉止不雅,但心中卻是明大義,尚且清澈。這一群人,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成為濟南,乃至山東的代言。
比起南方,北方盛產粗人,這點在山東體現得很明顯。街上的大爺可以隨口噴出一口痰,路邊的小孩可以隨地撒出一泡尿,一個人要是在小賣部買罐飲料,找老闆要根吸管的話,絕對會被輕蔑的眼神鄙視半天。計程車司機嘴裡總習慣罵著娘,無論是道路擁塞,還是紅燈時間過長。連續幾次坐計程車,我都報上了確切的位置,司機沒有任何疑義,最後都把我丟在了我目的地的周邊,我還向他確認是不是到了,他們都用點頭默認,最終我必須要折騰一番才能夠找到目的地。我覺得計程車司機的這種粗已經越過了粗糙,顯得有些兒粗卑了。從幾次搭乘計程車的經驗,可以看出濟南不是一座好品質的旅遊城市,無論我如何用普通話與其交流,他永遠用一口濃郁的濟南話接應。
濟南雖流露著北方的豪放與厚重,但並非沒有細膩的一面,意想不到是濟南竟相容了江南的清秀與靈潤,甚至是集蘇杭以大成。早在九百多年前,北宋名士黃庭堅就有「濟南瀟灑似江南」的感慨。
杭州城依靠浩淼的西湖揚名,水中的滿塘曲院風荷,岸邊的萬千垂柳細絲,勾勒了屬於杭州的江南,然而同樣的物與景,在濟南一樣可見,「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說的就是它。同樣,濟南市中心也有一個內湖,它雖不及西湖的名號響徹,但「大明湖」這三個字也早已聲名遠揚。湖內成片成片的闊大圓葉在水面鋪開,層層疊疊,在粼粼波光的映襯下,即便荷花凋落,沒有了紅嫩的花朵,少去了一抹亮色,只是眼前這一片碧綠,荷韻清芳足以躍然而出;而大明湖的岸邊,垂柳追隨著湖岸線密聚成蔭,在微風的吹拂下,飄逸多姿,盡顯婀娜,搖曳出一份江南意境。西湖優勢在於除了景色,更有人文的底蘊,詩詞歌賦都是它的絕佳廣告文案,而大明湖雖有些文人墨客造訪,卻少有留下詩篇,這點上有些欠弱,然而其作為乾隆下榻地,成為與夏雨荷結緣的風雪場,為世人津津樂道,增添了幾分人文的厚度。
湖光山色的大明湖,在我眼中,完全可以與西湖媲美,即便水體面積稍稍小了些。但我說的是曾經的大明湖,如今,它的風景則是在湖與山這兩個元素上硬生生地加了個建築物,林立的高樓大廈讓天際線頻繁被攔腰剪斷,以致破壞了傳統的整體風貌。
西湖雖好,可是一到盛夏,西湖水就成了熱氣騰騰的滾湯,用自身熱度降低了遊人興致的熱度,帶來幾分掃興,大明湖可就不會,無論烈日當頭,還是酷暑難耐,水溫都可以保持在二十度左右,因為大明湖內的水是濟南城內的眾多泉水彙集而成,在炎炎夏日依舊得以保持清涼。泉水為這個城市添興的地方不僅有大明湖,更有縱橫交織的溝渠。濟南城內有大小泉上千眼,因此得有別稱泉城一說,出了名的景點就有趵突泉、黑虎泉,除此以外,在老城深巷,隱藏著無數長流不息的泉,於是,常常可以見到清澈的泉水在河溝裡流淌,相結成網,四處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景象。由於湧之不斷的泉眼,濟南也成了北方城市中最多水的一個,使其具有了水的潤澤與靈動。出了大明湖景區的南門,跨過大明湖路,進入一片老街區,名叫百花洲的河塘是曲水亭街的起端,深入進去,博來我陣陣讚歎,直呼驚豔,這裡儼然是北方版的江南。彎柔的河道兩側襯以低矮古樸的房舍與婀娜多姿的垂柳,隔三差五地橫跨著一座小橋,河岸邊有老人品茗飲茶,有孩童嬉戲玩耍,恍惚間我以為夢迴蘇州古城,然而,坐在石拱橋上,低頭望,流動的河水,比蘇州河道裡的清澈多了,甚至可見水中雜草隨著水流左右擺動,青色的魚兒在雜草間躥動暢遊,而不遠處,有老婦在河邊用這清澈的泉水洗衣,身後,一對父親在帶著兒子捕魚,手中是自製的漁具。
在劉鶚的《老殘遊記》裡,「家家泉水,戶戶垂柳」是對濟南的描述。這八個字言過其實,算是對濟南的一種美化,尤其在當今,老城不復存在,泉水枯斷擱淺,然而,我眼前的這份景色,確實是對這句話的完美寫實。我沒想到,我以為早已枯死在腦海裡的傳統情趣畫面竟然可以在這濟南中心城區的現實中上演。事實上,讓我覺得似曾相識的記憶並不只是在曲水亭街這一條街,這整個一片古城區內都不斷有驚喜發現。
我先出現的地方是恆隆廣場,這是濟南城區新興的購物中心,引領這個城市的時尚與潮流。恆隆廣場的另一側,一條馬路之隔,從那一個帶有牌坊的路口進入,上面寫著芙蓉街三個字,眼前的景象則從奢華大氣的購物空間轉變為人潮湧動的細街小巷,兩邊都是低矮的古房舍,繼續往前走,穿過這喧囂的半段,則是一番令人歡喜的天地。你能夠見到某戶人家門口放著一個籃筐,裡面放著熱騰騰的大饃,有孩童蹦蹦跳跳而來,然後拎著一袋子歡歡喜喜離去;你可以見到刷著深綠色油漆的木門,上面玻璃直接寫著理髮兩個大字,裡面是上了年紀的剃頭匠,而非美容美髮店裡油光滿面的髮型師;你可以見到商鋪店家在門口的街邊支上一張桌子,全家圍成一團盡享午餐,完全不顧及過路人的觀望,偶爾有街坊湊上來聊幾句家常。在這個老城區,傳統的生活形態依舊在延續,它保留的不止是建築物樣貌,更有老百姓的。過去的歷史在這裡活靈活現,這是我所見過最精彩的大城市老城區之一。眼下,周邊正在大動干戈地開發改造,希望它可以躲過劫難,可以以一如既往地在這裡屹立,直到永久。
行走於濟南的古街老巷、泉邊湖畔,能夠明顯地感受到這是一座被文化和歷史浸潤的城市。行走在大陸城市,通常會因現代印跡毀掉歷史沉澱而懊惱不已,在濟南,也不例外。倘若,濟南只是古城濟南的放大版,我一定會想與其相擁長眠。
詢問過不少山東人,他們對青島的傾情明顯大於濟南,濟南作為歷史文化名城,舊的東西被毀掉了,而新建設出的東西又太不入眼,或許這是濟南在吸引力上逐漸被新崛起的青島超越的一個原因吧。山東最有名的人是孔子,最有名的景是泰山,前者在曲阜,後者在泰安,而在山東最有名的城,現在已經變成了青島。山東是個不容小覷的省分,然而濟南在省會城市影響力排行榜上並不靠前。這些對濟南而言,多少有些尷尬。
文∣衛軻
我不知道該怎麼定義一個生活了五年的城市,這個城市離家的距離只有短短的九十二公里,小時候,沒有所謂的地理概念,覺得除了首都北京,省會合肥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那兒有大人們經常去的城隍廟,有孩子們憧憬的逍遙津公園,有車水馬龍的三孝口、四牌樓,有著長達半個世紀歷史的長江飯店。多少年後,走過城隍廟,人頭攢動依舊如母親所形容的那樣,但卻發現與它格格不入,那個年代的痕跡已在自己身上尋摸不著,如同一個八○後對於五、六○年代的印象影影綽綽般不真切,歷史與自己無關,剩下的只有木然、徬徨和街口的一碗涼皮米線。於是,路過兒時朝思暮想的逍遙津,雖然沒有再踏入,卻很值得開心。每個人,或許都有幾個這樣的地方,放在最深處,曠遠而又真切,一旦想到就會打開記憶的閘門,頃刻間,無數的冷暖和人情湧上心頭。這種體驗源於獨自靜靜斟酌的美,走近了,觸摸了,也許,就不那麼美好了,景沒變,我們的心態已千差萬別。
青春,如同一場春夢,從沒想過,自己會把最美好的青蔥歲月留在這樣一片土地上,如果可以,我希望這個夢不要醒來。
二○○四年的某個早晨,一家老小把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送到這裡,然後這個孩子在這個城市結識了一幫稱為朋友的傢夥,開心的度過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直至第五個年頭,某天即將遠行之際突然發覺對這個城市依依不捨,與朋友們抱頭痛哭一場後堅定地背著包坐著火車離開。很難說清楚這個城市給予了什麼,就如同很難界定我與這個城市的關係:朋友,家人抑或是戀人。記憶真是個奇妙的東西,我與她似乎談了一場短暫的戀愛,醒來後,愛情已經變為親情,濃香得久久無法忘懷。依稀記得車子在高架橋上穿梭,望著縱橫交錯的水泥墩子,彷彿初戀般莫名興奮。
剛來到合肥的時候,總喜歡去找尋每一條以省內城市命名的街道,彷彿這樣離家的距離就不那麼遙遠,多少次徜徉在紅星路、淮河路、長江路、金寨路,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路,將這五年的青春軌跡連同那些歡笑、失意、癡語串在一起,於是青春也就不那麼渺小了。
每次透過大巴的車窗遠遠望見大蜀山,我就知道合肥已不遠了。這座因火山噴發的大別山餘脈,不管是在豔冶如笑的春天,蒼翠欲滴的夏天,明淨如故的秋天,還是慘澹如臥的冬天,始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安靜地訴說著關於這個城市的故事,見證著屬於這個城市的歷史。
讀大學沒多久,高速的動車將原本兩小時的回家車程縮短到半個小時,但對於生性就有很多不安因素的我來說,離群索居似乎是最好的自我釋放方法,所以,也只有在節日才會踏上歸程。日子像爬滿牆上的藤,對這城市的漸漸熟悉就如同生命個體的長大,有些東西會悄無聲息地鑽入身體內部,安營紮寨,將自己與原本毫無關聯的它緊緊聯繫。你探尋得越多,根紮得越深,直到某天不得不離開時,才發現腳步已沉重的不能自已。
在一個地方住久了,身體的氣息就會散發出這個城市的特質,一種純粹屬於這個城市的精神能量。人需要不停的行走,從一個地方搬去另一個地方,將所有路過的不同幻化成自己的逍遙快樂。但很多時候,我們真的快樂嗎?離開合肥幾年,現在的我,每天忙忙碌碌穿梭在多米諾的夾縫中,幾乎看不到日月交替,卻總是站在窗邊看著夕陽映射在遠處的玻璃幕牆上,想念遠方的親人和朋友,想念四季更替的噓寒問暖,想念落日餘暉下天鵝湖飛奔的快感,想念著家鄉的方圓一百公里,想念那回不去、只能如電影膠片般在腦海中閃過的從前。
在陌生的城市聽到鄉音,辨識鄉人,如同在一個黑暗房間裡,跌跌撞撞地打開一個開關,所有的燈在瞬間點亮的同時,那種久違的安全感又肆無忌憚地俘獲了我們的心。這是一個永遠玩不膩的遊戲,雖然知道終將擦肩而過,茫茫人海中散佈著、點綴著多少說著同一種方言的人,但偶爾的捕捉,使得語言早已喪失其原有的功能,只是扭轉到同一個頻率,一切都回歸到質樸的原點,簡單、純粹。
生命中有多少個五年,如果每個五年都待在一座城市中,又可以在自己小小的地圖上,驕傲地添上幾個圈,掐指算算,除去前面不諳世事的二十幾年,也不過十個城市左右。我們以不同的方式與路過的風景打照面,希望從一去不復返的點滴中,再去挖掘被時光磨滅的影子,城市一次次包容著我們的無理取鬧,一次次寬恕著我們的可悲,把人們從迷失中拉回正軌。走得遠了、累了,我們需要的就僅僅只是一份安寧,合肥這樣一個圈,給予了我滿滿的存在感,她不需要過多的修辭,在「天地轉,光陰迫」的歷史輪迴中,本分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每次面對她,心會變得越來越柔軟,每當手指劃過她的皮膚,會有驚喜和悸動,會感覺到她的每一個毛孔都在呼吸,會感知她的脈搏,願意傾聽她訴說的故事,沉浸在她的臂彎中沉沉睡去,哪怕這個故事只有開頭沒有結尾。難道這些不足以說明你對這個城市的渴求?
這幾年,我與合肥唯一的交集就是從機場降落,再從同樣的機場起飛,機場等候廳的面孔始終是我為之牽盼的理由。二○一三年,機場搬遷到了郊區,我也許會直接坐上機場大巴回家,不再路過合肥,我不知道自己與她邂逅的機率還有多少,但我知道,這個被稱作「兩個胖子」的城市,承載著我刻骨銘心的青春記憶,是我不管走到哪兒都會魂牽夢繞的地方。
我與這個城市的夢漸行漸遠,卻仍願一醉方休。
重慶人都是孫悟空
文∣甘果
是重慶人還是四川人?
以前大學宿舍有一部特別破舊的座機,聽筒的透聲性能特別囂張,每次閨蜜打電話來,我都得把聽筒拿開距離耳朵二十公分的位置,才能在避免耳朵折壽的情況下聽清她說什麼。終於幾次後,幾個室友終於忍不住問我為什麼她老是打來吵架。我嘿嘿:這就是典型的重慶妹兒嘛!日常聊天都有本事突然激動起來,且邏輯清晰語速極快,得理不饒人,語感似罵人。就像外地遊客在重慶問路,可能會得到對方劈哩啪啦外加手舞足蹈的指路,不要以為他不耐煩,他只是熱情過頭,講不清楚,又容易激動。
我人生的前二十四年是重慶土著,幾個室友都是外地人,山西、江西、浙江這幾個地方對那時剛進校的我來說算是擴展了本人在中國地圖西南角以外的認知,很欣喜自己總算認識了活的川渝以外的朋友了。在那之前對我和我的小夥伴來說,介不介意被叫做四川人,和成都之間長久的西南老大之爭誰又贏了一局,成渝快線什麼時候建成,可以提速多少,重慶火鍋還是成都串串更好吃,這就是我們的「世界觀」。自從直轄後,大多重慶人就開始介意被叫做「四川人」,可當別人講四川人壞話時,又忍不住跳出來罵他。這十六年來重慶與成都的關係變化很微妙,也很自然:從早期默默積蓄怨恨、明爭暗鬥,到中間不知什麼時候矛盾突然爆發開始公開口水戰,再到後來兩地都各自經歷幾次巨大天災人禍時的相親相愛互幫互助,到如今把口水戰升級為爭奪西南話事權的實戰——其實就是一對相愛相殺的親兄弟。
這裡是江湖
許多在外地念了幾年書、至今仍飄泊在外的重慶人,說起家鄉,那都是各自各話,沒個準調。譬如,有人認為杭州的城市形象和氣質好過重慶,擁有全球聞名的美景,富有藝術氣息的城市空間,乾淨的街道,完善的公共設施,和相對高素質的市民……。而相比這樣的陽春白雪,重慶當然就特別的下里巴人了:沒什麼特別拿得出手的城市景點,混亂無章的空間佈局,垃圾隨處可見的街道,小巷裡橫七豎八的小攤兒,在哪兒都能高分貝私聊的市民……。但是我要說,這些表面上看來特別讓人厭惡的缺點,在我看來就是重慶的魅力。如果每個城市都如杭州般「完美」,你真的還會愛它們?如果不能半夜出門就吃到路邊的燒烤,人生還有什麼樂趣?重慶自古就沒有高冷的命,可我們本來走的就是接地氣的路線,包括重慶人的俠氣和豪邁使得這個城市更具有別的城市無法複製的個性。當然,也有人恨鐵不成鋼,也有人認為花是自家香……我們雖然無法預測或引導重慶未來的樣子,但都希望它的個性和素質能共存。
瘋狂的石頭 vs. 重慶森林 vs. 盜夢空間
幾年前的那部電影《瘋狂的石頭》讓重慶很是火了一把,托它的福,這幾年羅漢寺的香火旺得有點過分,過江索道也成了外地遊客的必遊景點,這簡直就是部重慶城市的宣傳廣告片。《重慶森林》倒是跟重慶沒什麼關係,可莫名地讓眾多根本沒看過此片的文青認為重慶就是一座特別文藝的森林城市。而對我來說,《盜夢空間》才是最能描述重慶如此奇葩的城市空間的電影,只有在這裡你才能體會走進大樓門口發現竟是三樓,而回家得下一層且還不是地下室的奇幻感受。
在香港坐巴士路過西營盤那幾條向山上延伸坡度近三十度的街道時,同行朋友都覺得不可思議,只有我覺得特別親切;每天爬十分鐘的陡坡上到位於半山腰的學校後,其他同學都快斷氣,只有我氣閑神定;當大家對深夜的小巴車神以F1速度靈活地穿梭在扭曲糾結的羊腸小巷中表示下次再也不坐的時候,我想起了重慶幾年前由於超速屢屢出事故、已被取締的七字頭小巴。作為山裡的孩子,從幼稚園到高中,我前十八年求學生活都必有一天往返兩次、一次近一個小時的翻山越嶺。爬坡上坎不喘氣是每個重慶人的天生自帶技能,而相反的,作為眾多城市重要交通工具的自行車,在重慶只能淪為娛樂項目,因為街道大都與山體走向自由連接,毫無邏輯規劃和東南西北。如果你跟計程車司機講「請一直往北走到頭,然後向西轉」的話他會請你下車,這時你應該機智地開啟重慶模式說「直起開抵攏左倒拐」。山地城市就是3D城市。
除了山,我們還有江。兩江匯合的朝天門是重慶的門戶,是重慶古城十八座城門之首,也是自古以來這座城市的大碼頭。如果非要說出這個毫無生長邏輯的城市原點,那必屬朝天門——山體圍繞而立,江水以此發散,說得朝天門者得重慶一點也不過。也因兩江貫穿主城,重慶的橋多到讓人覺得江上總有未建完的鋼筋巨柱。而前面提到拉風的過江索道曾在兩江上各有一座,而如今只剩下長江索道,既是居民日常通勤工具,也是如摩天輪般的休閒娛樂設施,它們在二○一○年成為了重慶最年輕的文物。
重慶可能是全國、甚至全球唯一除基本地面交通外,還同時擁有地鐵、輕軌、索道、渡輪等交通工具的大型城市。遊覽重慶最好的方式就是將這些交通工具挨個兒坐一遍,繞著主城區一圈下來就一天了,這個城市也就立體地收進你心裡了。上山下海淩空穿梭,山城兩江四岸天塹變通途,重慶人每天都做孫悟空。
真正的魅力在全景
時不時有外地朋友問我「去重慶玩一兩天,有什麼推薦的景點?」,原來我總是不經大腦地脫口而出:「當然就是解放碑購物,朝天門觀江,洪崖洞小吃,磁器口毛血旺,歌樂山辣子雞,南山一棵樹,洋人街遊樂場啦……。」後來發現這些旅遊書式的推薦太過千篇一律,且不能體現重慶獨特的山城魅力,於是我開始告訴朋友:你將所有交通工具都挨個坐一遍,繞著主城區轉一圈,幾乎就可以感受整個重慶的特色了。如果可能,相信你離開之後還會再想起這座城市。因為我覺得一個城市真正值得被瞭解的不應該是幾個精彩的景點,而是平淡的全景,整體的感受。再者說,去景點多半遇上的也是同樣的遊客,還不如搭個索道跟旁邊的棒棒兒(重慶話:替人搬運物件維生的體力勞動者)學兩句重慶話呢。
重慶天氣不好,冬冷夏熱,天空常年都是灰濛濛的,哪天突然來個藍天白雲,我們可能會懷疑是不是要地震了。所以白天蹲在街邊打望(重慶話:打量觀望,賓語多為美女)就好,到了晚上就可以出來活動了,兩江四岸的燈光工程還是很能唬一唬人的,被稱「小維港」是不用臉紅的。
攔都攔不住的熱愛
如今的重慶,已經開啟了準大城市發展模式。每隔幾個月不見,再見的時候必定能發現一些不知道何時冒出的高樓。其中不乏全國,乃至全球著名建築師的作品。城市天際線開始被重視,主要街道的舊樓立面改造很新穎,至少從外表上整個城市翻了個新。規劃更新,街道擴寬,交通整治,景觀改造,再加上軟實力的全面提升,它正在為成為西南第一城市拼命地努力著。在發展程度上重慶還沒趕上「北上廣」,可對它的發展潛力,任何一個稍有眼力的人都不會忽視。它發展速度之快以至於我連它一年後的樣子也無法預估。我沒能力也沒足夠客觀的心態去評論好與壞,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會繼續愛它。
《新週刊》有期重慶特刊是這麼說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人,能像重慶人一樣,如此熱愛他們的城市」。我很贊同。
北方版江南
文∣劉二囍
剛出濟南西火車站,回望這個建築物,北方的厚重感撲面而來,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北回歸線以南的人而言,此時,北方這個字眼很帶感。
晚飯跟一個久違的大學同學謀面,約在了一個大排檔,這是一個市井味十足的地方,我很是喜歡。在這裡,民間百態很容易被察覺,有時,這樣的場景,就是一個城市的縮影。在不算炎熱的盛夏傍晚,燒烤攤的大排檔熱鬧非凡。一群老少爺們赤著上身三三兩兩地圍坐在餐桌前,壯碩的屁股下面是弱不禁風的小馬紮,而放眼望去,大街小巷四處可見,光膀子儼然已經成為了漢子們的生活習慣;旁邊一桌,走了幾個,換來一對夫婦,約莫四十歲左右,檯面上擺滿了啤酒,只見兩人如嘮家常一般,坐在熱風陣陣偶爾散發著下水道騷臭味的街邊,暢飲甚歡,上演了一場民間的市井浪漫;服務員端上來一大把烤肉串,香噴噴的孜然,惹得人眼饞,來不及等它稍稍涼下,就放到了嘴邊,定眼一看,肉串的中間都間隔著放有大蒜,真是應驗了無蔥無蒜不歡。一頓飯的時間,讓我深感這裡是北方,這裡是山東。
除了東北大漢、西北大漢以外,在中國地理名詞中,唯有山東作為前綴最為順耳了,即便是東北大漢,很多都是山東人闖過關東定居後留下的後人。耳聽周邊人的山東腔,口音厚重中氣十足,眼觀老闆眉宇之間,濃眉上斜兩側漸寬,恍惚間,我有身處《水滸傳》場景的錯亂感,作為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故事背景正是發生在山東,一幫梁山好漢,群起為雄,依仗著江湖義氣,謀其公平正義。水泊梁山的這一群大漢,雖為草寇,言行舉止不雅,但心中卻是明大義,尚且清澈。這一群人,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成為濟南,乃至山東的代言。
比起南方,北方盛產粗人,這點在山東體現得很明顯。街上的大爺可以隨口噴出一口痰,路邊的小孩可以隨地撒出一泡尿,一個人要是在小賣部買罐飲料,找老闆要根吸管的話,絕對會被輕蔑的眼神鄙視半天。計程車司機嘴裡總習慣罵著娘,無論是道路擁塞,還是紅燈時間過長。連續幾次坐計程車,我都報上了確切的位置,司機沒有任何疑義,最後都把我丟在了我目的地的周邊,我還向他確認是不是到了,他們都用點頭默認,最終我必須要折騰一番才能夠找到目的地。我覺得計程車司機的這種粗已經越過了粗糙,顯得有些兒粗卑了。從幾次搭乘計程車的經驗,可以看出濟南不是一座好品質的旅遊城市,無論我如何用普通話與其交流,他永遠用一口濃郁的濟南話接應。
濟南雖流露著北方的豪放與厚重,但並非沒有細膩的一面,意想不到是濟南竟相容了江南的清秀與靈潤,甚至是集蘇杭以大成。早在九百多年前,北宋名士黃庭堅就有「濟南瀟灑似江南」的感慨。
杭州城依靠浩淼的西湖揚名,水中的滿塘曲院風荷,岸邊的萬千垂柳細絲,勾勒了屬於杭州的江南,然而同樣的物與景,在濟南一樣可見,「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說的就是它。同樣,濟南市中心也有一個內湖,它雖不及西湖的名號響徹,但「大明湖」這三個字也早已聲名遠揚。湖內成片成片的闊大圓葉在水面鋪開,層層疊疊,在粼粼波光的映襯下,即便荷花凋落,沒有了紅嫩的花朵,少去了一抹亮色,只是眼前這一片碧綠,荷韻清芳足以躍然而出;而大明湖的岸邊,垂柳追隨著湖岸線密聚成蔭,在微風的吹拂下,飄逸多姿,盡顯婀娜,搖曳出一份江南意境。西湖優勢在於除了景色,更有人文的底蘊,詩詞歌賦都是它的絕佳廣告文案,而大明湖雖有些文人墨客造訪,卻少有留下詩篇,這點上有些欠弱,然而其作為乾隆下榻地,成為與夏雨荷結緣的風雪場,為世人津津樂道,增添了幾分人文的厚度。
湖光山色的大明湖,在我眼中,完全可以與西湖媲美,即便水體面積稍稍小了些。但我說的是曾經的大明湖,如今,它的風景則是在湖與山這兩個元素上硬生生地加了個建築物,林立的高樓大廈讓天際線頻繁被攔腰剪斷,以致破壞了傳統的整體風貌。
西湖雖好,可是一到盛夏,西湖水就成了熱氣騰騰的滾湯,用自身熱度降低了遊人興致的熱度,帶來幾分掃興,大明湖可就不會,無論烈日當頭,還是酷暑難耐,水溫都可以保持在二十度左右,因為大明湖內的水是濟南城內的眾多泉水彙集而成,在炎炎夏日依舊得以保持清涼。泉水為這個城市添興的地方不僅有大明湖,更有縱橫交織的溝渠。濟南城內有大小泉上千眼,因此得有別稱泉城一說,出了名的景點就有趵突泉、黑虎泉,除此以外,在老城深巷,隱藏著無數長流不息的泉,於是,常常可以見到清澈的泉水在河溝裡流淌,相結成網,四處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景象。由於湧之不斷的泉眼,濟南也成了北方城市中最多水的一個,使其具有了水的潤澤與靈動。出了大明湖景區的南門,跨過大明湖路,進入一片老街區,名叫百花洲的河塘是曲水亭街的起端,深入進去,博來我陣陣讚歎,直呼驚豔,這裡儼然是北方版的江南。彎柔的河道兩側襯以低矮古樸的房舍與婀娜多姿的垂柳,隔三差五地橫跨著一座小橋,河岸邊有老人品茗飲茶,有孩童嬉戲玩耍,恍惚間我以為夢迴蘇州古城,然而,坐在石拱橋上,低頭望,流動的河水,比蘇州河道裡的清澈多了,甚至可見水中雜草隨著水流左右擺動,青色的魚兒在雜草間躥動暢遊,而不遠處,有老婦在河邊用這清澈的泉水洗衣,身後,一對父親在帶著兒子捕魚,手中是自製的漁具。
在劉鶚的《老殘遊記》裡,「家家泉水,戶戶垂柳」是對濟南的描述。這八個字言過其實,算是對濟南的一種美化,尤其在當今,老城不復存在,泉水枯斷擱淺,然而,我眼前的這份景色,確實是對這句話的完美寫實。我沒想到,我以為早已枯死在腦海裡的傳統情趣畫面竟然可以在這濟南中心城區的現實中上演。事實上,讓我覺得似曾相識的記憶並不只是在曲水亭街這一條街,這整個一片古城區內都不斷有驚喜發現。
我先出現的地方是恆隆廣場,這是濟南城區新興的購物中心,引領這個城市的時尚與潮流。恆隆廣場的另一側,一條馬路之隔,從那一個帶有牌坊的路口進入,上面寫著芙蓉街三個字,眼前的景象則從奢華大氣的購物空間轉變為人潮湧動的細街小巷,兩邊都是低矮的古房舍,繼續往前走,穿過這喧囂的半段,則是一番令人歡喜的天地。你能夠見到某戶人家門口放著一個籃筐,裡面放著熱騰騰的大饃,有孩童蹦蹦跳跳而來,然後拎著一袋子歡歡喜喜離去;你可以見到刷著深綠色油漆的木門,上面玻璃直接寫著理髮兩個大字,裡面是上了年紀的剃頭匠,而非美容美髮店裡油光滿面的髮型師;你可以見到商鋪店家在門口的街邊支上一張桌子,全家圍成一團盡享午餐,完全不顧及過路人的觀望,偶爾有街坊湊上來聊幾句家常。在這個老城區,傳統的生活形態依舊在延續,它保留的不止是建築物樣貌,更有老百姓的。過去的歷史在這裡活靈活現,這是我所見過最精彩的大城市老城區之一。眼下,周邊正在大動干戈地開發改造,希望它可以躲過劫難,可以以一如既往地在這裡屹立,直到永久。
行走於濟南的古街老巷、泉邊湖畔,能夠明顯地感受到這是一座被文化和歷史浸潤的城市。行走在大陸城市,通常會因現代印跡毀掉歷史沉澱而懊惱不已,在濟南,也不例外。倘若,濟南只是古城濟南的放大版,我一定會想與其相擁長眠。
詢問過不少山東人,他們對青島的傾情明顯大於濟南,濟南作為歷史文化名城,舊的東西被毀掉了,而新建設出的東西又太不入眼,或許這是濟南在吸引力上逐漸被新崛起的青島超越的一個原因吧。山東最有名的人是孔子,最有名的景是泰山,前者在曲阜,後者在泰安,而在山東最有名的城,現在已經變成了青島。山東是個不容小覷的省分,然而濟南在省會城市影響力排行榜上並不靠前。這些對濟南而言,多少有些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