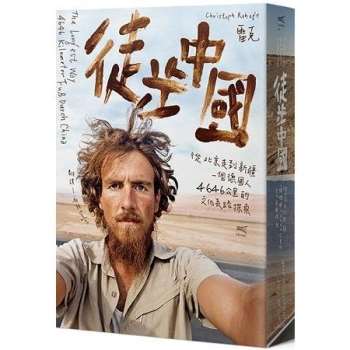劉爺爺的窯洞
我坐在劉爺爺家客廳裡,知道自己一定羞得滿臉通紅。
「這是從德國來的雷克!」餐館的女服務生一邊說,一邊將我推進屋裡,爺爺奶奶一臉愕然。她又喊了一句:「不用怕,他懂中文!」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兩位老人似信非信地望著我,在他們眼裡,我的出現一定如同一片陰沉的黑影,籠罩了他們家。
兩個小孩和一隻黃狗害羞地從另一間屋子探出頭來。
「你好!」我笨拙地擺擺手問好。
奶奶先開了口,「你好,德國雷克。」她大聲說,抬起手臂輕輕撞了撞老伴,又指了個位子讓我坐下。不一會兒,我面前的桌子上就擺上了茶和餅乾,接下來,她想聽聽我流落到她家的經過。
我結結巴巴地講了自己徒步旅行和我的壞脾氣,還有在旅館發生的不愉快,努力讓一切聽起來都在情理之中。說完後,我看看劉家奶奶─這家裡看樣子是她說了算。
她點點頭,「你可以在這兒睡,沒問題。」
「但我真的不想給你們添麻煩!」
「哪裡的話!」她擺擺手。
「你們住的這個……窯洞,真是美!」我讚揚道,一邊故意四下望望。粉刷得白亮的房間的確被佈置得非常舒適:電視、沙發、桌子,還有那有幾分俗氣的沙灘掛曆,應有盡有。人們幾乎不會意識到,這裡可是掘進山裡好幾公尺的窯洞。
奶奶臉上出現一抹自豪的微笑,「全都是我們自己修的。實用,冬天暖夏天涼。」
「而且還那麼乾淨!你都是怎麼保持的呀?」
她臉上的笑容又綻開了些,因受了我恭維而搖搖頭。
兩個小朋友終於壯起膽子走上前來,「雷克叔叔,」小女孩怯生生地問我,「你有北京的照片嗎?」
問我有沒有北京的照片?!
短短兩分鐘,我翻出筆記型電腦放到桌上。
「北京!」第一張照片剛出現在螢幕上,她就高興地叫了起來,「我也去過!」
「是嗎?」
「當然啦!」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說,這個問題真是荒謬。
「你什麼時候去的呀?」
「去年夏天。」
那時候她估計也就七、八歲吧。
她的小臉上洋溢著自豪的光芒,「北京可好啦!那兒很乾淨。」
乾淨?我想起了自己第一天到達北京的情景,想起了那散不開穿不透的塵霧。
我問小姑娘她說乾淨具體指的是什麼,她則似乎對我的無知驚訝不已。「你不知道在北京白裙子可以穿一整天嗎?」她說完,又小聲補充道,「在這兒,幾個小時就變黑了。」
奶奶帶著兩個孩子回裡屋睡覺後,劉爺爺和我還在客廳裡坐了一陣,喝茶。
他身體結實,話不多,桀驁不馴的頭髮旁分著,右眼皮微微下垂。從前,他和這裡大部分男人一樣在礦上幹活,現在兒子在外掙錢,他照顧孫兒孫女。
不知怎的,我們聊到了「文化大革命」。
「那時候慘啊,」他聲音低沉,「真是慘啊。」
這一段歷史是人們不樂於談及的,如果談到了,語氣也往往和德國人談到「第三帝國」時相近。人們努力尋找一個客觀中性的語調,謹慎地擇選每一個用詞,句子都以「他們」而不以「我們」為主語。
「最慘的是,那時候連自家人也鬥,」他說,「兄弟之間,父子之間,沒有例外。」
我忽然想起了朱輝講他父親的故事,「文革」中朱輝的父親為躲避政治鬥爭進山打獵孤獨度日。
「那時候人們關心的究竟是什麼?」我問。
劉爺爺思考了一會兒,「關心的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解讀,誰領會得最到位。」他歎了口氣,「你們外國人可能無法理解。」
「文化大革命」幾乎算是毛老人家的最後一搏。六○年代中期,「大躍進」的失敗使他的領袖威望大大受損,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北京的同志們開始在議政時排擠自己,一股深深的不滿擒住了他。「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位年過七十的老人,向青年人發出號召以打擊黨內對手。
年輕的一代回應了。
這場風暴席捲全國十年之久,憤怒的紅衛兵將老師教員趕出學校,偉大領袖觀望著,拍手叫好。緊接著受到批判的是所有的知識份子和黨內的老幹部,許多人被毆打至死。相比之下,那些和鄧小平一樣僅僅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平白給農民添了不少亂的人們,可以算是大幸了。
大字報貼滿了整個中國,「○○是修正主義者,革命的敵人!」或者,「○○與××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無論城鄉,沒有一處的廟宇佛像不被損毀。在走上革命道路前曾留學德法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也只得借助軍方力量才使紫禁城免遭一劫。
有一個問題困擾了我好久:「劉爺爺,真是江青和她的團夥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嗎?」這是官方的歷史結論。我又想起了博物館裡所見的絲質馬桶。
劉爺爺帶著一副詫異的表情看看我,「當然啦,他們不是還被判了刑嗎!」
「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對吧?」
「是啊,怎麼了?」
「我只是在想,如果毛主席不是真的……呃……希望文革發生的話,他難道沒辦法阻止她嗎?」劉爺爺歪著頭,「毛澤東,」他說道,還在末尾附上了一聲長長的「啊」,「毛澤東啊……那時候已經是個老人了。」
我坐在劉爺爺家客廳裡,知道自己一定羞得滿臉通紅。
「這是從德國來的雷克!」餐館的女服務生一邊說,一邊將我推進屋裡,爺爺奶奶一臉愕然。她又喊了一句:「不用怕,他懂中文!」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兩位老人似信非信地望著我,在他們眼裡,我的出現一定如同一片陰沉的黑影,籠罩了他們家。
兩個小孩和一隻黃狗害羞地從另一間屋子探出頭來。
「你好!」我笨拙地擺擺手問好。
奶奶先開了口,「你好,德國雷克。」她大聲說,抬起手臂輕輕撞了撞老伴,又指了個位子讓我坐下。不一會兒,我面前的桌子上就擺上了茶和餅乾,接下來,她想聽聽我流落到她家的經過。
我結結巴巴地講了自己徒步旅行和我的壞脾氣,還有在旅館發生的不愉快,努力讓一切聽起來都在情理之中。說完後,我看看劉家奶奶─這家裡看樣子是她說了算。
她點點頭,「你可以在這兒睡,沒問題。」
「但我真的不想給你們添麻煩!」
「哪裡的話!」她擺擺手。
「你們住的這個……窯洞,真是美!」我讚揚道,一邊故意四下望望。粉刷得白亮的房間的確被佈置得非常舒適:電視、沙發、桌子,還有那有幾分俗氣的沙灘掛曆,應有盡有。人們幾乎不會意識到,這裡可是掘進山裡好幾公尺的窯洞。
奶奶臉上出現一抹自豪的微笑,「全都是我們自己修的。實用,冬天暖夏天涼。」
「而且還那麼乾淨!你都是怎麼保持的呀?」
她臉上的笑容又綻開了些,因受了我恭維而搖搖頭。
兩個小朋友終於壯起膽子走上前來,「雷克叔叔,」小女孩怯生生地問我,「你有北京的照片嗎?」
問我有沒有北京的照片?!
短短兩分鐘,我翻出筆記型電腦放到桌上。
「北京!」第一張照片剛出現在螢幕上,她就高興地叫了起來,「我也去過!」
「是嗎?」
「當然啦!」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說,這個問題真是荒謬。
「你什麼時候去的呀?」
「去年夏天。」
那時候她估計也就七、八歲吧。
她的小臉上洋溢著自豪的光芒,「北京可好啦!那兒很乾淨。」
乾淨?我想起了自己第一天到達北京的情景,想起了那散不開穿不透的塵霧。
我問小姑娘她說乾淨具體指的是什麼,她則似乎對我的無知驚訝不已。「你不知道在北京白裙子可以穿一整天嗎?」她說完,又小聲補充道,「在這兒,幾個小時就變黑了。」
奶奶帶著兩個孩子回裡屋睡覺後,劉爺爺和我還在客廳裡坐了一陣,喝茶。
他身體結實,話不多,桀驁不馴的頭髮旁分著,右眼皮微微下垂。從前,他和這裡大部分男人一樣在礦上幹活,現在兒子在外掙錢,他照顧孫兒孫女。
不知怎的,我們聊到了「文化大革命」。
「那時候慘啊,」他聲音低沉,「真是慘啊。」
這一段歷史是人們不樂於談及的,如果談到了,語氣也往往和德國人談到「第三帝國」時相近。人們努力尋找一個客觀中性的語調,謹慎地擇選每一個用詞,句子都以「他們」而不以「我們」為主語。
「最慘的是,那時候連自家人也鬥,」他說,「兄弟之間,父子之間,沒有例外。」
我忽然想起了朱輝講他父親的故事,「文革」中朱輝的父親為躲避政治鬥爭進山打獵孤獨度日。
「那時候人們關心的究竟是什麼?」我問。
劉爺爺思考了一會兒,「關心的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解讀,誰領會得最到位。」他歎了口氣,「你們外國人可能無法理解。」
「文化大革命」幾乎算是毛老人家的最後一搏。六○年代中期,「大躍進」的失敗使他的領袖威望大大受損,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北京的同志們開始在議政時排擠自己,一股深深的不滿擒住了他。「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位年過七十的老人,向青年人發出號召以打擊黨內對手。
年輕的一代回應了。
這場風暴席捲全國十年之久,憤怒的紅衛兵將老師教員趕出學校,偉大領袖觀望著,拍手叫好。緊接著受到批判的是所有的知識份子和黨內的老幹部,許多人被毆打至死。相比之下,那些和鄧小平一樣僅僅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平白給農民添了不少亂的人們,可以算是大幸了。
大字報貼滿了整個中國,「○○是修正主義者,革命的敵人!」或者,「○○與××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無論城鄉,沒有一處的廟宇佛像不被損毀。在走上革命道路前曾留學德法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也只得借助軍方力量才使紫禁城免遭一劫。
有一個問題困擾了我好久:「劉爺爺,真是江青和她的團夥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嗎?」這是官方的歷史結論。我又想起了博物館裡所見的絲質馬桶。
劉爺爺帶著一副詫異的表情看看我,「當然啦,他們不是還被判了刑嗎!」
「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對吧?」
「是啊,怎麼了?」
「我只是在想,如果毛主席不是真的……呃……希望文革發生的話,他難道沒辦法阻止她嗎?」劉爺爺歪著頭,「毛澤東,」他說道,還在末尾附上了一聲長長的「啊」,「毛澤東啊……那時候已經是個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