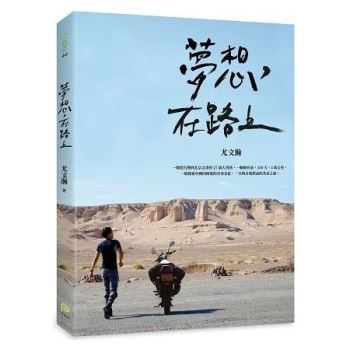驕傲的使命
「唯有我經歷過的世界,它的存在才有意義。」
故事的源起,應當回到前年九月某個深沉的夜,由一段夢境帶來的虛寂說起。那是我在北京經歷的第二個金秋,漫天落葉紛飛,為北國捎來蒼黃的凋零。北京大學擁擠的四人間宿舍,是這二年來生活的地方,狹窄的空間裡,卻滿是對夢想憧憬的芬芳。而自己的夢,大概也是浸沐於如此滋潤下,直入沉沉的夜裡悄悄萌芽。
夢境,一堵灰黑色的水泥石牆聳立,牆面漆色斑剝透露出歲月的沉積,它的存在好似為了隔絕某種聯繫。而我,距離牆面五公尺,竭力奔向牆壁兩端無限伸延的盡頭,視野逐漸迷失在狂奔的速度當中。裡頭能稱得上色彩的,大概僅有黑白交染相錯時的幽灰,不比黑色純粹,也不似白色單一,幽灰的夢裡襯托出混沌的空靈。這場從頭到尾虛無的夢境,透露出內容空白的荒誕,似乎也凝結了目前的人生縮影。除了盲目地拔腿奔往未知的遠方,甚至對於牆後一無所知的世界,存在一種未曾經歷的恐懼。
醒於唇乾舌燥之後,我摸著幽暗的宿舍房沿,爬往床邊書桌找水。房門頂端,格網狀透氣孔間隙,廊燈疲乏微弱的光線依稀鑽了進來。它緩緩淌向書架二層,抹在那本包裹米黃色書皮,印著深紅色《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的文字。書角寫著作者埃內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他是醫學系學生、共產主義者、政治領袖、革命家。但這些身分,遠遠不及時代所賦予的鮮明標幟「理想分子」,法國哲學家沙特(Paul Sartre)口中「我們時代的完人」。
關於「理想」的談論,大概是任何一位青年心底最有力的號召,而理想於他身上的展現,幾乎等同於個人行為與意志本身。面對反對者質疑,他曾這麼說道:「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甚至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我們將回答一千零一遍。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世上真能有「完美的人」嗎?時代精神,真能僅憑個人意志引領嗎?這或許是過去十年裡,存於心底最深刻的疑問。
沉寂的四周,僅存室友偶爾發出的鼾聲。我用帶著睡意的指尖,熟稔地喚醒架上的「日記」。舉止盡可能小心翼翼,不僅擔心驚擾旁人好夢,更牽掛著書本裡,正在環遊拉丁美洲的主人翁。他正著手計畫自己的環遊旅行嗎?正帶著濃厚綿密的憂傷,與家人們相互道別嗎?還是,與他的旅途夥伴阿爾貝托,在翻越山嶺的路途上經歷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又或者,正在整趟旅行中給予最大衝擊的痲瘋病院裡,進行著醫學系學生行醫治病的本分。或許,我也同無數青年與格瓦拉一樣,始終對理想抱有堅持,也對夢想富含渴望;甚至,對未曾親身經歷的世界充滿好奇、探索與欲望。而夢想的豐滿與現實的骨感,總在此消彼長、不斷撕扯中拉鋸。
當日後切‧格瓦拉完成革命理想,再度投身於那場令他喪命的玻利維亞民族解放運動時,所記錄下的一字一句,思想體現更加成熟、筆鋒力量更為流暢。但我仍舊鍾愛他在摩托車日記裡,記錄下僅屬於青年理想主義者的成長過程,一種參雜稚嫩陣痛與追根究柢的質疑;一種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首次最為純粹的交織、建構,再經歷一連串崩塌的過程。最終,遺留下幾道深深沉澱的疤痕以後,真正由男孩成為男人的蛻變痕跡。
我擰轉桌上的黑色檯燈,橙白色微弱光線在漆黑的房間裡渲染開來。幾秒間的光盲幻逝,我再度掀翻書本首章泛黃的紙頁。一段樸實無華,卻也深刻動人的文字敘述,映入眼底:「這不是一個英雄的傳奇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憤世嫉俗者的敘述。這是兩個生命的短暫交會,是兩個懷著相似希望與夢想的生命的一段共同歷程。」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也曾令我幻想獨自一人跨上摩托車,走在一九五一年格瓦拉的環遊之路,馳騁在拉丁美洲廣袤的土地上。一位摯友、一輛摩托車、一次漫長的旅行、一場充斥激情的革命,幾乎填滿所有二十歲青年心裡那份無處安放的熱情;在每個懷抱理想的青春歲月,關於世界的樣貌,應當盡滿所有美好期待。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對抗現實任何不公義的鬥爭,為之奉獻一顆純潔而鮮紅的心臟,基於內心崇高理念作出的選擇,這是永存於崩壞世代裡,最值得驕傲的偏執。
凌晨時分,窗外微風徐徐,透過窗簾散漫進北京這座城市的獨有氣息。北方空氣不同於南方溫潤,乾燥凜冽的北風,夾雜著一股濃厚的煙硝味兒。當我望向桌上那只顏色略微淺褪的深褐色皮革腕錶,黑色消光的玻璃鏡面底下,長短指針已停留在清晨的五時一刻。指針的實體,刻劃出時間的虛幻本質,而手裡捧著「日記」與甦醒後的唇乾舌燥,重新將我拉回當下的現實。翻開書頁下一行,寫道:「寫這些日記的人,再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離我們而遠去。我,重新整理和潤色這些日記的人,早已不再是當年的那個我。」一場自我放逐式的摩托車旅行,足以改變對一切事物的看法,重塑對世界的認識與內在價值。藉由實際走一遭這種直接而細膩的方式,在腳底下這片土地踏上深刻烙印,如果世上任何一種形式的存在,不曾與之產生牽絆與聯繫的共鳴,那它的存在便也毫無意義。
人的精神核心來自新的經驗與體驗,意義的賦予,最後則歸於內心渴望與源源不絕的好奇。一九五一年,當格瓦拉跨上那輛Norton 500摩托車,展開漫長的拉丁美洲穿越之旅。他目光所及盡是人們生活中的沉重與苦痛,感受的是財閥的壓迫與剝削,觸動心底的是人們渾然天成的樂觀及純樸,震撼的是古印加文明過去的輝煌與如今數不盡的滄桑。而經歷一甲子漫長的時間維度,橫跨太平洋來到世界的彼端,著眼於世界人口最多、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又將看見什麼樣的景色?五千年文化的歷史底蘊?紅色革命理想的實踐?或是,至今仍舊隨處彌漫充斥著,人性的墮落與貪婪?
在電影《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裡,同樣年輕的理想主義者Christopher面對大海時這麼說道:「我知道在生活中並不一定要堅強,但重要的是能夠堅強並且能夠感到堅強。」大約半年多前,我因為家族遺傳性疾病被醫院診斷出腎臟患有惡性腫瘤,或許,十多年來漫長的準備與等待,早就足以應付醫師對於病情略顯刻意的輕鬆描述。步出診間之時,內心倒也因此感到舒坦寬適,彷彿從長久以來的盲目與未知中,獲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而命運的催促,似乎讓自己對生命產生一種更為迫切的把握,從而加速推動手中「摩托車環遊中國」的旅行計畫,而不是作為原先給自己碩士班畢業的獎勵。或許,如今回頭看待這趟旅行裡的冒險成分,從跨上摩托車踏出的第一步開始,就早已決定以這種方式展現面對生活的勇氣。猶然記得出發的前一天夜裡,我在日記裡寫道:「雖然這是一個連自己都感到無比荒唐的想法,但任何意義及其延伸的可能,都始於一種看似不切實際的執著。面對即將展開的摩托車環中國之旅,能夠獲得怎樣的回報,只有當自己踏入終點的那一刻,才是具體真實的獲得、體會。而這個過程的失與得,在最終付諸實踐的當下,似乎也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我夢想在極其有限的生命裡,騎著摩托車遊覽世界各地,成為一個比任何人都認真生活的人,哪怕這個過程勢必將是如此短暫。然後,向這個世界宣示一條這樣的訊息:『我們都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義務,任何的原因與羈絆,都不足以成為逃避追求的理由,因為唯有經歷,才能真正確認關於它的真實存在』。」
一個人、一輛摩托車、整整一百天的時間與三萬公里的騎行,用兩顆十七吋輪框的軸距,丈量整片中國土地。我計畫走過中國、俄羅斯邊境最東端的城市──撫遠,與最北端的極光之地──漠河,一路向西前往最西端的中國、吉爾吉斯坦口岸──伊爾克什坦,再去往國境之南──三亞。在這段為期三個多月的旅行計畫裡,穿越中國面積最大的塔克拉瑪干沙漠、翻越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體驗令人脫水的四十五度高溫、挺過零度以下的高原嚴寒;在內蒙古草原享受與牧民們共同奔馳的歡愉、在海南島感受原始海洋的自然衝擊、在沙漠中欣賞日出日落的軌跡,與戈壁灘上布滿頂空的遙遙星際。
輕輕闔上手中米黃色書頁的日記,遠眺清晨窗外的北京,在地平線遙遠彼端的盡頭裡,射出一道略帶漸層的金黃色曙光。晨曦的背後,如此柔和、緩慢,連結著令我嚮往的遠方。將摩托車日記重新塞回那狹小書架的細縫,我並不清楚究竟是哪一本書抑或哪一個人,曾經明確地指引著這位二十三歲青年內心的熱情,但所有事件背後絕對都隱藏著一條只屬於它的宿命。如今,執起那支靜靜躺臥在抽屜裡滿溢鮮紅色墨水的筆。起程,由我來寫下這段,屬於自己的摩托車日記。邊境探奇
告別高句麗古文明,我順著G201國道離開吉林省去往黑龍江,前方迎來是俄羅斯邊界廣袤的遠東領地。甫過牡丹江,按捺不住心底對於中俄邊境的探奇,遂於G201國道去往雞西的岔路口,往東奔向G301國道盡頭,素有中俄友誼城之稱的「綏芬河」。路途上,左右兩旁成片鬱綠的林被,覆蓋著蒼茫漫天的黃土,造作於黃土上端蜿蜒無際的公路,闢出一條通往視野極限的遠方。在北方,越是往北人煙越發稀少罕見;而越是去往邊境的路,往往僅剩國際貿易貨車擦身並行。除了偶爾奔於林間的野兔及黃鼬,將周遭靜謐的沉寂偶染一絲生機,純然的平靜祥和,彷彿凝結了空間裡的所有生息。
綏芬河,是一座邊境移民城市,也是連結俄羅斯遠東地區重要的窗口橋梁。市區裡,每天兩班發往遠東第一大城海參崴的國際列車,與去往各地跨國專線的國際巴士,兩國人民密集交流就從一班班專車的輸送下延展開來。由此地出發,距離最近的俄羅斯濱海邊疆口岸「波格拉尼奇內」,也僅有短短的十六公里。在這座沾染濃厚商貿氣息的城市,販售俄羅斯貨品的商舖似乎更多於中國店舖。據地方政府公示,公共場所百分之百的俄語普及率,即便是在小的商場也能說上一兩句俄語。過去,施行貨幣管制政策的中國,嚴格禁止外幣於境內使用,而前幾年的綏芬河,不但成為中國首個俄羅斯盧布試用點,更是國內首次允許外幣自由流通的城市,其經貿重要性與國際戰略地位可見一斑。
然而,在綏芬河的兩天時間,穿梭於市內街道卻湧現一股莫名的蕭條。白天商場裡三兩結群的俄羅斯商人晃蕩,夜晚門庭冷落的酒吧與餐館,絲毫感受不出熱絡的商業氛圍。當地商人如此說道:「近幾年綏芬河已不復往日榮景,在俄羅斯的保護主義底下,使得對外貿易條件每下愈況。人民生活好不好,商人們最先嗅到;經濟形勢繁不繁榮,邊境城市最先知道。」綏芬河,過去的忙碌與繁華猶可追憶,如今城市風貌卻已略顯蕭瑟蒼涼。雖然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但實際走上一遭市區裡的大白樓、東正教堂舊址、俄羅斯駐綏領事館舊址,仍舊難以掩蓋在這座貿易城市底下,多元豐富的文化融合美景。我在綏芬河的停留,不單迷戀於濃郁的異國風情,更是想治療來時路上被蜂螫的傷口。抵達綏芬河傍晚,行經一處森林滿密的林場時,一股深切疲乏的倦意湧現。我隨手拉開包裹緊實的布織防風面罩,想透過冷冽寒風吹散濃濃睡意。忽然間,一陣突如其來的灼熱刺痛,猛然撕裂著我的上唇,彷彿被某種利刃劃下一道見骨傷口。我強忍劇痛,將車緩緩停向路旁雜道小徑,在模糊的後視鏡中,一根細長的黑針牢牢扎在唇裡。此時,我已顧及不了是為何物,內心只想趕緊將口中燃燒的黑針取出。那黑針牢牢地扎著,深深實實種在嫩白的唇裡,妄動挑取反倒是讓針的尾鉤越刺越扎實。幾次嘗試以後,除了兩行不爭氣的淚水滑落,似乎再也束手無策。在一片荒涼的曠野上,遑論想找間診所,一下午連人也沒見著幾個。我心想,距離百多公里的綏芬河,咬著牙也得挺過去,除此之外,更沒有其他辦法。
抵達綏芬河已是晚間九點,整日未進食的飢餓加上積累的疲態,早已掩蓋、或許麻痺嘴裡的痛楚。接近凌晨時分,我將帳篷紮在市區通天路的圓環裡,是一塊能夠俯視北海公園與成片綠野的高地,但似乎沒有出發時的雅興。我孱弱無力地躺在地面仰望星空,伴隨嘴裡喃喃的疑問:「為何要這樣折磨自己……」沉睡在高地圓環街燈圍繞的微弱光線裡。
翌日清晨,初夏的豔陽透過樹梢打在淡綠色帳篷頂,篷內悶熱的水氣附著於內帳與外帳間隙,飽滿結實的水珠順斜而下,落在黏膩的髮絲與臉龐。雖然不過七點,但陽光探頭以後,帳篷裡溫度攀升宛若一頂小型煉獄。恍惚之間,昨日針螫的傷口奇癢難耐,我搔撓著面部企圖止癢,癢處卻越是擴散。幾小時後,帶著腫脹的側臉與上唇,焦急地在大街上打探附近的診所消息。在一處綠色招牌,上頭寫著「北海社區衛生服務站」裡,衛生室護理師朝我投來訝異的目光,她打量眼前這位染上怪病的患者,淡淡說了一句:「我們這裡沒有藥。」爾後,彷彿驅趕著瘟疫般讓我離開,即便,我需要的也許僅是一罐可以簡單消毒的優碘。
逐漸腫脹變形的左臉,除了荒謬可笑以外,也許還帶點令人恐懼的詭譎。來到第二間診所,護理師在我苦苦央求下,勉為其難地替腫脹的傷口做清潔消毒,針扎部分相比昨日已未感疼痛,但裡頭彷彿仍有毒液在蔓延。往後的四、五天裡,搔癢與腫脹不僅打消了遊覽心情,甚至連進食咀嚼都成為奢侈,我幾乎依靠著流質食物與飲料繼續旅行,前往中國四極的第一站──撫遠。進入中國最北邊的省分「黑龍江」,偏遠山區、貧瘠土地、人煙荒蕪,是來此之前對於這片遙遠北國土地的印象。然而,實際來到這裡才驚覺,腳下竟是一塊「捏把黑土冒油花,插雙筷子也發芽」的沃土。上世紀五○年代以前,東北以北是從未被現代化開發的原始大地,人們將它的蒼涼稱之為「北大荒」。在嫩江流域、黑龍江平原、三江平原周邊約五萬多公里的面積土地,不僅有豐沛的水利資源,土壤肥沃程度甚至與烏克蘭大平原、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東北松遼流域齊名為世界三大黑土區。東北平原高含量有機質土壤,隨著五○年代以後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在政府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退伍幹部響應國家政策前往北方拓墾底下,當年的北大荒形象徹底搖身一變,如今儼然成為中國產量最高的農糧之都「北大倉」。
在往撫遠的路上,每天所行駛的三、四百公里距離,往往一天時間也走不出一塊農業屯墾區,公路沿途兩側光景,放眼所及皆是一面相同的水稻田景色。幾萬畝田間布下的初秧,隨著田水映出湛藍天色蕩漾,在曙光農場、前進農場、創業農場、勝利農場這些簡單卻充滿朝氣的農墾區裡,是一幅幅渾然天成的農事畫面。當地農場裡純樸的務農人,手指水田驕傲地說道:「你來的時間太早,田裡的秧苗不過剛剛播下,若再遲上幾個月,等到秋收那才是真正的遍地金黃哪。」我無緣見證豐收時的飽滿,但僅憑眼前一株株密麻的嫩苗,也能想像出秋收拾穗的豐碩場景。
離開北京的第十一天,我抵達中國四極第一站「撫遠」。素有「華夏東極」、「東方第一縣」之稱的撫遠縣,位於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交匯處,與俄羅斯隔江相望,是中國領土最東端的城市。而撫遠縣境內的黑瞎子島,長遠以來更以遺世獨立的神秘性引人矚目。黑瞎子,東北方言裡的「黑熊」之意,在這座一分為二的溼地島嶼上,東側為俄羅斯領地、西側為中國領地。民國初期爆發的中蘇軍事衝突「中東鐵路事件」,戰敗方中國最終簽下《伯力協定》,導致黑瞎子島就此被蘇聯占領。而兩國始終存在有關黑瞎子島的邊界問題,直至二○○四年雙方才達成協議,以十一塊界碑劃分中俄疆土,黑瞎子島的爭議就此落幕。時至今日,黑瞎子島的開發已趨於成熟,遊客登島已是熱門的旅遊觀光項目,兩國國界則以簡單的柵欄與鐵絲隔絕,沒有過去的戰火煙硝,反倒成為雙方最接近彼此的距離。在東方第一縣「撫遠」,由於地理位置因素,是中國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猶然記得初入此地,尚未意識自己早已身處地理東極,在凌晨三點鐘的帳篷裡睡眼矇矓,被外頭一陣強光的照射下驟然驚醒,日出時空的跨越恍若置身一場魔幻夢境。撫遠本地人們的時間,總要比「內地」早上幾個鐘頭,夏至之時,凌晨二點鐘便日光乍現,宣告一種獨特生活作息的開始。這座城市的特殊,除了經驗以外日常生活的萬物運行驚喜,還隱藏著不期而遇的人為驚奇。
在三個多月的旅行計畫,事前準備資金不足以應付每日的住宿開銷,即便百元人民幣左右的廉價旅館,也僅能作為旅途中偶爾奢侈的享受。「一路向東」,是撫遠鎮上唯一的青年旅社,一張三十五塊錢的床位包含熱水澡與被褥,已是旅途中最確切的幸福。在我抵達撫遠前,從未預期如此偏遠小鎮能有廉價住宿,北國一年二季的氣候結構,與冬天零下二十度左右的低溫,實在難以想像有人願意來此經營青年旅社。「一路向東」的店主老王,前年旅行時來到撫遠,停留在這家青旅打工換宿,因緣際會下持著一股衝勁離開家鄉山東,跑到千里之外的撫遠成為「一路向東」的新主人。從他靦腆的笑容中絲毫感受不出身為老闆的成熟穩練,而是對前來投宿的旅人,充滿無微不至的暖心照應。他的前老闆,也就是「一路向東」的催生者,在親手打造完這間內心的夢想青旅以後,短暫經營便辭去漂泊。而年輕的老王,作為當時店裡的一位換宿者,象徵性地以一塊錢從他手中接下「一路向東」。
我訝異著他口中那位實踐夢想爾後歸去的浪子,也感嘆著大老遠跑來極地接手青旅的老王,對於一個旅遊資源並不豐富、遊客人潮也並不多見的地方,他們的存在純粹出於緣分,或者帶著某種使命意義?是一種無價的回饋服務?還是一種關於夢想的執著?或許,給予往來旅人們的感受,更多是一種對「在路上」精神的堅持。
「唯有我經歷過的世界,它的存在才有意義。」
故事的源起,應當回到前年九月某個深沉的夜,由一段夢境帶來的虛寂說起。那是我在北京經歷的第二個金秋,漫天落葉紛飛,為北國捎來蒼黃的凋零。北京大學擁擠的四人間宿舍,是這二年來生活的地方,狹窄的空間裡,卻滿是對夢想憧憬的芬芳。而自己的夢,大概也是浸沐於如此滋潤下,直入沉沉的夜裡悄悄萌芽。
夢境,一堵灰黑色的水泥石牆聳立,牆面漆色斑剝透露出歲月的沉積,它的存在好似為了隔絕某種聯繫。而我,距離牆面五公尺,竭力奔向牆壁兩端無限伸延的盡頭,視野逐漸迷失在狂奔的速度當中。裡頭能稱得上色彩的,大概僅有黑白交染相錯時的幽灰,不比黑色純粹,也不似白色單一,幽灰的夢裡襯托出混沌的空靈。這場從頭到尾虛無的夢境,透露出內容空白的荒誕,似乎也凝結了目前的人生縮影。除了盲目地拔腿奔往未知的遠方,甚至對於牆後一無所知的世界,存在一種未曾經歷的恐懼。
醒於唇乾舌燥之後,我摸著幽暗的宿舍房沿,爬往床邊書桌找水。房門頂端,格網狀透氣孔間隙,廊燈疲乏微弱的光線依稀鑽了進來。它緩緩淌向書架二層,抹在那本包裹米黃色書皮,印著深紅色《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的文字。書角寫著作者埃內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他是醫學系學生、共產主義者、政治領袖、革命家。但這些身分,遠遠不及時代所賦予的鮮明標幟「理想分子」,法國哲學家沙特(Paul Sartre)口中「我們時代的完人」。
關於「理想」的談論,大概是任何一位青年心底最有力的號召,而理想於他身上的展現,幾乎等同於個人行為與意志本身。面對反對者質疑,他曾這麼說道:「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甚至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我們將回答一千零一遍。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世上真能有「完美的人」嗎?時代精神,真能僅憑個人意志引領嗎?這或許是過去十年裡,存於心底最深刻的疑問。
沉寂的四周,僅存室友偶爾發出的鼾聲。我用帶著睡意的指尖,熟稔地喚醒架上的「日記」。舉止盡可能小心翼翼,不僅擔心驚擾旁人好夢,更牽掛著書本裡,正在環遊拉丁美洲的主人翁。他正著手計畫自己的環遊旅行嗎?正帶著濃厚綿密的憂傷,與家人們相互道別嗎?還是,與他的旅途夥伴阿爾貝托,在翻越山嶺的路途上經歷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又或者,正在整趟旅行中給予最大衝擊的痲瘋病院裡,進行著醫學系學生行醫治病的本分。或許,我也同無數青年與格瓦拉一樣,始終對理想抱有堅持,也對夢想富含渴望;甚至,對未曾親身經歷的世界充滿好奇、探索與欲望。而夢想的豐滿與現實的骨感,總在此消彼長、不斷撕扯中拉鋸。
當日後切‧格瓦拉完成革命理想,再度投身於那場令他喪命的玻利維亞民族解放運動時,所記錄下的一字一句,思想體現更加成熟、筆鋒力量更為流暢。但我仍舊鍾愛他在摩托車日記裡,記錄下僅屬於青年理想主義者的成長過程,一種參雜稚嫩陣痛與追根究柢的質疑;一種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首次最為純粹的交織、建構,再經歷一連串崩塌的過程。最終,遺留下幾道深深沉澱的疤痕以後,真正由男孩成為男人的蛻變痕跡。
我擰轉桌上的黑色檯燈,橙白色微弱光線在漆黑的房間裡渲染開來。幾秒間的光盲幻逝,我再度掀翻書本首章泛黃的紙頁。一段樸實無華,卻也深刻動人的文字敘述,映入眼底:「這不是一個英雄的傳奇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憤世嫉俗者的敘述。這是兩個生命的短暫交會,是兩個懷著相似希望與夢想的生命的一段共同歷程。」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也曾令我幻想獨自一人跨上摩托車,走在一九五一年格瓦拉的環遊之路,馳騁在拉丁美洲廣袤的土地上。一位摯友、一輛摩托車、一次漫長的旅行、一場充斥激情的革命,幾乎填滿所有二十歲青年心裡那份無處安放的熱情;在每個懷抱理想的青春歲月,關於世界的樣貌,應當盡滿所有美好期待。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對抗現實任何不公義的鬥爭,為之奉獻一顆純潔而鮮紅的心臟,基於內心崇高理念作出的選擇,這是永存於崩壞世代裡,最值得驕傲的偏執。
凌晨時分,窗外微風徐徐,透過窗簾散漫進北京這座城市的獨有氣息。北方空氣不同於南方溫潤,乾燥凜冽的北風,夾雜著一股濃厚的煙硝味兒。當我望向桌上那只顏色略微淺褪的深褐色皮革腕錶,黑色消光的玻璃鏡面底下,長短指針已停留在清晨的五時一刻。指針的實體,刻劃出時間的虛幻本質,而手裡捧著「日記」與甦醒後的唇乾舌燥,重新將我拉回當下的現實。翻開書頁下一行,寫道:「寫這些日記的人,再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離我們而遠去。我,重新整理和潤色這些日記的人,早已不再是當年的那個我。」一場自我放逐式的摩托車旅行,足以改變對一切事物的看法,重塑對世界的認識與內在價值。藉由實際走一遭這種直接而細膩的方式,在腳底下這片土地踏上深刻烙印,如果世上任何一種形式的存在,不曾與之產生牽絆與聯繫的共鳴,那它的存在便也毫無意義。
人的精神核心來自新的經驗與體驗,意義的賦予,最後則歸於內心渴望與源源不絕的好奇。一九五一年,當格瓦拉跨上那輛Norton 500摩托車,展開漫長的拉丁美洲穿越之旅。他目光所及盡是人們生活中的沉重與苦痛,感受的是財閥的壓迫與剝削,觸動心底的是人們渾然天成的樂觀及純樸,震撼的是古印加文明過去的輝煌與如今數不盡的滄桑。而經歷一甲子漫長的時間維度,橫跨太平洋來到世界的彼端,著眼於世界人口最多、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又將看見什麼樣的景色?五千年文化的歷史底蘊?紅色革命理想的實踐?或是,至今仍舊隨處彌漫充斥著,人性的墮落與貪婪?
在電影《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裡,同樣年輕的理想主義者Christopher面對大海時這麼說道:「我知道在生活中並不一定要堅強,但重要的是能夠堅強並且能夠感到堅強。」大約半年多前,我因為家族遺傳性疾病被醫院診斷出腎臟患有惡性腫瘤,或許,十多年來漫長的準備與等待,早就足以應付醫師對於病情略顯刻意的輕鬆描述。步出診間之時,內心倒也因此感到舒坦寬適,彷彿從長久以來的盲目與未知中,獲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而命運的催促,似乎讓自己對生命產生一種更為迫切的把握,從而加速推動手中「摩托車環遊中國」的旅行計畫,而不是作為原先給自己碩士班畢業的獎勵。或許,如今回頭看待這趟旅行裡的冒險成分,從跨上摩托車踏出的第一步開始,就早已決定以這種方式展現面對生活的勇氣。猶然記得出發的前一天夜裡,我在日記裡寫道:「雖然這是一個連自己都感到無比荒唐的想法,但任何意義及其延伸的可能,都始於一種看似不切實際的執著。面對即將展開的摩托車環中國之旅,能夠獲得怎樣的回報,只有當自己踏入終點的那一刻,才是具體真實的獲得、體會。而這個過程的失與得,在最終付諸實踐的當下,似乎也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我夢想在極其有限的生命裡,騎著摩托車遊覽世界各地,成為一個比任何人都認真生活的人,哪怕這個過程勢必將是如此短暫。然後,向這個世界宣示一條這樣的訊息:『我們都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義務,任何的原因與羈絆,都不足以成為逃避追求的理由,因為唯有經歷,才能真正確認關於它的真實存在』。」
一個人、一輛摩托車、整整一百天的時間與三萬公里的騎行,用兩顆十七吋輪框的軸距,丈量整片中國土地。我計畫走過中國、俄羅斯邊境最東端的城市──撫遠,與最北端的極光之地──漠河,一路向西前往最西端的中國、吉爾吉斯坦口岸──伊爾克什坦,再去往國境之南──三亞。在這段為期三個多月的旅行計畫裡,穿越中國面積最大的塔克拉瑪干沙漠、翻越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體驗令人脫水的四十五度高溫、挺過零度以下的高原嚴寒;在內蒙古草原享受與牧民們共同奔馳的歡愉、在海南島感受原始海洋的自然衝擊、在沙漠中欣賞日出日落的軌跡,與戈壁灘上布滿頂空的遙遙星際。
輕輕闔上手中米黃色書頁的日記,遠眺清晨窗外的北京,在地平線遙遠彼端的盡頭裡,射出一道略帶漸層的金黃色曙光。晨曦的背後,如此柔和、緩慢,連結著令我嚮往的遠方。將摩托車日記重新塞回那狹小書架的細縫,我並不清楚究竟是哪一本書抑或哪一個人,曾經明確地指引著這位二十三歲青年內心的熱情,但所有事件背後絕對都隱藏著一條只屬於它的宿命。如今,執起那支靜靜躺臥在抽屜裡滿溢鮮紅色墨水的筆。起程,由我來寫下這段,屬於自己的摩托車日記。邊境探奇
告別高句麗古文明,我順著G201國道離開吉林省去往黑龍江,前方迎來是俄羅斯邊界廣袤的遠東領地。甫過牡丹江,按捺不住心底對於中俄邊境的探奇,遂於G201國道去往雞西的岔路口,往東奔向G301國道盡頭,素有中俄友誼城之稱的「綏芬河」。路途上,左右兩旁成片鬱綠的林被,覆蓋著蒼茫漫天的黃土,造作於黃土上端蜿蜒無際的公路,闢出一條通往視野極限的遠方。在北方,越是往北人煙越發稀少罕見;而越是去往邊境的路,往往僅剩國際貿易貨車擦身並行。除了偶爾奔於林間的野兔及黃鼬,將周遭靜謐的沉寂偶染一絲生機,純然的平靜祥和,彷彿凝結了空間裡的所有生息。
綏芬河,是一座邊境移民城市,也是連結俄羅斯遠東地區重要的窗口橋梁。市區裡,每天兩班發往遠東第一大城海參崴的國際列車,與去往各地跨國專線的國際巴士,兩國人民密集交流就從一班班專車的輸送下延展開來。由此地出發,距離最近的俄羅斯濱海邊疆口岸「波格拉尼奇內」,也僅有短短的十六公里。在這座沾染濃厚商貿氣息的城市,販售俄羅斯貨品的商舖似乎更多於中國店舖。據地方政府公示,公共場所百分之百的俄語普及率,即便是在小的商場也能說上一兩句俄語。過去,施行貨幣管制政策的中國,嚴格禁止外幣於境內使用,而前幾年的綏芬河,不但成為中國首個俄羅斯盧布試用點,更是國內首次允許外幣自由流通的城市,其經貿重要性與國際戰略地位可見一斑。
然而,在綏芬河的兩天時間,穿梭於市內街道卻湧現一股莫名的蕭條。白天商場裡三兩結群的俄羅斯商人晃蕩,夜晚門庭冷落的酒吧與餐館,絲毫感受不出熱絡的商業氛圍。當地商人如此說道:「近幾年綏芬河已不復往日榮景,在俄羅斯的保護主義底下,使得對外貿易條件每下愈況。人民生活好不好,商人們最先嗅到;經濟形勢繁不繁榮,邊境城市最先知道。」綏芬河,過去的忙碌與繁華猶可追憶,如今城市風貌卻已略顯蕭瑟蒼涼。雖然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但實際走上一遭市區裡的大白樓、東正教堂舊址、俄羅斯駐綏領事館舊址,仍舊難以掩蓋在這座貿易城市底下,多元豐富的文化融合美景。我在綏芬河的停留,不單迷戀於濃郁的異國風情,更是想治療來時路上被蜂螫的傷口。抵達綏芬河傍晚,行經一處森林滿密的林場時,一股深切疲乏的倦意湧現。我隨手拉開包裹緊實的布織防風面罩,想透過冷冽寒風吹散濃濃睡意。忽然間,一陣突如其來的灼熱刺痛,猛然撕裂著我的上唇,彷彿被某種利刃劃下一道見骨傷口。我強忍劇痛,將車緩緩停向路旁雜道小徑,在模糊的後視鏡中,一根細長的黑針牢牢扎在唇裡。此時,我已顧及不了是為何物,內心只想趕緊將口中燃燒的黑針取出。那黑針牢牢地扎著,深深實實種在嫩白的唇裡,妄動挑取反倒是讓針的尾鉤越刺越扎實。幾次嘗試以後,除了兩行不爭氣的淚水滑落,似乎再也束手無策。在一片荒涼的曠野上,遑論想找間診所,一下午連人也沒見著幾個。我心想,距離百多公里的綏芬河,咬著牙也得挺過去,除此之外,更沒有其他辦法。
抵達綏芬河已是晚間九點,整日未進食的飢餓加上積累的疲態,早已掩蓋、或許麻痺嘴裡的痛楚。接近凌晨時分,我將帳篷紮在市區通天路的圓環裡,是一塊能夠俯視北海公園與成片綠野的高地,但似乎沒有出發時的雅興。我孱弱無力地躺在地面仰望星空,伴隨嘴裡喃喃的疑問:「為何要這樣折磨自己……」沉睡在高地圓環街燈圍繞的微弱光線裡。
翌日清晨,初夏的豔陽透過樹梢打在淡綠色帳篷頂,篷內悶熱的水氣附著於內帳與外帳間隙,飽滿結實的水珠順斜而下,落在黏膩的髮絲與臉龐。雖然不過七點,但陽光探頭以後,帳篷裡溫度攀升宛若一頂小型煉獄。恍惚之間,昨日針螫的傷口奇癢難耐,我搔撓著面部企圖止癢,癢處卻越是擴散。幾小時後,帶著腫脹的側臉與上唇,焦急地在大街上打探附近的診所消息。在一處綠色招牌,上頭寫著「北海社區衛生服務站」裡,衛生室護理師朝我投來訝異的目光,她打量眼前這位染上怪病的患者,淡淡說了一句:「我們這裡沒有藥。」爾後,彷彿驅趕著瘟疫般讓我離開,即便,我需要的也許僅是一罐可以簡單消毒的優碘。
逐漸腫脹變形的左臉,除了荒謬可笑以外,也許還帶點令人恐懼的詭譎。來到第二間診所,護理師在我苦苦央求下,勉為其難地替腫脹的傷口做清潔消毒,針扎部分相比昨日已未感疼痛,但裡頭彷彿仍有毒液在蔓延。往後的四、五天裡,搔癢與腫脹不僅打消了遊覽心情,甚至連進食咀嚼都成為奢侈,我幾乎依靠著流質食物與飲料繼續旅行,前往中國四極的第一站──撫遠。進入中國最北邊的省分「黑龍江」,偏遠山區、貧瘠土地、人煙荒蕪,是來此之前對於這片遙遠北國土地的印象。然而,實際來到這裡才驚覺,腳下竟是一塊「捏把黑土冒油花,插雙筷子也發芽」的沃土。上世紀五○年代以前,東北以北是從未被現代化開發的原始大地,人們將它的蒼涼稱之為「北大荒」。在嫩江流域、黑龍江平原、三江平原周邊約五萬多公里的面積土地,不僅有豐沛的水利資源,土壤肥沃程度甚至與烏克蘭大平原、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東北松遼流域齊名為世界三大黑土區。東北平原高含量有機質土壤,隨著五○年代以後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在政府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退伍幹部響應國家政策前往北方拓墾底下,當年的北大荒形象徹底搖身一變,如今儼然成為中國產量最高的農糧之都「北大倉」。
在往撫遠的路上,每天所行駛的三、四百公里距離,往往一天時間也走不出一塊農業屯墾區,公路沿途兩側光景,放眼所及皆是一面相同的水稻田景色。幾萬畝田間布下的初秧,隨著田水映出湛藍天色蕩漾,在曙光農場、前進農場、創業農場、勝利農場這些簡單卻充滿朝氣的農墾區裡,是一幅幅渾然天成的農事畫面。當地農場裡純樸的務農人,手指水田驕傲地說道:「你來的時間太早,田裡的秧苗不過剛剛播下,若再遲上幾個月,等到秋收那才是真正的遍地金黃哪。」我無緣見證豐收時的飽滿,但僅憑眼前一株株密麻的嫩苗,也能想像出秋收拾穗的豐碩場景。
離開北京的第十一天,我抵達中國四極第一站「撫遠」。素有「華夏東極」、「東方第一縣」之稱的撫遠縣,位於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交匯處,與俄羅斯隔江相望,是中國領土最東端的城市。而撫遠縣境內的黑瞎子島,長遠以來更以遺世獨立的神秘性引人矚目。黑瞎子,東北方言裡的「黑熊」之意,在這座一分為二的溼地島嶼上,東側為俄羅斯領地、西側為中國領地。民國初期爆發的中蘇軍事衝突「中東鐵路事件」,戰敗方中國最終簽下《伯力協定》,導致黑瞎子島就此被蘇聯占領。而兩國始終存在有關黑瞎子島的邊界問題,直至二○○四年雙方才達成協議,以十一塊界碑劃分中俄疆土,黑瞎子島的爭議就此落幕。時至今日,黑瞎子島的開發已趨於成熟,遊客登島已是熱門的旅遊觀光項目,兩國國界則以簡單的柵欄與鐵絲隔絕,沒有過去的戰火煙硝,反倒成為雙方最接近彼此的距離。在東方第一縣「撫遠」,由於地理位置因素,是中國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猶然記得初入此地,尚未意識自己早已身處地理東極,在凌晨三點鐘的帳篷裡睡眼矇矓,被外頭一陣強光的照射下驟然驚醒,日出時空的跨越恍若置身一場魔幻夢境。撫遠本地人們的時間,總要比「內地」早上幾個鐘頭,夏至之時,凌晨二點鐘便日光乍現,宣告一種獨特生活作息的開始。這座城市的特殊,除了經驗以外日常生活的萬物運行驚喜,還隱藏著不期而遇的人為驚奇。
在三個多月的旅行計畫,事前準備資金不足以應付每日的住宿開銷,即便百元人民幣左右的廉價旅館,也僅能作為旅途中偶爾奢侈的享受。「一路向東」,是撫遠鎮上唯一的青年旅社,一張三十五塊錢的床位包含熱水澡與被褥,已是旅途中最確切的幸福。在我抵達撫遠前,從未預期如此偏遠小鎮能有廉價住宿,北國一年二季的氣候結構,與冬天零下二十度左右的低溫,實在難以想像有人願意來此經營青年旅社。「一路向東」的店主老王,前年旅行時來到撫遠,停留在這家青旅打工換宿,因緣際會下持著一股衝勁離開家鄉山東,跑到千里之外的撫遠成為「一路向東」的新主人。從他靦腆的笑容中絲毫感受不出身為老闆的成熟穩練,而是對前來投宿的旅人,充滿無微不至的暖心照應。他的前老闆,也就是「一路向東」的催生者,在親手打造完這間內心的夢想青旅以後,短暫經營便辭去漂泊。而年輕的老王,作為當時店裡的一位換宿者,象徵性地以一塊錢從他手中接下「一路向東」。
我訝異著他口中那位實踐夢想爾後歸去的浪子,也感嘆著大老遠跑來極地接手青旅的老王,對於一個旅遊資源並不豐富、遊客人潮也並不多見的地方,他們的存在純粹出於緣分,或者帶著某種使命意義?是一種無價的回饋服務?還是一種關於夢想的執著?或許,給予往來旅人們的感受,更多是一種對「在路上」精神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