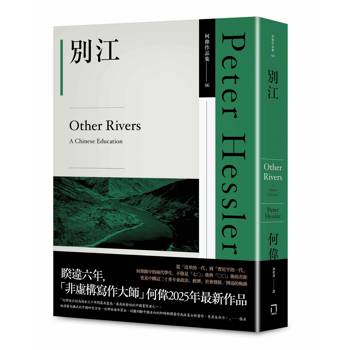第一章 閉門羹(節錄)
做老師最不情願的,就是通知學生說他們沒選上課,而這居然是我在四川大學做的第一件事,甚至我人都還沒踏進校園就幹了。當然,有人會說吃閉門羹對中國年輕人來說,是很尋常的經驗。打從上小學開始,孩子們經歷一連串的考試、排名與淘汰的鍛鍊,已經能處理失敗與失望。對於四川大學這樣的地方來說,就是數字問題:省裡有八千一百萬人,城裡有一千六百萬人,大學裡有七萬人。三十人出現在我的課堂上。課程名稱叫「新聞與非虛構寫作導論」,我之所以選這幾個詞,除了簡潔之外,也是因為它們沒有承諾什麼。鑑於中國當今政治氛圍,我不確定在這樣一堂課上會有什麼可能。
部分選課同學想的是同樣的議題。我任教的第一個學期,有個主修中文的同學從課程名稱裡挑了其中一個詞:「非虛構」,然後寫了一段她自己的介紹:
「在中國,你看到很多事情,(往往)卻不能說出口。要是你在社群平台上貼了敏感的內容,就會被刪掉……對很多事情來說,非虛構的描述已經消失了。即便我是讀文學的,如今我也不曉得怎麼樣用文字表達事實。兩年前,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發生一場大火,十九人喪生。災後,北京市政府展開為期四十天的低端人口清理行動。與此同時,「清理低端人口」在中國變成禁用詞,所有中國媒體都不准報導。我沒有針對這件事寫過文章,它只會永遠存在我的記憶裡。身為中文系學生,我想寫的東西都很難下筆,因為我擔心我寫的東西恐怕會被刪掉。」
想選課的同學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處理這個難題。我要求學生用英文撰寫寫作範本,許多學生交來的是他們在其他課堂寫過的報告。從某些文章的題目可以看出,之所以選上這些主題,是因為距離遙遠或性質模糊,所以不太可能起爭議,像是〈贖罪日戰爭之化解中的新自由主義機制〉、〈澳洲原住民女性作家的生命寫作動機〉。其他學生則反其道而行,找比較貼近自家的主題,但恪守政府的路線,例如一位申請者的文章題目是〈網路審查之必要性〉。恪守意識形態也很安全。一位文學與新聞學院的學生繳了一份對於《包法利夫人》的馬克思主義詮釋。(「資本主義已經打倒法國舊社會的當權派,一定程度上拆解了侷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種阻力。」)另一個學生放棄所有傳統題材,政治、商業、文化、文學統統不要,反而是寫了一篇隱約帶點《聖經人》調調的散文,用五百字的篇幅描述他在學校裡看到的正妹:
「她是花園──她的嫩芽是石榴園,是指甲花、番紅花、菖蒲與肉桂、乳香與沒藥。她是花園中的泉──她是從黎巴嫩流瀉的川流,清澈碧綠,寧靜粼粼……」
我對同學的第一印象是文學的印象:人未到,文字先到。他們的英文稍微偏正式,但不死板,其中不時流露情感與熱情。有時候,他們會道出想大刀闊斧的心思。(「我現在還不到十八歲,活在與世隔絕的象牙塔裡。我期許能有所改變。」)修課的都是大學部學生,大半是在世紀之交出生的。二○一二年,習近平成為中國領導人的時候,他們還是國中生。此後,習近平鞏固權力,是毛澤東時代以來所僅見。到了二○一八年,習近平的憲改廢止了任期限制。在這個習近平有可能終身執政的體制內,這些大學生是第一代成年人。
我上一回到四川當老師是一九九六年的事,當時鄧小平還在世。我一面讀選課申請,一面想像重返課堂會是什麼感覺,同時抄下幾個吸引我目光的句子:
「一個民族唯有知其史,領會其文化,才能得到認同。」
「沙特有言,人受咒詛而為自由。我們有太多選擇要煩惱,卻沒有什麼指點。」
「其實,我們所有人就像大機器中的小螺絲,雖然小,但不可或缺。唯有人人努力工作,我們的國家才能有光明的未來。」
主題的範圍實在太大,根本不可能去比較那些申請書,我只能盡量。我必須把修課人數限制在三十人以內,對於密集寫作課程來說,這樣的人數已經太多了。選完同學之後,我給其他沒選上的同學寄了短信,請他們下學期再申請看看。但有一位沒選上的女生從第一天上課就出現在教室。她坐在靠前排,這應該是我沒注意到她的原因。我本以為想要溜進來的人,會盡量靠後坐。第二週結束,她寄了一封長長的電子郵件,這時我還是不知道她是誰,長什麼樣。
老師好:
我的名字叫瑟蕾娜,是四川大學英文系學生,來信是希望您能允許我以旁聽生的身分來上您星期三晚上的課。我沒有選到課。從第一週開始我都有到教室,我猜想自己出現是可以的。
我想寫作。就像吳爾芙認為只有寫下來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我希望可以做一個熟練的觀察家,在紙上表現生命或理想的形象,就像復活,也像「在不朽的詩句中長生」︙︙我逐漸覺得,作者的用字遣詞不是自然流淌的表達,而是仔細的構思與努力;我開始與那些作者設身處地,要讓自己的耳更敏銳,要聽到寫作之音,包括和諧音或不和諧音、爵士、和弦,終於達到交響。
或許我有點執著,沒有人把我拉出來。若未蒙您允許,我會繼續低調來上課,直到被趕出去。
祝中秋節愉快!
感謝您撥冗。
您真誠的瑟蕾娜
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解釋我不能收旁聽生的原因。但我一直猶豫要不要按下「傳送」。我又讀了一遍瑟蕾娜的信,然後把原本的訊息刪了。我後來寫:
「學校對於旁聽有所疑慮,畢竟這門課必須照顧選到課的同學。但我很欣賞你的積極,想請問你願不願意以正式生的身分上課,繳交所有課程作業?」
我是在違反自己的規矩,但我還是把電子郵件寄出去了。短短三分鐘後,她就回信了。
***
一九九一年,我搬到北京,擔任自由記者。雖然不再教書,但我生活的一部分仍繼續按照中國教育界的行事曆在走。每學期初(九月與二月),我會手寫一批信,寄去四川的幾十個村子與重慶。現在我又回中國住了,以前的學生要回信比較容易。他們用便宜的牛皮紙信封回信,郵戳上的地名我一個都沒聽過:攔江、營耶(音譯)、茶園。大多數學生字寫得很漂亮,他們讀師專時,必須花好幾個小時練傳統的毛筆字。信上優美的字體,跟他們描述中的無情世界大相逕庭:
「學童一點讀書的興致都沒有。我們的故鄉跟現代社會差距太遠,農民擺脫不了窮愚。一連好幾代人用手、用牲口為勞動力來工作過活,而不是用拖拉機。懂得愈少,就變得愈窮。我常常告訴學生,你們一定要學習,不然就改不了笨……政府幹部大多無能,大多所知有限。這在你們美國是無法想像的。當官的只知道吃喝嫖賭、攀關係。」
日子漸久,我跟超過一百個以前的學生保持聯絡。經常寄到我北京辦公室的信件裡,就有吉米的牛皮紙信封。他信上郵戳寫著「江口」。從前的江口又窮又孤立,但沒過多久,吉米的信開始描述一些他以前絕對想不到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有個迷人的妹子來到了我的世界,她當時在一家餐廳工作。我眼裡的她分外吸引我,我愛上她,承諾愛她一輩子。最後在二○○○年三月十五日,我娶了她。結婚前,她開始自己經營一家裝潢很好的餐廳。我的看法是開店很辛苦,但她覺得這是份好工作,可以讓她一展長才。一開始我們欠親戚朋友很多錢。現在我們還開了一家酒店,花了我們十七萬元。很開心餐廳跟酒店都經營得很好……二○○一年九月五日,我們家多了個叫晨曦的寶寶,給我們帶來莫大的滿足。」
信裡內容變化之快,讓人印象深刻。二○○○年代初期,對於貧窮的描述少之又少,捎信來的人提到自己家鄉正在蓋新的高速公路和鐵路。關於錢的細節俯拾皆是:借錢、投資、副業。不時有以前的學生從東南的工廠城鎮來訊,許多農民都遷徙到了當地:
「我之後要去福建。有個親戚在福建福鼎市工作,在那裡的玩具工廠工作時受了傷,正在打官司。最近我們在跟工廠老闆談該賠給我親戚多少錢。我覺得這個地方不只好玩,還比重慶富很多,而且薪水好的工作很好找。」
他們幾乎生來都不具備家庭、財務或地緣上的優勢。但他們有歷史機緣的運,這時間點再好不過了。一九七八年,他們才幾歲大時,鄧小平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我的涪陵學生隨著這些經濟與社會變化長大,成為我後來所認為的「改革一代」的一部分。這一代人加入了人類史上最大的國內遷徙,有兩三億農民搬到城市。到了二○一一年,中國人口正式以城市居民占多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脫貧的人數甚至更多,將近八億人。
不貼近看的話,很難理解這些統計數字對個人層面意味著什麼。但同學的信給了我不同的觀點。二○一六年,一位名叫大衛的同學寫信來道歉,因為以前在一九九○年代,他不是個特別用功的學生。的確,大衛在文學課上經常無精打采,半睡半醒。二十年後,他才終於解釋自己委靡不振的原因:
「有三年時間,我吃不好也睡不好。我還記得在一九九六年,有半年時間我一天只吃一餐。當時我過得不好。但現在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
後來,牛皮紙信封漸漸不敵電子郵件跟簡訊。我的人生也在前進,萊絲莉跟我在西南科羅拉多住了一陣子,我們的雙胞胎女兒愛莉兒(Ariel)與娜塔莎(Natasha)二○一○年就是在那兒出生的。隔年,我們搬到埃及,萊絲莉和我當了五、六年的外電記者。無論我身在哪裡,我都維持著在每個中國學期初寄長信的做法。我一直有個想法,也許過了二十年或者更久,但總有一天我會回到熟悉的長江與烏江口生活。我覺得再度任教於涪陵師專很棒,也很好奇下一代的學生是什麼樣子。
二○一七年,我問起有沒有教學工作。有些舊同事還在校內,他們告訴我校方想聘用我。我提交申請,文件要轉送給重慶教育當局核可,因為涪陵屬重慶管轄。然後,啥都沒有。
在中國有很多種拒絕方式。最簡單的跟錢有關,有句話叫「在商言商」,商場上的拒絕多半直截了當。學術圈也可以很直,尤其中國教育以考試為導向。但假若拒絕的原因是政治,且假若跟外國人有關,那就完全不會有回音。沒有人提到決定是什麼,也沒人給出解釋。沒有魚雁往返,意思就是問題與解決方式都不存在。感覺就像一開始的申請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幾個月的石沉大海過後,我曉得要把事情搞清楚,只能親自走一趟。我從科羅拉多長途跋涉前往涪陵,跟一位有關係的朋友見了面。我問,問題是不是我的寫作?二○○一年,我出版《江城》,寫我在涪陵師專那兩年日子。但朋友保證問題絕對不在那。
「原因是習近平跟薄熙來。」他說。薄熙來是重慶最高的共黨官員,直到在二○一二年涉入爆炸性的醜聞,犯行甚至包括薄熙來之妻主導謀害英國商人一事。薄熙來失勢前,外界本來認為處無期徒刑。
我涪陵的朋友解釋道,自從醜聞之後,重慶的官員就受到國家領導層嚴密關注。他們不太可能核准任何有潛在負面影響的事情,包括任命某外國作家擔任教職。
「只要掌權的還是習近平,」我朋友說,「你就永遠別想在涪陵教書。」
他的口氣有點鬧,彷彿這是中央政治局直接下達的指示。我們頓時相對無語。接著我說:「那習近平身體好嗎?」
「很好!」他放聲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