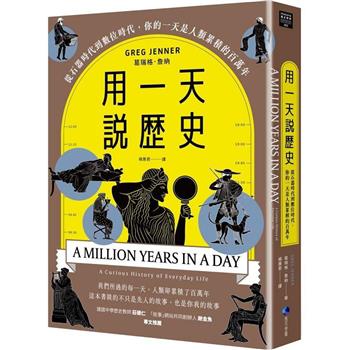11.15 a.m. 遛狗
我們舒舒服服洗了個澡,匆忙套上幾件衣服,正要去休息室的時候,一團流著口水的毛球跳到我們身上,尾巴搖個不停,眼睛閃閃發光。我們凝視這副乞求的表情,登時明白(雖然我們的狗不會說話),牠基本上在說:「我可不可以提醒你有潮濕的網球要撿回來,而且有個白癡(我姑隱其名)把大門鎖上了?」惱人的是牠說得有道理。不只我們要迎接新的一天,我們的寵物也有自己的例行公事。
(中略)
人類最好的朋友
慌張的狗兒拉扯鎖鍊,拚命要拉起綁住牠的柱子,但一點用也沒有。天空布滿黑色的濃煙,熾熱的火山浮岩如大雨降下。狗兒不斷嗚咽,主人不知所蹤,可能是被從山坡下沉的有毒氣體毒死,所以狗兒不停地吠叫,希望有其他人幫牠解開腳鐐。但一個人影也沒有,高達攝氏五百度的熱衝擊波席捲全城,沿途摧枯拉朽,不過幾個小時,屍體和建築物全部消失在二十二公尺的火山灰底下。
如今,這隻龐貝狗(Pompeian dog)悲慘的石膏鑄像仍絕望地蜷縮在柱旁,提醒著我們,西元前七十九年維蘇威火山(Vesuvius)爆發釀成的災難。不過在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和龐貝(Pompeii)挖出的廢墟中,不只發現這一隻狗而已,保存良好的馬賽克地磚刻畫一隻用皮帶牽著的大型黑色獵犬,齜牙咧嘴,一副充滿威脅的表情,腿上長了黑色的長毛。對羅馬及其他許多社會而言,狗是很熟悉的動物。舉個例子,我們知道狗在羅馬農場扮演重要角色,如農民作家尤尼烏斯.墨得拉特斯.科路美拉(Junius Moderatus Columella)建議,牧羊犬應該「兇猛好鬥成性」,而且最好是白色的,才不會在黎明的暮光中被誤認為狼,因此枉送性命。
我們在公園玩你丟我撿時,有個邪惡的搶匪從樹叢跳出來,搶走附近一位女士的皮包。如果我們是在丟飛盤讓寵物貓撿,那牠對這起攻擊事件的反應很可能是興味索然地斜睨一眼;但我們的狗馬上展開行動,齜牙咧嘴地發出刺耳的狂吠,搶匪看到迎面衝來的牙齒導彈,嚇得把皮包一丟,夾起尾巴溜了。
無論在科學上是否屬實,我們覺得狗不但忠心耿耿,還會保護弱小。這不是什麼新鮮事。中世紀的故事就說過狗兒如何守護主人死後的遺體,在極少數的案例裡,法庭甚至在後續的殺人案審判中納入牠們的「證詞」。近代以來,據說希特勒(Adolf Hitl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贊助一所訓練動物的學校,希望能訓練獵犬說話、數數兒,並偵察敵軍。這個指望固然有點過度樂觀──最耀眼的成就是讓小狗聽到有人問「暴君是誰?」的時候,可以吠一聲「希特勒先生」,只不過,聽起來恐怕十之八九比較像是……嗯,基本上,就是狗吠聲。
過去的狗並非全都是必須撲咬闖入者的腳踝、放牧牲畜,或偵察敵軍的役用動物(working animal)。拜尼哈桑(Beni Hasan)的埃及古墓壁畫描繪出好幾種獵犬:適合比賽的灰狗、兇狠的藏獒、短腿的臘腸狗,以及身材修長、尾巴多毛的狐狸,這些狗的肢體特徵大概完全符合牠們各自不同的用途。但這不是說我們的祖先不會飼養毫無用處的雜種狗──牠們發洩精力的方式就是悠閒從容地從一個椅墊跑到另一個椅墊。羅馬貴族婦女特別喜歡毛茸茸的鼻塞小娃兒,像睡著的嬰兒似地窩在她們懷裡,相當於好萊塢電影裡那些養尊處優,從皮包探出頭來的寵物狗。
我們和自己養的狗關係這麼密切,可能是因為我們必須花很多時間照顧牠們。不過,我們幫牠們洗澡,或是帶牠們看獸醫的時候,其實是循著從前許多狗主人的腳步(和爪印)前進。歐洲貴族總是把自己的獵犬保持在最佳狀態,《狩獵之書》(The Book of Hunt)有一幅法國中世紀的插圖,呈現出人類如何清洗狗兒的爪子、用刷子幫牠們梳毛、幫牠們鋪稻草床,以及檢查牠們的牙齒。這些當然不是好養的雜種狗,可以餵牠們吃剩菜,趕到多風的工具間去睡覺。話雖如此,反正不是貴族親自動手,你不會看到滿身泥濘的伯爵手忙腳亂地把一隻容易興奮的小狗按在浴缸裡。
約翰.凱斯(John Caius)一五七○年出版的小冊子《英國犬》(De Canibus Britannicus),證實中世紀英國的狗扮演哪些不同的角色。除了凶猛的獒犬(mastive),可能還會遇到守門的看門犬(keeper)、送信犬(messenger)、對著月亮狂吠的月亮犬(mooner)、轉動井輪的打水犬(water drawer)、背上馱著水桶的運鍋犬(tynckers curre)、一發現有人靠近就汪汪叫的警告犬(warner)、踩在腳踏輪上轉動烤肉軸的轉叉犬(turnspete),以及最好玩的一種,隨著音樂表演的跳舞犬(daunser)。這些林林總總的狗需要各種不同的名字,在十五世紀初期,約克公爵(Duke of York)在他的著作《狩獵大師》(The Master of Game)當中提出了一千一百個名字。這裡無法一一贅述,但我相當喜歡「嗅覺靈敏」(Nosewise)、「賭金全贏」(Swepestake)和「微笑盛宴」(Smylefeste)這幾個名字,雖然我很同情最後被稱為「無名氏」(Nameless)的可憐小狗。說來可愛,一個世紀以後,亨利八世薄命的第二任皇后安堡林(Anne Boleyn),最喜歡的寵物狗叫做「布瓜」(Purkoy),顯然是因為牠臉上總是一副困惑的表情,而「為什麼?」翻譯成中世紀的法文就叫purkoy。
膝下無子的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顯然是一位著名的愛狗人。他養了很多狗,取的名字也同樣多樣化,包括甜嘴唇(Sweet Lips)、真愛(Truelove)、微醺(Tipsy)和醉鬼(Drunkard),聽起來更像是有點飢不擇食的單身男女在交友網站上取的網路名稱。華盛頓是典型的十八世紀紳士,沉迷於打獵,喜愛飼養動物。他在佛農山的莊園裡有許多不同品種的狗兒跑來跑去,包括獵犬、牧羊犬、梗犬、紐芬蘭犬和大麥町犬,其中一隻叫麋鹿夫人(Madame Moose),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還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美國獵狐犬品種,把自家的英格蘭獵狐犬和拉法葉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送給他的幾隻法蘭西獵狐犬配對,生出「有速度、有智慧、有頭腦的優秀狗種」。我也是英格蘭─法蘭西繁殖計畫的產物,年輕的時候跑得很快,但應該稱不上「有智慧」,畢竟我曾經把除草車開進池塘裡。我是說真的。
貓科朋友
如果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那貓就是人類正值青春期的小孩,成天在家裡到處瞎混,心血來潮就往外跑,只對自己想要的東西有興趣。還有人爭論究竟是我們馴化了貓,還是貓馴化了自己。人類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把貓迎進我們的社會?最早的證據出現在塞浦路斯(Cyprus)的希魯洛卡姆波斯(Shillourokambos),是大約九千五百年前留下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家挖到一隻貓,就埋在距離一名男子不到幾吋的地方,如同前面提到的狗墓一樣,表示人類在處理貓的遺體時花了某些心思。貓的年紀很小,可能只有八個月大,骨骼比現代貓長得多,恐怕是一隻野生的貓,因為被馴化的貓通常比較嬌小。
這隻貓(或是牠兩、三代以前的祖先)想必在某一天晃蕩到這個聚落,宰了幾隻老鼠,被心懷感激的農夫深情地撫摸了幾下,赫然發現自己遇到了好運。貓潛伏在人類的聚落,大嚼被穀倉引來的齧齒動物,就這樣不經意地變成了寵物。雖然全球有五種野貓,但所有的家貓都是非洲野貓(Felis silvestris lybica,就是在希魯洛卡姆波斯發現的那種貓)的後裔,所以家貓是九千五百年前那隻狡猾貓咪的直系親屬,也難怪只要我們一不注意,牠們就晃到隔壁人家再吃一頓。
雖然網路使我們對貓咪有種病態的迷戀,但真正祭祀貓的是埃及人,他們把貓製成木乃伊,葬在聖城布巴斯提斯(Bubastis);而且每次有貓離世,他們就剃眉表示哀悼,因為貓是女神巴斯特(Bstet)的象徵。殺貓的人一律處死:希臘作家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曾經描述一名羅馬士兵的馬車意外碾過一隻貓,隨即被憤怒的暴民以私刑處死。埃及對貓十分崇敬,據稱波斯統治者岡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曾經指示他的部隊帶著貓去打培琉喜阿姆戰役(Battle of Pelusium),他知道敵軍埃及基於道德上的原因,不會把箭射向那些無辜的貓咪。
因為貓有潔癖,所以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對貓的喜愛遠勝於狗,另外因為貓是捕鼠專家,因此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偶爾會加以包容。在傑佛瑞.喬叟(Geoffrey Chaucer)所寫的《磨坊主人的故事》(The Miller’s Tale)當中,有個角色跪在地上,透過一扇門往裡面偷窺:「一會兒他找到個洞,這是在牆角下面貓兒常常鑽進鑽出的地方。」這是英國文獻第一次提到貓門,過了沒多久,一四二一年在英格蘭曼徹斯特興建的查塔姆圖書館(Chetham Library)就出現了真正的貓門。在英格蘭的埃克塞特大教堂(Exeter Cathedral),通往鐘塔的門在十七世紀開了一扇貓門,好讓貓進來捕獵咬斷敲鐘索的該死齧齒動物,據說以「滴答滴答滴,老鼠爬上鐘」(Hickory, dickory, dock,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這句歌詞開頭的童謠,就是來自這個典故。
但中世紀有許多人非常討厭貓。日耳曼女修道院長賓根的希爾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認為貓是長了毛皮的傭兵(毛傭?),只忠於餵養牠們的人,其他作家普遍把貓和女性的情慾及賣淫聯想在一起。而且每次只要爆發瘟疫或是獵巫熱,貓就成了代罪羔羊,因為有人把牠們連結到拜祭魔鬼的邪教和異端邪說。卡里特派信徒(Cathars,又稱純潔派,中世紀南歐一個被迫害的教派,信仰善惡二元論),被指控以親吻貓噘起的屁股做為宗教儀式。這是邪惡之吻(osculum infame)的延伸,所謂的邪惡之吻,是女巫熱吻魔鬼裸露的屁股來表示歡迎,而撒旦被認為經常以黑貓的形式出現。
雖然聖路加日(St Luke’s Day)有鞭打或溺死野狗的習俗,但野貓受到的待遇比野狗悲慘得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可能有倒楣的貓被叉在鐵籤上烤來吃(伊萊大教堂在一六四三年發生過這種事)、吊在柱子上、剝皮、折磨或活活溺死。一六七七年,英國新教徒把活貓塞進正在燃燒的教宗雕像的肚子裡,好讓人以為羅馬教皇(他們顯然不是很喜歡羅馬教皇)在被活活燒死的過程中痛苦尖叫。
在科學、理智與聖經語言並行不悖的迷信時代,貓也是女巫的親密伙伴(不能被信任的邪惡動物),而且這種印象是來自牠們和撒旦一樣,喜歡玩弄自己的獵物。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法國人才會幾乎像虐待狂一樣,喜歡用網子捕貓,在夏至這天丟進熊熊燃燒的篝火中。一六四八年的巴黎,法王路易十四甚至被恭請在柴堆點火,然後在當晚一面跳舞享樂,一面看著動物被活生生地燒死,以取悅民眾。
不過,儘管貓在中世紀定期遭到肅清,牠們仍然存活下來,且成為愈來愈受歡迎的寵物。據說牛頓(Isaac Newton)一直很喜歡貓,此外,大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也是百分之百的愛貓人(雖然美國人經常把貓形容成娘娘腔的寵物),而且開開心心地幫他的貓取很可愛的名字,像是酸醪(Sour mash)、阿波利娜(Apollonaris)、懶鬼(Lazy)、押尼珥(Abner)、饑荒(Famine)、單身女子(Fraulein)、水牛比爾(Buffalo Bill)和克利夫蘭(Cleveland)。看來他和喬治.華盛頓有許多共同點。
我們舒舒服服洗了個澡,匆忙套上幾件衣服,正要去休息室的時候,一團流著口水的毛球跳到我們身上,尾巴搖個不停,眼睛閃閃發光。我們凝視這副乞求的表情,登時明白(雖然我們的狗不會說話),牠基本上在說:「我可不可以提醒你有潮濕的網球要撿回來,而且有個白癡(我姑隱其名)把大門鎖上了?」惱人的是牠說得有道理。不只我們要迎接新的一天,我們的寵物也有自己的例行公事。
(中略)
人類最好的朋友
慌張的狗兒拉扯鎖鍊,拚命要拉起綁住牠的柱子,但一點用也沒有。天空布滿黑色的濃煙,熾熱的火山浮岩如大雨降下。狗兒不斷嗚咽,主人不知所蹤,可能是被從山坡下沉的有毒氣體毒死,所以狗兒不停地吠叫,希望有其他人幫牠解開腳鐐。但一個人影也沒有,高達攝氏五百度的熱衝擊波席捲全城,沿途摧枯拉朽,不過幾個小時,屍體和建築物全部消失在二十二公尺的火山灰底下。
如今,這隻龐貝狗(Pompeian dog)悲慘的石膏鑄像仍絕望地蜷縮在柱旁,提醒著我們,西元前七十九年維蘇威火山(Vesuvius)爆發釀成的災難。不過在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和龐貝(Pompeii)挖出的廢墟中,不只發現這一隻狗而已,保存良好的馬賽克地磚刻畫一隻用皮帶牽著的大型黑色獵犬,齜牙咧嘴,一副充滿威脅的表情,腿上長了黑色的長毛。對羅馬及其他許多社會而言,狗是很熟悉的動物。舉個例子,我們知道狗在羅馬農場扮演重要角色,如農民作家尤尼烏斯.墨得拉特斯.科路美拉(Junius Moderatus Columella)建議,牧羊犬應該「兇猛好鬥成性」,而且最好是白色的,才不會在黎明的暮光中被誤認為狼,因此枉送性命。
我們在公園玩你丟我撿時,有個邪惡的搶匪從樹叢跳出來,搶走附近一位女士的皮包。如果我們是在丟飛盤讓寵物貓撿,那牠對這起攻擊事件的反應很可能是興味索然地斜睨一眼;但我們的狗馬上展開行動,齜牙咧嘴地發出刺耳的狂吠,搶匪看到迎面衝來的牙齒導彈,嚇得把皮包一丟,夾起尾巴溜了。
無論在科學上是否屬實,我們覺得狗不但忠心耿耿,還會保護弱小。這不是什麼新鮮事。中世紀的故事就說過狗兒如何守護主人死後的遺體,在極少數的案例裡,法庭甚至在後續的殺人案審判中納入牠們的「證詞」。近代以來,據說希特勒(Adolf Hitl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贊助一所訓練動物的學校,希望能訓練獵犬說話、數數兒,並偵察敵軍。這個指望固然有點過度樂觀──最耀眼的成就是讓小狗聽到有人問「暴君是誰?」的時候,可以吠一聲「希特勒先生」,只不過,聽起來恐怕十之八九比較像是……嗯,基本上,就是狗吠聲。
過去的狗並非全都是必須撲咬闖入者的腳踝、放牧牲畜,或偵察敵軍的役用動物(working animal)。拜尼哈桑(Beni Hasan)的埃及古墓壁畫描繪出好幾種獵犬:適合比賽的灰狗、兇狠的藏獒、短腿的臘腸狗,以及身材修長、尾巴多毛的狐狸,這些狗的肢體特徵大概完全符合牠們各自不同的用途。但這不是說我們的祖先不會飼養毫無用處的雜種狗──牠們發洩精力的方式就是悠閒從容地從一個椅墊跑到另一個椅墊。羅馬貴族婦女特別喜歡毛茸茸的鼻塞小娃兒,像睡著的嬰兒似地窩在她們懷裡,相當於好萊塢電影裡那些養尊處優,從皮包探出頭來的寵物狗。
我們和自己養的狗關係這麼密切,可能是因為我們必須花很多時間照顧牠們。不過,我們幫牠們洗澡,或是帶牠們看獸醫的時候,其實是循著從前許多狗主人的腳步(和爪印)前進。歐洲貴族總是把自己的獵犬保持在最佳狀態,《狩獵之書》(The Book of Hunt)有一幅法國中世紀的插圖,呈現出人類如何清洗狗兒的爪子、用刷子幫牠們梳毛、幫牠們鋪稻草床,以及檢查牠們的牙齒。這些當然不是好養的雜種狗,可以餵牠們吃剩菜,趕到多風的工具間去睡覺。話雖如此,反正不是貴族親自動手,你不會看到滿身泥濘的伯爵手忙腳亂地把一隻容易興奮的小狗按在浴缸裡。
約翰.凱斯(John Caius)一五七○年出版的小冊子《英國犬》(De Canibus Britannicus),證實中世紀英國的狗扮演哪些不同的角色。除了凶猛的獒犬(mastive),可能還會遇到守門的看門犬(keeper)、送信犬(messenger)、對著月亮狂吠的月亮犬(mooner)、轉動井輪的打水犬(water drawer)、背上馱著水桶的運鍋犬(tynckers curre)、一發現有人靠近就汪汪叫的警告犬(warner)、踩在腳踏輪上轉動烤肉軸的轉叉犬(turnspete),以及最好玩的一種,隨著音樂表演的跳舞犬(daunser)。這些林林總總的狗需要各種不同的名字,在十五世紀初期,約克公爵(Duke of York)在他的著作《狩獵大師》(The Master of Game)當中提出了一千一百個名字。這裡無法一一贅述,但我相當喜歡「嗅覺靈敏」(Nosewise)、「賭金全贏」(Swepestake)和「微笑盛宴」(Smylefeste)這幾個名字,雖然我很同情最後被稱為「無名氏」(Nameless)的可憐小狗。說來可愛,一個世紀以後,亨利八世薄命的第二任皇后安堡林(Anne Boleyn),最喜歡的寵物狗叫做「布瓜」(Purkoy),顯然是因為牠臉上總是一副困惑的表情,而「為什麼?」翻譯成中世紀的法文就叫purkoy。
膝下無子的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顯然是一位著名的愛狗人。他養了很多狗,取的名字也同樣多樣化,包括甜嘴唇(Sweet Lips)、真愛(Truelove)、微醺(Tipsy)和醉鬼(Drunkard),聽起來更像是有點飢不擇食的單身男女在交友網站上取的網路名稱。華盛頓是典型的十八世紀紳士,沉迷於打獵,喜愛飼養動物。他在佛農山的莊園裡有許多不同品種的狗兒跑來跑去,包括獵犬、牧羊犬、梗犬、紐芬蘭犬和大麥町犬,其中一隻叫麋鹿夫人(Madame Moose),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還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美國獵狐犬品種,把自家的英格蘭獵狐犬和拉法葉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送給他的幾隻法蘭西獵狐犬配對,生出「有速度、有智慧、有頭腦的優秀狗種」。我也是英格蘭─法蘭西繁殖計畫的產物,年輕的時候跑得很快,但應該稱不上「有智慧」,畢竟我曾經把除草車開進池塘裡。我是說真的。
貓科朋友
如果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那貓就是人類正值青春期的小孩,成天在家裡到處瞎混,心血來潮就往外跑,只對自己想要的東西有興趣。還有人爭論究竟是我們馴化了貓,還是貓馴化了自己。人類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把貓迎進我們的社會?最早的證據出現在塞浦路斯(Cyprus)的希魯洛卡姆波斯(Shillourokambos),是大約九千五百年前留下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家挖到一隻貓,就埋在距離一名男子不到幾吋的地方,如同前面提到的狗墓一樣,表示人類在處理貓的遺體時花了某些心思。貓的年紀很小,可能只有八個月大,骨骼比現代貓長得多,恐怕是一隻野生的貓,因為被馴化的貓通常比較嬌小。
這隻貓(或是牠兩、三代以前的祖先)想必在某一天晃蕩到這個聚落,宰了幾隻老鼠,被心懷感激的農夫深情地撫摸了幾下,赫然發現自己遇到了好運。貓潛伏在人類的聚落,大嚼被穀倉引來的齧齒動物,就這樣不經意地變成了寵物。雖然全球有五種野貓,但所有的家貓都是非洲野貓(Felis silvestris lybica,就是在希魯洛卡姆波斯發現的那種貓)的後裔,所以家貓是九千五百年前那隻狡猾貓咪的直系親屬,也難怪只要我們一不注意,牠們就晃到隔壁人家再吃一頓。
雖然網路使我們對貓咪有種病態的迷戀,但真正祭祀貓的是埃及人,他們把貓製成木乃伊,葬在聖城布巴斯提斯(Bubastis);而且每次有貓離世,他們就剃眉表示哀悼,因為貓是女神巴斯特(Bstet)的象徵。殺貓的人一律處死:希臘作家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曾經描述一名羅馬士兵的馬車意外碾過一隻貓,隨即被憤怒的暴民以私刑處死。埃及對貓十分崇敬,據稱波斯統治者岡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曾經指示他的部隊帶著貓去打培琉喜阿姆戰役(Battle of Pelusium),他知道敵軍埃及基於道德上的原因,不會把箭射向那些無辜的貓咪。
因為貓有潔癖,所以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對貓的喜愛遠勝於狗,另外因為貓是捕鼠專家,因此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偶爾會加以包容。在傑佛瑞.喬叟(Geoffrey Chaucer)所寫的《磨坊主人的故事》(The Miller’s Tale)當中,有個角色跪在地上,透過一扇門往裡面偷窺:「一會兒他找到個洞,這是在牆角下面貓兒常常鑽進鑽出的地方。」這是英國文獻第一次提到貓門,過了沒多久,一四二一年在英格蘭曼徹斯特興建的查塔姆圖書館(Chetham Library)就出現了真正的貓門。在英格蘭的埃克塞特大教堂(Exeter Cathedral),通往鐘塔的門在十七世紀開了一扇貓門,好讓貓進來捕獵咬斷敲鐘索的該死齧齒動物,據說以「滴答滴答滴,老鼠爬上鐘」(Hickory, dickory, dock,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這句歌詞開頭的童謠,就是來自這個典故。
但中世紀有許多人非常討厭貓。日耳曼女修道院長賓根的希爾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認為貓是長了毛皮的傭兵(毛傭?),只忠於餵養牠們的人,其他作家普遍把貓和女性的情慾及賣淫聯想在一起。而且每次只要爆發瘟疫或是獵巫熱,貓就成了代罪羔羊,因為有人把牠們連結到拜祭魔鬼的邪教和異端邪說。卡里特派信徒(Cathars,又稱純潔派,中世紀南歐一個被迫害的教派,信仰善惡二元論),被指控以親吻貓噘起的屁股做為宗教儀式。這是邪惡之吻(osculum infame)的延伸,所謂的邪惡之吻,是女巫熱吻魔鬼裸露的屁股來表示歡迎,而撒旦被認為經常以黑貓的形式出現。
雖然聖路加日(St Luke’s Day)有鞭打或溺死野狗的習俗,但野貓受到的待遇比野狗悲慘得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可能有倒楣的貓被叉在鐵籤上烤來吃(伊萊大教堂在一六四三年發生過這種事)、吊在柱子上、剝皮、折磨或活活溺死。一六七七年,英國新教徒把活貓塞進正在燃燒的教宗雕像的肚子裡,好讓人以為羅馬教皇(他們顯然不是很喜歡羅馬教皇)在被活活燒死的過程中痛苦尖叫。
在科學、理智與聖經語言並行不悖的迷信時代,貓也是女巫的親密伙伴(不能被信任的邪惡動物),而且這種印象是來自牠們和撒旦一樣,喜歡玩弄自己的獵物。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法國人才會幾乎像虐待狂一樣,喜歡用網子捕貓,在夏至這天丟進熊熊燃燒的篝火中。一六四八年的巴黎,法王路易十四甚至被恭請在柴堆點火,然後在當晚一面跳舞享樂,一面看著動物被活生生地燒死,以取悅民眾。
不過,儘管貓在中世紀定期遭到肅清,牠們仍然存活下來,且成為愈來愈受歡迎的寵物。據說牛頓(Isaac Newton)一直很喜歡貓,此外,大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也是百分之百的愛貓人(雖然美國人經常把貓形容成娘娘腔的寵物),而且開開心心地幫他的貓取很可愛的名字,像是酸醪(Sour mash)、阿波利娜(Apollonaris)、懶鬼(Lazy)、押尼珥(Abner)、饑荒(Famine)、單身女子(Fraulein)、水牛比爾(Buffalo Bill)和克利夫蘭(Cleveland)。看來他和喬治.華盛頓有許多共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