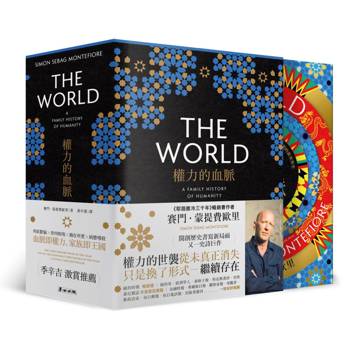前言
潮退,足跡露出。在今日東英格蘭境內小村黑斯堡(Happisburgh)的海灘上,可見某家族走過留下的腳印。腳印共五組,大概是一男子、四小孩所留下,距今九十五萬至八十五萬年。這些腳印於二〇一三年發現,為歷來所知最古老的家族腳印。但並非是最早的足跡:在人類發源地非洲已發現更古老的了。但黑斯堡腳印是一家人所留下的最古老足跡,動筆撰寫這部世界史,正出於它們的啟發。
世上已有多部世界史,而本書採用新手法,利用家族在漫長歲月裡的事蹟,提供一個不同且嶄新的視角。我心儀於這個手法,因為可以把重大事件和個人曲折的際遇連結在一起,時間範圍涵蓋從最早的古人類(hominin)至今,從削尖的石頭至iPhone和無人機時代。世界史是紛亂時代的靈丹妙藥:其優點在於讓人從長遠視角觀照世局;缺點則是時空距離太遙遠。世界史往往有主題,而沒有人的蹤影;傳記有人,沒有主題。
家族始終是人類基本的存在單位──即使在人工智慧和星際大戰時代亦然。我講述每個時期、每個大陸上諸多家族的故事,以此織就歷史,試圖錨定其不斷奔騰向前的腳步。這本書談的是許多人而非一人的生平際遇。即使這些家族的足跡遍及全球,他們的曲折際遇依舊是非常個人的──生、死、婚、愛、恨;他們崛起;垮臺;東山再起;遷徙;回到故土。在每齣家族大戲裡都有許多幕。那就是當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說,每個王國都是個家族,每個家族都是個小王國時,他所要表達的意思。
與伴隨我成長的許多歷史書不同的是,這是道道地地的世界歷史書,未因為過度著墨於英國和歐洲而有失公允,反倒給予亞洲、非洲、美洲應有的關注。把重點放在家族上,也使我們得以更加關注女性、孩童的際遇,而在我小時候所讀的書裡,女性、孩童無不受到輕忽。他們的角色──一如家族本身的樣貌──與時俱變。我的目標是讓世人認識歷史的囟門如何閉合。
家族一詞給人溫馨、溫情之感,但在現實生活中,家族當然也可能是鬥爭、酷行充斥之地。我筆下的諸多家族有權有勢,家族中源於撫養和愛的親情和溫情,同時被無情的政治算計所滲透和扭曲。在權勢家族,危險來自關係的親密。誠如韓非子在西元前三世紀的中國向其君主所勸誡的,「禍在所愛」。
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瑞寫道,「當其他每個人都在犁田、提水桶時,很少人會致力於歷史。」我所挑選的那些家族,大多是行使權力的家族,但其他家族包含奴隸、醫生、畫家、小說家、劊子子、將軍、歷史學家、教士、江湖術士、科學家、大亨、犯罪分子──以及戀愛中的人。甚至有一些神。
有些家族將家喻戶曉,但有許多家族不是:在此書中,我們講述了的王朝包括馬利、大明、梅迪奇和穆塔帕(Mutapa)、達荷美、阿曼、阿富汗、柬埔寨、巴西、伊朗、海地、夏威夷、哈布斯堡;講述了成吉思汗、孫賈塔.凱塔(Sundiata Keita)、武后、艾烏瓦雷一世(Ewuare the Great)、恐怖伊凡、金正恩、伊茨科阿特爾(Itzcoatl)、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海地國王亨利、甘加.尊巴(Ganga Zumba)、德皇威廉、英迪拉.甘地、索布扎(Sobhuza)、帕恰庫蒂.印加(Pachacuti Inca)、希特勒,以及肯亞塔家族、卡斯楚家族、阿薩德家族、川普家族、克麗奧佩脫拉、戴高勒、何梅尼、戈巴契夫、瑪麗.安托瓦內特、傑佛遜、納迪爾(Nader)、毛澤東、歐巴馬;莫札特、巴爾札克、米開朗基羅;凱撒家族、蒙兀兒王朝、紹德家族、羅斯福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斐勒家族、鄂圖曼人。
駭人之事與溫馨親情並存。有許多慈愛的父親、母親,卻也有綽號「胖子」(fatso)的托勒密八世肢解了自己的兒子,再派人把屍塊送去給兒子的母親;納迪爾.沙和皇后艾瑞絲(Iris)弄瞎幾個兒子;王后伊莎貝拉折磨女兒;查理曼大帝可能和女兒不倫;在鄂圖曼帝國掌握大權的女人科塞姆(Kösem)下令絞死兒子,後來被孫子下令絞死;瓦盧瓦王朝統治者凱撒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親手策畫女兒婚禮時的屠殺行動,而且對於女兒遭誘姦或被自己幾個哥哥強暴一事,她似乎予以容忍;尼祿和生母不倫,後來又殺了她。夏卡(Shaka)殺了母親,接著以此為藉口大開殺戒。薩達姆.海珊縱放兒子對付女婿。殘殺兄弟之事屢見不鮮──即使今日亦然:幾年前,金正恩謀殺兄長,而且手法很現代,以電視實境秀整人手法為幌子,運用神經毒劑殺害。
本書也講述了十幾歲女孩的悲慘遭遇。她們奉冷酷的父母之命遠嫁異邦陌生人,然後在異鄉難產而死;有時她們的婚姻有助於強化國與國的關係,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她們受了苦,卻鮮少達到目的,因為家族關係徹底不敵國家利益。本書也談到奴隸出身但攀上帝國統治者之位的女人──如鄂圖曼帝國的柯塞姆蘇丹(Kösem);又如莎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她是總統托瑪斯.傑佛遜的亡妻的同父異母妹,本身為奴隸,偷偷懷了這位總統的孩子;德里蘇丹國的統治者拉齊亞(Razia)掌握實權,但因為和一名非洲籍將領的親密關係而失勢;在安達盧斯(al-Andalus),哈里發的女兒瓦拉妲(Wallada)成為女詩人,一個我行我素的人。我們跟隨所選出的家族經歷大流行病、戰爭、水災、經濟榮景,勾畫出女人的生命遭遇,從村子到統治大位,再走向工廠到總理之位;從驚人的母親死亡率、法律上無權自主到有權投票、有權墮胎、有權避孕。同時也描繪孩童際遇的變化,從高得令人不安的孩童死亡率到工業化勞動再到兒童權益至上的現代。
這是本把重點擺在個人、家族、小圈子的歷史書。當然還有多種方法可用以探討這類範疇的歷史。而我是專攻權力的歷史學家;地緣政治又是推動世界史的引擎,而我已把大半職業生涯用於書寫俄羅斯領導人,而這正是我一直喜歡閱讀的那種歷史──其中包含激情和憤怒,充滿想像力和感官之娛,還有在純經濟學、政治學的論文裡見不到的日常生活的真切樣貌。把人與人的關聯性放在中心位置,係講述全球故事的一種方法,而且此法說明了政治、經濟、技術方面之改變所帶來的衝擊,同時揭露家族有何演變。這本書是結構與能動性、非人之力與人之特性間的漫長較量裡的又一回合。但這些未必有其排他性。馬克思寫道,「人創造自身的歷史,但非隨心所欲創造歷史;人不在自己選定的情況下創造歷史,而是在已存在的、特定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情況下創造歷史。」因此,歷史往往呈現為斷斷續續的一連串事件、革命、典範(paradigm),而且經歷這些事件、革命、典範者是被清楚分類且身分非常明確的人。只是,在真實世界裡的家族生活往往透露出不同於此的景象──在分層的、混雜的、閾限的、紛然雜陳的且使後人無法將其中之人分類、確定身分的世界裡,具有個人特有氣質的、與眾不同之人,在數十年、數百年的歲月裡生活、大笑、愛人。
我在本書所談的家族和人物往往迥異於常人,但他們也揭露了關於他們所處時代和地方的諸多事態。這是審視王國和國家如何演變,人與人的關聯性如何發展,不同的社會如何吸納外人、與之合併的方式之一。我希望,這種同時並陳卻也獨特的敘事手法能立即捕捉到現實生活裡毫無條理可言的不可預測性和偶然性,傳達出同時有許多事在不同地方、不同軌道上發生的感受,如一場令人不知所措、間歇性的、一往無前的衝鋒陷陣般的騷動和混亂,往往既殘酷又荒謬,但始終充斥著令人猝不及防的意外變化、離奇的偶發事件和沒人能預見的奇人異士。為何最成功的領導者是高瞻遠矚者,是卓越的戰略家,卻也是善於臨機應變者、機會主義者、不免失手且受運氣左右之人,原因在此。俾斯麥坦承,「就連世上最精明的人,都像個小孩走進黑暗裡。」歷史是由觀念、制度、地緣政治交織而成。這三者恰如其分的一起發力時,大改變即發生。但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冒險睹一把的,也是人……
本書同時談核心家族(inner family),以及更廣大的權勢家族,其往往擴展為氏族和部族。從生物學角度而言,核心家族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個實體,若從親代撫育的角度來說,對我們之中的多數人亦是,而且不管養育多麼失職皆然;更廣大的王朝則是以信賴和家系為膠合物,藉以把持權力、保護財富、分攤風險的建構物。而我們所有人出於本能地理解這兩種家族:從許多方面來看,我們都是王朝的成員,而王朝這部家族史是我們所有人的編年史。只是,統治家族所展開的手段相對致命,他們若保不住權位,必須付出的代價更是致命。
在歐洲和美國,我們往往把家族看成在個人主義、大眾政治、工業化、高科技的時代已不具政治重要性的小單位,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家族。這話不無道理,而在歷史的較後期,家族已呈現不同的面貌,尤以在西方為然。碰到已無顯赫家族的時代,我繼續使用性格和關聯性來拴住複雜的敘事,然事實表明,在當今個人主義當道且據稱理性的世界裡,竟有王朝發展出來,而且並未消失。根本未消失。
在今日的自由民主國家裡,我們自豪於純粹、理性且沒有氏族、親屬介入、不講私人關係的政治。家族的分量的確遠不如從前。只是大部分政治活動依舊既著眼於政治,也同樣程度著眼於人和恩庇。現代國家的錯綜複雜程度,比我們所樂於佯稱的還要高,理性程度則比我們所樂於佯稱的還要低,就連在北美、西歐的自由民主國家亦然:非正式網絡和包括家族在內的私領域(personal court),往往略過正規制度:在民主國家或半民主國家,只消想起甘迺迪家族和布希家族、肯亞塔家族和哈瑪家族(Khamas)、尼赫魯家族、布托家族和沙里夫家族(Sharifs)、新加坡李家和馬可士家。這些是意味著安心和延續性卻必須經由民選才能掌權(而且也可能落選)的民主王朝(demo-dynasty)。在今日美國、印度、日本境內所做的研究顯示,在國會議員家族、州政治家族裡,出現了同樣的全國性王朝。而且在亞洲和非洲,世襲性統治者愈來愈多,這些統治者以共和政體為幌子,實際上形同君王。
本書寫於寫史這門行業出現令人振奮且長期遭到延誤的一個新變化之際:著眼於亞洲、非洲的民族;政治、語言、文化的相互關聯性;著重女性角色和種族多元性。只是歷史已變得如同打火機一般,其道德威力既能立即點燃照亮知識的火炬,也能燃起失控的無知之火。只消瞧一眼推特、臉書上讓人極度反感的情況,聽聽推特、臉書上令人不適的偏見和陰謀論,就會知道由於數位扭曲,歷史愈來愈容易支離碎裂。歷史兼具科學、文學、神祕主義、倫理學的性質,始終非常重要,因為歷史,不管是光輝燦爛,還是令人動容的苦難,不管其中想像的成分有多高,都具有某種正當性、真實性,乃至神聖性,早己深植於我們之中──而且往往透過家族、民族的故事表達出來。歷史能以無聲的千軍威力打動無數人,能創造民族,能把殺戮和英勇、專制和自由合理化。為何在其最理想的狀況下,其追求真相之舉是不可或缺,原因在此。每個意識形態、宗教、帝國都想要控制神聖不可侵犯的過去,以賦予它們當下的任何作為以正當性。如今,在東西方,出現許多欲把歷史強塞入意識形態的舉動。
古老幼稚的「好人」、「壞人」歷史再度盛行,儘管當今的「好人」、「壞人」不同於以往。但誠如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所指出的,「虛構的過去永遠不管用;在生活的壓力下,其裂縫和易碎的質地在旱季時如同泥土。」最明顯的線索是使用亂無章法的術語一事。誠如傅柯所寫的,意識形態術語是脅迫性術語的表徵:「它動輒對其他論述施以某種壓力和類似約束力的東西」,因為術語讓人看不到事實根據的付諸闕如,令異議者噤聲,使勾結者有機會炫耀他們符合道德的傳統作法。講話常常一針見血的傅柯問道,「追求真相時,追求發出這個『真』論述時,人可能失去的東西,如果不是欲求和權力,還會是什麼?」鮑德溫示警道,「沒人比自認內心純潔之人更危險:因為既是純潔,顧名思義,就是無懈可擊。」歷史的意識形態,一碰上現實生活的亂無章法、微妙差異、錯綜複雜,鮮少能夠站得住腳。傅柯指出,「由權力構成的個人,本身同時是權力的工具。」
書寫歷史必然會對歷史的黑暗面──戰爭、罪行、暴力、奴役、壓迫等──多所著墨,因為這些是人所不樂見卻又無法改變的事物,它們是改變的動力。黑格爾寫道,歷史是「以人的福為祭品的屠宰臺」。戰爭始終具有加速進程的作用:九世紀伊拉克詩人阿布.坦瑪姆.伊本.奧斯(Abu Tammam ibn Aws)寫道,「劍所道出的真相多於書所道出者,劍刃使智慧和自大判然兩分。」「知識在長矛的閃光裡找到。」托洛茨基寫道,每支軍隊都是「社會的翻版,苦於社會的種種疾病,而且通常情緒更是高張」。帝國──具有中央集權統治、大陸版塊、遼闊版圖、多種民族的政治實體──無所不在,而且以多種形態呈現:數千年來構成定居型社會隱患的馬上游牧民所打造的乾草原帝國,大不同於西元一五〇〇至一九六〇年支配世界的歐洲人跨洋帝國。有些帝國是一個征服者或某種願景的傑作,但大部分帝國的征服和統治,係出於形勢的推動,而非事先計畫的作為,而且行動方式形形色色。如今爭奪天下者是「帝國型國家」(empire nation)──以中國、美國、俄羅斯為各陣營首領──它們既具有國家的聚合力,也擁有遼闊的帝國,令人敬畏的量體,往往是大陸型量體。在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得到新的極端民族主義加持,控制世上最大的帝國型國家──而且帶來致命後果。地緣政治較量──教皇尤利烏斯二世所謂的「世界博奕」──無法止息;成功始終只是一時,為此付出的人命代價始終太高。
許多罪行遭到忽略、隱瞞,勢必也遭到完全的掩蓋。在本書中,我的用意是寫下一部透顯微妙差異的歷史,在其中如實呈現人和其政治實體的複雜、缺陷、鼓舞人心之處。治療過去罪行的良藥是投以最明亮的光,使其無所遁形;一旦這些罪行已非法網所能懲治,這一揭露便是最真的挽救,唯一算數的挽救。本書意在投出那道光:按事件發生的順序道出成就和罪行,不管其造作者是誰。我想要盡可能多講述那些遇害的、受奴役的或受壓迫的無辜者的故事: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又或者沒有任何人是重要的。
如今我們有幸擁有令人振奮的新科學方法──碳十四定年法、DNA、語言年代學──使我們有機會發掘更多過去的真相,說明人透過地球暖化和污染給地球帶來的傷害。但即使有這些新工具,歷史基本上還是在講人。撰寫此書前,我最後一次旅行的地點是埃及:當我看到法尤姆(Fayum)墓室肖像的生動面容,我心裡想著,這些西元一世紀的人長得真像我們。他們及其家人的確和今日的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但差異同樣鮮明。如今,我們往往幾乎不了解我們熟知的人。而歷史的第一道法便是意識到對於過去的人、他們的想法、他們家族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
寫史時要避免流於目的論,勿以為歷史的結果始終為人所知,這些並不容易。歷史學家拙於預測未來,但當他們已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時,則善於預測未來。不過,與其說歷史學家是按事件發生順序記錄過去者或預見未來者,不如說只是映照其當下所處時刻的鏡子。要了解過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甩開現在:我們的職責是利用我們所知的一切事物尋找事實,以說明過去數代人的生活──全世界居高位者和居下位者的生活。
馬蘇迪(al-Masudi)於九世紀的巴格達寫道,世界史的史家就像「一個已找到各種樣式、顏色的珍珠,把它們串成一條項鍊,打造成一件得到其主人細心守護的飾物的人」。這正是我想書寫的世界史。
那一家人在黑斯堡海灘留下的腳印不久就被潮水沖掉,卻是在此之後的數十萬年,我們所謂的歷史方才展開。
(節錄自《權力的血脈》)
潮退,足跡露出。在今日東英格蘭境內小村黑斯堡(Happisburgh)的海灘上,可見某家族走過留下的腳印。腳印共五組,大概是一男子、四小孩所留下,距今九十五萬至八十五萬年。這些腳印於二〇一三年發現,為歷來所知最古老的家族腳印。但並非是最早的足跡:在人類發源地非洲已發現更古老的了。但黑斯堡腳印是一家人所留下的最古老足跡,動筆撰寫這部世界史,正出於它們的啟發。
世上已有多部世界史,而本書採用新手法,利用家族在漫長歲月裡的事蹟,提供一個不同且嶄新的視角。我心儀於這個手法,因為可以把重大事件和個人曲折的際遇連結在一起,時間範圍涵蓋從最早的古人類(hominin)至今,從削尖的石頭至iPhone和無人機時代。世界史是紛亂時代的靈丹妙藥:其優點在於讓人從長遠視角觀照世局;缺點則是時空距離太遙遠。世界史往往有主題,而沒有人的蹤影;傳記有人,沒有主題。
家族始終是人類基本的存在單位──即使在人工智慧和星際大戰時代亦然。我講述每個時期、每個大陸上諸多家族的故事,以此織就歷史,試圖錨定其不斷奔騰向前的腳步。這本書談的是許多人而非一人的生平際遇。即使這些家族的足跡遍及全球,他們的曲折際遇依舊是非常個人的──生、死、婚、愛、恨;他們崛起;垮臺;東山再起;遷徙;回到故土。在每齣家族大戲裡都有許多幕。那就是當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說,每個王國都是個家族,每個家族都是個小王國時,他所要表達的意思。
與伴隨我成長的許多歷史書不同的是,這是道道地地的世界歷史書,未因為過度著墨於英國和歐洲而有失公允,反倒給予亞洲、非洲、美洲應有的關注。把重點放在家族上,也使我們得以更加關注女性、孩童的際遇,而在我小時候所讀的書裡,女性、孩童無不受到輕忽。他們的角色──一如家族本身的樣貌──與時俱變。我的目標是讓世人認識歷史的囟門如何閉合。
家族一詞給人溫馨、溫情之感,但在現實生活中,家族當然也可能是鬥爭、酷行充斥之地。我筆下的諸多家族有權有勢,家族中源於撫養和愛的親情和溫情,同時被無情的政治算計所滲透和扭曲。在權勢家族,危險來自關係的親密。誠如韓非子在西元前三世紀的中國向其君主所勸誡的,「禍在所愛」。
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瑞寫道,「當其他每個人都在犁田、提水桶時,很少人會致力於歷史。」我所挑選的那些家族,大多是行使權力的家族,但其他家族包含奴隸、醫生、畫家、小說家、劊子子、將軍、歷史學家、教士、江湖術士、科學家、大亨、犯罪分子──以及戀愛中的人。甚至有一些神。
有些家族將家喻戶曉,但有許多家族不是:在此書中,我們講述了的王朝包括馬利、大明、梅迪奇和穆塔帕(Mutapa)、達荷美、阿曼、阿富汗、柬埔寨、巴西、伊朗、海地、夏威夷、哈布斯堡;講述了成吉思汗、孫賈塔.凱塔(Sundiata Keita)、武后、艾烏瓦雷一世(Ewuare the Great)、恐怖伊凡、金正恩、伊茨科阿特爾(Itzcoatl)、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海地國王亨利、甘加.尊巴(Ganga Zumba)、德皇威廉、英迪拉.甘地、索布扎(Sobhuza)、帕恰庫蒂.印加(Pachacuti Inca)、希特勒,以及肯亞塔家族、卡斯楚家族、阿薩德家族、川普家族、克麗奧佩脫拉、戴高勒、何梅尼、戈巴契夫、瑪麗.安托瓦內特、傑佛遜、納迪爾(Nader)、毛澤東、歐巴馬;莫札特、巴爾札克、米開朗基羅;凱撒家族、蒙兀兒王朝、紹德家族、羅斯福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斐勒家族、鄂圖曼人。
駭人之事與溫馨親情並存。有許多慈愛的父親、母親,卻也有綽號「胖子」(fatso)的托勒密八世肢解了自己的兒子,再派人把屍塊送去給兒子的母親;納迪爾.沙和皇后艾瑞絲(Iris)弄瞎幾個兒子;王后伊莎貝拉折磨女兒;查理曼大帝可能和女兒不倫;在鄂圖曼帝國掌握大權的女人科塞姆(Kösem)下令絞死兒子,後來被孫子下令絞死;瓦盧瓦王朝統治者凱撒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親手策畫女兒婚禮時的屠殺行動,而且對於女兒遭誘姦或被自己幾個哥哥強暴一事,她似乎予以容忍;尼祿和生母不倫,後來又殺了她。夏卡(Shaka)殺了母親,接著以此為藉口大開殺戒。薩達姆.海珊縱放兒子對付女婿。殘殺兄弟之事屢見不鮮──即使今日亦然:幾年前,金正恩謀殺兄長,而且手法很現代,以電視實境秀整人手法為幌子,運用神經毒劑殺害。
本書也講述了十幾歲女孩的悲慘遭遇。她們奉冷酷的父母之命遠嫁異邦陌生人,然後在異鄉難產而死;有時她們的婚姻有助於強化國與國的關係,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她們受了苦,卻鮮少達到目的,因為家族關係徹底不敵國家利益。本書也談到奴隸出身但攀上帝國統治者之位的女人──如鄂圖曼帝國的柯塞姆蘇丹(Kösem);又如莎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她是總統托瑪斯.傑佛遜的亡妻的同父異母妹,本身為奴隸,偷偷懷了這位總統的孩子;德里蘇丹國的統治者拉齊亞(Razia)掌握實權,但因為和一名非洲籍將領的親密關係而失勢;在安達盧斯(al-Andalus),哈里發的女兒瓦拉妲(Wallada)成為女詩人,一個我行我素的人。我們跟隨所選出的家族經歷大流行病、戰爭、水災、經濟榮景,勾畫出女人的生命遭遇,從村子到統治大位,再走向工廠到總理之位;從驚人的母親死亡率、法律上無權自主到有權投票、有權墮胎、有權避孕。同時也描繪孩童際遇的變化,從高得令人不安的孩童死亡率到工業化勞動再到兒童權益至上的現代。
這是本把重點擺在個人、家族、小圈子的歷史書。當然還有多種方法可用以探討這類範疇的歷史。而我是專攻權力的歷史學家;地緣政治又是推動世界史的引擎,而我已把大半職業生涯用於書寫俄羅斯領導人,而這正是我一直喜歡閱讀的那種歷史──其中包含激情和憤怒,充滿想像力和感官之娛,還有在純經濟學、政治學的論文裡見不到的日常生活的真切樣貌。把人與人的關聯性放在中心位置,係講述全球故事的一種方法,而且此法說明了政治、經濟、技術方面之改變所帶來的衝擊,同時揭露家族有何演變。這本書是結構與能動性、非人之力與人之特性間的漫長較量裡的又一回合。但這些未必有其排他性。馬克思寫道,「人創造自身的歷史,但非隨心所欲創造歷史;人不在自己選定的情況下創造歷史,而是在已存在的、特定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情況下創造歷史。」因此,歷史往往呈現為斷斷續續的一連串事件、革命、典範(paradigm),而且經歷這些事件、革命、典範者是被清楚分類且身分非常明確的人。只是,在真實世界裡的家族生活往往透露出不同於此的景象──在分層的、混雜的、閾限的、紛然雜陳的且使後人無法將其中之人分類、確定身分的世界裡,具有個人特有氣質的、與眾不同之人,在數十年、數百年的歲月裡生活、大笑、愛人。
我在本書所談的家族和人物往往迥異於常人,但他們也揭露了關於他們所處時代和地方的諸多事態。這是審視王國和國家如何演變,人與人的關聯性如何發展,不同的社會如何吸納外人、與之合併的方式之一。我希望,這種同時並陳卻也獨特的敘事手法能立即捕捉到現實生活裡毫無條理可言的不可預測性和偶然性,傳達出同時有許多事在不同地方、不同軌道上發生的感受,如一場令人不知所措、間歇性的、一往無前的衝鋒陷陣般的騷動和混亂,往往既殘酷又荒謬,但始終充斥著令人猝不及防的意外變化、離奇的偶發事件和沒人能預見的奇人異士。為何最成功的領導者是高瞻遠矚者,是卓越的戰略家,卻也是善於臨機應變者、機會主義者、不免失手且受運氣左右之人,原因在此。俾斯麥坦承,「就連世上最精明的人,都像個小孩走進黑暗裡。」歷史是由觀念、制度、地緣政治交織而成。這三者恰如其分的一起發力時,大改變即發生。但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冒險睹一把的,也是人……
本書同時談核心家族(inner family),以及更廣大的權勢家族,其往往擴展為氏族和部族。從生物學角度而言,核心家族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個實體,若從親代撫育的角度來說,對我們之中的多數人亦是,而且不管養育多麼失職皆然;更廣大的王朝則是以信賴和家系為膠合物,藉以把持權力、保護財富、分攤風險的建構物。而我們所有人出於本能地理解這兩種家族:從許多方面來看,我們都是王朝的成員,而王朝這部家族史是我們所有人的編年史。只是,統治家族所展開的手段相對致命,他們若保不住權位,必須付出的代價更是致命。
在歐洲和美國,我們往往把家族看成在個人主義、大眾政治、工業化、高科技的時代已不具政治重要性的小單位,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家族。這話不無道理,而在歷史的較後期,家族已呈現不同的面貌,尤以在西方為然。碰到已無顯赫家族的時代,我繼續使用性格和關聯性來拴住複雜的敘事,然事實表明,在當今個人主義當道且據稱理性的世界裡,竟有王朝發展出來,而且並未消失。根本未消失。
在今日的自由民主國家裡,我們自豪於純粹、理性且沒有氏族、親屬介入、不講私人關係的政治。家族的分量的確遠不如從前。只是大部分政治活動依舊既著眼於政治,也同樣程度著眼於人和恩庇。現代國家的錯綜複雜程度,比我們所樂於佯稱的還要高,理性程度則比我們所樂於佯稱的還要低,就連在北美、西歐的自由民主國家亦然:非正式網絡和包括家族在內的私領域(personal court),往往略過正規制度:在民主國家或半民主國家,只消想起甘迺迪家族和布希家族、肯亞塔家族和哈瑪家族(Khamas)、尼赫魯家族、布托家族和沙里夫家族(Sharifs)、新加坡李家和馬可士家。這些是意味著安心和延續性卻必須經由民選才能掌權(而且也可能落選)的民主王朝(demo-dynasty)。在今日美國、印度、日本境內所做的研究顯示,在國會議員家族、州政治家族裡,出現了同樣的全國性王朝。而且在亞洲和非洲,世襲性統治者愈來愈多,這些統治者以共和政體為幌子,實際上形同君王。
本書寫於寫史這門行業出現令人振奮且長期遭到延誤的一個新變化之際:著眼於亞洲、非洲的民族;政治、語言、文化的相互關聯性;著重女性角色和種族多元性。只是歷史已變得如同打火機一般,其道德威力既能立即點燃照亮知識的火炬,也能燃起失控的無知之火。只消瞧一眼推特、臉書上讓人極度反感的情況,聽聽推特、臉書上令人不適的偏見和陰謀論,就會知道由於數位扭曲,歷史愈來愈容易支離碎裂。歷史兼具科學、文學、神祕主義、倫理學的性質,始終非常重要,因為歷史,不管是光輝燦爛,還是令人動容的苦難,不管其中想像的成分有多高,都具有某種正當性、真實性,乃至神聖性,早己深植於我們之中──而且往往透過家族、民族的故事表達出來。歷史能以無聲的千軍威力打動無數人,能創造民族,能把殺戮和英勇、專制和自由合理化。為何在其最理想的狀況下,其追求真相之舉是不可或缺,原因在此。每個意識形態、宗教、帝國都想要控制神聖不可侵犯的過去,以賦予它們當下的任何作為以正當性。如今,在東西方,出現許多欲把歷史強塞入意識形態的舉動。
古老幼稚的「好人」、「壞人」歷史再度盛行,儘管當今的「好人」、「壞人」不同於以往。但誠如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所指出的,「虛構的過去永遠不管用;在生活的壓力下,其裂縫和易碎的質地在旱季時如同泥土。」最明顯的線索是使用亂無章法的術語一事。誠如傅柯所寫的,意識形態術語是脅迫性術語的表徵:「它動輒對其他論述施以某種壓力和類似約束力的東西」,因為術語讓人看不到事實根據的付諸闕如,令異議者噤聲,使勾結者有機會炫耀他們符合道德的傳統作法。講話常常一針見血的傅柯問道,「追求真相時,追求發出這個『真』論述時,人可能失去的東西,如果不是欲求和權力,還會是什麼?」鮑德溫示警道,「沒人比自認內心純潔之人更危險:因為既是純潔,顧名思義,就是無懈可擊。」歷史的意識形態,一碰上現實生活的亂無章法、微妙差異、錯綜複雜,鮮少能夠站得住腳。傅柯指出,「由權力構成的個人,本身同時是權力的工具。」
書寫歷史必然會對歷史的黑暗面──戰爭、罪行、暴力、奴役、壓迫等──多所著墨,因為這些是人所不樂見卻又無法改變的事物,它們是改變的動力。黑格爾寫道,歷史是「以人的福為祭品的屠宰臺」。戰爭始終具有加速進程的作用:九世紀伊拉克詩人阿布.坦瑪姆.伊本.奧斯(Abu Tammam ibn Aws)寫道,「劍所道出的真相多於書所道出者,劍刃使智慧和自大判然兩分。」「知識在長矛的閃光裡找到。」托洛茨基寫道,每支軍隊都是「社會的翻版,苦於社會的種種疾病,而且通常情緒更是高張」。帝國──具有中央集權統治、大陸版塊、遼闊版圖、多種民族的政治實體──無所不在,而且以多種形態呈現:數千年來構成定居型社會隱患的馬上游牧民所打造的乾草原帝國,大不同於西元一五〇〇至一九六〇年支配世界的歐洲人跨洋帝國。有些帝國是一個征服者或某種願景的傑作,但大部分帝國的征服和統治,係出於形勢的推動,而非事先計畫的作為,而且行動方式形形色色。如今爭奪天下者是「帝國型國家」(empire nation)──以中國、美國、俄羅斯為各陣營首領──它們既具有國家的聚合力,也擁有遼闊的帝國,令人敬畏的量體,往往是大陸型量體。在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得到新的極端民族主義加持,控制世上最大的帝國型國家──而且帶來致命後果。地緣政治較量──教皇尤利烏斯二世所謂的「世界博奕」──無法止息;成功始終只是一時,為此付出的人命代價始終太高。
許多罪行遭到忽略、隱瞞,勢必也遭到完全的掩蓋。在本書中,我的用意是寫下一部透顯微妙差異的歷史,在其中如實呈現人和其政治實體的複雜、缺陷、鼓舞人心之處。治療過去罪行的良藥是投以最明亮的光,使其無所遁形;一旦這些罪行已非法網所能懲治,這一揭露便是最真的挽救,唯一算數的挽救。本書意在投出那道光:按事件發生的順序道出成就和罪行,不管其造作者是誰。我想要盡可能多講述那些遇害的、受奴役的或受壓迫的無辜者的故事: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又或者沒有任何人是重要的。
如今我們有幸擁有令人振奮的新科學方法──碳十四定年法、DNA、語言年代學──使我們有機會發掘更多過去的真相,說明人透過地球暖化和污染給地球帶來的傷害。但即使有這些新工具,歷史基本上還是在講人。撰寫此書前,我最後一次旅行的地點是埃及:當我看到法尤姆(Fayum)墓室肖像的生動面容,我心裡想著,這些西元一世紀的人長得真像我們。他們及其家人的確和今日的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但差異同樣鮮明。如今,我們往往幾乎不了解我們熟知的人。而歷史的第一道法便是意識到對於過去的人、他們的想法、他們家族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
寫史時要避免流於目的論,勿以為歷史的結果始終為人所知,這些並不容易。歷史學家拙於預測未來,但當他們已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時,則善於預測未來。不過,與其說歷史學家是按事件發生順序記錄過去者或預見未來者,不如說只是映照其當下所處時刻的鏡子。要了解過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甩開現在:我們的職責是利用我們所知的一切事物尋找事實,以說明過去數代人的生活──全世界居高位者和居下位者的生活。
馬蘇迪(al-Masudi)於九世紀的巴格達寫道,世界史的史家就像「一個已找到各種樣式、顏色的珍珠,把它們串成一條項鍊,打造成一件得到其主人細心守護的飾物的人」。這正是我想書寫的世界史。
那一家人在黑斯堡海灘留下的腳印不久就被潮水沖掉,卻是在此之後的數十萬年,我們所謂的歷史方才展開。
(節錄自《權力的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