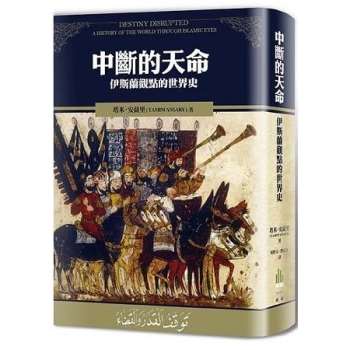鄂圖曼帝國何以衰敗
鄂圖曼人和歐洲基督徒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好幾個世紀了;他們的西方國境正是東西方的前線,摩擦就是在這裡出現的。但是在各次戰役的期間,甚至是雙方在一個地方激戰正酣的時候,在另一個地方,雙方正進行著大量的貿易往來,因為這並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那種形式的全面戰爭。戰爭是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進行的。有時候雙方正在戰場上對陣,但在幾英哩之外的地方卻在正常地進行貿易。這樣的衝突的確有十字軍運動留下的意識型態上的衝突,的確有——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衝突,但就實際層面來說,戰爭只是侷限在君主之間針對領土的職業性戰爭。總之,還是有大量基督徒和猶太人居住在鄂圖曼帝國的境內,有些人還屬於鄂圖曼軍隊,為了鄂圖曼帝國參展,這不是出於對鄂圖曼帝國的愛國熱忱,而是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份工作,他們需要的是錢。這類型的戰爭自然是讓其他人得以穿梭其中,靠買賣而獲利。
十七世紀時,不僅僅是威尼斯人,還包括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荷蘭人及其他的歐洲商人來到了穆斯林世界,他們並不是帶著錢,而是帶著槍。這些商人的到來幫助鄂圖曼帝國進入了一個緩慢卻不可逆轉的轉換進程,只是他們並不是帶著黃金,而是帶著槍械來到這裡,這些生意人導致一段緩慢卻無法逆轉的進程,將強大的鄂圖曼帝國變成被歐洲人叫作歐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的遲鈍畸形體,歐洲人有時候也更溫和——但是在某些方面卻更有優越感地稱鄂圖曼帝國為「那個東方的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上述進程的發展非常的慢,然而卻如此地影響廣泛和複雜,以至於不太可能有人能在這段歷史長河中逐日審視,找出歐洲人的闖入和迅速衰落之間的聯繫。
在這項進程中第一件值得留意的事就是有什麼事是沒有發生的。面對外來勢力的進逼,即便鄂圖曼帝國早已奄奄一息,只是比兀鷹來吃的腐肉稍強一點點而已,鄂圖曼帝國卻還是掌握有破壞性的軍隊實力。歷史學家指出有兩場重要的軍事失利開啟了鄂圖曼帝國的衰亡,雖然這兩場失敗在當時都被或多或少地被鄂圖曼人忽視了。第一場失敗是發生在一五七一年的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在這場以海戰為主的戰事之中,威尼斯和他們的盟友實質上是摧毀了鄂圖曼人的整個地中海艦隊。在歐洲,這場戰役被標榜為討人厭的突厥人終於走下坡路了的令人激動的信號。
然而在伊斯坦堡,大維齊爾(grand vizier)將艦隊的損失比喻成男人刮鬍子:被刮去的鬍鬚再長出來的時候只會比原來的更濃密。的確,在一年之內,鄂圖曼帝國就以一支數量更大、更現代的艦隊代替了損失的艦隊,有八艘比以前更大的大戰艦長時期地在地中海上巡航。在勒班陀戰役後的六個月,鄂圖曼人就贏回了地中海東部,征服了賽普勒斯,並且開始襲擾西西里。也難怪當時的鄂圖曼分析人士並不把勒班陀戰役看作是重要的轉折點。距離歐洲人在海上建立起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還要再等上至少一個世紀。
另一場重要的軍事事件所發生的時間比勒班陀戰役稍早一些,但是其後續影響要到很後來的時候才顯現出來。這一切都要回溯到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沒能將維也納收入囊中的那場戰役。由於鄂圖曼人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向西的擴張,在一五二九年,他們兵臨維也納城下,但是蘇萊曼大帝包圍這座著名的奧地利城市的時節已經太晚了。隨著冬季的到來,他決定先放過維也納一馬,等明年再來將其征服。但是對於蘇萊曼來說,這個機會已經不會再來了,因為有其他的事情突然出現並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畢竟他的帝國太遼闊了,邊境線是如此之長,總是在這裡或是哪裡的地方連續不斷地出現麻煩。這位蘇丹再也沒有再次試圖攻佔維也納,但是當時的人並沒有從中看到衰弱的信號。攻佔維也納始終位列在他的待辦事項中;他只不過是太忙了。他正忙著贏下其它的戰役,而且他的統治是如此的成功,只有亂說話的白痴才會只是因為沒有攻下維也納就在那個時候預示說鄂圖曼帝國正在衰落。畢竟那場戰役並不算是一場敗仗,只是沒有連珠砲似的取得又一場壓倒性的勝利罷了。但是當歷史學家回顧以往的時候,的確可以清楚看到蘇萊曼無法成功佔領維也納是一個轉捩點。在當時,帝國的領土已經大到了極點。在那之後,帝國就不再持績擴張了。這在當時是很難察覺出來的,而且從戰場上傳來的消息常常都是好消息。也許鄂圖曼人在這裡或是那裡打了敗仗,但是他們同時也在別的什麼地方取得了勝利。那他們在那時候是輸掉了關鍵戰役而贏得了沒那麼關鍵的戰役嗎?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是的」,但是這對於徜徉在各大歷史性事件中的人來說也是十分難以衡量的。人們要如何來衡量一場戰役的重要性呢?有的人喜歡危言聳聽,而且這樣的人總是存在。總之,在一六零零年的時候,鄂圖曼帝國絕對是沒有在萎縮。
但很不幸的是,對鄂圖曼帝國而言,只是做到沒有萎縮還不夠好。事實上,這個帝國是建立在不斷擴張的前提之下的。帝國需要在它的邊境上得到不間斷的、普遍性的軍事勝利來保證複雜的內部機制的運行。
首先,擴張是收入來源,在這一點上,帝國沒辦法承受失敗帶來的損失。
其次,戰爭起到了安全活閥的作用,可以將社會內部的壓力向外釋放。例如,因為各種理由被迫放棄土地的佃農不至於變得沒飯吃和喪失希望從而變成不安定的暴民。他們總是可以參軍,走上戰場,得到一些戰利品,從而回到家鄉開始做一些小生意……
然而,一旦擴張停了下來,這些壓力就會流向國家內部。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靠土地吃飯的人們開始流動到城市裡。即便他們有一技之長,也不一定能夠靠手藝吃上飯。因為各行各業的同業公會控制了所有的生產,他們只能吸收一定數量的新會員。有許多到處遊蕩的人最後變成了失業者並由此心懷不滿。由擴張的停止所帶來的類似後果還有很多。第三,本來的德夫希爾梅制度(devshirme)是取決於從不斷取得的新領土上徵得「奴隸」,而這些人可以進入到產生帝國精英的機構中去。本來的耶尼切里新兵(janissary)是受制在一項嚴格的規定之下的:他們不可以結婚生子,這樣的規定可以保證新鮮血液可以進入到這個行政系統之中。但是一旦對外擴張停了下來,德夫希爾梅制度也就停滯不前了。隨後耶尼切里也開始有了婚姻。接下來他們就開始了天下父母都會為自己的小孩所操心的事情:給他們的小孩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這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但是這意味著耶尼切里從此變成了一個永久且世襲的精英階層,這會減損帝國的活力,因為那些保障帝國運行的專業人員和技術官僚不再像早期那樣只能由有才能的人擔任,而是由許多貴冑子弟擔任。
沒有人把這些停滯歸咎於幾十年前蘇萊曼沒能征服維也納。人們怎麼會這麼說呢?這些後果和其原因之間是如此的遙遠又如此的間接,對於社會大眾來說,這一切僅僅是某種沒辦法下定義又難以解釋的社會萎靡,這類的事情使得宗教保守人士開始責罵世風日下,他們開始重申舊式道德的重要性,比如提倡自我控制,敬重老人等等。
接下來將要發生的則是蘇萊曼出征失利的後序動作了。在一六八三年,鄂圖曼人曾嘗試再次攻佔維也納,結果還是像是一百五十四年前一樣,他們再度失利,但這次他們是被歐洲聯軍所擊潰的。就技術層面而言,第二次征服維也納的戰役僅能算是沒能取勝,但是在鄂圖曼帝國精英們的心中,他們知道這是一次迎頭的痛擊,有些事情已經徹底失控了。
這次的失利讓鄂圖曼帝國的統治精英臥薪嘗膽地執意加強他們的軍事實力。他們太過簡單地認定帝國的實力和活力是取決於軍隊和武器上的。為了對抗正在侵蝕這個帝國的那些無形力量,他們認為要孤注一擲地提升軍力。他們將資源傾注到軍事力量中,然而這只是導致了本就財政失衡的政府要承擔更多的支出。
鄂圖曼帝國之所以會財政失衡一方面是因為進入此地的歐洲商人破壞了原本社會系統的微妙平衡。讓我們先忽略勒班陀戰役,也忽略維也納圍城的失利。歸根結底,還是商人而不是軍人,撂倒了鄂圖曼帝國。讓我們來闡述更多的細節。在鄂圖曼帝國,同業公會(和蘇非教團交織在一起)控制了所有的生產,他們通過排除競爭來保護成員的利益。比如說,生產肥皂的同業公會就壟斷了這項產業,同時也會有壟斷製鞋產業的同業公會……因為國家已經規定了各種物價的上限,所以同業公會要利用他們的壟斷地位來抬升物價。國家保護了民眾的利益,而公會則保護了會員們的利益。兩者之間是平衡的,而且所有事情都沒問題。
然後,西方人進入了這個體系。他們並不是靠著賣鞋或者賣肥皂來和同業公會競爭——國家並不允許他們這麼做。他們來這裡是為了找到可以買入的東西,主要是原材料,比如羊毛、肉、皮革、木材、油、金屬等等——只要是他們有用的,他們都會購買。供貨商很樂意把貨物賣給他們,甚至連國家也對此很滿意,因為這樣的貿易可以換來黃金,為什麼這會是一件壞事呢?不幸的是,歐洲人所購買的原料與當地製造業所需要的原料是相同的,歐洲人手中握有從美洲掠奪而來的黃金,因此他們的出價總是高於公會的出價,相形之下,公會受限於政府的價格限制,手中只有有限的利潤額來進行競價。他們也沒辦法通過加大產量來改變局面,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原料來加大生產。隨著外國人不斷地將原料從鄂圖曼的領土吸到歐洲大陸去,鄂圖曼帝國的手工業者開始感受到了壓力:國內的生產開始凋敝了。
鄂圖曼官方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於是禁止了國內製造業所需的關鍵原料出口。但這一類型的法律只是會開放走私的機會:當出口羊毛變成了犯罪,那就只有罪犯才會從事這樣的事。黑市經濟因此興盛起來。一整個由黑市企業家組成的暴發戶階級出現了。因為他們的收入是非法所得,所以他們必須要賄賂各種官員來給他們的財路行個方便,這又造成了貪腐的問題,從而帶來了一整個黑市企業家的附生階級:貪腐官僚階級。如此就有更多的人有了非法所得來消費,但這些錢並不是靠生產力的增加而得來的。這些錢是由可以自由支配金錢的歐洲人那裡輸入到鄂圖曼帝國的經濟中的,而那些錢又是歐洲人從美洲得來的。那些鄂圖曼的新富人士要如何花銷他們這些錢呢?總之肯定不會是光明正大地投資工業:這麼做肯定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他們開始做和現代美國毒販一樣的事情。他們自由自在地砸錢購買各種奢侈品。在鄂圖曼世界中,這些奢侈品也包括要靠非法途徑才能得到的歐洲商品。這一趨勢也削弱了鄂圖曼社會生產商品的能力,這也就給歐洲的工業提供了市場,意外地把黃金帶回了歐洲。
當生產衰落的時候,外來的熱錢湧入鄂圖曼體系引發了通貨膨脹:這是財富過剩但供給過低時就會產生的現象。我曾在北加州的鄉間看過相同的過程,當地有少部分人藉由種大麻賺到了巨額財富。在一個沒有明顯經濟活動的地區,你卻能看到有人開著BMW之類的豪華車,普通的房子卻要價上百萬美金,甚至在那些突然致富地區的商店中,連麵包都賣得比較貴。
誰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受害者呢?受害者主要是靠固定收入過活的人。在當今,我們習慣將將「固定收入」等同於「低收入」,一提到這個名詞就聯想到靠福利系統領取救濟金的人。事情並非如此,在鄂圖曼社會中,領取固定收入的人是領薪水的政府工作人員,更典型的則是在宮廷中領取薪水的官員——是那些驕傲又沒有生產能力的人。那些固定收入者是比克羅伊斯(Croesus)還富有的人,但即便是這些有錢人中的有錢人,也感受到了購買力下降的威脅。在一九二九年美國股市崩盤的時候,眾所週知有一些銀行家在跳樓自殺命喪路邊的時候,身價還有好幾百萬美金。由此可見,這些人擁有多少財產並不重要,他們在乎的是自己少拿到多少財產。於此相似的是,在鄂圖曼社會中,通貨膨脹使那些拿固定薪水的富裕大臣們覺得他們必須得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才行,而他們恰恰最討厭這樣。這時候他們就開始動用自己唯一能控制的工具來補貼家用了。這些大臣(以及官僚人員)掌握了什麼工具呢?他們掌握的是進入國家行政和立法系統的通道。當一個人的角色僅僅是提供通道的話,那麼,他能做到的也僅僅是拒絕別人進入這個通道了。鄂圖曼帝國的大臣和官員們開始以阻絕代替促進——除非他們能得到賄賂。帝國從此就變成了文書工作的夢魘。為了能夠「處理一下」這條通路,人們必須要串通門路上下打點才行。
為了打擊這一弊端,國家提升了薪資水平,讓那些大臣和官員覺得沒有收取賄賂之必要。但是國家在實際生產力上並沒有任何額外的經費,尤其是在帝國的對外擴張停滯下來後更是如此,國家已經沒有那些以往能從征服中得來的收入了。所以為了提高薪資水平、撫恤金和軍人薪餉,帝國只好印製鈔票。
印製鈔票會刺激通貨膨脹——這就讓所有的問題又回到了我們討論的原點了!鄂圖曼帝國政府所做的一切旨在杜絕貪腐和提升效率的努力都讓本來的問題變得更難以解決。最終,政府的官員們只能放手並且決定要僱用一些顧問人員來幫助他們把事情理順。那些被他們僱用的管理顧問和技術專家來自於那片看起來知道怎麼做事的地方:西歐。
或許早就應該有一些天資秉賦的執政者能夠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帶領鄂圖曼帝國的精英們走出這片可憐的境地,但是這個帝國最成功的地方,也就是它輝煌的統治家族已經將其皇室文化和生活轉變成了一種阻礙新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或是新的蘇萊曼大帝的誕生的一種帝國文化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帝國的宮廷,已經變得更大、更沈重並且更不作為,到最後就像是一個背負了整個社會的畸形巨人。
象徵著這種畸形狀態的原型大概可以算是帝國所謂的「後宮」,即蘇丹在伊斯坦堡的成群妻妾。當然了,在穆斯林世界的歷朝歷代都有後宮,但是在鄂圖曼帝國的社會中,這個糟糕的體制擴大到了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大小,也許只有明朝中國的後宮能夠與之相提並論。來自各個佔領地區的數千名女子居住在迷宮一樣縱橫交錯的後宮之中,她們雖然身處於奢華富麗的環境中,但是大部分的女子都住在迷宮中的小房間裡。後宮中的女子被供給予化妝品和其它各種用來搭配裝飾品的配飾,除了打扮自己以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她們沒有有用處的工作要做,沒有求學的機會,也不被要求生產任何東西,沒有任何事能把她們從百無聊賴中解救出來。她們就是寶石籠子中的囚徒。
把自家女性藏起來的風俗在伊斯蘭世界已行之百餘年了,但即便是在這個時間點,這種風俗仍然沒有流傳到整個社會中去而只是在上流社會中流傳。在偏遠的地區,一位旅行者大概仍然能夠看到佃農女性在田地中勞作或者在路上趕牲口。在都市裡,社會地位較低階級的女性會在公共的巴扎中經營小買賣,為家裡採買日用品或手工藝品。在社會的中間階級中,有些女性擁有財產,也管理生意和指揮僱員。但是這些女性在公共事務中的拋頭露面表示了他們丈夫謙卑的社會地位。
特權階級的男性通過將女眷隔離於公眾生活之外來炫耀他們的社會地位,她們的女眷被隱藏在家中的私領域中。這種風俗背後的心理學解釋(我覺得)是和男人的尊嚴有關——實際上就是在周圍其他男人們中間鶴立雞群昂首挺胸的能力——取決於他能不能讓和自己有關的女性免於成為其他男人的性幻想對象。到最後,這就是扣押女性這種行為歸根結底的理由,而且在這樣的文化大環境中,即便是社會較低層的男人也會感受到這樣的壓力而把自家的女人藏起來,免得在其他男人面前丟臉。
在蘇丹的後宮中,上述的綜合症狀簡直是大到一個令人震驚的地步。一般來說,尤其對於西方的東方學家來說,「後宮(harem)」這個詞有一種好色淫亂的涵義,就好像後宮中從早到晚都充斥著各種性方面的歡愉。但是這怎麼可能呢?蘇丹只是一個人而已,除了侍衛以外,根本就不會有其他人能看到這些女子,而且所有的侍衛都是閹人。而且對某幾個蘇丹來說,說來大家也許會覺得吃驚,他們根本就不是在後宮中尋求放鬆歡愉,也根本不和這些女子混在一起。有一個特定的閹人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為蘇丹挑選一個女子,這個閹人要在夜幕的掩護下將她護送到蘇丹的寢宮去。性愛的特許權利和性壓抑在這個機制中離奇地交織在一起。那些閹人可以在後宮和外面的世界之間自由走動,因此他們成了那些女人們了解外面世界的眼、耳和手,也是她們改變外面的世界和對其施加影響的工具。蘇丹的孩子們,包括兒子,都是在後宮中長到十二歲才離開,這些人從來沒有和平凡人接觸過,在青少年時期以前也沒有經歷過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辛苦。到了他們離開後宮的時候,這樣的一位登上王位的王子幾乎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功能失調的產物,而他們的主要技能大概就是在錯綜複雜的後宮迷宮中游刃有餘的能力。
後宮總是充斥著各種賭注極高、強度極大的陰謀,即便是指定了的繼任人選,其他王子的母親還是會不死心的持續運作,期望她們的兒子有天可以登上大位,(如此一來,她也能躋身帝國的權力人物)。因此,這群後宮佳麗和她們的子嗣們每天就是在籌劃謀殺潛在對手(有時這些陰謀會成功)直到蘇丹死去,後宮檯面下的陰謀鬥爭就會被抬到檯前來上演。從鬥爭中得勝的王子得以繼任大位,這一成功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更是為了他身後的一大群後宮佳麗和閹人們。鄂圖曼帝國的王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知道自己只有很小的可能性成為世界的主宰,而有很大的可能性還沒成年就會死掉,他們就是在這種狀態下成長的。
這一系統最後產生出了一長串孱弱、痴呆又偏執的蘇丹。但是這一事實本身並不是鄂圖曼帝國衰落和滅亡的原因,因為當這個系統發展成熟,變成了那個腐敗的機制的時候,鄂圖曼的蘇丹已經不再掌管國家了。在蘇萊曼大帝去世後不久,蘇丹之位的執行力就開始衰落了。在鄂圖曼系統中,大維齊爾(grand vizier)才是那個握有實權的人。
然而不作為的皇室和其巨大的後宮的確是束縛住了鄂圖曼帝國,因為他花費巨大卻產出甚少——實際上簡直就沒有產出,甚至連決定都沒有做過。維齊爾和其他的官員們必須要讓國家能夠運行,卻同時背負著那個該死的無能體系的龐大阻力,這使得整個運行機制不作為而且運行遲緩。
鄂圖曼人和歐洲基督徒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好幾個世紀了;他們的西方國境正是東西方的前線,摩擦就是在這裡出現的。但是在各次戰役的期間,甚至是雙方在一個地方激戰正酣的時候,在另一個地方,雙方正進行著大量的貿易往來,因為這並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那種形式的全面戰爭。戰爭是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進行的。有時候雙方正在戰場上對陣,但在幾英哩之外的地方卻在正常地進行貿易。這樣的衝突的確有十字軍運動留下的意識型態上的衝突,的確有——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衝突,但就實際層面來說,戰爭只是侷限在君主之間針對領土的職業性戰爭。總之,還是有大量基督徒和猶太人居住在鄂圖曼帝國的境內,有些人還屬於鄂圖曼軍隊,為了鄂圖曼帝國參展,這不是出於對鄂圖曼帝國的愛國熱忱,而是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份工作,他們需要的是錢。這類型的戰爭自然是讓其他人得以穿梭其中,靠買賣而獲利。
十七世紀時,不僅僅是威尼斯人,還包括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荷蘭人及其他的歐洲商人來到了穆斯林世界,他們並不是帶著錢,而是帶著槍。這些商人的到來幫助鄂圖曼帝國進入了一個緩慢卻不可逆轉的轉換進程,只是他們並不是帶著黃金,而是帶著槍械來到這裡,這些生意人導致一段緩慢卻無法逆轉的進程,將強大的鄂圖曼帝國變成被歐洲人叫作歐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的遲鈍畸形體,歐洲人有時候也更溫和——但是在某些方面卻更有優越感地稱鄂圖曼帝國為「那個東方的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上述進程的發展非常的慢,然而卻如此地影響廣泛和複雜,以至於不太可能有人能在這段歷史長河中逐日審視,找出歐洲人的闖入和迅速衰落之間的聯繫。
在這項進程中第一件值得留意的事就是有什麼事是沒有發生的。面對外來勢力的進逼,即便鄂圖曼帝國早已奄奄一息,只是比兀鷹來吃的腐肉稍強一點點而已,鄂圖曼帝國卻還是掌握有破壞性的軍隊實力。歷史學家指出有兩場重要的軍事失利開啟了鄂圖曼帝國的衰亡,雖然這兩場失敗在當時都被或多或少地被鄂圖曼人忽視了。第一場失敗是發生在一五七一年的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在這場以海戰為主的戰事之中,威尼斯和他們的盟友實質上是摧毀了鄂圖曼人的整個地中海艦隊。在歐洲,這場戰役被標榜為討人厭的突厥人終於走下坡路了的令人激動的信號。
然而在伊斯坦堡,大維齊爾(grand vizier)將艦隊的損失比喻成男人刮鬍子:被刮去的鬍鬚再長出來的時候只會比原來的更濃密。的確,在一年之內,鄂圖曼帝國就以一支數量更大、更現代的艦隊代替了損失的艦隊,有八艘比以前更大的大戰艦長時期地在地中海上巡航。在勒班陀戰役後的六個月,鄂圖曼人就贏回了地中海東部,征服了賽普勒斯,並且開始襲擾西西里。也難怪當時的鄂圖曼分析人士並不把勒班陀戰役看作是重要的轉折點。距離歐洲人在海上建立起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還要再等上至少一個世紀。
另一場重要的軍事事件所發生的時間比勒班陀戰役稍早一些,但是其後續影響要到很後來的時候才顯現出來。這一切都要回溯到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沒能將維也納收入囊中的那場戰役。由於鄂圖曼人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向西的擴張,在一五二九年,他們兵臨維也納城下,但是蘇萊曼大帝包圍這座著名的奧地利城市的時節已經太晚了。隨著冬季的到來,他決定先放過維也納一馬,等明年再來將其征服。但是對於蘇萊曼來說,這個機會已經不會再來了,因為有其他的事情突然出現並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畢竟他的帝國太遼闊了,邊境線是如此之長,總是在這裡或是哪裡的地方連續不斷地出現麻煩。這位蘇丹再也沒有再次試圖攻佔維也納,但是當時的人並沒有從中看到衰弱的信號。攻佔維也納始終位列在他的待辦事項中;他只不過是太忙了。他正忙著贏下其它的戰役,而且他的統治是如此的成功,只有亂說話的白痴才會只是因為沒有攻下維也納就在那個時候預示說鄂圖曼帝國正在衰落。畢竟那場戰役並不算是一場敗仗,只是沒有連珠砲似的取得又一場壓倒性的勝利罷了。但是當歷史學家回顧以往的時候,的確可以清楚看到蘇萊曼無法成功佔領維也納是一個轉捩點。在當時,帝國的領土已經大到了極點。在那之後,帝國就不再持績擴張了。這在當時是很難察覺出來的,而且從戰場上傳來的消息常常都是好消息。也許鄂圖曼人在這裡或是那裡打了敗仗,但是他們同時也在別的什麼地方取得了勝利。那他們在那時候是輸掉了關鍵戰役而贏得了沒那麼關鍵的戰役嗎?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是的」,但是這對於徜徉在各大歷史性事件中的人來說也是十分難以衡量的。人們要如何來衡量一場戰役的重要性呢?有的人喜歡危言聳聽,而且這樣的人總是存在。總之,在一六零零年的時候,鄂圖曼帝國絕對是沒有在萎縮。
但很不幸的是,對鄂圖曼帝國而言,只是做到沒有萎縮還不夠好。事實上,這個帝國是建立在不斷擴張的前提之下的。帝國需要在它的邊境上得到不間斷的、普遍性的軍事勝利來保證複雜的內部機制的運行。
首先,擴張是收入來源,在這一點上,帝國沒辦法承受失敗帶來的損失。
其次,戰爭起到了安全活閥的作用,可以將社會內部的壓力向外釋放。例如,因為各種理由被迫放棄土地的佃農不至於變得沒飯吃和喪失希望從而變成不安定的暴民。他們總是可以參軍,走上戰場,得到一些戰利品,從而回到家鄉開始做一些小生意……
然而,一旦擴張停了下來,這些壓力就會流向國家內部。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靠土地吃飯的人們開始流動到城市裡。即便他們有一技之長,也不一定能夠靠手藝吃上飯。因為各行各業的同業公會控制了所有的生產,他們只能吸收一定數量的新會員。有許多到處遊蕩的人最後變成了失業者並由此心懷不滿。由擴張的停止所帶來的類似後果還有很多。第三,本來的德夫希爾梅制度(devshirme)是取決於從不斷取得的新領土上徵得「奴隸」,而這些人可以進入到產生帝國精英的機構中去。本來的耶尼切里新兵(janissary)是受制在一項嚴格的規定之下的:他們不可以結婚生子,這樣的規定可以保證新鮮血液可以進入到這個行政系統之中。但是一旦對外擴張停了下來,德夫希爾梅制度也就停滯不前了。隨後耶尼切里也開始有了婚姻。接下來他們就開始了天下父母都會為自己的小孩所操心的事情:給他們的小孩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這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但是這意味著耶尼切里從此變成了一個永久且世襲的精英階層,這會減損帝國的活力,因為那些保障帝國運行的專業人員和技術官僚不再像早期那樣只能由有才能的人擔任,而是由許多貴冑子弟擔任。
沒有人把這些停滯歸咎於幾十年前蘇萊曼沒能征服維也納。人們怎麼會這麼說呢?這些後果和其原因之間是如此的遙遠又如此的間接,對於社會大眾來說,這一切僅僅是某種沒辦法下定義又難以解釋的社會萎靡,這類的事情使得宗教保守人士開始責罵世風日下,他們開始重申舊式道德的重要性,比如提倡自我控制,敬重老人等等。
接下來將要發生的則是蘇萊曼出征失利的後序動作了。在一六八三年,鄂圖曼人曾嘗試再次攻佔維也納,結果還是像是一百五十四年前一樣,他們再度失利,但這次他們是被歐洲聯軍所擊潰的。就技術層面而言,第二次征服維也納的戰役僅能算是沒能取勝,但是在鄂圖曼帝國精英們的心中,他們知道這是一次迎頭的痛擊,有些事情已經徹底失控了。
這次的失利讓鄂圖曼帝國的統治精英臥薪嘗膽地執意加強他們的軍事實力。他們太過簡單地認定帝國的實力和活力是取決於軍隊和武器上的。為了對抗正在侵蝕這個帝國的那些無形力量,他們認為要孤注一擲地提升軍力。他們將資源傾注到軍事力量中,然而這只是導致了本就財政失衡的政府要承擔更多的支出。
鄂圖曼帝國之所以會財政失衡一方面是因為進入此地的歐洲商人破壞了原本社會系統的微妙平衡。讓我們先忽略勒班陀戰役,也忽略維也納圍城的失利。歸根結底,還是商人而不是軍人,撂倒了鄂圖曼帝國。讓我們來闡述更多的細節。在鄂圖曼帝國,同業公會(和蘇非教團交織在一起)控制了所有的生產,他們通過排除競爭來保護成員的利益。比如說,生產肥皂的同業公會就壟斷了這項產業,同時也會有壟斷製鞋產業的同業公會……因為國家已經規定了各種物價的上限,所以同業公會要利用他們的壟斷地位來抬升物價。國家保護了民眾的利益,而公會則保護了會員們的利益。兩者之間是平衡的,而且所有事情都沒問題。
然後,西方人進入了這個體系。他們並不是靠著賣鞋或者賣肥皂來和同業公會競爭——國家並不允許他們這麼做。他們來這裡是為了找到可以買入的東西,主要是原材料,比如羊毛、肉、皮革、木材、油、金屬等等——只要是他們有用的,他們都會購買。供貨商很樂意把貨物賣給他們,甚至連國家也對此很滿意,因為這樣的貿易可以換來黃金,為什麼這會是一件壞事呢?不幸的是,歐洲人所購買的原料與當地製造業所需要的原料是相同的,歐洲人手中握有從美洲掠奪而來的黃金,因此他們的出價總是高於公會的出價,相形之下,公會受限於政府的價格限制,手中只有有限的利潤額來進行競價。他們也沒辦法通過加大產量來改變局面,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原料來加大生產。隨著外國人不斷地將原料從鄂圖曼的領土吸到歐洲大陸去,鄂圖曼帝國的手工業者開始感受到了壓力:國內的生產開始凋敝了。
鄂圖曼官方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於是禁止了國內製造業所需的關鍵原料出口。但這一類型的法律只是會開放走私的機會:當出口羊毛變成了犯罪,那就只有罪犯才會從事這樣的事。黑市經濟因此興盛起來。一整個由黑市企業家組成的暴發戶階級出現了。因為他們的收入是非法所得,所以他們必須要賄賂各種官員來給他們的財路行個方便,這又造成了貪腐的問題,從而帶來了一整個黑市企業家的附生階級:貪腐官僚階級。如此就有更多的人有了非法所得來消費,但這些錢並不是靠生產力的增加而得來的。這些錢是由可以自由支配金錢的歐洲人那裡輸入到鄂圖曼帝國的經濟中的,而那些錢又是歐洲人從美洲得來的。那些鄂圖曼的新富人士要如何花銷他們這些錢呢?總之肯定不會是光明正大地投資工業:這麼做肯定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他們開始做和現代美國毒販一樣的事情。他們自由自在地砸錢購買各種奢侈品。在鄂圖曼世界中,這些奢侈品也包括要靠非法途徑才能得到的歐洲商品。這一趨勢也削弱了鄂圖曼社會生產商品的能力,這也就給歐洲的工業提供了市場,意外地把黃金帶回了歐洲。
當生產衰落的時候,外來的熱錢湧入鄂圖曼體系引發了通貨膨脹:這是財富過剩但供給過低時就會產生的現象。我曾在北加州的鄉間看過相同的過程,當地有少部分人藉由種大麻賺到了巨額財富。在一個沒有明顯經濟活動的地區,你卻能看到有人開著BMW之類的豪華車,普通的房子卻要價上百萬美金,甚至在那些突然致富地區的商店中,連麵包都賣得比較貴。
誰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受害者呢?受害者主要是靠固定收入過活的人。在當今,我們習慣將將「固定收入」等同於「低收入」,一提到這個名詞就聯想到靠福利系統領取救濟金的人。事情並非如此,在鄂圖曼社會中,領取固定收入的人是領薪水的政府工作人員,更典型的則是在宮廷中領取薪水的官員——是那些驕傲又沒有生產能力的人。那些固定收入者是比克羅伊斯(Croesus)還富有的人,但即便是這些有錢人中的有錢人,也感受到了購買力下降的威脅。在一九二九年美國股市崩盤的時候,眾所週知有一些銀行家在跳樓自殺命喪路邊的時候,身價還有好幾百萬美金。由此可見,這些人擁有多少財產並不重要,他們在乎的是自己少拿到多少財產。於此相似的是,在鄂圖曼社會中,通貨膨脹使那些拿固定薪水的富裕大臣們覺得他們必須得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才行,而他們恰恰最討厭這樣。這時候他們就開始動用自己唯一能控制的工具來補貼家用了。這些大臣(以及官僚人員)掌握了什麼工具呢?他們掌握的是進入國家行政和立法系統的通道。當一個人的角色僅僅是提供通道的話,那麼,他能做到的也僅僅是拒絕別人進入這個通道了。鄂圖曼帝國的大臣和官員們開始以阻絕代替促進——除非他們能得到賄賂。帝國從此就變成了文書工作的夢魘。為了能夠「處理一下」這條通路,人們必須要串通門路上下打點才行。
為了打擊這一弊端,國家提升了薪資水平,讓那些大臣和官員覺得沒有收取賄賂之必要。但是國家在實際生產力上並沒有任何額外的經費,尤其是在帝國的對外擴張停滯下來後更是如此,國家已經沒有那些以往能從征服中得來的收入了。所以為了提高薪資水平、撫恤金和軍人薪餉,帝國只好印製鈔票。
印製鈔票會刺激通貨膨脹——這就讓所有的問題又回到了我們討論的原點了!鄂圖曼帝國政府所做的一切旨在杜絕貪腐和提升效率的努力都讓本來的問題變得更難以解決。最終,政府的官員們只能放手並且決定要僱用一些顧問人員來幫助他們把事情理順。那些被他們僱用的管理顧問和技術專家來自於那片看起來知道怎麼做事的地方:西歐。
或許早就應該有一些天資秉賦的執政者能夠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帶領鄂圖曼帝國的精英們走出這片可憐的境地,但是這個帝國最成功的地方,也就是它輝煌的統治家族已經將其皇室文化和生活轉變成了一種阻礙新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或是新的蘇萊曼大帝的誕生的一種帝國文化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帝國的宮廷,已經變得更大、更沈重並且更不作為,到最後就像是一個背負了整個社會的畸形巨人。
象徵著這種畸形狀態的原型大概可以算是帝國所謂的「後宮」,即蘇丹在伊斯坦堡的成群妻妾。當然了,在穆斯林世界的歷朝歷代都有後宮,但是在鄂圖曼帝國的社會中,這個糟糕的體制擴大到了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大小,也許只有明朝中國的後宮能夠與之相提並論。來自各個佔領地區的數千名女子居住在迷宮一樣縱橫交錯的後宮之中,她們雖然身處於奢華富麗的環境中,但是大部分的女子都住在迷宮中的小房間裡。後宮中的女子被供給予化妝品和其它各種用來搭配裝飾品的配飾,除了打扮自己以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她們沒有有用處的工作要做,沒有求學的機會,也不被要求生產任何東西,沒有任何事能把她們從百無聊賴中解救出來。她們就是寶石籠子中的囚徒。
把自家女性藏起來的風俗在伊斯蘭世界已行之百餘年了,但即便是在這個時間點,這種風俗仍然沒有流傳到整個社會中去而只是在上流社會中流傳。在偏遠的地區,一位旅行者大概仍然能夠看到佃農女性在田地中勞作或者在路上趕牲口。在都市裡,社會地位較低階級的女性會在公共的巴扎中經營小買賣,為家裡採買日用品或手工藝品。在社會的中間階級中,有些女性擁有財產,也管理生意和指揮僱員。但是這些女性在公共事務中的拋頭露面表示了他們丈夫謙卑的社會地位。
特權階級的男性通過將女眷隔離於公眾生活之外來炫耀他們的社會地位,她們的女眷被隱藏在家中的私領域中。這種風俗背後的心理學解釋(我覺得)是和男人的尊嚴有關——實際上就是在周圍其他男人們中間鶴立雞群昂首挺胸的能力——取決於他能不能讓和自己有關的女性免於成為其他男人的性幻想對象。到最後,這就是扣押女性這種行為歸根結底的理由,而且在這樣的文化大環境中,即便是社會較低層的男人也會感受到這樣的壓力而把自家的女人藏起來,免得在其他男人面前丟臉。
在蘇丹的後宮中,上述的綜合症狀簡直是大到一個令人震驚的地步。一般來說,尤其對於西方的東方學家來說,「後宮(harem)」這個詞有一種好色淫亂的涵義,就好像後宮中從早到晚都充斥著各種性方面的歡愉。但是這怎麼可能呢?蘇丹只是一個人而已,除了侍衛以外,根本就不會有其他人能看到這些女子,而且所有的侍衛都是閹人。而且對某幾個蘇丹來說,說來大家也許會覺得吃驚,他們根本就不是在後宮中尋求放鬆歡愉,也根本不和這些女子混在一起。有一個特定的閹人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為蘇丹挑選一個女子,這個閹人要在夜幕的掩護下將她護送到蘇丹的寢宮去。性愛的特許權利和性壓抑在這個機制中離奇地交織在一起。那些閹人可以在後宮和外面的世界之間自由走動,因此他們成了那些女人們了解外面世界的眼、耳和手,也是她們改變外面的世界和對其施加影響的工具。蘇丹的孩子們,包括兒子,都是在後宮中長到十二歲才離開,這些人從來沒有和平凡人接觸過,在青少年時期以前也沒有經歷過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辛苦。到了他們離開後宮的時候,這樣的一位登上王位的王子幾乎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功能失調的產物,而他們的主要技能大概就是在錯綜複雜的後宮迷宮中游刃有餘的能力。
後宮總是充斥著各種賭注極高、強度極大的陰謀,即便是指定了的繼任人選,其他王子的母親還是會不死心的持續運作,期望她們的兒子有天可以登上大位,(如此一來,她也能躋身帝國的權力人物)。因此,這群後宮佳麗和她們的子嗣們每天就是在籌劃謀殺潛在對手(有時這些陰謀會成功)直到蘇丹死去,後宮檯面下的陰謀鬥爭就會被抬到檯前來上演。從鬥爭中得勝的王子得以繼任大位,這一成功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更是為了他身後的一大群後宮佳麗和閹人們。鄂圖曼帝國的王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知道自己只有很小的可能性成為世界的主宰,而有很大的可能性還沒成年就會死掉,他們就是在這種狀態下成長的。
這一系統最後產生出了一長串孱弱、痴呆又偏執的蘇丹。但是這一事實本身並不是鄂圖曼帝國衰落和滅亡的原因,因為當這個系統發展成熟,變成了那個腐敗的機制的時候,鄂圖曼的蘇丹已經不再掌管國家了。在蘇萊曼大帝去世後不久,蘇丹之位的執行力就開始衰落了。在鄂圖曼系統中,大維齊爾(grand vizier)才是那個握有實權的人。
然而不作為的皇室和其巨大的後宮的確是束縛住了鄂圖曼帝國,因為他花費巨大卻產出甚少——實際上簡直就沒有產出,甚至連決定都沒有做過。維齊爾和其他的官員們必須要讓國家能夠運行,卻同時背負著那個該死的無能體系的龐大阻力,這使得整個運行機制不作為而且運行遲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