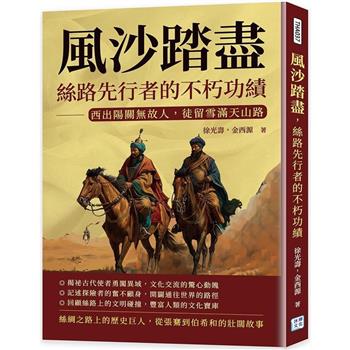第一章 張騫:通向世界的「鑿空」之旅
長長的商隊走過平原,步伐堅定,銀鈴奏鳴。
他們不再追求榮耀和收穫,不再從棕櫚樹環繞的水井中求得平安。
葛樂耐(Frantz Grenet)在其《駛向薩馬爾罕的金色旅程(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中,描繪了一幅通商之路上意境深遠的動人景觀:古道悠悠,一條道路將整個世界展開;瀚海茫茫,一片沙磧將所有的命運隱藏。叮噹……叮噹……清越的駝鈴聲正在久遠的絲綢古道上響起,無數人正踏著滿地蒼茫,走向遠方。
這條溝通世界東西文明的萬里彩虹,這條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交通路線,一八七七年,被德國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為「絲綢之路」。回眸遠望,在這條充滿荒涼和悲壯的道路上,許許多多手持使節和文書的使者,在不知疲倦的腳下,鋪開一條如絲綢般絢爛而又悠長的畫卷。
西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大地蒼茫,一個渺小的身影在前行,他叫張騫,從長安來,到西方去。
一、宏偉藍圖
這是一個動人心魄的故事,兩千年的風雨早已將紛亂的生活埋藏在大地深處,只留下人們艱難前行的足跡,在歷史的車轍中特別醒目。
那時,生活的版圖被匈奴、大月氏、大宛等部落劃分開來,高山、沙漠和戰爭成為阻隔人們與外界交流的屏障,沒有人知道荒山大漠之外那些遠道而來的人們心中所藏的、關於生活和遠方的祕密。
也正是那時,中國逐漸向世界展現出他遼闊的面目,硝煙和戰火,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人性的凈化和上升,在久遠的歷史長河裡,永遠是一件緩慢而又艱難的事。
假若我們回顧歷史,便會看到,在和匈奴有關的記載裡,一場「白登之圍」,曾使一代江山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這個故事,今日講來依舊寒冷。
西元前二〇二年(漢高祖五年),劉邦率三十二萬大軍攻打匈奴,不料卻被冒頓單于率四十萬大軍,圍困在白登山下(今山西大同)。劉邦被圍七天七夜,突圍無果,悲不可言。危難之中,透過用計賄賂冒頓單于的王后閼氏,才免遭滅頂之災。
至於所用之計,司馬遷在《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言:「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這裡的代詞「其」,則指當時的謀士陳平。陳平所用之計,司馬遷隻字未提。
那麼高祖被圍之後,四顧茫然,無計可施之時,這位跟隨漢高祖劉邦南征北戰、六次進獻妙計、六次獲得封賞的謀士陳平,到底用了怎樣的計謀,才使得劉邦得以脫離險境呢?
原來,陳平在漢高祖劉邦束手無策之時,暗中派使臣去見了冒頓單于的王后閼氏。使者以貴重的金銀珠寶相贈,又拿出一卷畫軸,請閼氏轉交冒頓單于。這位使臣,史書中並未提及其姓名,但此緊要關頭,臨危受命者,所肩負的使命便非同凡響。我們不難想到,面對重兵強大的壓力和王后閼氏難以猜測的反應,一個大國使者所表現出的謹慎、誠懇乃至卑微。
閼氏收下重金,卻對這一畫軸充滿疑惑,不禁展開畫軸,畫中有一女子,貌美絕倫,不悅。問及原委,才知漢王被圍於白登山下多日,身陷困境,願將漢朝第一美女獻與單于,希望單于退兵。閼氏怒,使者低頭,將目光從宏闊的萬里江山上收回,坦言所處被動之境,外表鎮定但內心不無忐忑。
閼氏思忖再三,讓使者把畫拿回了漢軍中。謀士陳平見此情狀,知閼氏中計。果然,閼氏勸說單于:兩國的君主不應該相互迫害,如今即使單于奪得漢朝的土地,也不能居住,況且漢朝君主也有神靈(相護),希望單于能明察定奪。加之當時單于和其他部隊會師的計畫出現失誤,單于撤去部分兵力,高祖藉大霧降臨之機勉強突圍脫離險境。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閼氏的勸說之言:
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
我們不難想像,漢王劉邦被圍困白登山下時內心的悲愴,以及被迫無奈接受如此下策,僥倖逃離白登山之圍後的狼狽與尷尬;亦不難看出,謀士陳平與這位不知名的使者,在白登之圍中的貢獻之大。
此後,便有了與匈奴的「和親」之約,漢宗室之女以公主之名,遠嫁匈奴首領,並按期饋贈大量禮品,以妥協來避免匈奴的大規模劫掠。儘管如此,牧馬寇伐之事依舊不斷。漢王朝雖穩居中原,但提及匈奴,內心卻從未感到安寧。
不管歷史塵埃中的人們是身陷泥淖還是壯志滿懷,時間從未停下行進的腳步,關於匈奴的故事聽來總讓人心若懸劍。
在長久的休養生息和等待之後,漢王朝政權日益穩固,至漢武帝時期,漢朝開始實施遠交近攻的戰略方針;但無論如何,先祖在白登山被圍的故事,從未因為時間的推移而變得黯淡。
西元前一三九年(建元二年),幾個落魄的匈奴人投降漢朝,漢武帝從他們口中得知,匈奴部落擊敗了大月氏,殺死了大月氏之王,並取其頭顱作為飲酒之器,大月氏部落因此逃離北方,向西遷徙。大月氏人對匈奴心懷怨恨,只是苦於無人願共擊匈奴。
在漢武帝看來,這是一個聯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的絕好機遇。深思熟慮之後,他準備派使者出使遠隔漢室萬里之外的大月氏,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這個宏大的想法,在今天看來依舊充滿著「宏偉藍圖」的意味。
這一事件,在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中有簡略的記載: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
提及大月氏,這支原本活動於祁連山以北的游牧部落,因匈奴的大舉西進而將其逐出故地,不得已西遷至伊犁河、楚河附近。要遠交大月氏,匈奴擋於其間,道阻且長,艱難險遠不言而喻。
有誰願意擔此重任冒死出使西域大月氏?
漢武帝下詔,公開招募西去之使者。
二、向西而去
西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的一天,一名宮廷侍衛如期而至,他自願出使西域。很快,這個叫做張騫的名字傳遍了長安。
關於張騫早期的生活經歷,歷史也有些健忘。這位年輕力壯,為人正直的宮廷侍衛,當時地位低下,但當他做出應徵使者的決定,並堅決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看法時,其果斷、機警、坦誠的性格,便為他的出使鋪平了道路,張騫如願被朝廷選中。
張騫深知,出使西域對他而言,是一次改變命運的難得機遇,同時也是一場歸來無期的生死博弈。
在應募的人群中,還有一人渴望透過遠行改變自己的生活,熱切希望自己能夠因此獲得自由的身分,他便是匈奴的俘虜甘父。甘父不僅擅長騎射,同時又可為張騫擔任翻譯,也被選中。
經過嚴格挑選,一百多人被選中出使西域,這些人中有奴隸、有平民,也有軍官和士兵,張騫被封為出使西域的使節,其他人作為他的隨從。不為人們所知的是,他們選擇出使西域的同時,便也選擇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和歸來無期的命運。
今天我們已無法得知,當張騫一行人自長安出發走向西域時內心的所思所想,亦無法得知這群迫切想改變自己命運的人們,在通往未知的路上遭遇險阻時,是否會對自己當初的決定心生疑慮,會不會在自己的腦海中生發出如詩人海子般的慨嘆: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但張騫和漢武帝大概也不會想到,這場與政治密切相關的軍事策略,會打開一扇溝通中西世界的窗口。一場關於西行的出使活動在東方的宏圖裡逐漸展開,呈現出歷史從未有過的久遠和宏闊。
西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張騫接受了自己遙遠又悲壯的使命,同甘父等隨從一起,離開長安,向西而去。他們希望能跨越匈奴統治下的土地出使大月氏,取道隴西,出玉門關向西而去。儘管張騫一行人謹慎行進,但是在匈奴控制下的河西走廊,他們很快便被匈奴騎兵抓獲,並被帶到了匈奴單于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
單于得知張騫一行人欲過河西走廊而出使大月氏,暴跳如雷。
「月氏在吾北,漢使何以得往使?無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史記·大宛列傳》)
一個出使西域的決定,一條遙不可及的道路,在起始不久便令張騫陷入困境,出使西域的計畫難道就此而前功盡棄?等待著張騫的,將會是怎樣的道路和命運?
事實證明,張騫所走的路依舊很長,除了等待,更是屈原式的求索之路,因此用屈子「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命運來形容張騫也十分貼切。大概每一個落魄於他鄉的遊子,面對艱辛難料的世事,都會有渺若栗粟之感,但他們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在這如蘆葦般的生命行程裡綻放光輝。
張騫和其他人一樣,被扣留在了荒涼的他鄉。此刻,在他身上並沒有傳奇性的故事,沒有英雄降臨,也沒有智謀祕計,等待成為了他的命運。
單于沒有殺害張騫,而是將張騫扣留在了單于庭,一個遠離故土又遠離大月氏的他鄉,他所要面對的是無盡的艱難和荒涼。張騫之外,除了他的嚮導甘父,隨行的一百餘人的命運在歷史的長河裡隨風飄散。的確,和歷史宏大的腳步相比,他們的命運顯得微不足道。我們不難想像,單于為了拉攏這位從漢朝遠道而來、心懷壯志的使者,想盡各種辦法來對付張騫的情景。後來,在匈奴兵的看守下,張騫和他所剩無幾的隨從做著放羊、打草、挖井的苦工。
幾年後,為了進一步控制張騫,單于為張騫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不久,張騫和這位匈奴女子有了兒子。在眾人的眼中,張騫已將自己的根扎在了這裡,對他的看管便十分鬆散。
時間一天天過去,張騫雖已習慣了在遠方荒涼的生活,但這將近十年的日子並沒有在他心裡生根發芽。他安靜眺望,向西遠望,彷彿那遠處的蒼茫裡有他魂牽夢繞的故鄉。張騫在匈奴的監視下,過了十年喪失自由的生活,但他無時無刻不在探聽關於漢朝和大月氏的消息,關於那裡的任何一點微小的動靜,都能牽動他如泉湧般流淌的心緒。張騫看似早已如一池沒有絲毫風浪的湖水,他平靜生活,平靜融入匈奴的日常起居,平靜將自己所有關於大月氏的想法藏在心底。
十年之後,這個看起來已如匈奴人一般的漢人,心裡依舊藏著那個想要回到遠方的祕密。
十年之後,「持漢節不失」的張騫,開始謀劃一場關於大月氏的遠行,他找到了那個對他忠心耿耿的隨從甘父,當張騫悄悄在四望無跡的靜默裡告訴甘父自己的想法時,這個在匈奴的壓迫下滄桑不堪的隨從,混沌的眼神裡有了久違的亮光。兩個堅定的眼神相遇,而後所有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探索化作匆忙的腳步。兩個在自己的使命裡停留了十年的身影,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了,留下身後一地的靜謐和驚嘆。
向西而去,向大月氏所在的方向而去,兩個不屈的靈魂在原野上奔走,內心急切又不失鎮定。
西行數十日,張騫來到了一個叫做大宛(今烏茲別克)的國家。
在張騫被困的十一年裡,我們無從得知張騫的內心,在時間的長河中曾掀起過怎樣的波瀾。面對歷史,我們的推究終顯得輕薄。但毫無疑問,這十年的時光,於那些身陷其中的人而言,裡面更是摻雜著各種複雜的味道,這種心情若用陳子昂的詩句來表達,正是: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我們可以用「風餐露宿」來形容張騫所經歷的苦難,但終究不能用語言丈量張騫在茫然無期的生命航程裡,所承受的艱難和困厄的重量,在今天看來他離我們很遠,但的確,又很近。
長長的商隊走過平原,步伐堅定,銀鈴奏鳴。
他們不再追求榮耀和收穫,不再從棕櫚樹環繞的水井中求得平安。
葛樂耐(Frantz Grenet)在其《駛向薩馬爾罕的金色旅程(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中,描繪了一幅通商之路上意境深遠的動人景觀:古道悠悠,一條道路將整個世界展開;瀚海茫茫,一片沙磧將所有的命運隱藏。叮噹……叮噹……清越的駝鈴聲正在久遠的絲綢古道上響起,無數人正踏著滿地蒼茫,走向遠方。
這條溝通世界東西文明的萬里彩虹,這條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交通路線,一八七七年,被德國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為「絲綢之路」。回眸遠望,在這條充滿荒涼和悲壯的道路上,許許多多手持使節和文書的使者,在不知疲倦的腳下,鋪開一條如絲綢般絢爛而又悠長的畫卷。
西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大地蒼茫,一個渺小的身影在前行,他叫張騫,從長安來,到西方去。
一、宏偉藍圖
這是一個動人心魄的故事,兩千年的風雨早已將紛亂的生活埋藏在大地深處,只留下人們艱難前行的足跡,在歷史的車轍中特別醒目。
那時,生活的版圖被匈奴、大月氏、大宛等部落劃分開來,高山、沙漠和戰爭成為阻隔人們與外界交流的屏障,沒有人知道荒山大漠之外那些遠道而來的人們心中所藏的、關於生活和遠方的祕密。
也正是那時,中國逐漸向世界展現出他遼闊的面目,硝煙和戰火,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人性的凈化和上升,在久遠的歷史長河裡,永遠是一件緩慢而又艱難的事。
假若我們回顧歷史,便會看到,在和匈奴有關的記載裡,一場「白登之圍」,曾使一代江山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這個故事,今日講來依舊寒冷。
西元前二〇二年(漢高祖五年),劉邦率三十二萬大軍攻打匈奴,不料卻被冒頓單于率四十萬大軍,圍困在白登山下(今山西大同)。劉邦被圍七天七夜,突圍無果,悲不可言。危難之中,透過用計賄賂冒頓單于的王后閼氏,才免遭滅頂之災。
至於所用之計,司馬遷在《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言:「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這裡的代詞「其」,則指當時的謀士陳平。陳平所用之計,司馬遷隻字未提。
那麼高祖被圍之後,四顧茫然,無計可施之時,這位跟隨漢高祖劉邦南征北戰、六次進獻妙計、六次獲得封賞的謀士陳平,到底用了怎樣的計謀,才使得劉邦得以脫離險境呢?
原來,陳平在漢高祖劉邦束手無策之時,暗中派使臣去見了冒頓單于的王后閼氏。使者以貴重的金銀珠寶相贈,又拿出一卷畫軸,請閼氏轉交冒頓單于。這位使臣,史書中並未提及其姓名,但此緊要關頭,臨危受命者,所肩負的使命便非同凡響。我們不難想到,面對重兵強大的壓力和王后閼氏難以猜測的反應,一個大國使者所表現出的謹慎、誠懇乃至卑微。
閼氏收下重金,卻對這一畫軸充滿疑惑,不禁展開畫軸,畫中有一女子,貌美絕倫,不悅。問及原委,才知漢王被圍於白登山下多日,身陷困境,願將漢朝第一美女獻與單于,希望單于退兵。閼氏怒,使者低頭,將目光從宏闊的萬里江山上收回,坦言所處被動之境,外表鎮定但內心不無忐忑。
閼氏思忖再三,讓使者把畫拿回了漢軍中。謀士陳平見此情狀,知閼氏中計。果然,閼氏勸說單于:兩國的君主不應該相互迫害,如今即使單于奪得漢朝的土地,也不能居住,況且漢朝君主也有神靈(相護),希望單于能明察定奪。加之當時單于和其他部隊會師的計畫出現失誤,單于撤去部分兵力,高祖藉大霧降臨之機勉強突圍脫離險境。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閼氏的勸說之言:
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
我們不難想像,漢王劉邦被圍困白登山下時內心的悲愴,以及被迫無奈接受如此下策,僥倖逃離白登山之圍後的狼狽與尷尬;亦不難看出,謀士陳平與這位不知名的使者,在白登之圍中的貢獻之大。
此後,便有了與匈奴的「和親」之約,漢宗室之女以公主之名,遠嫁匈奴首領,並按期饋贈大量禮品,以妥協來避免匈奴的大規模劫掠。儘管如此,牧馬寇伐之事依舊不斷。漢王朝雖穩居中原,但提及匈奴,內心卻從未感到安寧。
不管歷史塵埃中的人們是身陷泥淖還是壯志滿懷,時間從未停下行進的腳步,關於匈奴的故事聽來總讓人心若懸劍。
在長久的休養生息和等待之後,漢王朝政權日益穩固,至漢武帝時期,漢朝開始實施遠交近攻的戰略方針;但無論如何,先祖在白登山被圍的故事,從未因為時間的推移而變得黯淡。
西元前一三九年(建元二年),幾個落魄的匈奴人投降漢朝,漢武帝從他們口中得知,匈奴部落擊敗了大月氏,殺死了大月氏之王,並取其頭顱作為飲酒之器,大月氏部落因此逃離北方,向西遷徙。大月氏人對匈奴心懷怨恨,只是苦於無人願共擊匈奴。
在漢武帝看來,這是一個聯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的絕好機遇。深思熟慮之後,他準備派使者出使遠隔漢室萬里之外的大月氏,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這個宏大的想法,在今天看來依舊充滿著「宏偉藍圖」的意味。
這一事件,在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中有簡略的記載: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
提及大月氏,這支原本活動於祁連山以北的游牧部落,因匈奴的大舉西進而將其逐出故地,不得已西遷至伊犁河、楚河附近。要遠交大月氏,匈奴擋於其間,道阻且長,艱難險遠不言而喻。
有誰願意擔此重任冒死出使西域大月氏?
漢武帝下詔,公開招募西去之使者。
二、向西而去
西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的一天,一名宮廷侍衛如期而至,他自願出使西域。很快,這個叫做張騫的名字傳遍了長安。
關於張騫早期的生活經歷,歷史也有些健忘。這位年輕力壯,為人正直的宮廷侍衛,當時地位低下,但當他做出應徵使者的決定,並堅決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看法時,其果斷、機警、坦誠的性格,便為他的出使鋪平了道路,張騫如願被朝廷選中。
張騫深知,出使西域對他而言,是一次改變命運的難得機遇,同時也是一場歸來無期的生死博弈。
在應募的人群中,還有一人渴望透過遠行改變自己的生活,熱切希望自己能夠因此獲得自由的身分,他便是匈奴的俘虜甘父。甘父不僅擅長騎射,同時又可為張騫擔任翻譯,也被選中。
經過嚴格挑選,一百多人被選中出使西域,這些人中有奴隸、有平民,也有軍官和士兵,張騫被封為出使西域的使節,其他人作為他的隨從。不為人們所知的是,他們選擇出使西域的同時,便也選擇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和歸來無期的命運。
今天我們已無法得知,當張騫一行人自長安出發走向西域時內心的所思所想,亦無法得知這群迫切想改變自己命運的人們,在通往未知的路上遭遇險阻時,是否會對自己當初的決定心生疑慮,會不會在自己的腦海中生發出如詩人海子般的慨嘆: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但張騫和漢武帝大概也不會想到,這場與政治密切相關的軍事策略,會打開一扇溝通中西世界的窗口。一場關於西行的出使活動在東方的宏圖裡逐漸展開,呈現出歷史從未有過的久遠和宏闊。
西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張騫接受了自己遙遠又悲壯的使命,同甘父等隨從一起,離開長安,向西而去。他們希望能跨越匈奴統治下的土地出使大月氏,取道隴西,出玉門關向西而去。儘管張騫一行人謹慎行進,但是在匈奴控制下的河西走廊,他們很快便被匈奴騎兵抓獲,並被帶到了匈奴單于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
單于得知張騫一行人欲過河西走廊而出使大月氏,暴跳如雷。
「月氏在吾北,漢使何以得往使?無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史記·大宛列傳》)
一個出使西域的決定,一條遙不可及的道路,在起始不久便令張騫陷入困境,出使西域的計畫難道就此而前功盡棄?等待著張騫的,將會是怎樣的道路和命運?
事實證明,張騫所走的路依舊很長,除了等待,更是屈原式的求索之路,因此用屈子「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命運來形容張騫也十分貼切。大概每一個落魄於他鄉的遊子,面對艱辛難料的世事,都會有渺若栗粟之感,但他們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在這如蘆葦般的生命行程裡綻放光輝。
張騫和其他人一樣,被扣留在了荒涼的他鄉。此刻,在他身上並沒有傳奇性的故事,沒有英雄降臨,也沒有智謀祕計,等待成為了他的命運。
單于沒有殺害張騫,而是將張騫扣留在了單于庭,一個遠離故土又遠離大月氏的他鄉,他所要面對的是無盡的艱難和荒涼。張騫之外,除了他的嚮導甘父,隨行的一百餘人的命運在歷史的長河裡隨風飄散。的確,和歷史宏大的腳步相比,他們的命運顯得微不足道。我們不難想像,單于為了拉攏這位從漢朝遠道而來、心懷壯志的使者,想盡各種辦法來對付張騫的情景。後來,在匈奴兵的看守下,張騫和他所剩無幾的隨從做著放羊、打草、挖井的苦工。
幾年後,為了進一步控制張騫,單于為張騫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不久,張騫和這位匈奴女子有了兒子。在眾人的眼中,張騫已將自己的根扎在了這裡,對他的看管便十分鬆散。
時間一天天過去,張騫雖已習慣了在遠方荒涼的生活,但這將近十年的日子並沒有在他心裡生根發芽。他安靜眺望,向西遠望,彷彿那遠處的蒼茫裡有他魂牽夢繞的故鄉。張騫在匈奴的監視下,過了十年喪失自由的生活,但他無時無刻不在探聽關於漢朝和大月氏的消息,關於那裡的任何一點微小的動靜,都能牽動他如泉湧般流淌的心緒。張騫看似早已如一池沒有絲毫風浪的湖水,他平靜生活,平靜融入匈奴的日常起居,平靜將自己所有關於大月氏的想法藏在心底。
十年之後,這個看起來已如匈奴人一般的漢人,心裡依舊藏著那個想要回到遠方的祕密。
十年之後,「持漢節不失」的張騫,開始謀劃一場關於大月氏的遠行,他找到了那個對他忠心耿耿的隨從甘父,當張騫悄悄在四望無跡的靜默裡告訴甘父自己的想法時,這個在匈奴的壓迫下滄桑不堪的隨從,混沌的眼神裡有了久違的亮光。兩個堅定的眼神相遇,而後所有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探索化作匆忙的腳步。兩個在自己的使命裡停留了十年的身影,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了,留下身後一地的靜謐和驚嘆。
向西而去,向大月氏所在的方向而去,兩個不屈的靈魂在原野上奔走,內心急切又不失鎮定。
西行數十日,張騫來到了一個叫做大宛(今烏茲別克)的國家。
在張騫被困的十一年裡,我們無從得知張騫的內心,在時間的長河中曾掀起過怎樣的波瀾。面對歷史,我們的推究終顯得輕薄。但毫無疑問,這十年的時光,於那些身陷其中的人而言,裡面更是摻雜著各種複雜的味道,這種心情若用陳子昂的詩句來表達,正是: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我們可以用「風餐露宿」來形容張騫所經歷的苦難,但終究不能用語言丈量張騫在茫然無期的生命航程裡,所承受的艱難和困厄的重量,在今天看來他離我們很遠,但的確,又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