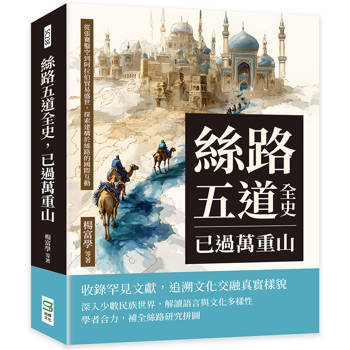一、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
「絲綢之路」這一名詞是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產物,在古希臘、古羅馬的著作中,有一個比印度更遠的國家──賽里斯(Seres)盛產絲綢,其出產的絲綢經由中亞、西亞到達羅馬,羅馬人為之痴迷。但絲綢的生產工藝、絲綢之路東段的具體走向,在西方人眼中則一直蒙著神祕的面紗。近代以降,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殖民地的擴張,以歐洲人為視角的地理大發現不斷拓展其對中國、對中亞的了解。西元1868年,德國地理學家、東方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來到中國,在中國14個省進行了為期長達4年的地理考察。從1877年開始,李希霍芬陸續將他在中國收集到的資料整理為五卷著作──《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在這一著作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德文原作Seidenstrasse或Sererstrasse)的概念。有時,他又命之曰「商業之路」(德文原作Handelsstrassen)。由此可見,「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提出,和連接中國與西方、印度等的古代貿易密切相關。學術界普遍的說法是,李希霍芬將自西元前114年至西元127年連接中國與河中以及印度的絲綢貿易的西域通道稱為「絲綢之路」,其實並不準確,這一說法並非出現在《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書中,而見於李希霍芬於1877年6月2日所做演講〈論截至西元二世紀為止的中亞絲綢之路〉中。李希霍芬之演講依時間先後將絲綢之路的歷史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間接絲綢貿易階段,指絲綢離開中國後經過不止一次的中間交易,方到達中亞。而直接絲綢貿易則為第二階段,指絲綢從中國直接交易到「圖蘭低地」(即中亞)。第二階段「開始於西元前114年……結束於西元120年,斯時統治著整個第二個階段的漢朝勢力已黯淡下來」。值得留意的是,在李希霍芬眼中,第二階段結束於120年而非127年。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lbert Hermann)在二十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流通道。在此書中,赫爾曼說:「『絲綢之路』一詞蓋由李希霍芬始用,專指那條中亞絲綢之路,即西元前114年至西元127年間中國與烏滸河(即阿姆河)、藥殺水(錫爾河的古稱)附近的國家及與印度之間進行絲綢貿易的中亞絲綢之路。」李希霍芬所謂的西元120年在這裡變成了西元127年。這是赫爾曼有意如此處理還是不小心出錯,現已無法判斷,但127年之說成為學界的共識。
在李希霍芬、赫爾曼之後的一百多年間,尤其是最近半個世紀,絲綢之路成為國際史學界的一門顯學,其研究的時代由兩漢時期延伸至自張騫出使西域到明代西北國際貿易的衰落,其研究的地域由河中、印度等地延伸至古羅馬帝國,其研究的內容也由單純的絲綢之路貿易延伸至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人物、宗教等的交流、借鑑與融合。
其實,早在張騫「鑿空」之前,絲綢之路即已存在。早在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時,就看到大夏有經印度輸入的中國邛竹杖、蜀布。因此在中國與中亞還不相通時,絲綢也是透過印度運往大夏。邛竹,又名方竹、羅漢,主要產地在中國雲南東北部,也產於廣西、福建等地。漢代時,中國的邛竹杖已經透過身毒傳到了大夏。此外,在大約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前一世紀時,中國的桃種已經傳入波斯,後來又輸入亞美尼亞、希臘等地。西元一世紀時,桃樹種子輸入羅馬,被羅馬史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y Eleder)稱為「波斯樹」。
河西史前墓葬中出土的海貝、蚌殼、玉石、瑪瑙、綠松石等,原本都不產於河西,要麼來自西域,要麼來自東南沿海,都是經過間接交換而來。據學界研究,海產品之西傳,應由東南沿海經貴州、四川而入青海,又進入甘肅中部,並折而向西,進入河西走廊。同時,經過河西走廊,還存在著一條由西向東延伸的玉石之路,這條道路由新疆和田直達河南安陽。法國學者蒂埃里.扎爾科內(Thierry Zarcone)甚至認為傳統的「絲綢之路」之謂名不副實,應該改稱「玉石之路」。來自河西周邊地區的瑪瑙、綠松石等,都是沿著這條道路在東西方穿行。西方文化東輸與東方文化西進,兩條傳播道路交會於河西,孕育了絲綢之路的雛形,誠如嚴文明先生所言:「早先是西方的青銅文化帶著小麥、綿羊和冶金技術,不久又趕著馬匹進入新疆,而且繼續東進傳入甘肅等地;東方甘肅等地的粟和彩陶技術也傳入新疆,甚至遠播中亞。這種互動傳播的情況後來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即本書所說的綠洲絲綢之路,或曰沙漠絲綢之路、陸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最早指的就是這條道路。至於本書所說的其餘四條道路,都可以說是這一概念的延伸。
「絲綢之路」這一名詞是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產物,在古希臘、古羅馬的著作中,有一個比印度更遠的國家──賽里斯(Seres)盛產絲綢,其出產的絲綢經由中亞、西亞到達羅馬,羅馬人為之痴迷。但絲綢的生產工藝、絲綢之路東段的具體走向,在西方人眼中則一直蒙著神祕的面紗。近代以降,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殖民地的擴張,以歐洲人為視角的地理大發現不斷拓展其對中國、對中亞的了解。西元1868年,德國地理學家、東方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來到中國,在中國14個省進行了為期長達4年的地理考察。從1877年開始,李希霍芬陸續將他在中國收集到的資料整理為五卷著作──《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在這一著作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德文原作Seidenstrasse或Sererstrasse)的概念。有時,他又命之曰「商業之路」(德文原作Handelsstrassen)。由此可見,「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提出,和連接中國與西方、印度等的古代貿易密切相關。學術界普遍的說法是,李希霍芬將自西元前114年至西元127年連接中國與河中以及印度的絲綢貿易的西域通道稱為「絲綢之路」,其實並不準確,這一說法並非出現在《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書中,而見於李希霍芬於1877年6月2日所做演講〈論截至西元二世紀為止的中亞絲綢之路〉中。李希霍芬之演講依時間先後將絲綢之路的歷史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間接絲綢貿易階段,指絲綢離開中國後經過不止一次的中間交易,方到達中亞。而直接絲綢貿易則為第二階段,指絲綢從中國直接交易到「圖蘭低地」(即中亞)。第二階段「開始於西元前114年……結束於西元120年,斯時統治著整個第二個階段的漢朝勢力已黯淡下來」。值得留意的是,在李希霍芬眼中,第二階段結束於120年而非127年。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lbert Hermann)在二十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流通道。在此書中,赫爾曼說:「『絲綢之路』一詞蓋由李希霍芬始用,專指那條中亞絲綢之路,即西元前114年至西元127年間中國與烏滸河(即阿姆河)、藥殺水(錫爾河的古稱)附近的國家及與印度之間進行絲綢貿易的中亞絲綢之路。」李希霍芬所謂的西元120年在這裡變成了西元127年。這是赫爾曼有意如此處理還是不小心出錯,現已無法判斷,但127年之說成為學界的共識。
在李希霍芬、赫爾曼之後的一百多年間,尤其是最近半個世紀,絲綢之路成為國際史學界的一門顯學,其研究的時代由兩漢時期延伸至自張騫出使西域到明代西北國際貿易的衰落,其研究的地域由河中、印度等地延伸至古羅馬帝國,其研究的內容也由單純的絲綢之路貿易延伸至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人物、宗教等的交流、借鑑與融合。
其實,早在張騫「鑿空」之前,絲綢之路即已存在。早在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時,就看到大夏有經印度輸入的中國邛竹杖、蜀布。因此在中國與中亞還不相通時,絲綢也是透過印度運往大夏。邛竹,又名方竹、羅漢,主要產地在中國雲南東北部,也產於廣西、福建等地。漢代時,中國的邛竹杖已經透過身毒傳到了大夏。此外,在大約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前一世紀時,中國的桃種已經傳入波斯,後來又輸入亞美尼亞、希臘等地。西元一世紀時,桃樹種子輸入羅馬,被羅馬史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y Eleder)稱為「波斯樹」。
河西史前墓葬中出土的海貝、蚌殼、玉石、瑪瑙、綠松石等,原本都不產於河西,要麼來自西域,要麼來自東南沿海,都是經過間接交換而來。據學界研究,海產品之西傳,應由東南沿海經貴州、四川而入青海,又進入甘肅中部,並折而向西,進入河西走廊。同時,經過河西走廊,還存在著一條由西向東延伸的玉石之路,這條道路由新疆和田直達河南安陽。法國學者蒂埃里.扎爾科內(Thierry Zarcone)甚至認為傳統的「絲綢之路」之謂名不副實,應該改稱「玉石之路」。來自河西周邊地區的瑪瑙、綠松石等,都是沿著這條道路在東西方穿行。西方文化東輸與東方文化西進,兩條傳播道路交會於河西,孕育了絲綢之路的雛形,誠如嚴文明先生所言:「早先是西方的青銅文化帶著小麥、綿羊和冶金技術,不久又趕著馬匹進入新疆,而且繼續東進傳入甘肅等地;東方甘肅等地的粟和彩陶技術也傳入新疆,甚至遠播中亞。這種互動傳播的情況後來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即本書所說的綠洲絲綢之路,或曰沙漠絲綢之路、陸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最早指的就是這條道路。至於本書所說的其餘四條道路,都可以說是這一概念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