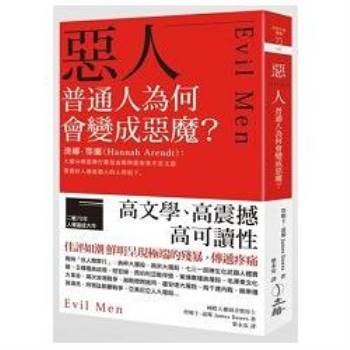你懷念你的老戰友嗎——就是那些跟你一起待到戰爭結束的人?
啊,會,我懷念他們。你知道,他們大部分人都像兄弟。真的。他們真的就像是你的家人。
我可以想像……
對,我們一起出生入死。我們一起經歷過的事情比親兄弟還多。對,我懷念他們。當然懷念。
*
每一次,我都會送給受訪者一小包明尼蘇達州的野生稻米。每一次,我一開始都會表現得笨嘴拙舌,反覆半鞠躬道歉,為同一件事情自嘲︰我連「很高興跟你會面」乃至「謝謝」之類的簡單日語都說不好。他們聽了會面露微笑(我敢說他們會為此驚訝)。在在看來,我每次一開始就先自暴其短是件好事。
每天早上,我和攝影師會到飯店外面喝咖啡和吃酥餅。每天傍晚,女譯員會帶我們去找消遣:看歌舞伎,看武術表演,吃最好吃而不昂貴的壽司,去她最喜歡的老酒館喝兩杯。我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唯獨不談那些我們採訪過的老兵。
*
為什麼我會幹得出那樣的事?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本來只是個農家子弟,一個在農民家庭長大的人。這是我後來會思索的問題。對,你最終一定會覺得奇怪。唉,我不是個會幹出那種事的人。
*
直至今晚以前,我不算是看過真正的格鬥。日本有些武術表演很文雅,像是液體舞(liquid dances),但今晚的表演卻是貨真價實的打鬥。其中一方眼見就要勝出。他把另一個男人壓倒在草蓆上,用拳頭狠狠揍對方的頭,一次又一次。觀眾會隨著每一下拳頭悶聲發出集體呻吟。挨揍的那個男人想必痛得厲害,但臉上卻看不見任何表情。揍他的那個男人反而表情豐富,像是憤怒或害怕——但我說不出來是憤怒還是害怕。
因為忙著跟攝影師和女譯員交談,我過了很久才離場,並因此跟先前兩位格鬥者在電梯裡湊巧遇上。這時我才看出來,他們其實不算是男人,只算是大孩子。我訝異於我的身高比他們高。但更讓我震撼的是看見他們站在一起,有說有笑。從這個近距離,我可以看見敗方的臉上破了皮︰想必是被草蓆擦傷。基於什麼理由,我對他生起悲憫之心。我很想湊近問他:經歷過方才的激烈打鬥,你是怎樣回到正常生活的?*
「你們這些小王八蛋!混帳東西!」——我們會罵這一類的話,但目的不是整垮他們,而是設法讓他們振奮起來。因為如果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我們搞砸了,他們一上戰場就會死掉。我們得推他們一把,促使他們學會快速反應。所以我們就斥喝他們。他們必須被訓練成懂得恰當反應,對不對?如果他們能變成那樣,那有子彈射過來就避得開。這就是我們那樣做的原因。
*
我對每晚外出消遣感到不自在。它給人一種很不協調的感覺。我一會兒參觀神社,一會兒問一個離死不遠的老人他是怎樣學會刑求,一會兒跟一個得過獎的攝影師邊喝酒邊談美學問題。我不知道要怎樣把這些事兜在一起。情形就像有人用鐵棒撬開了日常生活的縫隙,讓本來被封住的惡魔跑了出來,老是在我們旁邊晃,老是在一切的旁邊晃,令人不得安寧。
事實上,「在旁邊」(next to)就是我對我們三個每天早上和晚上一起消遣的時光。它們都是一些「在旁邊」時刻,是發生在訪談的「旁邊」。這讓它們聽起來毫無分量,而我起初也是這樣認為,直到過了好一陣子才改變想法。有「在旁邊」的東西存在——不管是什麼東西——太重要了。
我反覆思考何謂「在旁邊」,何謂「合得在一塊兒」(fits together)。有一天,我開車前往工作地點途中,車子一度在積雪上打滑,差點撞死人,最後有驚無險,但已足夠嚇人。經過這樣的事情後還照常去工作讓我覺得怪怪的。
在在看來,我以前都是把生活組織得毫無縫隙。
*
那些做不到的人會感到羞愧嗎?
沒有「做不到」這回事……我們會逼他們幹,逼他們捅刀子。
*
就著明尼蘇達州冬天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朋友安妮問我:他們幹麼不自殺算了?安妮是個習慣於問人困難問題的醫生,語氣平和但堅定。她把紅銅色的劉海從眼前撥開,定睛望著我。你為什麼不問他們這個問題?我不曾有過跟加害者打交道的經驗。聽著那些日本老兵回憶往事,我有時會覺得自己正由導遊帶領,參觀地獄。我同時覺得有憑靠和暈眩,同時覺得正在被帶領和迷失方向。為了處理這種矛盾,我採取大部分教授都會用來處理嶄新經驗的方法:透過把事情學術化來控制它。我向很多個方向求助,而大部分幫助是來自藝術與人文學的傳統。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怎樣理解歷史上的大屠殺?不同的宗教和哲學傳統是怎樣看待凶殘的問題,是怎樣把現實中的冷血凶殘跟對更高目的(higher purpose)、存在意義(existential meaning)及「神」(divine)的信仰調和起來?我同時也從社會科學領域獲得很大的幫助。所有種族清洗的共同政治與文化特徵是什麼?把人變成惡魔牽涉哪些組織過程與心理過程?要怎樣才也許可能逆轉這些過程?
這些都是重要問題,我也準備要跟各位分享我找到的答案。但若說本書有一個核心問題,則其性質乃非常不同。那就是:我給各位說書中故事的用意何在?各位聽它們的用意何在?這至今仍是困擾我最甚的問題。正是這問題的存在決定了本書的開展方式,決定了哪些部分重要,哪些部分次要。隨著本書的推進,我將會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問和答這個問題。
以下是第一則故事。
*
阪倉君
然後突然間,從村子裡衝出一群十五、六歲的人。在那之前我從未見過八路軍(中國共產黨的主力軍),不知道敵人是什麼樣子。因為不知道眼前這批人是什麼人,我馬上趴下。有更多人衝了出來。然後我聽到指揮官下令:「開火!統統打死!」於是我便開火。我射出的子彈打中了人。「打到了!」我心想。大部分人像蒼蠅一樣紛紛倒下。
之後我們繼續前進,然後是一片高粱田。當時是六月中,所以那片田看來很大一片。〔比出很大的手勢〕每個人都倒在裡面,或是跑到裡面。我緊追在後。在高粱田裡,有個人倒在地上。我看了看,是個家庭主婦。她倒在地上,已經死去。我心想:「好吧,是個家庭主婦。我沒什麼可以做的。」就在我要繼續往前走時,我注意到那女人手臂下抱著個小嬰兒。一個小嬰兒把頭凸了出來。他的手〔沉默了一下〕……他在找乳房,在摸乳房,明白嗎?然後他抬起頭看著我,向我微笑。我無比震撼。你知道嗎,我發現自己無法走路!然後,更讓人害怕的是︙︙我感到一陣寒意從脊椎竄起。我拚命想往前走,卻動不了。然後一些老鳥來到我背後。「快跑啊!」他們說。敵人正在追擊我們。然後我便跑了起來。事後,我想到那小嬰兒獨自一人待在田裡必死無疑,心裡非常不舒服。這是戰爭第一次讓我有這麼不舒服的感覺。對,真的很不舒服。
*
上述是阪倉君故事的中段。這故事開始之時他是個平民,這故事結束之時他已是個加害者。
告訴我上述故事時,阪倉君已離死不遠,設法要弄明白自己人生的意義。他在戰俘營待了很多年,事後又經歷了更多年的自我放逐,期間不斷反省他做過的事和別人對他做過的事。他犯下過許多凶殘暴行,導致過不可勝數的痛苦,但同時經歷了創傷。事實上,犯下的罪行成了他的創傷。他說,死亡的臨近讓他感到一種「壓力」。「我已經沒有未來……如果我不趕快說出來,如果我死了,這些事情便再沒有人會知道。」阪倉君和其他我訪談過的老兵構成獨特的一群。他們全是「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成員,努力了四十五年,要引起大眾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注意和促進中日兩國的友誼。他們為數約一千一百人,全都在戰後被蘇聯俘虜,若干年後再被引渡到中國,關在撫順監獄。西伯利亞的戰俘營不人道至極,但撫順監獄卻幾乎完全相反,待他們如貴賓︰對他們客客氣氣,給他們足夠飲食,照顧他們的醫藥需要,為他們安排體育和文化活動。這些戰犯也接受了思想改造: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經歷到一種如同宗教轉皈的經驗。他們批判自己過去的價值觀(事實上還批判自己過去的自我),又矢志把餘生貢獻於鼓吹和平。這批日本老兵把他們的轉化形容為「撫順奇蹟」。一九五六年,中國終於對他們召開軍事法庭。四十五個人被起訴,但最終全部無罪獲釋。
一九五七年,這批「中國歸還者」建立起一個正式組織,決計要相互扶持,致力打破日本對戰爭罪行的沉默。雖然受到大眾和主流媒體的輕蔑或冷落,但他們奮鬥不懈,直至二○○二年才因為大部分成員都年邁多病而難以為繼。不久之後,新一代的社會活動家在埼玉縣建立了「歸還者和平紀念館」。館裡收藏了超過二萬本書和相關的錄影帶及照片,擠滿書架和研討桌,樣子更像資源中心和圖書館多於紀念館。我們就是透過館方的引介採訪到那些老兵。
從一開始,我便覺得這些人自視為歷史的產物。他們願意承認自己的罪責,但又視之為一個更大脈絡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上升為亞洲的軍事霸權。自此,這個由神聖天皇統治的國家愈來愈軍國主義化,汲汲於展示實力和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但要確保區域性霸權,日本有需要控制中國的資源。結果就是一場災難性的競賽:「中國統一和日本在中國擴張」之間的競賽。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滿洲,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中日的全面戰爭在六年後爆發,導火線是發生在蘆溝橋的一場軍事小衝突。日本把後續的衝突和自己的所有戰爭罪行說成攸關民族榮耀和使命。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發表的報告把日本的領土野心粉飾為一種準人道主義介入:「我大和民族現今正流著『血』,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以達成我們在世界史的使命。為實現亞洲十億人民的解放,更為維持我們在大東亞共榮圈的領導地位,我們必須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這些『土壤』。」
帝國託辭獲得宗教託辭的回應。就連禪宗學者亦聯名指出,中國已成了一個不明佛理因此亟待拯救的國家,說是透過日本高一等的精神了悟,中國的「不可理喻性將會獲得糾正」。「透過一場慈悲戰爭,交戰國家將能夠改善自己,並帶來戰爭本身的戢止。」
這個脈絡是那些「中國歸還者」想向我(做為一個美國人)強調的。我們談話的當時,美軍正在佔領伊拉克。什麼事都總有一個脈絡。
*
凶殘既要求再現(representation)又抗拒再現。我們必須為凶殘當見證,我們必須把凶殘的故事說出來——這種信念居於人權工作的核心。我們之所以搜集證言,調查戰爭罪行的細節,是出於道德責任的要求。這種道德責任在法律起訴有現實可能性時最為迫切,但它在那些沒有了起訴可能但繼續矢口否認罪行和歷史修正主義大盛的地方(日本就是這個樣子)一樣有力。我們是在為未來世代創建一個我們時代的道德檔案庫。我們是在為那些個人最深真理每天都受到否認的倖存者締造可理解的公共歷史。而有時,我們是在(正如果我訪談過的老兵所認為的)利用一個「安全於想像」(safeto-imagine)的過去使目前正上演著的事情變得顯眼。近幾十年來,日本的政府官員、學者和各級前軍官一再否認和輕描淡寫化日本帝國犯下的暴行。一九九四年,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把南京大屠殺(估計有三十萬平民被殺害)說成是「虛構」。永野事後雖道歉,但卻措詞謹慎,只願稱南京大屠殺為「南京事件」。二○○七年,首相安倍俊太郎否認曾有韓國婦女被強迫充當慰安婦。二○○一年,文部省大臣贊同修訂歷史課本,刪去跟日本戰爭罪行有關的部分(包括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以中國平民實驗細菌生化武器等)。二○○五年,一位日本學者在著作中指斥已故華裔作家張純如不該繼續散播「南京發生過大屠殺的神話」。這樣的事例所在多有,此處只是列舉三四。維瑟爾(Elie Wiesel)說過,遺忘就是把一個人殺兩次。如果此言不假,那中日戰爭就迄未停止。它只是轉到記憶的領域開打罷了。
所以,我們三人(攝影師、女譯員和我)一開始是抱著同一個假定投入工作:不管在這個個案還是其他個案,為凶殘留下見證都是正確的事。不管是在罪行發生當時揭發罪行,還是事隔多年後搜集和分享證言,都是人權努力所理所當為。這是一場記憶之戰,有著黑白分明的道德立場︰要不是說出來就是沉默,要不是抵抗就是同謀。
但我已不再那麼確定。
再現苦難包含著一個弔詭。一方面,想阻止繼續有人受到傷害,我們必須說出發生過什麼事;但在說故事的過程中,我們有可能會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傷害到他人。我們想要讓加害者羞愧,但有時卻會刺激得他們更為暴力;我們想從旁觀者身分引發惻隱之心,但有時卻會讓他們愈來愈麻木,甚至憎厭;我們想要給倖存者帶來療癒的聲音,但有時卻會讓他們二度受創傷;我們想要把遙遠的陌生人變成鮮明具象的人,但有時卻會把他們化約為抽象和只有二度空間的「受害者」。
搜集證言是一種尊重倖存者和死者的舉動,也是對抗集體凶殘反覆上演的一座真實小碉堡。但收集和分享證據卻會觸發一個我們無法控制的連鎖反應過程。它同樣會引起傷害。在從事本專案的過程中,我開始相信收集加害者證言這工作需要戴著道德近視眼(moral myopia),甚至帶著一點自大。我看不出來還有別的路徑可以穿過這工作所引起的一大堆棘手問題︰在受害者無法說出他們故事的情況下,你說出加害者的故事會有什麼風險?當你一再聆聽和記錄加害者懇求寬恕,久而久之會不會變成一種對寬恕的默許(一種你無權給予或拒絕的寬恕)?你做這事的動機是什麼?是出於責任感的召喚,是出於孤芳自賞的道德正義感,還是出於作家對聳動材料的渴望?呈現最邪惡和殘忍的細節是否只是在販賣色情?沒這樣做是否就是一種道德上的懦弱?如果你進行自我審查,不去再現創傷,此舉是否就保護了創傷,讓它免受侵入性瞪視、簡化和解剖的蹂躪?還是說此舉只代表不理會創傷對再現的呼求,並重演了旁觀者的袖手旁觀(正是這種袖手旁觀讓凶殘從一開始得以發生)?
啊,會,我懷念他們。你知道,他們大部分人都像兄弟。真的。他們真的就像是你的家人。
我可以想像……
對,我們一起出生入死。我們一起經歷過的事情比親兄弟還多。對,我懷念他們。當然懷念。
*
每一次,我都會送給受訪者一小包明尼蘇達州的野生稻米。每一次,我一開始都會表現得笨嘴拙舌,反覆半鞠躬道歉,為同一件事情自嘲︰我連「很高興跟你會面」乃至「謝謝」之類的簡單日語都說不好。他們聽了會面露微笑(我敢說他們會為此驚訝)。在在看來,我每次一開始就先自暴其短是件好事。
每天早上,我和攝影師會到飯店外面喝咖啡和吃酥餅。每天傍晚,女譯員會帶我們去找消遣:看歌舞伎,看武術表演,吃最好吃而不昂貴的壽司,去她最喜歡的老酒館喝兩杯。我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唯獨不談那些我們採訪過的老兵。
*
為什麼我會幹得出那樣的事?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本來只是個農家子弟,一個在農民家庭長大的人。這是我後來會思索的問題。對,你最終一定會覺得奇怪。唉,我不是個會幹出那種事的人。
*
直至今晚以前,我不算是看過真正的格鬥。日本有些武術表演很文雅,像是液體舞(liquid dances),但今晚的表演卻是貨真價實的打鬥。其中一方眼見就要勝出。他把另一個男人壓倒在草蓆上,用拳頭狠狠揍對方的頭,一次又一次。觀眾會隨著每一下拳頭悶聲發出集體呻吟。挨揍的那個男人想必痛得厲害,但臉上卻看不見任何表情。揍他的那個男人反而表情豐富,像是憤怒或害怕——但我說不出來是憤怒還是害怕。
因為忙著跟攝影師和女譯員交談,我過了很久才離場,並因此跟先前兩位格鬥者在電梯裡湊巧遇上。這時我才看出來,他們其實不算是男人,只算是大孩子。我訝異於我的身高比他們高。但更讓我震撼的是看見他們站在一起,有說有笑。從這個近距離,我可以看見敗方的臉上破了皮︰想必是被草蓆擦傷。基於什麼理由,我對他生起悲憫之心。我很想湊近問他:經歷過方才的激烈打鬥,你是怎樣回到正常生活的?*
「你們這些小王八蛋!混帳東西!」——我們會罵這一類的話,但目的不是整垮他們,而是設法讓他們振奮起來。因為如果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我們搞砸了,他們一上戰場就會死掉。我們得推他們一把,促使他們學會快速反應。所以我們就斥喝他們。他們必須被訓練成懂得恰當反應,對不對?如果他們能變成那樣,那有子彈射過來就避得開。這就是我們那樣做的原因。
*
我對每晚外出消遣感到不自在。它給人一種很不協調的感覺。我一會兒參觀神社,一會兒問一個離死不遠的老人他是怎樣學會刑求,一會兒跟一個得過獎的攝影師邊喝酒邊談美學問題。我不知道要怎樣把這些事兜在一起。情形就像有人用鐵棒撬開了日常生活的縫隙,讓本來被封住的惡魔跑了出來,老是在我們旁邊晃,老是在一切的旁邊晃,令人不得安寧。
事實上,「在旁邊」(next to)就是我對我們三個每天早上和晚上一起消遣的時光。它們都是一些「在旁邊」時刻,是發生在訪談的「旁邊」。這讓它們聽起來毫無分量,而我起初也是這樣認為,直到過了好一陣子才改變想法。有「在旁邊」的東西存在——不管是什麼東西——太重要了。
我反覆思考何謂「在旁邊」,何謂「合得在一塊兒」(fits together)。有一天,我開車前往工作地點途中,車子一度在積雪上打滑,差點撞死人,最後有驚無險,但已足夠嚇人。經過這樣的事情後還照常去工作讓我覺得怪怪的。
在在看來,我以前都是把生活組織得毫無縫隙。
*
那些做不到的人會感到羞愧嗎?
沒有「做不到」這回事……我們會逼他們幹,逼他們捅刀子。
*
就著明尼蘇達州冬天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朋友安妮問我:他們幹麼不自殺算了?安妮是個習慣於問人困難問題的醫生,語氣平和但堅定。她把紅銅色的劉海從眼前撥開,定睛望著我。你為什麼不問他們這個問題?我不曾有過跟加害者打交道的經驗。聽著那些日本老兵回憶往事,我有時會覺得自己正由導遊帶領,參觀地獄。我同時覺得有憑靠和暈眩,同時覺得正在被帶領和迷失方向。為了處理這種矛盾,我採取大部分教授都會用來處理嶄新經驗的方法:透過把事情學術化來控制它。我向很多個方向求助,而大部分幫助是來自藝術與人文學的傳統。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怎樣理解歷史上的大屠殺?不同的宗教和哲學傳統是怎樣看待凶殘的問題,是怎樣把現實中的冷血凶殘跟對更高目的(higher purpose)、存在意義(existential meaning)及「神」(divine)的信仰調和起來?我同時也從社會科學領域獲得很大的幫助。所有種族清洗的共同政治與文化特徵是什麼?把人變成惡魔牽涉哪些組織過程與心理過程?要怎樣才也許可能逆轉這些過程?
這些都是重要問題,我也準備要跟各位分享我找到的答案。但若說本書有一個核心問題,則其性質乃非常不同。那就是:我給各位說書中故事的用意何在?各位聽它們的用意何在?這至今仍是困擾我最甚的問題。正是這問題的存在決定了本書的開展方式,決定了哪些部分重要,哪些部分次要。隨著本書的推進,我將會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問和答這個問題。
以下是第一則故事。
*
阪倉君
然後突然間,從村子裡衝出一群十五、六歲的人。在那之前我從未見過八路軍(中國共產黨的主力軍),不知道敵人是什麼樣子。因為不知道眼前這批人是什麼人,我馬上趴下。有更多人衝了出來。然後我聽到指揮官下令:「開火!統統打死!」於是我便開火。我射出的子彈打中了人。「打到了!」我心想。大部分人像蒼蠅一樣紛紛倒下。
之後我們繼續前進,然後是一片高粱田。當時是六月中,所以那片田看來很大一片。〔比出很大的手勢〕每個人都倒在裡面,或是跑到裡面。我緊追在後。在高粱田裡,有個人倒在地上。我看了看,是個家庭主婦。她倒在地上,已經死去。我心想:「好吧,是個家庭主婦。我沒什麼可以做的。」就在我要繼續往前走時,我注意到那女人手臂下抱著個小嬰兒。一個小嬰兒把頭凸了出來。他的手〔沉默了一下〕……他在找乳房,在摸乳房,明白嗎?然後他抬起頭看著我,向我微笑。我無比震撼。你知道嗎,我發現自己無法走路!然後,更讓人害怕的是︙︙我感到一陣寒意從脊椎竄起。我拚命想往前走,卻動不了。然後一些老鳥來到我背後。「快跑啊!」他們說。敵人正在追擊我們。然後我便跑了起來。事後,我想到那小嬰兒獨自一人待在田裡必死無疑,心裡非常不舒服。這是戰爭第一次讓我有這麼不舒服的感覺。對,真的很不舒服。
*
上述是阪倉君故事的中段。這故事開始之時他是個平民,這故事結束之時他已是個加害者。
告訴我上述故事時,阪倉君已離死不遠,設法要弄明白自己人生的意義。他在戰俘營待了很多年,事後又經歷了更多年的自我放逐,期間不斷反省他做過的事和別人對他做過的事。他犯下過許多凶殘暴行,導致過不可勝數的痛苦,但同時經歷了創傷。事實上,犯下的罪行成了他的創傷。他說,死亡的臨近讓他感到一種「壓力」。「我已經沒有未來……如果我不趕快說出來,如果我死了,這些事情便再沒有人會知道。」阪倉君和其他我訪談過的老兵構成獨特的一群。他們全是「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成員,努力了四十五年,要引起大眾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注意和促進中日兩國的友誼。他們為數約一千一百人,全都在戰後被蘇聯俘虜,若干年後再被引渡到中國,關在撫順監獄。西伯利亞的戰俘營不人道至極,但撫順監獄卻幾乎完全相反,待他們如貴賓︰對他們客客氣氣,給他們足夠飲食,照顧他們的醫藥需要,為他們安排體育和文化活動。這些戰犯也接受了思想改造: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經歷到一種如同宗教轉皈的經驗。他們批判自己過去的價值觀(事實上還批判自己過去的自我),又矢志把餘生貢獻於鼓吹和平。這批日本老兵把他們的轉化形容為「撫順奇蹟」。一九五六年,中國終於對他們召開軍事法庭。四十五個人被起訴,但最終全部無罪獲釋。
一九五七年,這批「中國歸還者」建立起一個正式組織,決計要相互扶持,致力打破日本對戰爭罪行的沉默。雖然受到大眾和主流媒體的輕蔑或冷落,但他們奮鬥不懈,直至二○○二年才因為大部分成員都年邁多病而難以為繼。不久之後,新一代的社會活動家在埼玉縣建立了「歸還者和平紀念館」。館裡收藏了超過二萬本書和相關的錄影帶及照片,擠滿書架和研討桌,樣子更像資源中心和圖書館多於紀念館。我們就是透過館方的引介採訪到那些老兵。
從一開始,我便覺得這些人自視為歷史的產物。他們願意承認自己的罪責,但又視之為一個更大脈絡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上升為亞洲的軍事霸權。自此,這個由神聖天皇統治的國家愈來愈軍國主義化,汲汲於展示實力和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但要確保區域性霸權,日本有需要控制中國的資源。結果就是一場災難性的競賽:「中國統一和日本在中國擴張」之間的競賽。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滿洲,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中日的全面戰爭在六年後爆發,導火線是發生在蘆溝橋的一場軍事小衝突。日本把後續的衝突和自己的所有戰爭罪行說成攸關民族榮耀和使命。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發表的報告把日本的領土野心粉飾為一種準人道主義介入:「我大和民族現今正流著『血』,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以達成我們在世界史的使命。為實現亞洲十億人民的解放,更為維持我們在大東亞共榮圈的領導地位,我們必須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這些『土壤』。」
帝國託辭獲得宗教託辭的回應。就連禪宗學者亦聯名指出,中國已成了一個不明佛理因此亟待拯救的國家,說是透過日本高一等的精神了悟,中國的「不可理喻性將會獲得糾正」。「透過一場慈悲戰爭,交戰國家將能夠改善自己,並帶來戰爭本身的戢止。」
這個脈絡是那些「中國歸還者」想向我(做為一個美國人)強調的。我們談話的當時,美軍正在佔領伊拉克。什麼事都總有一個脈絡。
*
凶殘既要求再現(representation)又抗拒再現。我們必須為凶殘當見證,我們必須把凶殘的故事說出來——這種信念居於人權工作的核心。我們之所以搜集證言,調查戰爭罪行的細節,是出於道德責任的要求。這種道德責任在法律起訴有現實可能性時最為迫切,但它在那些沒有了起訴可能但繼續矢口否認罪行和歷史修正主義大盛的地方(日本就是這個樣子)一樣有力。我們是在為未來世代創建一個我們時代的道德檔案庫。我們是在為那些個人最深真理每天都受到否認的倖存者締造可理解的公共歷史。而有時,我們是在(正如果我訪談過的老兵所認為的)利用一個「安全於想像」(safeto-imagine)的過去使目前正上演著的事情變得顯眼。近幾十年來,日本的政府官員、學者和各級前軍官一再否認和輕描淡寫化日本帝國犯下的暴行。一九九四年,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把南京大屠殺(估計有三十萬平民被殺害)說成是「虛構」。永野事後雖道歉,但卻措詞謹慎,只願稱南京大屠殺為「南京事件」。二○○七年,首相安倍俊太郎否認曾有韓國婦女被強迫充當慰安婦。二○○一年,文部省大臣贊同修訂歷史課本,刪去跟日本戰爭罪行有關的部分(包括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以中國平民實驗細菌生化武器等)。二○○五年,一位日本學者在著作中指斥已故華裔作家張純如不該繼續散播「南京發生過大屠殺的神話」。這樣的事例所在多有,此處只是列舉三四。維瑟爾(Elie Wiesel)說過,遺忘就是把一個人殺兩次。如果此言不假,那中日戰爭就迄未停止。它只是轉到記憶的領域開打罷了。
所以,我們三人(攝影師、女譯員和我)一開始是抱著同一個假定投入工作:不管在這個個案還是其他個案,為凶殘留下見證都是正確的事。不管是在罪行發生當時揭發罪行,還是事隔多年後搜集和分享證言,都是人權努力所理所當為。這是一場記憶之戰,有著黑白分明的道德立場︰要不是說出來就是沉默,要不是抵抗就是同謀。
但我已不再那麼確定。
再現苦難包含著一個弔詭。一方面,想阻止繼續有人受到傷害,我們必須說出發生過什麼事;但在說故事的過程中,我們有可能會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傷害到他人。我們想要讓加害者羞愧,但有時卻會刺激得他們更為暴力;我們想從旁觀者身分引發惻隱之心,但有時卻會讓他們愈來愈麻木,甚至憎厭;我們想要給倖存者帶來療癒的聲音,但有時卻會讓他們二度受創傷;我們想要把遙遠的陌生人變成鮮明具象的人,但有時卻會把他們化約為抽象和只有二度空間的「受害者」。
搜集證言是一種尊重倖存者和死者的舉動,也是對抗集體凶殘反覆上演的一座真實小碉堡。但收集和分享證據卻會觸發一個我們無法控制的連鎖反應過程。它同樣會引起傷害。在從事本專案的過程中,我開始相信收集加害者證言這工作需要戴著道德近視眼(moral myopia),甚至帶著一點自大。我看不出來還有別的路徑可以穿過這工作所引起的一大堆棘手問題︰在受害者無法說出他們故事的情況下,你說出加害者的故事會有什麼風險?當你一再聆聽和記錄加害者懇求寬恕,久而久之會不會變成一種對寬恕的默許(一種你無權給予或拒絕的寬恕)?你做這事的動機是什麼?是出於責任感的召喚,是出於孤芳自賞的道德正義感,還是出於作家對聳動材料的渴望?呈現最邪惡和殘忍的細節是否只是在販賣色情?沒這樣做是否就是一種道德上的懦弱?如果你進行自我審查,不去再現創傷,此舉是否就保護了創傷,讓它免受侵入性瞪視、簡化和解剖的蹂躪?還是說此舉只代表不理會創傷對再現的呼求,並重演了旁觀者的袖手旁觀(正是這種袖手旁觀讓凶殘從一開始得以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