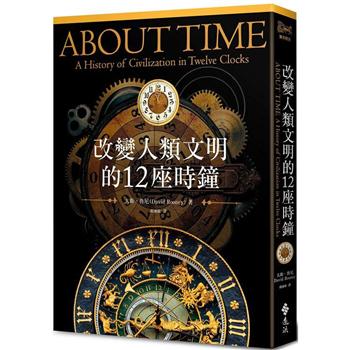事情要從阿波羅十七的登月計畫說起。當時打算在太空船上搭載一顆小型時鐘,觀察它往返月球後的情形。會這麼做,是因為當時科學界和天文界都亟欲驗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因為相對論認為,時間在不同的重力場下,如果以不同的速度移動,應該會導致時間變快或變慢。一位鐘錶匠在一九七二年時就曾說:「事實上,大家普遍覺得,這可能會是太空旅遊史上最讓人興奮的科學實驗。」然而,時間的差異變化實在太細微了,如果真的要能顯現出來,上太空所使用的時鐘必須非常精密才行。
那次阿波羅登月計畫中,科學家所遭遇的問題在於,當時最精密的時鐘——也就是原子鐘——可運用原子的特性來計時,但本身非常笨重、脆弱,而且很耗電。另一方面,體積小又重量輕到足以放進太空船的石英鐘,卻又不夠精確,在太空旅行中會受到干擾。還好,在德國慕尼黑有兩位科學家恩斯特.耶哈特和蓋哈特.胡布納,他們在耶哈特家的地下室想出一個解決之道。這兩位德國科學家在一九七一年成立一家名為艾夫拉原子(Efratom)的公司,在此打造了微型原子鐘,大小只有十立方公分,重量只有一.三公斤,而且幾乎不需要電力運作。他們在一九七二年推出這款微型原子鐘,成為史上最小的原子鐘,充分符合可以在外太空實驗室中驗證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條件。這麼一來,想把超精密的時鐘送上太空的任務,似乎完成了。
於是,阿波羅十七太空船搭載時鐘登月的計畫似乎已經就緒,只等升空,沒想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就離它在佛羅里達州發射台發射前八週時,美國太空總署卻臨時終止了時鐘登月的實驗——真讓所有人失望。不過,不到幾個禮拜的時間,耶哈特和胡布納公司又出現意外的訪客帶來好消息。
兩位訪客是遠從美國麻州來的鐘錶商羅伯.肯恩和亞瑟.麥科布里,他們和美國海軍研究室合作製造軍事衛星NTS一號,預計要在一九七四年升空。他們此行是為了找兩顆微型原子鐘,體積要小到可以裝進有限的衛星載物艙,因為時間緊迫,他們來不及自己研發了,剛好聽說阿波羅十七號登月計畫原本打算採用艾夫拉原子公司的德製時鐘,這正好是他們在找的東西。肯恩和麥科布里因此不辭千里往返美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買到這些鐘,將之帶回美國,加以改裝並放進衛星。一九七四年七月,NTS一號衛星被送上地球軌道,上面就搭載了艾夫拉原子鐘。這次航程成為美國導航星全球定位系統——即GPS的初期試航。這兩座在慕尼黑郊區製成的微型時鐘,成為史上首度登上太空的原子鐘。
早從一七五○年代起,時鐘就成為導航的核心工具。約翰.哈里森的經線儀首次證明,只要善用計時技術加上天文觀測,就能在航程中使軍事和商業艦隊得到辨知自己位置的方式,儘管大海再浩瀚無際,也能夠自由航行。相隔兩百年後,同樣的問題再次浮現,只是這次稍有不同。一九五○年代,美國海軍正在建造彈道飛彈系統,以做為對抗蘇聯的軍事防禦武器。這套系統一旦完成,就可以極度精確的命中任何目標,但它有一個障礙需要克服,那就是——這些飛彈都是從北極星飛彈潛艇(Polaris)上發射出來的,飛彈的命中率仰賴發射潛艇能夠得知自身的位置。但是,當時潛艇本身的導航系統卻還不夠精準,再加上潛在水底,也不可能靠天體如太陽、星星、月亮來輔助定位,所以迫切需要發展一套系統,可以讓潛艇一浮出水面,立刻獲得定位。
一九五七年,當蘇聯發射了全球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號後,這個問題迎刃而解。因為,當美國科學家使用無線電波追蹤這顆蘇聯人造衛星時,他們發現,如果把同樣的系統反轉過來,就可以解決定位問題,也就是說,要是能夠知道人造衛星在太空的確切位置,那就可以得知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到了一九六○年代,美國海軍所屬人造衛星導航系統「中天」(Transit)和「時儀」(Timation)就依此理論成功運作,同時空軍也擁有另一套六二一B的定位計畫。
就這樣,美國國防部慢慢將這些實驗性計畫運用到國防戰略上,並且也發現,這可能在科技和政治兩方面都具有更多樣和龐大的運用。當年主導全球定位系統計畫的布萊佛.帕金森說明:「到了一九七二年,有幾位國防部的高層官員就意識到,新的衛星導航系統可能會成為多種軍事運用上的重要資產。當時,美國國防部必須仰賴上百種的定位和導航系統來作戰,這些系統維護和升級都非常花錢。」一九七三年九月勞動節那個週末,五角大廈舉辦了三天的工作坊座談,他們設想即將成形的GPS種種細節,讓它可以結合海軍和空軍所有定位系統的優點,並確立新式全球定位系統的主要運作原則。同年十二月,美國國防部放行全球定位系統的籌建工作。
整個定位系統成功的關鍵,就是把這些小型、耐得住太空環境的原子鐘,送上許多人造衛星組成的太空艦隊上。每一座全球定位系統人造衛星都裝載數顆這種原子鐘,這些時鐘以光速將高度精確的報時信號傳回地球。在地球這端的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會搜尋四座不同的人造衛星所發射的報時信號。每一座人造衛星都位於太空不同的位置,其與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的距離也各自不同,所以每一座接收器所接收到的報時信號都會出現細微的差異,就是靠著這極其細微的時差,這些接收器就可以使用三邊測量法(trilateration)計算自己在地球上的定位。全球衛定位系統接收器這端所使用的時鐘,並不需要太精密,因為它所有報時資訊都由衛星信號提供,這表示接收器的生產成本和難度都得以降低。但絕對不能缺少的,就是由人造衛星所搭載的原子鐘一定要準確無比才行。
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初期,幾次人造衛星導航系統的測試中,初期使用的都是石英鐘,但石英鐘無法達到軍事用途所需要的準確度。一當恩斯特.耶哈特和蓋哈特.胡布納所研發的微型原子鐘在一九七二年派上用場後,這個精確度的問題似乎也被解決了。緊接著,一九七四年NTS一號衛星搭載微型原子鐘的測試結果,也相當令人滿意。但是,航太工程師很清楚,要用在全球定位系統的人造衛星上,原子鐘的強韌度還要再更高,因為它必須要在人造衛星環繞地球軌道經年累月的過程中,沒有絲毫差錯。這就像是再次重演十八世紀解決經度問題的情形。當初,約翰.哈里斯也好不容易才設計出一款經線儀,既能夠體積上小於當時的時計科技,又能夠在精確度及長期運作的可靠度上都獲得強化。另外,這些新的海上時計也要更強韌,才能面對長途海上航程中的種種惡劣環境,像是狂風巨浪下的晃動,或溫度的驟變等。同樣的,送上太空的時鐘,必須能夠承受幅射線的洗禮、真空環境、重力變化等。
一九七三年,NTS一號衛星還沒升空進行測試之前,耶哈特和胡布納的艾夫拉原子公司在加州另一家名為洛克威爾的公司旁設廠,洛克威爾公司在一九七四年收到國防部合約,要為全球定位系統的衛星艦隊製造原子鐘。靠著這兩家公司的合作,將艾夫拉原子公司劃時代的微型原子鐘改造成足以肩負全球定位系統重任的強韌度。之後,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搭載著這種新型堅韌原子鐘的人造衛星,就被一一送上太空,這些衛星都是靠改良過的美國老式洲際彈道飛彈推進太空。到了一九九五年,在這十七年的時間裡,美國總共送了十三部全球定位系統人造衛星進入地球軌道,至此這個定位系統的第一階段任務終於達成,全球定位系統得以全面運作。因為這些原子鐘,戰爭和日常生活的樣態全改變了,雖然過去歷代的新式時鐘也曾經締造歷史,但這次改變的程度之大,至今我們都還無法完全掌握。
我們也可以看看像湯瑪斯.莫瑟這類公司的產品。莫瑟是專事生產航海經線儀的公司,這些經線儀過去幫助過各國海軍征戰各大洋,建立起帝國的海外殖民地,不過,一等冷戰時代有了無線電波導航,經線儀被取代後,這些公司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莫瑟公司只能與時俱進。英國北極星號飛彈上所搭載的核彈頭,希望設計成在還沒擊中目標前就由計時器引爆,以發揮最大的殺傷力。但在空襲現場,會有其他飛彈同時引爆,其產生的電磁波脈衝,會破壞一般的電子計時器,莫瑟於一九八二年製造一款強化式作戰用機械計時器,這成了該公司在核子時代的新商機。這類計時器,現在也有在博物館中展示,只是因為其外觀不甚起眼,所以常被忽視。其實我們可以看得更仔細點。
一九四七年,瑪朵.蘭斯朵夫設計了「末日之鐘」,發表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以此表達她對於核子問題的焦慮。這只鐘的時間設在午夜前七分鐘,意指時日無多。之後,鐘上的指針經常有不同的變動,以反映全世界人們對於西方國家大災難迫近或強或弱的擔憂之情。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該公報的顧問團將末日之鐘的指針調到午夜前一百秒,這也是這座鐘問世以來離末日最近的一次。時鐘之所以被用來揭示核子世界末日,這是因為它會督促我們去思考,當末日來臨時,會有什麼下場。
除了為戰爭特製的鐘以外,我們也可以看看一整代的時計,如何因應戰爭需要而改變功能,進而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許多現代人每日不離身的手錶,其實和戰爭也有很大的關係。一八九九到一九二○年的南非戰爭,及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兩次戰爭中,士兵開始將懷錶改戴到手腕上,這樣才能夠依手錶計時,確定大家同時發動攻擊,同時還有另一隻手可以使用武器。其實,在這之前,手錶就已經存在了,但功能僅是女性首飾,或是女性騎單車、騎馬時配戴的。戰爭的需求讓原本女性專用的手錶成為男女皆可使用的道具,也讓市場需求翻倍,懷錶的市場快速走入黃昏。現在產值高達數百億的手錶市場,竟然是靠著兩次殘酷戰爭打開的。
放眼整體人類,甚至還能看到,所有人的生活作息,竟然也都直接受到戰爭需求所影響。本書稍早提到過日光節約時間,在夏季把時鐘調快一個鐘頭,以求早點起床——正是因為戰爭,讓這個原本只是老百姓自行發想的小眾念頭,成為軍隊求之不得的聖品,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生產軍火的工廠產能全開,但供給照明和電力的燃料卻極為短缺,在這種情形下產生這個需求。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時鐘如何廣泛的助長戰時生產力,但連戰後承平時期的生活模式也跟著被改變。
以上不過只是少數,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這些在在顯示,科技的發展,往往是因為戰爭的需要而出現、加速或是加以改變,時鐘就是這些戰爭科技發展中最核心的一環。時鐘就跟子彈、炸彈一樣,一直是戰爭武器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同為時鐘,全球定位系統讓時鐘武器化的程度,卻是全球軍事史上前所未見的。
(未完,詳見〈第十二章 戰爭〉)
那次阿波羅登月計畫中,科學家所遭遇的問題在於,當時最精密的時鐘——也就是原子鐘——可運用原子的特性來計時,但本身非常笨重、脆弱,而且很耗電。另一方面,體積小又重量輕到足以放進太空船的石英鐘,卻又不夠精確,在太空旅行中會受到干擾。還好,在德國慕尼黑有兩位科學家恩斯特.耶哈特和蓋哈特.胡布納,他們在耶哈特家的地下室想出一個解決之道。這兩位德國科學家在一九七一年成立一家名為艾夫拉原子(Efratom)的公司,在此打造了微型原子鐘,大小只有十立方公分,重量只有一.三公斤,而且幾乎不需要電力運作。他們在一九七二年推出這款微型原子鐘,成為史上最小的原子鐘,充分符合可以在外太空實驗室中驗證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條件。這麼一來,想把超精密的時鐘送上太空的任務,似乎完成了。
於是,阿波羅十七太空船搭載時鐘登月的計畫似乎已經就緒,只等升空,沒想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就離它在佛羅里達州發射台發射前八週時,美國太空總署卻臨時終止了時鐘登月的實驗——真讓所有人失望。不過,不到幾個禮拜的時間,耶哈特和胡布納公司又出現意外的訪客帶來好消息。
兩位訪客是遠從美國麻州來的鐘錶商羅伯.肯恩和亞瑟.麥科布里,他們和美國海軍研究室合作製造軍事衛星NTS一號,預計要在一九七四年升空。他們此行是為了找兩顆微型原子鐘,體積要小到可以裝進有限的衛星載物艙,因為時間緊迫,他們來不及自己研發了,剛好聽說阿波羅十七號登月計畫原本打算採用艾夫拉原子公司的德製時鐘,這正好是他們在找的東西。肯恩和麥科布里因此不辭千里往返美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買到這些鐘,將之帶回美國,加以改裝並放進衛星。一九七四年七月,NTS一號衛星被送上地球軌道,上面就搭載了艾夫拉原子鐘。這次航程成為美國導航星全球定位系統——即GPS的初期試航。這兩座在慕尼黑郊區製成的微型時鐘,成為史上首度登上太空的原子鐘。
早從一七五○年代起,時鐘就成為導航的核心工具。約翰.哈里森的經線儀首次證明,只要善用計時技術加上天文觀測,就能在航程中使軍事和商業艦隊得到辨知自己位置的方式,儘管大海再浩瀚無際,也能夠自由航行。相隔兩百年後,同樣的問題再次浮現,只是這次稍有不同。一九五○年代,美國海軍正在建造彈道飛彈系統,以做為對抗蘇聯的軍事防禦武器。這套系統一旦完成,就可以極度精確的命中任何目標,但它有一個障礙需要克服,那就是——這些飛彈都是從北極星飛彈潛艇(Polaris)上發射出來的,飛彈的命中率仰賴發射潛艇能夠得知自身的位置。但是,當時潛艇本身的導航系統卻還不夠精準,再加上潛在水底,也不可能靠天體如太陽、星星、月亮來輔助定位,所以迫切需要發展一套系統,可以讓潛艇一浮出水面,立刻獲得定位。
一九五七年,當蘇聯發射了全球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號後,這個問題迎刃而解。因為,當美國科學家使用無線電波追蹤這顆蘇聯人造衛星時,他們發現,如果把同樣的系統反轉過來,就可以解決定位問題,也就是說,要是能夠知道人造衛星在太空的確切位置,那就可以得知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到了一九六○年代,美國海軍所屬人造衛星導航系統「中天」(Transit)和「時儀」(Timation)就依此理論成功運作,同時空軍也擁有另一套六二一B的定位計畫。
就這樣,美國國防部慢慢將這些實驗性計畫運用到國防戰略上,並且也發現,這可能在科技和政治兩方面都具有更多樣和龐大的運用。當年主導全球定位系統計畫的布萊佛.帕金森說明:「到了一九七二年,有幾位國防部的高層官員就意識到,新的衛星導航系統可能會成為多種軍事運用上的重要資產。當時,美國國防部必須仰賴上百種的定位和導航系統來作戰,這些系統維護和升級都非常花錢。」一九七三年九月勞動節那個週末,五角大廈舉辦了三天的工作坊座談,他們設想即將成形的GPS種種細節,讓它可以結合海軍和空軍所有定位系統的優點,並確立新式全球定位系統的主要運作原則。同年十二月,美國國防部放行全球定位系統的籌建工作。
整個定位系統成功的關鍵,就是把這些小型、耐得住太空環境的原子鐘,送上許多人造衛星組成的太空艦隊上。每一座全球定位系統人造衛星都裝載數顆這種原子鐘,這些時鐘以光速將高度精確的報時信號傳回地球。在地球這端的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會搜尋四座不同的人造衛星所發射的報時信號。每一座人造衛星都位於太空不同的位置,其與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的距離也各自不同,所以每一座接收器所接收到的報時信號都會出現細微的差異,就是靠著這極其細微的時差,這些接收器就可以使用三邊測量法(trilateration)計算自己在地球上的定位。全球衛定位系統接收器這端所使用的時鐘,並不需要太精密,因為它所有報時資訊都由衛星信號提供,這表示接收器的生產成本和難度都得以降低。但絕對不能缺少的,就是由人造衛星所搭載的原子鐘一定要準確無比才行。
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初期,幾次人造衛星導航系統的測試中,初期使用的都是石英鐘,但石英鐘無法達到軍事用途所需要的準確度。一當恩斯特.耶哈特和蓋哈特.胡布納所研發的微型原子鐘在一九七二年派上用場後,這個精確度的問題似乎也被解決了。緊接著,一九七四年NTS一號衛星搭載微型原子鐘的測試結果,也相當令人滿意。但是,航太工程師很清楚,要用在全球定位系統的人造衛星上,原子鐘的強韌度還要再更高,因為它必須要在人造衛星環繞地球軌道經年累月的過程中,沒有絲毫差錯。這就像是再次重演十八世紀解決經度問題的情形。當初,約翰.哈里斯也好不容易才設計出一款經線儀,既能夠體積上小於當時的時計科技,又能夠在精確度及長期運作的可靠度上都獲得強化。另外,這些新的海上時計也要更強韌,才能面對長途海上航程中的種種惡劣環境,像是狂風巨浪下的晃動,或溫度的驟變等。同樣的,送上太空的時鐘,必須能夠承受幅射線的洗禮、真空環境、重力變化等。
一九七三年,NTS一號衛星還沒升空進行測試之前,耶哈特和胡布納的艾夫拉原子公司在加州另一家名為洛克威爾的公司旁設廠,洛克威爾公司在一九七四年收到國防部合約,要為全球定位系統的衛星艦隊製造原子鐘。靠著這兩家公司的合作,將艾夫拉原子公司劃時代的微型原子鐘改造成足以肩負全球定位系統重任的強韌度。之後,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搭載著這種新型堅韌原子鐘的人造衛星,就被一一送上太空,這些衛星都是靠改良過的美國老式洲際彈道飛彈推進太空。到了一九九五年,在這十七年的時間裡,美國總共送了十三部全球定位系統人造衛星進入地球軌道,至此這個定位系統的第一階段任務終於達成,全球定位系統得以全面運作。因為這些原子鐘,戰爭和日常生活的樣態全改變了,雖然過去歷代的新式時鐘也曾經締造歷史,但這次改變的程度之大,至今我們都還無法完全掌握。
我們也可以看看像湯瑪斯.莫瑟這類公司的產品。莫瑟是專事生產航海經線儀的公司,這些經線儀過去幫助過各國海軍征戰各大洋,建立起帝國的海外殖民地,不過,一等冷戰時代有了無線電波導航,經線儀被取代後,這些公司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莫瑟公司只能與時俱進。英國北極星號飛彈上所搭載的核彈頭,希望設計成在還沒擊中目標前就由計時器引爆,以發揮最大的殺傷力。但在空襲現場,會有其他飛彈同時引爆,其產生的電磁波脈衝,會破壞一般的電子計時器,莫瑟於一九八二年製造一款強化式作戰用機械計時器,這成了該公司在核子時代的新商機。這類計時器,現在也有在博物館中展示,只是因為其外觀不甚起眼,所以常被忽視。其實我們可以看得更仔細點。
一九四七年,瑪朵.蘭斯朵夫設計了「末日之鐘」,發表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以此表達她對於核子問題的焦慮。這只鐘的時間設在午夜前七分鐘,意指時日無多。之後,鐘上的指針經常有不同的變動,以反映全世界人們對於西方國家大災難迫近或強或弱的擔憂之情。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該公報的顧問團將末日之鐘的指針調到午夜前一百秒,這也是這座鐘問世以來離末日最近的一次。時鐘之所以被用來揭示核子世界末日,這是因為它會督促我們去思考,當末日來臨時,會有什麼下場。
除了為戰爭特製的鐘以外,我們也可以看看一整代的時計,如何因應戰爭需要而改變功能,進而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許多現代人每日不離身的手錶,其實和戰爭也有很大的關係。一八九九到一九二○年的南非戰爭,及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兩次戰爭中,士兵開始將懷錶改戴到手腕上,這樣才能夠依手錶計時,確定大家同時發動攻擊,同時還有另一隻手可以使用武器。其實,在這之前,手錶就已經存在了,但功能僅是女性首飾,或是女性騎單車、騎馬時配戴的。戰爭的需求讓原本女性專用的手錶成為男女皆可使用的道具,也讓市場需求翻倍,懷錶的市場快速走入黃昏。現在產值高達數百億的手錶市場,竟然是靠著兩次殘酷戰爭打開的。
放眼整體人類,甚至還能看到,所有人的生活作息,竟然也都直接受到戰爭需求所影響。本書稍早提到過日光節約時間,在夏季把時鐘調快一個鐘頭,以求早點起床——正是因為戰爭,讓這個原本只是老百姓自行發想的小眾念頭,成為軍隊求之不得的聖品,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生產軍火的工廠產能全開,但供給照明和電力的燃料卻極為短缺,在這種情形下產生這個需求。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時鐘如何廣泛的助長戰時生產力,但連戰後承平時期的生活模式也跟著被改變。
以上不過只是少數,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這些在在顯示,科技的發展,往往是因為戰爭的需要而出現、加速或是加以改變,時鐘就是這些戰爭科技發展中最核心的一環。時鐘就跟子彈、炸彈一樣,一直是戰爭武器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同為時鐘,全球定位系統讓時鐘武器化的程度,卻是全球軍事史上前所未見的。
(未完,詳見〈第十二章 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