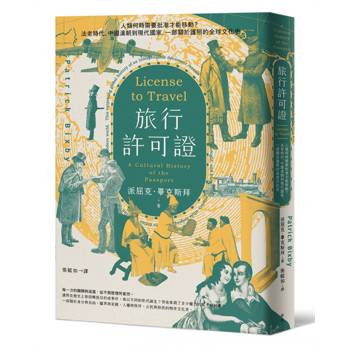序言
開始構思這本書時,我們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那裡沒有人聽過新冠病毒,沒有人預想過,即將到來的大流行竟然讓所有人措手不及。但當我以牌桌和折疊椅匆忙布置了居家辦公室,坐下來寫出幾頁文字時,卻已經生活在新的現實中:世界各地的民族國家*開始關閉邊界,限制內部流動,並要求訪客和返國公民進行隔離。幾乎在所有地方,緊急措施都大大減緩曾經定義全球互聯時代的流動和移民的加速步伐。人們的集體行動自由普遍受到根本的限制。
許多想去旅行的人連續幾個月都被迫關在家裡,在對前往遙遠目的地的念頭與對感染和強制隔離的恐懼之間搖擺不定;還有些人被困在遠方,因為旅行禁令或取消的航班而無法和親人相聚。當然,限制行動自由對那些必須越過邊界才有機會生存的移民、難民和其他弱勢群體造與對其他人的影響截然不同。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旅行證件似乎每天都具有新的含義,因為護照效力排名開始出現變化,因為出現疫苗護照提案,因為護照申請人在收到證件的過程中經歷長時間的耽誤。
這個全球幾乎停止流動的時刻是一段奇怪的時光,讓人開始思考旅行證件的悠久歷史。撰寫本書中的漫遊者故事,重溫他們跨越國界和跨越文化的經歷,同時卻不得不待在原地,實在稱得上怪異。但這也是完美的時機,讓人以好奇的態度,詳述這些關於旅行和流動、遷移及混亂的故事。我希望讀者在悠遊本書時能了解我所說的感受,無論他們閱讀的場所是在某個安靜、靜止的空間,或者更好的是,在狹窄的客機艙內滑翔到高空,在高速火車中看著向後衝去的陌生風景,或在某處的公共汽車後座一路顛簸。(後略)
導論:「我所擁有最珍貴的書」
一本小書,裡面有三十多頁厚紙,封面是粒狀的硬紙板,上面印著國家的名字、標誌,以及護照的英文「passport」或是在其他語言中的對應詞。根據發行國的不同,護照可能是紅色、綠色、藍色或黑色,但根據近一個世紀前首次制定的國際標準,其尺寸始終易於一手掌握,內頁一定會有一頁個人資料頁,其中包含序列碼、持有人的照片以及一系列個人詳細資訊。當護照邊角明顯磨損時,頁面起皺和髒汙時,裝飾著五顏六色的入境印章和搶手的簽證時,這份證件就成為在世界中漫遊者的護身符和生活故事的概要,無論他們是握有特權的遊客,或是絕望的移民。護照擁有一種奇怪的力量,可以準確地控制我們能去哪裡,不能去哪裡。護照可以提供安全通向遠方新生活的保證;可以使人們逃離危險、限制或只是平凡的熟悉環境;可以讓人快速來到隊伍最前頭,或者在海關的小房間裡受到不必要的審查。護照讓我們得以跨越各種邊界─地理上的,但也包括文化、語言、經濟、法律─去尋找在國內無法實現的事物,然後安全返國。在《跨越這條線》(二○○二)一書中,薩爾曼.魯西迪(他是全球移民和說故事大師)不帶諷刺地聲稱,「我所擁有最珍貴的書是我的護照。」他承認,儘管針對一個看似平凡無奇的物件下如此斷言顯得很誇張,但對他來說一點也不為過。是的,做為不可或缺的旅行證件,護照具有實用功能(絕不能弄丟);是的,我們可能不是特別喜歡護照裡的照片(如果可以請忽略);是的,我們可能會自滿地認為,護照會達成任務,並讓我們通過邊境管制官員(或現在的護照自動通關櫃臺)的檢查。但如果確實加以關注,護照就會開始接受更多的心理投資,承擔更多的情感重量,在此過程中成為「珍貴」的物件,而不僅具有實際或物質價值。魯西迪之所以會這麼說,主要是因為了解,並非所有護照都能如此輕鬆或不引人注目地完成工作。這位小說家講述了關於他的第一本護照的生動記憶,這是他在一九六○年代攜帶的一本印度護照,從其頁面可以了解,持有人所能造訪的國家少得可憐。當他十幾歲拿到英國護照時,感覺世界彷彿突然向他敞開大門,很快地,這本「小書」把他從家鄉帶到劍橋大學受教育,並踏入倫敦的文學圈。這本小書也極其直接與簡潔地講述他分裂的英印身分的故事;這本小書伴隨這位流浪作家環遊世界;這本小書在要求持有者行動自由的同時,針對他的生活可能發生的事情,宣告一系列的承諾。
因此,護照是最私人的文物,然而,正如魯西迪的故事所展示的,這本小書只有在對照於更廣大的國家和帝國歷史,才具有其私人的價值。他擁有印度護照的原因是,他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生後僅幾個月,印度就脫離英國獨立,並停止使用英屬印度護照。幾乎同時,次大陸的分裂和巴基斯坦這個新國家的建立,在魯西迪和他的大家庭多數成員之間劃出一條國際邊界。很快地,邊境兩邊的家人若想團聚都需要護照。但幾十年來,管轄範圍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秩序並不允許印度新主權領土的護照持有人大量進入,即使在今天,其他國家對印度公民的免簽證入境也遠少於對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公民。
可以肯定的是,護照與國家的興起和國際關係的演變密切相關,因此不斷涉入公民身分、全球移民、尋求庇護、國家安全及相關考量的規範中。它賦予個人官方身分,並推進國家在監測和控制某些民族和人口移動的努力。這就是護照不斷得到的悖論:儘管它承諾獨立和移動、冒險和機會、逃難和避風港,但表面上確保國土安全和跨國境交通管制的護照,卻也是政府監視和國家權力的重要工具。換句話說,它在個人和政治之間的連結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這種獨特的定位意味著,護照這樣的小書有能力講述歷史檔案中其他證件幾乎不曾講述的故事:護照提供人們流離失所的有形紀錄,為個人回憶錄和旅行故事補充說明,但也總是捲入更廣大的文化和政治歷史潮流中。魯西迪早期的護照講述的是關於他的身分認同,以及形塑過程中不可避免發生的種種,兩者之間的關係。多年後,他的英國護照還訴說他如何躲避伊朗最高領導人對他提出的伊斯蘭教令,對方在《魔鬼詩篇》(一九八九)出版後要求處決魯西迪*;以及在對追殺令的恐懼消退之後,與他有關的全球名人、學術任命、知名朋友和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的故事。護照因此詳述了一個看來真實的規則,那就是我們必須「屬於」一個地方,並且只能在「得到允許」時進入其他地方。護照講述關於這個時代一些最重要想法的故事,例如「現代性」、「民族」、「全球化」,儘管它們所說的故事比這些崇高的抽象概念所暗示的更貼近個人。它們提醒我們,在歷史的某個時刻,人類開始依賴國家做為身分和保護的來源,而在這個快速全球旅行和即時電子通訊的時代,這種
依賴只會變得更加難以擺脫。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仔細觀察這些珍貴的物件─仔細閱讀這些小書─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理解,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中與移動和遷移相關的情感和想像。
十八世紀現代領土型國家的興起,為國際邊界的劃定和控制提供新的動力,同時也為追蹤和管理其公民的移動提供新的方法。一個不管多麼日薄西山的國家只要還在,它仍然是這個流動性和連動性漸增的世界的一員,而在這個世界中,護照在促進人民和資本跨境流動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導致世界各國政府強化邊界管理,透過訓練有素的安全人員加強對乘客的篩檢、提高身分識別要求及其他新的監視技術。此後的幾年裡,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運動也有所抬頭,對新來移民表現出仇外態度,並呼籲採取旅行禁令和邊境牆等反動措施。但這一切都未能阻止人們移動。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估計,二○一九年有十五億國際遊客造訪,比二○○○年的六億八千一百萬人次增長兩倍多,比一九五○年全球旅行開始從二戰破壞中恢復過來的二千五百萬人次增長六十倍,或許是最能說明全球移動力的統計數據。移民的急劇上升,至二○一九年達到約二億六千萬人次。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如此多的人有能力或不得不跨越這些人為的界線;在國家的歷史上,這些路線從未像現在如此具有穿透性。就連全球性的疫情也無法長時間減緩全球移動力的步伐。(後略)
第二章 偉大的君主,偉大的旅客
我們之所以知道馬可波羅的旅程,幾乎完全是由於他在一二九五年從中國返回義大利不久,因為威尼斯軍隊和熱那亞的衝突意外遭到監禁(如果真有其事)。在那幾個月期間,為了打發獄中時光,他向獄友講述在東方旅行的奢華故事,而對方恰好是義大利浪漫主義作家魯斯蒂謙.達.比薩。這位作家(許多人認為是寫手)隨後將這些故事與其他故事相結合,包括他自己的亞瑟王傳奇故事和其他最近從中國回來的報導,創作了我們所知的巨作《馬可波羅遊記》。該文本迅速以各種翻譯版本在歐洲流傳,很快地就在西方理解遠東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馬可波羅經常被認為是第一個沿著絲綢之路冒險的歐洲人,但來自該大陸的其他冒險家也曾進入蒙古帝國,包括魯不魯乞和若望.柏郎嘉賓*在內的少數人甚至留下旅程的描述。但沒有人像馬可波羅旅行的範圍如此廣大,他離開威尼斯大約二十四年,穿越中國、印度、日本和其他遙遠的領域。也沒有人製作出如此引人入勝、有趣且廣為流傳的旅行報導。這一切都曾發生,馬可波羅踏上旅程,並活著講述這個故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些相當了不起的旅行證件。
廣闊的絲綢之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曾引發各種努力來控制、保護並促進人員和貨物的流動(更不用說思想和其他傳染病),這些努力預示著當代管理全球化流動的技術。在十三世紀,經過多年的破壞,成吉思汗企圖重建貿易路線,並將其置於統一的政治管理之 下,這有助於建立西臨黑海、東臨太平洋的蒙古帝國。在這裡,沿著商隊走過的看似無邊無際的道路網絡,旅行證件的使用再次站穩腳跟。為管理所謂的蒙古治世,追隨成吉思汗的幾位大汗經常提供使節和其他官員經久耐用的木、銅、銀或金製的牌子,提供旅行者穿越蒙古土地的安全通道,以及向沿途人口索取各種商品和服務的權利。鑑於這些利益,蒙古的地方政府濫用權限,發布允許虐待和剝削路邊居民的非官方通行牌。但可汗官方頒發的金牌很特別:它們聲稱,此君主授權之物的持有者,得橫越其領土,並得進入絲綢之路沿途涵蓋的其他司法管轄區。毫無疑問,收到這種牌子的最知名人士就是富有冒險精神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儘管他甚至不是第一個被授予此影響深遠特權的威尼斯人:一二六六年,成吉思汗的孫子,知名的忽必烈曾贈送金牌給他的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菲奧,讓他們得以從大都(今北京)長途跋涉回家。
身為最早一批穿越絲綢之路的歐洲人,波羅兄弟受到大汗的極大好奇和慷慨對待,大可汗已經熟悉「拉丁人」,但希望獲得有關西方政治和宗教事務的更多知識,尤其是天主教會。
忽必烈推測,他有可能受用於羅馬教會的智慧和權威,來平息自己龐大帝國的動亂,於是派遣波羅兄弟和一名使者向教皇提出請求:他應該派遣一百名教士,「以清楚的理由表明基督教比他自己的宗教更好」,另外加上帶回「從耶路撒冷耶穌聖陵上方長明燈中提取的聖油。」為了在這段馬拉松式的歸途中保護這對兄弟,蒙古君主給予這隊義大利商人一塊長約二十五公分,寬約七.五公分的金牌,上面刻著一道令人生畏的命令,大致翻譯為:「奉永世的蒼天之力,以可汗的名字為聖,不尊者死。」正如《馬可波羅遊記》所明確指出的,一個在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很可能會誤入歧途,導致監禁、奴役或立即處決。忽必烈提供的金牌不僅在一二七○年左右保護波羅兄弟返回威尼斯的旅程,從而使他們第二次、也是更為著名的遠東之旅成為可能,這次與十幾歲的馬可一起;但再多得到兩面金牌,三位波羅家人得以離開大可汗如世外桃源般的宮廷,護送闊闊真公主至波斯*成婚,最後在一二九五年永遠返歸威尼斯。
在他們的歸途中,在蒙古帝國中東地區的波斯統治者(以及忽必烈的侄孫)乞合都送給這些威尼斯人更多金牌,波羅兄弟在那裡停留了數月:
他給了身為大汗使者的他們四面金牌,每塊長一腕尺,寬五指,重三或四馬克。其中兩個帶有矛隼的標誌,一個是獅子的標誌,一個沒有圖案。這些金牌上刻的銘文寫著:永世蒼天在上,大汗尊名永垂,違其令者處死抄家。
忽必烈提供這些金牌,表現出他和家人對波羅家極大的信心甚至感情,允許他們以受信任的使者這樣的外交身分旅行。然而,這些金牌雖然令人印象深刻,卻也顯示在蒙古帝國遙遠的領土中,其所代表的權威有著局限,因為在成吉思汗統治兩代之後,王朝的實力日益受到威脅。安全通行證的權力與頒發它們的主權者的權力成正比,即使通行證正是透過在遙遠的領土上主張或重申君王權威,擴大權力範圍,但是他們斷言的命令並不能保證成功。馬可波羅告訴我們,這些金牌還賦予波羅家在旅途中的幾個地點擁有護送馬匹和騎兵的權利,「這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因為乞合並非合法的統治者,當地居民可能會騷擾他們,而他們若隸屬於居民愛戴的君主之下,便不會遭遇此事。」
自十三世紀後期首次出版以來,書中故事的真實性就一直受到質疑,這種懷疑在隨後的幾個世紀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該文本以大約一百五十種不可靠的版本存在於數十種語言中,而原稿早已遺失。毫無疑問,馬可波羅和魯斯蒂謙都試圖讓故事的某些元素變得活躍,同時也無需懷疑的是,多年來不同版本的重製和翻譯錯誤,導致了遺漏,也增加了錯誤。在此,金牌再次發揮重要作用。一三二四年,從東方歸來近三十年的馬可波羅躺在病床上,親朋好友同聚一堂,向他表達最後的敬意,希望他能針對大家認為的誇大傳奇故事和過度的謊言說出真相。按照慣例,一位牧師也被召喚到床邊,但他沒有接受最後的懺悔,而是擔任公證人的角色,在一張大約六十五公分乘以二十五公分的羊皮紙上抄寫最後的遺囑和遺言。二○一八年,義大利歷史學家團隊完成為期三年對馬可波羅遺囑的研究,由威尼斯的聖馬可國家圖書館出版一本關於遺贈的學術著作,其中包括近七百張羊皮紙的複製品。在遺贈中,這位旅行商人將大量財富分配給威尼斯的行會和宗教機構,以及他的幾位女兒,這在父系時代可說少見。
這部著作為波羅在東方的旅程提供見證,還列出韃靼騎士的銀腰帶、蒙古女士在閱兵時戴的金色頭飾、忽必烈為確保他安全回家而贈送給他的金牌等物品。(他從未帶回像義大利麵和冰淇淋這些易腐爛的食物,人們經常誤傳是他將這些食物引入西方。)學者還發現馬可的叔叔馬菲奧的遺囑,其中明確地交代了「來自偉大韃靼王的三塊金牌」的處置。雖然研究人員並未找到這些金牌,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發現其他與他們描述相匹配的牌子,其中並記錄蒙古貴族和官員在整個蒙古帝國時期的使用(和濫用)情形。
關於馬可和馬菲奧擁有的金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旅行者持有它們很長的時間。當然,這些珍貴的金牌具有可觀的經濟價值,但它們對波羅家的意義肯定更大─說到這裡,我們可能會感覺到護照一直到今天仍然重要的一項特徵。就像他們收藏的銀腰帶或金色頭飾一樣,這些金牌是紀念品,是他們旅行的實質紀錄,比他們離家萬里的經歷所收集的任何故事都更堅固、更具體。無論是為了向懷疑的人證明他們的可信度,也就是說,證明他們確實如他們自稱的,是了不起的冒險家;或者在更安靜、沉澱的時刻回憶過去的許多冒險,在絲綢之路上的所見所聞;或者也許是想起這些金牌提供的特權,維護他們的移動和安全,而這樣的支持來自一個幾乎統領大半已知世界的帝國,甚至神聖的當權者,波羅叔侄一直保留著他們的金色護照,直到生命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