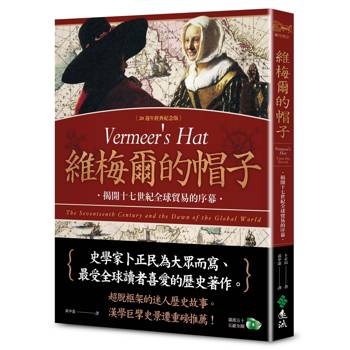第一章 從台夫特看世界
The View from Delft
二十歲那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買了輛腳踏車,往西南騎過荷蘭,展開從亞德里亞海濱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到蘇格蘭尼維斯山(Ben Nevis)這趟旅程的最後一段行程。第二天,我騎在荷蘭鄉間,時近傍晚,天色開始變暗,從北海飄來的毛毛雨,把路面變得又濕又滑。一輛卡車擦身而過,把我逼到路邊,我一個不穩,連人帶車跌到爛泥裡。我沒受傷,但渾身又濕又髒,擋泥板也給撞彎了,必須拉直。在外流浪,總會碰上壞天氣,我通常躲到橋下,但那時無橋可棲身,我於是找上最近一戶人家,敲門請求避雨。奧茨胡恩太太早就從家中前窗目睹我摔車──我猜她有許多漫漫午後是在前窗邊度過──因此,她開門露出一道縫,往外打量我時,我絲毫不覺驚訝。她遲疑了一會兒,然後甩開疑慮,把門大大打開,讓這個又濕又髒的狼狽加拿大青年進到屋裡。
我想要的就只是站著避一陣子的雨,打理好精神就出發,但她不同意,反倒讓我洗了熱水澡,請我吃了一頓晚餐,留我住一晚,還硬塞給我幾樣她已故丈夫的東西,包括一件防水外套。隔天早上,白花花的陽光灑在廚房餐桌上,她請我吃了一頓我這輩子吃過最美味的早餐,然後赧然輕笑,說起她兒子若知道她留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在家裡過夜──而且還是個男人──會有多生氣。吃完早餐,她給我當地景點的明信片當紀念,建議我去其中幾個地方逛逛再上路。那個星期天早晨,陽光耀眼,我又不趕行程,索性照她的建議,出去隨便走走看看。我沒想到,就那隨意的一遊,我與她所在的城鎮結下不解之緣。她給了我台夫特(Delft)。
「最賞心悅目的城鎮,每條街上都有好幾座橋和一條河,」以日記聞名於世的倫敦人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一六六○年五月走訪台夫特時,如此描述這城鎮。他的描述與我所見絲毫無差,因為台夫特大體上仍維持十七世紀時的模樣。那天早上,狀如十五、十六世紀西班牙大帆船的雲朵,從西北邊十幾公里外的北海急湧而來,將斑駁雲影灑在狹橋、以及大卵石鋪成的街道上,陽光映射在運河的河面,把屋宇的磚砌正立面照得亮晃晃的。義大利人以打入感潮沙洲的木樁為基礎,建造出規模更為宏大的海上運河城市──威尼斯。荷蘭人所建的台夫特則與此不同,它位在海平面之下。台夫特以堤防擋住北海,開鑿有閘水道,排乾沿海沼地。這段歷史就保留在台夫特這個字裡頭,因為荷蘭語的delven,意為「挖鑿」。貫穿台夫特西城區的主運河,如今仍叫奧德台夫特(Oude Delft),意為「古有閘水道」。
從台夫特的兩座大型教堂,特別能看出十七世紀的歷史面貌。位在大市場廣場(Great Market Square)的是新教堂(Nieuwe Kerk),興建時間比奧德台夫特運河邊的舊教堂(Oude Kerk)晚了兩世紀,因此而得名。這兩座宏大建築建造、裝飾之時(舊教堂是十三世紀,新教堂十五世紀)當然屬於天主教堂,但今天已不是如此。陽光從透明玻璃窗射進,照亮教堂內部,抹掉了那段早期歷史,只呈現那之後所發生的: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包括在一五六○年代打掉教堂的彩繪玻璃),將教堂改造成近乎世俗崇拜形式的新教集會所。當時的荷蘭人為了擺脫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統治,多方抗爭,而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就是其中之一。兩座教堂的地面大體是十七世紀的古蹟,因為上面布有銘文,用以標示十七世紀台夫特有錢市民墳墓的所在。當時的人希望埋骨之處離聖所愈近愈好,而埋在教堂底下又比埋在教堂旁邊好。歷來有無數畫作描繪這兩座教堂的內部,其中有許多幅畫裡可見一塊抬起的鋪砌石,偶爾甚至可看到正在幹活的挖墓工,以及正忙著自己的事的人(和狗)。教堂保留了每戶人家埋葬地點的紀錄簿,但大部分墳墓沒有刻上墓誌銘。只有負擔得起立碑費用的人,才會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一生行誼。
在舊教堂裡,我碰巧看到一塊刻有約翰內斯.維梅爾1632—1675年的石頭,每個字刻得工整而樸實。幾天前,我才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欣賞過維梅爾的畫作,想不到竟會無意中在這裡碰上這位藝術家的最後遺物。我對台夫特或維梅爾與台夫特的關係一無所悉。但突然間,他就出現在我面前,等著我打量。
許多年後,我得知那塊石頭並非他死時就鋪在墓上。當時,維梅爾還算不上是大人物,還沒資格擁有刻了銘文的墓碑。他只是個畫家而已,某個藝匠行業裡的一名工匠。沒錯,維梅爾是聖路加藝匠公會的頭頭之一,而且在該鎮的民兵組織裡位居高位──但他所住的鄰里裡,還有約八十個人擁有同樣的高位。他死時一貧如洗,即使他死時有錢,那也不足以讓他有資格享有銘文墓碑的殊榮。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收藏家和博物館館長才把維梅爾幽微縹緲、難以捉摸的畫作視為大師之作。如今所見的那塊石碑是到了二十世紀才擺上,好讓知道他埋骨之處而特意前來憑弔的許多人──不像我是不知他埋骨處而無意間碰上──能一償所願。但是那塊石板所在的位置,其實並非維梅爾真正埋葬之處,因為一九二一年大火之後,教堂重建,所有鋪砌的石頭全給拆掉再重鋪。今人所知的,就只是他的遺骸埋在那教堂底下某處。
維梅爾在台夫特生活的痕跡,除了埋骨處之外,其餘皆已不存。今人知道他在大市場廣場附近他父親的客棧長大,長大後,大部分歲月在舊長堤(Oude Langendijck)上他岳母瑪麗亞.蒂恩家度過。在岳母家一樓,圍繞他的子女愈來愈多;在二樓,他畫了大部分的畫作;最後,四十三歲時,債台高築、靈感枯竭的他,在岳母家猝然死去。那棟房子在十九世紀拆掉。與維梅爾在台夫特生活有關的具體東西,無一留存。
欲一窺維梅爾的世界,只有透過他的畫作,但是在台夫特,這也不可能。存世的三十五幅畫作中(另有一幅原收藏於波士頓的伊莎貝拉.斯圖亞特.迦納博物館,但是在一九九○年失竊,至今下落不明),沒有一幅留在台夫特。那些畫作全在他死後賣掉,或運到別處拍賣,如今散落從曼哈頓到柏林的十七座美術館裡。離台夫特最近的三幅畫作,位在海牙的莫里斯宅邸皇家繪畫陳列館(Mauritshuis)。那三幅畫離台夫特不遠──十七世紀時搭內河平底船到海牙,要花四個小時,如今搭火車只消十分鐘──但終究還是不在他畫那些畫的所在地。要看維梅爾的畫,就得到台夫特以外的地方。在台夫特,就得斷了親眼目睹維梅爾畫作的念頭。
維梅爾的繪畫生涯為何發跡自台夫特,而非別的地方,理由多不勝數,從當地的繪畫傳統到台夫特天然光影特色都是。但那些理由並不足以讓人斷定,維梅爾若是住在荷蘭其他地方,就畫不出那麼出色的畫作。環境很重要,但無法解釋所有的現象。同樣的,我可以提出許多理由,說明十七世紀人類生活跨文化轉變的全球史為何一定得從台夫特開始談起,但那些理由並無法讓人相信,台夫特是唯一一個該作為探討起點的地方。事實上,那裡所發生的事,除了可能改變了藝術史的進程之外,沒有一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而我也無意在這之外另發高論。我從台夫特開始談起,純粹是因為我碰巧在那裡摔車,因為碰巧維梅爾曾住在那裡,因為我碰巧欣賞他的畫作。只要台夫特不擋住我們遠眺十七世紀的世界,根據那些理由選擇該地作為立足審視十七世紀之地,自然也無不可。
The View from Delft
二十歲那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買了輛腳踏車,往西南騎過荷蘭,展開從亞德里亞海濱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到蘇格蘭尼維斯山(Ben Nevis)這趟旅程的最後一段行程。第二天,我騎在荷蘭鄉間,時近傍晚,天色開始變暗,從北海飄來的毛毛雨,把路面變得又濕又滑。一輛卡車擦身而過,把我逼到路邊,我一個不穩,連人帶車跌到爛泥裡。我沒受傷,但渾身又濕又髒,擋泥板也給撞彎了,必須拉直。在外流浪,總會碰上壞天氣,我通常躲到橋下,但那時無橋可棲身,我於是找上最近一戶人家,敲門請求避雨。奧茨胡恩太太早就從家中前窗目睹我摔車──我猜她有許多漫漫午後是在前窗邊度過──因此,她開門露出一道縫,往外打量我時,我絲毫不覺驚訝。她遲疑了一會兒,然後甩開疑慮,把門大大打開,讓這個又濕又髒的狼狽加拿大青年進到屋裡。
我想要的就只是站著避一陣子的雨,打理好精神就出發,但她不同意,反倒讓我洗了熱水澡,請我吃了一頓晚餐,留我住一晚,還硬塞給我幾樣她已故丈夫的東西,包括一件防水外套。隔天早上,白花花的陽光灑在廚房餐桌上,她請我吃了一頓我這輩子吃過最美味的早餐,然後赧然輕笑,說起她兒子若知道她留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在家裡過夜──而且還是個男人──會有多生氣。吃完早餐,她給我當地景點的明信片當紀念,建議我去其中幾個地方逛逛再上路。那個星期天早晨,陽光耀眼,我又不趕行程,索性照她的建議,出去隨便走走看看。我沒想到,就那隨意的一遊,我與她所在的城鎮結下不解之緣。她給了我台夫特(Delft)。
「最賞心悅目的城鎮,每條街上都有好幾座橋和一條河,」以日記聞名於世的倫敦人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一六六○年五月走訪台夫特時,如此描述這城鎮。他的描述與我所見絲毫無差,因為台夫特大體上仍維持十七世紀時的模樣。那天早上,狀如十五、十六世紀西班牙大帆船的雲朵,從西北邊十幾公里外的北海急湧而來,將斑駁雲影灑在狹橋、以及大卵石鋪成的街道上,陽光映射在運河的河面,把屋宇的磚砌正立面照得亮晃晃的。義大利人以打入感潮沙洲的木樁為基礎,建造出規模更為宏大的海上運河城市──威尼斯。荷蘭人所建的台夫特則與此不同,它位在海平面之下。台夫特以堤防擋住北海,開鑿有閘水道,排乾沿海沼地。這段歷史就保留在台夫特這個字裡頭,因為荷蘭語的delven,意為「挖鑿」。貫穿台夫特西城區的主運河,如今仍叫奧德台夫特(Oude Delft),意為「古有閘水道」。
從台夫特的兩座大型教堂,特別能看出十七世紀的歷史面貌。位在大市場廣場(Great Market Square)的是新教堂(Nieuwe Kerk),興建時間比奧德台夫特運河邊的舊教堂(Oude Kerk)晚了兩世紀,因此而得名。這兩座宏大建築建造、裝飾之時(舊教堂是十三世紀,新教堂十五世紀)當然屬於天主教堂,但今天已不是如此。陽光從透明玻璃窗射進,照亮教堂內部,抹掉了那段早期歷史,只呈現那之後所發生的: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包括在一五六○年代打掉教堂的彩繪玻璃),將教堂改造成近乎世俗崇拜形式的新教集會所。當時的荷蘭人為了擺脫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統治,多方抗爭,而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就是其中之一。兩座教堂的地面大體是十七世紀的古蹟,因為上面布有銘文,用以標示十七世紀台夫特有錢市民墳墓的所在。當時的人希望埋骨之處離聖所愈近愈好,而埋在教堂底下又比埋在教堂旁邊好。歷來有無數畫作描繪這兩座教堂的內部,其中有許多幅畫裡可見一塊抬起的鋪砌石,偶爾甚至可看到正在幹活的挖墓工,以及正忙著自己的事的人(和狗)。教堂保留了每戶人家埋葬地點的紀錄簿,但大部分墳墓沒有刻上墓誌銘。只有負擔得起立碑費用的人,才會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一生行誼。
在舊教堂裡,我碰巧看到一塊刻有約翰內斯.維梅爾1632—1675年的石頭,每個字刻得工整而樸實。幾天前,我才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欣賞過維梅爾的畫作,想不到竟會無意中在這裡碰上這位藝術家的最後遺物。我對台夫特或維梅爾與台夫特的關係一無所悉。但突然間,他就出現在我面前,等著我打量。
許多年後,我得知那塊石頭並非他死時就鋪在墓上。當時,維梅爾還算不上是大人物,還沒資格擁有刻了銘文的墓碑。他只是個畫家而已,某個藝匠行業裡的一名工匠。沒錯,維梅爾是聖路加藝匠公會的頭頭之一,而且在該鎮的民兵組織裡位居高位──但他所住的鄰里裡,還有約八十個人擁有同樣的高位。他死時一貧如洗,即使他死時有錢,那也不足以讓他有資格享有銘文墓碑的殊榮。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收藏家和博物館館長才把維梅爾幽微縹緲、難以捉摸的畫作視為大師之作。如今所見的那塊石碑是到了二十世紀才擺上,好讓知道他埋骨之處而特意前來憑弔的許多人──不像我是不知他埋骨處而無意間碰上──能一償所願。但是那塊石板所在的位置,其實並非維梅爾真正埋葬之處,因為一九二一年大火之後,教堂重建,所有鋪砌的石頭全給拆掉再重鋪。今人所知的,就只是他的遺骸埋在那教堂底下某處。
維梅爾在台夫特生活的痕跡,除了埋骨處之外,其餘皆已不存。今人知道他在大市場廣場附近他父親的客棧長大,長大後,大部分歲月在舊長堤(Oude Langendijck)上他岳母瑪麗亞.蒂恩家度過。在岳母家一樓,圍繞他的子女愈來愈多;在二樓,他畫了大部分的畫作;最後,四十三歲時,債台高築、靈感枯竭的他,在岳母家猝然死去。那棟房子在十九世紀拆掉。與維梅爾在台夫特生活有關的具體東西,無一留存。
欲一窺維梅爾的世界,只有透過他的畫作,但是在台夫特,這也不可能。存世的三十五幅畫作中(另有一幅原收藏於波士頓的伊莎貝拉.斯圖亞特.迦納博物館,但是在一九九○年失竊,至今下落不明),沒有一幅留在台夫特。那些畫作全在他死後賣掉,或運到別處拍賣,如今散落從曼哈頓到柏林的十七座美術館裡。離台夫特最近的三幅畫作,位在海牙的莫里斯宅邸皇家繪畫陳列館(Mauritshuis)。那三幅畫離台夫特不遠──十七世紀時搭內河平底船到海牙,要花四個小時,如今搭火車只消十分鐘──但終究還是不在他畫那些畫的所在地。要看維梅爾的畫,就得到台夫特以外的地方。在台夫特,就得斷了親眼目睹維梅爾畫作的念頭。
維梅爾的繪畫生涯為何發跡自台夫特,而非別的地方,理由多不勝數,從當地的繪畫傳統到台夫特天然光影特色都是。但那些理由並不足以讓人斷定,維梅爾若是住在荷蘭其他地方,就畫不出那麼出色的畫作。環境很重要,但無法解釋所有的現象。同樣的,我可以提出許多理由,說明十七世紀人類生活跨文化轉變的全球史為何一定得從台夫特開始談起,但那些理由並無法讓人相信,台夫特是唯一一個該作為探討起點的地方。事實上,那裡所發生的事,除了可能改變了藝術史的進程之外,沒有一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而我也無意在這之外另發高論。我從台夫特開始談起,純粹是因為我碰巧在那裡摔車,因為碰巧維梅爾曾住在那裡,因為我碰巧欣賞他的畫作。只要台夫特不擋住我們遠眺十七世紀的世界,根據那些理由選擇該地作為立足審視十七世紀之地,自然也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