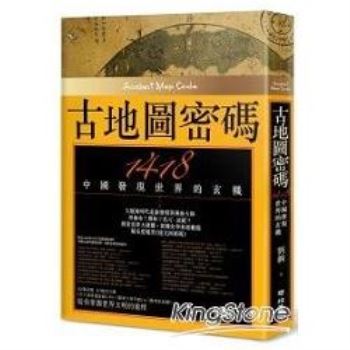第一章 《天下諸番識貢圖》
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時代,我是個火柴盒收藏迷。觀賞火柴盒上的各種圖畫是我兒時的一種樂趣。三十而立之後,收藏古地圖逐漸成為我的一項主要嗜好。回想起來,此愛好已經伴隨我度過了十八個春秋。
收藏古地圖就如同尋寶。當得到一幅罕見的古地圖時,我會感到無比興奮,有時竟然徹夜不眠。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意識到,研究古地圖遠比收藏更為重要。這種研究使我接觸到一種古老並且神祕的哲學。這一哲學不僅巧妙地將迷信、科學與技能結合在一起,並且一直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地理學和地圖學發展的推動力。在研究過程中,我還發現了一個歷史祕密:現代地圖學實際上是一種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
工作之餘,我經常伏案研究古地圖。在我的藏品之中,有些古地圖就像一本歷史教科書,圖上的地域輪廓、城鎮布局和文字注釋蘊藏著豐富的史實;有些古地圖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畫,圖中充滿韻律的山河好似出自一位藝術大師之筆,而這位藝術大師就是我們的大自然;有些古地圖給我帶來韶華易逝的感覺,發黃的圖紙和累累蛀痕經常喚起我對時間如煙的哀歎;還有的古地圖簡直就是令人費解的謎團,圖上的線條、符號和記述似乎是繪圖者故意留給後人的謎語。古地圖給我帶來的快樂和感慨是無法用語言來詳盡的,而這正是古地圖的奧妙之處。
古地圖的奧妙誘發出我對中國古代天文學和傳統科技的興趣。我逐漸發現,許多中國古代地圖學家跟占星術、古典數學和道教有著不解之緣。為了探究古地圖的奧祕,我研究的範圍漸漸擴展到古代天文學、數學以及宗教。
我從未預料到,收藏古地圖竟然會引導我獲得一系列令人驚奇的發現。這些發現的起因都源於一幅古地圖。這幅地圖不僅激發出我對地理大發現史的興趣,同時還引起我對相關歷史記載的質疑。
在我們的心目中,地理大發現史是一段蓋棺定論的「史實」。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績已成為眾人皆知、家喻戶曉的歷史常識: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斯(Bartholomeu Dias)駕船由西向東經過好望角,為此他被稱作世界上首位繞過這一岬角的探險家;
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領的船隊抵達美洲巴哈馬群島。由此,哥倫布被譽為美洲大陸的發現者;
1519年9月,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率領船隊自歐洲始航。這隻船隊歷時三年繞地球一周回到始發地。從而,麥哲倫被授予首次完成環球航行的桂冠。由於麥哲倫被視為發現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海峽的探險家,這一海峽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發現,這些歷史常識卻無法與我的一件地圖藏品相吻合。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麼樣的地圖?它與歷史常識之間存在著何種差異?它與我之間又有何種緣分呢?
第一節 發現《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
2001年春季,我因公務到上海出差。臨回北京之前,我來到著名的東台路古玩市場。這個分布在街道兩旁的露天市場被譽為「上海古玩一條街」。其實,市場中擺放的物品絕大部分都是冒牌貨。
在這個充斥假古董的市場裡,有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書鋪。這家店鋪的面積不足六平方公尺,裡面擺滿了舊書、舊報紙和舊雜誌。小書鋪的主人是一位姓向的老先生,他的前輩曾以古籍買賣為生,他的兒子也熱中於繼承祖業,而且在古籍收藏圈內小有名氣。我與向家有多年的交往,從他們那裡我買過不少古籍和古地圖。每次去上海出差,我總是抽空到這家小書鋪,看看有沒有值得收藏的東西。
我此次閒逛書鋪真是一次天賜的良緣。一進店門,我看見向先生正在往牆上掛一幅破舊的世界地圖(見彩圖1)。這幅地圖的右上角寫著「天下全輿總圖」,左下角注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在這一注釋左邊有一落款:「臣,莫易仝繪。」這些文字表明,此幅世界地圖是1418年間一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仿繪品,仿繪時間為1763年,仿繪者為「莫易仝」。地圖的左上角還寫有一段注釋:「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這幾個字意味著圖上的注釋有些是《天下諸番識貢圖》原有的,有些是仿繪者後加的,而原有的注釋都用紅墨加以圈注。
仔細察看這幅世界地圖之後,我感到非常困惑不解。這幅地圖不僅畫出了地球上所有的大陸和海域(其中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墨圈注的注釋。
很明顯,這幅世界地圖中的許多內容與我們所知的歷史常識完全不相吻合。難道中國人於1418年繪出了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十五世紀初期的地圖上怎麼會出現美洲和澳洲大陸?莫非此幅地圖是件贗品?
憑藉我多年積累的經驗,判定一幅古地圖的繪製年代,除了參考繪圖者在圖中所寫的注釋外,更重要的是採用中國古籍、古紙和古字畫等方面的傳統鑑定方法對繪圖年代加以驗證。
我仔細察看了一番地圖,聞了一下圖紙的氣味。這幅地圖外表發黃,紙質脆硬,並且散發出一種陳舊的氣味。這種氣味與在老房子中聞到的陳舊氣息很相似。從圖紙的色變、氣味和脆化程度我判斷出,地圖紙張已逾百年之久。
這幅地圖的中部有一條對折痕跡,這表明圖紙一直以面朝裡的對折方式保存。圖紙上有很多蟲蝕蛀孔,特別是在透氣性差的對折部位。圖紙左、右兩頁上的蛀痕相互吻合,這一現象再次證實,地圖曾長期處在對折狀態。蛀痕的布局顯示出,這些蛀孔均為自然狀態下產生的。我用高倍放大鏡仔細察看了蛀痕,蛀痕的邊緣為毛邊,這也是自然蟲蛀的特徵。
圖上注文的紅框以朱砂墨繪成。清朝時期的朱砂墨雖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兩百多年前留在紙上的朱砂顏色與現代人用老朱砂墨畫在古紙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彥在《圖繪寶鑑》中所云:「古人作畫墨色俱入絹縷。」「偽者雖極力仿效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很容易看出,紅框的朱砂墨顏色屬於「俱入絹縷」,為古人之跡;而圖中的三方紅色鑑藏印則是「浮於縑素之上」,為近現代人所蓋之印。
地圖上的海域以青綠色繪成。這種墨色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會呈現出褪色的效果。由於地圖對折部位的透氣性較其他部位差,這一部位的褪色程度明顯小於其他部位,從而在圖紙中部形成了一條縱向的深色帶。不均勻、不規則的褪色是自然褪色的特徵。這種褪色與古字畫造假者採用人工方法造出的「褪色」效果完全不同。人造「褪色」不僅顯得均勻,並且「褪色」程度也一致。
察看地圖的紙張、蛀痕和墨色之後,我又對繪圖者的書寫習慣和字體做了進一步的鑑別。
現代人作畫、寫字的書寫習慣與古人有很大區別。前者寫字順序為從左向右,而後者書寫則是從右上方開始。由於不同的書寫習慣,現代人塗色的第一筆通常畫在圖紙的左上部位,而古人著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基於褪色的緣故,很容易辨認出《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塗抹青綠色的第一筆和第二筆的墨蹟。這兩筆塗色都落在圖紙的右上方,這表明繪圖者具有古人的書寫習慣。
中國古代書法猶如古代服飾,幾乎每一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書法風格。清中期的科舉制度要求考生以規定的「館閣體」書寫答卷。這種「館閣體」看上去字字勻稱並且橫平豎直,然而卻是一種平庸、呆板的書體。現代人對「館閣體」持貶義之態,研習者寥寥無幾。「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於大清朝廷宣導「館閣體」,乾隆時期文人社會無形之中形成「館閣體」的書風。乾隆、嘉慶年間的著名學者洪亮吉對此評論道:「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以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的字體(尤其是落款)具有明顯的「館閣體」書風,這又是此圖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旁證。
採用中國傳統的書畫鑑定方法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進行檢驗之後,我斷定,這幅地圖是十八世紀的作品。
這幅古代世界地圖雖然有許多跟歷史常識相矛盾的地域圖形和注釋,但是這些奇怪的內容並沒有減弱我對此幅地圖的興趣,而是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摹本。
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時代,我是個火柴盒收藏迷。觀賞火柴盒上的各種圖畫是我兒時的一種樂趣。三十而立之後,收藏古地圖逐漸成為我的一項主要嗜好。回想起來,此愛好已經伴隨我度過了十八個春秋。
收藏古地圖就如同尋寶。當得到一幅罕見的古地圖時,我會感到無比興奮,有時竟然徹夜不眠。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意識到,研究古地圖遠比收藏更為重要。這種研究使我接觸到一種古老並且神祕的哲學。這一哲學不僅巧妙地將迷信、科學與技能結合在一起,並且一直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地理學和地圖學發展的推動力。在研究過程中,我還發現了一個歷史祕密:現代地圖學實際上是一種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
工作之餘,我經常伏案研究古地圖。在我的藏品之中,有些古地圖就像一本歷史教科書,圖上的地域輪廓、城鎮布局和文字注釋蘊藏著豐富的史實;有些古地圖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畫,圖中充滿韻律的山河好似出自一位藝術大師之筆,而這位藝術大師就是我們的大自然;有些古地圖給我帶來韶華易逝的感覺,發黃的圖紙和累累蛀痕經常喚起我對時間如煙的哀歎;還有的古地圖簡直就是令人費解的謎團,圖上的線條、符號和記述似乎是繪圖者故意留給後人的謎語。古地圖給我帶來的快樂和感慨是無法用語言來詳盡的,而這正是古地圖的奧妙之處。
古地圖的奧妙誘發出我對中國古代天文學和傳統科技的興趣。我逐漸發現,許多中國古代地圖學家跟占星術、古典數學和道教有著不解之緣。為了探究古地圖的奧祕,我研究的範圍漸漸擴展到古代天文學、數學以及宗教。
我從未預料到,收藏古地圖竟然會引導我獲得一系列令人驚奇的發現。這些發現的起因都源於一幅古地圖。這幅地圖不僅激發出我對地理大發現史的興趣,同時還引起我對相關歷史記載的質疑。
在我們的心目中,地理大發現史是一段蓋棺定論的「史實」。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績已成為眾人皆知、家喻戶曉的歷史常識: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斯(Bartholomeu Dias)駕船由西向東經過好望角,為此他被稱作世界上首位繞過這一岬角的探險家;
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領的船隊抵達美洲巴哈馬群島。由此,哥倫布被譽為美洲大陸的發現者;
1519年9月,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率領船隊自歐洲始航。這隻船隊歷時三年繞地球一周回到始發地。從而,麥哲倫被授予首次完成環球航行的桂冠。由於麥哲倫被視為發現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海峽的探險家,這一海峽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發現,這些歷史常識卻無法與我的一件地圖藏品相吻合。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麼樣的地圖?它與歷史常識之間存在著何種差異?它與我之間又有何種緣分呢?
第一節 發現《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
2001年春季,我因公務到上海出差。臨回北京之前,我來到著名的東台路古玩市場。這個分布在街道兩旁的露天市場被譽為「上海古玩一條街」。其實,市場中擺放的物品絕大部分都是冒牌貨。
在這個充斥假古董的市場裡,有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書鋪。這家店鋪的面積不足六平方公尺,裡面擺滿了舊書、舊報紙和舊雜誌。小書鋪的主人是一位姓向的老先生,他的前輩曾以古籍買賣為生,他的兒子也熱中於繼承祖業,而且在古籍收藏圈內小有名氣。我與向家有多年的交往,從他們那裡我買過不少古籍和古地圖。每次去上海出差,我總是抽空到這家小書鋪,看看有沒有值得收藏的東西。
我此次閒逛書鋪真是一次天賜的良緣。一進店門,我看見向先生正在往牆上掛一幅破舊的世界地圖(見彩圖1)。這幅地圖的右上角寫著「天下全輿總圖」,左下角注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在這一注釋左邊有一落款:「臣,莫易仝繪。」這些文字表明,此幅世界地圖是1418年間一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仿繪品,仿繪時間為1763年,仿繪者為「莫易仝」。地圖的左上角還寫有一段注釋:「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這幾個字意味著圖上的注釋有些是《天下諸番識貢圖》原有的,有些是仿繪者後加的,而原有的注釋都用紅墨加以圈注。
仔細察看這幅世界地圖之後,我感到非常困惑不解。這幅地圖不僅畫出了地球上所有的大陸和海域(其中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墨圈注的注釋。
很明顯,這幅世界地圖中的許多內容與我們所知的歷史常識完全不相吻合。難道中國人於1418年繪出了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十五世紀初期的地圖上怎麼會出現美洲和澳洲大陸?莫非此幅地圖是件贗品?
憑藉我多年積累的經驗,判定一幅古地圖的繪製年代,除了參考繪圖者在圖中所寫的注釋外,更重要的是採用中國古籍、古紙和古字畫等方面的傳統鑑定方法對繪圖年代加以驗證。
我仔細察看了一番地圖,聞了一下圖紙的氣味。這幅地圖外表發黃,紙質脆硬,並且散發出一種陳舊的氣味。這種氣味與在老房子中聞到的陳舊氣息很相似。從圖紙的色變、氣味和脆化程度我判斷出,地圖紙張已逾百年之久。
這幅地圖的中部有一條對折痕跡,這表明圖紙一直以面朝裡的對折方式保存。圖紙上有很多蟲蝕蛀孔,特別是在透氣性差的對折部位。圖紙左、右兩頁上的蛀痕相互吻合,這一現象再次證實,地圖曾長期處在對折狀態。蛀痕的布局顯示出,這些蛀孔均為自然狀態下產生的。我用高倍放大鏡仔細察看了蛀痕,蛀痕的邊緣為毛邊,這也是自然蟲蛀的特徵。
圖上注文的紅框以朱砂墨繪成。清朝時期的朱砂墨雖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兩百多年前留在紙上的朱砂顏色與現代人用老朱砂墨畫在古紙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彥在《圖繪寶鑑》中所云:「古人作畫墨色俱入絹縷。」「偽者雖極力仿效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很容易看出,紅框的朱砂墨顏色屬於「俱入絹縷」,為古人之跡;而圖中的三方紅色鑑藏印則是「浮於縑素之上」,為近現代人所蓋之印。
地圖上的海域以青綠色繪成。這種墨色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會呈現出褪色的效果。由於地圖對折部位的透氣性較其他部位差,這一部位的褪色程度明顯小於其他部位,從而在圖紙中部形成了一條縱向的深色帶。不均勻、不規則的褪色是自然褪色的特徵。這種褪色與古字畫造假者採用人工方法造出的「褪色」效果完全不同。人造「褪色」不僅顯得均勻,並且「褪色」程度也一致。
察看地圖的紙張、蛀痕和墨色之後,我又對繪圖者的書寫習慣和字體做了進一步的鑑別。
現代人作畫、寫字的書寫習慣與古人有很大區別。前者寫字順序為從左向右,而後者書寫則是從右上方開始。由於不同的書寫習慣,現代人塗色的第一筆通常畫在圖紙的左上部位,而古人著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基於褪色的緣故,很容易辨認出《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塗抹青綠色的第一筆和第二筆的墨蹟。這兩筆塗色都落在圖紙的右上方,這表明繪圖者具有古人的書寫習慣。
中國古代書法猶如古代服飾,幾乎每一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書法風格。清中期的科舉制度要求考生以規定的「館閣體」書寫答卷。這種「館閣體」看上去字字勻稱並且橫平豎直,然而卻是一種平庸、呆板的書體。現代人對「館閣體」持貶義之態,研習者寥寥無幾。「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於大清朝廷宣導「館閣體」,乾隆時期文人社會無形之中形成「館閣體」的書風。乾隆、嘉慶年間的著名學者洪亮吉對此評論道:「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以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的字體(尤其是落款)具有明顯的「館閣體」書風,這又是此圖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旁證。
採用中國傳統的書畫鑑定方法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進行檢驗之後,我斷定,這幅地圖是十八世紀的作品。
這幅古代世界地圖雖然有許多跟歷史常識相矛盾的地域圖形和注釋,但是這些奇怪的內容並沒有減弱我對此幅地圖的興趣,而是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