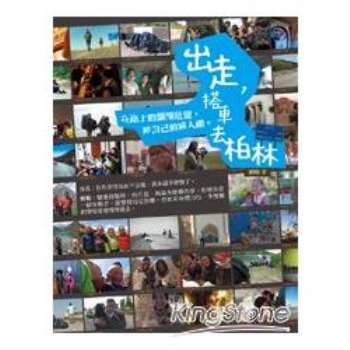◎為了「在路上」而展開的旅程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尋「搭車去柏林」,你可能會得到幾十萬條資訊:二○○九年,兩個北京小伙子──谷岳、劉暢用一個夏天,以舉手搭便車的方式途經十幾個國家,一萬六千公里的旅程到達德國柏林,看望一個女孩。這個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戀三年的女友,這種極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見證了普通人愛情裡的閃光點。那麼,兩個旅行者中的另一個人,劉暢,總是會遇到朋友們各種各樣的疑問,你,又是為什麼而去的呢?我想,寫這本書也許可以表達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為了逃離我們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一開始,我認為一切都跟一本書有關。那就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書中兩個年輕人不斷瘋狂地穿行美洲:搭車、自駕、不能抑制地無目的地旅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儘管幾乎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卻具有相當的迷人之處。」
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路上》出版後,《紐約時報》刊登的書評這樣寫道:「在極度的時尚使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支離破碎,敏感性變得遲鈍薄弱的時代,如果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義的話,該書的出版就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路上》讓無數的年輕人拿起簡單的行囊上路,開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目的地的旅途。他們害怕鏡子中的自我,最終丟失在物質洪流裡,或僅僅是表演著為尋找自我所做的逃離。去哪裡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做出反抗現實的姿態來,這些年輕人表演、鞠躬,之後就往後一躍,跳進舞臺的側幕裡,五十多年來重複上演著這樣一幕幕鬧劇。這一文化轟轟烈烈繁衍至今天,從文學、從音樂、從電影,成為主流消費文化之外的另一體系。說到這裡,我們為什麼選擇搭車旅行已經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會離「年輕」這一辭彙越來越遠,我們長年如同螞蟻一般的努力奮鬥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變得微不足道,物質的家園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園形單影隻,搭車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導演,在搭車旅行之前,我曾設想過拍一部公路電影,一男一女,兩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卻永遠沒有相遇。男主角路過生命的孤獨與割捨,女主角路過生命的迷惘與歡愉。寫作劇本是漫長艱辛的過程,我發現,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請彷彿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三個多月的旅程,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人的人生:在新疆廣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車司機;在吉爾吉斯酒後遭遇牧民熱騰騰的馬油大餐;烏茲別克沙漠船隻墓地的守墓老人;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伊斯坦堡雄渾壯觀的歐亞兩岸;羅馬尼亞堅強的孤兒院志願者;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旅館的韓國老闆;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屬俱樂部;東柏林的藝術家貧民窟……親自體驗並拍攝一部公路紀錄片,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夢想。我相信公路電影的製作者們都經歷著這樣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遊也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遊歷。
《在路上》這本書從二○○○年一直陪伴我到現在,四次閱讀都沒有翻到最終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給這次旅程。在搭車旅途的某輛大卡車上,我在顛簸的駕駛室的臥鋪上讀完了最後一頁。車窗外是何時何地的風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結尾這樣寫道:
我知道在愛荷華州,在人們允許孩子們哭泣的地方,孩子們在大聲地哭泣著。今夜,星星就要出來,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臨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輝灑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隱沒掉最後一片海灘,然而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
這本小書是我個人的小小旅行隨想,有些旅程段落詳細,有些只是一筆帶過。這趟旅程我和谷岳約定好一人寫一本書,同樣的旅行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收穫。我偏執於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視角,偶然的機緣巧合,展開搭車去十餘個國家的夢想之旅,我沒有超於常人的意志品質,也沒有職業旅行家的豐富經驗,更沒有超凡脫俗的個人魅力。我只是因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而與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終結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因為這段路而得到了某種圓滿,於是那個原來執著的目標也許就不再重要。
◎清晨五點半的地鐵五號線
你可曾見過北京地鐵五號線清晨五點半的月臺?它華而不實地被設計成海洋動物曬乾後的軀殼的樣子,乾巴巴地,等待著早班的地下鐵從這邊來再從那邊走,等待著面無表情的人們前來重複命中注定的日子。我經常會在清晨,趕最早的一班地鐵回家,因為工作通常需要熬夜,我便有了這樣一種機會,體會與人群相反的軌跡,體會身體在極度透支後的某種亢奮,身體是軟的,而心底卻清明一片,靜逸安詳。你會發現夜與晝的更替是隨鳥的叫聲來臨,天知道北京竟有這麼多種鳥,在你不知道的遠方喧鬧。
鳥的聲音會被對面月臺漸漸匯聚的人聲終結,列車會把他們帶往市中心,而我的方向相反,等候在回家的路上,獨自擁有這一半的月臺,以一種旁觀的心態默默注視著對面越聚越多的人群。那些人雖然陌生,卻都是再熟悉不過的陌生人,我們都從五環外的新建高樓裡醒來,或是十幾個人擠在兩室一廳分割的公寓裡,因為搶洗手間而爭吵,因為左鄰右舍的梳洗打扮而詛咒著為什麼不能再睡上十幾分鐘。找到熟悉的早點攤,排隊買著熟悉的糊弄肚子的食物,然後強打起精神隨擁擠的地鐵奔赴一個小時後另一個屬於自己的格子間。
熟悉這樣的世界,這樣的陌生人,這樣的生活,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紋一樣。常常問自己,三十多歲了,如果有機會和別人交換各自的生活,那麼,我會選擇和誰交換?瀟灑地開寶馬(BMW)車的,還是在地鐵車廂裡啃油條的?沒有,熟悉的生活僅有這一點點差別,我們擁有同樣的苦難,僅靠可憐的一點點財富來顯示彼此的差別。三十多歲了,人生不再新鮮,多少對未知的探求也泯滅在這許許多多的「不得不」裡。不得不去向看板上成功的人生靠近:一家三口,穿著一塵不染的夏裝,跑向以外國風景地命名的美好社區,女人很滿足,男人很得意,孩子的頭髮很整齊。雖然覺得這一切很可笑,但是,開往城郊的地鐵來了,我也只能低頭走進車廂裡。每天,我們在地鐵五號線裡路過路人甲,再路過路人乙,看別人看自己,沒有一絲絕望。因為五號線代表我每天的旅程,無可選擇。
這僅是我二○○九年年初的想法 ,六個月後,我和一個叫谷岳的傢伙去了一萬多公里外的城市,那裡有他的姑娘,也有無數條血管般蓬勃的地鐵線,喧鬧地在每一個清晨流過城市的龐大身軀,那裡叫柏林。
◎谷岳的三分鐘
「三分鐘內可以發生許多事,欣賞一段不錯的音樂,吃一頓倉促的速食,經歷一場感情變故,改變一個人的某種世界觀,獲得或失去一筆財富,也可能失去親人,或離開一片你摯愛的熱土,再或踏上一段征途,很多很多……」
在北京南鑼鼓巷的一家小酒館,我把自己的三分鐘給了對面這個叫谷岳的傢伙,他用三分鐘和我說明了他的計畫:他想尋找一個旅伴,拍攝經驗豐富,能各自負擔費用,花三個月的時間,一起從北京出發,搭車旅行去德國首都柏林。用他的話講,去看女朋友的旅程也要給自己留下些什麼,這裡借用他的演講文稿:
「一直崇拜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再加上電影《摩托車日記》(台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和《荒野生存》(台譯:阿拉斯加之死)的啟發,我要去找伊卡,也要親自體驗一下『在路上』的自由精神。如果我是坐飛機去見她,那麼舷窗下的原野,我就無法用腳步去丈量,我和伊卡也就沒有更多的收穫,我想慢慢去感受與她距離越來越近所帶來的影響,對我生命的影響。
以前我也上過班,在二○○一年的時候,我在美國的通用電氣做金融(工作),算風險評估吧。工作了一個月後,突然有一天有一個深省,我就想我從小學就努力好好學習,上中學、上大學、找著一份好工作,要買房子、買車、結婚生孩子,這一輩子的東西都已經知道了,我覺得有點兒太遺憾了。所以二○○三年我把工作辭掉了,把我的家當都賣了,開始環球世界旅行。二○○六年認識我現在的女朋友伊卡,她是德國人。我跟她相處兩年後,她說她要回德國一段時間,想家了,這又給我再次上路的動力。另外我覺得社會越來越實際了,所有的東西都建立在金錢和互利的關係上,所以我想用這種搭車的方式,來尋找不是在金錢,不是在互利的關係上創建的一種友誼。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搭車,要搭陌生人的車。」
其實在這以前兩年我們就通過旅遊衛視的朋友認識,那時他就已經是職業的旅行家了。而我,一個拍紀錄片的小小導演,雖然也經歷過諸如雅魯藏布江大峽谷、長江源、柴達木、可哥西裡等地的探險拍攝,但旅行一直不是我的直接目的。而這次,更是沒有任何理由,只是要走,要出發,要一直走在路上。
十年前在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拚命看《麥田裡的守望者》(台譯:麥田捕手)這樣的小說,聽《涅槃》,去中戲小劇場蹭話劇《盜版浮士德》,和同學們聊著某大師艱澀難懂的電影,憧憬著將來一起拍充滿新銳氣息的片子,唾棄著所謂俗氣的生活,那時候覺得這肯定就是自己將來的人生。但是慢慢地從畢業開始,我也進入了一種大家都會進入的生活。去掙錢,去過一種世俗人眼中你應該過的那種生活。谷岳用三分鐘說了他的想法後,問我能不能走,感覺言語中還要給我一些時間去思考。但我內心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定要走,雖然當時搭車對我來說還只是天空上飄著的一種概念。那時我正處於人生的低潮,感慨自己十多年的時間在北京這個城市裡做了很多莫名的事情,表面上熱熱鬧鬧,內心卻無比空虛。我的故鄉,這座巨大而喧鬧的城市,時常讓我害怕失去僅有的一點兒歸屬感,失去掙扎生存的勇氣。
我的生活像是在莫比斯環(Mobius band)上爬的螞蟻一樣,螞蟻一直以為能從紙的開端爬到紙的末端,爬到末端才發現其實又到了開始的地方。一直原地打轉,缺少生活的新鮮和激情。所以一定要走。決定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很多的顧慮:我的存款不多,這三個月走了,生活來源就沒有了,雖然我是自由職業,沒有固定工作,沒有辭職的問題,但是同樣面臨生存的壓力。房租怎麼交?以後怎麼辦?長期合作拍片的客戶這次拒絕了,以後人家還會不會來找你合作?很多的機會就因此失去了。但是能促使我把這些都拋下而毅然決定走的主要原因,還是對這個城市的感覺,有時候我會覺得整個城市已離棄了我,我從城市的中心漂流到了城市的周邊──記得小時候是在長安街沿線長大,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遷徙,到三環外,四環外,過了這麼多年,甚至置身五環以外,從二十三樓的出租房眺望環內,曾經的核桃樹與梧桐依然蒼翠,但已物是人非。我很想笑,既然生活已把自己趕得越來越遠,為何不乾脆痛快點兒走得更遠?去看看真正想看的東西,「在路上」這三個字,一下子跳出來,在腦海裡閃著神聖的光輝。
「有些事情現在不去做,就永遠不會做了。」對面拿著啤酒的谷岳沒來由地說了一句。
十年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科學新聞,至今想起仍會發冷。
一九九九年情人節那天,旅行者二號在掠過冥王星後,飛向沒有盡頭的宇宙深淵。它的孤獨讓人不寒而慄,在調整方向奔赴這一命運時,一個女科學家,遙控它做了最後一件事情:緩緩轉過身,將鏡頭朝向我們這個行星系,眨了最後一下眼睛。那張最孤獨的照片,遠沒有想像中宏偉,地球只是一粒可以拂去的塵沙。藍色的塵沙,與沙漠中任何一粒沙子一樣寂寞。
我無比羡慕旅行者二號,溫暖地告別後,一頭扎入冰冷的沒有盡頭的宇宙荒漠,飄蕩在充滿無盡可能性的虛空裡。
這次去柏林的旅程的紀錄片播出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感謝觀眾對我們的支持和厚愛。更令人鼓舞的是無數中國年輕人正拿起行囊,搭車奔走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去探索去收穫屬於自己的精彩旅程,完成自己的成人禮。
歡迎讀者能到網上或旅遊衛視收看我們的紀錄片《搭車去柏林》。
◎六月八日,從后海出發
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家裡把背包打了好幾遍,很少臨出門前會這麼仔細地準備行李。把東西拿出來又放進去,放進去又拿出來,反覆幾次都無從知道究竟要帶多少東西才能夠這三個月的旅行。這種心情有點兒像小學去郊遊的前一天晚上,興奮得睡不著覺,一直檢查自己包裡的糖果巧克力是不是夠吃一樣。愣愣地看著撐得滿滿的大包小包,它們靜靜地像在問我,到底準備好了麼?
雖然十年的拍片生涯中也經常出門,足跡基本上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但一直有著團隊的支持和精心的計畫。這次和谷岳一起,行程中太多要靠自己去解決和完成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恨不得把家也一起背走。沒錯,對背包客來講,這兩個歪歪扭扭的包就是家了。這種隨意旅行的方式,我一直嚮往很久,我痛恨充滿計畫的行程,彷彿一眼就可以看到結局的電影。然而,真的要上路時,我可以聽到來自遙遠內心的咚咚鼓聲。
六月八日,我們兩人在后海的一個酒吧裡面碰頭,就像平常一樣。我們把出發的地點定在后海,因為那曾經是少年時代的樂園,游泳,滑冰,刷夜(編按:不回家,在外面過夜)。中學時也會每天放學騎車專門到湖邊轉一圈,不為了什麼,只是單純地發呆,坐到太陽落山,水邊晚風吹來,聽著湖對面生澀的薩克斯,很舒服,也許這就是故鄉的感覺。與其說從后海的某一地出發,不如說是從我心裡的某一塊地兒出發。碰巧谷岳也有后海情結。他對北京許多快樂的記憶也是在后海沿岸發生的。但我們去了以後才發現,那天下了北京乾旱許久後的第一場大雨,我們被困在那兒了。
酒吧裡一個客人都沒有,早上十點,我們聚齊,外面雲霧濛濛,湖面平靜。拍了第一張合影照片,換上衝鋒衣(編按:透氣防水的登山服),各自背起四十公斤的負重。包裡除了衣服、帳篷、睡袋外,還有兩部攝影機和照相機、三角架、筆記本、各種充電器、電池,甚至一人還有一瓶防狼噴霧劑。把包一背,好像真是要遠行了。這時雨突然就大起來了,越等越大,中午了,不能再等下去,我們冒著大雨放棄了坐公車去公路邊的想法,攔了一輛出租車,趕赴六里橋京石高速入口,開始我們三個半月的搭車旅行……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尋「搭車去柏林」,你可能會得到幾十萬條資訊:二○○九年,兩個北京小伙子──谷岳、劉暢用一個夏天,以舉手搭便車的方式途經十幾個國家,一萬六千公里的旅程到達德國柏林,看望一個女孩。這個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戀三年的女友,這種極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見證了普通人愛情裡的閃光點。那麼,兩個旅行者中的另一個人,劉暢,總是會遇到朋友們各種各樣的疑問,你,又是為什麼而去的呢?我想,寫這本書也許可以表達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為了逃離我們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一開始,我認為一切都跟一本書有關。那就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書中兩個年輕人不斷瘋狂地穿行美洲:搭車、自駕、不能抑制地無目的地旅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儘管幾乎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卻具有相當的迷人之處。」
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路上》出版後,《紐約時報》刊登的書評這樣寫道:「在極度的時尚使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支離破碎,敏感性變得遲鈍薄弱的時代,如果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義的話,該書的出版就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路上》讓無數的年輕人拿起簡單的行囊上路,開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目的地的旅途。他們害怕鏡子中的自我,最終丟失在物質洪流裡,或僅僅是表演著為尋找自我所做的逃離。去哪裡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做出反抗現實的姿態來,這些年輕人表演、鞠躬,之後就往後一躍,跳進舞臺的側幕裡,五十多年來重複上演著這樣一幕幕鬧劇。這一文化轟轟烈烈繁衍至今天,從文學、從音樂、從電影,成為主流消費文化之外的另一體系。說到這裡,我們為什麼選擇搭車旅行已經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會離「年輕」這一辭彙越來越遠,我們長年如同螞蟻一般的努力奮鬥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變得微不足道,物質的家園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園形單影隻,搭車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導演,在搭車旅行之前,我曾設想過拍一部公路電影,一男一女,兩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卻永遠沒有相遇。男主角路過生命的孤獨與割捨,女主角路過生命的迷惘與歡愉。寫作劇本是漫長艱辛的過程,我發現,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請彷彿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三個多月的旅程,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人的人生:在新疆廣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車司機;在吉爾吉斯酒後遭遇牧民熱騰騰的馬油大餐;烏茲別克沙漠船隻墓地的守墓老人;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伊斯坦堡雄渾壯觀的歐亞兩岸;羅馬尼亞堅強的孤兒院志願者;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旅館的韓國老闆;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屬俱樂部;東柏林的藝術家貧民窟……親自體驗並拍攝一部公路紀錄片,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夢想。我相信公路電影的製作者們都經歷著這樣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遊也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遊歷。
《在路上》這本書從二○○○年一直陪伴我到現在,四次閱讀都沒有翻到最終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給這次旅程。在搭車旅途的某輛大卡車上,我在顛簸的駕駛室的臥鋪上讀完了最後一頁。車窗外是何時何地的風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結尾這樣寫道:
我知道在愛荷華州,在人們允許孩子們哭泣的地方,孩子們在大聲地哭泣著。今夜,星星就要出來,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臨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輝灑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隱沒掉最後一片海灘,然而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
這本小書是我個人的小小旅行隨想,有些旅程段落詳細,有些只是一筆帶過。這趟旅程我和谷岳約定好一人寫一本書,同樣的旅行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收穫。我偏執於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視角,偶然的機緣巧合,展開搭車去十餘個國家的夢想之旅,我沒有超於常人的意志品質,也沒有職業旅行家的豐富經驗,更沒有超凡脫俗的個人魅力。我只是因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而與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終結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因為這段路而得到了某種圓滿,於是那個原來執著的目標也許就不再重要。
◎清晨五點半的地鐵五號線
你可曾見過北京地鐵五號線清晨五點半的月臺?它華而不實地被設計成海洋動物曬乾後的軀殼的樣子,乾巴巴地,等待著早班的地下鐵從這邊來再從那邊走,等待著面無表情的人們前來重複命中注定的日子。我經常會在清晨,趕最早的一班地鐵回家,因為工作通常需要熬夜,我便有了這樣一種機會,體會與人群相反的軌跡,體會身體在極度透支後的某種亢奮,身體是軟的,而心底卻清明一片,靜逸安詳。你會發現夜與晝的更替是隨鳥的叫聲來臨,天知道北京竟有這麼多種鳥,在你不知道的遠方喧鬧。
鳥的聲音會被對面月臺漸漸匯聚的人聲終結,列車會把他們帶往市中心,而我的方向相反,等候在回家的路上,獨自擁有這一半的月臺,以一種旁觀的心態默默注視著對面越聚越多的人群。那些人雖然陌生,卻都是再熟悉不過的陌生人,我們都從五環外的新建高樓裡醒來,或是十幾個人擠在兩室一廳分割的公寓裡,因為搶洗手間而爭吵,因為左鄰右舍的梳洗打扮而詛咒著為什麼不能再睡上十幾分鐘。找到熟悉的早點攤,排隊買著熟悉的糊弄肚子的食物,然後強打起精神隨擁擠的地鐵奔赴一個小時後另一個屬於自己的格子間。
熟悉這樣的世界,這樣的陌生人,這樣的生活,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紋一樣。常常問自己,三十多歲了,如果有機會和別人交換各自的生活,那麼,我會選擇和誰交換?瀟灑地開寶馬(BMW)車的,還是在地鐵車廂裡啃油條的?沒有,熟悉的生活僅有這一點點差別,我們擁有同樣的苦難,僅靠可憐的一點點財富來顯示彼此的差別。三十多歲了,人生不再新鮮,多少對未知的探求也泯滅在這許許多多的「不得不」裡。不得不去向看板上成功的人生靠近:一家三口,穿著一塵不染的夏裝,跑向以外國風景地命名的美好社區,女人很滿足,男人很得意,孩子的頭髮很整齊。雖然覺得這一切很可笑,但是,開往城郊的地鐵來了,我也只能低頭走進車廂裡。每天,我們在地鐵五號線裡路過路人甲,再路過路人乙,看別人看自己,沒有一絲絕望。因為五號線代表我每天的旅程,無可選擇。
這僅是我二○○九年年初的想法 ,六個月後,我和一個叫谷岳的傢伙去了一萬多公里外的城市,那裡有他的姑娘,也有無數條血管般蓬勃的地鐵線,喧鬧地在每一個清晨流過城市的龐大身軀,那裡叫柏林。
◎谷岳的三分鐘
「三分鐘內可以發生許多事,欣賞一段不錯的音樂,吃一頓倉促的速食,經歷一場感情變故,改變一個人的某種世界觀,獲得或失去一筆財富,也可能失去親人,或離開一片你摯愛的熱土,再或踏上一段征途,很多很多……」
在北京南鑼鼓巷的一家小酒館,我把自己的三分鐘給了對面這個叫谷岳的傢伙,他用三分鐘和我說明了他的計畫:他想尋找一個旅伴,拍攝經驗豐富,能各自負擔費用,花三個月的時間,一起從北京出發,搭車旅行去德國首都柏林。用他的話講,去看女朋友的旅程也要給自己留下些什麼,這裡借用他的演講文稿:
「一直崇拜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再加上電影《摩托車日記》(台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和《荒野生存》(台譯:阿拉斯加之死)的啟發,我要去找伊卡,也要親自體驗一下『在路上』的自由精神。如果我是坐飛機去見她,那麼舷窗下的原野,我就無法用腳步去丈量,我和伊卡也就沒有更多的收穫,我想慢慢去感受與她距離越來越近所帶來的影響,對我生命的影響。
以前我也上過班,在二○○一年的時候,我在美國的通用電氣做金融(工作),算風險評估吧。工作了一個月後,突然有一天有一個深省,我就想我從小學就努力好好學習,上中學、上大學、找著一份好工作,要買房子、買車、結婚生孩子,這一輩子的東西都已經知道了,我覺得有點兒太遺憾了。所以二○○三年我把工作辭掉了,把我的家當都賣了,開始環球世界旅行。二○○六年認識我現在的女朋友伊卡,她是德國人。我跟她相處兩年後,她說她要回德國一段時間,想家了,這又給我再次上路的動力。另外我覺得社會越來越實際了,所有的東西都建立在金錢和互利的關係上,所以我想用這種搭車的方式,來尋找不是在金錢,不是在互利的關係上創建的一種友誼。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搭車,要搭陌生人的車。」
其實在這以前兩年我們就通過旅遊衛視的朋友認識,那時他就已經是職業的旅行家了。而我,一個拍紀錄片的小小導演,雖然也經歷過諸如雅魯藏布江大峽谷、長江源、柴達木、可哥西裡等地的探險拍攝,但旅行一直不是我的直接目的。而這次,更是沒有任何理由,只是要走,要出發,要一直走在路上。
十年前在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拚命看《麥田裡的守望者》(台譯:麥田捕手)這樣的小說,聽《涅槃》,去中戲小劇場蹭話劇《盜版浮士德》,和同學們聊著某大師艱澀難懂的電影,憧憬著將來一起拍充滿新銳氣息的片子,唾棄著所謂俗氣的生活,那時候覺得這肯定就是自己將來的人生。但是慢慢地從畢業開始,我也進入了一種大家都會進入的生活。去掙錢,去過一種世俗人眼中你應該過的那種生活。谷岳用三分鐘說了他的想法後,問我能不能走,感覺言語中還要給我一些時間去思考。但我內心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定要走,雖然當時搭車對我來說還只是天空上飄著的一種概念。那時我正處於人生的低潮,感慨自己十多年的時間在北京這個城市裡做了很多莫名的事情,表面上熱熱鬧鬧,內心卻無比空虛。我的故鄉,這座巨大而喧鬧的城市,時常讓我害怕失去僅有的一點兒歸屬感,失去掙扎生存的勇氣。
我的生活像是在莫比斯環(Mobius band)上爬的螞蟻一樣,螞蟻一直以為能從紙的開端爬到紙的末端,爬到末端才發現其實又到了開始的地方。一直原地打轉,缺少生活的新鮮和激情。所以一定要走。決定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很多的顧慮:我的存款不多,這三個月走了,生活來源就沒有了,雖然我是自由職業,沒有固定工作,沒有辭職的問題,但是同樣面臨生存的壓力。房租怎麼交?以後怎麼辦?長期合作拍片的客戶這次拒絕了,以後人家還會不會來找你合作?很多的機會就因此失去了。但是能促使我把這些都拋下而毅然決定走的主要原因,還是對這個城市的感覺,有時候我會覺得整個城市已離棄了我,我從城市的中心漂流到了城市的周邊──記得小時候是在長安街沿線長大,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遷徙,到三環外,四環外,過了這麼多年,甚至置身五環以外,從二十三樓的出租房眺望環內,曾經的核桃樹與梧桐依然蒼翠,但已物是人非。我很想笑,既然生活已把自己趕得越來越遠,為何不乾脆痛快點兒走得更遠?去看看真正想看的東西,「在路上」這三個字,一下子跳出來,在腦海裡閃著神聖的光輝。
「有些事情現在不去做,就永遠不會做了。」對面拿著啤酒的谷岳沒來由地說了一句。
十年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科學新聞,至今想起仍會發冷。
一九九九年情人節那天,旅行者二號在掠過冥王星後,飛向沒有盡頭的宇宙深淵。它的孤獨讓人不寒而慄,在調整方向奔赴這一命運時,一個女科學家,遙控它做了最後一件事情:緩緩轉過身,將鏡頭朝向我們這個行星系,眨了最後一下眼睛。那張最孤獨的照片,遠沒有想像中宏偉,地球只是一粒可以拂去的塵沙。藍色的塵沙,與沙漠中任何一粒沙子一樣寂寞。
我無比羡慕旅行者二號,溫暖地告別後,一頭扎入冰冷的沒有盡頭的宇宙荒漠,飄蕩在充滿無盡可能性的虛空裡。
這次去柏林的旅程的紀錄片播出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感謝觀眾對我們的支持和厚愛。更令人鼓舞的是無數中國年輕人正拿起行囊,搭車奔走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去探索去收穫屬於自己的精彩旅程,完成自己的成人禮。
歡迎讀者能到網上或旅遊衛視收看我們的紀錄片《搭車去柏林》。
◎六月八日,從后海出發
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家裡把背包打了好幾遍,很少臨出門前會這麼仔細地準備行李。把東西拿出來又放進去,放進去又拿出來,反覆幾次都無從知道究竟要帶多少東西才能夠這三個月的旅行。這種心情有點兒像小學去郊遊的前一天晚上,興奮得睡不著覺,一直檢查自己包裡的糖果巧克力是不是夠吃一樣。愣愣地看著撐得滿滿的大包小包,它們靜靜地像在問我,到底準備好了麼?
雖然十年的拍片生涯中也經常出門,足跡基本上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但一直有著團隊的支持和精心的計畫。這次和谷岳一起,行程中太多要靠自己去解決和完成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恨不得把家也一起背走。沒錯,對背包客來講,這兩個歪歪扭扭的包就是家了。這種隨意旅行的方式,我一直嚮往很久,我痛恨充滿計畫的行程,彷彿一眼就可以看到結局的電影。然而,真的要上路時,我可以聽到來自遙遠內心的咚咚鼓聲。
六月八日,我們兩人在后海的一個酒吧裡面碰頭,就像平常一樣。我們把出發的地點定在后海,因為那曾經是少年時代的樂園,游泳,滑冰,刷夜(編按:不回家,在外面過夜)。中學時也會每天放學騎車專門到湖邊轉一圈,不為了什麼,只是單純地發呆,坐到太陽落山,水邊晚風吹來,聽著湖對面生澀的薩克斯,很舒服,也許這就是故鄉的感覺。與其說從后海的某一地出發,不如說是從我心裡的某一塊地兒出發。碰巧谷岳也有后海情結。他對北京許多快樂的記憶也是在后海沿岸發生的。但我們去了以後才發現,那天下了北京乾旱許久後的第一場大雨,我們被困在那兒了。
酒吧裡一個客人都沒有,早上十點,我們聚齊,外面雲霧濛濛,湖面平靜。拍了第一張合影照片,換上衝鋒衣(編按:透氣防水的登山服),各自背起四十公斤的負重。包裡除了衣服、帳篷、睡袋外,還有兩部攝影機和照相機、三角架、筆記本、各種充電器、電池,甚至一人還有一瓶防狼噴霧劑。把包一背,好像真是要遠行了。這時雨突然就大起來了,越等越大,中午了,不能再等下去,我們冒著大雨放棄了坐公車去公路邊的想法,攔了一輛出租車,趕赴六里橋京石高速入口,開始我們三個半月的搭車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