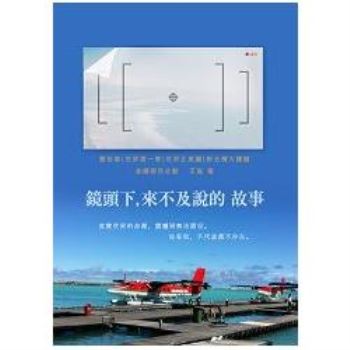年的味道──三兄弟的臘肉人生
每次採訪一個商家或是一個受訪者,我跟對方都會變成朋友,日後會互相關心。友情,才是工作中我最想要得到的東西;我不喜歡只把工作當工作,拍完了就閃人。
體驗三百六十五行,其實也是體會著三百六十五種人生。就算工作結束了,我回到自己的生活,還是會常常想起某一個採訪過的對象。他的表情、帶給我的印象,還有他說過的話,那些畫面與字句對我帶來的影響和改變,只有我自己知道。
嘉義的臘肉三兄弟,就是我常常放在心上的一家人。我永遠都記得當時去採訪他們,單是旁觀他們工作的樣子,就已暗自覺得:「天哪,我才不要做這個。」
那實在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但是,他們三兄弟一做就是六十年,一做就是一輩子。
阿里山下的大埕口
嘉義的水上鄉,有一家三兄弟做的湖南臘肉遠近馳名,好多媒體都曾經去採訪他們,我也不例外。大概在千禧年前後,我因為工作而去採訪他們。當年出發前,因為做了點功課,我已經大概知道他們家的臘肉和香腸是什麼樣子、用什麼方法製作;但即使如此,實地到場後,還是深深感慨自己「活像個城市鄉巴佬」。對於「臘肉」,我知道得太少太少……
三兄弟的家,也就是生產臘肉的地方,就在阿里山山腳下的一個小村落。過了那座村落,再往前去,就要上阿里山了。一進到他們家,映入眼簾的,彷彿就是台語說的「大埕口」。在一個像是三合院的建築結構裡,中央的廣場豎立起一根根黃色的支架。我看了有點疑惑,心想:「這應該是用來曬香腸的支架吧?但是那上面為何空無一物?香腸在哪?」
當時抵達的時間大約是清晨七點,我急著找資料裡的香腸,就隨口問起大哥。
我:「大哥,香腸在哪兒?不是有幾百斤的香腸嗎?」
大哥鎮定地說:「香腸都放進冰箱了。」
我:「香腸不是應該放在外面曬太陽嗎?」
大哥:「是啊,但是晚上會有露水,香腸如果還擺在外面會濕掉的,那香腸就會腐敗。」
我:「原來如此啊……」
當下,我有一種被當頭棒喝的感覺,覺得自己很糗,原來人家曬香腸不是一直丟在外面,而是白天曬完就得趕緊收起來。香腸需要風乾,而三兄弟的家位於阿里山山腳下,靠近山邊,露水更重,當然得更謹慎,一到傍晚就必須收好保存。身為「都市俗」,我知道露水,也知道香腸,但從沒想過這兩者之間是有關係的。
我終於看到員工把香腸從貨櫃裡「搬」出來,一串串放到架上。那時候我想著,眼前這些香腸終於跟印象中的香腸有點像了。但是過了一陣子,等全部的香腸都上了架,看著看著,我驚覺,它們散發出一種陌生的美,置身那一大片的紅,像是突然切換到過年的場景。
我被非常巨大的喜氣包圍著,那些喜氣一陣陣襲來,感染了我,讓我想到很多生活裡與小時候的畫面。平常都市人看到的香腸,頂多就是路邊攤或菜市場裡面吊個三串、五串,哪裡能夠想像得到,滿滿的香腸吊掛起來會是這樣的景象;當然也不會知道,原來製作香腸的老字號店家,每天要處理數百台斤的香腸
洞洞香腸
實際看到手工香腸的製作過程,才知道這中間有多少細節,大哥一家對待香腸又是多麼呵護備至。
單是日曬這個流程,他們不只是把香腸掛起來而已,也必須不時地去翻動,翻動後還要幫香腸按摩,按摩後還要拿出針來。對了,看到針,大家一定都很納悶吧?我當時也是。
那根針的大小,有如一般的縫衣針。大家都能理解翻動香腸,是為了均勻受熱,讓每截香腸的每個角落都能曬到太陽,但是拿針要做什麼呢?我站在太陽下的香腸架前,請主持人在鏡頭前問:「大哥,曬香腸,幹嘛拿針?」
「你仔細看,香腸表面已經變乾了,腸衣快要變脆了。香腸裡面有了氣體,產生氣泡,如果這時候不拿針把這些氣泡戳破,再晚一點,香腸就會整個膨脹起來,甚至爆開。」
大哥說,他們家的香腸是用真正的豬腸來製作,而天然的腸衣受不了劇烈的熱漲冷縮。所以日曬香腸時,必須時時注意風乾與受熱後的反應,在適當時機必須拿針刺穿氣泡。
「手工香腸是會有洞的!」
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自從知道這個道理之後,每次買香腸時,總會忍不住想觀察那上頭是不是真的有洞。因為,如果能看到腸衣上的洞,就代表這不是化學香腸,而是天然的香腸。
記得訪完大哥的兩年後,台灣有家很有名的香腸品牌出了問題,消費者有點恐慌,不知道如何才能買到安全無虞的香腸。但我卻有股莫名的自信,一直想著「看到腸衣上的洞,就是好香腸了」。現在回想起來,那種小小的驕傲,當然有點蠢,但是,這不就是實際採訪後所得到的、最實際的知識嗎?
當然,後來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在市面上找到表面有洞的香腸,除了可能因為這些香腸都是化學香腸;還有,都市人手中的香腸,往往都躺在封裝好的包裝盒裡,哪可能讓我們在買之前就見到、碰到它們的廬山真面目呢?
陽光下,不變的芬芳
除了腸衣上的洞,那一次採訪經驗還讓我知道,原來香腸名為「香腸」實在大有道理。單是日曬時,香腸裡與腸衣上的天然豬油,就會被陽光的熱度給逼出陣陣油脂芳香。也許因為城市人怕油怕慣了,看到「豬油」兩個字,總是觀感不佳,甚至覺得噁心,但是相信我,天然的豬油其實是很清香的。
在太陽照耀下,香腸裡均勻分布、白花花的油脂開始透著光,透亮之餘還襯著紅色的肉塊,特別好看,又散發出油脂的甜香……感受著眼前的這一幕,我生平第一次覺得「原來豬肉這麼美麗」、「香腸真是一種美麗而神奇的食物」,這實在與我平日理解的香腸大不相同。
這美麗而神奇的氣味,是大哥家祖傳數十年的味道。那趟採訪之前,我就知道大哥一家是從湖南來的,他們是所謂的「外省人」。早些年的「眷村」時代,其實我這年紀的人已經沒有實質的印象,只能從電視、長輩們口中重現關於眷村的種種畫面與故事,比如媽媽追著孩子打,左鄰右舍的媽媽圍坐一起包餃子,以及媽媽們做好家鄉菜互相交換嚐味道等等。
我想,大哥堅持的這個味道,應該就是家鄉的味道、眷村的味道,也是他們小時候的回憶。為了重現這個味道,他們煞費苦心。大哥做香腸的過程非常繁複,除了搬香腸、掛香腸,製作香腸肉餡的時候,他們對每種食材的選擇,以及調味料的比例掌握,也十分講究。油花、肉與調味料等等,該怎麼選、各該有多少重量,大哥一家人毫不馬虎。
但我一直以為,印象中的眷村媽媽做菜的時候,應該多半是信手拈來,不需要做到這麼精準。於是,我問大哥,為何要在材料跟比例上這麼斤斤計較?
「因為它好吃。」大哥說,這是六十年來大家都喜歡的味道,所以不能隨便調整它。
因為習慣的味道沒有變,所以遊子離開得再久,兩年、三年,甚至十幾年,每次回來都能吃到一樣的味道。讓這份味道的記憶伴隨成長,而不需要停留在過去。大哥的這份用心,不只放在香腸,還有臘肉。
時光裡,熟成的味道
看完了香腸,大哥領著我到「大埕口」的另外一頭,我看到一個大約兩百五十公分長、深度大約有一百二十公分的大窯;大哥要我猜猜那是什麼。當時一靠近大窯,覺得它非常燙,還可以聞到燒木頭、類似煙燻的味道。我靈機一動說:「那裡頭該不會是在燻香腸吧?」
「這裡頭燻的東西,是年的味道、家的味道。」大哥微笑地說著。當他搬開窯口上壓著的棉被、鋼筋做的支架,一股濃烈的氣味竄了上來,像是一個記憶的通道,一聞就會回到每年在家吃團圓飯、領紅包、跟兄弟姊妹打打鬧鬧的時刻。
大窯其實是燻窯,裡頭是成排吊掛整齊的臘肉,一眼看去,非常壯觀美麗。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以前看到臘肉都是躺在大賣場的架上、花車裡、被真空袋包裝好的,但原來臘肉的「成長背景」是這種近乎不真實、並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美麗。
每一塊窯裡的臘肉都被切得方方正正,但因為是手工,每塊肉雖然體積、重量大致相同,卻都長得不一樣。每塊臘肉被調味料浸漬、被煙燻染上的自然顏色,那種紅豔是如此通透而渾然天成,那個當下,我的視線完全無法離開那些臘肉。
大哥那時候要我猜這些臘肉要在窯裡待多久?香腸要曬七天,才算是熟成完畢,所以我半開玩笑地回答:「這些臘肉該不會得燻個七七四十九天吧?」大哥說:「沒有啦,這些臘肉燻個四天就好。」
到了傍晚,香腸就會被收進屋裡;但是臘肉,卻得在窯裡足足待滿四天,將近一百個鐘頭。待了這麼久的時間,才能讓臘肉的每個分子、每個細胞充分吸取燻香的氣味;而也要有足夠的煙燻量,才能封存住臘肉裡甜美的肉汁。
「遵循古法」這四個字對年輕人來說,有如天方夜譚,但我所看到的大哥一家人,做臘肉的態度跟方式,真的就是如此。
臘肉燻好之後,還要擺放到另一個房間裡,大哥說那個房間是「退煙室」;臘肉必須在退煙室裡待上一個禮拜,才能消除濃烈的煙燻味。因為,如果臘肉上的煙燻味太重,就會喧賓奪主,掩蓋了臘肉鮮甜的滋味,這也是我當初意想不到的事。
當時我看到一些臘肉上面有「白白的」痕跡,心想「這應該是發霉吧」?一度猶豫是否該發問,後來也的確問了大哥。
「這不是發霉,煙燻風乾之後,肉質的水分減少,鹽分會釋放出來,這是正常的現象。」大哥說。
掐不出成本的生意
這個答案除了再次讓我覺得自己很傻之外,我還想到,製作過程已經那麼辛苦、繁複,製作後的重量還會縮水,十斤的香腸風乾後只剩下六斤,十塊錢的成本只剩下六塊錢。大自然奪取了四塊錢的成本,你還得再補上那四塊錢,才能以十塊錢的規格賣出去。
「怎麼會有人做這麼傻的生意?」
「這麼傻的生意竟然一做六十年!」
「他,到底賺什麼?」
當下這些念頭與疑問,不停在我心裡翻攪。
老實說,那次採訪過程真的很愉快,尤其因為我自己就是外省小孩,跟大哥還有他的家人講話,聽到他們的口音,就想到小時候我跟爺爺奶奶聊天的樣子。
但是採訪結束後,大哥對我說的話,卻讓我的心頭有些沉重。
他問我:「是不是(覺得我們)很辛苦啊?」我說,當然啊,你們每天要搬五、六百斤的香腸出來曬,還要把重得要命的臘肉移來移去,真的是非常辛苦。我問他:「為什麼不用機器做呢?」
「這些東西,機器沒辦法做。」大哥說,除了攪肉機器可以勝任外,其他環節都是機器幫不上忙的;而且這些香腸和臘肉都不加防腐劑,很難大量生產。
「可是,你們現在年紀都大了耶,從小時候跟著爸媽過來台灣,到現在都已經變成大叔了……」我繼續追問。
「對啊,我媽也問。」
「媽媽怎麼說?」
「我媽說,你一整年都在做臘肉、曬香腸,可是別人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才會想起你,你怎麼會這麼傻?還要做這件事?」
大哥一家做了一整年的臘肉跟香腸,只有在過年那一個月生意最好,平常十一個月裡,生意都是清清淡淡。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堅持做呢?
「就算大家只在那個月裡想到我們,那也是快樂的。如果連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沒想到我們,那才真的是白做。」
「如果我不做,過年時,大家就只能吃到化學味道的臘肉。」
「我可以選擇做或不做,但這是我們家的味道。」
總有被人想起的時刻,這件事就值了!
可以讓大家年年都吃到記憶裡的味道,而這個味道足以串連起過去與現在,那這件事真是值了!
我在三兄弟身上看到了他們對食物品質的堅持,也看到了與眾不同的人生觀;即便他們坦言,真的很辛苦。從湖南到嘉義阿里山,要把一個味道完整地移植到不同的風土環境,這中間經過多少嘗試、失敗?如果沒有用心感受所處的土地,沒有摸清這一方鄉土的脾性,根本不可能做到,更不用談過程中無數的心力與材料耗損。
但是,他們堅定地說著:「如果我們不做,就再也沒有人吃得到這個味道了。」
六十年換一個不變的、年的味道、家的味道,你說,人生的值與不值,要如何衡量呢?
每次採訪一個商家或是一個受訪者,我跟對方都會變成朋友,日後會互相關心。友情,才是工作中我最想要得到的東西;我不喜歡只把工作當工作,拍完了就閃人。
體驗三百六十五行,其實也是體會著三百六十五種人生。就算工作結束了,我回到自己的生活,還是會常常想起某一個採訪過的對象。他的表情、帶給我的印象,還有他說過的話,那些畫面與字句對我帶來的影響和改變,只有我自己知道。
嘉義的臘肉三兄弟,就是我常常放在心上的一家人。我永遠都記得當時去採訪他們,單是旁觀他們工作的樣子,就已暗自覺得:「天哪,我才不要做這個。」
那實在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但是,他們三兄弟一做就是六十年,一做就是一輩子。
阿里山下的大埕口
嘉義的水上鄉,有一家三兄弟做的湖南臘肉遠近馳名,好多媒體都曾經去採訪他們,我也不例外。大概在千禧年前後,我因為工作而去採訪他們。當年出發前,因為做了點功課,我已經大概知道他們家的臘肉和香腸是什麼樣子、用什麼方法製作;但即使如此,實地到場後,還是深深感慨自己「活像個城市鄉巴佬」。對於「臘肉」,我知道得太少太少……
三兄弟的家,也就是生產臘肉的地方,就在阿里山山腳下的一個小村落。過了那座村落,再往前去,就要上阿里山了。一進到他們家,映入眼簾的,彷彿就是台語說的「大埕口」。在一個像是三合院的建築結構裡,中央的廣場豎立起一根根黃色的支架。我看了有點疑惑,心想:「這應該是用來曬香腸的支架吧?但是那上面為何空無一物?香腸在哪?」
當時抵達的時間大約是清晨七點,我急著找資料裡的香腸,就隨口問起大哥。
我:「大哥,香腸在哪兒?不是有幾百斤的香腸嗎?」
大哥鎮定地說:「香腸都放進冰箱了。」
我:「香腸不是應該放在外面曬太陽嗎?」
大哥:「是啊,但是晚上會有露水,香腸如果還擺在外面會濕掉的,那香腸就會腐敗。」
我:「原來如此啊……」
當下,我有一種被當頭棒喝的感覺,覺得自己很糗,原來人家曬香腸不是一直丟在外面,而是白天曬完就得趕緊收起來。香腸需要風乾,而三兄弟的家位於阿里山山腳下,靠近山邊,露水更重,當然得更謹慎,一到傍晚就必須收好保存。身為「都市俗」,我知道露水,也知道香腸,但從沒想過這兩者之間是有關係的。
我終於看到員工把香腸從貨櫃裡「搬」出來,一串串放到架上。那時候我想著,眼前這些香腸終於跟印象中的香腸有點像了。但是過了一陣子,等全部的香腸都上了架,看著看著,我驚覺,它們散發出一種陌生的美,置身那一大片的紅,像是突然切換到過年的場景。
我被非常巨大的喜氣包圍著,那些喜氣一陣陣襲來,感染了我,讓我想到很多生活裡與小時候的畫面。平常都市人看到的香腸,頂多就是路邊攤或菜市場裡面吊個三串、五串,哪裡能夠想像得到,滿滿的香腸吊掛起來會是這樣的景象;當然也不會知道,原來製作香腸的老字號店家,每天要處理數百台斤的香腸
洞洞香腸
實際看到手工香腸的製作過程,才知道這中間有多少細節,大哥一家對待香腸又是多麼呵護備至。
單是日曬這個流程,他們不只是把香腸掛起來而已,也必須不時地去翻動,翻動後還要幫香腸按摩,按摩後還要拿出針來。對了,看到針,大家一定都很納悶吧?我當時也是。
那根針的大小,有如一般的縫衣針。大家都能理解翻動香腸,是為了均勻受熱,讓每截香腸的每個角落都能曬到太陽,但是拿針要做什麼呢?我站在太陽下的香腸架前,請主持人在鏡頭前問:「大哥,曬香腸,幹嘛拿針?」
「你仔細看,香腸表面已經變乾了,腸衣快要變脆了。香腸裡面有了氣體,產生氣泡,如果這時候不拿針把這些氣泡戳破,再晚一點,香腸就會整個膨脹起來,甚至爆開。」
大哥說,他們家的香腸是用真正的豬腸來製作,而天然的腸衣受不了劇烈的熱漲冷縮。所以日曬香腸時,必須時時注意風乾與受熱後的反應,在適當時機必須拿針刺穿氣泡。
「手工香腸是會有洞的!」
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自從知道這個道理之後,每次買香腸時,總會忍不住想觀察那上頭是不是真的有洞。因為,如果能看到腸衣上的洞,就代表這不是化學香腸,而是天然的香腸。
記得訪完大哥的兩年後,台灣有家很有名的香腸品牌出了問題,消費者有點恐慌,不知道如何才能買到安全無虞的香腸。但我卻有股莫名的自信,一直想著「看到腸衣上的洞,就是好香腸了」。現在回想起來,那種小小的驕傲,當然有點蠢,但是,這不就是實際採訪後所得到的、最實際的知識嗎?
當然,後來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在市面上找到表面有洞的香腸,除了可能因為這些香腸都是化學香腸;還有,都市人手中的香腸,往往都躺在封裝好的包裝盒裡,哪可能讓我們在買之前就見到、碰到它們的廬山真面目呢?
陽光下,不變的芬芳
除了腸衣上的洞,那一次採訪經驗還讓我知道,原來香腸名為「香腸」實在大有道理。單是日曬時,香腸裡與腸衣上的天然豬油,就會被陽光的熱度給逼出陣陣油脂芳香。也許因為城市人怕油怕慣了,看到「豬油」兩個字,總是觀感不佳,甚至覺得噁心,但是相信我,天然的豬油其實是很清香的。
在太陽照耀下,香腸裡均勻分布、白花花的油脂開始透著光,透亮之餘還襯著紅色的肉塊,特別好看,又散發出油脂的甜香……感受著眼前的這一幕,我生平第一次覺得「原來豬肉這麼美麗」、「香腸真是一種美麗而神奇的食物」,這實在與我平日理解的香腸大不相同。
這美麗而神奇的氣味,是大哥家祖傳數十年的味道。那趟採訪之前,我就知道大哥一家是從湖南來的,他們是所謂的「外省人」。早些年的「眷村」時代,其實我這年紀的人已經沒有實質的印象,只能從電視、長輩們口中重現關於眷村的種種畫面與故事,比如媽媽追著孩子打,左鄰右舍的媽媽圍坐一起包餃子,以及媽媽們做好家鄉菜互相交換嚐味道等等。
我想,大哥堅持的這個味道,應該就是家鄉的味道、眷村的味道,也是他們小時候的回憶。為了重現這個味道,他們煞費苦心。大哥做香腸的過程非常繁複,除了搬香腸、掛香腸,製作香腸肉餡的時候,他們對每種食材的選擇,以及調味料的比例掌握,也十分講究。油花、肉與調味料等等,該怎麼選、各該有多少重量,大哥一家人毫不馬虎。
但我一直以為,印象中的眷村媽媽做菜的時候,應該多半是信手拈來,不需要做到這麼精準。於是,我問大哥,為何要在材料跟比例上這麼斤斤計較?
「因為它好吃。」大哥說,這是六十年來大家都喜歡的味道,所以不能隨便調整它。
因為習慣的味道沒有變,所以遊子離開得再久,兩年、三年,甚至十幾年,每次回來都能吃到一樣的味道。讓這份味道的記憶伴隨成長,而不需要停留在過去。大哥的這份用心,不只放在香腸,還有臘肉。
時光裡,熟成的味道
看完了香腸,大哥領著我到「大埕口」的另外一頭,我看到一個大約兩百五十公分長、深度大約有一百二十公分的大窯;大哥要我猜猜那是什麼。當時一靠近大窯,覺得它非常燙,還可以聞到燒木頭、類似煙燻的味道。我靈機一動說:「那裡頭該不會是在燻香腸吧?」
「這裡頭燻的東西,是年的味道、家的味道。」大哥微笑地說著。當他搬開窯口上壓著的棉被、鋼筋做的支架,一股濃烈的氣味竄了上來,像是一個記憶的通道,一聞就會回到每年在家吃團圓飯、領紅包、跟兄弟姊妹打打鬧鬧的時刻。
大窯其實是燻窯,裡頭是成排吊掛整齊的臘肉,一眼看去,非常壯觀美麗。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以前看到臘肉都是躺在大賣場的架上、花車裡、被真空袋包裝好的,但原來臘肉的「成長背景」是這種近乎不真實、並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美麗。
每一塊窯裡的臘肉都被切得方方正正,但因為是手工,每塊肉雖然體積、重量大致相同,卻都長得不一樣。每塊臘肉被調味料浸漬、被煙燻染上的自然顏色,那種紅豔是如此通透而渾然天成,那個當下,我的視線完全無法離開那些臘肉。
大哥那時候要我猜這些臘肉要在窯裡待多久?香腸要曬七天,才算是熟成完畢,所以我半開玩笑地回答:「這些臘肉該不會得燻個七七四十九天吧?」大哥說:「沒有啦,這些臘肉燻個四天就好。」
到了傍晚,香腸就會被收進屋裡;但是臘肉,卻得在窯裡足足待滿四天,將近一百個鐘頭。待了這麼久的時間,才能讓臘肉的每個分子、每個細胞充分吸取燻香的氣味;而也要有足夠的煙燻量,才能封存住臘肉裡甜美的肉汁。
「遵循古法」這四個字對年輕人來說,有如天方夜譚,但我所看到的大哥一家人,做臘肉的態度跟方式,真的就是如此。
臘肉燻好之後,還要擺放到另一個房間裡,大哥說那個房間是「退煙室」;臘肉必須在退煙室裡待上一個禮拜,才能消除濃烈的煙燻味。因為,如果臘肉上的煙燻味太重,就會喧賓奪主,掩蓋了臘肉鮮甜的滋味,這也是我當初意想不到的事。
當時我看到一些臘肉上面有「白白的」痕跡,心想「這應該是發霉吧」?一度猶豫是否該發問,後來也的確問了大哥。
「這不是發霉,煙燻風乾之後,肉質的水分減少,鹽分會釋放出來,這是正常的現象。」大哥說。
掐不出成本的生意
這個答案除了再次讓我覺得自己很傻之外,我還想到,製作過程已經那麼辛苦、繁複,製作後的重量還會縮水,十斤的香腸風乾後只剩下六斤,十塊錢的成本只剩下六塊錢。大自然奪取了四塊錢的成本,你還得再補上那四塊錢,才能以十塊錢的規格賣出去。
「怎麼會有人做這麼傻的生意?」
「這麼傻的生意竟然一做六十年!」
「他,到底賺什麼?」
當下這些念頭與疑問,不停在我心裡翻攪。
老實說,那次採訪過程真的很愉快,尤其因為我自己就是外省小孩,跟大哥還有他的家人講話,聽到他們的口音,就想到小時候我跟爺爺奶奶聊天的樣子。
但是採訪結束後,大哥對我說的話,卻讓我的心頭有些沉重。
他問我:「是不是(覺得我們)很辛苦啊?」我說,當然啊,你們每天要搬五、六百斤的香腸出來曬,還要把重得要命的臘肉移來移去,真的是非常辛苦。我問他:「為什麼不用機器做呢?」
「這些東西,機器沒辦法做。」大哥說,除了攪肉機器可以勝任外,其他環節都是機器幫不上忙的;而且這些香腸和臘肉都不加防腐劑,很難大量生產。
「可是,你們現在年紀都大了耶,從小時候跟著爸媽過來台灣,到現在都已經變成大叔了……」我繼續追問。
「對啊,我媽也問。」
「媽媽怎麼說?」
「我媽說,你一整年都在做臘肉、曬香腸,可是別人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才會想起你,你怎麼會這麼傻?還要做這件事?」
大哥一家做了一整年的臘肉跟香腸,只有在過年那一個月生意最好,平常十一個月裡,生意都是清清淡淡。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堅持做呢?
「就算大家只在那個月裡想到我們,那也是快樂的。如果連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沒想到我們,那才真的是白做。」
「如果我不做,過年時,大家就只能吃到化學味道的臘肉。」
「我可以選擇做或不做,但這是我們家的味道。」
總有被人想起的時刻,這件事就值了!
可以讓大家年年都吃到記憶裡的味道,而這個味道足以串連起過去與現在,那這件事真是值了!
我在三兄弟身上看到了他們對食物品質的堅持,也看到了與眾不同的人生觀;即便他們坦言,真的很辛苦。從湖南到嘉義阿里山,要把一個味道完整地移植到不同的風土環境,這中間經過多少嘗試、失敗?如果沒有用心感受所處的土地,沒有摸清這一方鄉土的脾性,根本不可能做到,更不用談過程中無數的心力與材料耗損。
但是,他們堅定地說著:「如果我們不做,就再也沒有人吃得到這個味道了。」
六十年換一個不變的、年的味道、家的味道,你說,人生的值與不值,要如何衡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