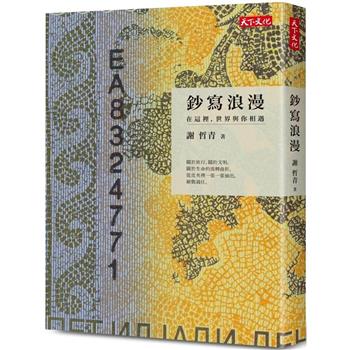雨林深處的天堂誘惑之舞
當我凝視著那向內陸延伸而去的疊翠層巒,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興奮;在山的另一邊,人類文明從未涉入……這裡的袋鼠在樹上爬,還有能抓破原住民肚皮的凶悍食火雞……。在這片幽暗的太古森林裡,有著地球上最奇特、最美麗的羽族—牠們是天堂鳥。
—華萊士《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The Malay Archipelago, 1869)
天還沒亮,我就跟著嚮導阿布深入幽黯泥濘的叢林。雖然這兩天沒有下雨,但是樹林下層仍然窒悶潮濕,走沒十公尺遠,身上的衣服就全濕了。一行人奮力地在雨林掙扎了四十分鐘後,我們來到了一塊小小的林間空地,阿布回頭咧嘴一笑,用眼神示意我找個地方坐下,然後靜待奇蹟發生。
半小時過後,第一隻鳥飛了進來,就站在枝頭最醒目的所在。牠有著優雅可愛的金黃色頭部,尾巴則是一長串瑰麗華美的緋紅色長羽,在波希米亞式的尾端後面,另外還綴著兩根捲曲的黑色纖羽,上下左右地小幅度跳動。
一會兒之後,其他鳥兒也加入牠的行列,接下來的時刻才讓我目瞪口呆,只見樹枝上所有的鳥不約而同地露出金屬光澤的亮綠前胸,把翅膀繞著頭部形成亮麗烏黑的誇張領圍,然後張開金黃色的前喙,一起炫耀式地舞動臀部、擺盪翅膀、旋轉身體。偶爾有一兩隻淡褐色的母鳥加入舞蹈,像選秀節目裡刁鑽無理的評審團一樣,在公鳥前後品頭論足,偶爾加入合音唱和。不過牠們琴瑟和鳴的吱嘎聲,對於人來說,聽起來只能用「不堪入耳」來形容。如果這個時候,配上探戈或佛朗明哥的舞曲,那就完美無憾了!
實際上,當第一隻天堂鳥開舞之後,大家都屏息專注地欣賞天堂鳥的求偶儀式,連呼吸都不敢太大聲,深怕一有驚動,天堂鳥就逃逸無蹤。
二十分鐘過去了,樹上的舞蹈火熱進行,就在不經意的下一秒鐘,牠們突然停止所有動作(真的很突然!),然後朝四面八方飛去。我在現場,尚未意會到發生了什麼事,這場華麗的舞會就倏然結束了。
我所看見的「舞會」,其實是生物學家所說的「群集展示」(Lek Mating),也就是集體求偶競爭,不僅天堂鳥會這麼做,我們人類也有類似行為。從台北東區夜店的排舞、維也納上流名門的社交舞會,一直到南島民族的豐年祭,都是兼具生物學與文化意義的競偶大會。阿布告訴我,其實,天堂鳥舞會每次結束的方式都相同(所以不是我的錯),如果願意的話,今天下午五點,再回到相同的地方,我會看到一樣的場景(當然要另外付錢)……明天早上、傍晚,接下來的每一天,這些鳥都會在同一棵樹碰頭、尬舞、然後一哄而散。
當年,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是在阿魯群島(Aru Islands),記錄了相同的情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當一八六二年華萊士回到倫敦時,他的行李箱內飼養了兩隻小天堂鳥,這對苦命鳥一路靠著吃米粒、香蕉,麵包裡的蟲及蟑螂,才勉強撐到英國。當這兩隻天堂鳥交到倫敦動物協會時,大家只能對華萊士頂禮膜拜。畢竟,在此之前,沒有歐洲人見過活生生的天堂鳥。
早在一五二二年麥哲倫環球船隊返回歐洲時,水手們就帶著天堂鳥的標本高價兜售。歐洲人訝異於這種鳥絢麗多彩的羽毛,以及「沒有腳」這件奇怪的事實。當大家問水手這種鳥為什麼沒有腳時,水手認真地轉述馬來商人的故事:這種神聖的動物生活在天堂最低層,牠們不需要翅膀,也沒有雙腳,更不會停留在陸地上,神奇的天堂鳥像雲朵一樣,曼妙婆娑地飄浮在天地之間……而且馬來人再三強調,這些鳥是無法打獵捕捉的,只有在天命將盡時,牠們會像落葉一樣墜地身亡,然後人們才有機會在密林撿拾。
因為這個以訛傳訛的古怪傳說,天堂鳥的學名被取為「Paradisaea apoda」,其中的「apoda」,在希臘文的意思就是「沒有腳」。八十八星座中的南天星座「天燕座」(Apus,意思也是「沒有腳」,是希臘學名拉丁化的結果),其實指的就是生活在新幾內亞的天堂鳥。
根據倫敦林奈學會(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的統計,全世界總共有四十二種天堂鳥,華萊士在《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一共記錄了五種,而我只在野外看過三種,後來在峇里島天堂鳥園又看到了一種,從羽毛像寶石一樣熠熠生輝的王風鳥(Cicinnurus regius),到保育區內常見,也被稱做「紅羽天堂鳥」的幾內亞大極樂鳥(Paradisaea raggiana),每一種天堂鳥都有令其他物種難以望其項背的絢爛,每一隻即興又華麗的舞蹈都教人目眩神迷。
在神話、傳說占有一席之地的天堂鳥,自然也不會在紙鈔世界裡缺席。
一九七五年脫離澳洲管轄獨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在國旗、國徽及紙鈔發行,都有幾內亞極樂鳥的身影。舉辦超過五十年,召集幾內亞島上各原住民的嘉年華「戈羅卡大會」(Goroka Show),就可以看到許多原住民頭戴搖曳繽紛的羽毛佩飾,多半是族群數量龐大的幾內亞極樂鳥的廓羽及尾羽。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紙鈔發行,正面也是幾內亞天堂鳥,二○○七年之前是占滿畫面的大圖騰,二○○八年以後天堂鳥被格縮放置到紙鈔正面的左上角。但無論如何,天堂鳥羽高氣昂的姿態是不變的主題。
而與巴布亞新幾內亞比鄰的印尼,使用天堂鳥的次數也不少。印尼群島最東方的巴布亞省與西伊里安查亞,一九四五年到六二年是荷蘭王國的海外殖民地「荷屬新幾內亞」(Netherlands New Guinea),五○年代所流通的紙鈔,就是荷蘭朱利安納女王(Juliana of the Netherlands)與天堂鳥的組合,不過氣虛貧弱的構圖似乎也預示了王國日薄西山的沒落。
一九五九年由英國德拉魯有限公司(Thomas de la Rue)印製、印尼國家銀行發行的花鳥系列最受喜愛,正面以爪哇傳統紋飾,再加上傳承自德國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筆法嚴謹的植物素描,只用簡單套色突顯花草的存在感,充滿沉寂靜謐的自然氛圍。背面的太陽鳥(五盧比)、鮭色鳳頭鸚鵡(十盧比)、大白鷺(二十五盧比)、白腹海鵰(五十盧比)、馬來犀鳥(一百盧比)、爪哇原雞(五百盧比)與大天堂鳥(一千盧比),跳脫政治綁架與歷史輻射,以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美國鳥類》(Birds of America)圖鑑式生動筆觸,勾勒出強烈的生命動感,是藝術史上第一套完全以生態為主題的法幣通貨,即使只是欣賞紙鈔上精緻的凹版印刷也十分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紀的時尚非常愛用羽毛來做為裝飾,仕女帽、胸針、頭飾都用得到羽毛。傳說沉沒的鐵達尼號上投保金額最高的,就是四十箱精緻高雅的珍禽羽毛。如果就重量來看,當時只有鑽石的價格比羽毛高。正是這個原因,大規模的獵殺,一度還讓天堂鳥瀕臨絕跡。有鑑於此,一九○九至一二年,英國下議院院長英格拉姆(Sir William Ingram)將只生存在印尼、新幾內亞與澳洲東北端的大天堂鳥引進千里達島,企圖繁殖生產。因此,今天我們在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所發行的一百元紙鈔上也看得到大天堂鳥。
不過更諷刺的是,當全世界開始關注亞洲與澳洲天堂鳥的生態困境,紛紛加以保護復育的同時,加勒比海的千里達島反而開始濫捕濫殺,一九六六年以後,大天堂鳥反而在西印度群島銷聲匿跡。
觀光客拿著兩萬盧比的紙鈔(上頭也是大天堂鳥),向票亭買了一張昂貴的鳥園門票,打算在這巨大的鋼絲籠裡,找尋華萊士筆下的天堂之鳥。每個人在園中上上下下,想知道傳說中會跳舞的鳥,真實模樣究竟為何,但是我知道,如此動人的誘惑之舞,不會在這裡發生,唯有回到雨林深處,我們才有機會見識到大自然最古怪,卻也最唯美的求愛儀式。
遇見沙漠中的曼哈頓
葉門之旅,艱困的程度遠超過我曾到過的任何地方……我的軟骨自膝蓋移位,很顯然地,我已將它們磨損……。
—塞西格《在群山之中》
葉門,是個具有精神分裂傾向的大地,一方面對海洋有熱切的期盼,而它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則是充滿傳說與未知,混合廣場焦慮與幽閉恐懼的內陸沙漠。
有文字記載開始,葉門的過去就充斥著無法辨認的荒謬無稽:為了歡祝國王誕辰的慶典,數以千計的奴隸相互殘殺……可以破壞水庫的巨無霸老鼠……岩洞居民用蜂蜜浸泡木乃伊,然後賣給遠方國度的蘇丹王,當做保健食品……沙漠中超過二千個部落,各自為政,而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風俗與語言……吃魚的駱駝、流血的樹……嚼著就可神清氣爽的葉子……藏著惡鬼,終年噴著火焰與毒氣的古井,是《聖經》使徒驅魔後的遺跡……穿著裙子,別著彎刀的男人……。所有的一切,聽起來既危險又迷人,讓人躍躍欲試。
不過我知道這些故事的地方,是在從印度孟買前往阿曼首都馬斯喀特(Muscat)的海上。除了睡覺、洗澡、上廁所以外,來自沙漠古城的哈第,總是眉飛色舞地講著有趣而奇怪的故事,他是我見過最會說故事的人之一。
下船道別之前,哈第拿出一張紙鈔,慎重其事地告訴我:「我家就在這裡,房子已經有千百年的歷史,有機會去看看……。」
我翻到紙鈔背面,仔細端詳這張面額五十里亞爾(Rial)上簡潔俐落,具有明顯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心裡想:「騙人的吧!」
許多年後,事實證明,孤陋寡聞的井底之蛙不是哈第,是我。
**********
葉門首都薩那(Sana'a),是一座質樸典雅、具有人情味的古老城市。
當地人總喜歡轉述先知穆罕默德的說法:「人間有三個天堂—呼羅珊的梅爾夫(Merv of Khurasan)、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以及葉門的薩那……。其中薩那更是天堂中的天堂。」
在《蒙古祕史》中被稱之為麻里兀的梅爾夫,原本是中世紀絲路上最大商業都會,人口超過一百萬。一二二○年,鐵木真的么子拖雷,派遣大軍圍困梅爾夫,在堅守半年之後不幸落城,戰後除了少數工匠倖免苟活之外,全市慘遭屠殺滅城。梅爾夫從此一蹶不振,在風沙中荒廢頹敝的清真寺、宮殿與城牆,充滿了無處話淒涼的悲戚。
我迷戀大馬士革的陳跡過往,而巷弄內茶館的說書人對於大馬士革的一切,更是如數家珍:使徒保羅歸信的教會、抗擊十字軍的英雄薩拉丁、暗中活躍潛伏的愛德華‧勞倫斯、徘徊在大市集的幽靈……,每個角落都有專屬的故事,每個轉角都能與歷史久別重逢。不過,大馬士革實在是太大了,稍不留意,就很容易迷失在茫茫人海,尋不回自己。
所以,我同意先知的看法,薩那有梅爾夫的清虛、大馬士革的豐厚,卻没有他們的寒愴或自大。薩那古城繁榮,卻少見喧譁爭鬧。來到薩那,你會發現時間不再奢侈,一壺涼茶、一袋水煙,就能消磨一下午的慵懶。
薩那,的確是天堂中的天堂。
打從一九六○年代開始,薩那就是葉門紙鈔貫穿時空的主題,唯一改變的,是不同的觀看角度。如果將它們一字排開,我覺得與歌川廣重的浮世繪《江戶百景》有異曲同工之妙,從鷹眼俯視、漫步觀望到格放特寫,每個視角都顯示葉門人對薩那的愛始終不移。我特別喜歡一九七一年二十里亞爾與九三年一百里亞爾的空中鳥瞰,全智全能的造物者視角,將畫面情境提昇到《一千零一夜》的神話層次,畢竟根據天方夜譚的文字轉述,阿拉丁與辛巴達,都曾造訪過這座美麗的城市。
時間來到二○一一年,第三次造訪葉門。不過這一次,是追隨著被偉大探險家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譽為「最後一位浪漫主義時代旅行家」的芙瑞雅‧史塔克(Freya Stark)的《阿拉伯南方之門》(The Southern Gates of Arabia)的故事,深入哈德拉毛(Hadhramaut)的神祕荒漠,也就是哈第告訴我發生許多超自然事件的阿拉伯沙地。拜科技文明所賜,從海岸線拉進沙漠只需要十四小時的車程,就當暮光將近之時,我看見地平線另一頭垂直與水平線所構成的建築線條,我知道,希巴姆(Shibam)近了。
對於現代人來說,希巴姆這個名字很陌生,聽起來像是某種不好吃的巧克力品牌。實際上這座千年古城,一九八二年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劃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名單,甚至出現在信用卡的電視廣告上。希巴姆的建築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是因為每棟高樓都以參天之勢拔地而起,而且不止一棟,而是整座城市。
早在中世紀之時,哈德拉毛沙漠的住民就用混漿混入磨碎的雜草,充分攪拌過後製作成磚頭的形狀,然後放在太陽下曬乾。最後的作品就是堅硬無比的長方泥磚。接下來的方式就和我們砌磚牆蓋房子相似,需要的只是一層層向上疊加。通常一棟大樓平均有七至十層樓的高度,建築物的外牆還會用石灰塗飾,除了美觀之外,防蟲也是主要功能。住戶大都是姓氏相同的親族,哈第的家族就在其中一棟。
如果看過薩那建築洛可可式的花邊飾帶,就會覺得希巴姆的風格太樸素簡單。隔天,我花了一下午的時間,找到了哈第所屬的哈斯曼家族,長老親切地招待我到客廳坐坐,哈德拉毛人似乎也不太在意房屋的內部裝飾,除了窗櫺和門框是雕花木架之外,室內空間極簡素淨。如果瑞士建築大師柯比意在現場,一定對希巴姆讚不絕口。後來我才了解,無論是建築形式或居家風格,都和伊斯蘭宗派與民族性格有關,不同的性別、不同的社會階層,分配到的是不同的室內空間,而觸目所及的一切都要力求樸質。
「我想,先知也要我們這麼做。」至少哈第的叔父是這樣告訴我的。
許多在海外工作的阿拉伯裔勞工,百分之九十都來自葉門,尤其哈德拉毛沙漠地區,這裡的荒涼雖然帶有不尋常的美感,但想在這片不毛之地維持生計是一件艱辛的事。哈第所屬的哈斯曼家族,有七成的男子都遠赴海外打工:在新加坡的餐廳、在印度洋的散裝貨輪、在大興土木的阿布達比、在沙烏地的鑽井油田……每個角落都可以看見葉門人辛勤揮汗的身影,他們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弱勢的一群。
向晚時分,我登上希巴姆古城對面的山頭,這是紙鈔上的取景角度,拍攝位置最好的所在地,早就被歐洲觀光客的腳架霸佔,所有人都來爭睹魔幻時光。當太陽接近西方的地平線時,沸騰的熱度迅速下降,西風在燠熱中夾帶些許涼意,相機快門在四周的感嘆聲中此起彼落。這座被譽為「沙漠中的曼哈頓」的古城,亮褐色外牆在塞尚色調的陽光下轉成金黃,水平與垂直線條構成的立面、銳角,在陰影下更加強烈,遠方傳來少年們踢足球的吆喝呼聲,街口破爛的卡車、廢棄大樓的斑駁殘跡、無人看管的羊群,讓希巴姆遙不可及的絕美,適度地回到人間,這是可以接受的衰敗,人人心知肚明,是看破卻不說破的祕密。
當最後一道餘暉從山頭褪去,天空從粉紅、酒紅到深紫,古城稀疏的燈火意興闌珊地逐一點亮,所有可辨認的形狀逐漸消融在暮色之中。
「我真想看見這樣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與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那時,我才可以對正在逝去的瞬間說:『請你為我停留片刻吧!你是如此的美!』我的浮生的痕跡才不致在永劫中消褪—我現在就彷彿已預感,屆時我徹底享受著那瞬間。」歌德在《浮世德》中寫下了如此的感慨,在這一瞬間,我明白了浮世德的心情。
摘自《鈔寫浪漫》
當我凝視著那向內陸延伸而去的疊翠層巒,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興奮;在山的另一邊,人類文明從未涉入……這裡的袋鼠在樹上爬,還有能抓破原住民肚皮的凶悍食火雞……。在這片幽暗的太古森林裡,有著地球上最奇特、最美麗的羽族—牠們是天堂鳥。
—華萊士《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The Malay Archipelago, 1869)
天還沒亮,我就跟著嚮導阿布深入幽黯泥濘的叢林。雖然這兩天沒有下雨,但是樹林下層仍然窒悶潮濕,走沒十公尺遠,身上的衣服就全濕了。一行人奮力地在雨林掙扎了四十分鐘後,我們來到了一塊小小的林間空地,阿布回頭咧嘴一笑,用眼神示意我找個地方坐下,然後靜待奇蹟發生。
半小時過後,第一隻鳥飛了進來,就站在枝頭最醒目的所在。牠有著優雅可愛的金黃色頭部,尾巴則是一長串瑰麗華美的緋紅色長羽,在波希米亞式的尾端後面,另外還綴著兩根捲曲的黑色纖羽,上下左右地小幅度跳動。
一會兒之後,其他鳥兒也加入牠的行列,接下來的時刻才讓我目瞪口呆,只見樹枝上所有的鳥不約而同地露出金屬光澤的亮綠前胸,把翅膀繞著頭部形成亮麗烏黑的誇張領圍,然後張開金黃色的前喙,一起炫耀式地舞動臀部、擺盪翅膀、旋轉身體。偶爾有一兩隻淡褐色的母鳥加入舞蹈,像選秀節目裡刁鑽無理的評審團一樣,在公鳥前後品頭論足,偶爾加入合音唱和。不過牠們琴瑟和鳴的吱嘎聲,對於人來說,聽起來只能用「不堪入耳」來形容。如果這個時候,配上探戈或佛朗明哥的舞曲,那就完美無憾了!
實際上,當第一隻天堂鳥開舞之後,大家都屏息專注地欣賞天堂鳥的求偶儀式,連呼吸都不敢太大聲,深怕一有驚動,天堂鳥就逃逸無蹤。
二十分鐘過去了,樹上的舞蹈火熱進行,就在不經意的下一秒鐘,牠們突然停止所有動作(真的很突然!),然後朝四面八方飛去。我在現場,尚未意會到發生了什麼事,這場華麗的舞會就倏然結束了。
我所看見的「舞會」,其實是生物學家所說的「群集展示」(Lek Mating),也就是集體求偶競爭,不僅天堂鳥會這麼做,我們人類也有類似行為。從台北東區夜店的排舞、維也納上流名門的社交舞會,一直到南島民族的豐年祭,都是兼具生物學與文化意義的競偶大會。阿布告訴我,其實,天堂鳥舞會每次結束的方式都相同(所以不是我的錯),如果願意的話,今天下午五點,再回到相同的地方,我會看到一樣的場景(當然要另外付錢)……明天早上、傍晚,接下來的每一天,這些鳥都會在同一棵樹碰頭、尬舞、然後一哄而散。
當年,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是在阿魯群島(Aru Islands),記錄了相同的情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當一八六二年華萊士回到倫敦時,他的行李箱內飼養了兩隻小天堂鳥,這對苦命鳥一路靠著吃米粒、香蕉,麵包裡的蟲及蟑螂,才勉強撐到英國。當這兩隻天堂鳥交到倫敦動物協會時,大家只能對華萊士頂禮膜拜。畢竟,在此之前,沒有歐洲人見過活生生的天堂鳥。
早在一五二二年麥哲倫環球船隊返回歐洲時,水手們就帶著天堂鳥的標本高價兜售。歐洲人訝異於這種鳥絢麗多彩的羽毛,以及「沒有腳」這件奇怪的事實。當大家問水手這種鳥為什麼沒有腳時,水手認真地轉述馬來商人的故事:這種神聖的動物生活在天堂最低層,牠們不需要翅膀,也沒有雙腳,更不會停留在陸地上,神奇的天堂鳥像雲朵一樣,曼妙婆娑地飄浮在天地之間……而且馬來人再三強調,這些鳥是無法打獵捕捉的,只有在天命將盡時,牠們會像落葉一樣墜地身亡,然後人們才有機會在密林撿拾。
因為這個以訛傳訛的古怪傳說,天堂鳥的學名被取為「Paradisaea apoda」,其中的「apoda」,在希臘文的意思就是「沒有腳」。八十八星座中的南天星座「天燕座」(Apus,意思也是「沒有腳」,是希臘學名拉丁化的結果),其實指的就是生活在新幾內亞的天堂鳥。
根據倫敦林奈學會(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的統計,全世界總共有四十二種天堂鳥,華萊士在《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一共記錄了五種,而我只在野外看過三種,後來在峇里島天堂鳥園又看到了一種,從羽毛像寶石一樣熠熠生輝的王風鳥(Cicinnurus regius),到保育區內常見,也被稱做「紅羽天堂鳥」的幾內亞大極樂鳥(Paradisaea raggiana),每一種天堂鳥都有令其他物種難以望其項背的絢爛,每一隻即興又華麗的舞蹈都教人目眩神迷。
在神話、傳說占有一席之地的天堂鳥,自然也不會在紙鈔世界裡缺席。
一九七五年脫離澳洲管轄獨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在國旗、國徽及紙鈔發行,都有幾內亞極樂鳥的身影。舉辦超過五十年,召集幾內亞島上各原住民的嘉年華「戈羅卡大會」(Goroka Show),就可以看到許多原住民頭戴搖曳繽紛的羽毛佩飾,多半是族群數量龐大的幾內亞極樂鳥的廓羽及尾羽。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紙鈔發行,正面也是幾內亞天堂鳥,二○○七年之前是占滿畫面的大圖騰,二○○八年以後天堂鳥被格縮放置到紙鈔正面的左上角。但無論如何,天堂鳥羽高氣昂的姿態是不變的主題。
而與巴布亞新幾內亞比鄰的印尼,使用天堂鳥的次數也不少。印尼群島最東方的巴布亞省與西伊里安查亞,一九四五年到六二年是荷蘭王國的海外殖民地「荷屬新幾內亞」(Netherlands New Guinea),五○年代所流通的紙鈔,就是荷蘭朱利安納女王(Juliana of the Netherlands)與天堂鳥的組合,不過氣虛貧弱的構圖似乎也預示了王國日薄西山的沒落。
一九五九年由英國德拉魯有限公司(Thomas de la Rue)印製、印尼國家銀行發行的花鳥系列最受喜愛,正面以爪哇傳統紋飾,再加上傳承自德國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筆法嚴謹的植物素描,只用簡單套色突顯花草的存在感,充滿沉寂靜謐的自然氛圍。背面的太陽鳥(五盧比)、鮭色鳳頭鸚鵡(十盧比)、大白鷺(二十五盧比)、白腹海鵰(五十盧比)、馬來犀鳥(一百盧比)、爪哇原雞(五百盧比)與大天堂鳥(一千盧比),跳脫政治綁架與歷史輻射,以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美國鳥類》(Birds of America)圖鑑式生動筆觸,勾勒出強烈的生命動感,是藝術史上第一套完全以生態為主題的法幣通貨,即使只是欣賞紙鈔上精緻的凹版印刷也十分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紀的時尚非常愛用羽毛來做為裝飾,仕女帽、胸針、頭飾都用得到羽毛。傳說沉沒的鐵達尼號上投保金額最高的,就是四十箱精緻高雅的珍禽羽毛。如果就重量來看,當時只有鑽石的價格比羽毛高。正是這個原因,大規模的獵殺,一度還讓天堂鳥瀕臨絕跡。有鑑於此,一九○九至一二年,英國下議院院長英格拉姆(Sir William Ingram)將只生存在印尼、新幾內亞與澳洲東北端的大天堂鳥引進千里達島,企圖繁殖生產。因此,今天我們在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所發行的一百元紙鈔上也看得到大天堂鳥。
不過更諷刺的是,當全世界開始關注亞洲與澳洲天堂鳥的生態困境,紛紛加以保護復育的同時,加勒比海的千里達島反而開始濫捕濫殺,一九六六年以後,大天堂鳥反而在西印度群島銷聲匿跡。
觀光客拿著兩萬盧比的紙鈔(上頭也是大天堂鳥),向票亭買了一張昂貴的鳥園門票,打算在這巨大的鋼絲籠裡,找尋華萊士筆下的天堂之鳥。每個人在園中上上下下,想知道傳說中會跳舞的鳥,真實模樣究竟為何,但是我知道,如此動人的誘惑之舞,不會在這裡發生,唯有回到雨林深處,我們才有機會見識到大自然最古怪,卻也最唯美的求愛儀式。
遇見沙漠中的曼哈頓
葉門之旅,艱困的程度遠超過我曾到過的任何地方……我的軟骨自膝蓋移位,很顯然地,我已將它們磨損……。
—塞西格《在群山之中》
葉門,是個具有精神分裂傾向的大地,一方面對海洋有熱切的期盼,而它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則是充滿傳說與未知,混合廣場焦慮與幽閉恐懼的內陸沙漠。
有文字記載開始,葉門的過去就充斥著無法辨認的荒謬無稽:為了歡祝國王誕辰的慶典,數以千計的奴隸相互殘殺……可以破壞水庫的巨無霸老鼠……岩洞居民用蜂蜜浸泡木乃伊,然後賣給遠方國度的蘇丹王,當做保健食品……沙漠中超過二千個部落,各自為政,而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風俗與語言……吃魚的駱駝、流血的樹……嚼著就可神清氣爽的葉子……藏著惡鬼,終年噴著火焰與毒氣的古井,是《聖經》使徒驅魔後的遺跡……穿著裙子,別著彎刀的男人……。所有的一切,聽起來既危險又迷人,讓人躍躍欲試。
不過我知道這些故事的地方,是在從印度孟買前往阿曼首都馬斯喀特(Muscat)的海上。除了睡覺、洗澡、上廁所以外,來自沙漠古城的哈第,總是眉飛色舞地講著有趣而奇怪的故事,他是我見過最會說故事的人之一。
下船道別之前,哈第拿出一張紙鈔,慎重其事地告訴我:「我家就在這裡,房子已經有千百年的歷史,有機會去看看……。」
我翻到紙鈔背面,仔細端詳這張面額五十里亞爾(Rial)上簡潔俐落,具有明顯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心裡想:「騙人的吧!」
許多年後,事實證明,孤陋寡聞的井底之蛙不是哈第,是我。
**********
葉門首都薩那(Sana'a),是一座質樸典雅、具有人情味的古老城市。
當地人總喜歡轉述先知穆罕默德的說法:「人間有三個天堂—呼羅珊的梅爾夫(Merv of Khurasan)、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以及葉門的薩那……。其中薩那更是天堂中的天堂。」
在《蒙古祕史》中被稱之為麻里兀的梅爾夫,原本是中世紀絲路上最大商業都會,人口超過一百萬。一二二○年,鐵木真的么子拖雷,派遣大軍圍困梅爾夫,在堅守半年之後不幸落城,戰後除了少數工匠倖免苟活之外,全市慘遭屠殺滅城。梅爾夫從此一蹶不振,在風沙中荒廢頹敝的清真寺、宮殿與城牆,充滿了無處話淒涼的悲戚。
我迷戀大馬士革的陳跡過往,而巷弄內茶館的說書人對於大馬士革的一切,更是如數家珍:使徒保羅歸信的教會、抗擊十字軍的英雄薩拉丁、暗中活躍潛伏的愛德華‧勞倫斯、徘徊在大市集的幽靈……,每個角落都有專屬的故事,每個轉角都能與歷史久別重逢。不過,大馬士革實在是太大了,稍不留意,就很容易迷失在茫茫人海,尋不回自己。
所以,我同意先知的看法,薩那有梅爾夫的清虛、大馬士革的豐厚,卻没有他們的寒愴或自大。薩那古城繁榮,卻少見喧譁爭鬧。來到薩那,你會發現時間不再奢侈,一壺涼茶、一袋水煙,就能消磨一下午的慵懶。
薩那,的確是天堂中的天堂。
打從一九六○年代開始,薩那就是葉門紙鈔貫穿時空的主題,唯一改變的,是不同的觀看角度。如果將它們一字排開,我覺得與歌川廣重的浮世繪《江戶百景》有異曲同工之妙,從鷹眼俯視、漫步觀望到格放特寫,每個視角都顯示葉門人對薩那的愛始終不移。我特別喜歡一九七一年二十里亞爾與九三年一百里亞爾的空中鳥瞰,全智全能的造物者視角,將畫面情境提昇到《一千零一夜》的神話層次,畢竟根據天方夜譚的文字轉述,阿拉丁與辛巴達,都曾造訪過這座美麗的城市。
時間來到二○一一年,第三次造訪葉門。不過這一次,是追隨著被偉大探險家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譽為「最後一位浪漫主義時代旅行家」的芙瑞雅‧史塔克(Freya Stark)的《阿拉伯南方之門》(The Southern Gates of Arabia)的故事,深入哈德拉毛(Hadhramaut)的神祕荒漠,也就是哈第告訴我發生許多超自然事件的阿拉伯沙地。拜科技文明所賜,從海岸線拉進沙漠只需要十四小時的車程,就當暮光將近之時,我看見地平線另一頭垂直與水平線所構成的建築線條,我知道,希巴姆(Shibam)近了。
對於現代人來說,希巴姆這個名字很陌生,聽起來像是某種不好吃的巧克力品牌。實際上這座千年古城,一九八二年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劃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名單,甚至出現在信用卡的電視廣告上。希巴姆的建築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是因為每棟高樓都以參天之勢拔地而起,而且不止一棟,而是整座城市。
早在中世紀之時,哈德拉毛沙漠的住民就用混漿混入磨碎的雜草,充分攪拌過後製作成磚頭的形狀,然後放在太陽下曬乾。最後的作品就是堅硬無比的長方泥磚。接下來的方式就和我們砌磚牆蓋房子相似,需要的只是一層層向上疊加。通常一棟大樓平均有七至十層樓的高度,建築物的外牆還會用石灰塗飾,除了美觀之外,防蟲也是主要功能。住戶大都是姓氏相同的親族,哈第的家族就在其中一棟。
如果看過薩那建築洛可可式的花邊飾帶,就會覺得希巴姆的風格太樸素簡單。隔天,我花了一下午的時間,找到了哈第所屬的哈斯曼家族,長老親切地招待我到客廳坐坐,哈德拉毛人似乎也不太在意房屋的內部裝飾,除了窗櫺和門框是雕花木架之外,室內空間極簡素淨。如果瑞士建築大師柯比意在現場,一定對希巴姆讚不絕口。後來我才了解,無論是建築形式或居家風格,都和伊斯蘭宗派與民族性格有關,不同的性別、不同的社會階層,分配到的是不同的室內空間,而觸目所及的一切都要力求樸質。
「我想,先知也要我們這麼做。」至少哈第的叔父是這樣告訴我的。
許多在海外工作的阿拉伯裔勞工,百分之九十都來自葉門,尤其哈德拉毛沙漠地區,這裡的荒涼雖然帶有不尋常的美感,但想在這片不毛之地維持生計是一件艱辛的事。哈第所屬的哈斯曼家族,有七成的男子都遠赴海外打工:在新加坡的餐廳、在印度洋的散裝貨輪、在大興土木的阿布達比、在沙烏地的鑽井油田……每個角落都可以看見葉門人辛勤揮汗的身影,他們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弱勢的一群。
向晚時分,我登上希巴姆古城對面的山頭,這是紙鈔上的取景角度,拍攝位置最好的所在地,早就被歐洲觀光客的腳架霸佔,所有人都來爭睹魔幻時光。當太陽接近西方的地平線時,沸騰的熱度迅速下降,西風在燠熱中夾帶些許涼意,相機快門在四周的感嘆聲中此起彼落。這座被譽為「沙漠中的曼哈頓」的古城,亮褐色外牆在塞尚色調的陽光下轉成金黃,水平與垂直線條構成的立面、銳角,在陰影下更加強烈,遠方傳來少年們踢足球的吆喝呼聲,街口破爛的卡車、廢棄大樓的斑駁殘跡、無人看管的羊群,讓希巴姆遙不可及的絕美,適度地回到人間,這是可以接受的衰敗,人人心知肚明,是看破卻不說破的祕密。
當最後一道餘暉從山頭褪去,天空從粉紅、酒紅到深紫,古城稀疏的燈火意興闌珊地逐一點亮,所有可辨認的形狀逐漸消融在暮色之中。
「我真想看見這樣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與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那時,我才可以對正在逝去的瞬間說:『請你為我停留片刻吧!你是如此的美!』我的浮生的痕跡才不致在永劫中消褪—我現在就彷彿已預感,屆時我徹底享受著那瞬間。」歌德在《浮世德》中寫下了如此的感慨,在這一瞬間,我明白了浮世德的心情。
摘自《鈔寫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