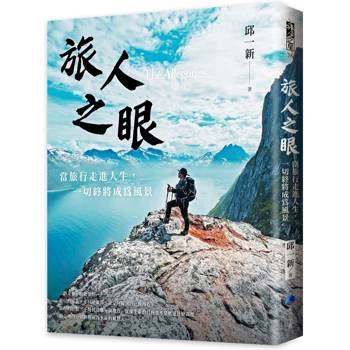【前言】
從旅人之眼到旅人之心
換一種看法,風景就會不一樣
之1、「浪子」回頭說的故事
猶記得二十多年前訪聖彼得堡,在冬宮博物館看到一張名畫《浪子回頭》,說是十七世紀荷蘭畫家林布蘭特作品,一群人駐足圍觀,甚有動容流淚。
此畫取材自《聖經•路加福音》中耶穌的一個比喻:說浪子將父親分給他的家產揮霍一空,潦倒他鄉,不得不返家投靠父兄。父親不計前嫌以「失而復得」心情擁抱浪子回家,長兄不以為然(或許在想,家法伺候?)——顯然,耶穌用「一父二子」的比喻,來說明上帝的慈愛,天父的家永遠歡迎迷途羔羊。
撇開神學意義,浪子回頭的故事引起我深思,或許他窮困潦倒,但真的是一事無成嗎?
如德國俗諺「遠行者必有故事可講」,我對這個沒有說盡的故事後面的發展充滿想像,沒有說出來的,有時候比說出來的更引人入勝,所以,這個故事兩千年之後仍保持著生根發芽的潛力,如同《天方夜譚》在一千零一夜之後,仍有許多夜晚等待訴說。
當某個夜晚降臨,父兄與家人圍坐火塘,會不會想要聽聽浪子在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外面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從某個角度,浪子外表上可能沒什麼變化,可在心智和歷練上已經不是大家原先認識的那個人了,旅行改變了他,讓他眼界大開,有時不免奇想,他會像格列佛那般返家後行止怪異,無法與人相處嗎?
當親人聆聽浪子的經歷,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有主題、有動機卻似是「漫無目的」,如同本書章節含括國內外許多地方,呈現一種零碎感,卻是生命的真實本質,絕不會像旅遊團行程那般井然有序、按表操課,而是彰顯美國作家保羅•索魯所言,「旅人不知該往哪裡去(因為那不重要),遊客不知自己去過哪裡」。
我關注的是,浪子的爐邊談話會不會調動親友的情緒、牽動他們的心呢?聽故事的年輕一代,會不會產生嚮往,成為另一位浪子呢?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再來,浪子會像父兄一樣固守家鄉?或者再次出發呢?
而父兄會不會後悔,沒有像浪子一樣出去看看這個世界呢?父兄從懂事起,就可以想像一輩子的樣子,日復一日,終老於家鄉。
父兄可能忘了每天閱讀的聖經,其實是一部充滿「移動」故事的典籍,從舊約亞伯拉罕告別烏爾、雅各遠走哈蘭、約瑟被賣到埃及、摩西出埃及,到新約耶穌和十二使徒、保羅四處傳福音。乃至今日,傳道人在世界各地不停地移動,例如馬雅各醫師、馬偕牧師來台,創造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旅行故事」。
我亦發現,聖經中的「移動」都是有意義的,都是為了創造一個更好的自我而產生的需要,所以,重點不是去了哪裡,而是去了那裡對他產生了什麼意義。移動,成為人生命運的觸發,就像「浪子的出走」,不僅象徵著心靈的覺醒和勇氣,也解放了人的保守思想和觀念,人類文明就這樣走出來了。
從某個意義,本書就像一位歸來的「浪子」,用文字敘述三十年來行走世界的觀察,每一次旅行都顯示,「移動」過程比抵達更能帶來啟示——或謂之「旅行之道」。這些旅途事件,經過歲月刨光、磨亮,宛若繁星熠熠生輝留存記憶裡,難免希冀用文學來捕捉那些旅途的靈光,但,書寫之際,記憶彷彿探照燈般,將過去的一切一幕幕地打撈出來,發現歲月不過是一連串過去的事件匯集而成,就像馬奎斯所言,「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麼,而是你記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銘記的。」又或者,瓊拜雅唱的,歲月讓記憶變成「鑽石與鐵鏽」。
我相信,喜歡聽故事的人,最終也會出發,尋求自己的故事,成為另一位「浪子」。嗯,就像我兒。
之2、踏上持續一生的重塑自我旅程
在我的第四次希臘之旅,遇到一位智者——drive-guide尼古拉斯。大約是滿肚子學問令他大腹便便,沒走幾步路就滿頭大汗,往往在車裡把景點簡明扼要說了,抵達就找家咖啡店坐下來,放我這隻台灣水牛自行吃草去了。我無所謂,我在乎的是,他的觀點(如何觀看),如果沒有尼古拉斯,我只是個tourist,只能看到指南描述的風景,但我想進入希臘人和諸神的世界,了解他們在想什麼。
記得前往德爾菲,尼古拉斯在車上三言兩語就把此地阿波羅神殿的歷史交代了,倒是「德爾菲神諭」提了不少。說希臘各城邦會派遣名為「Theorie」的代表團,到這裡向阿波羅請示神諭,希望能預知未來吉凶,只是經過女祭司傳達的神諭往往模稜兩可,代表團必須細心觀察、反覆揣測、思辨——這個過程演變成「Theoreo」一字,意思是,「用腦袋(思考)看見」,從中發展出一套對世界的解釋方法,即拉丁文Theoria,於是產生了英文Theory(理論、學說)這個字。
尼古拉斯還說,如果只是走馬看花,那就是「Blepo」,意思是「用肉眼看見」。這個說法,讓我想起第一次來希臘就是如此觀看,只覺得頂著大太陽,到處看「石頭」,有什麼好看呢?
後來有了一些希臘神話認識,觀看那些雕像和廢墟,感受就不一樣了,就像尼古拉斯提到阿波羅神殿入口處有三句箴言:「認識自我」、「妄立誓則禍近」、「凡事勿過度」。第一句常被引用,按傳統闡釋,就是勸人要有自知之明,只是尼古拉斯的理解更貼切,就是「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才能過好日子,不然就會得罪某位神祉,惹禍上身,與基督教的「認識上帝」概念大異其趣。
尼古拉斯引用一則希臘神話,詮釋自己的見解:話說亞特拉斯得罪了天神宙斯,被懲罰扛著地球,還跟他說如果地球掉落了,人類就滅亡了。因著道德感和成就感,亞特拉斯咬緊牙根扛住地球,直到有天赫丘力士來找他幫忙摘取金蘋果,願意替他扛幾天。沒想到亞特拉斯取回金蘋果、嘗到自由滋味後,推託要幫忙送回去交差,赫丘力士一聽便知他想乘機開脫,心生一計請他再扛一下,說要找片墊肩。就在雙方換手之際,一個不小心,地球沒接好,赫然發現地球會自己懸浮,才驚覺被宙斯騙了,竟然傻到以為地球沒有他扛著就會墜毀,於是兩人各奔前程而去。可亞特拉斯沒有「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認識自我),最終受到詛咒,變成北非的亞特拉斯山。
尼古拉斯還提到,希臘文中還有一種觀看方式,Eido,意思是「用心看」,他沒有多做解釋,我也忘了提問,直到多年後才體會。
我喜歡這則尼古拉斯版的希臘神話,忽然有所領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印證方式就是,從辦公室Escape許多天,再返回崗位,就會發現,地球照樣轉,公司一切如常。
讀書和旅行,一直是我看見遠方的一種方式。當我回望昔日旅行,聆聽記憶的回音,寫下本書的文字,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許多無關旅行見聞的個人感受,只能對讀者表示遺憾;同時我也發現我的天真、無知、不安、膽怯和恐懼,讓旅途更加戲劇化。與其說對流逝年華的重新發現,不如說是踏上持續一生的重塑自我旅程,重新書寫「何以成為一位旅人」的意義,所以,這也是一本關於發掘自我的半自傳式旅行故事集,呼應了保羅•索魯的至理名言,「旅行寫作是自傳的次要形式」。
之3、本書是作者觀看世界的方式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什麼時候會改變你的旅行方向、你的價值觀、你的一生。
拜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書中一段話——「唯一的真正旅行,唯一的青春之浴,不是去觀賞新的景物,而是獲得新的目光」,令我豁然了悟。旅行的奧義,不在於尋找新風景,而在於取得新的目光,將經驗折射成看世界的新觀點,即我謂「旅人之眼」,從路上獲得啟示和領悟。
試舉一例。
近年常走淡蘭古道群,有次行經虎豹潭,見一排混凝土石羅列溪水中,形成梳子壩,過溪時跳著方塊石便可走到對岸,類似「石碇」功能,在淡蘭古道過溪澗甚為常見,上面若覆蓋木板石板,不就是多孔橋的雛型?
附近有處灣潭,舊稱「跳石碇」,可以想見先民在此跳石過河情景,如果沒有石碇,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這句歇後語可是在這般情景下產生?
淡蘭古道的跳石碇,讓我想起某年春節在京都鴨川跳「浮石」(日本名稱),只是那些石碇更有趣些,除了方塊石,也有龜狀石,還有鳥形石——稱為「千鳥石」,何故?
原來祇園先斗町有條酒吧街,店家會懸掛「千鳥」(ちどり,Chidori)紋繪燈籠,隱喻喝醉時會像千鳥走路般晃來晃去,稱為「千鳥步」,因此被借用來形容跳浮石的步伐。
鴨川跳浮石就這樣讓我取得「新的目光」,得以重新回望我們的島,取得某種連結——請見本書〈他山之石〉一文,就不贅敘了。
上述觀看方式,猜想即尼古拉斯所謂的Theoreo(用思考觀看),也是本書指涉的主要觀看,包括兩方面:
一,知識上的觀看:若用知識的眼光,去理解風景,去經驗他人的文化體系,即便相同的風景和事物,也會發現與以前的理解不一樣了。
世界上已經沒有「空白之地」了,但是,個人的知識追求,一定有其空白之地、黑暗之地,所以,這種觀看,會讓我們走得更遠更深,擴大了知識邊界。
二,認知的改變:思維和心態的改變,往往會促成一個地方的「再發現」;易言之,換一種看法,風景就會不一樣。
如果說「風景」是一種意義的載體,本書每一則旅行故事涉及的旅行觀看,就是一種「意義的提取」。
之4、來自路上的啟示
我曾在職場上狠狠跌落,就像咖啡杯摔到地上破裂了,那時候我開始學習禱告,祈禱有一份安家活口的工作,祈禱有「行過幽谷」的勇氣和智慧;幸運的是,藉由閱讀,我發現日子變得容易多了,讀書之餘,也整理以前的旅行筆記,無意中翻到某次日光之行,順道拜訪了「人間國寶」陶藝大師濱田庄司(一八九四–一九七八)位於櫪木縣益子町的住家工坊(今為「濱田庄司記念益子参考館」),蒙其衣缽繼承人濱田晉作接待,解說「益子燒」特色,可旅行的真諦不在此。
無意間發現桌上擺放一只正在修復的舊茶碗,說是父親作品,再細察,碗中帶有幾條裂痕般金色脈絡,呈現某種侘寂美感,才知曉是日本陶藝的傳統修復方式——「金繼」(Kintsugi),或稱「金繕」(Kintsukuroi)。
所謂金繼,使用麥漆黏合碎片,或填補縫隙,再撒上金粉、銀粉或金屬粉末裝飾,為物品增添獨特而美麗的痕跡。按濱田晉作說法,茶碗是父親生前使用,有其意義,修復不僅是惜物,也是讓破損重生,而那幾條金色脈絡就是一種無常之美的象徵,顯示人生的坦然接受變化。
金繼之美,就隱藏在修補之中。如今讀來,有了不同啟發,我深切領悟到,自己的裂縫、傷痕,也可以成為某種金繼之美,讓我成為神的器皿,而職場跌落就成為一種「偽裝的祝福」(blessing in disguise)。
「哀痛有時,跳舞有時」(引自《聖經•傳道書》)。這就是人生。沒什麼好抱怨的。
彷彿我的禱告獲得回應似的,就在行過幽谷最深處時,手機響了,有赫斯特媒體邀請我擔任品牌顧問,有中興大學和南華大學邀請我授課,還有更奇妙的來電:
「我是吳寶春啦,我想邀請邱大哥到公司幫忙……」
他們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透過奇妙的金繼技藝,讓我這只破舊的咖啡杯,得以繼續在世界各地喝著美好的咖啡,在家裡書寫一個時代、我的旅行故事,然後領悟到,尼古拉斯所謂的Eido,可是揭示風景與觀看者之間「關係」的一種觀看方式?就像《小王子》裡玫瑰花和小王子之間的「關係」,用眼睛是看不見的,唯有用心看才看得見。
這個認知,從旅人之眼到「旅人之心」,將我的旅行帶往更美好的境界,最終將知識視野提升到心靈視野。
之5、認真老去
我汲汲於職場,一轉眼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十年已矣,兩鬢飛霜,齒搖髮禿,「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不免興起陶淵明「不如歸去」之念。
總之,二○二四年十一月底,我毅然從吳寶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職位上退下來。
在此借用企業思想家韓第《第二曲線:社會再造的新思惟》,來解釋我對退休生活的想法。韓第主張個人或企業都應該在第一條曲線尚未走下坡前,為自己開創第二曲線,簡言之,就是大膽改變、轉換路線,過去我都是應用在職場,例如主編TVBS周刊,同時又創辦《食尚玩家》、《女人我最大》和《健康兩點靈》,如今卻想應用在個人生涯上,把「退而不休」的生活視為人生的「第二曲線」,想要在健康走下坡前啟動第二曲線,或者說,在攸關自己的餘生,投入更多時間,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讓第二曲線成為一條「夢想曲線」,尤其是那些令自己開心、令生命有意義的事情,例如讀書和旅行,還有書寫。本書的寫作就是我「認真老去」的一個開始。
最後,請容我引用《lonely planet 》(孤獨星球)扉頁警語,「Things change–prices go up, schedules change, good places go bad and bad places go bankrupt–nothing stays the same.」作為本書「卸責」之言——的確,一切都在變化之中,許多景物都在消失之中,隨著世事變化無常,物價上升,行程改變,好地方變壞,壞地方每況愈下,沒有事情是不會改變的。不變的是,旅人的倔強身影與書寫,使自己在混濁之世保持清醒。
從旅人之眼到旅人之心
換一種看法,風景就會不一樣
之1、「浪子」回頭說的故事
猶記得二十多年前訪聖彼得堡,在冬宮博物館看到一張名畫《浪子回頭》,說是十七世紀荷蘭畫家林布蘭特作品,一群人駐足圍觀,甚有動容流淚。
此畫取材自《聖經•路加福音》中耶穌的一個比喻:說浪子將父親分給他的家產揮霍一空,潦倒他鄉,不得不返家投靠父兄。父親不計前嫌以「失而復得」心情擁抱浪子回家,長兄不以為然(或許在想,家法伺候?)——顯然,耶穌用「一父二子」的比喻,來說明上帝的慈愛,天父的家永遠歡迎迷途羔羊。
撇開神學意義,浪子回頭的故事引起我深思,或許他窮困潦倒,但真的是一事無成嗎?
如德國俗諺「遠行者必有故事可講」,我對這個沒有說盡的故事後面的發展充滿想像,沒有說出來的,有時候比說出來的更引人入勝,所以,這個故事兩千年之後仍保持著生根發芽的潛力,如同《天方夜譚》在一千零一夜之後,仍有許多夜晚等待訴說。
當某個夜晚降臨,父兄與家人圍坐火塘,會不會想要聽聽浪子在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外面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從某個角度,浪子外表上可能沒什麼變化,可在心智和歷練上已經不是大家原先認識的那個人了,旅行改變了他,讓他眼界大開,有時不免奇想,他會像格列佛那般返家後行止怪異,無法與人相處嗎?
當親人聆聽浪子的經歷,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有主題、有動機卻似是「漫無目的」,如同本書章節含括國內外許多地方,呈現一種零碎感,卻是生命的真實本質,絕不會像旅遊團行程那般井然有序、按表操課,而是彰顯美國作家保羅•索魯所言,「旅人不知該往哪裡去(因為那不重要),遊客不知自己去過哪裡」。
我關注的是,浪子的爐邊談話會不會調動親友的情緒、牽動他們的心呢?聽故事的年輕一代,會不會產生嚮往,成為另一位浪子呢?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再來,浪子會像父兄一樣固守家鄉?或者再次出發呢?
而父兄會不會後悔,沒有像浪子一樣出去看看這個世界呢?父兄從懂事起,就可以想像一輩子的樣子,日復一日,終老於家鄉。
父兄可能忘了每天閱讀的聖經,其實是一部充滿「移動」故事的典籍,從舊約亞伯拉罕告別烏爾、雅各遠走哈蘭、約瑟被賣到埃及、摩西出埃及,到新約耶穌和十二使徒、保羅四處傳福音。乃至今日,傳道人在世界各地不停地移動,例如馬雅各醫師、馬偕牧師來台,創造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旅行故事」。
我亦發現,聖經中的「移動」都是有意義的,都是為了創造一個更好的自我而產生的需要,所以,重點不是去了哪裡,而是去了那裡對他產生了什麼意義。移動,成為人生命運的觸發,就像「浪子的出走」,不僅象徵著心靈的覺醒和勇氣,也解放了人的保守思想和觀念,人類文明就這樣走出來了。
從某個意義,本書就像一位歸來的「浪子」,用文字敘述三十年來行走世界的觀察,每一次旅行都顯示,「移動」過程比抵達更能帶來啟示——或謂之「旅行之道」。這些旅途事件,經過歲月刨光、磨亮,宛若繁星熠熠生輝留存記憶裡,難免希冀用文學來捕捉那些旅途的靈光,但,書寫之際,記憶彷彿探照燈般,將過去的一切一幕幕地打撈出來,發現歲月不過是一連串過去的事件匯集而成,就像馬奎斯所言,「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麼,而是你記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銘記的。」又或者,瓊拜雅唱的,歲月讓記憶變成「鑽石與鐵鏽」。
我相信,喜歡聽故事的人,最終也會出發,尋求自己的故事,成為另一位「浪子」。嗯,就像我兒。
之2、踏上持續一生的重塑自我旅程
在我的第四次希臘之旅,遇到一位智者——drive-guide尼古拉斯。大約是滿肚子學問令他大腹便便,沒走幾步路就滿頭大汗,往往在車裡把景點簡明扼要說了,抵達就找家咖啡店坐下來,放我這隻台灣水牛自行吃草去了。我無所謂,我在乎的是,他的觀點(如何觀看),如果沒有尼古拉斯,我只是個tourist,只能看到指南描述的風景,但我想進入希臘人和諸神的世界,了解他們在想什麼。
記得前往德爾菲,尼古拉斯在車上三言兩語就把此地阿波羅神殿的歷史交代了,倒是「德爾菲神諭」提了不少。說希臘各城邦會派遣名為「Theorie」的代表團,到這裡向阿波羅請示神諭,希望能預知未來吉凶,只是經過女祭司傳達的神諭往往模稜兩可,代表團必須細心觀察、反覆揣測、思辨——這個過程演變成「Theoreo」一字,意思是,「用腦袋(思考)看見」,從中發展出一套對世界的解釋方法,即拉丁文Theoria,於是產生了英文Theory(理論、學說)這個字。
尼古拉斯還說,如果只是走馬看花,那就是「Blepo」,意思是「用肉眼看見」。這個說法,讓我想起第一次來希臘就是如此觀看,只覺得頂著大太陽,到處看「石頭」,有什麼好看呢?
後來有了一些希臘神話認識,觀看那些雕像和廢墟,感受就不一樣了,就像尼古拉斯提到阿波羅神殿入口處有三句箴言:「認識自我」、「妄立誓則禍近」、「凡事勿過度」。第一句常被引用,按傳統闡釋,就是勸人要有自知之明,只是尼古拉斯的理解更貼切,就是「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才能過好日子,不然就會得罪某位神祉,惹禍上身,與基督教的「認識上帝」概念大異其趣。
尼古拉斯引用一則希臘神話,詮釋自己的見解:話說亞特拉斯得罪了天神宙斯,被懲罰扛著地球,還跟他說如果地球掉落了,人類就滅亡了。因著道德感和成就感,亞特拉斯咬緊牙根扛住地球,直到有天赫丘力士來找他幫忙摘取金蘋果,願意替他扛幾天。沒想到亞特拉斯取回金蘋果、嘗到自由滋味後,推託要幫忙送回去交差,赫丘力士一聽便知他想乘機開脫,心生一計請他再扛一下,說要找片墊肩。就在雙方換手之際,一個不小心,地球沒接好,赫然發現地球會自己懸浮,才驚覺被宙斯騙了,竟然傻到以為地球沒有他扛著就會墜毀,於是兩人各奔前程而去。可亞特拉斯沒有「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認識自我),最終受到詛咒,變成北非的亞特拉斯山。
尼古拉斯還提到,希臘文中還有一種觀看方式,Eido,意思是「用心看」,他沒有多做解釋,我也忘了提問,直到多年後才體會。
我喜歡這則尼古拉斯版的希臘神話,忽然有所領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印證方式就是,從辦公室Escape許多天,再返回崗位,就會發現,地球照樣轉,公司一切如常。
讀書和旅行,一直是我看見遠方的一種方式。當我回望昔日旅行,聆聽記憶的回音,寫下本書的文字,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許多無關旅行見聞的個人感受,只能對讀者表示遺憾;同時我也發現我的天真、無知、不安、膽怯和恐懼,讓旅途更加戲劇化。與其說對流逝年華的重新發現,不如說是踏上持續一生的重塑自我旅程,重新書寫「何以成為一位旅人」的意義,所以,這也是一本關於發掘自我的半自傳式旅行故事集,呼應了保羅•索魯的至理名言,「旅行寫作是自傳的次要形式」。
之3、本書是作者觀看世界的方式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什麼時候會改變你的旅行方向、你的價值觀、你的一生。
拜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書中一段話——「唯一的真正旅行,唯一的青春之浴,不是去觀賞新的景物,而是獲得新的目光」,令我豁然了悟。旅行的奧義,不在於尋找新風景,而在於取得新的目光,將經驗折射成看世界的新觀點,即我謂「旅人之眼」,從路上獲得啟示和領悟。
試舉一例。
近年常走淡蘭古道群,有次行經虎豹潭,見一排混凝土石羅列溪水中,形成梳子壩,過溪時跳著方塊石便可走到對岸,類似「石碇」功能,在淡蘭古道過溪澗甚為常見,上面若覆蓋木板石板,不就是多孔橋的雛型?
附近有處灣潭,舊稱「跳石碇」,可以想見先民在此跳石過河情景,如果沒有石碇,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這句歇後語可是在這般情景下產生?
淡蘭古道的跳石碇,讓我想起某年春節在京都鴨川跳「浮石」(日本名稱),只是那些石碇更有趣些,除了方塊石,也有龜狀石,還有鳥形石——稱為「千鳥石」,何故?
原來祇園先斗町有條酒吧街,店家會懸掛「千鳥」(ちどり,Chidori)紋繪燈籠,隱喻喝醉時會像千鳥走路般晃來晃去,稱為「千鳥步」,因此被借用來形容跳浮石的步伐。
鴨川跳浮石就這樣讓我取得「新的目光」,得以重新回望我們的島,取得某種連結——請見本書〈他山之石〉一文,就不贅敘了。
上述觀看方式,猜想即尼古拉斯所謂的Theoreo(用思考觀看),也是本書指涉的主要觀看,包括兩方面:
一,知識上的觀看:若用知識的眼光,去理解風景,去經驗他人的文化體系,即便相同的風景和事物,也會發現與以前的理解不一樣了。
世界上已經沒有「空白之地」了,但是,個人的知識追求,一定有其空白之地、黑暗之地,所以,這種觀看,會讓我們走得更遠更深,擴大了知識邊界。
二,認知的改變:思維和心態的改變,往往會促成一個地方的「再發現」;易言之,換一種看法,風景就會不一樣。
如果說「風景」是一種意義的載體,本書每一則旅行故事涉及的旅行觀看,就是一種「意義的提取」。
之4、來自路上的啟示
我曾在職場上狠狠跌落,就像咖啡杯摔到地上破裂了,那時候我開始學習禱告,祈禱有一份安家活口的工作,祈禱有「行過幽谷」的勇氣和智慧;幸運的是,藉由閱讀,我發現日子變得容易多了,讀書之餘,也整理以前的旅行筆記,無意中翻到某次日光之行,順道拜訪了「人間國寶」陶藝大師濱田庄司(一八九四–一九七八)位於櫪木縣益子町的住家工坊(今為「濱田庄司記念益子参考館」),蒙其衣缽繼承人濱田晉作接待,解說「益子燒」特色,可旅行的真諦不在此。
無意間發現桌上擺放一只正在修復的舊茶碗,說是父親作品,再細察,碗中帶有幾條裂痕般金色脈絡,呈現某種侘寂美感,才知曉是日本陶藝的傳統修復方式——「金繼」(Kintsugi),或稱「金繕」(Kintsukuroi)。
所謂金繼,使用麥漆黏合碎片,或填補縫隙,再撒上金粉、銀粉或金屬粉末裝飾,為物品增添獨特而美麗的痕跡。按濱田晉作說法,茶碗是父親生前使用,有其意義,修復不僅是惜物,也是讓破損重生,而那幾條金色脈絡就是一種無常之美的象徵,顯示人生的坦然接受變化。
金繼之美,就隱藏在修補之中。如今讀來,有了不同啟發,我深切領悟到,自己的裂縫、傷痕,也可以成為某種金繼之美,讓我成為神的器皿,而職場跌落就成為一種「偽裝的祝福」(blessing in disguise)。
「哀痛有時,跳舞有時」(引自《聖經•傳道書》)。這就是人生。沒什麼好抱怨的。
彷彿我的禱告獲得回應似的,就在行過幽谷最深處時,手機響了,有赫斯特媒體邀請我擔任品牌顧問,有中興大學和南華大學邀請我授課,還有更奇妙的來電:
「我是吳寶春啦,我想邀請邱大哥到公司幫忙……」
他們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透過奇妙的金繼技藝,讓我這只破舊的咖啡杯,得以繼續在世界各地喝著美好的咖啡,在家裡書寫一個時代、我的旅行故事,然後領悟到,尼古拉斯所謂的Eido,可是揭示風景與觀看者之間「關係」的一種觀看方式?就像《小王子》裡玫瑰花和小王子之間的「關係」,用眼睛是看不見的,唯有用心看才看得見。
這個認知,從旅人之眼到「旅人之心」,將我的旅行帶往更美好的境界,最終將知識視野提升到心靈視野。
之5、認真老去
我汲汲於職場,一轉眼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十年已矣,兩鬢飛霜,齒搖髮禿,「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不免興起陶淵明「不如歸去」之念。
總之,二○二四年十一月底,我毅然從吳寶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職位上退下來。
在此借用企業思想家韓第《第二曲線:社會再造的新思惟》,來解釋我對退休生活的想法。韓第主張個人或企業都應該在第一條曲線尚未走下坡前,為自己開創第二曲線,簡言之,就是大膽改變、轉換路線,過去我都是應用在職場,例如主編TVBS周刊,同時又創辦《食尚玩家》、《女人我最大》和《健康兩點靈》,如今卻想應用在個人生涯上,把「退而不休」的生活視為人生的「第二曲線」,想要在健康走下坡前啟動第二曲線,或者說,在攸關自己的餘生,投入更多時間,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讓第二曲線成為一條「夢想曲線」,尤其是那些令自己開心、令生命有意義的事情,例如讀書和旅行,還有書寫。本書的寫作就是我「認真老去」的一個開始。
最後,請容我引用《lonely planet 》(孤獨星球)扉頁警語,「Things change–prices go up, schedules change, good places go bad and bad places go bankrupt–nothing stays the same.」作為本書「卸責」之言——的確,一切都在變化之中,許多景物都在消失之中,隨著世事變化無常,物價上升,行程改變,好地方變壞,壞地方每況愈下,沒有事情是不會改變的。不變的是,旅人的倔強身影與書寫,使自己在混濁之世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