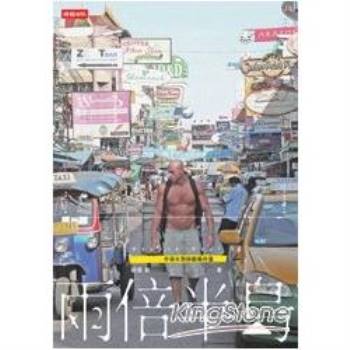迷你首都的落日與啤酒
我喜歡永珍,並且認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這樣的首都。
LP城市簡介文末提到:「這座城市雖然沒有龍坡邦所展現的那分典雅美麗,但日落時在河邊品嘗一瓶寮國啤酒,很快的你就會喜歡上這裡的。」一出現「雖然」二字,已是為當地的某些缺陷心虛了,後面再補上什麼都是強說詞。反之,若單單只靠「日落、河邊、寮國啤酒」就能讓人愛上的城市,肯定寥寥無幾。
遊客在永珍只有第一天需要地圖,後來只靠幾條街就足以建構每天主要的活動範圍。永珍首先打破我萬花筒般城市紋理的首都印象,既然這個深藏內陸的國家我一無所知,那麼「認知」也就得暫時放下。
城中最寬的馬路通往凱旋門,來回走過一次就不會再去。另兩條與湄公河平行,其間的小巷道開滿了餐廳、旅館、旅行社,旅客大多在這裡吃住玩樂(台北至今沒有這種專屬旅行者聚集的區域)。就這樣,永珍搞不好已經比你過年回外婆家的那個小鎮都還小,也許永珍不小,是端出來給外國遊客的永珍就是這麼小,概念的小。
迷你的首都,待了六天五夜,換過一次旅館,認識一個寮國朋友,愛上一條河流,看了五次落日,喝了N瓶寮國啤酒。
我不曾認識、也不曾去過在國界上的首都,永珍以特異的姿態站立在世界其中一條邊界上,臨著河,望向另個國家。這地理組成條件實在奇特且誘人,但若不說對岸就是泰國,風景則平凡無異。並非緊貼泰國有什麼奇觀或好處,而是一個城市因此有了一處不受打擾的概念邊陲,沒有穿過街廓的道路與欄杆高牆,彷彿一片大落地窗隔絕了噪音,冷風吹不透卻賞盡了美景。以政治空間的配比來說,既邊緣又中心,有種我家客廳就增建在別人家陽台外的錯覺,隨時窺視著某些羨慕與忌妒。
大街上的每一條小巷都通往河畔,讓我想起印度瓦拉納西與恆河,而我也只是逐日望著河的對岸不曾踏上造訪。我們下午四點就會來到河岸,帶著啤酒坐在堤防上。背後禁行車輛的馬路滿是慢跑騎車散步的優閒人們,前方是乾旱的河面,沙洲上偶有吃草的牛群和體力過剩的少年,對岸則是一排矮樹露出幾棟紅屋頂的房子,那已是泰國領土。
長長一兩公里河畔僅有基本的公共建設,看日落的廣場大階梯、運動休閒的公園、充當跑道的柏油路、光禿的水泥鋪面與設施,其實一點也不美不浪漫。但一處沿著河岸的空曠場所,有夕陽、有河流、草地、可以和朋友運動歡笑、可以和親人共度、可以和情人並肩而坐用只有兩人聽得見的音量說話,這些簡單的享樂在這簡單的國度,沒有太多景點的城市釀出沒有雜質的簡單韻味,好像好茶就得用高山泉水,才能沖出更清澈的香氣。
他們說寮國窮、說永珍無聊,到底是心底多麼空虛的人這麼難被填滿?到底是腦袋有多複雜的人感覺這麼麻痺?應是已失去享受﹁簡單﹂的能力。視線右方即是落日的位置,六點太陽沉入湄公河遠方的盡頭,喝完入夜前最後一口啤酒,把鋁罐捏扁,金屬扭擠的聲音與台啤無異,只缺少該被回收的情緒。
我特別喜愛這河畔午後,每天都來,也不為什麼,落日只是個每天上場的演員,不是「非去不可」。此刻就如週末自然醒後還賴在被褥中,十一點的陽光已經照進混亂的房間,就呆滯望著天花板,沒有催促,沒有提醒,沒有接下來。
廣場上的夜市亮燈開始熱絡起來,吃過晚餐的觀光客穿著短褲背心和拖鞋,逛街散步也散心,買件印上我愛寮國的踢恤紀念此行。堤外入夜之後的景色則無垠黑暗,鄰國土地消失,永珍被擠到世界盡頭,河流是海洋也是宇宙。
啤酒入夜後是酒吧裡的暢飲茫茫,是慰藉孤獨的酒後說愁,湄公河是陪伴也是傾聽者,他懂旅行者為何遠行至此,千里迢迢只為落日和啤酒,他明白這些都是藉口又不說破,就算一夜過後就是告別,還是伸出緩緩的台階讓你走下來,說,這是旅行啊。
昭阿努立在河邊的雕像抬起右手揮向泰國氣勢恢弘,而不遠處空地已被施工圍籬圈起,現代化的國際商業中心模擬圖宣示著永珍向錢看的未來,日後這片空曠將慢慢被慾望吞噬,人們不在乎何時落日,昭阿努的雕像將被移到公園裡陰暗的一角,那時永珍已不再需要這單純的景色和不值錢的優閒。過去與未來只供詠嘆,旅行者的資產只限當下,廣場陣列的旗竿高掛社會主義的旗幟,最窮的寮國幸福指數排行全球第二,經過這幾天河畔的流連,我喜歡永珍,我可以了解。(待續)清邁哪好
翻看起清邁照片,發現成像變細膩了、色彩更飽滿了,以為是第二次來清邁眼光變了嗎,才想起來這些相片是用琳達媽的相機拍的。相機是R帶來的,兩人旅行也是從此開始的。
回台後有天下午,我和R在景美的茶店又說起清邁,我問他:「清邁到底是哪裡好?」比起曼谷,R更喜歡清邁。我也很喜歡清邁。我們一致認為清邁是個令人放鬆的城市,但何以泰國到處是標榜「悠閒」的好地方,如南方的海島或泰北的小山城,而清邁卻特別惹人疼愛?
城市都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質感。北京是紅的,東京是透明的,首爾是硬的,曼谷是濕的,新加坡是塑膠的,瓦拉納西則是刺鼻的。若用食物來形容城市,我覺得清邁是戚風蛋糕,雖然蓬鬆,卻是飽滿的、有彈性的。
我認為城市分為兩種,一種如海洋般廣大、密密麻麻編織起來的、讓人無盡探索的,如曼谷或東京。而清邁是另一種,讓旅行者抱在懷裡的、絲絲耳語的、細數家珍的。清楚的護城河圍起了一公里半見方的城,即使城牆不在了,城的形狀依然清楚留下,明白的邊界讓旅行者感到安心,即使如今清邁早已越過城牆往外發展,這古城仍如心臟於此跳動。比起台灣的古都台南,許多古城門雖在,但舊城的邊界則難以察覺,城市仍以一個經濟發展至上的大都會自居。
以塔佩門延伸到帕邢寺的叻差當能路為主幹,再依個人喜好往左右長出自由的路線,寺廟、美食、按摩、咖啡小鋪等,都是徒步就能抵達的簡單明瞭。雖然這是錯覺,清邁遠比起認知的複雜廣大,但錯覺是美麗的,他像一本編輯好的參考書,已整理出摘要重點,不滿足的旅客則可自行深入。但它絕不是一本漫無目標的大字典。
清邁通常不是旅行者到訪泰國的第一個城市,經過曼谷或度假海灘的熱情轟炸,自然能感受到清邁閒散氣氛。也因如此,距離首都十二小時火車、九小時巴士的距離,過濾了對泰國風情只想嚐鮮的人潮,降低了觀光密度。來到清邁的旅客多已對泰國有更多的喜愛與認識,不再迷失於超大型百貨公司或批發商場,因此能更沉澱在安靜的旅行中。住在清邁的泰國朋友J便覺得大型購物中心的逐漸興起對清邁是一種都市化侵略。
悠閒到了底稱為無所事事。清邁悠閒,可以無所事事,而非只能無所事事,清邁的鬆緊是有彈性的。清邁身為舊朝首府依然底蘊豐富,位居泰北起點還擁有廣袤森林,空靈的佛寺與人氣夜市都有,古樸傳統與時髦設計兼具。
多數想「放空」的遊客,並非想完全掏空所有,而是在空虛時必須獲得適度填加,宜人的生活尚須載重偏低的運行。有如一盞黑暗房中的小夜燈,微微照亮了不大的視野,舒適而溫暖,完全的黑暗是將人隔絕於外界的。清邁的悠閒仍然貼近民生世俗,除了密度極高的佛寺,不乏色情酒吧和阻街女郎,街上的按摩院也可能暗藏春色,這些飲食男女都是生活的部分,清邁並未因標榜慢活古城而水清無魚。
如又比起泰國中部相同是古城的素可泰,清邁對外地遊客釋出的善意是更顯而易見,除了古城作為主菜以外還有選擇多樣的甜點來搭配,簡而言之,即是適度的觀光化。即便素可泰的歷史遺跡令人驚嘆,但出了古城到新城便是沒有驚喜的密集街道與樓房,於是遊客通常不出兩三日就往清邁或曼谷去。
房租飲食物價相對低廉,於是我們說清邁適合生活、長居。許多遊客在清邁住久了,甚至是退休後的永久移居,旅行已是以年月計。生活中安插課程學語文、學按摩、學做菜、學瑜伽,清晰簡單的時間安排讓自己找回在原所在城市已紊亂的生活步調,自己能慢慢的走,無人在後追趕或拉扯。
慢活之城,僅是將生活速度放慢,而非歸零。
清邁地圖在我腦中是簡明扼要的,由東至西也由低漸高,屏河、瓦洛洛傳統市場、觀光夜市、方正古城、尼曼明路流行街、清邁大學、動物園,最後上山至素帖寺又俯瞰溫習了整個城,令人易於掌握的安好境地,簡單而豐盛。
週日下午三點,我和R坐在一家十字路口旁咖啡店的戶外座位,看著周日夜市的商家慢慢將商品攤架搭設完備,突如其來的一場雨又讓大家手忙腳亂。整個下午耗在街角哪兒也沒去,就坐在屋簷下看著夜市從無到有。
這是清邁最大的市集,許多遊客也為了夜市刻意將旅程排在周末。天還沒暗遊客就已漸漸湧入,我們花了二十銖各買了一杯暗紫色的綜合果汁,我高舉果汁請R幫我拍下與熱鬧夜市的合照,此時帕邢寺那端的暗藍天空恰好射出煙火,原來正適逢皇后生日,全國各地都有慶祝活動。照片中人潮蔓延到遠方沒有盡頭,人人燦笑映著點點燈火,清邁彷彿正臨太平盛世。
週一,我和R到塔佩門前的麥當勞吃早餐,在二樓看著又恢復寧靜的廣場,工人們正在拆卸為昨天慶祝活動搭建的臨時舞台。一邊抱怨著速食店又貴又淡的爛咖啡,我們聊著清邁到底哪裡好,然後決定再多留下來一天。(待續)心上的佛寺
我一向不擅長參觀佛寺,信手拈不來歷史,也說不出一口好建築,佛祖哪兒來哪兒去終究是經過了此地,旅行者嘛,我們信仰當下相遇的緣分就好。東南亞的大小佛寺成千上萬,若全自旅遊書上刪去,旅程肯定是要少掉大半。不是不愛看,只是不擅長。
香火正旺的廟可以看看熱鬧,看那些鮮花金箔怎麼誇耀信徒合十的祈禱,看那些重簷壁畫怎麼包容荒野失落的神魂。但傾頹的遺跡就難懂了,像黑白照片在相本裡被遺忘,好久好久都不曾被翻開,顏色被抽掉復古味道頗好,但旁邊主角的名字是誰卻想破頭了也記不得。在意的,還嗅得到當時眷戀的餘味;若無心,就像上台報告時間不夠了的投影片,匆匆一瞥就趕緊翻到下一張去。我不是你,從未參與過你的過去,你拿當年的過去要我看到什麼呢?榮景如今要從磚瓦灰燼間說起,不談同情不讀書,我們拿什麼來當翻譯?我們只能一人拿一邊耳機聽同一首曲子,耳中聽見相同的旋律,但心底暗自唱著喜歡的歌詞。
素可泰曾是王朝首都、歷史之城,不過這道光芒夾在清邁和曼谷之間奄奄一息,特地到訪的遊客相對的少。我和R行程鬆散不趕時間,就決定到曼谷之前停留幾天,多認識一個泰國城市,並非為了朝聖而來。
我們住在一點觀光氣息都沒有的新城,不過食物好吃消費便宜,一如泰國各地都有的舒服友善。距離十二公里外的舊城,面積與現在清邁古城不相上下,但如今已是被掏空血肉的歷史公園,購買一百銖門票就可以觀賞輝煌城市的殘骨。我和R租了一台機車騎進攤開的地圖裡,寺廟佛塔斷垣殘壁有如電玩遊戲的關卡,一座接著一座拍照蓋章,機車引擎在空曠的園區裡不識相的咆哮,按表操課速度太快,不知為何而看好似索然無味。
幾百年的剩餘就是眼前的人去樓空,既殘酷又冷靜,我忽然想丟棄那些密麻的過去,走進現在眼前這光禿的楚楚可憐裡,無視王朝,不談歷史,反過來為當時的古人導遊起這最新的現場。
旅行若不貪求,只願領略一角心中的美景,沒沒無名微不足道即可。
我們丟下機車來到一座印度教寺廟,青綠平坦的草皮裹住一圈不起眼的石牆,三座高棉風格的佛塔探首其中,我無意入內鑽研建築或宗教,只是徒步繞圈緩緩感受這場所。走了半圈見到主入口,一位大叔坐在長凳上脫了鞋納涼,不遠處的小竹棚擺著販售給遊客的紀念品,小攤子只是他的配件。每天就選一座喜歡的寺,他擺攤如擺陣,風拂綠茵如詩,靜靜的定在此淡泊幽涼之中,說做生意嘛,合則來自有緣分。他沒說上半句話喚我買些什麼,我則悄悄加入他的春風沐浴裡,麻雀婉轉啁啾,三人共享這無爭之時,眼前靜好。古寺尚在也已融入生活片景,不只崇拜。
素可泰古寺何其多,從地圖上挑幾個有緣分的,有如探訪老友好好的聚上一會,在涼蔭處坐下聽聽古寺的聲音,收起急躁的相機、喝口茶敘敘舊,不急著走。若急忙趕場就跟候選人拜票一樣,作勢虛情難得收到心上。
書中神祕的娓娓描述在我腦海建起了想像的模型,我常相信直覺的選擇。趁天黑前我們找尋城外一處山坡上的佛寺,此寺位處荒僻訪客鮮少,我們靠著手機導航一路騎過無人的石徑,泰文的佛寺拼音難以辨讀,一座經過一座我們也一路停停走走,直到見到一道通往上坡的石橋,我們才確定找到了。
所謂石橋,是由石塊碎片堆疊築起的坡道,在陡坡覆蓋上另層緩坡讓人能逆行而上,不如人工水泥階梯的銳利速成,樸拙的石橋從山下就已然沉澱紛亂的心場,有些費勁的上坡則逐步讓身體勞動,是提醒也是儀式。途中可見前人疊起的祈福石堆,石頭只靠輕觸相疊,隨時可因風吹外力就倒塌分離,隨緣謙虛的心願令人珍惜。
百餘公尺山坡上的古寺荒而不廢,巨大的石塑立佛與柱列露天併立,佛像胸口龜裂腦後草葉攀生,背後也已經撐起防止倒塌的混凝土補強結構,沒有華美的雕梁畫棟,我們依然用盡誠心綿長信仰。一組信眾在大佛腳下焚香吟唱誦經,祂靜定的眉眼高高在上看俯瞰著素可泰古城,沉重巨大的存在賜人撫慰的力量,人的血肉軀體此刻顯得虛弱渺小,被捧在佛祖手心之上,不再憂慮惶恐。
一條忠誠的野狗引導我們上山,下山時又走在我們前頭帶路,萬物心靈相通,佛心也願伸手攙扶。
下山騎車離去之前我又回望山端,看那座被時間剩餘的寺廟,凋零殘破到底,信念卻低鳴遠道而來。從過往、從遠方,像流浪者把持的堅定意志,不惜居無定所衣不蔽體,只望自己能對自己說話,只願把寺築在心上。(待續)初戀周安琪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首歌嗎?以前我們住的那個村子,全都是木屋來的,就像這裡,下面就是海,我最愛跟我爸躺在木地板上,一面聽著海浪的聲音,一面聽這首歌。我們村子裡全都是姓周的,叫姓─周─橋─,在檳城很有名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給我取的,叫周─安─琪─。」躺在阿牛背上,左腳穿進水面踩出幾圈漣漪,李心潔在電影《初戀紅豆冰》裡這麼說。
為了寫檳城,我特別翻出電影來看,第二次看,但這些話好像第一次聽。周安琪說的我早知道,但從女主角口中說的,既真實又如夢似幻。電影是假的,但又因為假的原因是電影,所以可以被忽略,於是那又是真的了。旅行時我喜歡用感官揣摩情境,像演戲或彈琴揮手甩頭時閉眼陶醉,而厭惡導覽資訊的填充輸入。周安琪姓周,住在姓周橋。此時周安琪在旁白生活,就不歸類為資訊。
陽光太烈不出門,過了中午卻又下起陣雨,我仍在旅館走廊藤椅上懶散,在臉書上發了訊息:「我在檳城,下午四點,給我個地方去?」第一則回覆就是「周橋,傍晚的周橋最美。」我盯著答案想起一張學妹寄來的明信片,一邊查了網路。有些意外不解,此地我素昧平生,但這提醒又過於中的,既視感的似曾相識。這些在海岸的參差木屋掛了保證,沒有秩序的東西有意思,勢必原味,絕對生猛,生活嚴謹規律的人特別需要看這些風景。是我忘了曾經想去的念頭。
身在喬治市,就往東走就會遇上姓氏橋的其中一座,姓陳、姓林、姓李或混居的雜姓橋,姓周橋最大名氣最響,不用地圖也很容易就能找到。這些有姓氏的橋不是橋,是早期華人移民馬來西亞的聚落,全立柱築屋在檳城沿岸淺海,橋是各戶門前的街巷,同姓的住一起,離岸的另一頭除非搭上舢舨否則沒有出口。房屋就站在塑膠桶串起充當模板的水泥基礎上,房身屋頂多已是鏽蝕的金屬浪板,斜頂穿前插後方向不一,比台灣頂樓違建還有機,拐彎岔路看似死巷又總有捷徑。海味腥臭依舊,浪聲拍打腦海,家的概念像海草,一株株從陸地水平生長的海上村落,飄搖飄搖的,柔軟而堅韌。
「他也不管我就坐在客廳,沒問過就往家裡面拍!」兩個大嬸坐在門前用福建話牢騷抱怨著。週間遊客不多,大嬸們也不是針對我,但我瞬間再怎麼謙虛守秩序,彷彿也成了無地自容的加害者。
二??八年檳城登入文化遺產、二?一?年成為電影場景,雖然書上寫著這裡的居民依然生活如昔,但民宿、餐廳、禮品店開了幾家做起遊客生意,生活不是石頭很難不變。成天往家門口探頭探腦陌生人,不是透明海風吹過鹹鹹的而已,在城市的微血管末端,外來遊客像通過沙漏頸部的沙粒特別顯眼。當胸前掛著相機走進來,我也已是讓周橋「不像以前」的一分子。我非長住於此,變與不變對我來說只是一個下午的時光消遣,我沒有資格抱怨不見你們的往日生活,更愧疚於自己的生硬介入。
走出周橋,在右手邊的茶水攤坐下要了茶冰,大樹刺穿鐵皮屋頂在高處開枝散葉,這裡沒有講究的大理石圓桌,大夥拉著塑膠椅繞著樹幹飲茶好像還是小時候在樹下乘涼談天,對面的朝元宮和攤子旁的泥造金爐包圍了一個小埕是姓周的客廳,四周都是熟悉的福建話,我惦惦聽著閒話家常,像是兒時被父母拉到親戚家串門子,大人聊天小孩插不上嘴,只差現在我不需要對彼此的距離害怕,這是旅行者的陌生豁免權。
我一向是安靜的旅客,獨自低調的走著,偶有風花雪月,鮮少熱血勵志,其實我更希望能披上斗篷隱於無聲無形,像風吹進房間的窗口,看到所有精采的細節,像鬼魂坐在你們之間不被發現,聽盡昨日發生的八卦與瑣事。說說罷了,我能做到的僅是繼續低汙染的安靜走著。
「哥,你畫畫這樣美,為什麼不要拿去參加比賽?美的東西本來就要拿出來的啦!天生麗質難自棄嘛!」肥妹對每天偷偷畫著初戀情人畫像的Botak 說。後來肥妹偷偷寄了一張周安琪的側臉水彩肖像報名了比賽,並且贏得了冠軍。當大家為他的才華稱讚喝采,哥哥知道了卻是安靜的走到騎樓下傷心啜泣,因為初戀情人已經離開了小鎮,一袋幾毛的紅豆冰,也就為了初戀而美麗。
也許,美的東西不一定要拿出來,存放在安心的盒子裡,天生麗質只願給看到的人好好珍惜。(待續)馬來西亞到新加坡兩座橋
中南半島上最南邊的陸地國界,也是最後一個。
其實中南半島在馬來西亞最南端的新山已經終止,新加坡是隔著柔佛海峽的島國。兩座跨國通道像吊襪帶將新加坡掛在歐亞大陸底下。更誇張些形容,新加坡超高的人造密度與現代化發展,與中南半島各國全然異質化,已像顆垂在石灰岩下的透亮水滴,隨時會脫落。
從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跨越邊界對我是重要的,甚於比較兩邊國家的差異。我記述下途中的每次跨越,換車、走路、搭船或過橋,每回都因邊界的存在而必須調整自身姿態,有如道路上的裂縫或凸起,經過時總附帶一瞬震盪,提示著將臨的變異,即便差別只是相似的細微末節,都有個慎重的動作來轉接。
兩天前一抵達馬六甲,就直接在車站買兩天後要到新加坡的車票,問了幾家巴士公司都已客滿,原來新加坡人喜歡到馬六甲度週末,週日正是收假潮。幸好,一家巴士公司還有位置,只是一早十點就得離開。早起一向是我最困難的功課,就算在旅行時也不例外。
離開前到茶室喝了茶、吃了牛油麵包,記得在檳城時也是如此將城市收束打包。兩次來馬六甲,這家隆安茶室我已經光顧了不下十幾次,Sam 也常來,是他介紹給我的。把它當作台北公寓樓下的早餐店,在不變的城市角隅有一樣的味道,即便遊客的熟悉只是短暫,算是利用它營造些許迷幻歸屬。至少相隔一次分離,這是到訪兩次以上城市才有的把戲。
二十二令吉、三個小時就到了邊界,位於新山關口後是通往新加坡的新柔長堤。下車、出境、上車、過橋、下車、入境、上車,兩國的關口都如國際機場般新穎寬敞,一字排開的眾多櫃檯,旅客有如在講究效率的生產輸送帶上,流程明確通關快速,連入境卡都在巴士上就發放填寫。
平均每日有六萬車次往來兩國之間,原是相同國家的兩岸仍然因缺乏而彼此依存著,一公里多的斷裂,南北人車油水,這窄窄的通道日夜不停運輸彌補著。
橋再寬對於國家來說也只是沙漏間細瘦的頸子,星馬之間就這麼兩條通道,是否略嫌窘迫蹩腳?反觀自己的國家四面臨海,與他國的來往只是個小機場,客人出了機艙踏上台灣國土,伸手迎接的是只容兩人並肩通過的空橋,我才想起這是海島的宿命。何況台灣已沿海岸線自築了高牆,沒有道路,更沒有鄰國。
巴士下橋後駛進大雨中的新加坡,公路旁的植物高大濃綠,組屋樓舍色彩過分俗豔,濕淋淋的世界宛如野獸派的熱帶。這雨自啟程時一路沒忘下到了終點,我撐的小黃傘是隨身攜帶的太陽,在山林海島或市街低空發光,一道自北回歸線貫穿南國的軌跡,蒸騰冒著燥熱的濕氣,還以為走過的路都因我已茂密成林。
八年前首次來新加坡,對馬來西亞尚一無所知,為了看到柔佛海峽對岸的馬來西亞,我曾到克蘭芝地鐵站附近一處濕地叢林公園。走到水邊,對岸山坡上疊著紅屋頂的低層建築,一公里多的距離讓新山彷彿隔了描圖紙略感輕飄霧白。手機跳出馬來西亞電訊公司發送的簡訊,歡迎我光臨馬來西亞,當時仍是單色的小小手機螢幕上,就浮現了曾到馬來西亞一遊的證明,只不過是隔海借景。
巴士最後停靠在一處商場大廈旁,熱烈的大雨讓乘客抓著行李手忙腳亂,直到在騎樓底靜定下來,才看見我已處於百分百人造的文明都市中。此處是個華人很少的商場,像是中山北路上的金萬萬,招牌、商品或消費族群,都浮著一層陌生光暈。
把剩下的馬幣換成新幣,撐傘走到附近的地鐵站。
大雨持續,辦公大樓旁的草地修剪齊平,噴泉造景依然盡責定時射出不同高度的向心弧線,我走在排水良好的人行道上,想起泥路上常有的坑疤水窪和木屋前的潺潺流水聲。
站在售票機前,不預期的被轟然陌生偷襲,曾經來過的記憶已完全不剩,所有地名路線方位冷眼旁觀與我無干,先投幣或先按目的地非得先仔細閱讀機器上的說明。
我小看了八年時間的威力,一下子掀開以為準備齊全書包,才發現什麼都沒帶。
裝熟就是這樣。
我喜歡永珍,並且認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這樣的首都。
LP城市簡介文末提到:「這座城市雖然沒有龍坡邦所展現的那分典雅美麗,但日落時在河邊品嘗一瓶寮國啤酒,很快的你就會喜歡上這裡的。」一出現「雖然」二字,已是為當地的某些缺陷心虛了,後面再補上什麼都是強說詞。反之,若單單只靠「日落、河邊、寮國啤酒」就能讓人愛上的城市,肯定寥寥無幾。
遊客在永珍只有第一天需要地圖,後來只靠幾條街就足以建構每天主要的活動範圍。永珍首先打破我萬花筒般城市紋理的首都印象,既然這個深藏內陸的國家我一無所知,那麼「認知」也就得暫時放下。
城中最寬的馬路通往凱旋門,來回走過一次就不會再去。另兩條與湄公河平行,其間的小巷道開滿了餐廳、旅館、旅行社,旅客大多在這裡吃住玩樂(台北至今沒有這種專屬旅行者聚集的區域)。就這樣,永珍搞不好已經比你過年回外婆家的那個小鎮都還小,也許永珍不小,是端出來給外國遊客的永珍就是這麼小,概念的小。
迷你的首都,待了六天五夜,換過一次旅館,認識一個寮國朋友,愛上一條河流,看了五次落日,喝了N瓶寮國啤酒。
我不曾認識、也不曾去過在國界上的首都,永珍以特異的姿態站立在世界其中一條邊界上,臨著河,望向另個國家。這地理組成條件實在奇特且誘人,但若不說對岸就是泰國,風景則平凡無異。並非緊貼泰國有什麼奇觀或好處,而是一個城市因此有了一處不受打擾的概念邊陲,沒有穿過街廓的道路與欄杆高牆,彷彿一片大落地窗隔絕了噪音,冷風吹不透卻賞盡了美景。以政治空間的配比來說,既邊緣又中心,有種我家客廳就增建在別人家陽台外的錯覺,隨時窺視著某些羨慕與忌妒。
大街上的每一條小巷都通往河畔,讓我想起印度瓦拉納西與恆河,而我也只是逐日望著河的對岸不曾踏上造訪。我們下午四點就會來到河岸,帶著啤酒坐在堤防上。背後禁行車輛的馬路滿是慢跑騎車散步的優閒人們,前方是乾旱的河面,沙洲上偶有吃草的牛群和體力過剩的少年,對岸則是一排矮樹露出幾棟紅屋頂的房子,那已是泰國領土。
長長一兩公里河畔僅有基本的公共建設,看日落的廣場大階梯、運動休閒的公園、充當跑道的柏油路、光禿的水泥鋪面與設施,其實一點也不美不浪漫。但一處沿著河岸的空曠場所,有夕陽、有河流、草地、可以和朋友運動歡笑、可以和親人共度、可以和情人並肩而坐用只有兩人聽得見的音量說話,這些簡單的享樂在這簡單的國度,沒有太多景點的城市釀出沒有雜質的簡單韻味,好像好茶就得用高山泉水,才能沖出更清澈的香氣。
他們說寮國窮、說永珍無聊,到底是心底多麼空虛的人這麼難被填滿?到底是腦袋有多複雜的人感覺這麼麻痺?應是已失去享受﹁簡單﹂的能力。視線右方即是落日的位置,六點太陽沉入湄公河遠方的盡頭,喝完入夜前最後一口啤酒,把鋁罐捏扁,金屬扭擠的聲音與台啤無異,只缺少該被回收的情緒。
我特別喜愛這河畔午後,每天都來,也不為什麼,落日只是個每天上場的演員,不是「非去不可」。此刻就如週末自然醒後還賴在被褥中,十一點的陽光已經照進混亂的房間,就呆滯望著天花板,沒有催促,沒有提醒,沒有接下來。
廣場上的夜市亮燈開始熱絡起來,吃過晚餐的觀光客穿著短褲背心和拖鞋,逛街散步也散心,買件印上我愛寮國的踢恤紀念此行。堤外入夜之後的景色則無垠黑暗,鄰國土地消失,永珍被擠到世界盡頭,河流是海洋也是宇宙。
啤酒入夜後是酒吧裡的暢飲茫茫,是慰藉孤獨的酒後說愁,湄公河是陪伴也是傾聽者,他懂旅行者為何遠行至此,千里迢迢只為落日和啤酒,他明白這些都是藉口又不說破,就算一夜過後就是告別,還是伸出緩緩的台階讓你走下來,說,這是旅行啊。
昭阿努立在河邊的雕像抬起右手揮向泰國氣勢恢弘,而不遠處空地已被施工圍籬圈起,現代化的國際商業中心模擬圖宣示著永珍向錢看的未來,日後這片空曠將慢慢被慾望吞噬,人們不在乎何時落日,昭阿努的雕像將被移到公園裡陰暗的一角,那時永珍已不再需要這單純的景色和不值錢的優閒。過去與未來只供詠嘆,旅行者的資產只限當下,廣場陣列的旗竿高掛社會主義的旗幟,最窮的寮國幸福指數排行全球第二,經過這幾天河畔的流連,我喜歡永珍,我可以了解。(待續)清邁哪好
翻看起清邁照片,發現成像變細膩了、色彩更飽滿了,以為是第二次來清邁眼光變了嗎,才想起來這些相片是用琳達媽的相機拍的。相機是R帶來的,兩人旅行也是從此開始的。
回台後有天下午,我和R在景美的茶店又說起清邁,我問他:「清邁到底是哪裡好?」比起曼谷,R更喜歡清邁。我也很喜歡清邁。我們一致認為清邁是個令人放鬆的城市,但何以泰國到處是標榜「悠閒」的好地方,如南方的海島或泰北的小山城,而清邁卻特別惹人疼愛?
城市都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質感。北京是紅的,東京是透明的,首爾是硬的,曼谷是濕的,新加坡是塑膠的,瓦拉納西則是刺鼻的。若用食物來形容城市,我覺得清邁是戚風蛋糕,雖然蓬鬆,卻是飽滿的、有彈性的。
我認為城市分為兩種,一種如海洋般廣大、密密麻麻編織起來的、讓人無盡探索的,如曼谷或東京。而清邁是另一種,讓旅行者抱在懷裡的、絲絲耳語的、細數家珍的。清楚的護城河圍起了一公里半見方的城,即使城牆不在了,城的形狀依然清楚留下,明白的邊界讓旅行者感到安心,即使如今清邁早已越過城牆往外發展,這古城仍如心臟於此跳動。比起台灣的古都台南,許多古城門雖在,但舊城的邊界則難以察覺,城市仍以一個經濟發展至上的大都會自居。
以塔佩門延伸到帕邢寺的叻差當能路為主幹,再依個人喜好往左右長出自由的路線,寺廟、美食、按摩、咖啡小鋪等,都是徒步就能抵達的簡單明瞭。雖然這是錯覺,清邁遠比起認知的複雜廣大,但錯覺是美麗的,他像一本編輯好的參考書,已整理出摘要重點,不滿足的旅客則可自行深入。但它絕不是一本漫無目標的大字典。
清邁通常不是旅行者到訪泰國的第一個城市,經過曼谷或度假海灘的熱情轟炸,自然能感受到清邁閒散氣氛。也因如此,距離首都十二小時火車、九小時巴士的距離,過濾了對泰國風情只想嚐鮮的人潮,降低了觀光密度。來到清邁的旅客多已對泰國有更多的喜愛與認識,不再迷失於超大型百貨公司或批發商場,因此能更沉澱在安靜的旅行中。住在清邁的泰國朋友J便覺得大型購物中心的逐漸興起對清邁是一種都市化侵略。
悠閒到了底稱為無所事事。清邁悠閒,可以無所事事,而非只能無所事事,清邁的鬆緊是有彈性的。清邁身為舊朝首府依然底蘊豐富,位居泰北起點還擁有廣袤森林,空靈的佛寺與人氣夜市都有,古樸傳統與時髦設計兼具。
多數想「放空」的遊客,並非想完全掏空所有,而是在空虛時必須獲得適度填加,宜人的生活尚須載重偏低的運行。有如一盞黑暗房中的小夜燈,微微照亮了不大的視野,舒適而溫暖,完全的黑暗是將人隔絕於外界的。清邁的悠閒仍然貼近民生世俗,除了密度極高的佛寺,不乏色情酒吧和阻街女郎,街上的按摩院也可能暗藏春色,這些飲食男女都是生活的部分,清邁並未因標榜慢活古城而水清無魚。
如又比起泰國中部相同是古城的素可泰,清邁對外地遊客釋出的善意是更顯而易見,除了古城作為主菜以外還有選擇多樣的甜點來搭配,簡而言之,即是適度的觀光化。即便素可泰的歷史遺跡令人驚嘆,但出了古城到新城便是沒有驚喜的密集街道與樓房,於是遊客通常不出兩三日就往清邁或曼谷去。
房租飲食物價相對低廉,於是我們說清邁適合生活、長居。許多遊客在清邁住久了,甚至是退休後的永久移居,旅行已是以年月計。生活中安插課程學語文、學按摩、學做菜、學瑜伽,清晰簡單的時間安排讓自己找回在原所在城市已紊亂的生活步調,自己能慢慢的走,無人在後追趕或拉扯。
慢活之城,僅是將生活速度放慢,而非歸零。
清邁地圖在我腦中是簡明扼要的,由東至西也由低漸高,屏河、瓦洛洛傳統市場、觀光夜市、方正古城、尼曼明路流行街、清邁大學、動物園,最後上山至素帖寺又俯瞰溫習了整個城,令人易於掌握的安好境地,簡單而豐盛。
週日下午三點,我和R坐在一家十字路口旁咖啡店的戶外座位,看著周日夜市的商家慢慢將商品攤架搭設完備,突如其來的一場雨又讓大家手忙腳亂。整個下午耗在街角哪兒也沒去,就坐在屋簷下看著夜市從無到有。
這是清邁最大的市集,許多遊客也為了夜市刻意將旅程排在周末。天還沒暗遊客就已漸漸湧入,我們花了二十銖各買了一杯暗紫色的綜合果汁,我高舉果汁請R幫我拍下與熱鬧夜市的合照,此時帕邢寺那端的暗藍天空恰好射出煙火,原來正適逢皇后生日,全國各地都有慶祝活動。照片中人潮蔓延到遠方沒有盡頭,人人燦笑映著點點燈火,清邁彷彿正臨太平盛世。
週一,我和R到塔佩門前的麥當勞吃早餐,在二樓看著又恢復寧靜的廣場,工人們正在拆卸為昨天慶祝活動搭建的臨時舞台。一邊抱怨著速食店又貴又淡的爛咖啡,我們聊著清邁到底哪裡好,然後決定再多留下來一天。(待續)心上的佛寺
我一向不擅長參觀佛寺,信手拈不來歷史,也說不出一口好建築,佛祖哪兒來哪兒去終究是經過了此地,旅行者嘛,我們信仰當下相遇的緣分就好。東南亞的大小佛寺成千上萬,若全自旅遊書上刪去,旅程肯定是要少掉大半。不是不愛看,只是不擅長。
香火正旺的廟可以看看熱鬧,看那些鮮花金箔怎麼誇耀信徒合十的祈禱,看那些重簷壁畫怎麼包容荒野失落的神魂。但傾頹的遺跡就難懂了,像黑白照片在相本裡被遺忘,好久好久都不曾被翻開,顏色被抽掉復古味道頗好,但旁邊主角的名字是誰卻想破頭了也記不得。在意的,還嗅得到當時眷戀的餘味;若無心,就像上台報告時間不夠了的投影片,匆匆一瞥就趕緊翻到下一張去。我不是你,從未參與過你的過去,你拿當年的過去要我看到什麼呢?榮景如今要從磚瓦灰燼間說起,不談同情不讀書,我們拿什麼來當翻譯?我們只能一人拿一邊耳機聽同一首曲子,耳中聽見相同的旋律,但心底暗自唱著喜歡的歌詞。
素可泰曾是王朝首都、歷史之城,不過這道光芒夾在清邁和曼谷之間奄奄一息,特地到訪的遊客相對的少。我和R行程鬆散不趕時間,就決定到曼谷之前停留幾天,多認識一個泰國城市,並非為了朝聖而來。
我們住在一點觀光氣息都沒有的新城,不過食物好吃消費便宜,一如泰國各地都有的舒服友善。距離十二公里外的舊城,面積與現在清邁古城不相上下,但如今已是被掏空血肉的歷史公園,購買一百銖門票就可以觀賞輝煌城市的殘骨。我和R租了一台機車騎進攤開的地圖裡,寺廟佛塔斷垣殘壁有如電玩遊戲的關卡,一座接著一座拍照蓋章,機車引擎在空曠的園區裡不識相的咆哮,按表操課速度太快,不知為何而看好似索然無味。
幾百年的剩餘就是眼前的人去樓空,既殘酷又冷靜,我忽然想丟棄那些密麻的過去,走進現在眼前這光禿的楚楚可憐裡,無視王朝,不談歷史,反過來為當時的古人導遊起這最新的現場。
旅行若不貪求,只願領略一角心中的美景,沒沒無名微不足道即可。
我們丟下機車來到一座印度教寺廟,青綠平坦的草皮裹住一圈不起眼的石牆,三座高棉風格的佛塔探首其中,我無意入內鑽研建築或宗教,只是徒步繞圈緩緩感受這場所。走了半圈見到主入口,一位大叔坐在長凳上脫了鞋納涼,不遠處的小竹棚擺著販售給遊客的紀念品,小攤子只是他的配件。每天就選一座喜歡的寺,他擺攤如擺陣,風拂綠茵如詩,靜靜的定在此淡泊幽涼之中,說做生意嘛,合則來自有緣分。他沒說上半句話喚我買些什麼,我則悄悄加入他的春風沐浴裡,麻雀婉轉啁啾,三人共享這無爭之時,眼前靜好。古寺尚在也已融入生活片景,不只崇拜。
素可泰古寺何其多,從地圖上挑幾個有緣分的,有如探訪老友好好的聚上一會,在涼蔭處坐下聽聽古寺的聲音,收起急躁的相機、喝口茶敘敘舊,不急著走。若急忙趕場就跟候選人拜票一樣,作勢虛情難得收到心上。
書中神祕的娓娓描述在我腦海建起了想像的模型,我常相信直覺的選擇。趁天黑前我們找尋城外一處山坡上的佛寺,此寺位處荒僻訪客鮮少,我們靠著手機導航一路騎過無人的石徑,泰文的佛寺拼音難以辨讀,一座經過一座我們也一路停停走走,直到見到一道通往上坡的石橋,我們才確定找到了。
所謂石橋,是由石塊碎片堆疊築起的坡道,在陡坡覆蓋上另層緩坡讓人能逆行而上,不如人工水泥階梯的銳利速成,樸拙的石橋從山下就已然沉澱紛亂的心場,有些費勁的上坡則逐步讓身體勞動,是提醒也是儀式。途中可見前人疊起的祈福石堆,石頭只靠輕觸相疊,隨時可因風吹外力就倒塌分離,隨緣謙虛的心願令人珍惜。
百餘公尺山坡上的古寺荒而不廢,巨大的石塑立佛與柱列露天併立,佛像胸口龜裂腦後草葉攀生,背後也已經撐起防止倒塌的混凝土補強結構,沒有華美的雕梁畫棟,我們依然用盡誠心綿長信仰。一組信眾在大佛腳下焚香吟唱誦經,祂靜定的眉眼高高在上看俯瞰著素可泰古城,沉重巨大的存在賜人撫慰的力量,人的血肉軀體此刻顯得虛弱渺小,被捧在佛祖手心之上,不再憂慮惶恐。
一條忠誠的野狗引導我們上山,下山時又走在我們前頭帶路,萬物心靈相通,佛心也願伸手攙扶。
下山騎車離去之前我又回望山端,看那座被時間剩餘的寺廟,凋零殘破到底,信念卻低鳴遠道而來。從過往、從遠方,像流浪者把持的堅定意志,不惜居無定所衣不蔽體,只望自己能對自己說話,只願把寺築在心上。(待續)初戀周安琪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首歌嗎?以前我們住的那個村子,全都是木屋來的,就像這裡,下面就是海,我最愛跟我爸躺在木地板上,一面聽著海浪的聲音,一面聽這首歌。我們村子裡全都是姓周的,叫姓─周─橋─,在檳城很有名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給我取的,叫周─安─琪─。」躺在阿牛背上,左腳穿進水面踩出幾圈漣漪,李心潔在電影《初戀紅豆冰》裡這麼說。
為了寫檳城,我特別翻出電影來看,第二次看,但這些話好像第一次聽。周安琪說的我早知道,但從女主角口中說的,既真實又如夢似幻。電影是假的,但又因為假的原因是電影,所以可以被忽略,於是那又是真的了。旅行時我喜歡用感官揣摩情境,像演戲或彈琴揮手甩頭時閉眼陶醉,而厭惡導覽資訊的填充輸入。周安琪姓周,住在姓周橋。此時周安琪在旁白生活,就不歸類為資訊。
陽光太烈不出門,過了中午卻又下起陣雨,我仍在旅館走廊藤椅上懶散,在臉書上發了訊息:「我在檳城,下午四點,給我個地方去?」第一則回覆就是「周橋,傍晚的周橋最美。」我盯著答案想起一張學妹寄來的明信片,一邊查了網路。有些意外不解,此地我素昧平生,但這提醒又過於中的,既視感的似曾相識。這些在海岸的參差木屋掛了保證,沒有秩序的東西有意思,勢必原味,絕對生猛,生活嚴謹規律的人特別需要看這些風景。是我忘了曾經想去的念頭。
身在喬治市,就往東走就會遇上姓氏橋的其中一座,姓陳、姓林、姓李或混居的雜姓橋,姓周橋最大名氣最響,不用地圖也很容易就能找到。這些有姓氏的橋不是橋,是早期華人移民馬來西亞的聚落,全立柱築屋在檳城沿岸淺海,橋是各戶門前的街巷,同姓的住一起,離岸的另一頭除非搭上舢舨否則沒有出口。房屋就站在塑膠桶串起充當模板的水泥基礎上,房身屋頂多已是鏽蝕的金屬浪板,斜頂穿前插後方向不一,比台灣頂樓違建還有機,拐彎岔路看似死巷又總有捷徑。海味腥臭依舊,浪聲拍打腦海,家的概念像海草,一株株從陸地水平生長的海上村落,飄搖飄搖的,柔軟而堅韌。
「他也不管我就坐在客廳,沒問過就往家裡面拍!」兩個大嬸坐在門前用福建話牢騷抱怨著。週間遊客不多,大嬸們也不是針對我,但我瞬間再怎麼謙虛守秩序,彷彿也成了無地自容的加害者。
二??八年檳城登入文化遺產、二?一?年成為電影場景,雖然書上寫著這裡的居民依然生活如昔,但民宿、餐廳、禮品店開了幾家做起遊客生意,生活不是石頭很難不變。成天往家門口探頭探腦陌生人,不是透明海風吹過鹹鹹的而已,在城市的微血管末端,外來遊客像通過沙漏頸部的沙粒特別顯眼。當胸前掛著相機走進來,我也已是讓周橋「不像以前」的一分子。我非長住於此,變與不變對我來說只是一個下午的時光消遣,我沒有資格抱怨不見你們的往日生活,更愧疚於自己的生硬介入。
走出周橋,在右手邊的茶水攤坐下要了茶冰,大樹刺穿鐵皮屋頂在高處開枝散葉,這裡沒有講究的大理石圓桌,大夥拉著塑膠椅繞著樹幹飲茶好像還是小時候在樹下乘涼談天,對面的朝元宮和攤子旁的泥造金爐包圍了一個小埕是姓周的客廳,四周都是熟悉的福建話,我惦惦聽著閒話家常,像是兒時被父母拉到親戚家串門子,大人聊天小孩插不上嘴,只差現在我不需要對彼此的距離害怕,這是旅行者的陌生豁免權。
我一向是安靜的旅客,獨自低調的走著,偶有風花雪月,鮮少熱血勵志,其實我更希望能披上斗篷隱於無聲無形,像風吹進房間的窗口,看到所有精采的細節,像鬼魂坐在你們之間不被發現,聽盡昨日發生的八卦與瑣事。說說罷了,我能做到的僅是繼續低汙染的安靜走著。
「哥,你畫畫這樣美,為什麼不要拿去參加比賽?美的東西本來就要拿出來的啦!天生麗質難自棄嘛!」肥妹對每天偷偷畫著初戀情人畫像的Botak 說。後來肥妹偷偷寄了一張周安琪的側臉水彩肖像報名了比賽,並且贏得了冠軍。當大家為他的才華稱讚喝采,哥哥知道了卻是安靜的走到騎樓下傷心啜泣,因為初戀情人已經離開了小鎮,一袋幾毛的紅豆冰,也就為了初戀而美麗。
也許,美的東西不一定要拿出來,存放在安心的盒子裡,天生麗質只願給看到的人好好珍惜。(待續)馬來西亞到新加坡兩座橋
中南半島上最南邊的陸地國界,也是最後一個。
其實中南半島在馬來西亞最南端的新山已經終止,新加坡是隔著柔佛海峽的島國。兩座跨國通道像吊襪帶將新加坡掛在歐亞大陸底下。更誇張些形容,新加坡超高的人造密度與現代化發展,與中南半島各國全然異質化,已像顆垂在石灰岩下的透亮水滴,隨時會脫落。
從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跨越邊界對我是重要的,甚於比較兩邊國家的差異。我記述下途中的每次跨越,換車、走路、搭船或過橋,每回都因邊界的存在而必須調整自身姿態,有如道路上的裂縫或凸起,經過時總附帶一瞬震盪,提示著將臨的變異,即便差別只是相似的細微末節,都有個慎重的動作來轉接。
兩天前一抵達馬六甲,就直接在車站買兩天後要到新加坡的車票,問了幾家巴士公司都已客滿,原來新加坡人喜歡到馬六甲度週末,週日正是收假潮。幸好,一家巴士公司還有位置,只是一早十點就得離開。早起一向是我最困難的功課,就算在旅行時也不例外。
離開前到茶室喝了茶、吃了牛油麵包,記得在檳城時也是如此將城市收束打包。兩次來馬六甲,這家隆安茶室我已經光顧了不下十幾次,Sam 也常來,是他介紹給我的。把它當作台北公寓樓下的早餐店,在不變的城市角隅有一樣的味道,即便遊客的熟悉只是短暫,算是利用它營造些許迷幻歸屬。至少相隔一次分離,這是到訪兩次以上城市才有的把戲。
二十二令吉、三個小時就到了邊界,位於新山關口後是通往新加坡的新柔長堤。下車、出境、上車、過橋、下車、入境、上車,兩國的關口都如國際機場般新穎寬敞,一字排開的眾多櫃檯,旅客有如在講究效率的生產輸送帶上,流程明確通關快速,連入境卡都在巴士上就發放填寫。
平均每日有六萬車次往來兩國之間,原是相同國家的兩岸仍然因缺乏而彼此依存著,一公里多的斷裂,南北人車油水,這窄窄的通道日夜不停運輸彌補著。
橋再寬對於國家來說也只是沙漏間細瘦的頸子,星馬之間就這麼兩條通道,是否略嫌窘迫蹩腳?反觀自己的國家四面臨海,與他國的來往只是個小機場,客人出了機艙踏上台灣國土,伸手迎接的是只容兩人並肩通過的空橋,我才想起這是海島的宿命。何況台灣已沿海岸線自築了高牆,沒有道路,更沒有鄰國。
巴士下橋後駛進大雨中的新加坡,公路旁的植物高大濃綠,組屋樓舍色彩過分俗豔,濕淋淋的世界宛如野獸派的熱帶。這雨自啟程時一路沒忘下到了終點,我撐的小黃傘是隨身攜帶的太陽,在山林海島或市街低空發光,一道自北回歸線貫穿南國的軌跡,蒸騰冒著燥熱的濕氣,還以為走過的路都因我已茂密成林。
八年前首次來新加坡,對馬來西亞尚一無所知,為了看到柔佛海峽對岸的馬來西亞,我曾到克蘭芝地鐵站附近一處濕地叢林公園。走到水邊,對岸山坡上疊著紅屋頂的低層建築,一公里多的距離讓新山彷彿隔了描圖紙略感輕飄霧白。手機跳出馬來西亞電訊公司發送的簡訊,歡迎我光臨馬來西亞,當時仍是單色的小小手機螢幕上,就浮現了曾到馬來西亞一遊的證明,只不過是隔海借景。
巴士最後停靠在一處商場大廈旁,熱烈的大雨讓乘客抓著行李手忙腳亂,直到在騎樓底靜定下來,才看見我已處於百分百人造的文明都市中。此處是個華人很少的商場,像是中山北路上的金萬萬,招牌、商品或消費族群,都浮著一層陌生光暈。
把剩下的馬幣換成新幣,撐傘走到附近的地鐵站。
大雨持續,辦公大樓旁的草地修剪齊平,噴泉造景依然盡責定時射出不同高度的向心弧線,我走在排水良好的人行道上,想起泥路上常有的坑疤水窪和木屋前的潺潺流水聲。
站在售票機前,不預期的被轟然陌生偷襲,曾經來過的記憶已完全不剩,所有地名路線方位冷眼旁觀與我無干,先投幣或先按目的地非得先仔細閱讀機器上的說明。
我小看了八年時間的威力,一下子掀開以為準備齊全書包,才發現什麼都沒帶。
裝熟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