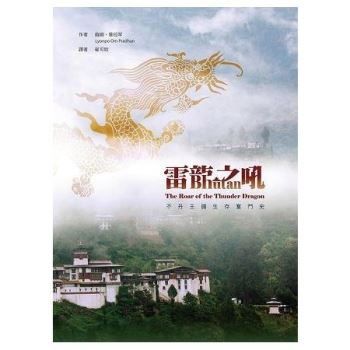第一篇 不丹崛起為政治實體
與近鄰的歷史關係
不丹的國際關係總是受制於其作為內陸國家所處的地緣政治位置而決定。西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綿延王國北疆長達四七o公里之遠。不丹的南部、西南部與東部,分別由印度的錫金、西孟加拉邦、阿薩姆邦與阿魯納恰爾邦所環繞,長達六o五公里。居住於國境交界處的這些人民,也對國家的民族組成有所影響。
自十七世紀夏尊昂旺•南嘉(一五九四-一六五一)創立所謂「政治的」不丹之後,不丹鄰國也相繼發生內政與外交上政治地位的重大改變。一直到一九五O年代早期,不丹人仍將西藏視為獨立政體,對錫金的狀況也是一樣,後者直到一九七五年才併為印度的一部分。不丹仍與阿霍姆王國(Ahom)、庫奇•比哈爾王國(Cooch Behar)統治者進行獨立自主的交涉,直到這兩個王國先後被英國併吞、合併為阿薩姆邦和孟加拉邦的一部分為止。不丹對於這些王國的直接政治影響力、干預並介入其間事務的能力,於一八六四年英不戰爭之後斷然中止,並於一八六五年簽署「辛楚拉條約」(Treaty of Sinchula)予以確認。如果尼泊爾與西藏等喜瑪拉雅政體能與不丹形成聯盟,那麼在英國兩度將勢力延伸至喜瑪拉雅區域之前,也許還會考慮一下。然而,所有想要促使喜瑪拉雅諸國被迫共同對抗英國統治的企圖,包括西藏在內,最後都沒能成功,西方殖民勢力利用老謀深算的外交手段與優良的現代化新型武器,在政治與經濟上宰制世界的各個不同地區。「分治」(divide and rule)策略極其成功地運用於印度次大陸,包括喜瑪拉雅地區的國家。一方或另一方受到英國人的分化所影響,而未能形成對抗英軍的聯盟。中國人則似乎只對掌控西藏有興趣,宣稱該區域為中國的一部分,否則這個地區是唯一有能力組織出有效抵抗西方殖民野心的區域政體。一旦落入印度帝國手中,孟加拉王國與阿薩姆王國即不復獨立之日。有關不丹與這些昔日王國的久遠關係,旅居不丹的法國學者馮斯娃斯•彭瑪黑(Francoise Pommaret)考察了一些詳細的歷史記載,顯示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期間,不丹與庫奇•比哈爾王國和阿薩姆王國之間存在著貿易往來 。
不丹還與東邊的達旺(Tawang)以及今天隸屬於印度阿魯納恰爾邦的鄰近地區 有直接往來。不丹與尼泊爾、拉達克(Ladakh)等地也存在著貿易、文化與宗教的聯繫,儘管這些王國位於西邊的一段距離之外,並未直接與不丹接壤。這些鄰近關係因相近的宗教傳承而提供刺激作用,例如最著名的竹巴噶舉 嘿密寺(Hemis)即位於拉達克。目前拉達克為印度查謨和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 state)的一部分。
上述事實顯示出,不丹地區自古以來, 在十七世紀成為獨特政體的前後,就已經與周圍的「外國」土地與人民,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具有實質的互動。
鄰國對不丹的理解以及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
夏尊昂旺•南嘉於西元一六一六年由西藏惹龍寺(Ralung)抵達不丹西部,隨後創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竹域」,當時鮮為人知的不丹地區似乎被誤認為是西藏的附屬地,特別是南方鄰國這麼認為。前文描述,在這種情況下不丹直到一八六O年仍受西藏影響,並且到了一九四O年代中期為止,不丹名義上仍向西藏朝貢(Savada, 1993)。若因為夏尊來自於西藏而將不丹視為西藏藩屬,這種觀點並不完全正確。因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標,就是斷絕或避免受西藏所影響,特別是在政治、社會與文化方面。在他的統治期間,他盡一切努力使不丹與西藏截然不同。他改變了宗教儀式、服飾以及宮廷禮儀。甚至在口語方面採用宗喀語(Dzongkha),以盡量縮小與藏語的語言相似性。夏尊所作的一切,強化他所創建的王國具有獨立地位,避免給人的印象是,他的國家是西藏的延伸。時至今日,現今國家領導人依然在內政與外交兩方面,繼續深化這項政策。這似乎也是至少到目前為止,不丹領導人依然儘可能優先維持每項夏尊傳統的原因。別無選擇地,不丹無法在廿一世紀中,輕易將現代化發展與外來影響拒於門外,只能堅守傳統來抵禦國際浪潮。我意識到第四任國王陛下晉美•桑格•旺楚克多次提出這個進路,他分析並解釋夏尊政策對於推動不丹主權與獨立的成功之道。
不丹創立者:夏尊昂旺.南嘉(1594~1651)
昂旺.南嘉(Ngawang Namgyal)於一五九四年出生於西藏竹江秋寺附近的嘎東寺(Gardong)。他的父親滇佩.尼瑪(Tenpai Nyima,1567~1619)是米龐.確嘉(Mipham Chhogyal,1543~1606)之子,為竹巴噶舉主寺惹龍寺的第十七代法嗣住持。昂旺.南嘉的母親為索南.帕姬.布蕊(Sonam Palgyi Buthrid),是拉薩領主之女。她曾與藏德悉(Tsang Desid;或稱藏巴汗,為後藏領主,其領地為西藏與不丹毗臨的主要地區)滇松.旺波(Tensung Wangpo)共結連理,育有一女。兩人離異後,索南.帕姬.布蕊改嫁滇佩.尼瑪。昂旺.南嘉出生後,認證為竹巴傳承大學者與尊聖者貝瑪.嘎波的轉世(Pema Karpo, 1527~1592)。然而另一位帕桑.旺波(Pagsam Wangpo),同時也被認證為貝瑪.嘎波的轉世,並得到最後一任藏巴汗噶瑪.丹迥.旺波(Karma Tenchong Wangpo,統治期:1622~1642年)的承認。
從昂旺.南嘉幼年開始,米龐.確嘉即對孫子的前途寄予厚望,他親自訓練孫子,望其成為竹巴法王。訓練內容還包括前往藏中與藏南游歷,連當地的桑昂寺(Sang-nga-chholing)都試圖調解兩位轉世者之間的競爭,但收效甚微。昂旺.南嘉在祖父於一六○六年辭世之後,入主惹龍寺,成為第十八代竹巴主寺住持 。然而十年之後,昂旺.南嘉自認離開西藏為佳,避免繼續與帕桑.旺波競爭,長期的敵對狀態不利於竹巴傳承的統一。情勢既然如此,他立時接受不丹竹巴僧人的邀約,旅行穿越林希(Lingshi),並於當地得到不丹竹巴高僧的熱情接待 。在不丹竹巴僧眾的既有基礎上,昂旺.南嘉輕易受推舉為政教領袖,即將由他與追隨者建立並擴展,結合了宗教與寺廟的不丹政治實體。
西藏攻打夏尊法王
隨著夏尊昂旺.南嘉進入不丹之後,蒙古政權所支持的西藏軍隊分別於西元一六一七年、一六二九年、一六三一年以及一六三九年先後入侵不丹,但這些侵略行動皆未能削弱夏尊的勢力。不丹與西藏傳統上愛恨交加的關係,始於昂旺.南嘉抵達不丹後,即擁有無數追隨群眾。這些人大部分定居於夏區(Sha) 、旺區(廷布)、帕羅地區等地,稱之為昂洛人(Ngalong) 。
一六四二年到一六四三年期間,蒙藏聯軍為了追擊寧瑪派僧眾而入侵不丹,當時寧瑪派的追隨者為避免落入強勢統治的格魯派(Gelugpa)迫害者手中,而四處逃亡於不丹、錫金與尼泊爾。一六三○年代,蒙古人控制西藏,並建立格魯巴政權 。昂旺.南嘉的不丹政敵慫恿蒙古人侵略不丹。然而,蒙古人「很輕易地就被擊潰於南不丹的潮濕低地之中。」(Savada, p. 256-7)
西元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四五年間,藏巴汗囊措.歐(Nangso Ao)為了征討不丹,集結藏人、蒙古人以及霍康家族(Hor)的族人,組織了一支史無前例的龐大兵團。夏尊的首席大臣認為不丹無法力抗這支已進入國境,且正朝向普納卡而來的大軍。他們主張先與藏人達成共識與和解,也許較為妥善。夏尊對此建議充耳不聞,反而規劃迎戰策略以抵抗西藏威嚇。故事的發展是,儘管夏尊僅在普納卡佈署少數兵力,卻設法讓藏人誤信他編列大軍迎戰。他命令少量部隊步行穿越宗堡大門,看似正要出行應戰。這些士兵隨後返回宗堡後方,躲在藏軍探哨眼力未及之處,從宗堡後門進入,然後再度行列步出前方大門。這個善巧戰略也包括,西藏大軍從紀立岡(Jiligang)前往普納卡的路途中,看見不丹軍人搬運成堆的米糧及其他物資。從宗堡傳出嘹亮的號角吹奏聲,整個景象讓藏人以為,將有大軍從宗堡湧出,敵軍將士現正摩拳擦掌準備應戰。再者,藏人處於不利的戰略位置:山腰與斜坡朝往普納卡的方向傾斜,正巧因秋葉掉落而陡滑。這使得有秩序的部隊行軍變得困難。士兵們的陣形最終被隨後發生的一團混亂給破壞殆盡,火燒濃煙突然竄入營帳之中,而他們的主帥竟已逃往帕羅。總之,夏尊的戰術運用以及令藏人震驚的「霉運」,漂亮的消滅了考驗新政權的嚴峻軍事威脅。
在夏尊與藏巴汗的衝突當中,藏人總是重複提及竹巴傳承的珍貴聖物。當昂旺.南嘉離開西藏時,帶走了聖物「壤烱.卡薩帕尼」(Rangjung Kharsapani)。這個聖物是一尊觀世音菩薩像(不丹文稱為「千瑞吉」Chenrezig),據說在貝瑪.嘎波的脊椎骨中自然形成(即壤烱,rangjung),而在他圓寂後為人所發現。昂旺.南嘉的對手發現他將此物佔為己有,後藏當局下令發兵奪回聖物。
當兩方爭論達到高潮,據說昂旺.南嘉從普納卡宗堡穿越河流,欲前去與藏人對質。他假裝取出聖骨,然後對著藏人的方向大喊:「這就是你們在這裡與我作戰的原因吧!」他出示聖骨並揮舞著。當然真正的聖骨太小,尤其在過河的那當頭難以看清楚,因此任何一個在場的見證者都只能說,他們看到昂旺.南嘉弟子們經常都看得到的收藏聖骨的傳統寶盒。昂旺.南嘉將盒子裡的東西丟入普納卡河中,然後再度對著已無心再戰的藏軍喊話。
「現在你們已經沒有理由再繼續留在不丹了。滾回去!」這樣似乎就結束了普納卡之役的對峙。今天這個聖骨依舊保存在普納卡宗的宮殿中,作為國家一級宗教珍品而妥善保存 。每逢年度普納卡佛法節慶期間,就會大肆慶祝這個歷史事件。
一六四七年,西藏人捲土重來,派遣入侵部隊,試圖奪取對不丹的控制權。他們因無法戰勝不丹人,而再度挫敗。藏人與蒙古人未能從歷史中習得教訓,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入侵不丹。來自北方的軍隊慣於在中亞結凍的廣闊曠野間作戰,即便已與不丹人有過作戰經驗且又是驍勇善戰的將士,他們卻無法在不丹繁茂溫暖的森林山谷與丘陵間對抗不丹人。當地軼聞傳誦著,不丹人誘使藏蒙軍隊進入茂密的杜鵑花叢裡,這些北方軍人的一頭不羈長髮牢牢的被花叢纏住。當他們的行動受限或甚至無法動彈時,下場就是遭不丹人俘虜或者補上一劍。不丹人自豪之處,就在於十七世紀昂旺.南嘉來到不丹以後,一直到十八世紀初葉這段期間,一再擊潰並驅趕藏人與蒙古人 。這與成吉斯汗大軍縱橫中亞與歐洲的蒙古勝利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