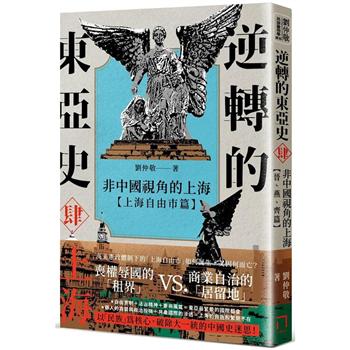鴉片戰爭的結果是簽訂《南京條約》。簽訂《南京條約》以前,在黃浦江口有一場戰役,就是牛鑑和陳化成主持的炮台戰役。牛鑑是一個文官,他並不懂軍事,但陳化成是福建總兵出身,是打過海盜的。在大清國的體制內,他是公認的火器和火炮專家。道光皇帝認為,把揚子江口的要地交給他是可以放心的,帝國找不出比他更懂火炮的人了。另外,陳化成本人也是一個深通軍事的人。
他首先修築了一連串的要塞防禦線,部署了幾百門大清國最好的大炮,然後採取了誘敵深入的計策。他斷定,英國人如果膽敢登陸、深入他的火炮陣地,他就可以全殲他們。然後大家都沒有料想到的事情發生了──英國海軍出現在揚子江口,從海上向大清國的陸地炮台開火,在幾個小時之內把這些炮台全部打到啞火,然後海軍陸戰隊從側後方登陸。
陳化成的虎蹲炮,從技術上來說是紅衣大炮的變形,也就是天主教傳教士、耶穌會士在登萊替孫元化和孔有德他們引進的那些當時的海船炮。後來孔有德叛變崇禎皇帝,帶著他的火炮一路逃到滿洲去了,再把他的火炮技術教給了盛京(今瀋陽)的朝廷。然後盛京的朝廷就利用他們現成的冶鐵工廠,在火連寨和滿洲各地大規模地造出炮來。在十幾年之內,他們造出的炮的數目就多出了明人的十倍。他們就是憑著這些火炮,最終打敗了洪承疇在松山的軍隊。
清朝廷入關以後,出現了軍事史上的奇蹟──當暹羅人和緬甸人都在不斷增加他們的火炮的同時,比暹羅和緬甸所轄領地大上幾十倍的大清國,火炮數目反而越來越少。康熙時代的火炮就比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代還少,道光時代的火炮則是連原有的規模都維持不了。陳化成的這些虎蹲炮是紅衣大炮留下的標準式樣,但是從英國人的角度來看,這些葡萄牙式的火炮早就應該進軍事博物館了。
英國人用他們的海船炮,輕而易舉地摧毀了這些炮。而且事實證明,這些炮在開火的時候,使用的火藥也已經不如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代的火藥了。那時候的火藥技術雖然簡陋,但大家是真的要打仗,是要認真準備火藥的;而現在的火藥都承包給一些奸商了。因此,炮一發射的時候,火藥往往會先在炮膛裡炸開,把自己的炮手活活炸死。海軍陸戰隊從側後方登陸以後,還沒有被海船摧毀的一些炮因為無法轉動,根本發揮不了抵抗作用,於是所有的防線都被英國人輕易地摧毀了。
在這些防線被摧毀以後,上海知縣迅速逃跑,因為上海已經變成一個不設防的地方了。於是,上海縣城的有產階級陷入眾多盜匪和會黨的搶劫威脅之下。他們派出代表,就像北京市民歡迎滿洲人那樣,要求英國人替他們維持秩序,保護他們的財產安全。但是英國人表示,我們只是為了要求自由貿易而來的,我們並不想在上海建立任何統治。如果你們要我們替你們剿匪的話,那我們就要做一些額外的勞動,浪費一些軍械,這對於我們是預算外的開支,這種事情不是不可以做,就看你們願意出多少錢了。
於是,上海縣城的有產階級就湊了三十萬兩白銀給英國軍隊,要他們代勞剿匪。於是英軍司令官發布了一個剿匪布告:「兩國交兵,不是你們這些廣大盜匪趁機搶劫的理由,我要剿一剿你們。至於廣大的和平居民,你們只管安居樂業就是了。」他們維持秩序以後就走了,然後再留下一個布告:「等我們和大清皇帝簽署了條約以後,你們這三十萬可以從賠款當中扣除,我們不會多拿你們的錢。」《南京條約》簽訂以後,這三十萬果然從清國應付的賠款中扣除了。英國人就用這種方式,讓吳越的居民(我們要注意,上海縣城是屬於吳越,而不屬於上海自由市)第一次見識了歐洲式的法治觀念是怎麼一回事。
五口通商,眾所周知,是和上海縣叫同一個名字的上海自由市的真正起源。從歐洲法律的觀念上來說,它只是授權歐洲的商團(特別是英國的商團)在五個通商口岸按照自己的習慣法自我治理。這樣就能夠避免以前在廣州多次發生的那種你應該按照誰的法律辦事的糾紛。
眾所周知,英國人不能忍受大清國衙役審理案件的那種方式,而大清國的外交官並不像後來國、共兩黨編纂的歷史書所說的那樣低能,他們敏銳地看到機會來了,可以藉此清理一下實際上已經在吳越各地定居的那些法律上來說是不合法的、但事實上已經取得了半合法地位的英國商人。
他們告訴這些人:「既然我們已經簽署了五口通商的條約,而條約明文規定英國商人可以在五口建立自己的自治團體,那麼反過來說,在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你們的地位就是不合法的。你們應該集中到那些地方去,這樣可以免除我們管理上的麻煩。」雖然這種要求合不合法是很成問題的,然而無論合法還是不合法,清國官吏都是沒有能力去執行這些條件的。如果住在上海縣城或者蘇州府的英國商人一定要說:「你這樣做損害了我的財產權,我要跟你沒完沒了」的話,那麼當地的地方官紳顯然是沒有能力把他們怎麼樣的,但是英國政府在這方面卻樂於配合大清國政府。
英國人有一個管理方面的麻煩──從原則上來說,女王陛下的政府當然有義務在世界各地保護女王陛下的臣民的安全,如果他們被林則徐虐待的話,不管一管是不行的,因為這是有損人權的(當然只是有損英國人的人權);但實際上英國政府和所有政府一樣,都不願意多花錢、不願意有預算外的開支。所以,早在林則徐引起鴉片戰爭以前,類似的糾紛已經鬧了幾十年,而每一次事情鬧到西敏寺,英國政府都表示它寧願息事寧人。
戰爭開支是一筆預算外的開支,而戰爭不僅要死人,還會導致派到遠東去的這些水土不服的將士病死在他鄉,政府還要付一大筆醫療費和撫恤費給家屬,怎麼看都是不划算。只要能夠含糊地應付過去,英國政府其實是比大清皇帝更不願意開戰的(這和國、共兩黨的教科書所說的恰好相反)。只有等到英國臣民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政府如果不開戰就無法對國內輿論交待的時候,政府才會勉強開戰。
對於政府來說,如果英裔商人和其他什麼人都集中到一個只有英國人的居留地來,那麼萬一發生糾紛的話,皇家海軍要保衛他們是很容易的,這真是一個省錢、省事的好辦法。從封建制度脫胎而來的英國立憲君主制的角度來說,其實不論是英國臣民,還是義大利人,甚至是封建歐洲的所有法人團體,只要他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按照自己的習慣法建立起自治團體,他們就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保衛的義務。
但是如果他們保衛得不到位,比如說在希臘或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的什麼地方被土耳其蘇丹虐待了,就會引起他們的法定君主有沒有義務出兵的問題。這是很麻煩的事情,能避免還是盡量避免。所以,英國領事就發出文告表示,如果英裔居民願意在黃浦江口的荒地替自己建立一個居留地,那麼有事情的時候就可以由英國領事出面處理。
我們要注意,租界的法定英文名詞「Settlement」應該翻譯成「居留地」,「租界」這個詞是歷史建構的產物。近代所謂的國恥教育教給你們的所有東西都是歷史建構的產物,和它真實的法律意義是不相符的。居留地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它沒有誰占誰便宜的意思。而且,即使在遠東居留地這種制度也是自古以來就有。
例如,我們都知道,唐帝國允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建立他們的居留地,而這些居留地也是用伊斯蘭教法和他們自己的習慣法來自治的,從來沒有人說李世民(唐太宗)喪權辱國。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以後,主動允許投降的希臘東正教徒和熱那亞商人按照他們的習慣法自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寫在《古蘭經》裡面的。沒有人說征服者穆罕默德從那些戰敗者手裡接受了喪權辱國的條件。
大清國在入關以前,早就允許晉商(山西商人)在張家口和盛京建立自己的居留地,替他們走私軍火、販賣人蔘和皮毛,這些貿易替滿洲皇帝帶來了很大的收入。我們要注意,他們並不是什麼阿拉伯人、波斯人,就只是在張家口做貿易的晉商而已。所以,你如果要說喪權辱國的話,那麼大清國在入關以前早已對晉商喪權辱國了。
居留地這件事情在道光、嘉慶、咸豐這些皇帝眼中,根本不是喪權辱國,他們答應這一點也沒有引起任何爭議。他們認為什麼是喪權辱國呢?派駐大清國的公使要求按照歐洲慣例常駐北京、並且隨時可以見到皇帝這件事情,這才叫做反了、違反大清國的體制。大清國皇帝寧願對所有歐洲商人免稅,只要他們願意留在上海和廣州而不要進京;進京這件事情才是喪權辱國。
(摘自第一章 原住民的遷入和拓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