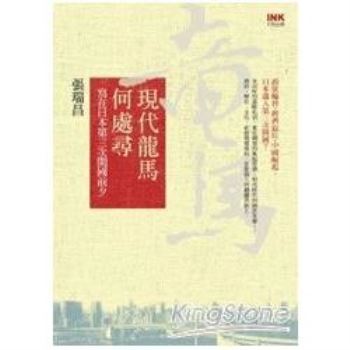作者序
一生懸命
從那須搭往東京的新幹線,火車剛駛離月台邊,我就開始惆悵,夜色沉沉,思念綿綿,疾行的鐵道上乘載著感傷的心情。雖然旅行已近尾聲,但回憶卻不斷湧現,瑞宜和佐藤在剪票口駐足,向月台上的我揮手送別,宛如在腦海裡定格的影像,清晰如一幅恆久的畫作。
曾幾何時,離別的月台已成了我最深刻的日本記憶,無論是和好友的離別、重逢,或者是獨自旅行的過程,月台總是默默地見證我的人生離情。多年後,我在倉本聰的《來自北國》(富良野三部曲之一)看見熟悉的動人畫面,明瞭月台與生命的緊密關係,原來人生有數不清的悲歡離合在此上演,而我們卻始終不察,或者似有若無地感受過,只有隨著年歲漸長,才知道那是從小讀朱自清的〈背影〉就深藏其中的生命密碼。
瑞宜是我以前的報社同事,也是台中同鄉,她與在《下野新聞》任職的佐藤結婚,兩個人在?木縣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佐藤從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就立志在鄉下地方跑新聞,瑞宜因為我的推薦參加台灣記者協會,在一次代表記協出席國際會議的場合中,與天性樂觀的佐藤相識、相戀,進而共結連理,譜出了一段美好的台日聯姻。
某種程度來說,我算是瑞宜和佐藤的媒人,她遠嫁東洋之初,如多數異國婚姻,有一段辛苦的適應期。那時我正好在東京研修,特地跑去宇都宮看他們,聽一對新人聊起台灣和日本的生活習慣、文化差異,好不羨慕。但甜蜜的背後總有不為外人知的辛酸,譬如那時瑞宜要拿日本駕照,卻在報考過程中備受刁難,心情經常盪在谷底。從上山下海的地方記者變成凡事都得仰賴先生的家庭主婦,如果不是佐藤的溫柔陪伴,平撫生活中的挫折,堅強如瑞宜這樣的台灣女子,其實也會有脆弱的一面。
我認識一些日本朋友,他們的另一半都是台灣女性,有大學教授,也有在外務省工作,而他們對台灣的好感,除了愛屋及烏之外,也有部分原因是來自島嶼之間的親善感,以致於彼此吸引。但不盡然都是寶島女孩嫁日本人,台灣男娶櫻花妹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一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駐外朋友,他和日本老婆就是在留美期間結識,後來因為職務調動的緣故,他們也曾在台北、東京兩地跑。
異國婚姻不只需要勇氣,也需要更多的尊重、包容及體諒。因為在他們背後的家族、親友和人際網絡,甚至整個社會環境、生活習性、文化價值,無非都是一個衝突和融合的過程。我從周遭台日朋友的婚姻找到一些理解與領悟,那是屬於兩個島國之間千絲萬縷的糾結,像是見證了台灣與日本兩種海洋文化的交會,也接續了電影《海角七號》中那一段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從而催促我去回溯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生命記憶,並且嘗試以媒體人的角度觀察、解讀乃至詮釋當代日本的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文化內涵。
我最初的日本記憶來自一把武士刀,那是世代務農的外公放在儲藏室裡的日據古物,旁邊還有一把用來練武防身的木刀。然而,隨著年代久遠,武士刀早已生鏽缺角,不堪使用,有如廢鐵般被棄置在農舍角落。在童年記憶中,每次回三合院的外婆家,總是偷偷拿出來把玩,想像自己是浪跡天涯、劍術高強的武士,模仿《暴坊將軍》、《水戶黃門》等時代劇中打擊貪腐特權的俠義角色。
那也是我和外公的記憶連結。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外公在鄉公所任職,村裡頭貧困的農家,為了私藏一點剛收成的米糧,不想讓日本巡查發現,經常得躲躲藏藏,而他則是一個宅心仁厚的掩護者。戰後,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鄉下地方不僅多文盲而且台語、日語夾雜,知識水準相對較高的外公,因此成了村內寫信、看公文的請益對象,太陽下山後,村裡有專門為農民開設的夜間私塾,外公自然當起教「國語」的老師。至於武士刀、木刀,則是外公在曬穀場教人打拳頭的兵器之一,印象中還有農用的加長型鐮刀、柴刀、爪耙和雙節棍。
人生有一半是在殖民統治下的外公,其實很本土化,但不容諱言,他的語言、思想及價值觀,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夜不閉戶的社會治安,以及惜情好禮的待客之道,都是我兒時經常聽到「日本經驗」好的一面,那些坐在板凳上聆聽他講古,有如天寶年間的往事,即使在外公已經過世多年之後,依舊歷歷在目。我常想念外公,他寬厚樸實的為人,有來自這塊土地的哺育,也有跨越殖民和戰後的磨練。對於無從選擇的異族統治,外公讓我看見台灣人的真誠、包容與生命韌性。
外公帶我遙想他的「日本時代」,而我第一次的日本行卻是要等到出社會做記者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那時夏天已經接近尾聲,京都嵐山快要染紅前的楓葉,以及初次直闖居酒屋比手畫腳的畫面,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與我同行的是宜蘭縣省議員劉守成,他為人豁達開朗,談吐幽默風趣,有這樣的朋友結伴自助旅行,其實是人生快意。我們從關西進、關東出,一路上都是隨意而行,每每在不經意的地方轉彎,有著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感受。
在那回與日本的初次邂逅中,箱根溫泉是旅行
一生懸命
從那須搭往東京的新幹線,火車剛駛離月台邊,我就開始惆悵,夜色沉沉,思念綿綿,疾行的鐵道上乘載著感傷的心情。雖然旅行已近尾聲,但回憶卻不斷湧現,瑞宜和佐藤在剪票口駐足,向月台上的我揮手送別,宛如在腦海裡定格的影像,清晰如一幅恆久的畫作。
曾幾何時,離別的月台已成了我最深刻的日本記憶,無論是和好友的離別、重逢,或者是獨自旅行的過程,月台總是默默地見證我的人生離情。多年後,我在倉本聰的《來自北國》(富良野三部曲之一)看見熟悉的動人畫面,明瞭月台與生命的緊密關係,原來人生有數不清的悲歡離合在此上演,而我們卻始終不察,或者似有若無地感受過,只有隨著年歲漸長,才知道那是從小讀朱自清的〈背影〉就深藏其中的生命密碼。
瑞宜是我以前的報社同事,也是台中同鄉,她與在《下野新聞》任職的佐藤結婚,兩個人在?木縣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佐藤從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就立志在鄉下地方跑新聞,瑞宜因為我的推薦參加台灣記者協會,在一次代表記協出席國際會議的場合中,與天性樂觀的佐藤相識、相戀,進而共結連理,譜出了一段美好的台日聯姻。
某種程度來說,我算是瑞宜和佐藤的媒人,她遠嫁東洋之初,如多數異國婚姻,有一段辛苦的適應期。那時我正好在東京研修,特地跑去宇都宮看他們,聽一對新人聊起台灣和日本的生活習慣、文化差異,好不羨慕。但甜蜜的背後總有不為外人知的辛酸,譬如那時瑞宜要拿日本駕照,卻在報考過程中備受刁難,心情經常盪在谷底。從上山下海的地方記者變成凡事都得仰賴先生的家庭主婦,如果不是佐藤的溫柔陪伴,平撫生活中的挫折,堅強如瑞宜這樣的台灣女子,其實也會有脆弱的一面。
我認識一些日本朋友,他們的另一半都是台灣女性,有大學教授,也有在外務省工作,而他們對台灣的好感,除了愛屋及烏之外,也有部分原因是來自島嶼之間的親善感,以致於彼此吸引。但不盡然都是寶島女孩嫁日本人,台灣男娶櫻花妹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一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駐外朋友,他和日本老婆就是在留美期間結識,後來因為職務調動的緣故,他們也曾在台北、東京兩地跑。
異國婚姻不只需要勇氣,也需要更多的尊重、包容及體諒。因為在他們背後的家族、親友和人際網絡,甚至整個社會環境、生活習性、文化價值,無非都是一個衝突和融合的過程。我從周遭台日朋友的婚姻找到一些理解與領悟,那是屬於兩個島國之間千絲萬縷的糾結,像是見證了台灣與日本兩種海洋文化的交會,也接續了電影《海角七號》中那一段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從而催促我去回溯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生命記憶,並且嘗試以媒體人的角度觀察、解讀乃至詮釋當代日本的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文化內涵。
我最初的日本記憶來自一把武士刀,那是世代務農的外公放在儲藏室裡的日據古物,旁邊還有一把用來練武防身的木刀。然而,隨著年代久遠,武士刀早已生鏽缺角,不堪使用,有如廢鐵般被棄置在農舍角落。在童年記憶中,每次回三合院的外婆家,總是偷偷拿出來把玩,想像自己是浪跡天涯、劍術高強的武士,模仿《暴坊將軍》、《水戶黃門》等時代劇中打擊貪腐特權的俠義角色。
那也是我和外公的記憶連結。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外公在鄉公所任職,村裡頭貧困的農家,為了私藏一點剛收成的米糧,不想讓日本巡查發現,經常得躲躲藏藏,而他則是一個宅心仁厚的掩護者。戰後,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鄉下地方不僅多文盲而且台語、日語夾雜,知識水準相對較高的外公,因此成了村內寫信、看公文的請益對象,太陽下山後,村裡有專門為農民開設的夜間私塾,外公自然當起教「國語」的老師。至於武士刀、木刀,則是外公在曬穀場教人打拳頭的兵器之一,印象中還有農用的加長型鐮刀、柴刀、爪耙和雙節棍。
人生有一半是在殖民統治下的外公,其實很本土化,但不容諱言,他的語言、思想及價值觀,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夜不閉戶的社會治安,以及惜情好禮的待客之道,都是我兒時經常聽到「日本經驗」好的一面,那些坐在板凳上聆聽他講古,有如天寶年間的往事,即使在外公已經過世多年之後,依舊歷歷在目。我常想念外公,他寬厚樸實的為人,有來自這塊土地的哺育,也有跨越殖民和戰後的磨練。對於無從選擇的異族統治,外公讓我看見台灣人的真誠、包容與生命韌性。
外公帶我遙想他的「日本時代」,而我第一次的日本行卻是要等到出社會做記者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那時夏天已經接近尾聲,京都嵐山快要染紅前的楓葉,以及初次直闖居酒屋比手畫腳的畫面,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與我同行的是宜蘭縣省議員劉守成,他為人豁達開朗,談吐幽默風趣,有這樣的朋友結伴自助旅行,其實是人生快意。我們從關西進、關東出,一路上都是隨意而行,每每在不經意的地方轉彎,有著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感受。
在那回與日本的初次邂逅中,箱根溫泉是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