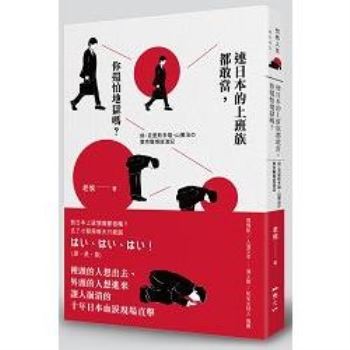◆去了日本工作,還怕地獄?
到日本工作超過半年了。之前在日本工作,是在一家外商公司,週遭都是碧眼金髮的老外,幾乎沒怎麼和日本人接觸。這次再度來日本,情況不同了。這是一家道道地地的日本公司,日本同事「純度」之高,超乎想像。十個同事當中,看英文信不借助google翻譯的,不到兩個;有能力開口說英文的,不到半個;「S、T、V、X」能正確發音的,則是一個也沒有。搞得我暈頭轉向的,不是同事們英文不佳,而是日文太好!
話說,幾天前,我們開發了一個系統,交付客戶(位在香港的日商)作測試。當天,客戶就把測試報告交給我們。針對客戶回報的測試結果,我們要研商方法,一一排除問題,附帶解釋溝通。這要是在臺灣,打一通電話,或親赴現場,溝通了解一番,在客戶email認可下(留作證據)把問題一一解決。不能溝通的,則另開會議,決定是否要修改系統。一來一往,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就該交付另一個新系統版本。換成日本公司,慘了!客戶回報的問題,先按兵不動,信不回、電話不打,如臨大敵地逐項查明原因,還要研商會議計畫、確立會議目標、擬訂會議邀請函、決定參加人員名單、制定時間表。每一項,都是日文!
那天晚上,我從下午六點開始擬會議邀請函,我的主管兩眼盯著我,催我的進度。我小心翼翼擬好了信,發給了主管。主管看了,冷笑兩聲,說:「你要把信分三段,第一段,把這會議的背景說清楚;第二段,寫明會議的預定議程;第三段,告訴客戶我們附加了哪些文件。」
通常一封電子信寄到對方信箱,會被對方的郵件伺服器搞成甚麼模樣,完全無法預期。這廂辛苦排版,那廂面目全非,司空見慣。主管對信件、而且是一個會議邀請的信件,要求「格式美」,大出我意料之外。但主管既然要求,我只有照辦。廿分鐘後,我再把改好的信發給了主管。這回,主管看得面色鐵青,口氣一變,問我:「我跟你說的三段,你怎麼寫成了五段?」
「我...您交代的三段,我都寫進去了,我另外還附帶了招呼語,以及一些說明,比方說,希望能在開會前把參加人數弄清楚之類的,這就不知道該歸哪一段了,所以獨立出來。我想,信還沒發出去,還可以和您商量......」我戰戰兢兢地解釋道。
主管正色道:「你想自作主張前,先告訴我!三段要寫成五段,先告訴我!」
我被訓得無話可說,懊惱自己自作聰明,只得照辦。好不容易把信擬好,主管勉強認可了,但仍加了一句:「內容可以了,但還沒到能發出去的程度。我來修改吧!」我一聽,不禁心中暗自叫苦!搞了半天,剛剛折騰了三個小時,純粹只是要訓練我這老外的日文撰寫,最終,還是要老闆親自出馬寫這邀請函!!
往好處想,算是這主管願意栽培後進;往壞處想,這人簡直就是偏執狂了。主管把信擬好,再發給我,要我把附加文件貼上去後,定稿,再讓他過目,然後發出去。我想,這下總該脫離苦海了。貼好了文件,把格式再弄漂亮點,主管寫過的內容,一字不改,然後再發給主管作最終審核。
你道我這苦海脫離了嗎?不,沒脫離,而且好戲來了!
主管收到我的「最終定稿」,臉色由鐵青變成了糞青:「你動了我的格式?」
「我動了...我是看有的段落隔了兩行,有的段落隔了一行,想把格式統一一下,所以......」
主管面帶慍色道:「你再把我原來的信打開來看看!」
我的手,顫顫巍巍地打開了主管的原信,開始端詳。
「看出來了嗎?我信裡隔兩行和隔一行,有甚麼不同?」
我仍在端詳。但沒看出所以然。
「對不起,這兩行和一行的區別...真沒看懂。」
「你再看仔細!兩行上下的內容,和一行上下的內容,有甚麼不同?」
深夜十二點了,只剩我和主管兩人。我在東京,一棟人去樓空的大廈裡,拚命研究這兩行和一行的奧秘。腦子早非處於適合邏輯歸納的狀態,一切只能靠奇蹟。
二分鐘後,奇蹟出現了。「大概...兩行隔開的,代表大段落;一行隔開的,代表小段落...。」我提出我的新解,語氣完全沒自信。
主管總算點頭道:「這就對了!你把我格式弄亂了,要怎麼區別大段落小段落?」
豁然開朗後,我趕忙把兩行的歸兩行、一行的歸一行,重新發給主管,拍板定案後,傳給了客戶,心中默禱著:「但願客有時間、有雅興,能欣賞這兩行與一行的苦心孤詣呀...」。
六個多小時,只為了一封會議邀請信。看倌要是有耐心,這日本公司磨人的事情,多得不勝枚舉,我日後可以一一和各位分享。
日本人在程序,體面上的堅持,由此可想。我從這件小事上,充分理解了當年阪神大震災時,連日本媒體記者都趕到了,偏偏自衛隊遲遲不到的原因。不就是在人命關天的時刻,政府的某個官員,死抱著某個流程、堅持寫某個文件、緊守著分成三段或隔成兩行之類的莫名其妙的「程序正義」嘛!
如果是做一名觀光客,你會喜歡日本;作一名留學生,對日本印象也不會太差;但若是作一名日本上班族,企圖融入日本社會,那就省省吧!身為一個外人,你可以用純欣賞的眼光,喜歡日本的乾淨,有秩序,也可以喜歡日本人的有禮。但這美麗表象的背後,是靠著怎樣的森嚴紀律和一絲不茍,甚至要抹滅掉多少個性乃至人性,才能粉飾出來的?這哪是乳臭未乾的哈日族可以管窺得到的呢?
有看倌問道:「老侯,你也真奇怪。一肚子苦水,幹甚麼不回來?」這位看倌有所不知,我這是在累積經歷。連日本的上班族都敢當,你還怕地獄嘛?這可是黃金也買不來的履歷,不出幾年,只要我還沒被操死,就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您說,是不是呀?
BOX---【?業(?????)】
加班,日文稱「?業」,這在日本各大公司是常態。戰後好一段時間,為公司不眠不休加班的日本上班族,建立了日本人勤奮認真的形象。同時,「過勞死」的事件頻傳,世人震驚,逼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對策洗刷惡名。對策之一,就是規定一個月工作超過一定時間(一百個小時),必須接受健康診斷。我在日本公司任職時,就有兩次眼見同事送去醫院接受診斷。
與日本昂貴的生活費相比,日本上班族其實收入並不高,一般而言,拿到手的薪資,九成以上都做家用,因此,「加班津貼」成了上班族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所以日本政府儘管三令五申禁止「過重勞動」,為了生活,恐怕日本上班族一時還無法享受這個德政。◆日本發生的「人身事故」
「人身事故」,這個詞,中文日文都有,意思也都相通。一旦有甚麼事件上升到「人身事故」的層次,那就是非同小可,不可能輕忽。畢竟人命關天,如果眼前發生了一件「人身事故」,依照人之常情,救死扶傷之不暇,哪可能等閒視之?
東京的電車經常傳出「人身事故」的消息。在日本是怎麼對待人身事故呢?車站內的電子告示板,打出短短幾行字:「XX線往○○方向因為人身事故的關係,現在停駛」,除此之外,再沒任何訊息。是誰?甚麼原因?自殺還是意外?死還是活?電視新聞不會報導,網上新聞也找不到。由於電聯車引起的「人身事故」的頻率太多,讓人不禁懷疑:是否連輕傷或車門夾到皮包,在日本都以「人身事故」視之,所謂「人身事故」其實只是虛驚一場?
我抱著疑惑,問了日本同事。同事的回答如下。
「虛驚一場?人和電聯車撞,還可能是虛驚一場?當然是非死即殘!」
「事故原因是?」我追問道。
「當然是自殺。」同事雲淡風輕地說著:「我還可以告訴你,東京的『中央線』死人最多,知道為甚麼嗎?」
「為甚麼?」
「因為路線直,車速快,死得快。」
同事替我解了部分疑惑。我想起每次在車站目擊「人身事故」四個大字時,感受不到車站人群表情上一絲絲躁動。大家如平時般上車、下車、等車。沒看到人們針對事件竊竊私語。「人身事故」四個原本份量很重的字,頂上的電子看板一打出,就如一陣風似地從人的頭上吹過,驚不起一點點波瀾。
是甚麼讓日本人這麼「淡定」?死人太多,所以麻木了?訓練有素,所以老僧入定了?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去年日本發生震災,東北死人無數,東京電車停駛,日本上班族回不了家,大家沉穩有序、面無表情地坐在每一個避難所等著疏散。面對泰山崩於前,這個民族仍能維持著集體的沉穩,確實讓我們外人感動。
但也有不近人情之處。
去年,我和兩個日本同事一起到東莞的一家日資客戶工廠出差,從事為期三個月的長期專案。我們工作的地點,就在客戶工廠二樓的一間會議室。
儘管是出差在外,但畢竟是跟著日本人來。日本人到哪,「日本空氣」就帶到哪。辦公室內,主管坐鎮在場,員工埋首辦公桌。專心工作之下,一個鐘頭也難得聽到有人開口講一句話。一次,我憋了三小時,試著打破沉默,離席上廁所前報告一聲:「我想排除體內多餘水分。」這種水平的冷笑話,在臺灣根本激不起一點點「反響」,但日本人聽來似乎很新鮮,我說完走向廁所,身後即傳來一陣大笑。日本人平時工作之沉悶由此可見。我們所在的這家日資客戶工廠,也照樣移植日本職場文化。早上九點一到,所有員工起立聽主管訓話,下午三點半一到,播放體操音樂。但這究竟是間上萬員工的工廠,平日不出點事情不太可能。工廠不時傳來一些「風波」,不是員工在外被人砍了,就是工廠原料被監守自盜。我們駐在的三個月裡,印象中就發生過四次騷動,連帶一次小火警。一有事件,二樓辦公室人事部、總務部的管理人員自然要出面處理,辦公室內鬧得人聲鼎沸、東張西望,不在話下,但基本上,這是客戶的工廠,我們身為客戶請來的顧問,儘管耳裡不時傳來客戶工廠的騷動,我們只需、也只許專心在自己的工作上。這對我這兩名日本同事不是難事,但對我是難事。
有看倌道:「老侯,我看你就是少一根筋!專心工作,為何日本人辦得到,你就辦不到?」
這位看倌有所不知。我的耳朵裡,不論傳來日本話或是中國話,我都得聽得懂。當一個廣東口音的員工大喊「起火了」、或者一個湖南口音的員工叫著「有人受傷了」,你能裝作甚麼也沒聽見,繼續專心工作嗎?
就拿那天發生的例子來說,客戶工廠一個已經被解雇的女員工,突然出現在公司辦公室,大吵大鬧地說自己「不甘心」。聲音傳到我們三個顧問這裡。我的耳朵如狗一般地反射動作豎了起來,但眼看左右日本同事沒動靜,再加上事不關己,豎起的耳朵又垂了下去。
「嗚~~」、「你們為甚麼這樣對我!」傳來的聲音一聲比一聲悽厲,哭訴的內容一個比一個悲慘。我不禁抱怨起來:我要是不懂中國話,不也就像眼前兩名日本同事一樣,心無旁鶩地專注工作嗎?現在外頭吵得淒淒慘慘,我偏偏憋了一肚子水,直想「出恭」洩洪。只是此時藉上廁所離席,恐怕會被日本同事視為「愛看熱鬧」,只有暫且忍著。
不久,外頭恢復平靜。客戶一名叫山口的日籍主管走進我們的會議室,一臉歉意地說:「對不起呀,剛剛那場鬧劇。」
「請問,是怎麼回事呢?」我的同事上田忍不住好奇,開口問道。
「唉,」山口嘆了口氣道:「那女的是管工廠保安的。她年紀太輕,管保安管不好,工廠連續發生了幾次工人偷原料到外面變賣的事情。我們看她做得不好,把她辭了。她跑來鬧,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上田追問:「現在她人呢?」
「我們把她請出去了。」
原來如此。東莞畢竟外來人口多,龍蛇雜處,外資企業在這裡打拚確實不易。但我沒心思想這些問題。日本人還對這個話題熱烈討論不已,我帶著肚裡接近1公升的水,先告退直奔廁所。直到我上廁所前,這事本來只是個小插曲。但就在我上廁所中,事情發生變化。
我面對著牆,站著洩洪,正漸入佳境時,廁所敞開的窗外,突然幽幽地傳進來女孩子的哭聲。原來這間工廠一樓入口處有個突出的鋼筋水泥屋簷,高度剛好到這間二樓廁所的窗臺下。女孩子不知道何時爬到了這屋簷上,站在那裡哭了起來。邊哭,邊像是在打電話:「媽,我對不起妳們。妳們把我養這麼大,我沒機會報答妳們了。嗚~~。」
我稍稍歪著頭看著窗外,隱約可見女孩子站在屋簷邊緣的背影。雖然是一樓的屋簷,但這間工廠,一樓高度就接近一般屋子的二樓。從一樓跳下去,只要決心夠,自殺身亡是絕對有可能。
廁所沒有其他人。我的洪還沒洩完,此時叫住女孩別跳樓,不很雅觀;但不叫住女孩,她若真跳下去,事情就嚴重了。我恨,既恨我尿多;又恨這廁所半天沒人來。
「算了!人連死的念頭都有了,還在乎死前看到啥嗎?小便讓人看到,就看到吧!救人要緊。」我將心一橫,一隻手維持正常洩洪,另一隻手伸出窗外揮,喊著:「您千萬別衝動!有甚麼委屈好好說!」
女孩子回過頭了,看了我一眼。
我歪著上半身、掩著下半身,模樣很是狼狽,嚥了一點口水,繼續說:「我是您們這裡的顧問,會說日文的。您有甚麼話,想和您領導溝通的,可以告訴我,我幫您轉達。」
我說完,不禁心裡悲從中來,就在剛剛,我成了地球上第一個小便時作自我介紹的「顧問」。
「你甚麼時候叫他們來?我要死給他們看!」
「別這樣,等我這邊…忙完了,我立刻叫他們來。有話好好說、好好說!」
正在說話時,一個男員工進了廁所,看到這景象,大吃一驚。
「你快叫你們山口先生、還有保安的人來吧!」我說著,剛好也洩洪完畢。男員工立刻奪門而出。我整理好褲子後,趕忙走到窗臺探出頭,繼續想辦法安撫那女孩。從女孩口音聽出她是湖南石門人(這家公司用了很多湖南同鄉),我用我懂得的湖南石門話勸她,穩住她情緒:「我們都是出外工作的,妳受的委屈我能懂,先別鑽牛角尖,好不好?」
女孩仍在哭。此時,山口、保安,還有人事部的人都趕來了。山口拜託我做翻譯,把公司的立場和女孩說清楚。
我翻譯完後,女孩哭著說:「你跟山口先生講,保安又不是我請來的,是公司自己聘來的,明明就不是我的錯,為何出了事情要算到我頭上?要我走也就算了,資遣費一毛也不給,我回老家總得要路費吧!」
我這下安心了。能具體講到錢上面,大概就不是個想死的人了。我把原話轉達給山口。山口爽快答應,要女孩先進來辦公室,其他則讓人事部去交涉。最終結果:人事部答應給她兩個月薪資、共八千元人民幣的「資遣費」,一場鬧劇總算收場。
我回到座位,埋首電腦中的同事見我回來,慢慢抬起頭來,好奇地問我:「你怎麼一泡尿要這麼久時間?」BOX──【人身事故】
如同很多人的感受,人命本來比甚麼都貴重,但眼見東京電車站打出「人身事故」的頻率越來越多、因「人身事故」而造成的交通中斷越來越多,人命再貴重,活著的人也會麻木,面對別人的死亡,從驚愕到淡定,這當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有人會說:怎麼向來不愛給人添麻煩的日本人,會在死的時候選擇跳軌,用數萬到數十萬人交通停滯的代價,來給自己生命畫上句號?
這問題不好回答,因為已死的人生前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活著的人已無法臆測。但是,如果仔細查一下在日本與自殺相關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的資料,日本每年在鐵軌上自殺死亡的人數,約五百到六百人,平均每天都會有人死在鐵軌上,這聽來已經很可怕了,但和全日本每年大約三萬人的自殺者相比,「跳軌自殺」還算是小宗哩。
確實,在鐵軌上自殺,身首異處,屍肉橫飛,對於注重形象的人而言,絕非「首選」。浪漫點的死法,則是到人煙罕至的漂亮林子裡上吊。這還吊出了一處「自殺聖地」:富士山的「青木原」。有一個叫做早野梓的作家,為了找寫作靈感,成天往「青木原」溜達,幾年下來,他一個人就在「青木原」見到了一百具自殺遺體。我在日本這麼久,儘管「人身事故」的告示成天在看,但親眼目擊的則是一個都沒有。您說,這跳軌自殺的「密度」,能算高嗎?
總之,一年要自殺三萬人,分五、六百人到鐵軌上,絕不算是突出。生死本是大事,但用數據來看,就是這麼冰冷的事。◆「開動了」嗎?
比起我們吃飯時,多半舉起筷子就吃,日本人開飯前的禮儀則是「熱鬧」多了。要動筷子前,日本人都會說一聲「??????(ITADAKIMASU)」,這句話,在現代中文中經常翻譯成「開動了」、「要吃了」,但總讓我覺得意思不到位。
「??????」能用的場面不少。在吃飯前說「??????」,是隱含著對主人盛情招待的謝忱,帶著些誠惶誠恐的味道;在與客戶對談中,用上「??????」,則是作為承受客戶物品(如文件)、小惠(如茶水招待)時的感謝語。中文的「開動了」,純粹單指一個動作,沒任何感謝的意味,硬是把這句情深意重的日語簡化成了一個口令。
所以,我主張在古文中找答案,把「??????」翻譯成「生受」。「生受」這個詞,出現在明清的章回小說中,相當頻繁。可見這在當時還是個日常用語。從前中國人在人家家中作客,進餐前與日本人一樣,口中說著「生受」,就是「叨擾您這一餐」的意思,禮數周到,表達的意思與日文的「??????」完全相同,翻譯起來可說是百分之一百到位。
當然,為了翻譯一個外文,而把一個死語復活,恐怕看官們很難接受。但在那之前,我們不妨想想:「生受」一詞的消失,再無替代語可用,是否也意味著我們本來的「禮儀之邦」在近百年內變得「人情澆薄」,如今只能禮失求諸野,眾口一致地誇獎日本人「有禮」?
最後要提的是,所謂禮多人不怪,「??????」的多用,大致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用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小心了。早年我學日語未久,曾試著對一個可愛的日本女孩子說道「??????」,原意是「希望你做我女友」,有些半開玩笑的意味。女孩子一怔,乾笑了幾下。後來,女孩子問我「是否想帶她去開房間」,我嚇得連忙否認,就差沒下跪求饒。事後才弄清楚:在日文裡,「生受」一個女孩子,就是整碗捧去,沒有柏拉圖的可能。
但對著餐飲說「??????」,依舊是百分之一百正確,共餐的女伴不會因此誤會。誤會了,就當是你賺到的。
到日本工作超過半年了。之前在日本工作,是在一家外商公司,週遭都是碧眼金髮的老外,幾乎沒怎麼和日本人接觸。這次再度來日本,情況不同了。這是一家道道地地的日本公司,日本同事「純度」之高,超乎想像。十個同事當中,看英文信不借助google翻譯的,不到兩個;有能力開口說英文的,不到半個;「S、T、V、X」能正確發音的,則是一個也沒有。搞得我暈頭轉向的,不是同事們英文不佳,而是日文太好!
話說,幾天前,我們開發了一個系統,交付客戶(位在香港的日商)作測試。當天,客戶就把測試報告交給我們。針對客戶回報的測試結果,我們要研商方法,一一排除問題,附帶解釋溝通。這要是在臺灣,打一通電話,或親赴現場,溝通了解一番,在客戶email認可下(留作證據)把問題一一解決。不能溝通的,則另開會議,決定是否要修改系統。一來一往,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就該交付另一個新系統版本。換成日本公司,慘了!客戶回報的問題,先按兵不動,信不回、電話不打,如臨大敵地逐項查明原因,還要研商會議計畫、確立會議目標、擬訂會議邀請函、決定參加人員名單、制定時間表。每一項,都是日文!
那天晚上,我從下午六點開始擬會議邀請函,我的主管兩眼盯著我,催我的進度。我小心翼翼擬好了信,發給了主管。主管看了,冷笑兩聲,說:「你要把信分三段,第一段,把這會議的背景說清楚;第二段,寫明會議的預定議程;第三段,告訴客戶我們附加了哪些文件。」
通常一封電子信寄到對方信箱,會被對方的郵件伺服器搞成甚麼模樣,完全無法預期。這廂辛苦排版,那廂面目全非,司空見慣。主管對信件、而且是一個會議邀請的信件,要求「格式美」,大出我意料之外。但主管既然要求,我只有照辦。廿分鐘後,我再把改好的信發給了主管。這回,主管看得面色鐵青,口氣一變,問我:「我跟你說的三段,你怎麼寫成了五段?」
「我...您交代的三段,我都寫進去了,我另外還附帶了招呼語,以及一些說明,比方說,希望能在開會前把參加人數弄清楚之類的,這就不知道該歸哪一段了,所以獨立出來。我想,信還沒發出去,還可以和您商量......」我戰戰兢兢地解釋道。
主管正色道:「你想自作主張前,先告訴我!三段要寫成五段,先告訴我!」
我被訓得無話可說,懊惱自己自作聰明,只得照辦。好不容易把信擬好,主管勉強認可了,但仍加了一句:「內容可以了,但還沒到能發出去的程度。我來修改吧!」我一聽,不禁心中暗自叫苦!搞了半天,剛剛折騰了三個小時,純粹只是要訓練我這老外的日文撰寫,最終,還是要老闆親自出馬寫這邀請函!!
往好處想,算是這主管願意栽培後進;往壞處想,這人簡直就是偏執狂了。主管把信擬好,再發給我,要我把附加文件貼上去後,定稿,再讓他過目,然後發出去。我想,這下總該脫離苦海了。貼好了文件,把格式再弄漂亮點,主管寫過的內容,一字不改,然後再發給主管作最終審核。
你道我這苦海脫離了嗎?不,沒脫離,而且好戲來了!
主管收到我的「最終定稿」,臉色由鐵青變成了糞青:「你動了我的格式?」
「我動了...我是看有的段落隔了兩行,有的段落隔了一行,想把格式統一一下,所以......」
主管面帶慍色道:「你再把我原來的信打開來看看!」
我的手,顫顫巍巍地打開了主管的原信,開始端詳。
「看出來了嗎?我信裡隔兩行和隔一行,有甚麼不同?」
我仍在端詳。但沒看出所以然。
「對不起,這兩行和一行的區別...真沒看懂。」
「你再看仔細!兩行上下的內容,和一行上下的內容,有甚麼不同?」
深夜十二點了,只剩我和主管兩人。我在東京,一棟人去樓空的大廈裡,拚命研究這兩行和一行的奧秘。腦子早非處於適合邏輯歸納的狀態,一切只能靠奇蹟。
二分鐘後,奇蹟出現了。「大概...兩行隔開的,代表大段落;一行隔開的,代表小段落...。」我提出我的新解,語氣完全沒自信。
主管總算點頭道:「這就對了!你把我格式弄亂了,要怎麼區別大段落小段落?」
豁然開朗後,我趕忙把兩行的歸兩行、一行的歸一行,重新發給主管,拍板定案後,傳給了客戶,心中默禱著:「但願客有時間、有雅興,能欣賞這兩行與一行的苦心孤詣呀...」。
六個多小時,只為了一封會議邀請信。看倌要是有耐心,這日本公司磨人的事情,多得不勝枚舉,我日後可以一一和各位分享。
日本人在程序,體面上的堅持,由此可想。我從這件小事上,充分理解了當年阪神大震災時,連日本媒體記者都趕到了,偏偏自衛隊遲遲不到的原因。不就是在人命關天的時刻,政府的某個官員,死抱著某個流程、堅持寫某個文件、緊守著分成三段或隔成兩行之類的莫名其妙的「程序正義」嘛!
如果是做一名觀光客,你會喜歡日本;作一名留學生,對日本印象也不會太差;但若是作一名日本上班族,企圖融入日本社會,那就省省吧!身為一個外人,你可以用純欣賞的眼光,喜歡日本的乾淨,有秩序,也可以喜歡日本人的有禮。但這美麗表象的背後,是靠著怎樣的森嚴紀律和一絲不茍,甚至要抹滅掉多少個性乃至人性,才能粉飾出來的?這哪是乳臭未乾的哈日族可以管窺得到的呢?
有看倌問道:「老侯,你也真奇怪。一肚子苦水,幹甚麼不回來?」這位看倌有所不知,我這是在累積經歷。連日本的上班族都敢當,你還怕地獄嘛?這可是黃金也買不來的履歷,不出幾年,只要我還沒被操死,就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您說,是不是呀?
BOX---【?業(?????)】
加班,日文稱「?業」,這在日本各大公司是常態。戰後好一段時間,為公司不眠不休加班的日本上班族,建立了日本人勤奮認真的形象。同時,「過勞死」的事件頻傳,世人震驚,逼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對策洗刷惡名。對策之一,就是規定一個月工作超過一定時間(一百個小時),必須接受健康診斷。我在日本公司任職時,就有兩次眼見同事送去醫院接受診斷。
與日本昂貴的生活費相比,日本上班族其實收入並不高,一般而言,拿到手的薪資,九成以上都做家用,因此,「加班津貼」成了上班族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所以日本政府儘管三令五申禁止「過重勞動」,為了生活,恐怕日本上班族一時還無法享受這個德政。◆日本發生的「人身事故」
「人身事故」,這個詞,中文日文都有,意思也都相通。一旦有甚麼事件上升到「人身事故」的層次,那就是非同小可,不可能輕忽。畢竟人命關天,如果眼前發生了一件「人身事故」,依照人之常情,救死扶傷之不暇,哪可能等閒視之?
東京的電車經常傳出「人身事故」的消息。在日本是怎麼對待人身事故呢?車站內的電子告示板,打出短短幾行字:「XX線往○○方向因為人身事故的關係,現在停駛」,除此之外,再沒任何訊息。是誰?甚麼原因?自殺還是意外?死還是活?電視新聞不會報導,網上新聞也找不到。由於電聯車引起的「人身事故」的頻率太多,讓人不禁懷疑:是否連輕傷或車門夾到皮包,在日本都以「人身事故」視之,所謂「人身事故」其實只是虛驚一場?
我抱著疑惑,問了日本同事。同事的回答如下。
「虛驚一場?人和電聯車撞,還可能是虛驚一場?當然是非死即殘!」
「事故原因是?」我追問道。
「當然是自殺。」同事雲淡風輕地說著:「我還可以告訴你,東京的『中央線』死人最多,知道為甚麼嗎?」
「為甚麼?」
「因為路線直,車速快,死得快。」
同事替我解了部分疑惑。我想起每次在車站目擊「人身事故」四個大字時,感受不到車站人群表情上一絲絲躁動。大家如平時般上車、下車、等車。沒看到人們針對事件竊竊私語。「人身事故」四個原本份量很重的字,頂上的電子看板一打出,就如一陣風似地從人的頭上吹過,驚不起一點點波瀾。
是甚麼讓日本人這麼「淡定」?死人太多,所以麻木了?訓練有素,所以老僧入定了?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去年日本發生震災,東北死人無數,東京電車停駛,日本上班族回不了家,大家沉穩有序、面無表情地坐在每一個避難所等著疏散。面對泰山崩於前,這個民族仍能維持著集體的沉穩,確實讓我們外人感動。
但也有不近人情之處。
去年,我和兩個日本同事一起到東莞的一家日資客戶工廠出差,從事為期三個月的長期專案。我們工作的地點,就在客戶工廠二樓的一間會議室。
儘管是出差在外,但畢竟是跟著日本人來。日本人到哪,「日本空氣」就帶到哪。辦公室內,主管坐鎮在場,員工埋首辦公桌。專心工作之下,一個鐘頭也難得聽到有人開口講一句話。一次,我憋了三小時,試著打破沉默,離席上廁所前報告一聲:「我想排除體內多餘水分。」這種水平的冷笑話,在臺灣根本激不起一點點「反響」,但日本人聽來似乎很新鮮,我說完走向廁所,身後即傳來一陣大笑。日本人平時工作之沉悶由此可見。我們所在的這家日資客戶工廠,也照樣移植日本職場文化。早上九點一到,所有員工起立聽主管訓話,下午三點半一到,播放體操音樂。但這究竟是間上萬員工的工廠,平日不出點事情不太可能。工廠不時傳來一些「風波」,不是員工在外被人砍了,就是工廠原料被監守自盜。我們駐在的三個月裡,印象中就發生過四次騷動,連帶一次小火警。一有事件,二樓辦公室人事部、總務部的管理人員自然要出面處理,辦公室內鬧得人聲鼎沸、東張西望,不在話下,但基本上,這是客戶的工廠,我們身為客戶請來的顧問,儘管耳裡不時傳來客戶工廠的騷動,我們只需、也只許專心在自己的工作上。這對我這兩名日本同事不是難事,但對我是難事。
有看倌道:「老侯,我看你就是少一根筋!專心工作,為何日本人辦得到,你就辦不到?」
這位看倌有所不知。我的耳朵裡,不論傳來日本話或是中國話,我都得聽得懂。當一個廣東口音的員工大喊「起火了」、或者一個湖南口音的員工叫著「有人受傷了」,你能裝作甚麼也沒聽見,繼續專心工作嗎?
就拿那天發生的例子來說,客戶工廠一個已經被解雇的女員工,突然出現在公司辦公室,大吵大鬧地說自己「不甘心」。聲音傳到我們三個顧問這裡。我的耳朵如狗一般地反射動作豎了起來,但眼看左右日本同事沒動靜,再加上事不關己,豎起的耳朵又垂了下去。
「嗚~~」、「你們為甚麼這樣對我!」傳來的聲音一聲比一聲悽厲,哭訴的內容一個比一個悲慘。我不禁抱怨起來:我要是不懂中國話,不也就像眼前兩名日本同事一樣,心無旁鶩地專注工作嗎?現在外頭吵得淒淒慘慘,我偏偏憋了一肚子水,直想「出恭」洩洪。只是此時藉上廁所離席,恐怕會被日本同事視為「愛看熱鬧」,只有暫且忍著。
不久,外頭恢復平靜。客戶一名叫山口的日籍主管走進我們的會議室,一臉歉意地說:「對不起呀,剛剛那場鬧劇。」
「請問,是怎麼回事呢?」我的同事上田忍不住好奇,開口問道。
「唉,」山口嘆了口氣道:「那女的是管工廠保安的。她年紀太輕,管保安管不好,工廠連續發生了幾次工人偷原料到外面變賣的事情。我們看她做得不好,把她辭了。她跑來鬧,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上田追問:「現在她人呢?」
「我們把她請出去了。」
原來如此。東莞畢竟外來人口多,龍蛇雜處,外資企業在這裡打拚確實不易。但我沒心思想這些問題。日本人還對這個話題熱烈討論不已,我帶著肚裡接近1公升的水,先告退直奔廁所。直到我上廁所前,這事本來只是個小插曲。但就在我上廁所中,事情發生變化。
我面對著牆,站著洩洪,正漸入佳境時,廁所敞開的窗外,突然幽幽地傳進來女孩子的哭聲。原來這間工廠一樓入口處有個突出的鋼筋水泥屋簷,高度剛好到這間二樓廁所的窗臺下。女孩子不知道何時爬到了這屋簷上,站在那裡哭了起來。邊哭,邊像是在打電話:「媽,我對不起妳們。妳們把我養這麼大,我沒機會報答妳們了。嗚~~。」
我稍稍歪著頭看著窗外,隱約可見女孩子站在屋簷邊緣的背影。雖然是一樓的屋簷,但這間工廠,一樓高度就接近一般屋子的二樓。從一樓跳下去,只要決心夠,自殺身亡是絕對有可能。
廁所沒有其他人。我的洪還沒洩完,此時叫住女孩別跳樓,不很雅觀;但不叫住女孩,她若真跳下去,事情就嚴重了。我恨,既恨我尿多;又恨這廁所半天沒人來。
「算了!人連死的念頭都有了,還在乎死前看到啥嗎?小便讓人看到,就看到吧!救人要緊。」我將心一橫,一隻手維持正常洩洪,另一隻手伸出窗外揮,喊著:「您千萬別衝動!有甚麼委屈好好說!」
女孩子回過頭了,看了我一眼。
我歪著上半身、掩著下半身,模樣很是狼狽,嚥了一點口水,繼續說:「我是您們這裡的顧問,會說日文的。您有甚麼話,想和您領導溝通的,可以告訴我,我幫您轉達。」
我說完,不禁心裡悲從中來,就在剛剛,我成了地球上第一個小便時作自我介紹的「顧問」。
「你甚麼時候叫他們來?我要死給他們看!」
「別這樣,等我這邊…忙完了,我立刻叫他們來。有話好好說、好好說!」
正在說話時,一個男員工進了廁所,看到這景象,大吃一驚。
「你快叫你們山口先生、還有保安的人來吧!」我說著,剛好也洩洪完畢。男員工立刻奪門而出。我整理好褲子後,趕忙走到窗臺探出頭,繼續想辦法安撫那女孩。從女孩口音聽出她是湖南石門人(這家公司用了很多湖南同鄉),我用我懂得的湖南石門話勸她,穩住她情緒:「我們都是出外工作的,妳受的委屈我能懂,先別鑽牛角尖,好不好?」
女孩仍在哭。此時,山口、保安,還有人事部的人都趕來了。山口拜託我做翻譯,把公司的立場和女孩說清楚。
我翻譯完後,女孩哭著說:「你跟山口先生講,保安又不是我請來的,是公司自己聘來的,明明就不是我的錯,為何出了事情要算到我頭上?要我走也就算了,資遣費一毛也不給,我回老家總得要路費吧!」
我這下安心了。能具體講到錢上面,大概就不是個想死的人了。我把原話轉達給山口。山口爽快答應,要女孩先進來辦公室,其他則讓人事部去交涉。最終結果:人事部答應給她兩個月薪資、共八千元人民幣的「資遣費」,一場鬧劇總算收場。
我回到座位,埋首電腦中的同事見我回來,慢慢抬起頭來,好奇地問我:「你怎麼一泡尿要這麼久時間?」BOX──【人身事故】
如同很多人的感受,人命本來比甚麼都貴重,但眼見東京電車站打出「人身事故」的頻率越來越多、因「人身事故」而造成的交通中斷越來越多,人命再貴重,活著的人也會麻木,面對別人的死亡,從驚愕到淡定,這當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有人會說:怎麼向來不愛給人添麻煩的日本人,會在死的時候選擇跳軌,用數萬到數十萬人交通停滯的代價,來給自己生命畫上句號?
這問題不好回答,因為已死的人生前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活著的人已無法臆測。但是,如果仔細查一下在日本與自殺相關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的資料,日本每年在鐵軌上自殺死亡的人數,約五百到六百人,平均每天都會有人死在鐵軌上,這聽來已經很可怕了,但和全日本每年大約三萬人的自殺者相比,「跳軌自殺」還算是小宗哩。
確實,在鐵軌上自殺,身首異處,屍肉橫飛,對於注重形象的人而言,絕非「首選」。浪漫點的死法,則是到人煙罕至的漂亮林子裡上吊。這還吊出了一處「自殺聖地」:富士山的「青木原」。有一個叫做早野梓的作家,為了找寫作靈感,成天往「青木原」溜達,幾年下來,他一個人就在「青木原」見到了一百具自殺遺體。我在日本這麼久,儘管「人身事故」的告示成天在看,但親眼目擊的則是一個都沒有。您說,這跳軌自殺的「密度」,能算高嗎?
總之,一年要自殺三萬人,分五、六百人到鐵軌上,絕不算是突出。生死本是大事,但用數據來看,就是這麼冰冷的事。◆「開動了」嗎?
比起我們吃飯時,多半舉起筷子就吃,日本人開飯前的禮儀則是「熱鬧」多了。要動筷子前,日本人都會說一聲「??????(ITADAKIMASU)」,這句話,在現代中文中經常翻譯成「開動了」、「要吃了」,但總讓我覺得意思不到位。
「??????」能用的場面不少。在吃飯前說「??????」,是隱含著對主人盛情招待的謝忱,帶著些誠惶誠恐的味道;在與客戶對談中,用上「??????」,則是作為承受客戶物品(如文件)、小惠(如茶水招待)時的感謝語。中文的「開動了」,純粹單指一個動作,沒任何感謝的意味,硬是把這句情深意重的日語簡化成了一個口令。
所以,我主張在古文中找答案,把「??????」翻譯成「生受」。「生受」這個詞,出現在明清的章回小說中,相當頻繁。可見這在當時還是個日常用語。從前中國人在人家家中作客,進餐前與日本人一樣,口中說著「生受」,就是「叨擾您這一餐」的意思,禮數周到,表達的意思與日文的「??????」完全相同,翻譯起來可說是百分之一百到位。
當然,為了翻譯一個外文,而把一個死語復活,恐怕看官們很難接受。但在那之前,我們不妨想想:「生受」一詞的消失,再無替代語可用,是否也意味著我們本來的「禮儀之邦」在近百年內變得「人情澆薄」,如今只能禮失求諸野,眾口一致地誇獎日本人「有禮」?
最後要提的是,所謂禮多人不怪,「??????」的多用,大致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用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小心了。早年我學日語未久,曾試著對一個可愛的日本女孩子說道「??????」,原意是「希望你做我女友」,有些半開玩笑的意味。女孩子一怔,乾笑了幾下。後來,女孩子問我「是否想帶她去開房間」,我嚇得連忙否認,就差沒下跪求饒。事後才弄清楚:在日文裡,「生受」一個女孩子,就是整碗捧去,沒有柏拉圖的可能。
但對著餐飲說「??????」,依舊是百分之一百正確,共餐的女伴不會因此誤會。誤會了,就當是你賺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