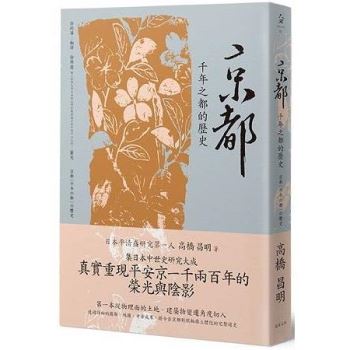第七章 作為形象的古都――江戶時代的京都
花之鄉
京都町奉行在第五代將軍綱吉執政期間,和老中、戡定頭(奉行)並列成為全國的幕府領地統治的最高責任人之一,但進入十八世紀以後地位不斷降低,到了享保七年(一七二二)時,統治範圍從畿內八國變為山城、大和、近江、丹波四國,其他地方成為大坂町奉行的支配國。其權限也被大幅縮減,僅限於處理民政。
此外,正如江戶琳派的成立所象徵的那樣,京都在美術與藝能方面的地位也逐漸受到了江戶的威脅。歌舞伎方面,在元祿時期(一六八八~一七○四)的江戶,荒事(主角為怪力勇猛的武士或非人類的鬼神等,表演形式粗暴誇張的武戲)與新興都市的風氣相吻合,備受歡迎,獲得了民眾的喜愛。與此相對,京都則繼承初期歌舞伎的傾城買(同遊女飲酒作樂)的狂言傳統,確立了和事(男女之間的愛戀、情事)的表演形式。這種劃分方式其實略為武斷,在京都地區也會上演武戲,江戶也有戀愛戲。但是在江戶頗具聲望的演員初代市川團十郎在京都演出的一年間,由於用詞過於粗暴,觀眾的反響並不好。
然而即使京都是歌舞伎的發源地,在十八世紀中葉隨著創造力的衰竭,其演出策劃能力、製作能力也逐漸下降。三都的歌舞伎相互競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只剩江戶與大坂兩極,京都所謂的復興也只是大坂歌舞伎分支一類的水平。慶長至寬文年間(一五九六~一六七三),是江戶時期京都最輝煌的年代。
安永(一七七二~一七八一)末期,出身旗本的江戶狂歌師二鐘亭半山來到了京都。在他所著的《京物語見聞》中,有「花之都已是兩百年前的往事,如今乃是花之鄉,作為鄉野倒尚顯風雅」的精彩描述。在江戶時代的後半期,京都雖然依舊「尚顯風雅」,但在江戶人看來已經完全淪落為鄉野了。
京都早就不再是政治中心,在經濟方面,由於河村瑞軒於寬文十二年(一六七二)改良了西向航線,以往從敦賀、小濱經由琵琶湖進入京都的日本海一側的物產,自此只要通過繞行日本海―關門海峽―瀨戶內海便可以直達大坂,京都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京都在金融和經濟面被大坂所超越,對於這種情況,「花之鄉」可以說是頗有狂歌師特色的辛辣評價。此外在寶永五年(一七○八)三月的大火中,京都有四百九十七個町、一萬四千間房屋被燒毀;天明八年(一七八八)正月的天明大火則燒毀了一千四百二十四個町,據說有三萬七千家的房屋在這場大火中化為灰燼。後一場火災對京都的地基下沉影響尤為嚴重。二○一一年東北大地震後,如何處理數量眾多的瓦礫成為災後重建的沈重任務,在沒有推土機和砂石車的江戶時代,災害後的瓦礫等無法被運到城外,只能在當場挖一個巨大的洞穴進行填埋。因此如今在發掘一些重要地點時,平安時代的遺址因垃圾掩埋場而被毀壞的狀況也並不少見。
天明大火也波及到了內裏和二条城等地。秀吉修建的內裏在文祿五年(一五九六)閏七月的大地震(文祿伏見地震)中受損,因此德川家康於慶長十六年(一六一一)開始著手修復,翌年完工。從此之後經過江戶時期共計八次的修建,內裏的面積擴大至接近原先的八倍,約是平安時代本內裏的一.七倍。
寬政二年(一七九○)的重建雖然遭遇了財政困難,但負責工程的老中松平定信迫於朝廷的強烈要求,在紫宸殿、清涼殿等部分殿舍中採用了舊制(平安末期)標準,將其建成了莊重而復古的御所。公家的裏松光世(法號固禪)回答了定信的諮詢,盡力重現平安時期內裏的樣式。竹內式部為國學家、神道家,寶曆八年(一七五八)在朝廷內部的主導權之爭中,被流放出京都(寶曆事件),固禪受此事牽連,被罷免了官職,自那之後蟄居三十年,期間埋頭於創作《大內裏圖考證》等著作,對平安京大內裏殿舍的位置、構造、沿革等進行了考證。
從這一時期開始,為了彌補京都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落後,人們開始大力關注起京都作為王城之地的歷史。平安遷都已是千年之前這一事實,將會催生宣傳京都為「千年之都」的趨勢,與觀光旅遊相結合,最終成為振興城市的力量。
名勝導遊記
在近世文藝的種類當中,有名為「名勝導遊記」的一眾地方志。其中很多作為出版品,為眾多的同時代人所閱讀。「京都名勝」系列出版了許多冊,近世初期的「導遊記」是一種「讀物」,其特徵因此古典教養為基礎的名勝觀,使人通過閱讀就能在家中感受到京都之美(圖7-5)。名勝不單單只是風景之美,而是要確立一種模式化的形象,激發人們對世事的聯想和對人類社會中發生的各種事件的思考。名勝是富有意義並成為一種觀念象徵的地名。從這個意義上看,比起親自去參觀京都,接連出版的名勝導遊記實際上更具有滲透人們的觀念與精神的作用。這樣一來,京都的古都形象就滲透進未曾見過京都的其他地方的人心中,並不斷地層層加深。
古都形象的誘惑遠不止於知識。一六八○年前後是一個分水嶺,「京都名勝」逐漸變為了「實用書」。例如,後者的初期作品中有寶永五年(一七○八)刊行的《京內觀光》。書中介紹了以三条大橋為起點,用三天遊覽八十二處名勝的旅遊攻略。一天的移動距離為二十公里,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完全力所能及的距離。第一天從知恩寺出發,途經東山山麓到達清水寺,可遊遍南北方向的廣闊地區;第二天為京內、東西本願寺、三十三間堂、東福寺、伏見稻荷;最後一天為下鴨、上賀茂、大德寺、北野天滿宮、金閣寺、二条城,行程非常豐富。今天的觀光景點基本上都已網羅其中。
無論在哪個時代,旅行的自由都能使人們從社會制度的壓抑與人際關係的煩惱中暫時解脫出來。江戶中後期,旅行的條件及理由都已具備。京都匯集了佛教各宗派的總寺院和寺院,能夠吸引全國的信徒與門徒前來。同時頻繁舉辦的宗派奠基、開山遠忌以及本山秘佛、秘寶的開龕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兼備觀光與拜佛、參拜神社的京都觀光就這樣誕生了,旅行者可以盡情享受京都的名勝和四季之美。這種觀光在當時被稱為京內參拜或京內參詣。
觀光客和遠忌參加者帶回故鄉的特產是「京」的名產。川柳中也寫道:「語畢再送京土產」(《柳多留》)。特產以傳統手工業技術為基礎,包括觀光客用的陶瓷器、扇子、人偶、佛壇、袋子、香粉、胭脂、點心等。這些產品上一定冠有商標「京」的字樣,先不論特產質量的好壞,每件特產都在傳遞著「雅」的形象。
花之鄉
京都町奉行在第五代將軍綱吉執政期間,和老中、戡定頭(奉行)並列成為全國的幕府領地統治的最高責任人之一,但進入十八世紀以後地位不斷降低,到了享保七年(一七二二)時,統治範圍從畿內八國變為山城、大和、近江、丹波四國,其他地方成為大坂町奉行的支配國。其權限也被大幅縮減,僅限於處理民政。
此外,正如江戶琳派的成立所象徵的那樣,京都在美術與藝能方面的地位也逐漸受到了江戶的威脅。歌舞伎方面,在元祿時期(一六八八~一七○四)的江戶,荒事(主角為怪力勇猛的武士或非人類的鬼神等,表演形式粗暴誇張的武戲)與新興都市的風氣相吻合,備受歡迎,獲得了民眾的喜愛。與此相對,京都則繼承初期歌舞伎的傾城買(同遊女飲酒作樂)的狂言傳統,確立了和事(男女之間的愛戀、情事)的表演形式。這種劃分方式其實略為武斷,在京都地區也會上演武戲,江戶也有戀愛戲。但是在江戶頗具聲望的演員初代市川團十郎在京都演出的一年間,由於用詞過於粗暴,觀眾的反響並不好。
然而即使京都是歌舞伎的發源地,在十八世紀中葉隨著創造力的衰竭,其演出策劃能力、製作能力也逐漸下降。三都的歌舞伎相互競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只剩江戶與大坂兩極,京都所謂的復興也只是大坂歌舞伎分支一類的水平。慶長至寬文年間(一五九六~一六七三),是江戶時期京都最輝煌的年代。
安永(一七七二~一七八一)末期,出身旗本的江戶狂歌師二鐘亭半山來到了京都。在他所著的《京物語見聞》中,有「花之都已是兩百年前的往事,如今乃是花之鄉,作為鄉野倒尚顯風雅」的精彩描述。在江戶時代的後半期,京都雖然依舊「尚顯風雅」,但在江戶人看來已經完全淪落為鄉野了。
京都早就不再是政治中心,在經濟方面,由於河村瑞軒於寬文十二年(一六七二)改良了西向航線,以往從敦賀、小濱經由琵琶湖進入京都的日本海一側的物產,自此只要通過繞行日本海―關門海峽―瀨戶內海便可以直達大坂,京都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京都在金融和經濟面被大坂所超越,對於這種情況,「花之鄉」可以說是頗有狂歌師特色的辛辣評價。此外在寶永五年(一七○八)三月的大火中,京都有四百九十七個町、一萬四千間房屋被燒毀;天明八年(一七八八)正月的天明大火則燒毀了一千四百二十四個町,據說有三萬七千家的房屋在這場大火中化為灰燼。後一場火災對京都的地基下沉影響尤為嚴重。二○一一年東北大地震後,如何處理數量眾多的瓦礫成為災後重建的沈重任務,在沒有推土機和砂石車的江戶時代,災害後的瓦礫等無法被運到城外,只能在當場挖一個巨大的洞穴進行填埋。因此如今在發掘一些重要地點時,平安時代的遺址因垃圾掩埋場而被毀壞的狀況也並不少見。
天明大火也波及到了內裏和二条城等地。秀吉修建的內裏在文祿五年(一五九六)閏七月的大地震(文祿伏見地震)中受損,因此德川家康於慶長十六年(一六一一)開始著手修復,翌年完工。從此之後經過江戶時期共計八次的修建,內裏的面積擴大至接近原先的八倍,約是平安時代本內裏的一.七倍。
寬政二年(一七九○)的重建雖然遭遇了財政困難,但負責工程的老中松平定信迫於朝廷的強烈要求,在紫宸殿、清涼殿等部分殿舍中採用了舊制(平安末期)標準,將其建成了莊重而復古的御所。公家的裏松光世(法號固禪)回答了定信的諮詢,盡力重現平安時期內裏的樣式。竹內式部為國學家、神道家,寶曆八年(一七五八)在朝廷內部的主導權之爭中,被流放出京都(寶曆事件),固禪受此事牽連,被罷免了官職,自那之後蟄居三十年,期間埋頭於創作《大內裏圖考證》等著作,對平安京大內裏殿舍的位置、構造、沿革等進行了考證。
從這一時期開始,為了彌補京都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落後,人們開始大力關注起京都作為王城之地的歷史。平安遷都已是千年之前這一事實,將會催生宣傳京都為「千年之都」的趨勢,與觀光旅遊相結合,最終成為振興城市的力量。
名勝導遊記
在近世文藝的種類當中,有名為「名勝導遊記」的一眾地方志。其中很多作為出版品,為眾多的同時代人所閱讀。「京都名勝」系列出版了許多冊,近世初期的「導遊記」是一種「讀物」,其特徵因此古典教養為基礎的名勝觀,使人通過閱讀就能在家中感受到京都之美(圖7-5)。名勝不單單只是風景之美,而是要確立一種模式化的形象,激發人們對世事的聯想和對人類社會中發生的各種事件的思考。名勝是富有意義並成為一種觀念象徵的地名。從這個意義上看,比起親自去參觀京都,接連出版的名勝導遊記實際上更具有滲透人們的觀念與精神的作用。這樣一來,京都的古都形象就滲透進未曾見過京都的其他地方的人心中,並不斷地層層加深。
古都形象的誘惑遠不止於知識。一六八○年前後是一個分水嶺,「京都名勝」逐漸變為了「實用書」。例如,後者的初期作品中有寶永五年(一七○八)刊行的《京內觀光》。書中介紹了以三条大橋為起點,用三天遊覽八十二處名勝的旅遊攻略。一天的移動距離為二十公里,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完全力所能及的距離。第一天從知恩寺出發,途經東山山麓到達清水寺,可遊遍南北方向的廣闊地區;第二天為京內、東西本願寺、三十三間堂、東福寺、伏見稻荷;最後一天為下鴨、上賀茂、大德寺、北野天滿宮、金閣寺、二条城,行程非常豐富。今天的觀光景點基本上都已網羅其中。
無論在哪個時代,旅行的自由都能使人們從社會制度的壓抑與人際關係的煩惱中暫時解脫出來。江戶中後期,旅行的條件及理由都已具備。京都匯集了佛教各宗派的總寺院和寺院,能夠吸引全國的信徒與門徒前來。同時頻繁舉辦的宗派奠基、開山遠忌以及本山秘佛、秘寶的開龕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兼備觀光與拜佛、參拜神社的京都觀光就這樣誕生了,旅行者可以盡情享受京都的名勝和四季之美。這種觀光在當時被稱為京內參拜或京內參詣。
觀光客和遠忌參加者帶回故鄉的特產是「京」的名產。川柳中也寫道:「語畢再送京土產」(《柳多留》)。特產以傳統手工業技術為基礎,包括觀光客用的陶瓷器、扇子、人偶、佛壇、袋子、香粉、胭脂、點心等。這些產品上一定冠有商標「京」的字樣,先不論特產質量的好壞,每件特產都在傳遞著「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