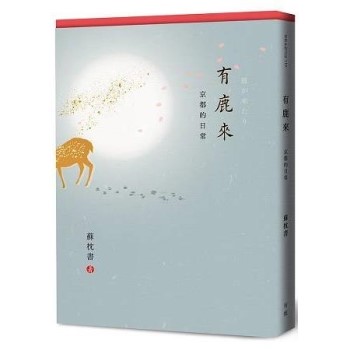緣起
某夜,無意中看到新聞,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掐死了同居女友的三個月大的孩子。「看到女嬰痛苦的樣子,很有快感,死了也沒關係。」相關新聞中,還有一串此年發生的類似事件:十九歲的女學生產下孩子,覺得麻煩,便將其扔到壁櫥裡任之死去;二十二歲的女子因為沒錢,將剛生下的孩子放置死去;二十歲的母親生下孩子沒多久便將之遺棄——這些令人心寒的內容,竟呈現出歷史上最黑暗時期的麻木感。可見戰爭與和平之間,也有某種令人震撼的相似性。人心本易趨死寂,苦難之後,煥然重建,激盪一陣,又趨麻木。一位剛結婚的朋友,丈夫失業,不願出門,也懶得領低收入戶補助,每日但憑妻子打零工所得勉強維生。近來妻子懷孕,夫婦都極為苦惱,不知如何養活孩子。想到「無緣社會」,默默死去的,不單是孤獨的老人,還有孤獨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幼小的孩子。這些思考—不,算不得思考,只是平凡生活中一點輕浮的感嘆,無暇深入,散珠一樣滾落在幽暗角落,懶得撿起來。
年歲漸長,時常懷疑寫作的意義。自己沒有什麼長進,這是最清楚不過的。長時間與自己周旋,呈現平靜的假象。痛苦的源頭,也許是認識到自己的貧乏與無趣。不,不是這樣的,有一瞬想辯解的欲望,但沒有任何意義。為什麼有這麼多懷疑?如自己這般愚鈍的人,並不該有這麼多懷疑。無法妥善處理自己許多可笑的想法。所有痛苦與衝突,不會有出口。我知道這沒有出口,因此沉默是好的。
那麼現在,為什麼又要寫點兒什麼?時常,一些外來刺激,或曰觸動,就能燃起書寫欲。看到某人寫的書,想:「啊,我也想寫呢!」這種蠢蠢欲動、激情與焦慮混雜的感覺,寫作的人最清楚不過。可惜真要動筆,又有很多理由阻撓:太忙、找資料太費勁、沒感覺。在習以為常的環境裡生活慣了,也很難有動力寫作。我對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同情並不樂觀。每個人對於生命、生活、城市都有獨特的感知,而我為何要不厭其煩地記錄這些沒有意義的情緒、無足輕重的瑣事? 如果寫下來,又何必要公諸於眾,徒然打擾讀者?去年秋天,有一位朋友從北京來到京都,我們在同一個研究室相處了半年。她十分能享受京都之美、京都之樂,古本屋、舊書市、居酒屋、庭園、寺社、美食、秋天的紅葉、冬天的大雪、清池的錦鯉、鴨川沿岸永恆又稍縱即逝的風景—她都喜愛,並敏銳地把握了最關鍵處。我們一起喝過很多回酒,有非常快樂的回憶。有時候,一起到某個地方,我也忍不住告訴她一些可有可無的背景與細節。她的好奇心令我大為感動,給我很大的信心。寫點兒什麼吧,至少可以給她看,以此紀念我們在京都共處的愉快時光,並將她未曾來得及親自體會的京都的種種傳遞過去。
某日,去老師的研究室喝酒,那是一小罐我去年泡的梅酒。老師翻到一篇我剛寫的小文:「你把京都寫得很美,讀書生活也寫得不錯。」停頓道,「不過,這還不夠。瑣碎的、不好的、不愉快的,你也要寫。」是的,我又要寫大家很熟悉的京都了。有 太多人寫過京都,種種禮讚、旁觀、走馬看花,都使讀者產生了對京都的強烈興趣。我自己也是如此,因為讀了幾頁《枕草子》、《源氏物語》,才對京都抱有朦朧的幻想。兩年前,我寫過一篇很短的〈京都第五年〉,轉眼已是「第七年」。對於日常生活,似乎什麼都不必提,然而真要說些什麼,又千頭萬緒。數年前的初秋,第一次在車窗內望見夕光籠罩下東寺的五重塔,望見水草豐茂的鴨川,難免激動:「啊,就是這裡。」如今,雖已對此地習以為常,但從外地回來時,見到東寺的五重塔和流水不息的鴨川,還是會有一種十分清晰的安心感:「我回來了。」不過,旅人的身分與視角無法改變,因此我能寫的,仍只是客居者的日常。在這裡搬過三次家,如今住在銀閣寺前,附近有條小路,曰鹿ケ谷通。常被問:「真有鹿?」是的,據說平安時代比叡山的僧人元珍在此險要迷路,幸有鹿的指引。現在路上當然沒有鹿,但在不遠處的東山,就常有鹿的影子。山裡動物很多,此外還有蛙、蜥蜴、狸貓、鼯鼠、蛇、野豬、猴子、狐狸。大部分我都見過,最怕蛇,有時草叢一陣窸窣,嚇得汗毛直豎,牠們往往也溜得飛快。有寶藍色蜥蜴,非常漂亮,轉眼間就消失了。野豬可怕,幸好暫未會面,只在山中聽過號叫。山鹿就像精靈,曾見母鹿領小鹿出來喝水,見人輒驚走,與奈良公園跟人混熟了的鹿完全不一樣,牠們清瘦機警,烏黑的眼睛特別大。
鴨川也有鹿,時而從附近山裡下來喝水。曾在月夜看到母鹿領小鹿在水邊,波光清淺,水草蓊鬱,不似人間。在岸上望著,大氣都不敢出,唯恐驚擾。有時意識到人的存在,牠們就會飛奔離開。也有膽大的,白天出來散步,在淺水中央走,與白鷺、野鴨、老鷹、烏鴉共處。岸上的人擔心牠走到深水裡,被激流沖走,就在岸邊遙遙跟著。最終大概還是回到山中去了吧。
去年初夏,放學回來的夜裡,漫天星辰,涼風可喜。遂往屋後山坡散步。四圍靜寂,人家燈火已暗。忽聞群犬爭吠,又聞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完全猝不及防地,眼前轉角處竟剎那現身一頭大鹿,鹿角巍巍,前蹄騰起,健壯貌美。似乎有一瞬對視,我驚呆,鹿也驚呆,飛快回身,消失在黑暗山影中,復一片犬吠。待我回過神,追去兩步,早已行跡杳然。
就從這裡說起吧。銀閣寺前
京都很多著名的景點,都是我在頭兩年還懷著「興致勃勃的遊客」心態時逛完的。後來漸生出「本地人」的懶惰與矜持,不再出去亂跑,也難有時間出門。日常活動範圍變得極窄,最熟悉、最親切的,是銀閣寺到百萬遍一帶;跨過鴨川去同志社,就覺得好遠;走到丸太町通,便覺車水馬龍,已失去向前走的動力;河原町三四条是城裡,每番進城,看到街上妝容精緻、衣裝明麗的姑娘,尤覺賞心悅目,偶爾也想效仿,打起精神提高「女子力」,但一回到百萬遍,看到樸素的本校女生,就覺得特別安全,何況男生更加樸素;若去京都車站,那就是出遠門;去大阪? 簡直就像出國。因此在這裡住久了,回北京最不習慣的,就是城市空間感。從朝陽到海澱,到豐台,都有出國的感覺。
雖然住在景區,回家的小徑與去銀閣寺的觀光小道僅隔一排店面,但住處與景區卻涇渭分明,遊客也絕無興趣拐進這條平常的小徑。疏水道旁的櫻樹下、銀閣寺前的小橋頭,常年有笑容明亮、肌肉健美的人力車夫招徠生意,他們也是京都發達的旅遊業不可或缺的一環。剛搬來時,走出門,常會被當成遊客招呼。後來臉熟了,他們就會非常熱情地打招呼:「早安!路上小心!」有時他們正在樹下吃便當,也會放下筷子給我一個溫柔的笑臉。我沒有坐過這樣洋氣的車,也不好意思讓人拉著走。有幾回傍晚,薄暗的暮色裡遇到人力車,車前已掛起古樸長燈,隨著車夫的步伐悠然晃動。車上坐著一對情侶,或夫妻,或母女,膝上蓋著紅毯。車夫一邊慢跑,一邊滿含笑意地介紹沿途風景。有一回,一連過來五六輛車,每一輛坐兩位盛裝老太太,滿頭銀絲,和服的顏色嬌軟清柔,非常好看—原來是同一個花道協會的老朋友出來賞花。每年三月末,風突然變得極溫暖,大晴天,櫻花迅速漫開。最盛的幾天,家門口的哲學之道上擠滿了人,牽枝拍照,折花留念,不時有特意穿著明麗和服的姑娘翩然而過,還有盛裝的新人在花下聽從攝影師指點,熱鬧極了。17號、100號公車將大批遊客送至「銀閣寺道」、「銀閣寺前」這兩站。白川通與今出川通交叉處的東北角,有一塊「哲學之道」的路牌,因此很多人誤以為旁邊的公路就是哲學之道,常年都有人與這塊牌子合影。常聽有人說:「這裡就是哲學之道哦,好漂亮。快來拍照片。」更有匆忙的遊人,走到這裡,跟牌子合了影,便匆匆趕赴下一站。
上學途中,騎車路過花樹下的心情,與特地來賞櫻的人肯定不同。很想停車看會兒花,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很快就騎過去了。等走到僻靜的吉田山中時,又想:「明天一定要多看會兒,不然都該落了。」我的朋友香織一家對櫻花的心情也很微妙:「盛開就等於凋零,實在慘澹。況且天氣乍暖,懶洋洋,提不起精神。」這大概就是惜春與傷春。
銀閣寺前的小道兩邊,有許多景區特有的小店,金閣寺前、清水寺前、仁和寺前及嵐山都有這樣洋溢的風情,有烏冬麵店、蕎麥屋、醃菜店、抹茶霜淇淋店、茶店、和菓子「八橋」店等等。八橋是京都隨處可見的點心鋪,井筒八橋、本家西尾八橋、聖護院八橋……派系眾多,和很多老鋪一樣,有本家、分家之別。不過不用管,買一盒八橋在手,就是典型的京都遊客了。西尾家十分慷慨,善於革新,毫不吝嗇地擺出大量試吃盤,還提供免費熱茶。遠遠就能聽見店裡姑娘非常溫柔的召喚:「不用客氣,請進來嘗一嘗吧!」飽飽地試吃各種口味的八橋,是很多來京都修學旅行的孩子們美好的回憶。我的學長學姊們,談起來也很懷念:「什麼時候再去試吃吧!」銀閣寺很小,背後小山名月待山,可以想像坐在廊下,等待月光照亮銀沙灘的情景。這番妙處,我們都體會不到,因為黃昏銀閣寺就關門了。下午五點左右,遊客陸續散去,兩旁店鋪紛紛拉下捲簾門,合上門板。打工的姑娘們換下和服,拎著東西回家了,能聽到她們與店主極其熱切、誠懇的道別聲:「辛苦啦! 明天再見!」重複很多回,不停地鞠躬。不過多時,小街清場一般寂靜,只有附近放學的學生三三兩兩地路過。遛狗的人也零星出現了,有位老奶奶,養了兩隻柴犬,一隻叫茶茶,一隻叫櫻,人見人愛。櫻可以任意撫摸,茶茶則不可褻玩。「所以才叫茶茶呀。」老奶奶解釋。這個名字,自然是源自豐臣秀吉的側室、淺井三姊妹的大姊,她是日本戰國時期著名的美人。據說曾有京大學生夜裡翻牆進銀閣寺。月亮升起來的時候,一定很美。樸素的鳳凰堂,也與月光相宜。月待山這個名字,實在很不錯。
銀閣寺旁,有一座很小的淨土院,門前種著紫珠草(日人呼曰「紫式部」),遊客極少光顧。但該寺管理著八月十六夜五山送火之一「大文字」,故有「大文字寺」之稱。這一帶的居民組成了「大文字保存會」,共同完成點火的任務。狹窄的寺內花木扶疏,有山茶、臘梅、茱萸、木賊、白玉蘭、四照花、繡球、碗蓮,四季不斷。本堂供奉等身阿彌陀如來像,還有一尊丹後局人像。丹後局名高階榮子,曾嫁平業房,後為後白河法皇的寵姬,與源賴朝也有親密關係。據說她熱衷政治,與法皇育有六子。後來失勢,法皇去世後即出家為尼,歸隱淨土寺,即淨土院的前身。有時在家待了一天,黃昏想去散步,就到淨土院看會兒花。某日貪看碗蓮,回過神時,院門已落鎖,殿內也無人,只好坐在廊下等。頭頂一方狹窄天空,流動層雲被夕光染作金赤,又緩緩浸透深藍夜色。樹梢摩挲,蚊蟲開始活躍。終於有一位婦人走過,驀地看到我,很驚詫的樣子,愣了一秒,連聲道歉,開門將我放了出去。
生協買書
某先生說,這本書,你不要寫舊書店,不是專門寫過一本嗎?因此,我在盡量克制講舊書店的欲望,雖然對我來說,那是極大的樂趣,也是最熟悉的範圍。不過,我仍忍不住想講生協的書店—那是新書店,不算犯規。生協書店是生活協同組合(即生活合作社,簡稱「生協」)下屬的書店,在校學生加入生協後,買書可打九折。日本書店極少打折,生協的優待是學生特有的權利。書店在本部校區西側的體育館旁,平時經常去逛。雖然有些書在舊書店能以稍低的價格入手,但逛新書店自有不可替代的樂趣。書本的擺放方式,包括新上架的圖書,都凝聚了店員許多心血。醒目的專區一直在把握潮流,譬如山崎豐子去世後,專區立刻就擺出其作品專輯。去年校長換屆,新校長山極壽一是著名的人類學家、靈長類學者,有「大猩猩研究第一人」之譽。專區也很應景,隨即擺上生物學、大猩猩研究類圖書,以示慶賀。
近來書店主題是「西博多與分類學研究」,專區便擺出大量植物分類學、動物分類學、博物學的圖書,且為八五折。有一本大場秀章編的豪華大冊《櫻花圖譜》,纖毫畢寫,宏博精美,又有西博多編輯的《日本植物誌》,令喜愛植物的我難以自拔。不過我最後還是理智地只買了兩本資料書:威爾弗里.布朗特(Wilfrid Blunt)的《植物圖譜的歷史》及《西博多日記》。西博多的經歷和精力均極豐富,著述極多,這也是為什麼我雖然對他很早就感興趣,卻至今一篇文章也沒寫出來的緣故——在盡可能地把握資料之前,根本不敢下筆。
生協書店雖不大,但盡量照顧到各學科,圖書種類很豐富。觀察不同群體的讀者很有意思。科技雜誌區的宅男,女性雜誌區的小姑娘,法律區的未來的經營管理人士,還有在文史一帶遊蕩的奇人,不同專業的人常有不同的氣質。
我很愛買辭典,雖然使用率不高。比如小川環樹編角川書店《新字源》、岩波書店《國語辭典》、三省堂《全譯讀解古語辭典》、雄山閣《假名連綿字典》。有時也會去看看天文、生物圖冊。若在非專業區遇到熟人,有時會略顯窘迫,因為暴露了自己的閱讀習慣與惡趣味。逛書店是很奢侈的事,我指的是時間。浮光掠影般地邂逅許多有趣的書名、精采的封面,隨便翻兩頁,某種新興趣輕易就被點燃了,要是缺乏定力與判斷力,很容易被誘惑。但我無法抵禦這種引誘,在書店泡了大半天,不買點兒什麼回去,是絕對不會甘心的。實在想不到買什麼,就去文庫本區域,至少可以買那些經典譯著。有幾位學長總嫌棄早些年的翻譯:「翻譯得實在不好,讀不懂。為什麼會讀不懂?因為明治年間的讀書人,就以硬讀讀不懂的書為傲。」這在《日本讀書論》中已詳細論及。現在,我讀英文文獻很慢,多半仰賴日文翻譯。時常痛感自己的困乏,內心深處有不明所以的躁動,發出焦灼枯渴的呼喚,因外界侵擾而深感絕望,過度的敏感使我頻繁經歷情緒波動所帶來的困擾。這種時候,混亂的頭腦亟需重構秩序,讀書無疑是最好的選擇。我知道自己的感慨與痛苦都非常淺薄,前人一定早有精采的解釋及論述,幫助我釐清思緒,平復心情。有時翻到某些書,雖是全然不了解的陌生領域,卻能意外地觸動思考,帶著這點兒新鮮感,再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又有了新的認識與感受。
不過,外國作者名的中文、日文譯法不同,二者都是直接音譯,有的能一下認出來,有的則差別很大,要聯繫書名才能反應過來是誰。這種時候我又痛切地認識到精通原文的必要性,然而受精力、智力之限,至今都在語言隔閡的桎梏下掙扎。小時候讀過一些名著,最早接觸的文學作品,或者說自我選擇的作品,這對我此後的審美取向、閱讀趣味,乃至人生觀,都產生了至為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固然有積極的一面,令我沉溺於某一類風格的深邃之美、永恆的憂鬱及悲觀之中,但這種強大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思維定勢,或者說被某種無形卻無處不在的﹁印象﹂籠罩,使我在閱讀其他作品時受到某些先入觀的干擾。不管我生吞活剝多少西方譯著,都始終沒有捕捉到一二真髓。那些句式、人名、地名,是我完全陌生的,我拚命看,也無法理解,就像隔著蒙上霧氣的玻璃,以為自己看到了什麼,卻永遠朦朧,難以總結任何感想。對於這種閱讀障礙,我深感痛苦。生協書店南側的西部講堂,有著異常激盪的歷史。巨大的屋頂上有三顆獵戶座黃星,曾被塗成紅色,見證了左翼青年們的激情歲月。昭和天皇去世次日,據說這裡還舉行了相當熱鬧的﹁cry day event﹂,試圖打破天皇家葬禮的壓抑氣氛,畢竟,這不應該成為限制國民自由的理由。有各種演出,還有電影播放,並以焚燒日本國旗隆重收場,由此驚動了警備隊。如今,京大生對政治很淡漠,二○一四年秋,便衣公安員警入校的騷動發生後,周圍埋頭學術的好學生、積極進取的未來精英多有這樣的評價:「不知道什麼情況。」「那些學生看起來也不像學生,是專門搞政治的吧。」想必他們對這些事情抱有本能的懷疑與敬而遠之的態度,我了解很少,也無法多談。
生協書店以北有體育館,每到學期末,就有本科生組成的啦啦隊排演,從音樂到舞姿都非常青春熱血。羅森(Lawson)便利商店隔壁有家和菓子店,名叫「かぎや政秋」,我最常在那裡買叫「野菊」的杏仁味點心,是「落雁的一種,口感類似雲片糕或薄荷糕,小小的圓圓的,不知不覺就吃掉了。青木正兒寫過《落雁與白雪糕》,是篇「很好吃」的文章。「落雁」名字好,據說做法源自明代的軟落甘,大概是麵粉蒸熟,微乾後磨粉,曬乾微炒,用糖水浸泡,入模壓緊。初夏有柚子餅,蒻竹葉包裹,繫金線,甘香柔軟。求肥餅常年都有,名字很有趣,是米粉加砂糖或麥芽糖漿熬製的點心,很軟,雪莓娘即其變種。
生協書店以東,街對面,是大學綜合博物館,定期會更換主題,本校學生不必買門票。常設展分自然史、文化史、技術史三塊。自然史展廳有大量昆蟲、植物標本,文化史展廳有古石棺、古器物、古文書,技術史展廳有我完全不了解的精密儀器。自然史展廳光線幽暗,路過恐龍骨架,不時響起恐龍號叫的音效,還有隆隆的雷聲。去年有一場叫「海」的特別展,講某課題組研究海龜一日二十四小時、一年四季的作息規律及活動範圍,吸引了很多小朋友。課題組人員還在海龜身上綁了微型攝影機,拍到海龜求愛、交配的畫面。留言牆上貼滿了觀眾的感想小紙片,好幾個人都畫了背著攝影機的海龜,有位小朋友善用雙關,給「カメラマン」(攝影師)的「カメ」(龜)標了著重號,很萌。在生協食堂吃完飯,去樓下書店買幾本書,到點心鋪買一盒﹁秋菊﹂,再去博物館轉一圈,是難得清閒時固定的遊樂路線。
某夜,無意中看到新聞,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掐死了同居女友的三個月大的孩子。「看到女嬰痛苦的樣子,很有快感,死了也沒關係。」相關新聞中,還有一串此年發生的類似事件:十九歲的女學生產下孩子,覺得麻煩,便將其扔到壁櫥裡任之死去;二十二歲的女子因為沒錢,將剛生下的孩子放置死去;二十歲的母親生下孩子沒多久便將之遺棄——這些令人心寒的內容,竟呈現出歷史上最黑暗時期的麻木感。可見戰爭與和平之間,也有某種令人震撼的相似性。人心本易趨死寂,苦難之後,煥然重建,激盪一陣,又趨麻木。一位剛結婚的朋友,丈夫失業,不願出門,也懶得領低收入戶補助,每日但憑妻子打零工所得勉強維生。近來妻子懷孕,夫婦都極為苦惱,不知如何養活孩子。想到「無緣社會」,默默死去的,不單是孤獨的老人,還有孤獨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幼小的孩子。這些思考—不,算不得思考,只是平凡生活中一點輕浮的感嘆,無暇深入,散珠一樣滾落在幽暗角落,懶得撿起來。
年歲漸長,時常懷疑寫作的意義。自己沒有什麼長進,這是最清楚不過的。長時間與自己周旋,呈現平靜的假象。痛苦的源頭,也許是認識到自己的貧乏與無趣。不,不是這樣的,有一瞬想辯解的欲望,但沒有任何意義。為什麼有這麼多懷疑?如自己這般愚鈍的人,並不該有這麼多懷疑。無法妥善處理自己許多可笑的想法。所有痛苦與衝突,不會有出口。我知道這沒有出口,因此沉默是好的。
那麼現在,為什麼又要寫點兒什麼?時常,一些外來刺激,或曰觸動,就能燃起書寫欲。看到某人寫的書,想:「啊,我也想寫呢!」這種蠢蠢欲動、激情與焦慮混雜的感覺,寫作的人最清楚不過。可惜真要動筆,又有很多理由阻撓:太忙、找資料太費勁、沒感覺。在習以為常的環境裡生活慣了,也很難有動力寫作。我對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同情並不樂觀。每個人對於生命、生活、城市都有獨特的感知,而我為何要不厭其煩地記錄這些沒有意義的情緒、無足輕重的瑣事? 如果寫下來,又何必要公諸於眾,徒然打擾讀者?去年秋天,有一位朋友從北京來到京都,我們在同一個研究室相處了半年。她十分能享受京都之美、京都之樂,古本屋、舊書市、居酒屋、庭園、寺社、美食、秋天的紅葉、冬天的大雪、清池的錦鯉、鴨川沿岸永恆又稍縱即逝的風景—她都喜愛,並敏銳地把握了最關鍵處。我們一起喝過很多回酒,有非常快樂的回憶。有時候,一起到某個地方,我也忍不住告訴她一些可有可無的背景與細節。她的好奇心令我大為感動,給我很大的信心。寫點兒什麼吧,至少可以給她看,以此紀念我們在京都共處的愉快時光,並將她未曾來得及親自體會的京都的種種傳遞過去。
某日,去老師的研究室喝酒,那是一小罐我去年泡的梅酒。老師翻到一篇我剛寫的小文:「你把京都寫得很美,讀書生活也寫得不錯。」停頓道,「不過,這還不夠。瑣碎的、不好的、不愉快的,你也要寫。」是的,我又要寫大家很熟悉的京都了。有 太多人寫過京都,種種禮讚、旁觀、走馬看花,都使讀者產生了對京都的強烈興趣。我自己也是如此,因為讀了幾頁《枕草子》、《源氏物語》,才對京都抱有朦朧的幻想。兩年前,我寫過一篇很短的〈京都第五年〉,轉眼已是「第七年」。對於日常生活,似乎什麼都不必提,然而真要說些什麼,又千頭萬緒。數年前的初秋,第一次在車窗內望見夕光籠罩下東寺的五重塔,望見水草豐茂的鴨川,難免激動:「啊,就是這裡。」如今,雖已對此地習以為常,但從外地回來時,見到東寺的五重塔和流水不息的鴨川,還是會有一種十分清晰的安心感:「我回來了。」不過,旅人的身分與視角無法改變,因此我能寫的,仍只是客居者的日常。在這裡搬過三次家,如今住在銀閣寺前,附近有條小路,曰鹿ケ谷通。常被問:「真有鹿?」是的,據說平安時代比叡山的僧人元珍在此險要迷路,幸有鹿的指引。現在路上當然沒有鹿,但在不遠處的東山,就常有鹿的影子。山裡動物很多,此外還有蛙、蜥蜴、狸貓、鼯鼠、蛇、野豬、猴子、狐狸。大部分我都見過,最怕蛇,有時草叢一陣窸窣,嚇得汗毛直豎,牠們往往也溜得飛快。有寶藍色蜥蜴,非常漂亮,轉眼間就消失了。野豬可怕,幸好暫未會面,只在山中聽過號叫。山鹿就像精靈,曾見母鹿領小鹿出來喝水,見人輒驚走,與奈良公園跟人混熟了的鹿完全不一樣,牠們清瘦機警,烏黑的眼睛特別大。
鴨川也有鹿,時而從附近山裡下來喝水。曾在月夜看到母鹿領小鹿在水邊,波光清淺,水草蓊鬱,不似人間。在岸上望著,大氣都不敢出,唯恐驚擾。有時意識到人的存在,牠們就會飛奔離開。也有膽大的,白天出來散步,在淺水中央走,與白鷺、野鴨、老鷹、烏鴉共處。岸上的人擔心牠走到深水裡,被激流沖走,就在岸邊遙遙跟著。最終大概還是回到山中去了吧。
去年初夏,放學回來的夜裡,漫天星辰,涼風可喜。遂往屋後山坡散步。四圍靜寂,人家燈火已暗。忽聞群犬爭吠,又聞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完全猝不及防地,眼前轉角處竟剎那現身一頭大鹿,鹿角巍巍,前蹄騰起,健壯貌美。似乎有一瞬對視,我驚呆,鹿也驚呆,飛快回身,消失在黑暗山影中,復一片犬吠。待我回過神,追去兩步,早已行跡杳然。
就從這裡說起吧。銀閣寺前
京都很多著名的景點,都是我在頭兩年還懷著「興致勃勃的遊客」心態時逛完的。後來漸生出「本地人」的懶惰與矜持,不再出去亂跑,也難有時間出門。日常活動範圍變得極窄,最熟悉、最親切的,是銀閣寺到百萬遍一帶;跨過鴨川去同志社,就覺得好遠;走到丸太町通,便覺車水馬龍,已失去向前走的動力;河原町三四条是城裡,每番進城,看到街上妝容精緻、衣裝明麗的姑娘,尤覺賞心悅目,偶爾也想效仿,打起精神提高「女子力」,但一回到百萬遍,看到樸素的本校女生,就覺得特別安全,何況男生更加樸素;若去京都車站,那就是出遠門;去大阪? 簡直就像出國。因此在這裡住久了,回北京最不習慣的,就是城市空間感。從朝陽到海澱,到豐台,都有出國的感覺。
雖然住在景區,回家的小徑與去銀閣寺的觀光小道僅隔一排店面,但住處與景區卻涇渭分明,遊客也絕無興趣拐進這條平常的小徑。疏水道旁的櫻樹下、銀閣寺前的小橋頭,常年有笑容明亮、肌肉健美的人力車夫招徠生意,他們也是京都發達的旅遊業不可或缺的一環。剛搬來時,走出門,常會被當成遊客招呼。後來臉熟了,他們就會非常熱情地打招呼:「早安!路上小心!」有時他們正在樹下吃便當,也會放下筷子給我一個溫柔的笑臉。我沒有坐過這樣洋氣的車,也不好意思讓人拉著走。有幾回傍晚,薄暗的暮色裡遇到人力車,車前已掛起古樸長燈,隨著車夫的步伐悠然晃動。車上坐著一對情侶,或夫妻,或母女,膝上蓋著紅毯。車夫一邊慢跑,一邊滿含笑意地介紹沿途風景。有一回,一連過來五六輛車,每一輛坐兩位盛裝老太太,滿頭銀絲,和服的顏色嬌軟清柔,非常好看—原來是同一個花道協會的老朋友出來賞花。每年三月末,風突然變得極溫暖,大晴天,櫻花迅速漫開。最盛的幾天,家門口的哲學之道上擠滿了人,牽枝拍照,折花留念,不時有特意穿著明麗和服的姑娘翩然而過,還有盛裝的新人在花下聽從攝影師指點,熱鬧極了。17號、100號公車將大批遊客送至「銀閣寺道」、「銀閣寺前」這兩站。白川通與今出川通交叉處的東北角,有一塊「哲學之道」的路牌,因此很多人誤以為旁邊的公路就是哲學之道,常年都有人與這塊牌子合影。常聽有人說:「這裡就是哲學之道哦,好漂亮。快來拍照片。」更有匆忙的遊人,走到這裡,跟牌子合了影,便匆匆趕赴下一站。
上學途中,騎車路過花樹下的心情,與特地來賞櫻的人肯定不同。很想停車看會兒花,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很快就騎過去了。等走到僻靜的吉田山中時,又想:「明天一定要多看會兒,不然都該落了。」我的朋友香織一家對櫻花的心情也很微妙:「盛開就等於凋零,實在慘澹。況且天氣乍暖,懶洋洋,提不起精神。」這大概就是惜春與傷春。
銀閣寺前的小道兩邊,有許多景區特有的小店,金閣寺前、清水寺前、仁和寺前及嵐山都有這樣洋溢的風情,有烏冬麵店、蕎麥屋、醃菜店、抹茶霜淇淋店、茶店、和菓子「八橋」店等等。八橋是京都隨處可見的點心鋪,井筒八橋、本家西尾八橋、聖護院八橋……派系眾多,和很多老鋪一樣,有本家、分家之別。不過不用管,買一盒八橋在手,就是典型的京都遊客了。西尾家十分慷慨,善於革新,毫不吝嗇地擺出大量試吃盤,還提供免費熱茶。遠遠就能聽見店裡姑娘非常溫柔的召喚:「不用客氣,請進來嘗一嘗吧!」飽飽地試吃各種口味的八橋,是很多來京都修學旅行的孩子們美好的回憶。我的學長學姊們,談起來也很懷念:「什麼時候再去試吃吧!」銀閣寺很小,背後小山名月待山,可以想像坐在廊下,等待月光照亮銀沙灘的情景。這番妙處,我們都體會不到,因為黃昏銀閣寺就關門了。下午五點左右,遊客陸續散去,兩旁店鋪紛紛拉下捲簾門,合上門板。打工的姑娘們換下和服,拎著東西回家了,能聽到她們與店主極其熱切、誠懇的道別聲:「辛苦啦! 明天再見!」重複很多回,不停地鞠躬。不過多時,小街清場一般寂靜,只有附近放學的學生三三兩兩地路過。遛狗的人也零星出現了,有位老奶奶,養了兩隻柴犬,一隻叫茶茶,一隻叫櫻,人見人愛。櫻可以任意撫摸,茶茶則不可褻玩。「所以才叫茶茶呀。」老奶奶解釋。這個名字,自然是源自豐臣秀吉的側室、淺井三姊妹的大姊,她是日本戰國時期著名的美人。據說曾有京大學生夜裡翻牆進銀閣寺。月亮升起來的時候,一定很美。樸素的鳳凰堂,也與月光相宜。月待山這個名字,實在很不錯。
銀閣寺旁,有一座很小的淨土院,門前種著紫珠草(日人呼曰「紫式部」),遊客極少光顧。但該寺管理著八月十六夜五山送火之一「大文字」,故有「大文字寺」之稱。這一帶的居民組成了「大文字保存會」,共同完成點火的任務。狹窄的寺內花木扶疏,有山茶、臘梅、茱萸、木賊、白玉蘭、四照花、繡球、碗蓮,四季不斷。本堂供奉等身阿彌陀如來像,還有一尊丹後局人像。丹後局名高階榮子,曾嫁平業房,後為後白河法皇的寵姬,與源賴朝也有親密關係。據說她熱衷政治,與法皇育有六子。後來失勢,法皇去世後即出家為尼,歸隱淨土寺,即淨土院的前身。有時在家待了一天,黃昏想去散步,就到淨土院看會兒花。某日貪看碗蓮,回過神時,院門已落鎖,殿內也無人,只好坐在廊下等。頭頂一方狹窄天空,流動層雲被夕光染作金赤,又緩緩浸透深藍夜色。樹梢摩挲,蚊蟲開始活躍。終於有一位婦人走過,驀地看到我,很驚詫的樣子,愣了一秒,連聲道歉,開門將我放了出去。
生協買書
某先生說,這本書,你不要寫舊書店,不是專門寫過一本嗎?因此,我在盡量克制講舊書店的欲望,雖然對我來說,那是極大的樂趣,也是最熟悉的範圍。不過,我仍忍不住想講生協的書店—那是新書店,不算犯規。生協書店是生活協同組合(即生活合作社,簡稱「生協」)下屬的書店,在校學生加入生協後,買書可打九折。日本書店極少打折,生協的優待是學生特有的權利。書店在本部校區西側的體育館旁,平時經常去逛。雖然有些書在舊書店能以稍低的價格入手,但逛新書店自有不可替代的樂趣。書本的擺放方式,包括新上架的圖書,都凝聚了店員許多心血。醒目的專區一直在把握潮流,譬如山崎豐子去世後,專區立刻就擺出其作品專輯。去年校長換屆,新校長山極壽一是著名的人類學家、靈長類學者,有「大猩猩研究第一人」之譽。專區也很應景,隨即擺上生物學、大猩猩研究類圖書,以示慶賀。
近來書店主題是「西博多與分類學研究」,專區便擺出大量植物分類學、動物分類學、博物學的圖書,且為八五折。有一本大場秀章編的豪華大冊《櫻花圖譜》,纖毫畢寫,宏博精美,又有西博多編輯的《日本植物誌》,令喜愛植物的我難以自拔。不過我最後還是理智地只買了兩本資料書:威爾弗里.布朗特(Wilfrid Blunt)的《植物圖譜的歷史》及《西博多日記》。西博多的經歷和精力均極豐富,著述極多,這也是為什麼我雖然對他很早就感興趣,卻至今一篇文章也沒寫出來的緣故——在盡可能地把握資料之前,根本不敢下筆。
生協書店雖不大,但盡量照顧到各學科,圖書種類很豐富。觀察不同群體的讀者很有意思。科技雜誌區的宅男,女性雜誌區的小姑娘,法律區的未來的經營管理人士,還有在文史一帶遊蕩的奇人,不同專業的人常有不同的氣質。
我很愛買辭典,雖然使用率不高。比如小川環樹編角川書店《新字源》、岩波書店《國語辭典》、三省堂《全譯讀解古語辭典》、雄山閣《假名連綿字典》。有時也會去看看天文、生物圖冊。若在非專業區遇到熟人,有時會略顯窘迫,因為暴露了自己的閱讀習慣與惡趣味。逛書店是很奢侈的事,我指的是時間。浮光掠影般地邂逅許多有趣的書名、精采的封面,隨便翻兩頁,某種新興趣輕易就被點燃了,要是缺乏定力與判斷力,很容易被誘惑。但我無法抵禦這種引誘,在書店泡了大半天,不買點兒什麼回去,是絕對不會甘心的。實在想不到買什麼,就去文庫本區域,至少可以買那些經典譯著。有幾位學長總嫌棄早些年的翻譯:「翻譯得實在不好,讀不懂。為什麼會讀不懂?因為明治年間的讀書人,就以硬讀讀不懂的書為傲。」這在《日本讀書論》中已詳細論及。現在,我讀英文文獻很慢,多半仰賴日文翻譯。時常痛感自己的困乏,內心深處有不明所以的躁動,發出焦灼枯渴的呼喚,因外界侵擾而深感絕望,過度的敏感使我頻繁經歷情緒波動所帶來的困擾。這種時候,混亂的頭腦亟需重構秩序,讀書無疑是最好的選擇。我知道自己的感慨與痛苦都非常淺薄,前人一定早有精采的解釋及論述,幫助我釐清思緒,平復心情。有時翻到某些書,雖是全然不了解的陌生領域,卻能意外地觸動思考,帶著這點兒新鮮感,再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又有了新的認識與感受。
不過,外國作者名的中文、日文譯法不同,二者都是直接音譯,有的能一下認出來,有的則差別很大,要聯繫書名才能反應過來是誰。這種時候我又痛切地認識到精通原文的必要性,然而受精力、智力之限,至今都在語言隔閡的桎梏下掙扎。小時候讀過一些名著,最早接觸的文學作品,或者說自我選擇的作品,這對我此後的審美取向、閱讀趣味,乃至人生觀,都產生了至為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固然有積極的一面,令我沉溺於某一類風格的深邃之美、永恆的憂鬱及悲觀之中,但這種強大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思維定勢,或者說被某種無形卻無處不在的﹁印象﹂籠罩,使我在閱讀其他作品時受到某些先入觀的干擾。不管我生吞活剝多少西方譯著,都始終沒有捕捉到一二真髓。那些句式、人名、地名,是我完全陌生的,我拚命看,也無法理解,就像隔著蒙上霧氣的玻璃,以為自己看到了什麼,卻永遠朦朧,難以總結任何感想。對於這種閱讀障礙,我深感痛苦。生協書店南側的西部講堂,有著異常激盪的歷史。巨大的屋頂上有三顆獵戶座黃星,曾被塗成紅色,見證了左翼青年們的激情歲月。昭和天皇去世次日,據說這裡還舉行了相當熱鬧的﹁cry day event﹂,試圖打破天皇家葬禮的壓抑氣氛,畢竟,這不應該成為限制國民自由的理由。有各種演出,還有電影播放,並以焚燒日本國旗隆重收場,由此驚動了警備隊。如今,京大生對政治很淡漠,二○一四年秋,便衣公安員警入校的騷動發生後,周圍埋頭學術的好學生、積極進取的未來精英多有這樣的評價:「不知道什麼情況。」「那些學生看起來也不像學生,是專門搞政治的吧。」想必他們對這些事情抱有本能的懷疑與敬而遠之的態度,我了解很少,也無法多談。
生協書店以北有體育館,每到學期末,就有本科生組成的啦啦隊排演,從音樂到舞姿都非常青春熱血。羅森(Lawson)便利商店隔壁有家和菓子店,名叫「かぎや政秋」,我最常在那裡買叫「野菊」的杏仁味點心,是「落雁的一種,口感類似雲片糕或薄荷糕,小小的圓圓的,不知不覺就吃掉了。青木正兒寫過《落雁與白雪糕》,是篇「很好吃」的文章。「落雁」名字好,據說做法源自明代的軟落甘,大概是麵粉蒸熟,微乾後磨粉,曬乾微炒,用糖水浸泡,入模壓緊。初夏有柚子餅,蒻竹葉包裹,繫金線,甘香柔軟。求肥餅常年都有,名字很有趣,是米粉加砂糖或麥芽糖漿熬製的點心,很軟,雪莓娘即其變種。
生協書店以東,街對面,是大學綜合博物館,定期會更換主題,本校學生不必買門票。常設展分自然史、文化史、技術史三塊。自然史展廳有大量昆蟲、植物標本,文化史展廳有古石棺、古器物、古文書,技術史展廳有我完全不了解的精密儀器。自然史展廳光線幽暗,路過恐龍骨架,不時響起恐龍號叫的音效,還有隆隆的雷聲。去年有一場叫「海」的特別展,講某課題組研究海龜一日二十四小時、一年四季的作息規律及活動範圍,吸引了很多小朋友。課題組人員還在海龜身上綁了微型攝影機,拍到海龜求愛、交配的畫面。留言牆上貼滿了觀眾的感想小紙片,好幾個人都畫了背著攝影機的海龜,有位小朋友善用雙關,給「カメラマン」(攝影師)的「カメ」(龜)標了著重號,很萌。在生協食堂吃完飯,去樓下書店買幾本書,到點心鋪買一盒﹁秋菊﹂,再去博物館轉一圈,是難得清閒時固定的遊樂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