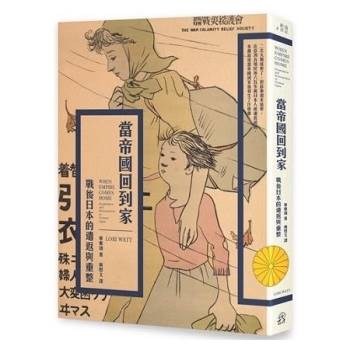第四章 「最終,我們卻落入日本人的手裡」──文學、歌曲與電影中的遣返者(摘錄)
■ 一九五○年代小說的滿洲殖民地終結
五味川出版《人間的條件》的時候,安部公房的《獸群尋找故鄉》也開始在文學雜誌《群像》中刊載。小說裡,一名滿洲出生命運多舛的青年久木久三,為了擺脫近似俘囚的童僕地位而逃離哈爾濱某個蘇聯軍官的家,之後便往南方走,想返回日本。一九四八年的滿洲,無情的地理與政治形勢讓久木層層受阻,天真的他獲得狡詐的韓國海洛英販子高石塔的幫助,但也遭到他的剝削。高石塔的母親是日本人,所以他會說日文與中文,對於國共內戰下後殖民社會的複雜情況瞭若指掌。在旅途中,高石塔搶走久木的財物,將他遺棄在瀋陽等死。久木存活下來,並經由他人協助下找到了一處社區,這裡有少數殘留的日本技術工人和他們的家人依然在此生活。久木懇求日本守衛,表示他一心只想返鄉,但守衛說:「遣送營全都關閉了,遣返船也全開走了……沒辦法。」遭到拒絕後,久木走到一戶日本人家前面。「我是日本人。」他對孩子們說。孩子們嘲笑他。「你是乞丐!日本人不會這麼黑!」孩子們叫道。母親把孩子叫進屋裡然後關上門。
遭中國守衛驅逐後,饑餓而絕望的久木遇見了幾個日本走私客。當久木告訴他們自己的名字時,他們第一個反應是驚訝不已,因為有一個來自哈爾濱的久木久三已經和他們談好要回日本。他們不懷好意地想瞧瞧這兩個久木碰面時會發生什麼事。走私客帶著久木一起走,並且安排兩人在回日本的船上對質。原來冒名頂替的是偷走久木證件的高石塔。但高石塔精神錯亂,被拴上了鎖鍊,他真以為自己是久木久三。小說到了最後,久木與高石塔,一個滿洲日本人與一個滿洲韓國人,兩人都被扣留在船上,永遠無法抵達日本。
小說家安部公房在一九二四年生於東京,出生後不久即遷往滿洲城市奉天(瀋陽),他的父親安部淺吉在當地的滿洲醫科大學教書。一九四○年,安部十六歲,返回東京就讀高中,之後便經常往返奉天與東京兩地。一九四三年,安部十九歲時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一九四四年,安部開始相信日本即將戰敗的傳言。他偽造自己的身分證件後返回滿洲。戰爭結束時,安部與家人一起待在奉天,在他父親的診所幫忙。安部提到,日本投降後,他興高采烈,但很快就面臨戰後滿洲的混亂。蘇聯占領軍把安部一家趕出自宅,此後安部一家便經常躲著蘇聯軍人。一九四五年底,安部的父親在治療患者時被傳染斑疹傷寒而死去。安部靠著在街上叫賣冷飲養活自己(或許還有他的母親與弟妹──他是四個兄弟姊妹中的長子)。一九四六年秋,二十二歲的安部與家人搭乘遣返船前往長崎縣佐世保引揚援護局。由於船上爆發霍亂疫情,遣返船在日本外海下錨停留超過十天,所有的返國者都必須接受檢疫。被迫待在外海骯髒的船上,日常用品供應有限,有些人開始呈現出瘋狂的症狀。安部寫道,這個經驗成為小說《獸群尋找故鄉》船上最後場景的基礎。筆者凸顯這些類似之處,並不是為了說明這部小說具有傳記性質。儘管如此,安部的創作確實運用了自己在戰後滿洲與遣返的經驗。
在安部的作品中,《獸群尋找故鄉》有著相當奇特的地位。這部小說的英文譯本至今尚未出版,而它首度問世時,評論者也未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到了一九五七年,安部已經建立起創作幻想小說的名聲,而一名失望的評論家表示,當他拿起《獸群尋找故鄉》時,他還預期這會是一部充滿奇妙內容的作品。另一名評論家猜測,或許這名年輕人已經江郎才盡。雖然《獸群尋找故鄉》不如安部其他的小說和戲劇來得知名,但卻充滿安部作品特有的主題與比喻。
文學學者已經指出安部作品的幾個核心主題。E.達爾.桑德斯(E. Dale Saunders)是安部《砂之女》與其他作品的譯者,他歸結安部作品有三條主線:「疏離與喪失身分這兩個孿生主題」;「都市孤立讓現代人陷入無聊沉悶」;「運用文學這項工具來翻轉或顛倒角色,讓獵人變成獵物」,或讓侵略者變成受害者。威廉.居里(William Currie)詮釋安部的小說是「尋找存在的根源」,而其象徵就是沙子;「溝通困難」,表現在面具的使用上;以及「內在與外在現實的落差」,是藉由探索地圖與城市而發現這點。文學批評家川村湊指出,安部作品裡追逐與被追逐、城市與荒野、故鄉與異鄉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呈現了相反但實際上連續的經驗,看起來更像是莫比烏斯帶(Mobius strip)。安部將《獸群尋找故鄉》的主角取名為久木久三,暗示了這部作品的深層主題。久木久三(Kuki Kyūzō)其實是巧妙改動哲學家九鬼周造(Kuki Shūzō)的名字而來,安部或許是想諷刺地提出本真性、多元主義以及與土地的連結等這些主題。
在《獸群尋找故鄉》中,安部以文學的方式呈現許多這類進退兩難的局面。久木經歷了桑德斯歸結的問題。首先,他失去了身分,而且與周遭的人疏離。在瀋陽這座城市,他明明已經接近日本人居住的社區,卻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地方。一名中國青年主動表示要帶他「到日本人住的地方」,久木心想怎麼可能這麼容易,但當他抵達時,那裡的日本人卻將他拒於門外,因此他還是孤伶伶一個人。這本書的設定是角色的翻轉:久木原本是支配國的人民,此時卻要仰賴韓國人高石塔才能生存。當久木與高石塔在滿洲平原上忍受饑寒時,出現了獵人與獵物之間模稜兩可的局面。他們碰上一群野狗,這群野狗和他們一樣又餓又冷。年輕人與狗彼此打量,到底誰是掠食者誰是獵物。
久木無法與周遭的俄國人、中國人與韓國人溝通,他變得無助,只能仰賴高石塔。地圖扮演了關鍵角色。久木從幫助他的俄國人那裡偷來一份地圖,徒勞地希望地圖可以為他指出回家的路。彷彿為了強調地圖的重要似的,原初的版本還在正文旁邊附了一張手繪地圖。在《獸群尋找故鄉》中,久木這個身處滿洲的無助外國人,經歷了疏離、孤立與角色翻轉,這些狀況在安部日後的作品中都轉而以抽象的形式表現。對久木而言,對安部其他小說的主角也是如此,家鄉永遠是異鄉。
《獸群尋找故鄉》的一些主題與其他遣返小說的主題呼應。首先,久木無法維持自己的身分。蘇聯人給他身分證件,但當他試圖使用證件時,人們卻笑他天真地以為這些證件──就像地圖一樣──真的有用。之後,當他遺失證件時,滿洲的日本人社群拒絕接納他,因為他無法證明自己的身分。他們無疑相信他是日本人,卻因為他沒有證明文件而輕易地打發他走。一九四八年,滿洲陷入混亂,久木不見容於殘留的日本人社群,又沒有身分文件,於是成了一個無國籍的人(無籍者)。久木也在另一個領域失去了身分──他的身分被韓國人高石塔偷走了,而高石塔打算冒充久木前往日本。久木無法拿出文件證明自己的身分,以及高石塔很輕易就偷走他的文件,這兩件事顯示身分與劃定疆界的政治國家之間的連結是反覆無常的,兩者隨時可能崩潰消散。
從日本人社群的社會性質來看,特別是海外日本人,久木被身旁的日本人孤立是相當特出的。父親在他出生不久就過世了,母親與他一起在哈爾濱生活,靠著租屋給日本工人維生。就在蘇聯入侵後不久,他們的社群準備疏散。但一顆流彈擊中久木的母親。當久木留下來照顧垂死的母親時,其餘的人拿走了久木保管的錢,繼續疏散。到底是誰射死久木的母親,我們不得而知,而在語言不通之下(書中有幾則因為語言不通而產生的黑色幽默),蘇聯占領軍士兵以為她是被某個法西斯主義者殺害。在蘇聯人的世界觀裡,凡是法西斯主義造成的孤兒都值得同情,於是他們收留他做為童僕,並提供他生活所需。久木逃離哈爾濱抵達瀋陽後,他在當地找到日本人,但他與自己所屬的哈爾濱日本人社群失散後,就再也無法加入其他的日本人社群。久木自此一直是一個人。
會說日語的韓國人高石塔是《獸群尋找故鄉》的關鍵人物。其他以戰後滿洲為背景的小說也有說日語的韓國人。在《人間的條件》中,出現了兩種說日語的韓國人。第一個是販賣中國奴工的邪惡韓國人,第二個是和善的韓國家庭,他們在梶返鄉的路上與他閒話家常。在之後要討論的小說《大地之子》中,一名會說日語的韓國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工作,他威脅被當成中國人的小說主角,表示要揭發他的日本人身分,如此他便不免一死。但韓國人沒有真的這麼做,主角也因此存活下來,但說日語的韓國人對日本青年構成的威脅,卻推動著情節持續展開。在《獸群尋找故鄉》中,殖民角色的翻轉,使久木發現自己必須仰賴高石塔才能生存。戰後文學在處理遣返這個主題時,把韓國人當成焦慮的來源:殖民地創造物在戰後滿洲反過來糾纏日本人。《獸群尋找故鄉》的結尾讓所有人處於懸而未決、身分不明的狀態,凸顯出殖民計畫模稜兩可的遺留物。至少在小說中,並未對這個混淆的狀態提出任何解決之道。
一九五七年,另一部與遣返相關的作品,導演五所平之助的《黃色的烏鴉》問世了。電影一開始是一群小學生在畫畫,畫的是峙立於他們面前的鐮倉大佛。九歲的清堅持為自己的畫塗上黃色與黑色。老師對於清與他的畫感到擔心,於是請教男同事的意見。清原是適應良好的孩子,但最近卻經常惹麻煩、不守規矩。老師的同事以權威的語氣對她說,根據最新的心理學研究,戰爭孤兒與來自破碎家庭的孩子經常把畫塗成黃色與黑色。清的老師樂觀地對同事說,清的家庭很圓滿──事實上,他的父親才在一年前從中國遣返回來。「啊,」男老師恍然大悟地嘆道,「是遣返者啊。」
在一連串的倒敘中,電影提到父親返回日本。清與母親前往舞鶴迎接他從未謀面的父親。父親戰前的僱主不情願地重新僱用他,但在他長期不在公司的期間,年輕後輩已經當了他的上司,而且以高傲的態度對待他。他與兒子關係疏遠,原本清與母親一起睡,現在父親取代了他在床上的位置。電影情節在父親趕走清的寵物烏鴉時出現危機。清於是用黃色與黑色畫了烏鴉。
危機過後,清去投靠鄰居。那是一名慈祥的戰爭寡婦,她已經有一個孤兒要照顧,但清希望她也收留自己。清的母親偷聽到他們的對話,感到心碎。接下來這名寡婦講出了這部電影的訊息:清的父母親很自私,他們只關心自己,忽略了男孩,清自從父親返國後就形同孤兒。清的母親與丈夫把話攤開來談,兩人決心要像家人一樣生活,而他們也做到了,從此一家人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黃色的烏鴉》是一部相對直接的電影,在接近電影開頭說的那句「啊,是遣返者啊」,向觀眾預示麻煩人物即將登場:一個社會適應不良的「好辯者」,把社會和家庭搞得一團糟。最終,這個家庭在睿智鄰居協助下,讓「遣返者」重新融入這個家,但他的返國也差點讓家庭分崩離析。這部電影似乎要表達,唯由透過親情與適應,家人才能讓遣返的成員重新成為家中的一份子。
遣返者不斷出現在電影與小說中。一九六三年的電影《她與他》,看起來與常人無異的家庭主婦直子因為照顧一名無家可歸的拾荒者、他的狗與一名孤兒,而將衝突帶進自己的婚姻中。直子的穿著打扮、上街購物與操持家務,就和其他家庭主婦一樣,但在電影一開頭,觀眾從兩名中年鄰人婦女的閒聊得知,直子是從滿洲歸來的遣返者。這兩名婦女重複熟悉的模式,一方面同情(「她肯定有過恐怖的經歷」),另一方面又汙名化。直子遣返的過往在與拾荒者的對話中又出現了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她不知不覺陷入過去的回憶裡,她說自己小時候曾經在滿洲走了幾百英里的路,最後才遣返回日本。
《她與他》是直子與丈夫英一兩人在新中產階級社區(團地)生活的故事。在電影中段,直子的丈夫英一表示自己對於社區生活感到滿意。到了末尾,隨著直子愈來愈投入於無家可歸者的家庭時,一向疼愛妻子的英一憤怒地吼道,他只是個普通人,想擁有一個普通的家庭。這或許是為了對比出直子。直子的遣返經驗並未在電影中出現,但她需要與其他家庭主婦有些不同。日本大眾文化裡其他用來凸顯差異的比喻,包括外國人、非人性的性格、被某種經驗(如原爆受害者)影響的人以及歷史上國內的少數族群(如部落民)。有時候,光是來自北海道或沖繩就能說明一切。《她與他》的情節需要一個內部的他者,必須要有一個人,她的日本特質濃厚到足以讓她嫁給普通的生意人,住在普通的社區裡,但又要具備一定的差異性,足以讓她產生問題。戰爭結束過了十八年,遣返者依然扮演著國內他者的角色,至少在小說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另一部描述滿洲遣返者的電影發表了。大島渚的《儀式》講述一個名叫滿洲男的男子的故事。影片內容是由櫻田家的五場集會構成:一九四七年,滿洲男父親的悼念儀式;一九五二年,滿洲男母親的喪葬儀式;一九五六年,滿洲男的叔叔櫻田勇的婚禮儀式;一九六一年,滿洲男毫無意義的婚禮儀式[新娘逃婚,但櫻田家的大家長(滿洲男的祖父)逼迫他獨自一人舉行婚禮];與一九七○年,櫻田家大家長的喪葬儀式。每一場儀式都呼應著戰後日本政治經濟史的重要時刻:一九四七年,天皇發表人間宣言一週年紀念;一九五二年,盟軍結束對日本的占領,大家長在整肅後又重新回到公眾面前;一九五六年,保守派自由黨執政,開啟了「五五年體制」;一九六○年,修訂美日安保條約;與一九七○年代初為沖繩返還做準備。以每個儀式代表戰後日本歷史的重要時刻,大島藉由電影批判戰後日本社會,在他的描繪下,這個社會充斥著戰犯、亂倫與鬧劇。
《儀式》也談到殖民地日本人的返國以及他們試圖融入本土社會遭遇的困難。第二個場景描繪一個日本女人與孩子,衣衫襤褸,破爛的物品捆綁在背部,他們在原野上奔逃,躲避身後不知名的攻擊者。這是日本人在戰後滿洲逃亡的經典形象。但諷刺的是,電影裡兩人卻身在日本,位於家族的土地上,他們躲避的對象是他們的親戚。在戰後滿洲淪為難民後過了十八個月,十四歲的滿洲男與母親獲得遣返,他們返國時正好趕上滿洲男父親的悼念儀式。他的父親在一年前,也就是天皇發表人間宣言的那天自殺。
大家長與兒媳婦(滿洲男的母親)最初的會面,完全表現出戰爭結束後對滿洲日本女性的刻板印象。大家長質問她為什麼逃跑,她解釋自己不想成為家族的負擔,她與滿洲男兩個人可以自己過活。大家長斥責她,提醒她現在她的丈夫已經死了,滿洲男成為唯一的繼承人。大家長又說:
「大家都說俄國人是惡魔。妳的經驗也是這樣嗎?」
「那的確是非常可怕的經驗。」
「妳的眼睛泛黃。俄國人抓妳去當妓女嗎?」
「確實有女人遭遇這樣的不幸。」
「妳,妳,我是問妳。」
「若是如此,我絕不可能順利回家。」
但滿洲男的母親仍受到懷疑,滿洲男還被迫參與詆譭自己的母親。
「告訴我們關於俄國人的事!」
「他們給我一些黑麵包。」
「他們有給妳母親任何東西嗎?」
[沉默]
「你曾與她分開過嗎?」
[沉默]
滿洲男母親的病一直未能痊癒,五年後,她的喪禮成了家族再次集會的理由。大家長在大家面前宣稱她有悲慘的經驗。十九歲的滿洲男只能無力地抗議,他說母親在滿洲過得很幸福。
在《儀式》中,櫻田家的亂倫問題導致身分的錯亂。家族裡絕大多數的女性全遭到大家長的侵犯,四個孫子孫女中有三個完全搞不清楚父親是誰。過去,他性侵外甥女節子,為了處置她,就把她送到滿洲嫁給與他有合作關係的中國人。藉由這種方式,《儀式》把滿洲呈現為一個把被玷汙的女子送去的適當處所,而被玷汙的女子也從那裡歸來。滿洲男真正的父親是誰,這個問題只出現過一次。滿洲男的叔叔櫻田勇是日本共產黨成員,他曾公然質問大家長是不是滿洲男真正的父親。大家長以這個問題無關緊要而拒絕回答,然後反過來利用這個機會嚴厲批評日本共產黨並駁斥一切對他的權力的挑戰。除了父親是誰,在滿洲出生成長、從滿洲遣返回國的滿洲男最感掙扎的還是自己的身分。在電影一開頭,成年後的滿洲男與表妹律子談起他們的關係。滿洲男愛著她,但她堅持稱他為「親戚」。滿洲男毫無說服力地表明自己的身分,他說他有名有姓,他叫滿洲男,是滿洲出生的男子。雖然他試圖與櫻田家疏遠,但他無法製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