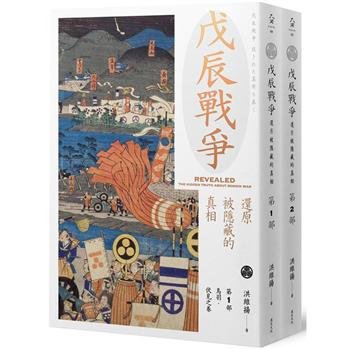小御所會議之後
筆者在前作第二部最後,談到慶應三(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王政復古大號令」和小御所會議做出結論:已在該年十月十四日奉還大政於朝廷的慶喜必須辭官納地。「辭官」指的是辭去內大臣(征夷大將軍已在大政奉還時辭去)及右近衛大將,納地則是向朝廷歸還多達四百萬石的天領。
十二月十日晝四時,前前任尾張藩主德川慶恕以及前任越前藩主松平春嶽二人以朝廷的敕使身分,前往二條城向德川慶喜轉述小御所會議的結果,亦即要慶喜辭官納地。筆者在前作提到慶恕、春嶽二人轉述小御所會議的訊息造成二條城內的旗本、會津及桑名藩士陷入混亂、恐慌、憤怒之中,混亂、恐慌、憤怒的原因不在於慶喜必須辭官納地,而是慶恕、春嶽二人竟成為背後有薩長撐腰的朝廷代表前來勸說主君。
慶喜的反應倒沒有這些旗本、藩士來得激烈,因為慶喜並不把不具實力的朝廷召開的會議結果當一回事,即便朝廷背後有薩、長、藝等討幕諸藩為後盾,慶喜也有恃無恐。慶喜自去年十二月五日就任將軍以來推動的慶應改革頗具成效,法皇拿破崙三世派出的軍事顧問團來日一年訓練完成的一萬餘人近代陸軍是慶喜有恃無恐的主因。
儘管慶喜對於法國軍事顧問團親手調教出的近代陸軍深具信心,不過鑒於京都勤王氣息過於濃厚,一旦在此開戰將不利於幕府。慶喜在不與任何幕僚商議下,獨自沉思,於十二日暮六時帶領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老中首座板倉勝靜悄悄離開二條城,翌日晝八時抵達大坂城,二條城則由慶喜的心腹梅澤孫太郎坐鎮。
梅澤孫太郎與原市之進是慶喜成為將軍後最重要的心腹,他們兩人都出身水戶藩,弘化四(一八四七)年慶喜過繼為一橋家養子時奉齊昭之命前往一橋家成為其家臣。原市之進於安政二(一八四九)年進入藩校弘道館就讀,接受會澤正志齋、藤田東湖兩大當代水戶學龍頭的薰陶,成績優異的原被任命為弘道館舍長,在會澤、藤田的推薦下於安政六年轉往幕府官學校昌平坂學問所深造。
慶喜於文久二年七月六日被任命為將軍後見職時,兩人被延攬為慶喜的側近,此時慶喜的智囊是一橋家的家老並、旗本出身的平岡圓四郎。慶喜之所以由攘夷轉向公武一合,有一說是受到平岡巧妙操控(實際上並非如此),因此在水戶藩士看來,平岡成為蠱惑慶喜的佞臣,他的下場也就不難想像了。元治元(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水戶藩士江幡貞七郎(廣光)、林忠五郎埋伏在京都町奉行所與力長屋(都市中下層民眾居住的大雜院)旁暗殺平岡,享年四十三歲。江幡、林二人得手後,旋即為傾巢而出的町奉行所與力殺害。
平岡死後,梅澤和原成為慶喜的左右手而受重用,較為年長的梅澤被慶喜任命為大坂警備而駐守大坂城。慶應二年底慶喜就任將軍後任命兩人為目付,正式從一橋家臣躍升為幕臣。慶喜任用有弘道館、昌平坂學問所資歷的原市之進取代平岡圓四郎,成為慶喜的新智囊主導慶應改革,此舉讓原步上平岡的後塵。慶應三年八月十四日原市之進在京都板倉老中首座宅邸門前遭到同樣前來拜訪的幕臣鈴木豐次郎、依田雄太郎二人殺害,整起事件幾乎與三年前平岡遇刺如出一轍。平岡和原遇刺後,慶喜身邊再也沒有能上得了檯面的智囊。雖同樣隨侍在慶喜身旁超過二十年,但是梅澤充其量只有忠誠而已。在面臨據守二條城與薩長軍作戰與否的抉擇時,梅澤只能忠實接受慶喜下達坐鎮大坂城約束按捺不住的會津及桑名藩兵的指令而不能為主子出謀劃策。
如果平岡或原還在的話,必能為我分析利害得失,但是梅澤的話就……
慶喜一生大概再也沒有比這時候更渴望身邊有個可以出謀劃策的智囊吧!
慶喜決心開戰
撤出二條城的慶喜一行人,在十三日夕七時進入大坂城。慶喜略作休息後於翌日先接見立場親近幕府的法國公使侯許(Michel Jules Marie Léon Roches),前作已有提過法皇拿破崙三世除了借貸鉅款給幕府外,更派出軍事顧問團為幕府訓練近代陸軍。英國公使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無意間聽聞此消息後,認為大英帝國的駐日使節理應享有日本外交的優先權,豈能落在法國之後?12月14日是格列高里曆1868年1月8日,兵庫已經正式開港,巴夏禮緊急喚來使館通譯官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冒著傾盆大雨趕赴大坂城。有讀過筆者前作的讀者,對這兩位公使以及薩道義想必並不陌生。
由於巴夏禮臨時亂入,慶喜因而擱置原先和侯許的話題,改向侯許和巴夏禮述說五日前「王政復古大號令」的經過。由於慶喜並未參與政變過程,很多細節他無法清楚交代,只能敘述已知的部分。慶喜說完之後,詢問兩位公使該如何因應接下來的政局。兩位公使先是講了漂亮的場面話安慰慶喜,接著話鋒一轉,質疑慶喜撤出京都、轉進大坂的目的。如前文所述,兵庫在格列高里曆1868年1月1日(日本曆為慶應三年十二月七日)正式開港,慶喜卻在開港後數日離開京都,來到大坂,是否有以政治力阻撓兵庫開港的意圖呢?
在薩道義看來,慶喜並未表現出絲毫想要重新奪回權力的樣子(從之後的歷史看來,薩道義的觀察有誤),對於巴夏禮和侯許的質疑,慶喜也無心回覆,彷彿因為一連串的打擊而顯得意興闌珊。
最後,慶喜說道自己疲累至極,結束與兩位公使的會面。不過慶喜又補充道,將擇日再做安排會面。據薩道義《明治維新親歷記》一書記載,慶喜離去後,外國奉行遞交書面告知:
慶喜已辭去將軍職(十月廿四日主動向朝廷辭職),今後請以「上樣」稱之。
十二月十六日晝八時半,慶喜在大坂城御白書院正式接見英、法、美、荷、義大利、普魯士六國公使,親自說明自大政奉還以來兩個月間日本政局的演變。過程中痛訴岩倉具視和薩摩主導數名諸侯、帶兵突入禁門的凶暴舉動,重申王政復古是場不合法的政變。慶喜的演說打動六國公使,一致表態支持幕府,對慶喜而言,無疑是場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只要能獲得列強支持,不當將軍又有何妨!
當然,打動六國公使內心的並非這場演說,而是慶喜允諾會繼續承認以往簽下的修好通商條約並保障各國在先前取得的種種利益,這才是六國公使最為關心的事項。
慶喜決定乘勝追擊。翌十七日,慶喜以自己的名義命右筆起草為己辯護的《舉正退奸之表》,於十八日命大目付戶川伊豆守安愛帶往京都遞交新政府總裁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戶川找上若年寄兼山陵奉行(文久二年新成立的幕府職務,負責山陵的管理和修補,雖說是幕府的職務卻必須由朝廷任命及同意)戶田大和守忠至在當日晚上將此表上呈給總裁有栖川宮熾仁親王過目。
慶喜在《舉正退奸之表》強烈要求清君側(指岩倉具視、正親町三條實愛、中御門經之等人),以激烈的語氣提到「要向幼少的天子進諫,火速聚集天下列藩的眾議,以舉正退奸」。並以「薩賊」稱呼薩摩藩。此外,慶喜在該表還提到會命諸藩率兵前來大坂以防萬一,等於在暗示有栖川宮若不自行清君側,他將率領諸藩藩兵攻入京都親自執行。
諸藩是否願意聽從慶喜之命率兵前去大坂不得而知,不過板倉老中首座早在十一日寫信給江戶的稻葉美濃守正邦、松平周防守康直、小笠原壹岐守長行、松平縫殿頭乘謨四位老中,提到近期之內將會發生戰事,要求盡快調派步兵四大隊、騎兵兩小隊、大砲兩門以及軍艦數艘至大坂灣。
板倉老中首座一定有向慶喜提及此事,慶喜撤出京都想來應與板倉老中首座此舉不無關係,可見慶喜撤出京都並非全然無謀之舉,他在下令撤出京都的同時應該已有一段時間後將與討幕派作戰的念頭,六國公使的表態支持加強他與討幕派開戰的決心。
筆者在前作第二部最後,談到慶應三(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王政復古大號令」和小御所會議做出結論:已在該年十月十四日奉還大政於朝廷的慶喜必須辭官納地。「辭官」指的是辭去內大臣(征夷大將軍已在大政奉還時辭去)及右近衛大將,納地則是向朝廷歸還多達四百萬石的天領。
十二月十日晝四時,前前任尾張藩主德川慶恕以及前任越前藩主松平春嶽二人以朝廷的敕使身分,前往二條城向德川慶喜轉述小御所會議的結果,亦即要慶喜辭官納地。筆者在前作提到慶恕、春嶽二人轉述小御所會議的訊息造成二條城內的旗本、會津及桑名藩士陷入混亂、恐慌、憤怒之中,混亂、恐慌、憤怒的原因不在於慶喜必須辭官納地,而是慶恕、春嶽二人竟成為背後有薩長撐腰的朝廷代表前來勸說主君。
慶喜的反應倒沒有這些旗本、藩士來得激烈,因為慶喜並不把不具實力的朝廷召開的會議結果當一回事,即便朝廷背後有薩、長、藝等討幕諸藩為後盾,慶喜也有恃無恐。慶喜自去年十二月五日就任將軍以來推動的慶應改革頗具成效,法皇拿破崙三世派出的軍事顧問團來日一年訓練完成的一萬餘人近代陸軍是慶喜有恃無恐的主因。
儘管慶喜對於法國軍事顧問團親手調教出的近代陸軍深具信心,不過鑒於京都勤王氣息過於濃厚,一旦在此開戰將不利於幕府。慶喜在不與任何幕僚商議下,獨自沉思,於十二日暮六時帶領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老中首座板倉勝靜悄悄離開二條城,翌日晝八時抵達大坂城,二條城則由慶喜的心腹梅澤孫太郎坐鎮。
梅澤孫太郎與原市之進是慶喜成為將軍後最重要的心腹,他們兩人都出身水戶藩,弘化四(一八四七)年慶喜過繼為一橋家養子時奉齊昭之命前往一橋家成為其家臣。原市之進於安政二(一八四九)年進入藩校弘道館就讀,接受會澤正志齋、藤田東湖兩大當代水戶學龍頭的薰陶,成績優異的原被任命為弘道館舍長,在會澤、藤田的推薦下於安政六年轉往幕府官學校昌平坂學問所深造。
慶喜於文久二年七月六日被任命為將軍後見職時,兩人被延攬為慶喜的側近,此時慶喜的智囊是一橋家的家老並、旗本出身的平岡圓四郎。慶喜之所以由攘夷轉向公武一合,有一說是受到平岡巧妙操控(實際上並非如此),因此在水戶藩士看來,平岡成為蠱惑慶喜的佞臣,他的下場也就不難想像了。元治元(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水戶藩士江幡貞七郎(廣光)、林忠五郎埋伏在京都町奉行所與力長屋(都市中下層民眾居住的大雜院)旁暗殺平岡,享年四十三歲。江幡、林二人得手後,旋即為傾巢而出的町奉行所與力殺害。
平岡死後,梅澤和原成為慶喜的左右手而受重用,較為年長的梅澤被慶喜任命為大坂警備而駐守大坂城。慶應二年底慶喜就任將軍後任命兩人為目付,正式從一橋家臣躍升為幕臣。慶喜任用有弘道館、昌平坂學問所資歷的原市之進取代平岡圓四郎,成為慶喜的新智囊主導慶應改革,此舉讓原步上平岡的後塵。慶應三年八月十四日原市之進在京都板倉老中首座宅邸門前遭到同樣前來拜訪的幕臣鈴木豐次郎、依田雄太郎二人殺害,整起事件幾乎與三年前平岡遇刺如出一轍。平岡和原遇刺後,慶喜身邊再也沒有能上得了檯面的智囊。雖同樣隨侍在慶喜身旁超過二十年,但是梅澤充其量只有忠誠而已。在面臨據守二條城與薩長軍作戰與否的抉擇時,梅澤只能忠實接受慶喜下達坐鎮大坂城約束按捺不住的會津及桑名藩兵的指令而不能為主子出謀劃策。
如果平岡或原還在的話,必能為我分析利害得失,但是梅澤的話就……
慶喜一生大概再也沒有比這時候更渴望身邊有個可以出謀劃策的智囊吧!
慶喜決心開戰
撤出二條城的慶喜一行人,在十三日夕七時進入大坂城。慶喜略作休息後於翌日先接見立場親近幕府的法國公使侯許(Michel Jules Marie Léon Roches),前作已有提過法皇拿破崙三世除了借貸鉅款給幕府外,更派出軍事顧問團為幕府訓練近代陸軍。英國公使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無意間聽聞此消息後,認為大英帝國的駐日使節理應享有日本外交的優先權,豈能落在法國之後?12月14日是格列高里曆1868年1月8日,兵庫已經正式開港,巴夏禮緊急喚來使館通譯官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冒著傾盆大雨趕赴大坂城。有讀過筆者前作的讀者,對這兩位公使以及薩道義想必並不陌生。
由於巴夏禮臨時亂入,慶喜因而擱置原先和侯許的話題,改向侯許和巴夏禮述說五日前「王政復古大號令」的經過。由於慶喜並未參與政變過程,很多細節他無法清楚交代,只能敘述已知的部分。慶喜說完之後,詢問兩位公使該如何因應接下來的政局。兩位公使先是講了漂亮的場面話安慰慶喜,接著話鋒一轉,質疑慶喜撤出京都、轉進大坂的目的。如前文所述,兵庫在格列高里曆1868年1月1日(日本曆為慶應三年十二月七日)正式開港,慶喜卻在開港後數日離開京都,來到大坂,是否有以政治力阻撓兵庫開港的意圖呢?
在薩道義看來,慶喜並未表現出絲毫想要重新奪回權力的樣子(從之後的歷史看來,薩道義的觀察有誤),對於巴夏禮和侯許的質疑,慶喜也無心回覆,彷彿因為一連串的打擊而顯得意興闌珊。
最後,慶喜說道自己疲累至極,結束與兩位公使的會面。不過慶喜又補充道,將擇日再做安排會面。據薩道義《明治維新親歷記》一書記載,慶喜離去後,外國奉行遞交書面告知:
慶喜已辭去將軍職(十月廿四日主動向朝廷辭職),今後請以「上樣」稱之。
十二月十六日晝八時半,慶喜在大坂城御白書院正式接見英、法、美、荷、義大利、普魯士六國公使,親自說明自大政奉還以來兩個月間日本政局的演變。過程中痛訴岩倉具視和薩摩主導數名諸侯、帶兵突入禁門的凶暴舉動,重申王政復古是場不合法的政變。慶喜的演說打動六國公使,一致表態支持幕府,對慶喜而言,無疑是場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只要能獲得列強支持,不當將軍又有何妨!
當然,打動六國公使內心的並非這場演說,而是慶喜允諾會繼續承認以往簽下的修好通商條約並保障各國在先前取得的種種利益,這才是六國公使最為關心的事項。
慶喜決定乘勝追擊。翌十七日,慶喜以自己的名義命右筆起草為己辯護的《舉正退奸之表》,於十八日命大目付戶川伊豆守安愛帶往京都遞交新政府總裁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戶川找上若年寄兼山陵奉行(文久二年新成立的幕府職務,負責山陵的管理和修補,雖說是幕府的職務卻必須由朝廷任命及同意)戶田大和守忠至在當日晚上將此表上呈給總裁有栖川宮熾仁親王過目。
慶喜在《舉正退奸之表》強烈要求清君側(指岩倉具視、正親町三條實愛、中御門經之等人),以激烈的語氣提到「要向幼少的天子進諫,火速聚集天下列藩的眾議,以舉正退奸」。並以「薩賊」稱呼薩摩藩。此外,慶喜在該表還提到會命諸藩率兵前來大坂以防萬一,等於在暗示有栖川宮若不自行清君側,他將率領諸藩藩兵攻入京都親自執行。
諸藩是否願意聽從慶喜之命率兵前去大坂不得而知,不過板倉老中首座早在十一日寫信給江戶的稻葉美濃守正邦、松平周防守康直、小笠原壹岐守長行、松平縫殿頭乘謨四位老中,提到近期之內將會發生戰事,要求盡快調派步兵四大隊、騎兵兩小隊、大砲兩門以及軍艦數艘至大坂灣。
板倉老中首座一定有向慶喜提及此事,慶喜撤出京都想來應與板倉老中首座此舉不無關係,可見慶喜撤出京都並非全然無謀之舉,他在下令撤出京都的同時應該已有一段時間後將與討幕派作戰的念頭,六國公使的表態支持加強他與討幕派開戰的決心。